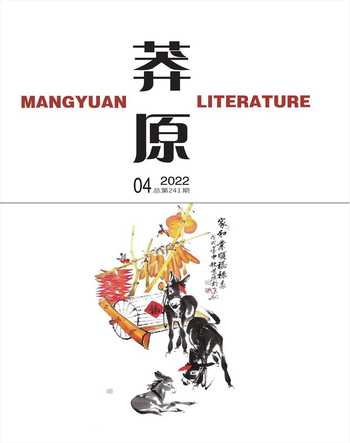宛在水中央
王业芬
大河弯弯
记事起,这条河就一直在村边。大河从西到南环绕大半个村庄,岁岁年年守在村外,看着村子兴衰荣辱,陪着村民喜怒哀乐。它在地图上叫什么名字,村里似乎没人关注,都亲切地称之为“河湾”。
河湾,一听就不是什么正经八百的名字,跟农家孩子唤小三、小四、小石头一样,随心随意,但听起来熟悉,叫起来亲热。
河湾,特指流过我们村的这一段,别的地方叫什么,咱村人不太清楚,也没有那闲工夫去了解清楚。河湾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似乎也没有人关心过。只知道河水自北往南流淌,一直往南,流向很远很远的地方,很远有多远,村里大概没人真正搞明白。似乎也没打算搞明白,因为搞不搞明白,河都在这里,供人浆洗灌溉、喂马饮牛、捕鱼捞虾……年复一年,河湾周流不息,人们也习以为常了,认为它本来就是这个模样,甚至把它当成村庄的一部分。
村里老人说,河湾原本不是河,是一条沟。有一年大旱,河水干涸,河床裸露,仅剩沟底几个深潭有些存水。河湾就这样露出了原形,有经验的老人看出了端倪,说它原本就是一条沟,上游的水顺地势而下,长期冲刷,形成了一条河道。一个小沟变成汤汤大河,这得多少年啊!
河湾从村庄西北面一直环绕到东南面,村庄就成了一座半岛。除了正北和东北能从陆路通行,其他地方出村要渡河。
村庄在西河湾和南河湾之间。西河湾是一片沙质土,存不住水,只能种植旱作物,更适合种花生,不仅果实多,个头还大。另有一个好处,就是起花生容易——抓住花生秧子,稍稍一提就连根拔起,轻轻一抖,沙土脱落,便露出一蓬蓬白生生饱鼓鼓的花生。母亲常说,她种了大半辈子地,最舍不得的还是这片沙土地。
不知何时,那些吸沙的人看上了这片沙土地。这里的沙,细密纯净,能卖大价钱。一拨拨人开着水泥船过来吸沙,河岸崩塌了,河水不停地往田地推进,沙船也跟着推进,直接将尖利的牙齿伸向种着庄稼的沙田。母亲喘着大气赶来,站在沙船前面横竖不让吸沙子。这哪里是吸沙,简直是在啃母亲的肉啊。吸沙人可不管什么血啊肉的,不给吸沙就是挡他们财路,直接跳下船,把我母亲推倒在地。母亲倒在沙水坑里,衣裤湿透,挣扎着刚爬起来,又被一脚踹倒。这一脚狠啊,母亲膝盖受了伤,躺了三个月,最终落下腿疾。此后,她失去了劳动能力,也永远失去了那块沙土地。
南河湾的地,水旱皆宜,水稻种得,花生种得,小麦种得,油菜也种得。但这里落差很大,紧邻河湾最低处那一片地,潮气大,且容易受涝,只能种一季水稻,其他时节只能轮空。轮空时,这片空地上荒草茂盛,是我们放牛、放鹅的好去处,也是我们嬉戏玩乐的好场所——比如哪个植物果实能吃,哪个植物根茎清甜,哪种野菜鹅喜欢,哪种水草牛喜欢;再比如用草叶拦住一只蚂蚁,迫使它改变前进方向,看它还能不能找到蚁穴,或者用茅草挑翻蚂蟥来个肚皮朝天,让它好好享受一场日光浴,看它是不是真的能曬死;又比如,捉住一条水蛇,拎起尾巴,使劲抖动,看看它嘴里会不会吐出蛇信子……总之,小花小草、蚂蚱蝴蝶等任何一样可见之物,都令乡下孩子兴味盎然、快活无比。
碧水盈盈
多数情况下,河湾是一幅温润恬静的水墨画:河水清清,波光粼粼,鱼翔浅底,鸥鹭凌空。
夏日的河湾则另有一番景象,奔放而热烈,好似一幅色彩斑斓的油画。清晨,一缕晨曦投射到河面,轻声召唤淘米洗衣的妇人和担水的汉子;鹅鸭们也出来凑热闹,咕嘎咕嘎一路欢歌冲进大河,撒着欢儿展示各种泳姿。这些声响惊醒了河湾的梦,一河的水立时活泛起来了,跳跃起点点金光,翻腾起朵朵水花。
傍晚,是河湾最热闹的时刻。老的、少的,男的、女的,统统拥到河里,河湾简直成了一个天然大浴场。河湾把阳光揣进怀里,一天下来,装得满满当当,河水恰似温泉,泡在里面温润舒适,脚底的沙土暖融融的,软绵绵的,仿佛还带着阳光的气息。谁能抵得住这种诱惑呢?人们成群结队来到浅滩,尽情荡涤一天的辛劳。他们有的静置水中,双目微闭,物我两忘;有的纵身一跃,箭一般射向河心;有的默不作声,一遍遍揉搓自己的身体;小孩子们聚集水边,抄起河水,你朝我身上洒,我朝你脸上泼,嘻嘻哈哈,你追我打,溅起一阵阵水花。
敢到河里洗澡的,基本上都会划水。“划水”就是游泳,村里小到六七岁的孩童,大到七八十岁的老人,个个都是划水高手。生在水边要是不会划水,就像生在草原不会骑马一样,差不多会被人笑掉大牙。
河湾有东、西两块河滩。西河滩是大姑娘和小媳妇们的浴场,偶尔也有老妇人来凑热闹;东河滩是老少爷们和孩童的天地。这是规则,没有人制定,没有人安排,就这样约定俗成了,世世代代从没有人打破。
东河滩曾是我的荣耀地,也是我的伤心地。在这里我被冠以划水高手,在这里我也有过屈辱和愤懑。六岁那年,姐姐带我到河里洗澡。她的伙伴们听说我是旱鸭子,合计着要教训我,故意把我拖到深水区撂下不管。我在水里“啊呜啊呜”直扑腾,灌了好几口水,直往水里沉。我感到自己正在沉入无底深渊,人影越来越缥缈,人声越来越遥远。茫然失措之际,忽地伸来一只手抓起我,拽到岸边。我惊魂未定,坐在沙地上大口喘粗气,呆呆看着有说有笑的人们,只觉得那是另外一个世界,压根不属于我。
那日以后,我暗暗发誓一定要学会划水。接连几个晚上,都趴在水边的一块巨石上勤学苦练,甩开两腿在水里不停扑打。渐渐地,水中有一股力量将我托起,又好像有一块垫子把身体支撑,我猛地从石头上松开双手,居然在河里游起来了。接着,一连扎了好几个猛子,来到深水区,在人堆里游来荡去,活脱脱如一条撒欢的泥鳅。
夏日的午后,屋外骄阳似火,屋内酷热难耐。屋外的树上知了无休止地聒噪,屋内的顽童已无心睡觉,焦急等待着大人睡着,好溜到河里去洗澡。待大人们微微发出鼾声,便蹑手蹑脚爬起来,踩着猫步溜出门去。院子里接应的小伙伴们,相互使个眼色,一溜烟冲到河边,纵身跃入水中。一群水猫子在水里或仰游,或蛙蹬,或扎猛子,玩得极尽性情。估摸着时间也差不多了,才忽地想起大人的叮嘱,纷纷爬上岸,站在太阳底下烤晒,等不到衣服五六成干,就匆忙跑回家,悄悄卧倒在凉榻上,假意睡去……
并非每次都这么好运气,有时,精明的大人会追到河边把我们逮个正着。他们手拿树枝,怒目圆瞪,粗声呼喝。调皮鬼们个个战战兢兢上岸,刚才还是活蹦乱跳的鲜鱼活虾,转眼变成缩头缩足的咸干鱼。“咸干鱼”们有的被揪耳朵,有的被打手心,有的被打屁股。那新鲜的枝条满含水分,瓷实得很,抽打在屁股上,很快鼓起一条条红梗子,蚯蚓似的,爬满两个光溜溜的屁股蛋子。当晚睡觉决不能仰着,屁股不能碰床板啊,一不小心碰着,火辣辣的滋味直往心里钻!几天后,屁股上的“蚯蚓”渐渐消退,我们又心心念念谋划着下河洗澡。这是典型的好了伤疤忘了疼。
河湾对于顽童们的诱惑远不止于此。他们时常潜伏岸边一动不动,眼睛滴溜溜瞅着水底的小鱼。有一种叫作“沙钻”的鱼喜欢伏在河底的沙地上,是个超级伪装者,披着一身淡淡沙土黄的外衣,很难被发现。可惜清澈的河水出卖了它,一旦在沙地上伏定,便被孩童们盯上,迅捷伸手去捉。但“沙钻”更迅捷,在孩童伸手入水的一刹那,便闪电般遁逃无踪。孩童们只得悻悻地撒开空有黄沙的手掌,拍手顿足好一番懊恼。
好在淘米、洗菜时,能捕获馋嘴的白鲹。将米菜篮子潜入水中,不一会儿,便有成群的白鲹游来,啄食米糠和菜屑。这时,心仿佛要从嗓子眼蹦出来,有按捺不住的,手忙脚乱猛地往上提篮子,惊得白鲹四散逃窜;总有沉住气的,等白鲹聚到米篮中央,再悄悄将篮子提出水面。出水后,这些贪吃的家伙才发现上了当,拼命蹦跶,却为时已晚。白亮亮的肉鲹在篮子里跳跃,银光闪闪,少则四五条,多则八九条。伴随着白鲹的跳跃,孩童们发出一阵阵欢呼。
河蚌也是孩童们喜欢的捕捞对象。这不需要什么技术,只沿着河边浅滩一路捡拾,即能盆满钵满。河蚌们总是一副懒散样儿,在温热的河水里泡澡,许是觉得乏味了,会把头潜进潮湿的沙土里,漫无目的画着弧线。却不知,这些线条恰恰成了孩童寻到它们的标记。没有鱼虾,河蚌也算得上一道河鲜。记忆中,母亲做的河蚌肉,味极鲜美,放了葱姜蒜红烧,或是放入米面做成糊糊,都让人食之难忘。
河湾是水族的天堂,鱼虾蟹鳖纷纷来此安家。村里人还曾捕获过珍贵的鳜鱼和白鳝。农闲时节,一些村民划着小船到河里捕鱼,归来总是鱼虾满仓。也有外地人赶着鱼鹰来捕鱼,他们驾着连体小船,鱼鹰列队船舷,如同即将出征的猛士。渔人一声令下,它们迅疾俯冲入水,逮到鱼,便游上船,挺着胸脯交给主人。此时,鱼卡在鱼鹰喉咙里,进退不得,它们脖颈下部早被一根细绳系住,无法吞咽,只得求助主人取出。鱼到嘴里却吃不着,鱼鹰只好拍拍翅膀,抖抖羽毛,一个纵身又跃入水中。
收工时,渔人总不忘拿出一堆小鱼犒赏这些战功卓著的猛士,偶尔也会毫不吝啬抛出数条大鱼让鱼鹰过把瘾。
逃水荒
河湾也有翻脸的时候。
连日大雨过后,河水汹涌而下,原来的碧水清波,变成滚滚浊浪,一路翻滚着往前冲。不时有树枝、门板、牲畜随着洪流冲过来。站在高处看过去,让人头晕目眩。临近河湾的几户人家大门紧闭,人畜早已撤离,任由河水越过门槛,肆无忌惮地登堂入室。其他人家虽未进水,但也没有人在户外活动。
有一年夏天雨水特别多,一直传闻上游的马湖坝要炸坝子泄洪。一旦马湖坝溃堤,咱们村将被洪水淹没。大人们个个心中惶惶,不知如何是好;孩子们只惦记着雨什么时候停,能出去玩个痛快,连日的阴雨,早把他们憋坏了。没想到,等来的不是天晴,而是炸坝子的消息。
那天夜里我睡得正酣,突然被姐姐从梦中拽起,不由分说拖着我就朝屋外跑。我迷迷糊糊地问姐姐这是怎么回事,姐姐喘着粗气,说要炸坝子了,赶紧跑。啊?要炸坝子!我惊得张大了嘴巴。父亲从后面追上来,催促我和姐姐快些赶路。当时,我并不知道什么叫“泄洪”,只晓得不跑,就会被大水吞掉。我吓得打了一个激灵,鞋掉了也顾不上捡,就跟在大人后面跑。
村北的路上全是逃水荒的人,男女老少,拖家带口,在烂泥中跌跌撞撞往前奔。这是一支溃不成军的队伍,像吃了败仗的残兵败将。队伍中孩子的哭闹声,大人的呼喊声,赶牲口的吆喝声,和着哗哗的雨声,嘈杂一片。
马灯在暴虐的风雨中玩命挣扎,想给队伍带来一小片光明,却忍不住左摇右晃,一副力不从心的狼狈相。雨幕劈头盖脸压过来,手电光也明暗不定,若隐若现,仿佛昏花的老眼。此时,所有的光亮都成了一种心理安慰,成为一种往前奔突的信号,人们盯着那一点微弱的光亮,凭着感觉在雨夜里艰难跋涉。忽然,队伍一阵骚乱——村西头的四丫掉坑里了。几个壮汉一齐上阵,连拖带拽把她拉了上来。四丫头泥水裹身,脚上的胶鞋早已不知去向。也顾不得这些了,就这么赤着脚逃吧。不一会儿,谁家的大肥猪掉沟里了,人群中又是一阵骚乱,一声吆喝,壮汉们一齐出手,喊着号子,三下五除二就将笨重的大家伙抬了上来。
风雨不驻,脚步不歇,我们一路往北狂奔。村北大坝,正是马湖坝的下游蓄水区,马湖坝一破,水就会汹涌而下,淹没村庄。我们拼命奔跑,生怕在半路上遇到翻滚的洪流。一旦洪流阻断道路,我们将无路可退。我们沿着大坝狂奔,也不知跑了多久,我随父母来到了地势较高的邻村堂舅家。
在堂舅家躲水荒那两天,雨小了许多。两天后仍没传来炸坝的消息,父亲说水情有缓解,政府应该不会炸坝了。我们后来才知道,炸坝并非官方消息,只是雨水太大的一种可能,消息还没得到确认,不知怎的就传开了,闹得周边百姓人心惶惶。
渡口悠悠
河湾有两个渡口,一个在村子南头,另一个在村子北面。南渡口设在水面收敛、水流平缓处,北渡口设在两岸的低洼处。
南渡口紧邻村子,但渡过河就是全椒地界。人们常开玩笑说河湾就是楚河汉界,河这边是肥东县,河那边是全椒县。虽然这么说,两边的百姓却从来没有楚汉相争,他们往来密切,非亲即故。
因为离村庄近,南渡口是村里孩子经常光顾之地。顽童们经常趁摆渡人不在,上船肆无忌惮玩耍。所谓的船,实际上是一个圆形的大木盆,最多能坐七八个人;多数情况下,一次也就坐一两个人。
调皮鬼们学着大人的样子摆渡。我们这里摆渡与边城茶峒那边相像,不用船桨,也不用竹篙,靠的是一根绳子。绳子横在河面上方约一米处,两头分别拴在两岸的杆子上。摆渡人站在盆里,双手交替用力拉绳子,船就借势往前走。
大人个子高,绳子大约齐平胸口,拉起来正好顺手。顽童们需高举双手才能够到绳子,拉起来自然十分费力。偏有些捣蛋的家伙,根本不老老实实在盆里待着,东一个西一个分散开,你狠跺几脚,他猛晃几下,更有甚者,跳起来重重地砸下去,把木盆撞得剧烈摇晃。这时候,木盆就像喝醉了酒的老汉,一会儿往东倒,一会儿朝西歪,一会儿冲南倾,一会儿向北斜。玩得过火了,直接把木盆弄个底朝天。水猫子们这时候心最齐,合力把木盆翻过来,继续摆渡。
北渡口历史久远,人们都称“老码头”,是交通要道,南来北往,载人运货,有两人专门摆渡,顽童们根本别想沾边。“老码头”两岸,一面是土坡,一面是石坡。码頭在坡下,呈两山夹一凹的格局,与凤凰古城的渡口有几分相似。然而这里只有爷爷,少了翠翠和黄狗。
摆渡的两个“爷爷”是河西沙河村的村民,大家称他们“拉盆的”。“拉盆的”专人不专职,他们轮流值班,拉盆种田两不误。但他们很敬业,白天夜里都值班。河东岸码头高坡的向阳处,有一间茅草屋,是他们的值班室,里面一张单人床、一口水缸、一方小凳子,应该还有一个煤炉子吧,渡河的人渴了,会去讨一口凉茶。我也去过,并不喝茶,直接从水缸里舀一瓢水,咕咚咕咚一气灌下去。
老渡口的木盆比南渡口的块头大,盆身黝黑,盆沿磨得溜光锃亮,看上去很有些年头了。别看它又老又黑,却是“老码头”的当家“宝贝”,一次能盛得下十二三个人。大木盆深约两尺,盛满人后,盆身沉下大半,倘若有几个重量级的,水面就会紧贴着盆沿。夏天渡河,将手搭在盆沿外边,水浪从指缝间穿梭而过,凉丝丝滑溜溜的,会生出一种鱼在水中游的畅爽,真是说不出的惬意。
外地人坐木盆过河,望着白茫茫的水面,总在心里担忧,怕水漫到盆里,怕掉到河中,便不敢站立,干脆一屁股瘫在木盆里。本地人有胆大的,直接坐到盆沿上,方寸之地,居然稳如磐石。盆靠岸,胆小的像给狼撵了一般,迫不及待跳下木盆,岸上站定,才长长舒一口气;那些盆沿上坐的,则不慌不忙站起来,抬脚跨上码头,气定神闲地迈开步子赶路。
我和村里几个在沙河小学读书的小伙伴,过河总不老实,一心想坐在盆沿儿上。可“拉盆的”怕我们落水,坚决不让。我们只好紧靠盆边蹲下,歪着身子,抄起河水,互相往对方身上洒。“拉盆的”往往回头看看我们,笑而不言。
我一直想自己拉盆过一次河,没想到机会真的来了。一个雨天,“拉盆的”不在,眼看要迟到了,怎么办?我当机立断,决定自己拉盆带两个小同学过河。或许是老天考验我,雨越下越大,到了河心又刮起大风。风雨交加,我把伞夹在脖子下,双手紧紧握住上方的绳索,一点一点往前移动。毕竟才十来岁,个子矮,力气又小,只觉得手掌被绳子磨得生疼。忽地吹来一阵大风,险些把伞刮飞。我一个趔趄,绳子从手中滑了出去。没有绳子,木盆就像一只无头苍蝇在河里打转转。眼看就要随着水流漂走,我吓出一身冷汗,一边命令两个小同学不要动,一边迅速甩出伞把,用伞柄的弯钩钩住了绳子。我不敢再打伞,冒雨摆渡到对岸。太险了,如果没有抓到绳子,木盆被水流冲向下游,后果不堪设想……
每年秋季,是老渡口最繁忙的时候,那只黑黢黢的大木盆,把一袋袋鼓鼓囊囊的稻谷,一趟一趟运到河西岸的小高粮站,河东六个村的粮食从这里过河,源源不断进入公家粮仓。码头上刚运走一拨挑粮的农人,又过来一拨。一担担粮食按照先来后到的次序,整齐排列在码头的平地上,农人们一手扶扁担,一手抓下草帽不停扇风。河西岸,交完粮的人们陆续返回,将空挑子往地上一放,坐在各自的扁担上,谈收成、拉家常。
送粮的人越来越多,队伍排到了码头高坡上。“拉盆的”的不急也不躁,一趟顶多运三担粮食三个人,绝不允许多上一个人。木盆上有吃水的刻度,“拉盆的”必须保证盆沿超出水面二十厘米。因为运粮是大事,不能有半点闪失,人掉水里可以爬上来,粮食掉水里,谁赔得起啊?
“老码头”平安运送过无数粮食,也运送过无数的人。“拉盆的”始终牢记着一句古话——小心驶得万年船。
若干年后,一桥飞架东西,高峻阔直,各种机动车在桥上呼啸而过。完成历史使命的老渡口,兀自静处,成为桥上人眼中的风景。此时的“老码头”,更像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将人间岁月埋藏在深邃的眸子里,无语胜千言。
心愿与偶像
老一辈人说,河湾的水位高低与农家粮仓里谷堆的高低密切相关。水位太高,洪水泛滥,必有涝灾;水位过低,少水灌溉,必发旱荒;若水位恰恰齐平东沙滩与河岸的交接处,必是丰年。
村里的先辈们总想早些知道河湾水位,预测丰歉,就供了观世音菩萨。这尊观音菩萨木刻金身,约半人高,端坐莲花宝座,供奉在一处别院。村里人平时上香敬供,到了正月十五隆重地请出来,由几个壮汉抬着到河边去“踩水”。壮汉们走在前面,身后跟着村里的男女老少,长长的队伍一直排到村西头。每过一处,都有噼噼啪啪的爆竹一通脆响,表示万分欢迎。
“踩水”仪式在东沙滩举行。说是菩萨“踩水”,其实是一位得了菩萨神命的尊长代替菩萨“踩水”。他紧紧跟随,菩萨抬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菩萨“踩水”并不下到河里,只在沙滩上“踩”。菩萨在沙滩各处“走”动,踩到某地停下来,那位尊长就开口说话了——无非是水大水小的话,有时春水大,有时夏水大,有时秋水大,有时四季少水。随后接着“踩”,又“踩”了很久,他才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说出这句话时,锣鼓队就该出场了,咚咚咚,哐哐哐,敲锣打鼓地在前面引着观音菩萨,观看“踩水”仪式的人们跟随其后,浩浩荡荡在村里周游一圈,把佛光普照到各家各户后,菩萨才被送回去。
其实,菩萨“踩水”,预测水情恐怕只是虚名,正月里来好过年,大家热闹一番倒是真的。俗话说月半大似年,正月十五这天我们那里也吃元宵,但不说元宵节,而是称“小年”。既是年,总得热闹一番。这样一个偏远小村,没有城里火树银花不夜天的灯会,借着与农事密切相关的“踩水”,全村人集体欢庆一下,算是对春节的告别,对春耕即将到来的一种提示吧。老辈人说:“吃了月半饭,就把生活干。”这一天,家家户户一大早就准备一桌丰盛的饭菜,中午吃元宵,晚上则是炒饭,叫作“炒秧根”,预示着秧苗旺盛。
菩萨“踩水”仪式许多年前停办了,青壮年多数外出务工,村里只有稀稀拉拉的老人和孩子,无法再举办这样的大型活动。这应该是一种地方风俗,也是非物质文化吧!被遗弃了,感觉好可惜。不过,村外的两座小庙还在,沿河而建,一座在西岗头,一座在南湖冲。
走出村口大约二百米,就到了西河岸最高处。这里树丛茂密,一座人字顶小庙背树端坐,庙门正对着进出村子的路,门脸不大,香火很旺,香炉里的香灰堆积不下,泼洒到外面,淹没了香炉半个身子。这些香是敬供土地老爷的。庄稼人土中讨饭,地里淘金,对土地老爷发自内心地敬重。大年三十来土地庙上香、贴对子的,多是家主或长男。土地庙的对子年年都一个样:田中生白玉,土内出黄金。就像春节贴在牛角上的一定是:六畜兴旺;贴在门栓上的一定是:开门大发——这些是祖祖辈辈庄稼人恒久不变的心愿。土地庙上红红的对联一层压一层,远看好比披挂上艳丽的云霞。
南湖冲的小庙在伸向河湾的一个小洲上,离村庄很远,少说有几里地。小洲呈 “几”字形,凸出部分伸在水中,小庙坐落在“几”字头颈处的中心位置。
不知为什么,去南湖冲上香的人家不多。我奶奶是“观音会”的,每到年三十下午,奶奶总遣我去观音庙送香。南湖冲里一片阒寂,连个鸟影也不见,只我一个小小的身影走在冲里,恐惧从四面八方席卷过来,让人透不过气。我一路小跑,把香往小庙香炉里一插,拔腿就跑,也不知插上没插上,也不管火灭了还是没灭。我每次送香都慌里慌张,从没看清庙里的菩萨。奇怪得很,越是没看清,心里越惦记着菩萨长什么样儿。一次,借着双亲在小庙西边的花生地除草,我大着胆子凑到庙跟前,仔仔细细瞅了,才发现原来观音菩萨这么好看。这尊观音像比“踩水”观音小得多,没有金身,通体乳白,衣袂飘飘,欲舞欲飞,样子也煞是好看,乌发粉面,修眉细眼,眉间一点殷红,手持白玉净瓶,斜插一枝翠柳。这尊观音像,不知道和“踩水”那个观音是不是同一位,反正都从南海来的吧。
责任编辑 申广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