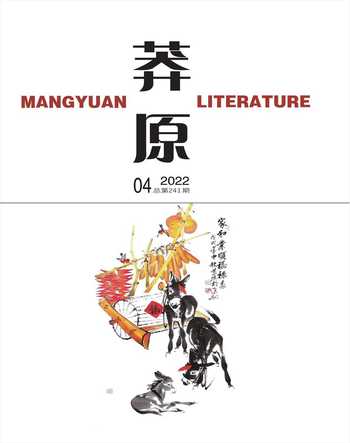喀什的天空(组诗)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
喀什的天空
遥望帕米尔高原
山的黄色涟漪朝天边袭去
吐曼河水满目羞涩
流向百年茶馆
浪花在茶壶里飞溅
岁月的残渣
依附在窝窝馕的后面
咸涩在舌尖打转
绕城一周的风倜傥无比
黄灿灿的无花果
催情的纹路
在叮当作响的铜器里发光
色满路旁野花盛开
三五成群的蜜蜂交头接耳
节庆时的艾提尕尔
纳格尔皮鼓在耳膜里作响
一个早熟的男孩
倚靠在门外的砖墙上
裤子总是多余的物件儿
高台民居里的小路
走不出岁月的流觞
光阴未必不回首
老街里的故事光怪陆离
往事可以随意倒流
无论何年何月
买买提的烤肉总也卖不完
无论何时何地
香妃的故乡香味扑鼻
喀什的天空
在白云里发酵
街头的剃头匠悄然隐没
剩余的抓饭
在倾斜的锅底打盹儿
时尚的古丽,假冒的香奈儿
如老街的路灯
古城的开门仪式后
人流开始涌动
老旧生活口味浓重
来一碗癫狂的冰酸乳
盛夏的天空总会清澈许多
百年茶馆
那一年秋
艾提尕尔院内的白杨
落尽的秋叶
给乌鸦筑巢腾出了空间
方言浓烈的风
刻薄地四处游荡
刮伤老店的一些门板
屋顶的茅厕
稳居高台之上的标配
与色满路上空的飞鸟遥相呼应
用于识别出路的条形砖
散发着麻烟的气味
毛拉的灰驴格外受宠
它们懂得优先交配
那时的袷袢条纹清晰
成为喀什葛尔的地标维度
晌午的阳光开始灼烧
让刚出炉的窝窝馕灿如骄阳
用于交流的各色绯闻
在茶客们的棉衣里莹莹出汗
散发酸楚的气味
随都塔尔琴声随意飘散
铜壶里的浓茶
等待糖果
萨玛瓦尔里的水已不能自拔
沸腾是另一种咆哮
络绎不绝的烤包子
叮当作响的铜匠
和尖酸入骨的玩笑
耀眼地挤进古宅二楼.
盘腿打坐更显稳当
香妃的话题比蜜还甜
寡妇的名字被唱成民歌
满堂的茶客
忍受彼此的基因扩散
看一眼都会怀孕的女人
浓眉是传情的道具
百余年来
繁衍未必只为喝茶
近千年的愚昧干粮
赤足之下的热土
打通剩余的血脉
四肢未必发达
头脑何曾简单
靠阳具完成所需的思考
丰乳肥臀像多情的牵牛花
四处攀岩
这些茶客
昨晚还在墙头做爱
茶碱和纳斯唇烟
用于消磨时光
还能让岁月延年益寿
深秋的云
随意飘在空中
比翻飞的鸽子还要悠闲
熙熙攘攘的人群
把勤劳租借给蚂蚁
从春忙到秋
不知蚁群的茶社又在哪里
叶尔羌河东岸
或许时空
就是流淌的水
朝深处流去
我看到天与地的缝隙里
一条清冷的河
拉开东与西的界线
流向一片原始的荒野
仿佛北非的遥远
蜿蜒北上的叶尔羌河
无声无息的波纹
排列成水的文字
記录荒芜
我站在夕阳的位置
遥望远古的刀郎从晨曦里走来
缓步走向他们的极乐
让古老的歌声在两岸生长
东岸的胡杨
仿佛一支穿越大漠的驼队
饮马叶河
头顶黑色皮帽的樵夫
拥挤在周日的巴扎
一群游走的菌类
在丛林密布的荒野
无根生长
无品的二弦古琴
空灵的琴声敲打天空
歌者席地而坐
含糊的歌词在口腔里流浪
足下的土质在齿间钙化
一层厚厚的硫磺
成为他们二次咀嚼的草料
东岸的辽阔
涌向克里雅的史书
汹涌的沙丘
成为斯文赫定的向导
蔑儿乞部落的营帐里
炉火渐渐熄灭
镰刀取代了弯刀
五颜六色的孩子
糖分在他们脸上开裂
游牧就此歇脚
苍天无界,大地无边
把围裙赠给女人
男人采花不亦乐乎
沉重的花帽四周
色与情同时绽放
眉飞色舞地挑逗
居无定所的心
在空旷的原野上漂泊
狂野的舞蹈
试图摆脱自身的苦涩
季风是两岸最出色的画师
它用河水泼墨
大漠生宣
丛林,随笔峰驰骋
南飞的大雁给写意题词
西部的天空
留下一枚落日的红印
遥远的村庄
风吹清寒
晨已退
遥望大漠长空,黄沙驰骋
一抹淡青脚步迟缓
塔克拉玛干是风的祖籍
三月巴扎回暖
驴车身形短小
碎步无痕,与驴同行者
走不出人的风采
倒也有一番生活情趣如美酒
堪无比
春来风绿
尘渐落
抚琴大地山河,春意盎然
一缕微风柔情似水
叶尔羌河涛声依旧缠绵
四月桃花笑春
农家炊烟缭绕
幸福无声,与风伴舞者
舞不出风的曼妙
殊不知山南塔河也几多春秋
地无双
杏花待嫁
蜂伴郎
飞过春色花香,山野遍绿
一组春诗惹人陶醉
准格尔大地也信马由缰
五月春潮滚滚
田间歌声如潮
乡村无界,与春争媚者
美不过春之烂漫
忘不了天山南北山河更锦绣
赞无言
树影如织
光飘落
岁月沧桑斑驳,大地奇美
一汪泪眼驰目遥望
疆北疆南辽阔视野茫茫
六月风光如画
山涧涛声旷古
瓜果留香,与水妩媚者
流不出波涛汹涌
抒不尽心中狂野举杯邀山川
醉无语
岁月远去
逝如烟
沧海人寰无际,草木春秋
两鬓风声谈笑古今
墙里墙外说不尽故乡情
今朝七月似火
树影婆娑无序
秋风渐近,与叶飘落者
飘不定四海为家
望不断夕阳如歌把酒空对月
归无期
责任编辑 李清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