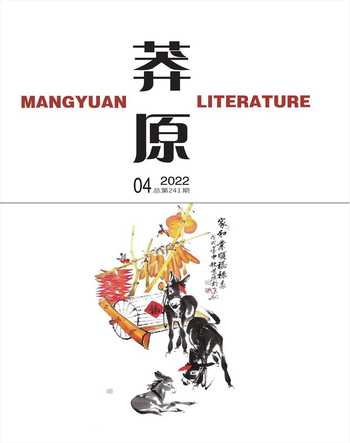伊犁河左岸
杨方
我回到伊犁河边的时候,一切都变样了,我也变样了。
伊犁河的河洲上以前拴着锡伯族人的鹿,散落着孤独吃草的马,现在落着几只蓑羽鹤,这种体积最小的鹤,有闪亮的蓝灰色羽毛。它们以前从没在伊犁河边出现过。
伊犁河下游新修了座可克达拉大桥。这座年轻的大桥闪闪发光,比伊犁河一桥和二桥都要长,也更雄伟,壮观。以前,伊犁河左岸的人到右岸,要跑到上游,从一桥或二桥过河,现在不用了,直接从可克达拉大桥过河,可以少走很多路。
伊犁河左岸是我的叫法,伊宁人把我说的左岸叫南岸,1954年,南岸的河南县改成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居住在这里的锡伯族人,长相和蒙古人有点像,骨骼粗大,颧骨凸起,但他们的眼睛和蒙古人不一样,蒙古人的眼睛里,是草原的开阔和高地的阳光;锡伯族人有的是林中的眼神,这可能与他们曾经生活的地域有关。锡伯族人不是伊犁土著,是两百多年前从东北的嫩江流域西迁到伊犁河谷的。嫩江流域的森林里奔跑着鹿和狍子,河中游鱼肥大,锡伯族人被称作打牲部落,祖传的生活方式是狩猎和打鱼。他们的眼睛里,闪烁着林中流水暗沉的光。伊犁河发源于海拔六千多米的汗腾格里峰,这条亚洲腹地的内陆河流经了雪山,高地,谷地和大片草原,一路敞亮,开阔,水声喧哗。锡伯族人从那样的一条河流边,来到这样的一条河流边,他们一直是生活在河流边的民族,始终与河流保持着亲密的关系。
我在伊犁河右岸出生,长大。十几岁之前,我从未去过伊犁河左岸。我只站在伊犁河右岸,朝左岸那片平坦开阔的土地眺望过,那片略微向西倾斜的大地上,生长着旺盛的庄稼和树木。各种走向的道路,仿佛也在向着远方生长。一切都充满了人世的朝气和烟火气。有一个黄昏,我看见河对岸的葵花地低垂着大片金黄的头颅,锡伯族人在落日旁升起细细的炊烟,接近地平线的地方,一排互有间距的树木,犹如大地弓起的脊椎骨。更远处,是背景般永恒存在的乌孙山,这座黑色山脉即便是在夏天也有着苍老雪白的峰顶。再一次,是春天快要到来的时候,结冰的伊犁河发出巨大的冰裂声,好像冰层下囚禁着一头猛兽,想要破冰而出。几个河对岸的人在冰上打陀螺,他们全然不理会闪电般四处延伸的裂缝,以及危险的冰块碎裂声。我听见旁边有个大爷,用富有经验的口气,十分肯定地断定这几个人是锡伯族人无疑。
这个黄昏,我坐在伊犁河右岸的大桥公园,看见河对岸开着烟雾般小花的灌木林里,走出一个人来,他来到河边,脱下衣裤,先是抡圆手臂前后甩动一番,然后扑通跳进河里,奋力地想从对岸游过来。我猜想这可能也是一个锡伯族人,在伊犁,大概只有锡伯族人才这么不惧怕伊犁河。哈萨克人是马背上的民族,四五岁的孩童,骑着高大的昭苏骏马,跟骑了个玩具马一样;维吾尔人是爬树高手,就算是七八十岁的老人,爬起果树来也敏捷得让人吃惊,他们能麻溜地爬到树尖尖上,摘星星一样摘下那个最红最大的果子。但无论是哈萨克人还是维吾尔人,大多不习水性。伊犁的汉人也不怎么习水性,这可能是地域环境造成的。新疆少河流,少湖泊,没有大江大海,更不像南方,明亮的小水塘星罗棋布。伊犁虽然气候远比南疆湿润,降水也多,被称作塞外江南,但地表上能见到水的地方不多。大地上浇果园浇麦地的水渠,平时是干的,只有需要浇灌的时候才会引进水。林则徐在伊犁的时候,修建的湟渠,是一条著名的灌溉渠,总长也不过三十多公里。这些大大小小的渠,只能算是流水的通道,不能算做河流。伊犁河可能是大多数伊犁人见过的最大的河。它的上游和中游,有大大小小1600多条冰川流先后汇入。其中主源特克斯河年径流量八十亿立方米,之后汇入的巩乃斯河年径流量二十多亿立方米,喀什河年径流量四十多亿立方米,三条大河,汇流成一条更大的大河,全伊犁的流水,几乎全都集中在了这条大河里。伊犁河谷的植物,动物,飞鸟,鱼类,虫类,包括牲口和人,全依赖这条河生存,繁衍。我从小对伊犁河充满畏惧,站在河边,腿会发抖。它的漩涡裹挟着一股危险的力量,它的喧哗大有淹没尘世的气势,它的水深不可测,它的宽在某一段宽得有些不着边际。它的下游与霍尔果斯河汇合后,流入哈萨克斯坦境内,最后注入遥远的巴尔喀什湖。每年冬天,都有天鹅从巴尔喀什湖飞到伊犁河边过冬,春天再飞回巴尔喀什湖。
这时节春天已经接近尾声,伊犁河里的天鹅已经飞走,远山上的残雪还没有消退到雪线上,从伊犁河左岸吹来的南风还带着寒意。在伊犁河边生活了二百多年的锡伯族人,深谙伊犁河的水性,照理,他们不会在不适宜的季节贸然下河。我推翻刚才的推测,觉得这个试图从河对岸游过来的人很有可能不是锡伯族人,而是一个刚从内地来的年轻人,他的人生还没有蹚过多少河,他不知道伊犁河的深浅,不知道伊犁河的水,源自汗腾格里峰千年积雪的融化,即便是在大地上流淌了几百公里,即便是在天气最热的大夏天,也依旧保持着冰川纪刺骨的冰冷。想游过这样一条大河,身上没有点北极熊的脂肪是不行的。果然,这个人还没有游到河中间,就退了回去。上岸后他瑟缩着跑进灌木林,等他再次从灌木林里出来的时候,身后拖着一张橡皮筏子。看样子他打算划着橡皮筏子到河这边来。伊犁河上已经很多年没有船只出现,记忆里,我几乎没有看见伊犁河上有船出现过。大桥公园修建后,有段时间,伊犁河边出现过汽艇和游船。白天很少有人光顾,汽艇和游船基本上处于“野渡无人舟自横”的状态。到了傍晚,游客多起来,汽艇和游船开始出动,汽艇溅起老高的水花,游船在河面上逆流而上或顺流而下,观光伊犁河两岸的风景。伊犁河两岸其实没什么风景可以观光,吸引人们的是伊犁河上的落日。伊犁河有比任何一条河流都令人惊讶的落日,每一个黄昏,落日都耀眼得像是星球坠毁,人们几乎可以用肉眼看见从球体里蔓延出来的火焰。这些火焰落进伊犁河里,河面被大面积点燃,金光一片。乘坐汽艇的人,乘风破浪地迎着金光驶去,像是驶入了世界末日。等他们返回,每个人都像燃烧过一样,皮肤上带着灰烬的颜色。
我没有坐过伊犁河上的汽艇和游船。伊犁河上的游船是电动的,突突突地响,感觉跟开水上拖拉机一样。汽艇更是大声,这些机器的声音破坏了伊犁河干净明朗的流水声,伊宁人对这些水上漂浮物没有太大的热情,新鲜过去后,就弃之河边。我在冬天回来的时候,看见伊犁河边被冻住的游船,像撞击冰山后遇难的船只。
河对岸这个想要游过伊犁河,失败之后又试图划橡皮筏子过河的人,吸引了伊犁河右岸很多人驻足观望。划船过河的场景,应该多年未见,或者说,大部分人从来未见。1959年以前,伊犁河上没有桥,伊犁河左岸的人到右岸来,都是这样划着船过河的。伊犁河流到伊宁市附近的时候,河面宽的地方,有一公里多。水流算不上湍急,但平静的河面下险象环生,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伊犁河左岸的锡伯族人划着船,在河面上轻巧地来去,像神仙踩着一片云。这在骑马的民族和果树上的民族看来,实在有点神奇。他们猜测,肯定是锡伯族人的萨满对伊犁河念了咒,施了法,要不,伊犁河里十几公斤重的大头鱼,尾巴一甩,就能把小船弄翻,更别说那些魔鬼眼睛一样的漩涡了。过河的锡伯族人全然不把伊犁河当一回事,可能他们觉得有了萨满的巫术,自己就算是坐着核桃壳或者鸡蛋壳之类的东西,也能平安到达对岸。
划橡皮筏子的人也许是想证实一下,锡伯族人过河的方式不是传说。伊犁河上曾经船只往来也不是传说。我在亚历山大手风琴博物馆里看见过几张伊犁的老照片,老照片中伊犁河边的老渡口停泊着船只,是一些普通的木船,看上去不是很大。曾经,伊犁河左岸的粮食就是靠这些船运到伊犁河右岸来的,伊犁河左岸的马牛羊,也是靠这些船运到伊犁河右岸来的。傍晚,锡伯族人在汉人街的大巴扎上卖掉了粮食和牲口,怀揣钱币和酒,划船返回伊犁河左岸。青灰的暮色尾随着锡伯族人的小船,从伊犁河水中爬上岸,将伊犁河左岸吞没下去。伊犁河左岸的暮色,总是比右岸来得早,也比右岸更浓。左岸的土地上,仿佛生长着一种叫悲壮的东西。这种悲壮不是一种情绪,而是一种气质,它从伊犁河左岸黑色的山脉上长出来,从笔直的树木上长出来,从小麦的麦芒长出来,从茂盛的野草里长出来,从一匹马的蹄声里长出来,从一头公牛的牛角尖里长出来,从男人的胡子里长出来,从一个女人高耸的胸部长出来。
这种悲壮,在伊犁河左岸已经生长了两百多年。两百多年前,确切的年份应该是公元1764年,清政府下令将锡伯族人西迁到伊犁河谷,一边屯田,一边戍边。乾隆皇帝之所以选中锡伯族,是因他们忠诚,精骑射,且擅农耕。这支优秀的部落民族,在这一年的农历四月十八,从他们生活的嫩江流域出发,跋涉五千多公里,历时一年零三个月,终于到达伊犁河左岸。出发的时候,有四千多人,其中官兵一千零八十一名,家眷三千多名。路途中有人死去,也有婴儿出生,到达时,人数是三千多。他们集中定居在伊犁河左岸。伊犁河左岸没有森林可以狩猎,但是伊犁河里鱼类丰富,青黄鱼,伊犁鲈,大头鱼,白鱼,狗鱼。锡伯族人在伊犁河上捕鱼,在伊犁河左岸耕种。精通农耕的锡伯族人,仿佛拥有萨满的巫术,他们没用几年时间,就将伊犁河左岸长满野草的土地变成了胡麻地和小麦地。锡伯族语察布查尔是粮仓的意思,粮仓是对伊犁河左岸的赞美,也是对锡伯族人的赞美。
本来清政府允诺,六十年后锡伯族人可以回迁。六十年过去,朝还是清朝,但皇帝已不是当年下旨的那个皇帝了。1824年,是清宣宗道光四年,年轻的新皇帝完全忘了有回迁这一回事。锡伯族人永远留在了伊犁河左岸。二百五十八年后的今天,在嫩江流域的锡伯族文化几近消失的时候,远在伊犁河左岸的这一支,从最初的三千多人,繁衍到近三万人。他们在自己的领地里过着祖传的生活,努力保持着祖辈遗留下来的习俗,烤锡伯族大饼,吃烧茄子烧辣子,用伊犁河边一种叫椒蒿的野草,来炖伊犁河里的大头鱼。椒蒿有一种特殊的无法描述的味道,因为太过浓烈,喜欢的人很喜欢,不喜欢的人会难以接受。这种草在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地生长,不知道伊犁河边的椒蒿是不是锡伯族人西迁的时候从东北带来的。伊犁河边,可以看见整片生长的椒蒿,叶片细长,开淡紫色的小花。这种桔梗目的菊科植物,在风吹草动的伊犁河边,也生长出一种悲壮的气质。
锡伯族人不仅用椒蒿炖鱼,还用椒蒿做凉拌菜,用椒蒿炒土豆丝,炒肉片,甚至在汤面片子里也放一把椒蒿,就像是放香菜一样。以前汉人街的巴扎上,卖鱼的锡伯族人也卖椒蒿,五六月卖椒蒿的嫩尖,冬天卖晒干的椒蒿叶子,一小把几块钱。伊犁河的鱼,在巴扎上像羊肉牛肉一样摆在案子上,用刀剁着卖。鱼肥大如猪,没人能一口气买走一整条鱼,只能这样剁成段卖。我小时候去大巴扎,看见剁下来的鱼头,足有猪头那么大,一个一个,目瞪口呆地摆放在巴扎上,鲜有人问津。本地游牧民族喜食牛羊肉,他们对有刺又有鳞的鱼不感兴趣,嫌吃起来麻烦,烹调也麻烦,远不如大块的肉来得痛快。卖鱼的基本上都是锡伯族人,也有俄罗斯人和汉人。买鱼的也基本上是这些人。后来巴扎上再看不见这么大的伊犁河大头鱼,市场上卖的伊犁河大头鱼,只有两三公斤重,都是养殖的,而不是来自伊犁河。有一年回伊宁,姐姐请我吃鱼,说是伊犁河里捕捞上来的大头鱼,十几公斤重,朋友送了她一小段。一小段鱼,就烧了满满一大盆子。这几年,伊犁河里这么大的大头鱼已经是稀罕物了,想到这个,吃鱼的时候,也有了种悲壮感。
打算划橡皮筏子过河的人扛着橡皮筏子往河边走的身影也让人觉得有点悲壮,落日照得他皮肤闪闪发光,银色的橡皮筏子也在闪闪发光,他像是扛着一个金属的飞行器,他更像一个史无前例的冒险者。春天伊犁河里的水流速有点急,橡皮筏子下河后還没有划出多远,就被激流冲向了下游,然后在那片耀眼的金光中,很快不见了踪影。感觉橡皮筏子是被那片金光吸走的。伊犁河右岸的人们“歪——歪”地叹气,摇头,表示遗憾。伊宁人叹气发出的声音不是“唉”,是很大声的“歪”,而且要连说两个“歪”,两个“歪”之间还要拖很长的音,越是遗憾,两个“歪”之间的音就越拖得长。橡皮筏子消失后,人们大声地“歪”着,但是,没人为橡皮筏子担心。伊宁人相信,伊犁河的水会把所有掉进河里的东西,都冲回到岸边来。伊宁有段时间,流传着一个抖音视频,有个失恋的小伙,想跳伊犁河自杀,跳了几次,最后都被水冲回到岸边。小伙趴在岸边捶胸顿足,哀叹想要在伊犁河里淹死自己,实在是太难了。
我走过伊犁河大桥,打算去看看划橡皮筏子的人是否被水冲回了岸边。我其实是想知道他到底是不是锡伯族人。他划橡皮筏子的举动让我再次改变猜测,我觉得他应该是个锡伯族人才对。这个战斗民族,从来不畏惧什么。他们的女人都能骑马射箭,当年在邻国人的一场偷袭中,伊犁河左岸的女人们在没有男人在场的情况下,像男人一样冲杀出去,击退了敌人。上高中的时候,我们班有个女生是锡伯族人,投铅球投标枪可以投到操场外边去,一个过背摔能把男生摔出脑震荡。我们一直以为她和我们一样是汉族人,直到高考,我们才知道她是锡伯族。。她后来考上了伊犁体校,当了一名体育老师。这个女同学到现在奔跑起来还像一匹马,头发带风,脚下卷起尘土,像马蹄踏过大地。
我走过的伊犁河大桥,和伊犁河二桥、可克达拉大桥相比,算得上是伊犁河上的老桥了。1959年的时候,人们在伊犁河的旧渡口上修建起第一座桥。这座木桥在当时是两岸唯一的通道,马车,驴车从桥上跑过,卡车和拖拉机从桥上开过,转场的羊群也队伍庞大地从桥上经过。木桥使用了十六年,1975年拆除的时候,桥面已经被马蹄驴蹄羊蹄踩出了一个一个的大窟窿,桥板也肋骨一样断了好多根。人从桥上走过,不小心会掉下一只脚去。重修后的伊犁河大桥长三百多米。当我走过这三百多米,站在伊犁河左岸的时候,发现不管是谁,双脚一旦踏上伊犁河左岸,就会被伊犁河左岸的悲壮所感染。我看见伊犁河左岸的土地上,落日散淡地照着万物,大地有原始部落般的宁静,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停顿住了。然后,时间开始倒流,伊犁河一起倒流,在散淡日照中回到二百五十八年前。那一年,锡伯族人从一条河边来到另一条河边,他们看见伊犁河左岸草木丛生,狐狸拖着火焰一样的尾巴从深草中跑过,宽宽的伊犁河中,游鱼肥大如猪,从时光中浮游而来,又浮游而去。
责任编辑 李清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