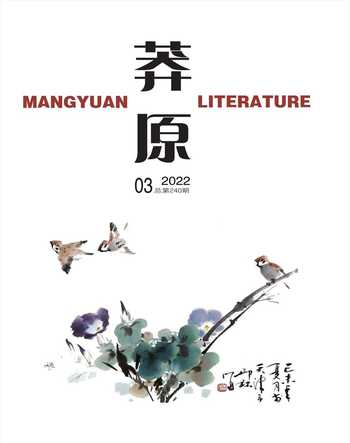纸魂灵
刘国欣
坐在车上极目远眺,会看见很多小镇,就像盲肠的一部分,火车在大地的肚腹深处穿行。她想起那个小镇,不由自主感觉到心脏突然颤动。
一路盘旋着往山上去,山坡这边那边弯弯曲曲,不同的村庄,零零落落的房子,阳面阴面,一个又一个。她喜欢这样,像在梦里飘着不知往哪里去。陌生的人,几乎不可能再次进入的车厢,沿途倒退的风景。她知道不该如此,但好几年了,总是这样的感觉,过着不知是谁的生活,所以有空就出逃。对于拥有的一切,应该怀有美好的感激:体面的工作,还有一套房子被赠予,同事们也都算得上热心,重要的是没有孩子需半夜起来喂食,上班无非就是一周去几个小时……按理说,一切都很好了,然而空气太干燥,她怀念湿热的南方,那些茂密的灌木丛,以及矮树上小小的鸟巢,还有一些随处溜达的小动物。在北方工作,总让她觉得缺失了什么东西,女娲炼石补天,也补不了的缺憾,人生中总有一些无可奈何。好处在于大雪封山,哪里也去不了,一整个冬天,仿佛冬眠,长日无事,就在打盹处排练梦境。
现在,冰雪在融化,大地解冻了,疫情放松了,身体也可以放飞了。南方应该已经是春天,春有春花,还有春水,必须走一走,必须看一看,生命需要喘息,要活过来。
目光所及是窗外远远近近的风景,以及偶然得来的一本书,封面是灰底黑字,半截子画在书封的下方,一截白墙掩映着层叠的木头房子,墙头杏花探出,楼上有一年轻妇人在望,楼下有一老妇踽踽而行。
二月里,收到快递送来的这套书,上下两册的《金瓶梅》,齐鲁书社1991年版。翻开纸张泛黄的书本,涌起了一种陈旧的激情。出门时想着带本什么书,扫眼而过,仿佛一种心应,那套书呼喊着让她带上它,于是就带上了。厚厚的书,占了四分之一的拖拉箱,然而并不拥挤,因为早就养成了极简的习惯,一切空空,所以完全有的是地方。
读书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是最不亏本的事情。这是寄书的人在一次采访里提到的。访谈发在一张报纸上,配着他背靠一墙书的照片,在四堵墙的书房里,到处放满了书。大多有点文化的人都这样,书是最好的门面装潢,占有书本就像占有了知识,他们会获得奇特的满足感。
老师们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她总想着行万里路,而不是读万卷书。苦行者有自己的悲哀和快活。
已经说了,《金瓶梅》是偶然来的,就像漂流瓶;寄书人也是偶然从网络世界漂流而来。他在一个海边的城市,海鸟群飞,碧空万里,看一眼就爱上了。因为爱着他的海,所以近乎想去爱上一个男人。他说送礼物,就要了这套他展示在桌面上的《金瓶梅》。
从出版日期可以推断,他是读过了的。可是纸张干净,除了有些微微泛黄,没有任何脏污的痕迹,当然没有签名,没有购书时间,没有恶俗的红章子。就这样把它放着,时间久了,说不定自己也会忘记来处。这样的好处在于,目光所及的一本书充满了书本之外的故事和念想。她习惯于这样,一本书引出一个故事或一个人。不会有其他人知道,只是自己的草蛇灰线。问一个人拿钱是俗气的,也太劳心,钱可以自己赚,一个人活着并不需要太多钱。那么,只是书——也可以说是输,就像水过留痕雁过留声。她喜欢零落的感觉,喜欢自己是失败的,被抛弃了。生命在叹息,而叹息如同一种祈祷,不必被听见,也不必被看见,最终会在下落中浮起,反求诸己。在下者有在下者的骄傲,她习惯于此。只是书,不需要留住哪个人;只是输,不必要留住哪段情。是生活教会她如何做减法的。减法,把自己减成一段枯柴,最后化为一堆灰烬,那还需要更多的时间。书可以随看随弃,天一阁也不过就一把火。人生最后的归宿,也在土与火之间,灰烬的上升与下落……
有很多书的人是贪婪的,她怕自己也形成那样的习惯;而且书太重,占太多的地方,她不喜欢,总是随意就弃置了。长年不断到处搬迁,太多和过重的东西是一种牵绊,她无师自通地实践着向空而行的艺术。那些有着实体重量的纸质书,不管有没有按序列被摆在书架上,都会制造一种恐怖——会不会忽然掉下来,砸在头上?另外,防火防水防霉防蛀也是大事。那些一本又一本垒着的书,用虫蚁的眼光看,是一座又一座楼;在大众眼里,也可以说是一座又一座标有作者的坟茔,它们被人收进房间,骨灰盒一样束之高阁,久不问津。如果逢着搬迁,有的会被重新上架;有的,擱置在某个角落,终至于下落不明,不再会被想起,就如被人忘记的一座座坟墓,最后又化为了纸浆,摊平成了大地,进行新的轮回。
少年时代,黄昏时分,每当躺在炕上或者坐在门槛上看书时,祖母就会对她说:“快把书放下,有辱斯文啊……”祖母对纸张充满敬畏,觉得看书就要端端正正规规矩矩,而不是随意坐着躺着就可以。祖母还有一个习惯,每次当她获了奖,会赶快将那奖状收起来,怕别人看见她的名字,说三道四,怕家人不小心烧了奖状,毁了她的名字,仿佛会伤及她的真身。
她一直认为祖母那种说辞是蒙昧无知,是山间乡野村妇的见识。可是她很奇怪为什么自己却暗暗支持这种见识,尽量不在任何地方随意地写下名字,当然包括照片,能不留下就不留,能删除就删除。多年之后,她为了赚点稿费在报刊上写起了文章,却不喜欢别人寄给她样报样刊,因为想到很多报刊会化成灰烬,而上面有她的名字,像她自己也被火化了一样……即使她的第一本书出版,也还对是否署上名字心有余悸,觉得书会被很多人读到,就难免流长蜚短,而“众人的嘴有毒”——这是祖母的原话。随着年岁的增长,她逐渐明白那山野老妇的祖母虽不识字,但智慧过人,她早就谙熟了纸张的危险,书本的恐惧,被命名的可怕……
每一句,每一段,每一篇,每一本书,都是一种哀悼。当她每次看到有人声情并茂地读着悼文,当她在一张张有质感的纸上看着一句句话,她就有这感觉——亡者阴魂不去。
很多人,他们留下的藏书都不知道哪里去了。一部分可能进了图书馆(很多图书馆的书也总向外流),一部分被扔掉了,还有一部分呢?她不知道每一本书的命运,但文字则四四方方,被钉死在它们有形无形的格子里,是封闭而不是飞翔。她爱着文字,也爱着书,却总想着如何释放它们。不去占有,也许就没有抛弃……
阳历二月的一天早上,她收到这个藏着《金瓶梅》的包裹,里面居然没有短笺,也没有夹着书签,扉页上更没有温润优美的话。三年前,从已经分手的恋人处,拿得一本《世说新语》,新版的书籍,装帧精美,里面居然有书签,签字上还有手写的话:最是你眉眼一弯……重要的是,后面有单字的签名。和那个人分手后,细细想这些,才发现这种拐弯抹角的隐喻无处不在,不发一语却言犹在耳。虽然那本书在翻完之后还回去了,可那余留的感觉还在,仿佛一种警示。
她对已分手的恋人的房间不甚了了,却总是会进行想象——房间里放着哪些书,书架是怎样摆列的,冰箱里又存放着哪些食物。她记得那段时光。那时候租了房子住在他家对面的楼上,每天考虑着要不要对他的生活进行监控,而实际监视已经开始,她脑海里随时想去不远的一条满是户外用品的商店购置望远镜。他晾晒在顶楼那猪肝红的床单,曾经像一面旗帜高高飞扬。那是一面胜利的沾满液体的旗帜,无论是眼泪还是体液,最后终于让她望而却步……
她和他第一次的见面,是一次户外活动的巧遇。在分手后的日子里,靠着推算知道他早有预谋,趁着那种活动之便,谈过一场又一场的闪电恋情,以此满足自己的虚荣,满足自己对“文明”的攫取。说出事实令人耻辱,但因爱贪婪的那个人又何其无辜?
三年是一段漫长的岁月。这三年,她离开他所在的那个城市,又离开了她被抛弃时所在的那个城市,便是她现在的城市,他也曾经踏足——一切都被污染过了。她的伤心在时间和空间里藏着,所有一切都在提醒她曾经经历过怎样的悲伤。
她对寄她《金瓶梅》的这个人几乎一无所知,唯一动心的就是他拍来的那片海。两个人借着网络像老朋友叙旧一样,她在微信里告诉他搬城市搬房子的不便,不愿意购书的尴尬,当然,亦毫无保留地暴露了她的孤陋寡闻。她对那座海边的城市一无所知,脑海里的仅有的一点认知也仅限于高中地理课上看地图的那点模糊记忆。前次失恋之后,她一个人在大年夜买了飞往一个远岛的机票,如期飘落那里。当时曾迫切希望飞机能落在大海上,孤叶断雁一般飘零。那样悲壮的想象在事后看来毫不值得,可当时就那么想。每一个被爱情放弃的人都是可悲的,她在被弃的命运里远走他乡,也是一种自我放弃。这样的可悲怎么可以继续活着承受?
那南方海滩给予了她蓝天的广阔,海水的清碧。一日又一日,她沿着那座岛屿的堤岸盘桓徘徊,忘记了是什么东西让她忽然想开了,不要死,不要跳海。也许是一望无际的海,也许是倔强的浪,也或者,仅仅是渔人们在各个码头打捞起来的各种海中生物,让她感觉到她不能死,还有风景没看够……这世间万物让她惶惑不安,也让她充满好奇,它们带给她的激情并不比她的恋人给她的少,甚至,更多。
她的恋人以他虚构的一场疾病,以及一封又一封放弃之后又追索的邮件,在抛弃里向她索要爱情。其实只是成年男人谙熟的一场世故的游戏,因为他不动声色地保持了他的生活,就连那场他打动她告诉她死亡随时可能袭来的疾病,也被事实证明是一场虚妄。一千多个日子过去了,他仍然健康地活着。如果为了证明他的话是真的,他就已经被死亡带走,然而实际上,她更希望他活着,以此证明一个谎言。
他炫耀过他的书房,炫耀那些他所进入的大大小小的书店,炫耀一些音乐和电影,以及认识的或死掉的人,但她并不能准确地了解他的阅读习惯。他也有一些书,以至她看他的东西,总不由自主落入别人书里的情节中,因为句子相仿情节相仿。也许这也是坍塌的原因,他从来没有给出她渴望的崇拜。
在文字里,他行礼如仪,一字一句地进行平庸的叙事。他对文学有隔世的抱负,说穿了和很多人的政治抱负一样,漫天的声誉可以隔着死亡远远传来。他一直追求那种文明世界里充斥着成功、名望和仪式的优渥生活。总而言之,城市生活,也就是符号化的生活,他得到了,早就可以体面地出入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光鲜位置,却还希望在死后亦能永垂不朽。她只是一个可能坍塌的借口和灾难,因此必须删除。他有严格的书写秩序,执行起来井然有序,他需要靠文字一笔一画把自己的境况抬起来,就像那个掉入垃圾坑的驴子一样,视一切为营养。她和他搜集的那些书本一样,也是可以摄取的垫在脚下抬高自身的一部分,是可以被榨取然后抛弃的材料,馊掉的水果,爬满虫卵的花朵……如大多成功人士一样,在镜头里,他生活在极端化的秩序里,随时朝著鲜花盛开的地方行走,等待高光时刻的到来。他深谙如何出镜,随时等待登上舞台享受掌声。他教她拍照要侧拍,要斜视不是正视,不要故意表现出对镜头的兴趣,显得像个乡巴佬。事实上,就原生的地理位置划分,他是个乡巴佬,而她是个村巴佬,一个乡巴佬对一个村巴佬进行造作的登台教育,他将这称之为艺术。也确实,城市生活几十年,他早就学会了如何拿腔作调装腔作势,如何看起来有模有样做一个所谓“文化界名流”。
这一切,都像是一场有计有谋的策划。他还不忘许给她一个她并不需要的诺言,六十岁写传记,她是其中的一个章节,好像浑然忘记了在此之前他神神秘秘地对她进行算命师的宣讲:我只能活到四十八岁。之后,就是对她进行突袭的宣言——为她,他得了要命的疾病,随时可能死掉,根本就等不到四十八岁。
说这一切的时候,他浑身散发着一股悲戚,同时却因为她赋予的爱情,泛出几缕崇高。尽管现在这一切已经无从说起,但是想起这些,她仍然能在耻辱之上感到柔情无限。甜蜜岁月不虚,她曾与他紧紧依偎,还记得贴着他额头的手掌仿佛找到了它觉得舒适的位置,记得他吃到好东西会动物一样舔舐嘴唇,记得他突然像走了很远的路精疲力竭地向她索要力量。
开始,人们会很爱很爱一个人,接着呢,会在分开之后陷入失望或绝望。他也许死了,也许活着,这不重要。然后呢?再开始一段恋爱,或者,一切都累了,并不是因为还爱着那个人,也已经没有了怨恨,只是不想再有任何作为。包括看见那个人的样子,也已经没有任何感觉,会思念,不期待,就像拿个橡皮擦,一点一点抹除。
书写是一种修改还是涂抹?
现代社会,文学的苍穹熠熠闪光,到处是闪耀的明星,凭借帮闲与帮官的合谋,报纸杂志和网络,时时准备制造文学天才,文学奖项如一地鸡毛在飞舞,他还在跃跃欲试,说着《金瓶梅》,渴望《世说新语》的风流,写着想要隔世流传的文章……
她在南下的列车上,翻开手边这部很多年前出版的《金瓶梅》,涌起一种陈腐的激情,仿佛看见了很多纸上的魂灵,挣扎着,一步步走完自己的光阴。他如果活着,也会在文字里展开对她的编排。今人会和前人一样,一把灰烬的热情在时光的隧道里等着,在此之前,守更熬夜,图谋瀑布般的掌声,人也会是战利品,爱也会是战利品。
列车穿越山洞,一截截漆黑的隧道,昏暗的灯光,到了哪里?又会到哪里去呢?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她的名字被污染了,亵渎过了,无法再干净了。然而,世界缺乏唯一性,何为我?不区分就无亵渎。这是很好的安慰。被情欲围困的好几年岁月,像一把火燃到了尽头,所爱之人以他虚拟的疾病和真实的消失,在漫长时光里草长莺飞,很好地叙述了何为苦集灭道。
一个又一个隧道,一片又一片山坡,一堆又一堆墓地,一个又一个小镇,远远的村落,是纪实也是写意,其实只是想说出,最后的最后,她去他从小长大的小镇,坐在山坡上,猜测他由哪一个山头长出,曾经也是坐着这样的车,翻着不知是哪本书,向她走来,又离她而去。
猝不及防,生活就是如此,无常即有常。她一直暗暗猜测,如今他埋在哪座山上?因为已经是三年三年又三年,世事不断变迁,给他如何的安排?在文字的尽头,是草青草黄又一年,还是得其所愿?而她自己呢,一次心不在焉的出行,最后在山村的尽头消失。
一篇近乎精神失常的文字,断魂无依,不知在哪个醉酒的夜晚被发出。经年之后,陌生编辑从收藏夹里无意捻出,也许是好奇故事的真实,加了微信问是散文还是小说,说可以改改。
浏览旧踪迹,陈腐泛酸的一段过往,居然还剩一抹徒劳的哀思,深悔当时的怨艾。火车在前进,驶入夜晚,河汉流星,仍然在此情深处。
责任编辑 丁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