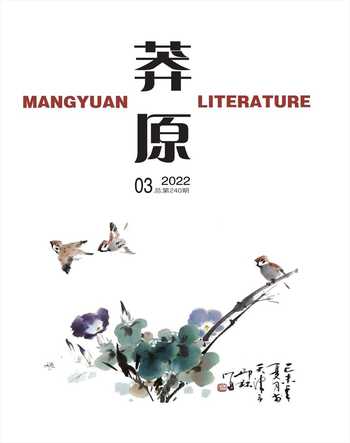阁楼里的锈镰刀
吕刚要
老大媳妇说晚饭要吃蒜薹炒肉,张幸福到超市转一圈儿,手里就多了半斤后腿肉、两个手工蒸馍、一把蒜薹、一瓶酱油。空调咝咝吐着冷气。刚进门时一身粘汗,不大一会儿就全都落了。
已经到了五月尽头。他突然想起,往年这时节,该操心割麦的事了。不晓得眼下麦子成熟了没有,今年的长势如何……同土地打了半辈子交道,他怎么也想不到,有一天他会和土地、庄稼形同陌路。
前些年,没有大型机械,每年麦收都得一镰一镰地割,一杈一杈地挑,一车一车地拉,一场一场地碾,一锨一锨地扬。中午的太阳能把人烤焦,一季麦打下来,哪个人都得脱一层皮、掉几斤肉。那时他年轻,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可一到麦天也两腿打战。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四五张嘴等着他叼食呢,再害怕,也得硬着头皮往前冲。有时他想,要是成了城里人,那不和进了天堂差不多?当然只是想想,刨粪的鸡,怎么飞得上城里的高枝?
1
今年春节,俩儿子儿媳都回来了,大包小包,让张幸福心花怒放。一家人团团圆圆吃了年饭,儿子们对老两口说要商量个事。坐下一听,原来是让老两口各自到一个儿子家里帮忙照看孩子。看看哥儿俩笃定的样儿,肯定提前说好了。张幸福看看老伴,老伴也拿眼看他,都没说话。说啥呢?老大超学两口子打了几年工,没黑没夜地干,在县城首付了一套房,又匆匆装修了,让儿子龙飞到县城读书,说是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俩人要还房贷,又要供儿子上学,不容易。老二超进大学毕业留在省城,妻子媛媛在省城一所学校教书,两口都是工薪族,眼下的目标就是攒钱在省城买房。但省城房价高得吓死人,哪那么容易?年前,又添了女儿蔓芸,日子突然紧张得喘不过气来。
兄弟俩说了他们的打算,又对老两口做了分配:张幸福去老大家照顾孙子龙飞,老伴去老二家照看孙女蔓芸——一切似乎都合情合理。可有谁设身处地为他们老两口想过?辛苦操劳大半辈子,老了老了,却变成牛郎织女了。再说,张幸福才五十三岁,还心气汹汹地想要去建筑队再挣几年钱呢,没承想兄弟俩兜头给了他一棍。唉,都是为儿为女,农村父母不就这点用处吗?又想,年轻时不就想进天堂吗?真的要进来了,咋没想象中的喜悦呢?
过罢年,老二超进就急慌慌地收拾东西回省城。租着房住,偏偏掏十几万买辆车显摆,张幸福打心眼里不以为然。老伴坐到车上,玻璃摇下来,一双眼毛绒绒地看他,到底没说出一句话。
老大超学没车,叫好友二毛把车开来,拉张幸福一起进城。出村四五里地了,张幸福忽然大呼小叫地让停车。超学问,咋了爸?张幸福说,我得回家一趟。
车掉头开回家,张幸福打开院门,又开了屋门,转一圈儿,却只拿了一张破镰刀。这张镰是张幸福使顺手的,一天能放倒二亩多麦子。镰把盘得滑溜溜、油亮亮,看见它,心里就透出一股子说不出的亲切。这些年有了大型收割机,镰刀再没了用武之地,放得久了,已挂上一层红锈。
2
張幸福在超学家的任务是接送孙子龙飞上学、放学,做好一日三餐,照顾好孙子的生活,监督好他的学习。看着稀松平常的事,做起来却不顺利。就说做饭吧,张幸福几乎没摸过勺子,即便最简单的稀饭,一大一小爷孙俩,添几碗水,和多少面糊,熬多长时间……都让他挠头。
第一次烧稀饭,给锅里添了水才发现问题。摸出手机,想打电话问问老伴,可老伴没手机,超进家又没装座机,只能打给老二超进。拨号时,又想到正是上班时间,不能让儿子抱着手机跑七八里路回家给他妈接听吧?而孙子放学是要吃上饭的。没办法,只能赶鸭子上架了。开火,和面糊;面糊有些稠,那就兑水;又稀了,再兑面;先还能搅,熬了一会儿,成凉粉了,一坨一坨粘锅上,一股子焦煳味,只好倒进了垃圾篓。
接到孙子,张幸福故意诱惑他,龙飞,想喝稀饭还是饮料?龙飞有点丧气,说,当然想喝饮料,可你给买吗?买!张幸福爽快地说。真的?龙飞想抱住爷爷的老脸亲一口。平日里儿媳是不许龙飞喝饮料的,说饮料里都是防腐剂、色素、香精,喝了对孩子发育不利。张幸福想执行儿媳的命令,可没有稀饭,拿什么给孙子喝?总不能让孙子给他妈说爷爷连稀饭都没给他烧吧?
龙飞喝可乐的时候,张幸福拨通了老二超进的手机,说赶紧让你妈听电话。
几百里外的省城,老伴腰里系着围裙,正把一盘菜往饭桌上端。老二媳妇坐在客厅,孙女拱她怀里,小嘴儿巴咂巴咂吃得正香。超进说,爸的电话。老伴说,稀饭还在火上冒泡哩,啥事啊……一边让超进去厨房看着锅,一边接过手机进了卧室。要关门时,一扭头,看见老二媳妇的目光在背上贴着呢。老二媳妇话不多,目光却经常飞来飞去。
张幸福电话又臭又长,先汇报了第一顿晚餐烧糊的事。老伴眼圈泛红,心里发酸,让那一双糙手来捉锅铲,真难为他了。张幸福又请教她稀饭怎么烧,菜如何炒,说要拿支笔记下来。红缨背后贴着眼光呢,说,写啥?我说慢点,你用心记就行了。先说熬稀饭,一二三的;又说炒菜——可刚到热锅、倒油,菜还没下锅呢,厨房就出状况了。先是超进一声惊叫,接着是锅盖哐哐啷啷一阵响,原来是锅里的稀饭溢出来了。老伴慌慌地说,不说了,正做饭呢,又叮嘱,以后少打电话……她怕老二媳妇说她人在这儿,心在那儿。唉,做人难啊,老二媳妇的每句话都得品着点儿味。
挂断电话,张幸福心里怏怏的。正在这时,微信嘀嘀嘀叫起来,点开看了,是老大媳妇的视频:爸,龙飞在吗?把手机给他。张幸福把手机递给孙子,马上就后悔了——龙飞抱着可乐,正喝得高兴呢。老大媳妇声音一下子变了,龙飞,怎么又喝可乐?龙飞说,爷爷让喝的。老大媳妇说,爷爷没烧稀饭吗?龙飞说,没有。老大媳妇说,把手机给爷爷……爸,咋没给龙飞烧稀饭啊?声音不大,却震耳朵。张幸福真想抽自己几个耳光,仿佛作弊被抓了现形的学生,结结巴巴地说,明,明,明天吧……一定给他熬……
当然,只喝稀饭是不够的,孙子还需要各种营养。这不,老大媳妇早上出门时就交代了,晚饭要给龙飞做蒜薹炒肉。张幸福在超市晃悠了好大一阵儿,终于打算结账撤离了。虽然外面太阳依旧火辣,终究不能总待在这里。
3
收银台前有几个人在排队结账。张幸福前边是一个女的,烫着头,大红裙子松松垮垮的,乍一看挺鲜艳,仔细一瞅,俗气,没品位。女人零零碎碎拿着一大堆东西,收银员一样一样扫码计价。终于嘀一声付完款,轮到张幸福了。他说,算账。那女人已经走出两步了,又回过头来——俩人都乐了。女人说,张幸福,真的是你?我说声音咋恁耳熟呢!女人叫麦花,一个村的。张幸福说,麦花,你咋也在这儿?
偌大的县城,一张张都是陌生面孔,难得遇个熟人,自有一种说不出的亲近。张幸福看着眼前的麦花,脑子里闪出的却是老伴的模样。四个多月没见老伴了,电话也打得稀少,时不时就会想她。以前一出去大半年,咋就没想过呢?这人真他妈奇怪。
结完账出来,张幸福和麦花说说笑笑的,坐在树凉阴下。仔细问了才知道,麦花也在县城照看孙子,俩人不一个小区,但离得不远。张幸福奇怪,几个月接送学生,咋一次也没遇上呢?
对村里事情,麦花门儿清。谁谁在广州,谁谁在上海;谁谁一天多少钱,比谁谁多,比谁谁少;谁谁砸断了腿,才出去一个月就回来了,床上躺着呢;谁谁得了肺癌,郑州做的手术,花了七八万,人却难救回来;谁谁出去打工了,老婆和村主任不清不楚;谁谁的媳妇过年没回来,听说在外面又找了一个,正闹离婚呢……
这些女人翻舌头的家长里短,以前张幸福是不屑一顾的,现在却听得津津有味。张幸福进城四个多月,都没有今天下午说的话多。他一肚子话,不知找谁说,门挨门,户对户,却都是铜墙铁壁;城里人似乎全是哑巴,在楼道或电梯间遇到,最多只点个头,或者眼光一飞,装作不认识。张幸福只能躲家里看电视,可所有电视剧全他妈假声假气的,没半点意思。
令张幸福不解的是,麦花和自己一样住城里,咋对村里事知道这么清楚呢?麦花说,都是群里说的,里面热闹着呢。张幸福说,啥群?麦花说,老家群。张幸福说,把我也拉进去吧。张幸福点开二维码,麦花拿手机扫了,叮一声,过去了。麦花说,生锈的镰刀,你咋叫这么个名字?张幸福说,飘香的麦穗,还是你名字好听。麦花说,哈,你是镰刀我是麦穗,难不成你要收割我呀?张幸福笑着说,没看都生锈了吗?割不动喽。
这就想起了麦收的事。地虽然租出去不种了,和那麦田也再无瓜葛,可依旧想得心慌。心里寻思,这两天无论如何得骑上电动车,到麦田里转一圈儿。
加完好友,张幸福又问麦花男人在哪里干活儿。麦花说,村里十几个人去了石家庄,说是做外墙保温。这活儿张幸福以前也干过,甚至年前还有人找过他,说工钱涨了,一天能拿到二百八,问他愿不愿去。他动过心,可是还没有想好去不去,就被儿子媳妇一根绳拴到了县城。张幸福挺留恋打工生活的,一帮大男人,年饭一毕,就背上行李出了门。一天下来腰酸背疼,可心里干净,啥事不用想。一顿饭撂炸弹似的,每个人都能消灭它五六个大蒸馍。晚上躺那里,荤话浑话俏皮话,看谁的话多。说着说着,就是一片呼噜声。早晨起来,又是一派生龙活虎。关键是打工养家。这些年在外打工,张幸福盖了两座平房,供出了一个大学生,还娶了两房儿媳妇。要不是打工,钱从哪儿来?
遇见麦花,张幸福算捞着救命稻草了,生活中的诸多难题也都迎刃而解了。比如:稀饭熬到什么成色算熟了;面条煮多久才不烂;炒菜撒多少盐,放多少油,啥菜和啥菜搭配着好吃……麦花几乎要手把手教他了。俩人嘀嘀咕咕的,说得热闹。特别是麦花,总是嘻嘻哈哈笑,很开心。
4
回到家里,四下静得吓人。张幸福放下东西,到沙发上坐着,屁股下却似扎着一把葛针;那就起来走走,橐橐的脚步声又变成了铁锤,扑通扑通往心上砸。走了几圈,他干脆顺着楼梯,一阶一阶爬上阁楼,把自己撂倒在了床上。张幸福清楚,是自己心不静。正是雄赳赳气昂昂的年纪,以为往北京上海至少还能跑上七八年。妥了,儿子儿媳一句话,所有雄心壮志全变成一个臭屁,嘟一声,放没了。他这个掂着瓦刀爬高下低的人,现在操起锅铲钻厨房了,这不是逼着张飞绣花吗?
超学当初买这套房时,图的是顶楼便宜,还送阁楼。装修时,阁楼也吊了顶,罩上白,勉强搁进一张床。张幸福住进儿子家以后,很自觉地选择在这里安营扎寨。超学本来不愿意他住这里,说阁楼又矮又窄,像鼻窟窿,咋住人?可老大媳妇没说话。除了阁楼,家里还剩两间卧室,她和超学一间,龙飞很自然地霸占另一间,让张幸福住哪儿?所以,超学也就识趣地把嘴闭上了。
张幸福躺床上还是不行,鼻息呼呼的,像两列隆隆行驶的火车;团两个纸蛋把耳朵眼堵上,耳根清净了,可是屋顶、四面墙壁都变成坏笑的脸,向他挤压过来,连空气都有了沉甸甸的重量。张幸福憋闷得要死,他必须赶紧透口气。阁楼有扇小窗子,推开,新鲜空气扑面而来,他大口大口呼吸着,半天才缓过劲来。阁楼在二十七层,往下一望,密密麻麻的行人小得像蚂蚁,张幸福感觉自己离他们那么遥远,每个人都忙忙碌碌的,只有他像被吊在了半空。
张幸福不愿再待在这监牢似的家里了,他要走出去,专往人多的地方走。可是,所有人都忙,没一个人理他。他就往一处建筑工地走去。远远听到叮哐叮哐的敲打声,心里一股热气开始涌动。他想到工地上去,再掂掂久違的瓦刀,摸摸棘手的青砖,同一帮汉子开开粗俗的玩笑。可是,工地有把门儿的,非施工人员,一律不准入内。张幸福有点沮丧,只好原道返回。路上,他在一个小摊上买了一盒烟,回到小区,门卫室里有俩穿制服的保安,年龄比他还大,皱纹沟沟壑壑爬满一脸。他揭开锡封,给每人递上一支,三个人一边抽烟,一边天南海北地聊。聊得正投机,门口汽车嘀嘀嘀长鸣起来,保安脸一白,赶紧对他说,老弟,快走吧,被经理发现,够我们喝一壶的……
唉,和谁才能痛痛快快说上一席话呢!
同张幸福最亲的算是金毛嘟嘟了。它是自来熟,一开门,就扑过来,绕着脚跑。起初,张幸福瞧不上它,只会摇头摆尾,耍萌卖乖。张幸福想找龙飞说话,可孙子总有写不完的作业,偶尔得空,还要摆弄变形金刚,打游戏,刷小视频,没空搭理爷爷。退而求其次,张幸福只能和嘟嘟说话。无聊得紧了,他就汪汪叫两声,嘟嘟回应他,也汪汪叫两声。
5
这天,张幸福又跟麦花碰上了。他同麦花讲起了做饭闹的一些笑话,把麦花逗得前仰后合,眼泪都出来了,一伸手,轻轻在他身上捶了一拳。张幸福正陪着她傻笑,心一颤悠,捶过的地方就麻酥酥的,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感受荡漾开来。张幸福脸上热热的,笑就假了。又想想麦花说的闲话,谁家男人在外打工,女人在家跟谁好了;谁家女人外出,有了外遇……如此一想,他心里又不舒服了,自己在县城,老伴在省城,她会不会也背着他养汉?这问题他可不愿深思。
树影子不晓得啥时拉得老长,一道阳光斜斜打在俩人身上,晃得眼睛有些睁不开。张幸福慌慌地跳起来,瞧,咱俩只顾说话,眨眼到了接学生时间,晚饭还没做呢。麦花神色也有些紧张。要走了,她又让张幸福站住,见他屁股上有两蛋子灰土,上前拿手使劲拍,终于拍干净了。张幸福看见麦花屁股上也沾着灰土,可他没敢替她拍,只说,土,你也拍拍吧。麦花自己拍了两下,脚步匆匆地走了。他看着麦花的背影,仿佛突然有一根绳子,牢牢地牵住了他的目光——也许是太阳照着的缘故,她身上似乎多了层光彩;在老家时,她脚步走得嗵嗵地,现在却轻灵得像只猫,腰身也细软起来,屁股蛋一扭一扭的。
吃罢晚饭,老大媳妇又是一番视频督查,见龙飞坐在灯下写作业,这才放下心来。张幸福刷锅刷碗,然后洗龙飞换下的脏衣服。才穿了一天,并不脏,可老大媳妇却还是要求他一天一洗。庄稼地里滚大的人,咋恁多讲究!心里这么想,却不敢违拗。
洗完衣服,龙飞作业还没写完。张幸福只好先上阁楼,一会儿龙飞写完了,他还得下来,伺候孙子睡下了,他才能睡。
微信群里热闹起来,一个个大呼小叫的。张幸福清楚,都下工吃罢饭了,又没到睡觉时间,还不出来撒会儿欢?果然,发抖音的、喷大话的、发牢骚的、呼叫着联系活儿的……老家群瞬间变成了嘈杂的市场。张幸福有些兴奋,主要是感觉神奇,一村子的人,本来像蒲公英种子,被吹得七零八落散在各地,一个群就把人们全归拢到一起了。他写了一句话发出去:快割麦了,有谁回去收麦?半天,竟没人理他。现在这人,对割麦都这么不当回事了吗?
他又发了一句:明天到县城北郊看麦去,有没有人和我一起?这次有人回应了,我去。张幸福一看,是飘香的麦穗。有人发了一句语音:生锈的镰刀是谁?有人说,刚被麦花拉进来的,不清楚。也有人说怪话,生锈的镰刀不是专门用来割麦穗的吧?只是不晓得生了锈,还割不割得动?麦花发一张图标,是一把锤子在使劲捶打一个人头,同时配发一句语音:镰刀是割韭菜的,拿回家割你娘那茬韭菜去!群里有人起哄,甚至发出了尖叫。隔着手机,张幸福都闹了一个大红脸,心里却美滋滋的。
第二天,把龙飞送进学校,小半天没啥事,张幸福把电动车一掉头,往城北驶去。
才吃罢早饭,外面却热得离谱,东天一片灰红。越往外走,车辆越稀,路面平展展的,车轮碾出一路沙沙的声响。出了城,景色全变了,蓝色天空下,麦田像一片无垠的大海,金色浪涛向远处汹涌而去;细细的电线上,俏生生站着几对燕子,叽叽喳喳不晓得在议论些什么;麦香扑面而来,令人迷醉……整个世界恢宏、明亮、炫目。多么熟悉的场景!张幸福微微闭上眼,把阳光连同饱满的麦香一齐吸到身体里去,仿佛一尾久久晾在沙滩上的鱼,突然被疯涨的潮水带回大海,有种说不出的愉悦,似乎所有细胞都在欢叫。
有人在背后拍了他一下,扭头看,竟然是麦花。张幸福说,你咋也来了?麦花说,送了学生没事,我也想来看看麦子熟了没有,这城里生活太不习惯了……
麦芒炸开,麦子算熟了,但收割机还没进地。现在人懒,麦子不熟到十成,谁也不割,省得到时还得倒腾着晒。地里很空旷,一阵风吹过,麦田传出轻微的唰唰声。麦花掏出手机,咔嚓咔嚓拍照,说要发到群里。她把手机递给张幸福,让把她也拍进去。
拍完了照片,他们走进麦田,各自找到几穗还略略泛青的麦穗在手里揉。柔软、饱满的麦粒出脱出来,像一群赤肚小孩儿,惹人怜爱。捧至鼻端,仍是那熟悉的、令人心醉的芳香。张幸福倒着用嘴吹去麦糠,不知怎么就迷了眼,酸酸涩涩的,睁不开;用手背揉,越揉越难受,有泪流出来。麦花说,我帮你拨拨。就去地里掐一段草茎,青青葱葱的。走近了,几乎要贴他身上了,衣服擦着衣服,隐隐能感到肌肤的温柔。麦花一手撑开他的眼皮,一手拿草茎在他眼里拨弄。张幸福心扑腾扑腾跳,突然就嗅到一阵浓郁的麦黄杏的甜香。旷野里,怎么会有麦黄杏的香味?张幸福有点晕眩了。
6
好久没给老伴打电话了。晚上睡觉时,张幸福老想给她打个电话,手机在手里摆弄了半天,到底没拨出去。
翻来覆去,到半夜也没睡着。到底咋回事呢?楼下突然传来金毛嘟嘟的叫声,说不出的亲昵。张幸福慌慌张张下楼,才发现,自己竟也变成了一只金毛,胖乎乎毛绒绒。再看金毛嘟嘟,才知道它是一条小母狗,窈窈窕窕的,散发着迷人的香气。他们一起在屋里跑,欢欢地叫着,头拢着头,毛挨着毛,伸出舌头,彼此舔一舔脸。
嘟嘟不愿在屋里待著了,它要到外面去。虽然张幸福变成了金毛,可他还会开门。他们俩快快乐乐地跑了出去。人们都睡了,小区成了狗的天下,大大小小的狗跑了一院子。张幸福说不出地兴奋,甚至是幸福。满院子的狗,数他家嘟嘟最迷人。突然,一条大狗恶恶地扑过来,样子很吓人。张幸福赶紧逃到一边。嘟嘟竟然很愉快地接纳了大狗,当着他的面,两条狗行起了那不要脸的事。张幸福又怒又急,汪汪汪地狂吠,心都碎了……
手机叫得昂扬又固执,张幸福才发现睡过头了。又一想,今天不是星期六吗?龙飞不用上学,他本来想多睡一会儿,是谁这么早打电话?赶忙把手伸到桌子上去摸手机,突然一阵钻心的疼,睡意全无。爬起来一看,大拇指被割了一道龇牙咧嘴的口子,鲜血吧嗒吧嗒正往下滴。桌子上是那张锈镰刀,镰刀上沾着血,正充满恶意地看着他笑。大概它饿得久了,这一口咬得有点狠。
是儿子超学的电话。张幸福问,有事?儿子的质问冷得像冰块,劈头砸向他,看看老家群,你做的啥事?他一脸懵,点开微信。群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却透着邪门,仿佛看到了手机后面躲着的一双双幸灾乐祸的眼睛。往上划了一下,一张艳照,正在那里接受展览——一男一女两具身子贴得那么紧,女的踮起脚尖,把脸往上凑,说不出的暧昧和香艳——这不正是他和麦花吗?张幸福全身的血都冲到脸上,脸红脖子粗的,拇指反倒不疼了。他说,超学,不是你们想的那回事……超学啪地挂了手机,像甩给他一记响亮耳光。
到了楼下,超学说,要他和妈对换,超进载着妈已经在高速上了。这算咋回事?连一句解释也不听,就把这盆脏水全泼在他身上了吗?他们就是这么想爹的?张幸福感到窝囊,又生气,抓住手机摔在了地上。他赌气说,老子哪儿也不去,既然你妈回来了,我们就回老家种那几亩薄地去,以后啥事不管,啥事不问!
枯坐了两个小时,算算超进差不多要下高速了。张幸福叹了口气,心想,儿子们也不容易,正需要人呢,委屈点就委屈点吧。只是他不甘心——这一去,那丑事就算默认了,唾沫星子能淹死人啊。他倒无所谓,可麦花呢?咋能让人家一个女人背这黑锅?还有自家老伴,跟着他几十年了,福没享一天,却有操不完的心。或许她不会跟他大吵大闹,但以后几十年心里系着个死结,还能畅快得起来?
得想想办法,无论如何这事都得解释清楚。
责任编辑 刘钰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