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与义《和张规臣水墨梅五绝》衍说
钟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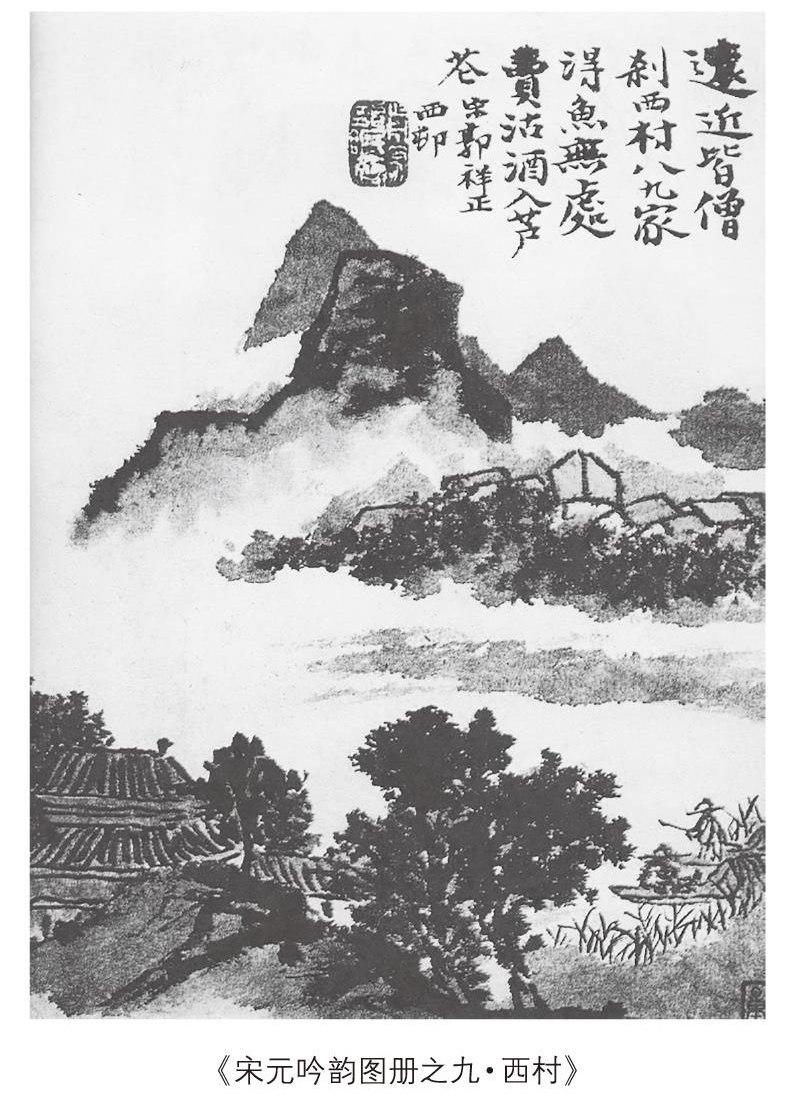
陈与义因为生得较迟,没有来得及被吕本中列入《江西宗派图》,却被方回在《瀛奎律髓》里推为江西派“一祖三宗”的一宗,成为江西诗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这些门派的分别,远没有陈与义在诗歌本身艺术原则上的继承和发明来得重要,转向对艺术原则的关注,才能更好地理解门派内的嬗变。
可以说,在黄庭坚之后,诗歌想不受江西派的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有大的背景,就是诗歌到了宋代,利用经典的语汇进行叙写,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这个趋势被以学问渊博著称的王安石和苏轼无以复加地推进,最终在黄庭坚那里形成具有理论背景的方法—“点铁成金”。不论拥护黄庭坚也好,反对他也好,这方法逐渐成为中国诗歌创作中无人可以回避的“共法”了。“法”一旦凝固,很容易背离艺术的本质,于是想要跳出法的局限也就自然而然了。甚至从黄庭坚开始,已经在有意识、无意识地突破这局限,当他发现经典语汇和现实叙写之间产生了龃龉,就力图将两者之间的异质性达成一致性,这形成了新的美学过程。所谓“不协调因素的协调”(尼柯玛赫《数学》卷二第十九章引斐安语),往往别有奇趣,比起王安石和苏轼的诗歌的博雅,黄庭坚的诗歌显得更加奇崛,这个新的美学过程起了作用。几乎是同时,陈师道从“立格和命意”上下功夫—当然,这跟他不能娴熟地驱遣经典语汇有关—开辟出另外一种江西诗法:从格调上接近经典。
陈与义面临的处境就是如此,一方面要在大背景里标新立异,一方面又不能走入黄、陈的套路。我认为,他首先考虑的不是自己如何归派,而是寻找某种“新法”。徐度《却扫编》记载:“陈参政去非少学诗于崔鶠德符,尝请问作诗之要。崔曰:‘凡作诗,工拙所未论,大要忌俗而已。天下书虽不可不读,然慎不可有意于用事。”一般说,利用经典的语汇进行叙写,主要是为了避俗,而这里讲“忌俗”,却先说“慎不可有意于用事”,就很有意思了。大略可见“用事”成了凝固的法则,自身也成为一种“俗”。不用事之俗,众所易知,用事之俗,才需要特别强调。我们认为,这里针对的正是黄庭坚,因此,下面又记述陈与义“亦尝语人言:‘本朝诗人之诗,有慎不可读者,有不可不读者,慎不可读者梅圣俞,不可不读者陈无己也”。慎不可读的梅尧臣,比起黄庭坚来,缺乏“用事”,所谓“天下书虽不可不读”,也算一种俗。不可不读的陈师道,比起黄庭坚来,不那么有意于“用事”,也就避免了黄庭坚那种俗。这话说得很委婉,也很隐晦,通过对黄庭坚的批评,主要在思考自己的处境。如果不理解这一点,这段记载会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王士禛就反复表示“殊不可解”(参《带经堂诗话·评驳》)。
其实陈师道的方法更容易形成套路,尤其是通过句法模拟古人的气象,就是明代七子“假盛唐诗”的先驱。但是,陈师道发于真性的品格,使其诗在“立格和命意”上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比起黄庭坚沉迷在用字的技巧中,显得更近于宋人理想中的诗人典范杜甫。另外,在模拟气象时个人的风格更容易得到表现,如果不像“七子”那样被条律所限制,还是不难表现出独特性的。这大概是陈与义曾经刻意学习陈师道的主要原因,而他学习之所获也得到一致的认可。罗大经在《鹤林玉露》里说:“自陈、黄之后,诗人无逾陈简斋。其诗由简古而发秾纤,值靖康之乱,崎岖流落,感时恨别,颇有一饭不忘君之意。”首先肯定陈与义的地位,仅次于陈、黄,这也开了方回“一祖三宗”之说的先声。其次,说“其诗由简古而发秾纤”,即指从陈师道的方法入手,却把简古的风格换作了秾纤,展现了自己的独特性。比如“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怀天经智老因访之》),是陈与义很出名的句子,方回评论说:“‘老形已具臂膝痛,春事无多樱笋来,后山诗也。简斋诗本诸此,然亦出于少陵翁也。”(《桐江续集》卷二八)实际上,方回把二陈的方法全追到了杜甫,同时对他们的风格都给予了认可。很有意思的是,陈衍却说:“视放翁之‘杏花,气韵倜乎远矣。”(《宋诗精华录》)陈衍说的也是陆游的名句“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临安春雨初霁》),有了高下判断,则是陆游的气象比起陈与义来,高古尽失了,由此见出陈与义的格调。再次,陈与义经历了家国之难,其自陈师道“立格和命意”上之所得,反而更易于接近杜甫,这也是后来有些论者进简斋而退后山的一个因素。陈与义得自陈师道的影响,以及他个人的风格特色,互相融合,成就了他在诗歌史上的地位,这也是人们容易看到的。
不过,陈与义另有学黄庭坚一路的,却为人们所忽略。这一来是陈与义刻意“忌俗”,避免对黄庭坚的亦步亦趋,一来是他实在已从中变化出新,不易被察觉了。他早年的成名之作《和张规臣水墨梅五绝》,就是很有代表性的学黄庭坚之作。据胡稚《简斋先生年谱》,宣和五年(1123),那时陈与义只有三十三岁,宋徽宗看到他这组诗,“善之,亟命召对,有见晚之叹,以七月除秘书省著作佐郎”,其得意可想。根据曾敏求《独醒杂志》的记载,这幅水墨梅是宋代著名画僧仲仁所画,他以画墨梅闻名于当时。张规臣,字元东,是陈与义的表兄。其诗云:
巧画无盐丑不除,此花风韵更清姝。从教变白能为黑,桃李依然是仆奴。
病见昏花已数年,只应梅蕊固依然。谁教也作陈玄面,眼乱初逢未敢怜。
粲粲江南万玉妃,别来几度见春归。相逢京洛浑依旧,唯恨缁尘染素衣。
含章檐下春风面,造化功成秋兔毫。意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
自读西湖处士诗,年年临水看幽姿。晴窗画出横斜影,绝胜前村夜雪时。
全组五首都紧扣梅花被画成了墨色来写,但是角度、写法各有不同,组合在一起显得异彩纷呈,虽然每首也各有高下之别,但都被这纷呈的异彩遮盖了。最为人称赏的大概是第三首,不妨先来看一下。“万玉妃”,在韩愈的《辛卯年雪》里,“白霓先启途,从以万玉妃”,自是指雪言,在这里指白梅,或许只是借用韩愈的字面,不过苏轼早就这么用—“玉妃谪堕烟雨村”(《花落复次前韵》),成了宋人的常语。“粲粲”,是鲜明的样子。陈与义生长在洛阳,可能曾去江南,见过明艳的梅花。于是说,别来几度,忽然从画卷中看到,梅花依旧美好,只是京洛风尘甚重,把那素色的衣服都弄黑了。这用了陆机《为顾彦先赠妇诗二首》其一:“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还有谢朓《酬王晋安德元诗》:“谁能久京洛,缁尘染素衣。”不仅用字面,也用了意思。明写梅花被画成墨色,暗里透出名利场中多卑污的慨叹,尽管慨叹了千年之久,既未见得有新意,也未见得有真感,但表现在这样新巧的写法里,还是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朱熹的学生问:“简斋墨梅诗,何者最胜?”有人说第四首,朱熹说:“不如‘相逢京洛浑依旧,唯恨缁尘染素衣。”(《朱子语类》卷一四○)其实,巧于用古典,又巧于牵合两件无关的事情(墨梅和“缁尘染素衣”)使之一致,骨子里正是黄庭坚的方法,只是面貌上没有黄的奇崛,而显得秾纤委婉而已。但大家似乎忽略了黄的影响,都以这样的“简斋诗为新体”,倒是陈善指出这其实还是“夺胎”法(《扪虱新话》上集卷四)。王若虚对江西诗派太过敏感,尽管他眼光低劣,竟也发现此首渊源有自,大骂“乃知此弊有自来矣”(《滹南遗老集·滹南诗话》)。
不过,从写法的拓新来说,第一首和第四首更值得重视。也并非所有人都认为第三首好,翁方纲就说:“简斋以《墨梅》诗擢置馆阁,然唯‘意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句有生韵,馀亦不尽佳也。”(《石洲诗话》卷四)这里指出的,正是被朱熹否定的第四首。我们须先了解陈与义的拓新,其源头仍在黄庭坚。看来陈与义很能领会黄庭坚“点铁成金”诸法则的内在精神,因为他的诗中突出了某种谐趣,正和黄庭坚互为表里。我们在从异质性的东西中发现一致性时,往往会伴随着出现一致性中的反规律,所谓谐趣就是由反规律性造成的美感。如果说,丑是我们根本没有认识到规律就在无规律中试图实现合规律,由此而来的必然失败使我们感到的某种不愉悦的情感,那么,谐趣则是我们认识到了规律却有意造成对规律的违反,使对合规律的期待突然转变成虚无,由此而使我们感到某种愉悦的情感。这情感的色彩,重一些谓之幽默,轻一些就谓之谐趣。宋人敏锐地看出古典用得过多时,往往伴随了这样的谐趣,他们称之为“打诨”,如说“东坡长句波澜浩大,变化不测,如作杂剧,打猛诨入却打猛诨出也”(阮阅《诗话总龟》后集卷三一),即是如此。第一首和第四首可以比照来看,前者梅花是主、画家是宾,后者画家是主、梅花是宾,相同的是两者具有谐趣。
胡稚注引《古列女传》:“钟离春者,齐无盐邑之女,为宣王正后,极丑无双。”第一首头两句用了反比的手法,说不管怎样巧妙地去画丑女,都没有办法除去她本来的丑陋,就像你不管怎样唐突地去画美女,也没有办法遮掩她本来的美丽一样。所以虽然你把洁白的梅花用墨色画出来,却不仅没有使之失色,反倒更显出它自身风韵的清姝。“巧画”,黄丕烈校元本、武英殿本俱作“刻画”,可能以为《晋书·周顗传》有“刻画无盐,唐突西施”之句,陈与义一定“无一字无来处”。其实,就这句来说“巧画”更为顺畅,用事不胶着于字句,自缘更着意在由反比透出的谐趣。紧跟着一句,却是用了屈原《怀沙》的句子“变白而为黑兮,倒上以为下”,来写画家把白梅画黑了,用其语不用其意,最是黄庭坚的家法。第四句的出处,胡稚引了苏轼“天教桃李作舆台”(《再和杨公济梅花十绝》)和杜牧“奴仆命骚”(《李贺集叙》),以江西派的标准而言就稍稍差了些。这两句承接上两句说,任教画家恶作剧似的变白为黑,梅花依然凭借自身的出群风韵,使那些争奇斗艳的桃李与之相比似乎都成了它的奴仆。这首以玩笑似的笔调,突出梅花之美好,让画家没法丑化。
第四首,首句胡稚注引《杂五行书》:“宋武帝寿阳公主人日卧含章檐下,梅花落额上成六出花。”这里借用这个典故,以人比花,用寿阳公主美丽的容颜来比梅花。秋兔毫,指画笔,胡稚注引《笔谱》:“凡作笔,须用仲秋兔毫。”这句说,画师笔补造化,把世人难得见到的珍奇梅花—其珍奇一如宫内公主—画了出来,让我这样的普通人也看到了。虽以美人比拟,却怕着了色相,这里马上用到九方皋的故事来化解。胡稚注引《列子》:
秦穆公欲求马,伯乐荐九方皋。穆公使之,行三月而返,曰:“得之矣。”问之,曰:“牝而黄。”使人往取,则牡而骊。公不乐,召伯乐,谓之曰:“求马者,物色牝牡且不能知,又何马之知也?”伯乐喟然曰:“皋之所观,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而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若皋者,乃有贵乎马也。”
不但去除了色相之俗,还称赞了画师用水墨画梅花,只求意足不求形似,境界更高。需要注意的是,口角依然风趣可喜。陈模评论:“使事而得活法者也。”(《怀古录》卷中)“活法”让我们想到杨万里,他就更加“活”了,风趣加重,成了幽默。
比较起来,第二首和第五首就显得逊色了。第二首意思近于第三首,说好久没见梅花,结果变成黑色,我的昏花病眼都不敢相认。第三句用韩愈《毛颖传》“绛人陈玄”,那是墨的游戏之称,翁方纲认为“伧气”(《石洲诗话》卷四),说得并不错,因为意思太平常了。第五首把水墨梅的画面看作林逋“疏影横斜水清浅”(《山园小梅二首》其一)的意境,说梅影比梅花更好。“前村夜雪时”用齐己“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早梅》)。意思也同样平凡不奇,没有什么意趣。
这五首诗是陈与义早年学习黄庭坚的一个代表,可以看出他在文字技巧上的天分,至少在陈师道之上,或者并不亚于黄庭坚。但他后来并未把这里的特色推得更远,我们却在杨万里那里看到了。总体来看,陈与义的诗还是刘克庄说得不错:“《墨梅》之类,尚是少作,建炎以后,避地湖峤,行路万里,诗益奇壮。”(《后村诗话》前集卷二)那就通过陈师道讲的“立格和命意”更接近杜甫了,成为后人眼中的高峰。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从陈与义生平解读其佛禅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