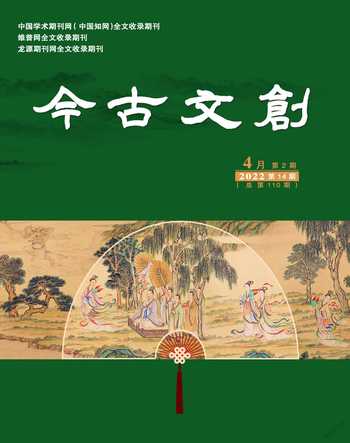跳不出的枷锁 , 触不可及的幸福
【摘要】 《伊芙琳》是乔伊斯短篇故事集《都柏林人》中的一个子集,主要讲述了不堪忍受家庭琐事和暴君父亲压迫的青年女性伊芙琳想要逃脱原本生活的桎梏,最后却又无法跳出自己精神的牢笼的故事。本文从弗洛姆精神异化的理论,从自我的异化、与家庭关系的异化、与社会关系的异化三个方面探讨《伊芙琳》中的异化主题,并探析当时社会背景下青年女性的自我異化原因及消除异化的方式。
【关键词】 乔伊斯;《伊芙琳》;弗洛姆;异化理论
【中图分类号】I5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14-0016-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14.005
一、引言
19世纪末20世纪初,爱尔兰受到来自英国的政治、经济方面的殖民统治与天主教会的精神压迫,整个爱尔兰社会充满了悲观、颓废和令人难以喘息的绝望。都柏林是它的“瘫痪的中心”,瘫痪、颓废和堕落的悲剧在这个城市的每一个地方,每时每刻都在上演。身处爱尔兰庸俗琐碎的社会习惯中,面对被压抑和扭曲的堕落人性,始终保持清醒的乔伊斯对此嗤之以鼻,感到万分厌恶。他在愤懑中创造了《都柏林人》,以促进同胞的觉醒和精神救赎。其创作宗旨正如乔伊斯在写给出版商理查兹的一封信中所表述的“我相信在我以自己的方式编写这一章道德史的同时,我已经朝我国的精神解放迈出了一步……我要为我国的道德和精神史写下自己的一章。”[1]现代主义文学创始人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集《都柏林人》一经发表便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都柏林人》中的子集《伊芙琳》讲述了青年女性伊芙琳想要和自己的情人一起逃离被家庭琐事和暴戾父亲压迫的生活,但是最后却又无法踏上驰向“新生活”的轮船,无法跳出自己精神牢笼的故事。《伊芙琳》的研究主题多侧重于精神瘫痪、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圣经原型分析、象征等。本文从弗洛姆精神异化的理论从自我关系的异化,与家庭关系的异化,与社会关系的异化三个方面探讨《伊芙琳》中的精神异化主题,并探析当时社会背景下青年女性的自我异化原因及消除异化的方式。
二、自我的异化与疏离
“所谓异化,就是一种经验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人体验到自己是一个陌生人。我们可以说,他同自己离异了。他不觉得自己是他那小天地的中心,是他本身行为的创造者,他的行为及其后果则成了他的主人,他服从这些主人,也许还会对主人顶礼膜拜,异化了的人同自己失去了联系,就像他同他人失去了联系一样。他感到自己同他人都像物一样,他有感觉,也有常识,可是他同自己以及同外界并不存在创造性关系。”[2]弗洛姆认为异化是人内心的一种心理体验方式。显然,伊芙琳并未真正认知自己,她是她自己的陌生人,在长期压抑的环境下,她已经与她自己、家人乃至社会异化了。
伊芙琳没有为自我而活的勇气,她完全在为给予自己枷锁的家庭而活。“她坐在窗口,凝视着夜幕渐渐笼罩在林荫道上。她的头依旧依在窗帘上,鼻孔里嗅到沾满灰尘的窗帘布的味儿。她累了。[3]”年纪轻轻的少女本应朝气蓬勃,天真烂漫,而伊芙琳或者说生活在爱尔兰的普通女子,每天的生活却陷在做不完的家务和无穷无尽的琐事之中。而伊芙琳想要逃离的那个家,那些熟悉的物件就算每周打扫一次,依旧布满了灰尘。心里老是纳闷:究竟哪儿来的这么多灰尘?或许,再也见不到这些熟悉的东西了,她连做梦都没想到跟它们分手呐。”(乔伊斯,34)真的存在这么多灰尘吗?
事实上,“这些肮脏的东西象征着我们心中的负面情绪,我们平时说话的时候,会把负面情绪变成‘情感垃圾’,想象中的垃圾就是‘情感垃圾’的象征形象。”[4]这就如同伊芙琳对自己的认知,布满了灰尘,她是谁?她又在追寻什么?她总是把自己挣的钱全部用在自己的家庭上,筋疲力尽地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然后再提着沉甸甸的菜篮回家。母亲去世后,她就担任了母亲的角色,照料两个弟弟,让他们准时吃饭准时上学。而伊芙琳似乎在这些劳作下默认了自己是母亲的替代品,她应该忍受无穷无尽的家务劳作还有父亲的暴戾。伊芙琳的精神已经与自我疏离,无法把自己当作一个精神独立并且健全的青年女性。
三、与家庭关系的异化
当伊芙琳自己不能成为自己世界的中心时,她的世界早已四分五裂。在麻木的生活中伊芙琳默默地承受这一切,唯一顾念的还是母亲临终时自己许下的承诺——保证尽力支撑这个家。而母亲真正理解伊芙琳吗?母亲在精神上其实也已经异化,早已成为了劳动的附庸品,也是自己辛苦劳作和麻木生活的奴隶。伊芙琳的母亲辛辛苦苦劳作了一生,却得不到丈夫的尊重与呵护,还要忍受丈夫的暴力和阴晴不定的情绪,明知道自己生活的不幸,却依旧让伊芙琳代替自己去为这个家服务和劳动。
“她已经十九岁出头了,但即使现在,她有时还会觉得受着父亲暴虐的威胁”(乔伊斯,35),和父亲相处时自己胆战心惊,自己弟弟也不知道体谅自己,和都柏林里其他的男人一样对女人毫不关心,认为女人就应该为家庭为男人所付出。在父亲眼中,伊芙林是她母亲的替代品,为家里操劳和劳作是她的应当承担的义务。伊芙琳回忆自己母亲的一生,为这个家辛苦劳作了一辈子,在平凡的生活中牺牲了一切,但最终竟发疯而死,郁郁而终。想到自己最后的结局可能也会像母亲一样在麻木无情的桎梏中被慢慢地逼疯,伊芙琳最终选择了逃。“她吓得惊跳起来。逃!非逃不可!弗兰克会救她的。他会给他美好的生活,也许,还会给她爱情,她渴望生活。为什么她应该受苦?!她有得到幸福的权利。弗兰克会把他搂在怀里,抱住她。弗兰克会救她的。”(乔伊斯,38)
偶像代表着以异化形式出现的人自身的生命力。偶像崇拜、对上帝的偶像式崇拜、对一个人产生偶像似的爱,对政治领袖或国家的崇拜,以及对非理性感情的外化形式的偶像式崇拜,凡此种种现象,都具有一个通性,即包含着一个异化的过程。这些现象表明了这样的事实:人不再感受他是自己的力量和丰富感情以及品质的主动拥有者,他感受自己只是一个贫乏的“物”,依赖于自身之外的力量,他向这些外界力量投射出他生存的实质。[5]与水手弗兰克相恋后,伊芙琳极度崇拜他,并且把自己的幸福也归附于弗兰克,认为自己只要和弗兰克远走高飞,就有幸福的权利,“在那遥远的陌生的地方……她将结婚,人们将尊重她。她不会像妈妈生前那样遭受虐待。”(乔伊斯,35)她崇拜和依赖弗兰克,“他心地善良,又有男子气概,他热爱音乐还能哼上几句(乔伊斯,36)” 在伊芙琳眼里,弗兰克如同一位救世主,是她最后的救命稻草,弗兰克会救她脱离苦海,可是她足够了解弗兰克吗?还是说伊芙琳爱的究竟是弗兰克?还是那个勇敢挣脱枷锁,精神不被压抑后的自己?从乔伊斯对弗兰克的描写中,我们可以推断出弗兰克并非是那么美好与诚实,他“后脑勺上戴着尖顶帽”,“常开玩笑似的管她叫‘小宝贝’”,但他们两个人的相识“算来不过是几星期以前的事”。(乔伊斯,36)弗兰克的浪漫与挑逗,激发了伊芙琳被压抑的内心,一直波澜不惊甚至麻木的内心激起了爱情的浪花。一个从未得到男性关爱,渴望幸福的单纯少女又怎么能经得美好生活的诱惑呢?休·霍加特曾在他的著作中说过:“不熟悉都柏林的人可能会认为这艘船要去南美洲。但前往南美洲的大西洋船是从利物浦或其他英国港口出发,而不是从都柏林出发。弗兰克很可能只是想把伊芙琳带到利物浦或伦敦,在那里引诱她,然后把她扔掉。就像许多雄辩的恶棍遗弃掉简单的爱尔兰女孩一样。”[6]因此,弗兰克或许并非那么真心与美好。尽管这个时候伊芙琳有了逃脱枷锁和追求自由的意识,但这种对美好生活追求的意识是完全依附于他人的,这也说明了伊芙琳依旧不具有成熟,独立的自我人格意识。
四、与社会关系的异化
弗洛姆认为人的异化是来源于人的本身,“人的存在于他的本质疏远,人在事实上不是他潜在的那个样子,或者,换句话说,人不是他应当成为的那个样子, 而他应当成为他可能成为的那个样子。[7]”缺少身份认同感的伊芙琳与她的社会关系也是异化的,无法融入自己的社交圈,也无法交到知心朋友。當她决定私奔的时候,她却在暗自揣摩同事对她的看法,“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店里,都得拼命干活。一旦店里的同事发现她跟一个年轻力壮的汉子离家出走了,他们会怎么议论呢?会登广告,找人补她的缺……这下子加万小姐该高兴了……(乔伊斯,34)”伊芙琳对社交关系的揣摩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无论在家庭关系中还是在社会关系中,伊芙琳一直被他人排除在外。这种与家庭和社会格格不入的感觉,完全来源自伊芙琳对自己认知。她原本可以不必成为家庭的牺牲品,原本自己也有追求幸福权力,可在伊芙琳内心深处,她完全把自己摒弃了,潜移默化之中把内心里那个渴望热情和幸福的伊芙琳埋葬了。
当驰向未来陌生生活的船即将出发时,伊芙琳还是退却了。“不!不!不!绝不!她的手狂乱地住铁栏。在风涛中,她凄绝地尖叫一声”(乔伊斯,52)最后伊芙琳还是没有勇气像《死者》里面的布里埃尔一样挣脱掉困住自己的枷锁,勇敢出走去寻求一条新出路。即使把弗兰克换成任何一个真心追求伊芙琳的年轻小伙子,伊芙琳都不会有勇气选择和情人私奔。因为伊芙琳无法认知真正的自我,她没有意识到自我的价值,她对自己的价值与人生意义都寄托在外人身上。伊芙琳无法寻回自己的独立人格,即使面对未知的生活时,缺少自我意识的伊芙琳内心深处依旧充斥着苍凉感和无助感。
五、异化解除的方式
巴西教育家保罗·弗莱雷在《被压迫者教育学》中认为:“所谓压迫,就是任何一方客观上剥削对方(或阻碍对方)的情况下为了追求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人的自我肯定。弗莱雷从人的本性的角度分析和解释了压迫者的压迫行为和被压迫者对自由的追求的相关理论,这本书认为人性化是人的使命。压迫和被压迫普遍存在于社会中,阻碍了人类的人性化。为了摆脱他们的悲惨处境,被压迫者必须主动寻求自身的解放。被压迫者自己属于压迫者所拥有财富的一部分,属于为压迫者创造财富的廉价劳动力。因此,在寻求人性化的过程中被压迫阶级必然会遭遇巨大的抵抗。[8]”因为来自生活、精神、宗教、政治压迫的爱尔兰人才会精神麻木,而爱尔兰的女性除此之外还承受着来自家庭和男性在肉体和精神上压迫与奴役,在种种压力下,女性与自身,与外界都会发生精神上的异化。
弗洛姆认为消除异化的方式在于健全人的理性,就是创建健全的社会。“一个健全的社会使人在易于管理的和可观察到的领域内,积极而负责地参与社会生活,并且成为自己生命的主人。一个健全的社会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战斗团结,不仅允许而且鼓励同成员友爱相处;健全的社会促进人人在工作中进行创建性活动,刺激理性的发展,使人能够通过集体的艺术和仪式,表达出自己内心深处的需要。” [9]可见,弗洛姆“要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激发人的自我意识,使人了解自己在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荒谬性,使社会人道主义化,使人从内心深处获得解放。” [10]在《为自己的人》中,弗洛姆提出的生产性指的是“每个人都具有的一种态度,除非他是精神上和情感上的残疾人” [11]。
乔伊斯以他的家庭为基础描绘了伊芙琳的角色,乔伊斯年少时的家庭生活就像恶魔的梦魇一般,他的父亲是一个恶棍,他的母亲被折磨致死,而他的大多数兄弟姐妹也过早的夭折。他说:“我的心早就抛弃了整个社会秩序和天主教,以及对道德的追求。我怎么会喜欢‘家’这个概念呢?” [12]。伊芙琳是当时爱尔兰千千万万女性的缩影,为家庭奉献一切,却又被家庭和丈夫奴役着,生活麻木不堪,想要反抗却又无能为力。生活的麻木不仅来自生存的困境,还来自女性自我的精神疏离与异化,女性无法完善自己的独立人格,也无法把自己当作自己生活的主人。如果伊芙琳能够正视自己情感需要和生活需求,她还是能够选择一条更加适合自己的出路并最终实现自我救赎,而不是依附与他人,做无谓的憧憬和希望。正如弗洛姆所说,克服异化就必须用爱进行革命,人与人之间建立真正平等的关系,呼唤每个人从内心发出真正爱的声音,用爱去消除人类世界的异化,建立充满爱与尊重的世界。在整个都柏林,消除女性的异化仍然需要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关爱与尊重。每个人都应该都关心、尊重和认识自己和他人。而这些要求在当时精神瘫痪和麻痹社会里,依旧是遥不可及的希冀而已,这也正是乔伊斯写作的出发点之一,试图唤醒和感染任何一个精神有所向往自由和清醒的都柏林人。
六、结论
乔伊斯是一位面向世界和未来的伟大作家,他不仅以一位作家的冷峻目光审视着当时精神淡漠和瘫痪的整个爱尔兰社会,对其国人也怀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他希望青年都能像布里埃尔一样出逃,寻找一条新的出路。但又深知勇敢逃脱束缚自己精神枷锁的困难。乔伊斯也从男性的视角对处于被社会压迫、被男性压迫和被家庭压迫的女性们投出了关怀的目光。《伊芙琳》绝对不是一篇简单的故事,故事背后的女性的身份和地位值得得到更多的人文关怀。尽管伊芙琳最终还是无法形成自己的独立人格,无法挣脱掉自己身上的枷锁。但这位对女性充满关怀和怜惜的作家却在警醒女性,在麻木瘫痪的社会环境和家庭背景中,每一个爱尔兰女性都更加应该地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单独、完整且健全的人,而不是社会、家庭和琐碎劳作的附庸,女性在精神层面有能力和力量掸去落在身上的“灰尘”和摆脱掉那会让人失去自我光辉的桎梏。
参考文献:
[1]Harry Blamires. Studying James Joyce. Longman York Press,1987.p.30.
[2]詹姆斯·乔依斯.都柏林[M].孙梁,宗白,王智量等译.上海:上海译出版社,1984:34,35,38,6,35,34,52.
[3]朱建军.我是谁:心理咨询与意象对话技术[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22.
[4]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孙恺祥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111.
[5]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孙恺祥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115.
[6]范婷婷.浅析《伊芙琳》中的《圣经》原型文化[J].文学教育(下),2019,(09).
[7]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M].张燕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50.
[8]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59.
[9]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孙恺祥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271.
[10]弗洛姆.人之心——爱欲的破坏性倾向[M].都本伟等译.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58.
[11](美)弗洛姆.为自己的人[M].孙依依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92-106.
[12]O'Halloran,Kieran.The Subconscious in James Joyce’s “Eveline”:A Corpus Stylistic Analysis that Chews on the “Fish hook”[J].Langmzge and Literature,2007(3).
作者简介:
常新亚,女,汉族,河南周口人,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