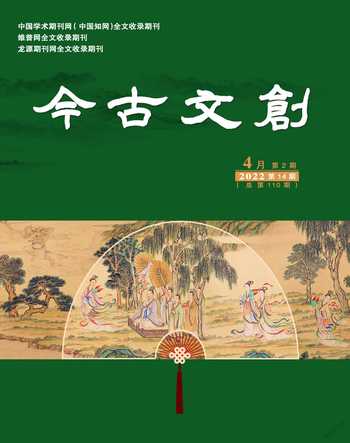《花圃》中 “ 花圃 ” 空间的叙事功能
【摘要】 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于1933年出版中篇小说《花圃》,小说围绕花圃展开叙事,在主人公妮尔佳身体健康时她与丈夫阿迪多共同经营花圃,在妮尔佳因身体原因无法参与管理花圃后,妮尔佳也逐渐颓废直到最后悲惨死亡。本文借鉴空间叙事理论,分析“花圃”在文本中的叙事功能。这一空间对推动情节发展、塑造人物形象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主人公妮尔佳来说,“花圃”是具有“神圣意义”的“神圣空间”,由于空间的变易与冲突,妮尔佳的人物形象也随之改变,妮尔佳对花圃的执念其本质是对自己身份和生存意义的守护。
【关键词】 花圃;空间;叙事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14-0013-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14.004
一、花圃:妮尔佳的“神圣空间”
在小说中,花圃占据了重要地位,对于女主人公妮尔佳来说,花圃就是她心之所向的“神圣空间”,是妮尔佳曾经无限爱怜的生存场所。在妮尔佳眼中,花圃有着如生命般珍贵的意义,所以在自己失去花圃之后,她的性格才会逐渐产生变化,在亲人眼中变得越来越不可理喻,甚至扭曲,直至在死亡之时变得彻底疯狂。“‘神圣空间’借自宗教学术语。对于普通人来说,空间意味着‘均质’和广延;但对于宗教徒来说,某些空间由于它的特殊性而被赋予了‘神圣’的特性。比如说,圣树、圣石就能够作为一种‘显圣物’,展示出不再属于一块石头、不再属于一棵树,而是属于神圣、属于完全另类的东西。” ①
花圃之于妮尔佳就如同神庙或教堂之于宗教徒,花圃在妮尔佳的生命中具有无与伦比的神圣性。“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在世俗空间中有时也能够体验到能够唤起空间的宗教体验所特有的非均质的神圣价值。例如有一些特殊的地方,它们与所有其他的地方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像一个人的出生地、初恋的地方、年轻时造访过的第一个外国城市的某处。甚至對于那些自我坦陈不是宗教徒的人而言,所有这些地方仍然具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无与伦比的意义。这些地方是他们个人宇宙中的‘圣地’,是他们生活的意义得以产生的‘神圣空间’,似乎正是在这些地方,他们得到了一种关于实在的启示;于是,这些地方对他们而言,不仅仅是日常生活中的一处普通的地方”。②花圃成就了妮尔佳的全部,塑造了“美好的妮尔佳”,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花圃是妮尔佳青春的凝聚;第二,花圃是妮尔佳爱情的见证;第三,花圃是妮尔佳幸福婚姻的象征。
花圃是妮尔佳青春的凝聚。在小说开始部分,妮尔佳无奈地躺在病床上,听到不远处花圃的钟声响起之后,不自觉地回忆起了往昔的美好时光:“从结婚第二天开始,妮尔佳和她丈夫的爱情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在管理花圃的工作中融合在一起了。花圃里的每一朵花,每一片叶子上都浸透着他们二人的欢乐,随着这种欢乐不断日新月异,不时显现出迷人的风采”。③妮尔佳少女时期成婚,到如今已结婚十年,婚姻的最初时光,同样可以视为妮尔佳的青春时期。妮尔佳从步入婚姻开始,她的精力与激情大部分投入到家中的花圃,这是她与丈夫共同的劳动场所。花圃里生机勃勃的花朵更是妮尔佳青春的象征,也可视为妮尔佳从少女到少妇、从青涩到成熟的隐喻。这是妮尔佳身为女性在人生中极为关键的一个成长过程,在这一层面上,花圃之于妮尔佳的意义自然非比寻常,是“神圣空间”一个表征。
花圃是妮尔佳爱情的见证。初入婚姻的妮尔佳与阿迪多生活幸福美满。令人惋惜的是,小说中使人心醉的甜蜜点滴都只是出现在妮尔佳的回忆之中。每当妮尔佳感觉自己已经失去了花圃和阿迪多,往昔时光中的美好不经意间就闯入了愁惨的现实。在与丈夫阿迪多恩爱生活的过去,阿迪多常常将妮尔佳比作印度古代著名诗人迦梨陀娑,也认为只要有妮尔佳的存在,“每天走过的小路上,开满了五颜六色的鲜花,春风中弥漫着酒的芳香,整个玫瑰园都被陶醉了”。④记忆中的字里行间浸透着爱情的甜蜜,阿迪多对妮尔佳表白爱意的话语中,多次将美丽的妮尔佳与缤纷的鲜花相联系,不仅妮尔佳与阿迪多的爱情之花开放在花圃当中,作为丈夫的阿迪多也不自觉地将青春四溢的妮尔佳与花圃融为一体。在妮尔佳自我认知和他人认知中,妮尔佳都与花圃紧密相连。
花圃是妮尔佳幸福婚姻的象征。对于妮尔佳来说,青春、爱情与婚姻是水乳交融的,妮尔佳与阿迪多通过自己的努力组建了属于自己的小家庭。夫妻二人在花圃中延展了爱情,在花圃中互相扶持鼓励。这种看似平淡却流溢幸福的细节,在妮尔佳的回忆中也时常闪现。当亲友们夸赞花圃里的鲜花芬芳,水果可口时,阿迪多都会夸赞妮尔佳,将花圃中的成果归功于妮尔佳的辛勤和聪慧。这些花卉和果实不仅是大自然的美丽产物,更是妮尔佳与阿迪多幸福生活的“客观对应物”,花卉的美、果实的甜,就是二人生活的美、情感的甜。
花圃对于妮尔佳来说就是虔诚宗教徒心中的“神圣空间”,她与阿迪多曾经共同拥有的花圃,是妮尔佳青春、爱情和婚姻的折射,这几乎是妮尔佳生命的全部。妮尔佳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了价值,是花圃使她成为一位美丽、自信的女性。“一个神圣空间的确立,使得一个‘基点’成为可能,因此也使在均质的混沌中获得方向成为可能,并使‘构建这个世界和在真正意义上生活在这个世界’成为可能。” ⑤
二、性格扭曲:空间变易与冲突
小说中花圃的空间意象具有重要的叙事功能,塑造人物形象便是其中的重要一点。女主人公妮尔佳的人物形象与花圃这一特定空间有密切关系:妮尔佳从一位温柔可爱、自信美丽的女性逐渐转变成性格暴躁、多疑扭曲的形象。这一转变的重要原因便是空间的变易与冲突:因为身体原因,妮尔佳只能长期卧床休息,再也不能进入她心爱的花圃,更不能通过打理花圃来实现自身价值。妮尔佳失去了实现自身价值最主要的途径,这意味着往昔的一切美好今后只能留存于记忆之中。更为痛苦和残忍的是,在物理距离上,花圃不是距离妮尔佳遥不可及的,正如小说开篇描述妮尔佳养病的房间时写道:“东边的窗户敞开着,从这里能看到下面花圃里的兰花房,它是由栅栏围成的,栅栏上面长满了爬山虎。” ⑥
人物形象不是直线型产生的,“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逐渐生成的,可以说,他们的生成与整个叙事文本的创作过程相始终。” ⑦在具体空间中理解人物,才能摸清人物心里和行为的来龙去脉,人物形象才会展现出一种相对的固定性。妮尔佳后期复杂性格的生成,正是“天使”与“疯女人”的相互转变与冲突,而正是因为自己赖以生存的空间发生了突变,这一突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空间变易:花圃转变为病床。妮尔佳曾经在分娩时难产,手术后保住了性命,失去了孩子。巨大的身心打击使得妮尔佳从此卧床不起,“她那贫血的身体就像拜沙克月的河流倒卧在沙滩上一样,显得疲惫不堪,她那无穷的生命力已经消失殆尽。” ⑧在小说开头,首先映入读者眼帘是妮尔佳当前的生活环境:“屋子里只有一张床,一个三角架和两把藤椅。在房间的一角拴着一条晾衣服的绳子。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了。在房间的另一个角落里,放着一个铜花瓶,花瓶里插着一束夜来香,在这个密不透风的房间里发出淡淡的清香。”
愁惨,冷落、孤寂的压抑感扑面而来。年轻的妮尔佳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日复一日地消耗着自己的生命。此时的家宅与她从前活泼美丽的形象形成强烈的反差,与妮尔佳现在的病体相互对应。这样“生存场所”,是妮尔佳性情大变的生成基础。住宅与人的关系密不可分,加斯东·巴什拉为了强调住宅与人的密切关系,将住宅称为“家宅”。“家宅是一种强大的融合力量,把人的思想、回忆和梦融合在一起。在这一融合中,联系的原则是梦想……没有家宅,人就成了流离失所的存在。家宅在风暴中保卫着人。它既是身体又是灵魂。它是人类最早的世界。” ⑨
家宅越是重要,对妮尔佳的打击就越大:理想中的家宅无法缺少花圃,而她现在的房间却弥漫着病态与虚弱。当阿迪多无奈地问妮尔佳,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出现裂痕的。妮尔佳痛苦又绝望地说:“自从你拥有了世界上的一切东西,而我只拥有这个房间的一角。” ⑩妮尔佳道出了自己痛苦与改变的真正原因,自己的生存空间只有房间里的病床一角,他们再也不是那美丽花圃中的幸福夫妻了,并且自己也不能像从前那样为花圃服务了。
第二,空间冲突:花圃与病床既远又近。如果家中的花圃在物理距离上与妮尔佳相距遥远,那么妮尔佳也许只能沉浸在对过去美好的回忆中,现实与记忆就会成为一种单纯的虚实转换。但现实却是残酷的:花圃近在咫尺,妮尔佳却无法触及。尖锐的空间冲突时刻都在折磨着妮尔佳。这种空间冲突就是妮尔佳性格冲突的空间化象征。
首先,妮尔佳距离花圃很近,她能够透过窗户闻到花圃中的花香;能够听到特定时刻花圃的钟声;家里送花的车来来往往,她也能够大致了解花圃的生意情况。每当妮尔佳听到花圃中的钟声时胸口就开始疼痛,即使如此,她还是不允许仆人关闭东边那扇能看到花圃的窗户。妮尔佳目前的生存空间与往昔的生存空间产生了强烈的冲突。
其次,小说中多次提到,丈夫阿迪多每天都会带一束花圃中的鲜花放在妮尔佳的房间中,尤其是妮尔佳最喜欢百合花。家人希望妮尔佳看到鲜花能够心情舒适,这却加重了妮尔佳的痛苦,因为眼前的鲜花实实在在地成为花圃的象征,在视觉上折磨着妮尔佳。冷寂房间中的百合花,成为了卧室中内在的“小空间”,这一空间也表征了人物的性格与冲突。
三、最后的疯狂:空间中的身份转换
妮尔佳常年卧床之后,丈夫阿迪多請来了自己的表妹绍罗拉帮助自己打理花圃。绍罗拉有比较丰富的花卉种植与花圃管理的经验,渐渐地,绍罗拉在很大程度上接管了花圃,更重要的是,她似乎代替了妮尔佳原本在花圃中的地位。这对于妮尔佳来说是巨大的打击。在妮尔佳眼中,绍罗拉不是助手,而是过去的自己,她成为了花圃的管理者,甚至还有可能成为阿迪多的新妻子,成为整个家庭的女主人。妮尔佳的猜想是正确的,阿迪多渐渐对绍罗拉产生了情愫,最后也向妮尔佳承认自己爱上了绍罗拉。此时的妮尔佳更加绝望。妮尔佳知道自己的生命快要走向尽头,于是努力听从小叔罗蒙的建议,整理自己的情绪,在思想上准备接纳绍罗拉。但是当绍罗拉出现在妮尔佳面前时,妮尔佳还是爆发了最绝望的情绪,称绍罗拉为“女魔鬼”,自己永远不会给绍罗拉腾出位置。在绝望的嘶吼中,妮尔佳走向了死亡。
妮尔佳对绍罗拉的态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接纳与驱逐,理解与痛恨间来回纠缠。一方面妮尔佳很理解丈夫请来绍罗拉,因为花圃中确实需要得力人手,但是每每看到绍罗拉在花圃中如鱼得水,妮尔佳就十分厌恶。对于妮尔佳来说,绍罗拉占据了花圃,抢夺了原本属于自己的空间,进而占据了阿迪多以及整个家庭。妮尔佳与绍罗拉进行了“身份置换”,妮尔佳看到绍罗拉,就是看到了曾经的自己。妮尔佳有多向往曾经的生活,就有多痛恨绍罗拉。这种特定空间中身份的置换,是妮尔佳最终走向“癫狂”的真正原因。
首先,妮尔佳对于绍罗拉的厌恶,最初源于绍罗拉的形象与自己当前形象的冲突。在妮尔佳的眼中,“绍罗拉身材高挑儿,皮肤黝黑,她那双神采奕奕和略带忧伤的大眼睛格外引人注目,她身着粗布纱丽,头发很随意地梳着,任它散落在肩上。她那毫无装饰的身体,仿佛不欢迎青春的到来”。⑪即使没有繁复的装饰,绍罗拉的全身也散发着青春的气息。每当妮尔佳因为绍罗拉占据了花圃而向阿迪多诉说不满时,妮尔佳总是以绍罗拉的身体形象开始。曾经的妮尔佳也是青春活泼的,并且希望能够继续学习,与阿迪多一起经营花圃。现在换成了绍罗拉,青春、智慧与能力变成了负面的因素。
其次,妮尔佳认为,绍罗拉进入花圃,就是剥夺了自己肉体与生命。因为妮尔佳早已把自己看作是花圃的对应者,花圃是妮尔佳的“神圣空间”,一定意义上,花圃就是妮尔佳。妮尔佳曾对阿迪多说自己在婚后就和花圃之间没有任何一点缝隙了,“我已经把它融化在我的血液中,我们已经融为一体了。” ⑫在妮尔佳看来,自己就是花圃的肉身。而绍罗拉进入花圃,是对自己生命的伤害与剥夺,最后又代替了自己,成为曾经的自己。当妮尔佳听说绍罗拉被关在监狱并且快要死的时候,似乎回到了一种放松的状态,而且建议阿迪多不要荒废花圃的工作,并且愿意亲自在病床上指挥花匠霍拉干活。妮尔佳明确表示“我要在花圃中完全留下我的痕迹” ⑬。这是对妮尔佳对花圃的一种占有,更是恢复自己身份的努力。
不过,这种努力终究是徒劳的,绍罗拉最终还是回到了花圃。“她抓住绍罗拉的手,用尖厉的声音嚷道:‘这里没有你的位置,你这个女魔鬼!没有你的位置。我要在这里待下去,待下去,待下去。’” ⑭妮尔佳还是在爆发的疯狂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妮尔佳对于空间的占有,是维护自己身份与意义的方法。她最终的疯狂,是不能容忍绍罗拉占有曾经属于自己和阿迪多的花圃,他者的占有,就是对妮尔佳肉体、精神、身份与意义的全面剥夺。
从特定的空间“花圃”入手,可以看出花圃在文本中重要的叙事意义,一方面“花圃”是小说情节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也可以从空间的变易中梳理出人物形象变化的原因。对于妮尔佳来说,花圃这一空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神圣空间”,从而使得空间变易与冲突出现后,妮尔佳的人物形象与性格也随之变易与冲突。妮尔佳对于花圃的维护,是对于自身存在意义的守护。
注释:
①②⑤⑦龙迪勇:《空间叙事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40页,第115页,第115页,第259页。
③④⑥⑧⑩⑪⑫⑬⑭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著、董友忱主编:《泰戈尔作品全集·第6卷》(下),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35页,第649页,第635页,第637页,第657页,第642页,第658页,第681页,第685页。
⑨加斯东·巴什拉著、张逸婧译:《空间诗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参考文献:
[1]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泰戈尔作品全集·第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2]龙迪勇.空间叙事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3]加斯东·巴什拉.空间诗学[M].张逸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
贺晓璇,女,山西太原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2018级博士,研究方向:东方作家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