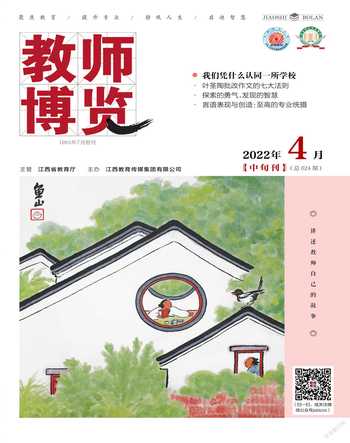罗兰·巴特与母亲
陈蔚文

读林贤治先生的一则随笔,是关于罗兰·巴特与他的母亲。
1977年10月25日,法国著名作家、思想家罗兰·巴特的母亲在经历了半年疾病折磨之后辞世。母亲的故去,使罗兰·巴特陷入极度的悲痛之中,他甚至想到过自杀。
从母亲逝去的翌日,他开始写《哀痛日记》,历时近两年。
“这是一部特别的日记,共330块纸片,短小而沉痛的话语,记录下了他的哀痛经历、伴随着哀痛而起的对母亲的思念,以及他对于哀痛这种情感的思考和认识。”
在罗兰·巴特的笔下,这是一位美丽、质朴、仁慈,有着相当的文化修养和高贵的自尊心的女性。当母亲活着的时候,罗兰·巴特担心失去她而使自己处于神经症的状态之中。及至母亲去世,他已然无力承受孤独和虚无的重压。他一个劲儿使用灰色调,在纸片上这样涂写他的自画像——悲痛、温存、消沉、害怕,总之脆弱得很。
我们完全相信,罗兰·巴特的母亲一定是一位尽责的好母亲,这位23岁就因为战争而成了寡妇的女性(丈夫是一位海军军官,在罗兰·巴特未满一岁时阵亡),靠微薄的战争抚恤金把罗兰·巴特和比他小11岁的同母异父的弟弟养大成人。
她用一生守护着儿子,“她不但是罗兰·巴特生活的缔造者,而且是罗兰·巴特灵魂的养育者和庇护者”。
然而,当看完这篇随笔,我却觉得这位母亲也许不能算是完全称职。因为对罗兰·巴特来说,“失去母亲以后,他有被遗弃感,觉得失去了活着的理由。他多次说到死。他想死,然而又想疯狂地活着”。
能否说,至少在“分离教育”方面,罗兰·巴特的母亲并不成功?而这是亲子关系中重要的一环。
“他制造假象,复制过去,他不能接受与母亲分离的事实。”从某种意义上,罗兰·巴特在情感上还是个孩子,对母亲的极度依赖使他像个尚在哺乳期的婴儿,他无法独立处理好一件原本正常不过的事——任何人都要面对的生老病死。
在《哀痛日记》中,他写道:“我可以在没有母亲的情况下活着……但是,我所剩下的生活直到最后肯定是没有质量的。”
在1978年2月21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支气管炎。自妈妈死去以来的第一种病。”
3月25日他写道:“这天早上,继续想到妈妈。令人作呕的悲伤。无可救药的恶心。”
还有次他写道:“昨晚,噩梦:妈妈丢了。我不知所措,处在泪水的边缘。”
如果这是个孩子或少年的日记,或许并不奇怪,因为面对亲人的死亡的确是需要准备的(心理的准备、时间的准备),但当时的罗兰·巴特已六十多岁。
除了日记,他还给母亲写了一本书《明室》,上半部分谈论摄影的本质,下半部分谈论母亲。他借用普鲁斯特失去祖母时的话说:“我不仅情愿忍受这种痛苦,而且要尊重这种痛苦的与众不同。”
“没有母亲我可以生活(我们每个人迟早都会过没有母亲的日子),不过,我剩下来的生活,一直到死,都一定是坏得无法用语言形容(无优秀品格)。”母亲去世以后,他一直未走出哀痛和对母亲的追忆。
在精神上,他和母亲住了一辈子。
罗兰·巴特,一方面他是法国作家、思想家、社会学家、社会评论家和文学评论家,开创了研究社会、历史、文化、文学深层意义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方法,其丰富的符号学研究成果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是一个始终未长大的孩子。
母亲逝世两年多,罗兰·巴特从一场宴会离开返家时,据说由于精神恍惚,被一辆卡车撞伤,一个月后伤重不治而逝世,享年64岁。后来人们在车祸发生的地点刷上标语:“请开慢一点,不然您可能会軋到罗兰·巴特。”
据说,符号学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回忆罗兰·巴特临死前的情景:“他的眼睛闪动着疲惫和忧郁,脸色无光,他向我做了一个要求放弃和永别的动作,意思是说:不要挽留我,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好像活着已经令他厌倦。”
或许,从母亲逝世那刻起,罗兰·巴特已觉得生无可恋,死亡对他反而是一种解脱。
林贤治先生在那则随笔的结尾说:“能做到博爱固然可崇敬,倘若不能,爱一个人就够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爱一个人那里,罗兰·巴特显得那么纯粹。
是的,我同意罗兰·巴特对母亲的爱非常“纯粹”,不过,有时“纯粹”也会使一种情感走向偏执。
罗兰·巴特便是如此,作为一个思想家,他应当清楚生老病死本是人类的基本课题,没有人能逃脱死亡,人不应当为不能逃脱之宿命而钻牛角尖。
罗兰·巴特却耽溺于丧母之痛,数年未能解脱。“他已经陷入人生的最低潮:隐隐沮丧,感觉受到攻击、威胁、烦扰,情绪失落,时日艰难,不堪重负,‘强制性劳动等。他深知,这是哀痛的经典机制。可怕的是,后来连最可靠的记忆也受到了影响,他不能不把所有这些同母亲去世一事联系起来。”
这样一份“纯粹之爱”,我似乎难以去歌颂。正如我不能去歌颂罗兰·巴特受过的心灵折磨与痛苦。
如果这份“纯粹之爱”发生在爱情当中,尚可以理解与令人敬佩,可它发生在亲子关系中,对孩子来说,并不是一桩好事。
“母子间的感情应该是绵长而饱满的,但母亲对孩子生活的参与程度必须递减。强烈的母爱不是对孩子恒久的占有,而是一场得体的退出。”教育学者尹建莉说。这段话如此清醒地说出了亲子关系应有的面目。
罗兰·巴特的母亲是如何与罗兰·巴特相处的,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她一定是位倾情付出的母亲,或许正因为太倾情付出,才使罗兰·巴特在她走后,陷入不知所措的悲伤中——像一个从母亲身边走丢的幼儿。
母亲将她的爱,如一根绳子牢牢系紧了孩子,即使在她死后,这根隐形的绳子仍没有松开。
再来看看尹建莉说的一段话:“爱的第一个任务是和孩子亲密,呵护孩子成长;第二个任务是和孩子分离,促进孩子独立。”母子一场,是生命中最深厚的缘分,深情只在这渐行渐远中才趋于真实。若母亲把顺序做反了,就是在做一件反自然的事,既让孩子童年贫瘠,又让孩子的成年生活窒息。
“分离”,的确是需要学习的。
母亲对孩子,不是只有深情即可。这份深情更要伴随“放手”,让孩子学会独立地去面对自我的道路。它不应当如一根紧缚的绳子,而应当如一根风筝之线,当风筝迎风起飞时,这根线就应松手,让风筝去找自己的天空。
大概是自己做了母亲后的自我警醒——我何尝不是一个过分操心的母亲?对儿子关注过多,包括他的衣食、情绪种种,有时说是他依赖我,不如说是我过分依赖他,依赖他对我的需要。
但我也清楚,健康的亲子关系应当是伴随成长带来的逐步分离,直到他有自己的人生与家庭——“父母从第一亲密者的角色中退出,让位给孩子的伴侣和他自己的孩子,由当事人变成局外人,最后是父母走完人生旅程,彻底退出孩子的生活……而检验一个母亲是否真正具有爱的能力,就看她是否愿意分离,并且在分离后继续爱着”。
在亲密联结与泛滥母爱之间,如果未能把握好那根绳子,“亲密”对孩子有可能成为一种破坏力和灾难——孩子要么恐惧或反抗这种依恋,要么永远走不出这种对“亲密”的依恋。像罗兰·巴特一样,把母亲的死也视作自我生命意义的终结。
而对一个真正深爱孩子的母亲来说,这肯定是她不愿看到的。
在经过一番艰难的抉择后,今年夏天,我和丈夫做了一个决定,让孩子去上海读他考上的高中,去开始他自己完全独立的生活。
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我不想再把他牢牢系在身边,不想一直无微不至地关心着他,也干扰着他。我想让空间的距离真正帮助我完成一次早晚要到来的必然的分离。
让从未离家的他,在一方更开阔的天空开始他青春的翱翔吧。只有在翱翔中,他的羽翼才会日渐丰满,而不是用“呵护”去令他的羽翼萎缩。
如果罗兰·巴特的母亲知道在自己死后,儿子会如此痛苦颓废地度过以后的日子,她一定会在活着时,鼓励孩子去建立自己独立的感情世界,那里不仅有母亲,还有伴侣与朋友,以及他自己的孩子。
她一定会为他走出家门而高兴。
她一定希望他是这样一个人——爱母亲,但他依然会在她离开后,达观地走下去,完成好自己的生活和意义,并把爱传递给身边的人。
也许,这才是“纯粹”而健康的爱。
(插图:珈 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