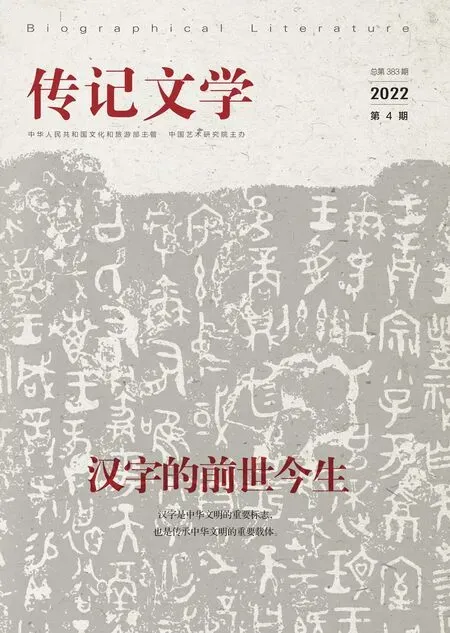柳宗元的永州十年(一)
林加妹

长安日远
贞元二十一年(805)七月,诏令皇太子监国。
禁中的消息随着天光传进住地,宁静的坊市开始有人走动,渐渐地,街市里巷变得热闹,杂沓的声音与气味充斥五感。
柳宗元一夜未眠,如今也无丝毫困意,坐在车里,他眉头紧蹙。车驾在建福门外停了许久,车夫再一次叩问:“老爷?”
他回过神来,整了整衣冠,缓缓地从车中出来。车夫是柳宅的老人,朝上的高官也见过不少,只自家这位新贵与旁人不同。年纪轻轻已经做到了礼部员外郎,每日投帖拜谒的人跟赶集似的。据说,交往的贵人有的是天子身边的大红人,管着国家的钱库,收的金银珠宝堆得家里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这样的人,却天天皱着眉、黑着脸,也不知道成天愁个什么!
车夫送到,便赶着车去应承的地方等候。
刘禹锡早已到了,他看着格外热,似乎身体里烧着一个火盆。七月里,长安虽还有些暑气,但时候尚早,夜的清凉还未散去,柳宗元觉得心里堵着一块又硬又冷的石头。刘禹锡低声道:“东宫主政半日不到,朝中便有人公然以‘三竖’称先生,是可忍,孰不可忍!”
正说着,柳宗元目视前方,原本与他们歃血同生死的韦执谊正与宦官俱文珍领着一干侍卫驾马而过。神策军掌禁中防卫,控制了神策军便是控制了宫中的大势。
执谊倒戈,不见韩泰。
一路上都无人与他们说话,刘、柳二人颇有失落之感。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们舌战群儒,经常将人辩得瞠目结舌。今日,他们尚未开口,众人便绕开了。
延英殿议事,讨论了藩镇、灾情,临了宣布提拔一批人。柳宗元在心中有一丝存念,或许太子能萧规曹随,昨日政变就当从未发生过。陛下还在宫中静养,太子是仁孝的。
朝会结束后,柳宗元冒了一身冷汗,他心里堵塞的石块越变越大,垂坠着,时不时撞击他的胸口。刘禹锡也不似先前的急躁,沉默的脸上尽是不甘。凌准、韩晔几人也被疏远,很快就在四散的人群中显露出来。他们不敢多言,交换了眼神,各自回家。
长街上,他们遇到了一支重兵押送的队伍。刘禹锡先认了出来,大呼:“先生。”
王叔文没有应答刘禹锡,他垂丧着头,念念有词。旁人低声窃语,窸窸窣窣传着昨夜的惊变。柳宗元听清了王叔文嘴里念的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众人哗笑:“跳梁小丑,竟自诩诸葛孔明?”
王叔文出身低微,凭着高超的棋艺成为陛下在东宫时的侍读。他不由读书出仕,也非名门世家,参政总被人说成是小人得势。
八月,顺宗内禅,太子登基。这一年,王朝换了三任皇帝。正月里,德宗皇帝驾崩,陛下即位,如今才入秋,又换了一朝天子。
王伾贬开州司马,王叔文贬渝州司户,柳宗元知道二王都活不长了。一道一道严令压下来,他们什么也不能做,什么也不敢做。宅第前后都被看守起来,禁军也已搜过好几回。府中的奴婢大多遣散,只剩一些世仆在军吏的刀下战战兢兢。柳宗元抚慰母亲:“儿子为官数载,德行不亏,纵有冤枉,绝不至死。”门下看守的军吏冷笑:“死不死,由不得大人。”
九月,皇帝的诏令下:
京西神策行营节度行军司马韩泰贬抚州刺史,司封郎中韩晔贬池州刺史,礼部员外郎柳宗元贬邵州刺史,屯田员外郎刘禹锡贬连州刺史,坐交王叔文故也。(《旧唐书》卷十四)
柳宗元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自立太子那日起,他就预料到今日的结局。他听到了门墙外呜呜咽咽的哭声,问宣旨的中官:“何人新丧?”
中官袖子一摆,嘴巴一咧,语带嘲讽:“陆质死了,好些学生在哭呢。”
老师走了?
太子侍读陆氏文通先生,当代大儒,柳宗元一直将他当作老师对待,如今竟走了?
秋风渭水,落叶长安,肃杀的气氛笼罩京都。他的亲故为免受牵连,昨日已经商定,今日不来相送。眼下,除了母亲卢氏,便只有堂弟宗直、表弟卢遵相随。
马车渐行渐远,柳宗元回首眺望,太阳在西边落下,城墙上光影如水波涨起,长安城一点一点被地平线淹没,最终消逝在昏暗中。
长安日远,举目不见。
行路难
十一月,比寒霜更早侵袭而来的是一道追加的圣旨:
再贬抚州刺史韩泰为虔州司马,河中少尹陈谏台州司马,邵州刺史柳宗元为永州司马,连州刺史刘禹锡朗州司马,池州刺史韩晔饶州司马,和州刺史凌准连州司马,岳州刺史程异郴州司马,皆坐交叔文。(《旧唐书》卷十四)
此时的柳宗元,人还未到达邵州。南方潮湿的水汽中似有针尖,细细密密地侵入肌理、骨髓,让人无可躲藏。南下不久,柳母卢氏便染上了风寒。表弟卢遵去船家借炭火,船家神情古怪,两手一摆:“贵人身娇,多加忍耐,我们没有那东西。”
柳宗元要亲自去问,卢氏将他叫住:“小伤寒罢了,勿生事端。”一面又让取了银钱,让卢遵去与船家买些烧酒。
柳宗元取了袄子,替母亲盖上。卢氏道:“现下就穿袄子,再冷穿什么?”
“总有办法。孩儿不孝,让母亲受罪。”
卢氏抚着柳宗元的背:“我与乃父曾历天宝乱,往后所见的宦海沉浮并不算什么。”
安史之乱,柳镇年仅十六,柳宗元尚未出生。兵乱一起,就到处是抱头鼠窜的百姓。占了先机的王孙公子跟着陛下“西巡”,跟不上的都成了叛军的俘虏,长安城内一时成了屠宰场。一开始,他们以为只是暂时离乱,于是柳镇护送母亲避难王屋山。谁想北方皆被战火牵连,一打就是许多年。他们的粮食耗尽,料想南方还算太平,柳氏便举族入吴。太平盛世的过往像一场迷梦缠着逃亡的百姓,他们身上还穿着苏杭的绫罗,沿路的哭声像长安夜夜笙歌的回响,人生富贵繁荣像上天的游戏,随意放置,随意取走。
到了江南,在这毫无根基的地方,族人所剩的银钱并不足以支撑开销。战乱使米价上涨,北方的田产是不能指望了,他们只能典当、借贷。江南人精明,专做他们这些落难世家的生意,他们无以为食,便只得将祖传的物件换几斗米。柳氏家道中落,没什么可抵押的,族中子弟过惯了养尊处优的日子,除了读书,就是等死。柳镇便扛起了维持家道的重任,采买、交涉等事都由他去。他是正房嫡孙,只能硬着头皮去受冷眼、受奚落。
一日,柳镇去城郊借贷,天晚下起了暴雨,他连夜赶回,路过山涧,却遇上山洪,将他冲走。族人见他一夜未归,以为遭遇不测。第二天让家中的男人去寻,寻了半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正要放弃,却见山坳里一个泥人缓缓蠕动,向他们爬来。
众人确认是他,不等他开口,已先哭出声来。柳镇却颇为镇定,只是道:“青驴死了,粟米都进了河里,白白浪费了许多粮食。”
“你的父亲一生都在为他人洗冤,自己也蒙受了许多冤屈。”
柳镇有王朝最硬的骨气和头颅。他在汾阳王郭子仪门下做文书,一步步升到大理评事,掌刑法。军中将领野蛮不讲理,更无法纪,随意惩处下属,决人生死。柳镇据理力争,以书生文弱的身躯护在无辜的兵卒身前,代受鞭笞。那裨将施展不开,又怕将柳镇打死,不好与上峰交代,只得作罢。如此顽抗了几回,大家都晓得柳氏子是直肠子、硬骨头,是个认死理的倔牛。军中人虽无礼凶蛮,却服他的硬气,因此不再以言行侮辱。
柳镇回到长安,做了殿中侍御史,一个从七品下的京官,随后又陷入了一桩遗产争夺案。贞元四年(788),陕虢观察使卢岳死,他的妻子分家却不给妾裴氏及庶子财产。裴氏不忿,状告正妻,御史台卢佋偏袒正妻,要治裴氏重罪,责令下属侍御史穆赞审理。穆赞不听,还了裴氏公道。当时的权相窦参正与卢佋狼狈为奸,因此寻了个罪名诬陷穆赞受裴氏贿,将他下狱。柳镇打抱不平,为穆赞敲登闻鼓鸣冤,争取到一次三司会审的机会,为其平反。柳镇因此将窦氏及其上司彻底得罪,虽赢得一时令名,却难逃排挤,过了些日子就被寻了个错处,贬到夔州。
柳宗元当时正在准备考试,不能随往,他早慧天才,是家族的希望。那时柳镇已经年过五十,夔州阴湿,尤易致病,此次放逐,有生之年恐怕都不能得见。柳宗元永远记得送父亲到蓝田时,他倔强的面孔与决绝的话语:“吾目无涕。”
柳镇在夔州待了三年,直到窦参被贬死去,陆贽陆相公主政,他才得以返京。但是天不假年,回到长安不过一年,柳镇便病死在家中。
永贞时,柳宗元得官尚书吏部员外郎,陛下曾欲追赠柳镇,可陛下内禅,他因罪被贬,这件事就不了了之。柳镇从未身居高位,但一直在是非的漩涡中,朝廷之事瞬息万变,他从来都能秉持正道,为正义而活,为正义而死,虽然一生颠沛流离,却问心无愧。而如今的柳宗元,万人唾弃,从天子到朝臣,从奏议到史书都将把他录在佞臣之列、名在刑书,与那些父辈不耻、不屑、不忿的宵小为伍。世泽家声,在他手里毁于一旦!
卢氏知他心中郁结,不免开导:“我儿当知,不论是柳氏还是卢氏,虽世代为官,但没有哪一身官服来得容易。我儿颇肖乃父,性格刚直,易与人为敌,骤然得势,难免为人所妒。这一贬也好,懂得惊惧慎戒,未必不是修身之道。”
柳宗元垂首听训,母亲出自大家,向来颇有见识。他安置了母亲,出来甲板透气。
另一艘船头,刘禹锡已饮了半壶酒,举杯相邀,柳宗元摆手婉拒,他心中有事,易醉,但照应卢氏仍需保持清醒。
“是否我们的仕途太过顺遂,德不配位?”
比起柳宗元,刘禹锡要更加幸运,他连中三科,都是一试即中。他们都是少年天才,一路又有德高望重的前辈为其扬名,科考顺,做官顺,没有遭受什么挫折。便是入朝,资历虽浅,却不把人放在眼里,确实不能和杜佑、权德舆等前辈相比。
刘禹锡哂笑:“你记不记得李实?”
李实,柳宗元当然记得。
“他才是德不配位。”
李实是宗室子,道王元庆的玄孙,凭着荫封入仕。贞元十九年(803),他担任京兆尹,刘禹锡和柳宗元都曾在他手下做过事。李实目无法纪,随意残害百姓。贞元二十年(804),关中大旱,百姓饿殍遍野,德宗皇帝问民间疾苦,李实说:“今年虽旱,谷田甚好。”德宗听了,便自欺欺人地相信了。于是,租税照旧,百姓为了缴税倾家荡产。京中有人因戏作语,将其暴政编成曲子传唱。李实怀怨,向德宗进谗言,德宗即令杀了作曲之人。那几年,仗着德宗皇帝的宠信,李实弄权,把手伸到了三省六部,连官员升降都要按他的意愿来执行,被他害死的人,从官员到百姓,有几十人之多。
刘禹锡说:“这么厉害的人是被我们参奏的,别人不敢,我们做了。”
是啊,是他们。他们是初生牛犊,没有根基也就没有顾忌,其他大臣或为明哲保身,或和光同尘,都敢怒不敢言,是他们直愣愣地,借着陛下的力量将其贬黜。李实离京的时候,百姓纷纷出动,备了瓦片石头要将他当街砸死。李实不得已,自西逃窜,最后死在任所。
忆起这段往事,柳宗元仍觉振奋,在礼部员外郎任上,是他为官最有意义的时候,他没有浪费一天。李实才是遗臭万年的恶人,其错事人人都可评判,而他与刘禹锡则不同。他二人现在是输了,但是未必错了。
刘禹锡想得通透,他改贬的地方在朗州,旧时称武陵郡。这一路来,他遭受的诟骂、冷遇不比柳宗元少,但他性子豪放外向,看起来并不很往心里去。大概,在刘禹锡看来,这就是一次平常的贬谪吧,宦海沉浮,起起落落,再正常不过。
元和元年(806),先帝顺宗下葬丰陵。随后,当今天子颁下一道圣旨:
左降官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等八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旧唐书》卷十四)
一息尚存
去往永州途中,柳宗元曾在岳父杨凭的治所潭州盘桓了几日。杨凭时任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他的本性疏荡,是当年有名的才子,与弟弟杨凝、杨凌并称“三杨”。岳父早岁受德宗皇帝赏识,征为监察御史,但因不喜约束自己,也不喜检束别人的过失,便求免官。
杨凭在朝中各部都做过,这两年才到地方做一任要员。德宗皇帝晚年对地方的约束相对松散,这样的政治氛围正适合他。杨凭喜欢奢侈的生活,心高气傲却重诺,颇有一点豪侠的气派,他对不喜欢的人从来不假辞色,因此朋友多,敌人也不少。
杨家与柳家是世交,女儿与柳宗元的亲事在他们幼时就定下了。虽然女儿早夭,但两家的情分却在。杨凭对柳宗元是很看重的,况且这位女婿性子虽不肖他,才华却过于他。此次,柳宗元左迁永州,杨凭从容地接纳了他。几番勉励鼓舞之后,杨凭带女婿去了一些自己时常游玩的地方。
东池为戴氏所有,环之九里,水中小洲错落,水岸曲折蜿蜒,像一块玉玦。柳宗元见此美景,暂时放下了心事,畅叙幽情。杨凭向柳宗元介绍主人戴简,他是名门之后,虽有文名,却不愿出仕。
“嗣仁品性谦逊温和,与人为善,与山水为伴,在这里过得颇为潇洒自适。”
柳宗元有感,写了一篇文章《潭州杨中丞作东池戴氏堂记》,他夸赞东池名胜和戴氏风度,寓意弘农公得其政。杨凭看到文中“既硕其内,又扬于时,吾惧其离世之志不果矣”等字样,笑而不语,这个女婿念兹在兹,一时是无法从功利事中解脱了。杨凭还要多留他几日,柳宗元思及自己是新朝罪臣,不敢耽搁,随即带着母亲与族弟、表弟去往贬所。
在外人看来,柳宗元的处境虽然不及往日,但也没有糟糕到一败涂地。可事实如何,只有他自己知道。人在痛苦时,有时别人的探问都是搅扰,他需要独自嚼咽,慢慢将心中那块大石消化。
一路,除了向母亲问安,柳宗元便独自一人看书、写字,对着江面,静默沉思。他凭吊苌弘、屈原、乐毅,下笔成文,心中的愤懑愈发激切。偷风不可去,直道无所施,接下来的日子,他着实不知该如何应对。
彼时,永州的刺史姓韦,一番例行公事的盘问后,便将柳宗元客客气气地送走了。柳宗元所任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是个极低微的官职,没有官舍,他又是戴罪之身,旁人都不愿招惹他,更不敢施以援手,柳宗元只好带着母亲寄住在龙兴寺。所幸,柳宗元从小便与佛教有所接触,龙兴寺的住持重巽又是个颇有学识的高僧,住在佛寺倒合他现在的处境。
龙兴寺照柳宗元的说法,乃“佳寺也”,但它的位置还是较为偏僻的,寺庙也有些破落。柳宗元住在龙兴寺的西边,房子朝北,室内终年都很阴暗。柳宗元想了一个办法,把房子拓出去,造了一个有多面窗户的小屋,这样不仅改善了屋内的光线,树木的枝条可以在窗边舒展,而且将四周的美景尽情收纳。
他努力适应现下的生活,佛家的一些道理冒出头来,恍然间,他有了感触,便随手记下:
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遗言冀可冥,缮性何由熟?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日出雾露余,青松如膏沐。澹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晨诣超师院读禅经》)
他与佛教的亲近吸引了许多僧人不远万里而来。当然,这是后话了。
刚到永州之时,柳宗元是很煎熬的。因为元和元年(806),宪宗皇帝追加了“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的诏令。也就是说,只要宪宗在位,他就永远不可能有翻身之日。而年轻的宪宗皇帝确实显示出了一个精明强悍的君主的所有气质,才登基不久,就收了剑南西川作乱的刘闢、斩了反叛的杨慧琳,给藩镇一个下马威。从历史上看,宪宗确实有些作为,后世将他在位期间较为安定繁荣的局面称为“元和中兴”。
永州的春夏闷热,寺庙四周多有草植,时有山火,柳宗元住的地方被焚毁了好几次。惊悸的情绪加上恶劣的气候,让卢氏的病情雪上加霜。永州没有好的大夫,柳宗元买不到必需的药材,也无力为母亲置换好一点的生活环境,只能做些于事无补的尝试,缓解母亲的病痛。
五月的一个夜晚,柳宗元在母亲帐前为其驱蚊、守药。一直昏迷的卢氏醒转,她伸出枯柴一般的手握住柳宗元,浑浊的目光中闪着不真实的光。柳宗元忍不住颤抖,他知道母亲的大限到了。
未等卢氏开口,他已泪如雨下,跪在床边。卢氏知他,这个孝顺的孩儿将背负一生的罪责,她细细叮嘱,宽慰道:“明者不悼往事,吾未尝有戚戚也。”她心里放心不下儿子,她教育出了一个好孩儿,教他修身、齐家、治平,却没有教他如何过上顺遂的人生。儿子什么都往心里去,排解不开,只能让自身变得坚强、冷硬。而作为母亲,她除了陪伴,什么也帮不上。现今,她也要走了,将他一个人孤独地留在世上。

[唐]韩愈作,[宋]苏轼书《荔子碑》原刻拓片
侄儿卢遵也已来到床前,卢氏紧紧握住他的手。她喘不过气,虽勉力撑着,但沙哑的声音断断续续被泪水覆盖。卢遵没有听清,却明白姑母所愿,他是要跟着表兄的,从决意离京那刻起便要和表兄同进退、共患难。卢遵不住地点头、应答,这位谨慎朴实的青年一直相随,直到柳宗元死去。
卢氏留下了一声叹息,溘然长逝。
身居陋寺,死后诸事便宜。卢氏有诰命在身,为河东县太君,按照唐朝礼制,丧礼当庄严隆重,不过现在只能将就。柳宗元跪在殓前,寺僧为超度所念的经文就像母亲的低声絮语。他想起自己少时,长安爆发“建中之乱”,母亲带他避祸长安城西郊的时光。那时父亲在吴地李兼门下做幕僚,不能团聚。家中没有藏书可读,于是母亲口授古诗文,一点一点地教他。他的记忆力很好,母亲讲解一遍,他便大致能背下来,这个时候母亲就格外高兴。闲暇时,母亲会与他讲柳氏和卢氏的故事,一些没有记载在史书上的先祖事迹。她知书达理,温柔耐心,没有人不称赞她的德行。柳宗元被贬时,卢氏本可在京养老,卢、柳的亲族虽然稀少,但也不会不顾她。大概是老夫人预料到此次离京当是永别吧,所以才跟着儿子一路颠簸。炎暑熇蒸,寿命骤减。这样好的人,一世与人无怨,却因儿子的罪愆而过早离世。
这一年,被贬到连州的凌准遭遇了比柳宗元更甚的不幸。凌准被黜,他的母亲没有一同前往,在祖宅抑郁而亡,紧接着两个弟弟也相继死去。凌准长柳宗元19 岁,他早立功勋,在德宗年间不管是治学还是平乱、理政都很有成绩,但他能以谋略使奸吏衰止,却不能以官势护佑家人安宁。柳宗元在凌准的悼亡诗开篇言:“废逐人所弃,遂为鬼神欺。”或许是世态炎凉,凌准的母弟遭受了乡人的欺凌。凌准不能回乡为母亲料理丧事,终日以泪洗面,以至于哭瞎了双眼,最终抛下了两个孩儿,死在桂阳佛寺。
高堂倾故国,葬祭限囚羁。仲叔继幽沦,狂叫唯童儿。一门既无主,焉用徒生为!举声但呼天,孰知神者谁?泣尽目无见,肾伤足不持。溘死委炎荒,臧获守灵帷。(《哭连州凌员外司马》节选)
这一年,王叔文被宪宗赐死,而背叛了他们的韦执谊也没能逃过跌落的命运,去到了自己的死地——岭南崖州。
有好事之人,想见不可一世的柳子厚落得怎样境地,特来永州探问:“我见你目光明朗,气度犹胜以往,真是可喜可贺。”来人不知,嬉笑之怒,甚于裂眦;长歌之哀,过于恸哭。母亲至死不作戚戚之态,他也不愿向命运摇尾乞怜。
也是在这一年,存了死志的柳宗元选择活下去。大概是因为凌准带来的触动,柳氏不能无后;也可能是三十余年所建立的信念与价值观,让他守住了为人的理性;也可能只是坚韧的生命意志在告诉他,活着,看看世界还能糟糕成什么样子!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