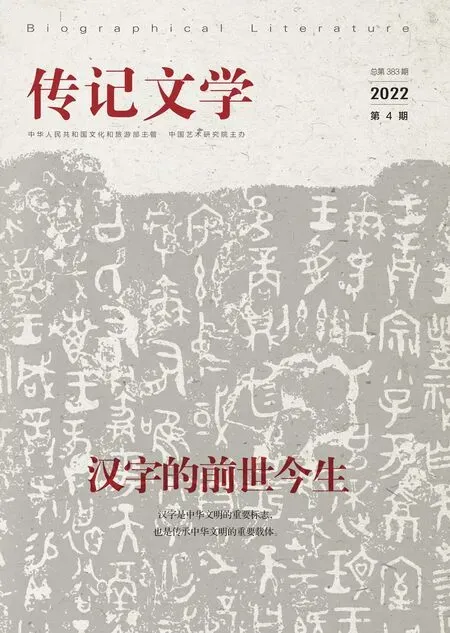游击队员在136街
刘大先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2009年9月的某一天,在经过了十几个小时的航行之后,我终于抵达了纽约。飞机在哈德逊湾盘旋了一圈,我坐在窗口,看到底下楼宇历历在目,心里颇有些轻松。我终于要摆脱在北京的琐碎日常,要在哥伦比亚大学开始一段无人干扰的生活了。此前的一年,我刚刚博士毕业,一边上班一边写论文的日子实在是太辛苦了,因而一旦有机会,我赶紧申请了出国的项目。
学校在百老汇116 街,我住在西136 街斜下坡的一幢开着绿色大门的公寓楼里,与另外三个人合租一套三居室,住其中一个房间,卫生间和厨房共用,就跟中国社会科学院在通州给刚入职人员安排的单身宿舍差不多。这里是贫民区,主要住的是来自西班牙、墨西哥和波多黎各裔的一二代移民,很奇怪地被包围在黑人区之中——往南的125 街和往北的140街左右据说都是黑人区。好在这些邻居们谨小慎微,基本上还算安全,尽管有些人往往无论白天黑夜坐在楼洞门口无所事事、聊天或者听音乐。几乎每到周末,这些芳邻一大帮人开party,能喧嚷到凌晨三四点,虽然让人不堪其扰,但因为这里距离学校不算远,也勉强可以接受。
我知道有许多国内的访问学者都住在皇后区的法拉盛,那里是华人较多的区,地方倒是便宜(能便宜一半房钱,大约套间里的一个房间也就是400 美元多一点),但是到学校需要花一个半小时,并且不用说一句外语就可以生活,没有语言环境,所以我没有选择那里。从绿色大门往西走很快就到哈德逊河边的河岸州立公园,可以看到原先的建筑是弗兰德式的,很见气派,据说以前是荷兰富人们住的,后来他们都搬到类似长岛那样的地方去了,如今这里成了拉丁裔的聚集区。公园周边是网球场、溜冰场和垒球场,都是沿河而建,可以看到北面不远处通往新泽西州的高速路桥。新泽西是花园之州,但是在那边租房子没有车几乎不可能,而每天来回的过桥费对我而言就挺贵。
安顿下来之后,生活变得非常简单:白天到学校上课或者在图书馆看书,晚上回到宿舍睡觉,闲暇的时候去逛美术馆、听音乐会、看戏看电影。尽管国家给予的资助并不丰厚,但可以维持日常开销。这个时期的访问学者不再如同改革开放初期时那样存在一定经济压力,相对而言生活和精神上都要轻松很多。现在回想起来,初到美国,我丝毫没有“文化震惊”之类的反应,毕竟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便捷的交通和网络已经让文化沟通尤其是学术交流变得日常化。当时刚刚成功举办的北京夏季奥运会无疑展示了中国和平崛起的综合实力,很明显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重提升了,中国学者的声音也日益得到重视。大学校园基本上还属于一个较为独立的场域,对于心无旁骛、只想读书的我来说,简直称得上如鱼得水。
访学并无明确具体的任务,我选了几门课,以免过于信马由缰,同时可以获得课程大纲,那上面一般会附有推荐阅读的书目或论文,是很好的指南。这个时候网上已经可以找到各种常春藤名校的课程视频资源,但是看视频总归没有课堂的现场感和即时互动的讨论,后者可能更重要。听课与讨论让我重回到读研究生时候的状态,固然艰苦,却有种在山阴道上行走,满目美景应接不暇之感。纽约给我的感觉类似北京,在这个陌生人麇集的都市,everybody from everywhere,没有人在意你的背景、衣着等诸如此类的东西,万人如海一身藏的感觉,让人有一种隐秘的欣喜。我奔波在各个学校的楼宇和图书馆,游走于博物馆、音乐厅和剧院,如同穿梭在丛林中的游击队员。
课程当然没有那么轻松,事实上绝大部分指定阅读材料我都未必能够在上课前读完,大部分时候都要阅读到凌晨两三点。我的室友有两位是学电子工程的硕士,也非常刻苦,从来没有在我睡觉前回来过,当我早上八九点钟起床时,他们已经去学校了,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同他们打过照面。高强度的学习就像是体育运动的极限训练,可能会在不长的时间里让人的视野与思维得到强化和突破。
在最初申报研究计划的时候,我写的是寻找域外少数族裔相关资料,但因为硕士时候攻读的是西方美学专业,内心中还是对理论充满了热情。最初选的课程就是《当代理论的背景》,内容主要是美国与欧陆理论的关系,尤其是德法哲学的影响。这门课的主讲教授布鲁斯·罗宾斯是“新世界主义”的倡导者,他的妻子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原住民权利委员会工作,对我关于少数民族的研究很有兴趣,我们聊得比较开心。从整体的学术话语来说,20世纪理论的热潮已经退去,中外信息不对称的因素也在减少,我们这一代人显然不太可能如同前代学者那样,靠述介外来理论便可以立足学界,我个人也不愿意将自己的精力完全用在研究某个大家比如福柯或者海德格尔之上,但理论依然是面对材料与现象时的基础。由于博士阶段攻读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彼时已经五六年不太关注西方理论,所以课上关于巴迪欧、齐泽克、列维纳斯、阿甘本这些时髦学术明星的讨论,让我觉得还是有些收获的。
追逐学术时髦热点与粉丝追星从情感本质上来说是一样的,像特里·伊格尔顿、齐泽克、巴迪欧、朱迪斯·巴特勒、查尔斯·泰勒这些大腕到纽约讲座,我总是像少女去见偶像一样满怀激动,其实也没听懂多少。记得有一次去听巴里巴尔的讲座,此人是阿尔都塞的弟子,被称为法国最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罗宾斯竭力推荐我去听,会场人头攒动,但我根本什么都没听懂,一方面是英文程度有限,力有未逮;另一方面是睡眠不足,居然睡着了。那天觉得一无所获,晚上心灰意冷,躲到图书馆自哀自怜。无意中看到一本书叫《异见者说》(),其中有位埃及学者萨达维(Nawal El Saadawj)写了篇《异见者与创造性》()。这位母语是阿拉伯语的教授在杜克大学教书,看来对德里达之类的后现代理论不感冒。他写到一个轶事,说有个朋友一次到杜克开会,德里达在会上发表了个演讲,结果那位阿拉伯老兄跟我听利科(Paul Ricoeur)的感觉一样,满头雾水,心里受不住,晚上回去就做了个噩梦,梦见德里达用双手掐他的脖子,他都快窒息了。萨达维女士于是感慨:后现代主义之害,为祸甚深啊,它们是知识恐怖主义(intellectual terrorism)!
话虽这么说,我从接触文艺理论开始,基本上就身处于总体性瓦解的后现代氛围之中。可以说,经过尼采,那种体系性的哲学建构就失去了合法性,此后是林林总总的“理论”,都不再具有统摄性的意义和权威。我读书时虽然是从古代经典开始,但它们只是构成了知识背景,真正产生影响并内化为思维和方法的还是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后殖民这些新兴理论。这无形中可能造成了在学术品格上某种难以归纳的游击性——不会遵从哪一家的学说,或者哪一派的“家法”,没有什么门户之见,也缺乏所谓的学科边界意识。理性认知中,我知道在所谓的“学术界”,咬定某个主题深耕细作是正统路径,如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则会被认为游学无根,但我性格上比较跳脱,徘徊于易感与深沉之间,从为学路径上来说一直属于自由生长的状态。
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去外婆家玩,小舅曾经给我出过一个脑筋急转弯,问你最了解的人是谁?我立刻就给出了答案:自己。按照标准答案,这是对的,不过小舅认为,话是这么说,但其实人很难真正了解自己。我当时不明所以,隐隐觉得也有点道理。现在回想,小舅那个理工男将原本轻松的娱乐上升到了哲理的高度,当然他适时打住了,可能觉得跟一个小学生无法进行更深层次的讨论。这个问题涉及到人的自我认知,关乎“我是谁”这样根本性的话题。
我是谁?即便到了今天说起来,我也一片茫然,可能外界对我的印象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当代文化批评者、学术期刊的编辑,但人的社会角色、职业和身份有着不同维度和层面,在不同的场合呈现出不同的面目,并且随着语境的变化和自我的成长会有所变化与侧重。就职业生涯而言,我感觉自己就像唐德刚对胡适的一个评价,大致的意思是胡先生在各种文化运动中如同中药方中的甘草,哪一剂都少不了,却也从来不会成为主打药,而是一个药引子。我涉足的领域从人文学的角度而言比较广泛,在文艺理论、影视研究、少数民族文化、近现代与当代文学方面几乎都写过文章乃至出过书,在专业化的学术分科中这是一个忌讳,就像一个没有根据地的散兵游勇,但我倒是挺欣慰自己并没有被某种单一形象所定型,换言之依然保持了开放的生机和多种可能,而思维的活力就潜藏在这种生长性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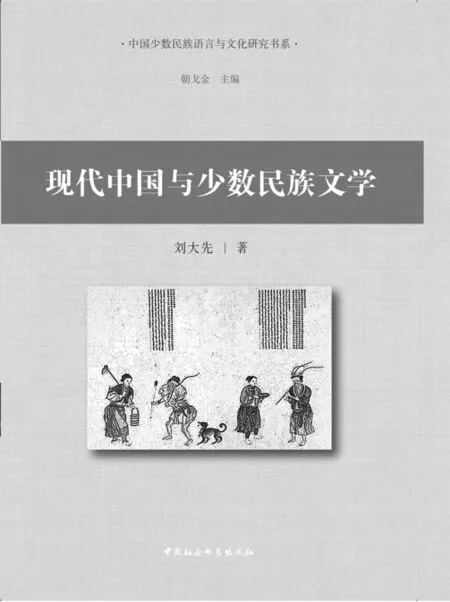
刘大先:《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
坦率地说,虽然从事文学事业,我对文学并无特殊爱好,只是喜欢读书而已,读书也更多钟情于智性的启迪而不是华美的修辞。暨南大学的赵静蓉这个时候在哈佛访学,我们2006年在一个文学人类学的会议上认识,一直有联系。她经常打电话跟我聊天,说被霍米·巴巴弄得很沮丧,后者的英文佶屈聱牙,反倒比英美本土的学者在修辞上要繁难。我那时候也在读《文化的定位》(),深有同感。当时正值余英时在中国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未尽的才情——从〈顾颉刚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不久,她读了后找来《顾颉刚日记》看,发现余英时过于强调谭慕愚对于顾的影响,浪漫化了二人的爱情,实际上到最后顾谭二人彼此都无甚感情。晚年深刻影响了顾颉刚的其实是张静秋。“千古文章未尽才”“堪叹古今情不尽”种种,免不了余英时本人的主观臆断甚至有意为之。赵静蓉看到许多细节,比如张静秋晚年因为逼迫顾颉刚去参加运动和思想学习,乃至动手殴打顾,她想探讨一下三个女人(殷履安、谭慕愚、张静秋)对于顾颉刚本人的影响,这个大约也是她关于“记忆”研究的一个案例吧。
我没有赵静蓉那样有个一以贯之的研究主题,兴趣点颇多。因为工作的原因自然要关注少数民族及其文学,关于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的阅读也是源于此,但我很快发现后殖民理论必须结合其产生的历史与社会背景,印度经验与中国相去深远,包括我从2000年左右就开始接触的萨义德,也只能是对其方法上进行借鉴。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试图引入美国少数族裔批评,为此在到美国之前做前期准备还翻译了骆里山(Lisa Lowe)、谢利·费希尔·菲什金(Shelley Fisher Fishkin)和韩瑞(Eric Hayot)的一些论文。亚裔和拉丁裔文学研究路径一般从移民法(Migration Law)和全球资本主义(Global Capitalism)两个方面入手,黑人文学更多涉及历史遗产与种族遗留问题。race 和ethnicity 之间有着鲜明的区别,《美国新移民文学》(.)是很好的参考书,美国少数族裔作家将race 这个词义转换为一种反抗的运用,这些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生与关怀大相径庭,无疑也颇有意思。
虽然少数族裔批评理论方面的译介我后来并没有继续下去,但是它们所通向的历史和法律问题让我对涉及到种族文化差异的话题有了更深的理解。我所住的地方算是泛哈莱姆地区,从宿舍到学校中间虽然只隔了20 个街区,步行顶多也就是20 分钟,但是116 街和136 街显然已经不是同一个世界——把它们分开的就是125 街。125 街是个东西贯通的大道,站在阿姆斯特丹大街和125 街的十字路口,可以看到北面有个Mink Building,上面写着“Where downtown meets uptown”。其实从地理上来说,哥大也就是上城了,但是如果从文化心理上来说,过了125街才是真正的哈莱姆上西区,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125 街绝对是个值得做个民族志的地方,我很早就听过种种有关此地的传闻,无外乎相关抢劫、吸毒、暴力之类,有好心人还叮嘱我兜里一定要揣点零钱,万一遇到有人要钱,就直接给他,不要发生冲突,因为你不知道他有没有吸毒或者持有枪械。
第一次去125 街,是一个从俄克拉荷马过来的朋友喊我一道去那里的一个店买东西。他带我绕了半圈,顺着阿姆斯特丹大街走到125街,我很奇怪为什么不从城市学院那里直接穿过去,他说那里不安全。半路看到一个建筑上写着“哈莱姆之心”,却是个救火队。然后就是著名的阿波罗剧场,据说迈克尔·杰克逊就是在这里起家的,他去世的那段时间,整个125 街都是直播车。此时经过还可以看到附近的墙上都是涂鸦签名,最大的当然是:迈克尔·杰克逊!这一块就是哈莱姆区的中心了,街道两边遍布着各种各样贩卖图书光碟、印度香料的小摊和各类人物。

本文作者在阿姆斯特丹大道
经过第七大道是一个小广场,我看到一个穿着西服、挺胸向前、颇有些革命风范的雕像,夜色中看不清。走近了发现,雕像底座写着Jr.Adam Clayton Powell,坐在上面的两个老瘦的黑人冲我挤眉弄眼喊话,我也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他们就在那里自得其乐地呵呵笑。我打算过去细看一下雕像介绍的字,室友不让我过去,说这里是流浪汉的天堂,我们走快点。Powell 是第一个进入国会的非裔,1945年至1971年是纽约曼哈顿哈莱姆区国会议员,并在1961年成为教育和劳动委员会主席。2002年,他被非裔学者阿桑迪(Molefi Kete Asante)写入100 个最伟大的非裔美国人名录中。

刘大先:《文学的共和》
一般人对于纽约的想象往往都是由大众传媒的符号构成的,自由女神、帝国大厦、华尔街、第五大道、中央公园……很少有人会在意哈莱姆的底层生涯。我来纽约之前不久,正好出了个来自世界各地的12 个导演合拍混剪的电影《纽约,我爱你》,大约最能体现人们对于纽约的想象:暧昧、欲望、孤独、多元,每个人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所有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但是当我每天走在路上,那些小资式的想象就完全灰飞烟灭了。我知道那是事实的一个部分,在林肯中心、在百老汇、在华盛顿广场,还有更残酷的真实。
在马丁·路德·金节的一个活动中,我又一次去125 街参加一个纪念黑人民权运动的活动。我记得当时与会的人回顾了美国民权运动的历史从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是与当时的国际反法西斯运动相平行的国内反法西斯运动,不仅强调的是政治权利(比如选举),更主要的还是在于经济权利(比如就业)。印象最深的莫过于结束的时候,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说奥巴马虽然是黑人,也不可靠,我们要靠自己争取权利。马丁·路德·金如今也已经成为美国文化的一个符号,在他的节日举行这样的活动却只是茶杯中的风暴,在现实生活中发不出多大的声音了——他们放弃了马克西姆·X 的激进道路,也没有在制度和文化教育层面进行深层次的变革,只会酝酿更为激进乃至走偏了的行为,又两届总统之后发生的BLM 运动是后话了。
我在百老汇剧院看过一个戏《邻居》,通过居住在对门的两户人家——一户是底层从事通俗娱乐表演的黑人家庭,一户是中产阶级黑人丈夫和白人妻子家庭——的参差对照,表现根植在美国文化深处的种族主义无意识。其中突出地体现在中产阶级黑人身上,剧情的矛盾并不起于他与白人妻子,而是集中于他与同为黑人的底层家庭之间的矛盾,这样就把种族问题与阶级问题纠合在了一起。因为将白人作为完美的人格范型,这个中产阶级黑人努力想要做的就是摆脱他的先天黑人因素而成为一个白人,如果外表上做不到,那么至少在价值观、道德和价值尺度上也要努力去靠拢(这有点像菲利普·罗斯的《人性的污秽》)。身份认同上的错位造成了他的性格上的内爆和精神分裂。在舞台设计上导演颇具匠心,尤其在戏剧结尾的时候,底层黑人家庭说“表演开始”,然后静立在舞台之上,凝视着观众,背景则是中产阶级家庭夫妻俩在撕扯。这个设计造成了“看”与“被看”的换位,底层黑人在看观众,观众看到的“表演”却是后台的中产阶级黑人家庭,这就使得处于前台的底层黑人获得了主动性,在整个场景中由原先的“被看者”(从事低俗表演)成为“观看者”——审视观众们内心深处的种族观念。不过,这样的“文化政治”在现实中显得颇为无力,这可能是文学艺术本身在我们时代无力的体现。

刘大先:《八旗心象:旗人文学、情感与社会(1840—1949)》
还有几门课印象比较深,《比较文学入门》是刘禾教授主持,说是入门,其实是给博士生的课,因为每次课都要读很多原典,以我的阅读速度根本读不完,我问那些博士生,他们基本也读不完。这个课程听课的人不多,但生源驳杂,来自历史系、古典学系、建筑系、电影系、艺术系、文学系和人类学系的不同系别。这门课关注现实前沿,后人类、新媒体什么的也有专题,每次课刘老师都会请涉及到的相关学科的教授来讲下半堂课,形式很有意思,像做图像学研究的W.J.T.米歇尔、人类学家阿帕杜莱、做新媒体研究的马克·汉森(Mark Hansen)、日本文化研究者哈如图涅(Harry Harootunian)等人都来过。我印象深刻的有一次课是乔治·萨里巴(George Saliba)来讨论伊斯兰的科学对欧洲文艺复兴的影响,还有一次是安德鲁·琼斯(Andrew Jones)讨论中国爵士乐对美国音乐的影响。不过,我大部分情况下都张不开口,因为阅读材料都没有消化,只有某一次讲到地方性知识和文化翻译,还有一次是日本战后大众文化,这两个话题我略熟悉一些,才能参与讨论。这种“比较文学”的理念突破了所谓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是真正的跨学科,或者可以说就是广义的“文化研究”,同我的想法和兴趣接近。
《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这门课接受起来最简单,我的博士论文就是《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前期有一定的思想史与文化史积累,果然是自己有多大瓢才能舀起多少水。课程安排是每次围绕一个主题,讨论过老舍与笛福、萧红与女性主义、萧乾与旅行文学、韩少功与语言变异、张爱玲与音乐、王家卫与香港、王安忆与上海、聂华苓与历史、徐冰与符号、北岛的诗歌,等等。内容对于我来说虽然谈不上新鲜,但是收获倒是最多的,主要是视角和观点的启发。“独立研究”课没有老师,就是我和东亚系以及比较文学系的博士生,像美国的Anatoly、以色列的Gal、印度的Arulabu、国内清华过来的钟雨柔,每次大约五六人讨论各自心得。我们共读了章太炎、梁启超、康有为、林纾、何震,以及电影史的一些著作和文章。我主要是去练习说英语,大家彼此大约都会从对方那里学到一些东西吧——大学的好处就是有一群知识、志趣、智力水准接近的人,同学之间的交往互动,往往比从老师那里受益更多。
课堂学习和课下阅读占去了绝大部分时间,我对纯粹外出旅游没有太大兴致,春假和暑假期间从俗,跟室友去华盛顿、布法罗、弗吉尼亚、田纳西几个地方随便转了转,很快就又回到136 街,也许我以前游玩的地方、虚度的光阴太多,眼见进入而立之年,迫感时间有限,不能浪费。刘禾老师可能看我好学,替我争取了一个工作,辅助她上一门课,这样就有了一定的收入,可以支持在国家留学金基金委的资助到期后延期生活的费用,对我也是很好的学术训练。许多年后,我依然对这个善意心存感激。
来美之前,我没有任何的海外联系,一无所知地在自己的命运中东突西进。曾经和外文所的钟志清聊过,她是浦安迪的学生,但我最终没有和浦安迪联系,自然也就没有到普林斯顿,只是中间抽空去普林斯顿、哈佛、麻省理工匆匆一游。我从未上过名校,这也算是人生遗憾吧。走马观花没有什么印象,只记得到离普大主校区比较远的Fuld Hall 是爱因斯坦的办公室,屋后是大片草地,雄浑的树木,有一口千年的老池塘,落叶纷飞,夕阳西下中,沁人的美。然后就去研究生院,教堂式的老建筑,干净、幽静、娴雅,没有什么人,是读书研究的好地方。

刘大先:《千灯互照: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生态与批评话语》
这期间又来了两位新的访问学者,一位是做戏剧的陶庆梅,一位是做建筑学的林鹤。林鹤原先在清华大学任教,写过《西方20世纪别墅二十讲》,翻译过几本大众文化研究的著作,因为身体原因已经辞职移居纽约给孩子伴读,她到哥大学习是非常纯粹的自我提升。我们经常结伴去看戏、听音乐会、到刘禾、李陀的寓所聊天。他们家周末或者节日时候往往高朋满座,像冯象、徐冰、商伟、卡尔·瑞贝卡、高彦颐、包卫红、林凌翰、欧阳江河、于晓丹……仅仅听那些来宾的交谈就能得到许多耳食之学。我最快乐的时光就是默默坐在一边听他们议论风声的时候,偶然灵光一闪听到的词语,顺藤摸瓜,可以勾连起学术史意味的话题。比如,有一次我同林鹤聊到建筑史和建筑现代主义的问题。现代主义建筑强调的是功能,比如玻璃在建筑中运用的变迁。一方面,尽管玻璃很早就出现,在中国至少在汉代就有琉璃瓦,但是由于技术的限制,不能大量生产,从而造成它的昂贵,于是进一步形成了富足奢华的象征含义。另一方面,由于玻璃的透明性,从身体角度来说,玻璃将原本被不透明的墙区隔开来的外部空间可视化,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第三方面,玻璃的使用还有在工艺自身发展的进程的“炫技”(spectacle)的意味。玻璃的大规模使用并不很早,大约是从17世纪末才开始,最初是用于博物馆(比如水晶宫),然后是用于工厂等场所,最后才是民用建筑。这是一个现代性的过程,如果做文化史,“玻璃与现代性”就是一个很好的题目。
所谓耳食之学如果有意义,显然不是停留在听到一些支离破碎的观点或掌故,而是一个开启新旅途的契机。比如关于安托南·阿尔托的“残酷戏剧”,后来就引发了我对东亚“极端电影”的思考。“特修斯之船”的典故也不禁让我想到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身份”问题:一艘可以在海上航行几百年的船,在不间断的维修和替换部件的过程中,终究有一天船的所有功能部件都不再是最初的那些。那么,这艘船是原来的那艘船,还是一艘完全不同的船呢?如果不是原来的船,那么它在什么时候不再是原来的船了呢?霍布斯(Thomas Hobbes)又进一步将这个思想试验进行了延伸:如果用船上取下来的老部件来重新建造一艘新的船,那么两艘船中哪艘才是真正的原初之船?一个人的身份总是在不断地应对各种外部环境和内部思想的改变而相应改变,在这种自我修复和新陈代谢之中,旧我总是不断地自我颠覆和毁灭,新我总是不断地新生和裂变。因此,某个具体族裔身份的本质化说法从根本上来说,如果不是僵化心灵造成的暗昧,很有可能就是某种观念主导下的刻意强化。进而言之,一个人的学术进路其实也一样,不断开辟的游击队员也并不一定就丢掉了根据地,相反充实了他鲜活的生命和生涯。
我是2011年离开纽约的,直到那时尚未出版过任何专著,也还没有涉足当代文学批评,但这一切都在后来变得顺理成章。多年之后回眸那段生活于136 街的日子,我确乎始终如同一个游击队员,游弋在人文学科各种细分领域中间,绿色大门破败不堪,却是一道开启新的生涯的旋转门。今日之我,昨日之我,不进行自我设限,而总是拥有一颗敞开的心灵,136 街的生活是一个缓冲,让我理解和沉浸于自主学习和自我提升,在未来的日子里成为无尽的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