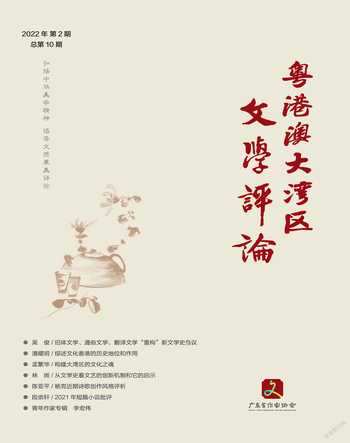执恶魔镰刀的信使
李振 乔梦桢
摘要:李宏伟小说中存在一种异常坚定的意志,这不仅仅是对语言、字句依次铆紧的掌控力,还有必须把它讲述出来的使命感。他渴望将自己察觉到的异象说与众人,这种迫切与真诚,正是李宏伟小说魅力所在,或许也是一个作家或者信使寻求解脱与救赎的唯一途径。
关键词:李宏伟;引路人;虚构;现实
死亡、控制、被植入头脑的芯片、被仪器改造的现实,以及与之对应的求生、逃亡和困兽般不得不进行的抵抗……这几乎构成了李宏伟近几年来小说创作的重要内容。我不太在意那些在小说中作为点缀或掩体的技术或规则是面向未来还是源自过去,而更珍视作家在小说里被某种不安甚至危机催动的诉说的激情。与此同时,李宏伟的小说里又存有一种异常坚定的意志,这不仅仅是对语言、字句依次铆紧的掌控力,还有必须把它讲述出来的使命感。他觉察到世间异象,披灰色斗篷,遮着脸,手持镰刀也拿着火把,在光怪陆离又充满不确定的黎明之前寻找着某种言说的方式与更多的同路人。
一
不得不承认那些被未来科技妆扮起来的故事同样令人心惊胆颤。《超现实顾问》里,唐山摘下超现实眼镜,发现身上被长期捆绑的印痕,发现身边同样被束缚的黑压压的人群;发现从前所习惯的世界满是虚幻,他在无尽的跋涉后目睹了那仿佛刚刚被清洗过的新鲜,哪怕只是黄沙与烈日;他寻到钥匙,返身解救尚被困于浓重梦魇而无知觉的人们,带着他们走向粗粝却真实的世界……这几乎是柏拉图洞穴之喻的具象化上演。说是幻觉也好,就是作家以“幻觉”为幌子透露出的又一重真实也好,这其实并不重要,要紧的是从中释放出的信息与线索——被遮蔽的人在种种指引之下,发觉身之所处尽是幻象,拨开迷雾将新世界的门推出缝隙后,被指引者又变成引路人,试图把更多的消息传递出去。这可以说是李宏伟大部分作品共通的精神内核,同时也是趁手的小说器械,以此对小说进行观照,能看到李宏伟创作中稳定、坚实又不失变化的特性。
早在第一部长篇小说《平行蚀》中,李宏伟的这种写作偏好就已显出端倪。故事并不复杂,是苏平苏宁兄弟由少年成长为青年与中年人的经历。这样一个看似单线叙事就能讲得精彩的成长故事,却被分割为“夜”“编年”“日”“纪传”四部分,并注满令人眼花缭乱的蒙太奇手法和密密匝匝的心理书写。这大概不是为了炫技,而是以此尽力捕捉人物在指引与被指引的过程中,那些细微的、不为人知甚至自己也无察觉的心理微澜,展现出一段精神上的成长,一场可接续、可弥漫的启蒙运动。小说从一个夜晚写起,但事情或许要从兄弟俩撞见父亲外遇的那个下午说起。父亲形象的坍塌給苏平以叛逆的契机,他选择的叛逆方式是囫囵吞下大量哲学著作,用以反击父亲的言论,并于这报复性的阅读中升腾出一种专属于少年的固执又激烈的观念。家庭变故将苏平引至陌生的精神世界,而他的言行又成为弟弟苏宁的引路人,连同那张车票,那场“盛宴”,共同鼓动着苏宁从无知无觉的童年中张开眼,爬上大货车,奔向那个含义不明的远方。苏宁这一晚的冒险,酒精,性,暴力,要素齐全,像一场紧锣密鼓的成人礼,尽管有掩盖不住的狼狈,但也宣告他迈入了全新的成长阶段。他所遇见的青年们那笃定的悲观,试图让自己与历史发生关系的无望宣泄,也将成为嵌入苏宁精神底色的重要元素,无可消弭。成年后的苏宁仍紧握着理想主义的交接棒,在他与朋友大段大段的讨论中,这样一个群体浮现了出来,他们都曾主动或被动地以“盛宴”为引路人,认知中的一部分被留在那个理想当道的年代,而肉身则早已置于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社会。社会转型以两种逻辑撕扯的方式,内化为个体的挣扎,唯一破解的方法是如苏宁和冬子般互相指引,搀扶着走出那场八十年代末的余痛。
及至《引路人》,指引与被指引的关系铺展得越发庞大,几乎撑起了整部小说的叙事空间。从赵一平到赵匀,从江教授到赵一,再从赵一到司徒绿,一场场宿命般的指引,和一次次引路者与被指引者的角色变化,让六十余年、几十个行政区的叙述跨度显得自然又合理。小说由《月相沉积》《来自月球的黏稠雨液》和《月球隐士》三部构成,每部中作为被指引者的主人公出场时,身上都带有苏宁式的懵懂,似乎按部就班于既有的生活,心中却伏匿着本能的困惑与渴求。年少的赵匀自不必说,协会教育体制下的优秀模板小学生,但也会执拗地在作文中使用老师没教过的“忧郁王子”的字眼,并为纪念叔叔改名为赵一。青年时的赵一通过层层遴选,以丰裕社会精英候选人的身份参加实习,看似苦行,实则是令人垂涎的嘉奖,传闻中骇人的匮乏社会就光秃秃铺在眼前,所谓的精神领袖,则可以作为意念中用于悬挂无聊的钉子,哪怕只是透过一台监控器、一辆吱呀作响的破车,却是协会为了进一步驯化而预支的特权滋味,而实习期间的表现更直接关系着前程,关乎父母的养老待遇,是将自己牢固揳入协会宏大机器的关键步骤。《月相沉积》中司徒绿收到的刺杀指令也有近似的实习性质,可当作樱桃园培训成果的实际演练,以期在刀光血染中升腾起作为团契“粒子”的坚定自觉,最好能自觉到下意识的程度,将服从和执行化为肌肉记忆,不需要思考任务合理与否,或生命是否宝贵,只需默念口号,执行如收割作物,那便是“有力量的粒子”——聚沙成塔,滴水穿石,靠的都是无知觉个体之累加,若粒子们纷纷思索,各行其是,还如何凝聚出力量?
然而每一枚粒子都蕴含着变异的可能,一旦被引路人触发,一场不可逆的个体启蒙便由此滋长。引路人的形象不尽相同,或是如江教授、赵一这般的金字塔顶端的角色,身处权力上游,丰裕、匮乏都了然于心,也愿意为被遮蔽的年轻人拨开些许迷雾,不动声色地透露内情,从唇齿间流出骇人讯息,赏味身处计划中的年轻人的惊惧,同时又期待着某种脱离计划的失控发展;又或是如赵一平般坦诚且身体力行,这个在赵匀眼中“最干净”的叔叔,毫不避讳地向孩子谈及以购物等级确认自由的吊诡之处,以自我放逐的方式寻求个人意义上的自由,用那个并无回首的告别和“月球隐士”的故事,在赵匀心中埋下一个时时震颤的伏笔。指引手段各不相同,触发变异的过程却十分相似,它是散播下火种,等待它与被指引者自身的好奇相撞,激发出潜意识里本能的叛逆,那种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的、在协会严令禁止下反而更强烈的热念,登时便燃起熊熊大火,不可收拾——由此,引路人的使命宣告终结。
但事情还远远没能结束。变异一旦开启,精神便无法退化如初,目之所及的一切都将被扯去看似合理的面纱,露出其下的病候来。前站公交车上浓污似血迹的画作,西线里透支生命和欲望的人群,死湖上围坐的枯骨,带着病子逃亡十几年的父亲,都将化作不同形态的指引,将主人公引向未知之域。而在步入未知的过程中,已觉醒的主人公又将自觉或不自觉地变成他者的引路人,一如趙一影响着司徒绿,司徒绿也会对小允产生尚不可知的深切影响,仿佛石子掷入湖心,涟漪一圈圈荡开,愈来愈广,直至冲出堤坝,成为击打在读者心中的浪涛。
二
李宏伟当然不会满足于仅在小说内部设置一系列的指引关系,更多时刻,他会直接扮演起引路者的角色,以小说本身为载体,向读者传递怀疑与思考,直接抵达某种更切肤的真实或现实。在这个过程中,虚构就是使得这种指引行之有效的书写策略,是李宏伟握在手中的、能够穿透重重迷雾的火把。
《并蒂爱情》里,一觉醒来,情侣二人的肋部黏连为一体且有蔓延之势,真正意义上实现了“要一直在一起”的愿望。读到此处,仿佛能感到李宏伟在憋笑:“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不是为人称道的至高爱情愿景吗,那不如成全这些爱侣,把它异化成一种真实吧。于是,他颇有耐心地娓娓道来,看似浪漫实则诡异的同体爱情生活就此展开。如果一起上班、一起穿定制服饰、将家中所有物件配对、对镜间接做爱还能称得上是有趣或情趣,那么不得不一起如厕、分享纸尿布使用体验的污秽感则在很大程度上扯下了那层玫瑰色的面纱——爱情被歌颂得再瑰丽再圣洁无暇,不也难以逃脱吃喝拉撒睡的庸常底色。物质层面的“亲密无间”在小说中成为客观存在,个人空间被压缩得稀薄,但更恐怖的是精神层面的混淆,最私密的思想仿佛成为两人共享,而无从分辨哪些才是属于自己的想法。“我们”凌驾于“我”之上,爱情凌驾于“我”之上,让渡自我甚至丧失自我成为完美爱情童话的暗黑结局。虽然小说结尾处借“城市仙女”的温柔童话将魔法撤销,让二人生活归于正常,但在这一场关于同体爱情的虚构中,那种无可逃避的窒息感逼迫人们去重新审视早已习以为常的爱情观念,并惊觉其中遮掩不住的尴尬、诡异乃至畸形。将既有观念化为虚构空间中的真实是李宏伟略带戏虐趣味却十分有力的指引方式,生活中那些看似可靠的“真理”或“常识”,在虚构之火的映照下原形毕露、漏洞百出、蹊跷丛生,而所谓现实的虚幻也在此刻被虚构的真实撬动。
如果说李宏伟早期创作对既有观念的祛魅还带着些许恶作剧意味,那么他关于现实的指认与警示则显得急迫得多。可以把他想象为一个提早从梦魇中惊醒的信使,或许他早已察觉那即将到来的坍塌,但周遭同伴依旧酣然于洞中的安全假象。但意味着巨大危机的地面震颤又细微得几不可见,那么如何让人人分辨出这正在发生的现实?与其徒劳发出无望的呼号,不如点亮一束火把,将那微弱的震颤在火光跳动中放大,放大为石壁上狰狞的影子,犹如从地狱中脱离的魔鬼。正如李宏伟所说:“尝试着往远处退或者把这一点放大,这固然会让我看到的进而呈现出来的有‘失真,有着浓烈的一望而知的虚构色彩,却也能让触动自己的‘这一点突出来,更容易被他人看到,更有力地传递那份触动。”于是有了李宏伟的“思想实验”,他将自己捕捉到的社会病候加以提纯,移植至未来,以虚构的方式具象上演,让现实问题在名为未来的实验场域中膨胀成令人毛骨悚然的模样。正因这种置身于未来的言说方式,让小说获得了更具弹性的话语空间,让原本难以言说的指引以更加鲜明的方式进行,同时也让人们得到某种抽离于既有时空的可能,进而以旁观者的身份去更加镇静地体味、辨别、处理身之所处的现实。
《国王与抒情诗》以诗人之死为开场,借由信息传播的方式,展示了人类同处意识共同体的未来生活:纸媒已成古物,取而代之的是将事件无限分解的视角,医生视角、警察视角、路人视角甚至是担架视角,化作不同颜色不同层次的信息流,洪水般从意识层面汹涌扑来,容不得人有丝毫喘息。荒诞的是,这样一个以如此压迫甚至是入侵方式进行信息传播的媒介,一个亿万人意识共在、些微动念便能被他人感知的绝非“自在”的场域,竟然被称作“自在空间”。更荒诞的是,意识共同体早已根植于全人类的基本生活,12岁植入意识晶体成为约定俗成的成人礼,意味着被正式纳入帝国的庞大体系并随之运转,所见所知所感都将于帝国规划好的框架中有序生长。因此,人们真的能够在其中感到自在,甚至只能在其中感到自在。然而随着情节的推进,人们也许会在某一刻惊觉,这看似极富未来感的2050年,或许也与自己所在的现实存在着某种关联。它是作家虚构的幻象、未来,或只不过是眼下的生活在远方的某种投影。“意识共同体”上令人眼花缭乱的信息流,与当代人在网络上遭遇的无休止的碎片化信息并无二致;移动灵魂和意识晶体的组合,似乎也难逃电子设备的现实控制,衣食住行工作社交全赖于此,一旦脱离,会意识混沌,出现“意识晶体幻在感”,酷似关闭手机后仍频繁听见消息提示音的症状;至于以分享鲜嫩视角为人生全部意义的“信息奴”,何尝不是大事小情都发布于社交网络再焦急等待回应的人们的缩影?小说附录最后一篇《拍卖零》中写到帝国霸权竟始于一部普普通通的手机,这个并未超出当下经验的揭示更像是某种暗号,给人们留下了一个近乎直露的指引:现实即是“未被普及的未来”,而未来的一切都已在此刻埋下伏笔。
一旦确认了李宏伟所书写的“未来”,那么循着线索破译出他试图传达的信息就变得不那么困难。他在小说中留给读者的线索足够茂盛,帝国把控下的社会虽颇有“大同”意味,“意识共同体”也被国王渲染得看似理想至极、浪漫至极,但在一片整饬之中,常冒出些偏离轨道之外的元素,像混入画面的噪点,吸引了全部注意力。正如宇文燃那几乎绝迹的清亮眼神,在不加入“意识共同体”便会与社会脱节的大环境下,人们已然习惯于将注意力集中在视域里的信息,外界不过是用于承载信息的无关紧要的背景,不值得浪费眼神,于是群体的目光便有了共同指向,如同被集体输入了某种指令代码。这让宇文燃眼中那种真正具有“人”的意味的灵动,成为世间罕见的珍宝,也倒映出信息掌控下人们自主性的丧失与沦为“信息奴”的状况。当然,还有“信息游击群”的存在。当“意识共同体”以自由发布、全体共享为招牌时,试着追求一点独立思考都需要“游击”似的躲开警方与帝国的监控,这构成了对所谓“自由”的有力反讽,让人不难发觉海量信息之下,是严格的筛选和级别分层,再根据权限等级有选择地输入给特定群体,借此塑造服务于帝国的集体思想。尽管“信息游击群”的动态实际上都在帝国掌控之内,但就像创建者阿尔法所说:“这种垄断继续下去,帝国迟早要成为人类历史最庞大、最强悍的机构,帝国将以信息操纵、控制我们所有人。我个人当然抵挡不了帝国庞大的身躯向着必然的方向奔进,但我至少可以建立信息游击群。”同质化的信息洪流中,如此异类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抵抗,其中泄露的只言片语也或将触发自由意志的复苏。在某种意义上,李宏伟的讲述或与“信息游击群”有着相似的效用,它是完美平滑面上那个突兀的线头——好奇心起,一路撕扯下去,平滑面轰然解体。
三
《现实顾问》里,当唐山带着被他解救的人走出洞穴,走向真实的世界,他注意到人群中迸发出的怒火。那指向明确的愤怒似乎要扑上来将他撕碎,让他在心生恐惧的同时也充满了困惑。小说于此似乎抛出了一个关于引路与否的拷问:将洞穴中的人拉至洞外,用陽光刺痛他们的双目,用火把照亮他们身上因束缚而生的伤痕,这究竟是慈悲还是残忍?而习以为常的戴着镣铐的舞蹈,和沙漠中无所遮蔽的流浪,究竟哪一种是值得求索的自由?李宏伟没有直接给出答案,只将红蓝胶囊放在读者手上。但在小说里似乎可以看到,作家习惯于放置几个从茫然人群中走出来的觉醒者,为故事留下一点希望的尾巴,这种写作偏好或许已经泄露了他的答案。
《暗经验》是具有典型的李宏伟风格又气质独特的作品。小说中建造的那个“暗经验局”,既可以看作帝国的前身或分部,也完全可以自成一体。它有着完整而自洽的运行逻辑,即在艺术价值和社会功用的双重制约与统一之下,对文学作品进行衡量和把握,使之符合文学传统的要求,并进一步融为文学传统中的一部分。它在“暗经验局”具体地呈现为种种措施,翻检、筛查、设定、擦拭的流水线作业,一番加工再出版的文学作品都有着恰到好处的美感与质地齐整的内核。这种潜规则为创作者所默认,更有摸清规则投其所好者,可李宏伟偏偏于此安置了一个不肯配合的萧峰。从各个层面讲,萧峰在小说中都算是小角色,出现篇幅不多,于故事推动作用不大,侥幸发表小说《宠人》也是运气使然,是张力职位提升后附赠的小小特权。然而,这次发表经历却指引着萧峰就此搁笔,他本想出于最纯粹的创作欲望,依着本心踏踏实实地完成自己的作品,可在“暗经验局”的审核与指导下,写作变成了工厂流水线式的标准作业,字句、情节、主旨、情感,都被严格定义为原材料,按要求一一连缀即可。看似给作者和审查员都省了力气,可写作中最让人迷狂的那股冲动却消失了,作品中那些粗糙又动人的缺口也随之耗尽。经此一遭,萧峰像从幻觉中被唤醒,发觉自己所神往的辽阔世界,实则只有洞穴般的逼仄面目,他无力去更改现状,但也不愿迎合这种规则,更无法再度闭上眼,回归混沌无知的状态。搁笔退出,保持个人的认知与判断,是他作为一个被指引者给出的答案。
《引路人》中的人物似乎比萧峰走得更远。安分守己,勤勉工作,三十五岁前娶妻,换取留在丰裕社会的资格,这是协会给出的“尊严”样板,也是无数人奉为圭臬并为之奋斗终生的目标。按此规划,大概率能过上一种看似体面完满的生活,或者说是不那么匮乏的生活。但这种被社会构建出来的“尊严”并不能使小说中的每个人都信服。本能的敏感,天生的“反骨”,和生而为人的尊严,混合在一起,让他们成为自己的引路者,凭直觉感知到“协会”加诸于自身的束缚,再凭直觉试着向光亮处摸索去。于是就有了那个穴居于桥洞、清贫却洁净的女人,有了主动前往污染区以冥想度日的年轻人。他们不愿将自己的行为称作流浪或放逐,其中的被动意味太强,“觉醒”更符合他们的初衷,即放弃被纳入“正常”生活的机会,寻求自己定义下的人生道路。或许能够选择的方向终究有限,但做出尝试这一行动本身就昭示了他们不再回首的决心,也显示出觉醒的不可逆来。
或许还可以更加乐观一些。《国王与抒情诗》的末尾,李宏伟为读者留下了一个可供想象的开放式结尾,帝国那看似稳固如山的基业,产生了在未来被改写的可能性。作为国王候选人的黎普雷,身上承载着人类对于文字的迷恋,收集文字、书写文字是他获得精神安宁的重要方式,初出茅庐时提交的《帝国未来蓝图与根基》亦以文字为基点进行设想。这份设想直接被吸纳入帝国的扩张,尽管是以相反的方式。这样一个被诗人之死一路指引前来、已然知晓帝国面目又极富创造性的角色,如果真的接任国王,以他对文字和抒情的理解,会不会调整帝国舵向,把“意识共同体”变成以原初情感凝聚全人类的载体,创造出一种新秩序、新前景?即便接任的不是黎普雷,其他几位候选人也均是灰衣人口中那种“天赋异禀的影子”,当他们被种种手段指引至真相面前时,被遮蔽的愤怒掺杂不安分的天性,又会怎样影响着帝国和人类的未来?这一切皆不可知,也皆有可能。这种未知或许正是李宏伟给予小说和人类命运最温柔的一笔,由此也能从中窥见他对于指引与否的暗示——固然会茫然,固然有怨怼,但只有走出洞穴,那些被束缚已久的人才能有机会去拥抱可能。而尽可能地提供这种可能性,大概就是引路人的使命,尽管他点亮火把,在洞穴墙壁上投下的可能只是被人误解的魔鬼的影子。
李宏伟曾说:“如果不是认为自己看到一点点不同的地方,尽全力把它说出来,以求被人听到,更求做个验证,验证它是否真的不同,写作是没有必要的。”他渴望将自己察觉到的异象说与众人,这种迫切与真诚,正是李宏伟小说魅力所在。观察、理解并对现实做出回应,再依据得到的回应重复这一过程,于精神共鸣中确定自我、他人与世界的存在。也许这便是一个作家或者信使寻求解脱与救赎的唯一途径。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