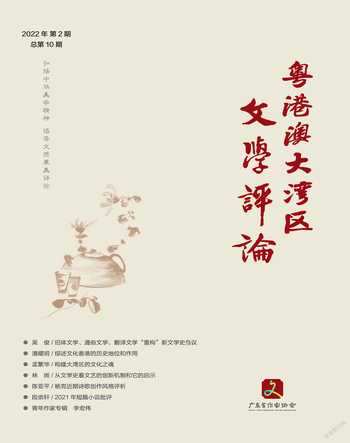近思录(一)
吴俊
摘要:鉴于世纪之交以来几代学者的努力和倡导,新文学史的观念正在发生持续性的转型变化。旧体文学、通俗文学等进入新文学史谱系、进而重构新文学史(现当代文学史)的理论和实践,已经渐趋成熟。本文对此一方面进行了阐述重申,另一方面提出新文学史重构的“四维”观点,即将旧体文学、俗文学、翻译文学纳入传统的狭义新文学史中,拓展现当代文学的历史空间,构建一个与传统中国文学史贯通相契的结构体系。限于篇幅,有关翻译文学的论述未及展开。而且,如何处理海外和世界华文文学的问题,还未提及。一并留待后续讨论。
关键词:旧体文学、通俗文学、翻译文学、重构、新文学史
小引:读书或闲聊时,胡思乱想多了,觉得也有点儿意思,不记下来就忘了。但没时间写成正经文章或论文,就想到了近思录这种兼有札记性的方式了。并无效仿古人之意,仅取其字义,谓最近的想法录写而已。先大致写下来再说,表达个基本意思,以后如何正经起来就看机缘吧。本来这第一篇想说三个问题,结果寒假和壬寅春节的时间不如我预想的宽松。匆忙赶稿,连一个问题都没谈全。主要是水平有限,还没想透。贺仲明教授主编刊物的发稿已经宽限我几天了,最后只能以第一个问题的部分内容为题交稿了。写得不周全也不管了,行文也嫌糙。万一有高明屈尊拨冗赐教指谬最好。壬寅初七日沪宁雨雪间记。
新文学史或者说现代文学史的重构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新问题——准确地说,再度成为一个问题,在我是由李遇春教授的新著《中国现代旧体诗词编年史》(第一辑)引起的。该书的出版把一个旧话题置入新的研究视野中,拓展出了一种新的探讨路径,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学术高度。我对此的再度思考也是受到了遇春教授新著的直接启发。不久后又看到了栾梅健教授的文章《寻找文学史研究的“三维空间”》,主旨评论李遇春教授主编的《中国现代旧体诗词编年史》(第一辑),栾文从遇春教授的现代文学史研究“三变”而论文学史研究的“三维空间”。我简称之“三变三维说”吧。从文学史体系构成的结构角度看,我想应该是有一个四维构成的体系,即旧体文学、俗文学、翻译文学、新文学。此或谓之“四维说”。这一想就促使我把有关想法扼要地写出来,以备后续进一步研讨。
先要说明的是,所谓重构,主观意图当然有别于以往所说的重写云云。但也并无有意看轻或否定重写的意思。只是重构之意是想特别强调重新构造一种文学史体系内部组成结构的意图;对于文学史体系的主体或整体构成部分的结构性关系重组,是一种有关自身内部的结构系统的整体性调整和改变。重构改变的是原来文学史书写的生态面貌描述和历史逻辑演绎,也因此形成了新的文学历史生态、形成了新的历史逻辑及阐释方式,最终在历史叙述中归纳形成有关文学价值的重新评估结论。由此来说,文学史的重构不仅改变了历史书写逻辑,更重要的是改变了文学史的观念和文学的观念,是一种经由历史阐释而达成的文学价值观的理论重构。以往的重写文学史也许更多着眼于局部、段落或个案的改写或完善,至少并没有改变文学史主体构成的整体结构方式;或者说是一种新的排列组合,意图彰显或抑制某种特定文学价值的地位,强制阐释的冲动或许显得格外明显一些,甚至表达动机多缠绕在政治意识形态的诉求方面。我现在所见、所谓的重构文学史,当然希望不同于此种意义或动机上的文学史重写;重构有着自身特定的学术观念(文学价值观、文学史观)支持、学术文献和史料基础、学术实践路径的新拓。
也许可以简明地说,随着现代俗文学、旧体文学的文献挖掘、学术研究和一般传播的推进——前者较早集大成标志如范伯群、汤哲生、孔庆东等几代学者论著,后者重大成果著述历年来有胡迎建、刘梦芙、李遇春等为突出代表(遇春教授提示我:最早是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首次将民国旧体诗文正式入史),再次全面宣告了中国新文学、现代文学史的语言生态、作品形态、结构逻辑、历史价值等,正在发生着无可置疑、不可逆转的学术路向演变。以现代白话和现代汉语、“启蒙—革命”意识形态为主流形式和内涵的新文学、现代文学作品一股独大、一统天下的历史描述及其学术观念,已经到了应该更新、终结的时代。换言之,新文学史的传统观念和叙述方式应该要被重新审视、整体重构并应该予以学术史的再度全面阐释了。
这意味着:同时代的各体文学构成同时代文学存在形态的事实,特别是同时代各体文学的价值地位,不应该再继续受到功利观念、意识形态转型的强制阐释或判决。传统新文学史观也是一种强制性的意识形态,并非只有政治的刚性才是唯一重要的意识形态威权裁定——很难说启蒙文学、新文学是出于政治权力的诉求而发动了一场文学史革命。新文学取代旧文学成为现代文学正宗,同时却长时期剥夺了俗文学、旧体文学在新文学、现代文学主流历史中的合法地位和价值地位。这种历史的“革命”霸权所衍生的偏颇、极端,特别是一元论的新文学史观,现在看来已经严重损害了文学史的丰富性和文学价值观的多元多样性,而且必然会产生历史虚无主义的后果,应该到了必须予以纠正和止损的时候了。不仅是学术意义上的局部“重写”“改写”或完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成为一种必须,更重要的是新文学史的整体性“重构”——生态、逻辑、价值地位的历史重构,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必须进行和完成的一种学术实践使命。
其实,这本是一个源于、基于常识性的认知和观念,但“革命”的功利短视产生出、助长成了这一有违常识和公理价值观的低级历史性错误。今之视昔倒也不该苛责前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觉醒于和响应起时代的发展呼唤,承担现实的学术责任。而且,新文学史的整体性重构理应成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前沿课题。
为什么说新文学史、现当代文学史的重构是源于、基于常识和公理的一种觉悟?这是可以简单论证一下的逻辑事实。
在我们后世、也是现代文学历史所形成的古代文学史观念及脉络流变评价的一般谱系上,很明显、几乎不证自明的一种事实,就是各朝代的各体文学都有合法身份,都是文学史的主体构成部分,都拥有不可剥夺的文学资格和历史地位。各朝代的诗词文如此,六朝志怪、唐代变文和传奇、元明朝后小说、戏曲等,乃至清末的各体俗文学等,都和同时代同朝代“正宗”的诗词文一样,拥有着文学史的主体价值地位。这一学术逻辑事实说明,新文学独尊白话、现代汉语文学的文学逻辑和历史逻辑,恰恰是反文学、反历史的。所以就会看到一种常见不怪的反逻辑悖论现象,旧体文学被驱逐了好像不用大惊小怪,但旧体诗词的一些特例却又可以进入新文学史;一方面中国古代俗文学研究一直风生水起,民间文学研究也是正经学术,唯独20世纪以来的俗文學遭人轻视和鄙视,俗文学研究也长期处于边缘化的学术位置。这实在不能不说就是一种混乱的文学史逻辑和混乱的文学价值观体现了吧。新文学的价值观和语言文体的身份政治,因“激进革命”的功利而引出、导致了狭隘、偏颇、单向、单面、孤立、断裂、反常的文学史后果。按其逻辑也能扣它一顶“政治大帽子”,可以叫作违反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文学史观。一个很显然的质问就是,为什么旧体文学、俗文学之类传统文学形式,在现当代文学的同时代仍在不断创作的文学发展过程之中,却完全或长期没有资格进入、被排斥于同时代的文学史呢?
溯源申言之,新文学的“白话文学正宗说”为白话争得了、恢复了历史地位,改写了千年文学史,开创了百年新文学史。但是,“白话正宗”却因此排斥了文言(正宗)和部分贬低了现代俗文学的文学合法身份及文学史地位,实际上却是违反“白话文学正宗说”的理论旨趣尤其是其历史科学精神和革命思想精髓的。原因在于,“白话文学正宗说”固然是为白话争得了地位,但并未因此剥夺文言文学的历史正宗地位——只是恢复了白话的历史地位合法性和正当性,使白话和文言处于同等的文学史正宗地位。文言(文學)仍是中国文学史的正宗文学形态。遗憾的是,白话革命成功之后,它自身固然不再委曲求全,缩手缩脚,而且凌驾于文言之上,却因此很快就产生了新的文学等级差别。形同是用进化论和启蒙观念支持了文学文体的新文学“阶级论”:以激进方式宣判了文言(文学)的“死刑”,并几乎活埋了文言(文学)的生命;同时,俗文学也如影随形般地烙上了低级趣味、道德缺陷、愚昧落后之类的原生嫌疑。这种现代激进主义的历史演进既走向了“白话文学正宗说”的革命精神的反面,甚至连文言时代的文化宽容度也远远不如了——白话文学是在文言主流独大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但白话却几乎迄今都没有给文言在新文学史上留下一个容纳合法身份的足够空间。两者的器量在历史上留下的是对照鲜明、完全不同的高下境界。也许文言不愧为没落的贵族或绅士,白话更像是不折不扣的豪横暴发户。后者其实轻视、忽略了传统渊源(历史资源和演进逻辑)、文化雅量(丰富性和包容度)对于文化创新的重要性。创新既是朝向未来的想象和实践,也是源自历史内涵和积淀的强力支持与推进。激进潮流则往往把高调口号和极端姿态视为革命道德的标识,裹挟着文化流变的时代走向难免受到粗鄙化和反智、失智的精神伤害。俗文学的遭遇或更加难堪而暧昧,它是在新文学的意识形态上被简单粗暴地置于、连带上了堕落、不道德、无社会积极意义等负面角色定性。启蒙的革命需要、历史正确性和时代新潮重建和塑造了精英化的新文学正确形象及高尚地位,低估、无视甚至强力抹杀了俗文学的社会价值和文学意义。“文学革命”将文学的正确观念进行了“统一归化”,不能改编和收编的“异端”就予以驱除了吧。新文学的价值观成为唯一的正确标准。说到底,这种极端立场或二元对立思维实质上是对政治革命和革命政治的一种伤害,严重削弱了后者的文化基础,并有损革命政治文化的历史承传和建设资源。
物极必反。有点宿命的意味,或许是历史的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力量终于产生出了强大的正本清源、重构历史的思想纠偏作用。旧体文学和俗文学的现代文学身份及其文学史合法地位,在当代文学的演进中终于从文学地表之下上升到了学术关注瞩目的现实视野之中,重新获得了失落已久的身份认可和价值肯定。某种程度上说,这也只是恢复了中国传统文学史的历史逻辑和学术逻辑而已。对新文学的历史观念也许可说是一种“二次革命”或学术新拓,而在整个中国文学史的观念和视野里,这只不过是回到了文学的常识轨道上了而已。
文学史重构既成必然和必须,那么,更进一步的思考还有什么?文学史观的历史逻辑中应该还有着更为基础性的文学价值观内涵。如果说在文学形式、文体形态、美学趣味、一般价值旨趣和思想倾向方面,原本的旧体文学和俗文学等,都有自身的高度成熟了的经验、常规乃至基本范式,那么在新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的历史时期,这种同时代的旧体文学、俗文学的基本价值标准是否就将被新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的标准所取代、以后者的标准为价值衡量依据呢?旧体俗文是否必须皈依新文学的意识形态?旧文学在新文学主流的历史时代是否必须以脱胎换骨为代价?类似于当代京剧艺术领域中曾经有过的“移步换形”之争,这是在旧体文学、俗文学获得了合法身份后展开具体研究评价时,必然就会发生的学术问题。新文学就此不言自明、名正言顺地成为旧文学的主要标准?这个问题涉及的已经是文学史究竟如何重构、如何新建价值标准、如何完善文学史体系逻辑、如何形成新的文学史理论的一连串重大问题。其中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远远超过了恢复旧文学、俗文学的文学合法身份这种观念意义上的革命性转换。观念的文字表述方式毕竟相对简单、相对抽象,具体的评价实践将重构具体落实为文学史的价值阐释,则需要充分周密有力的理论支撑,需要有关文学阐释的内涵和形式的学术支撑。否则,所谓重构也是流于表面的形同虚设或大言空谈。
显然,就迄今的学术进展和文学史评价而言,对于旧文学、俗文学的评价标准,在主要做法和主流标准上,还是大体沿用或依据了新文学、现代文学的传统评价方式。即主要是用新理念新规范来评价旧文学俗文学。这是新文学沿袭至今的一种文学史政治正确的基本传统。本来或也无可厚非,已经成为一种文学史的历史惯性和思想本能了吧。严重点说,也就是业已固化了的新文学的价值观、历史观和意识形态了吧。这样一种缘起于西风东渐、现代启蒙思潮的文学政治,虽无现实社会政治的威权,却也形成了一种立场界限和文化权威,左右、支配着文学评价的实际展开及历史结论。稍加分析其中的缘由,也或有点儿复杂,不可一概而论。在我看来,对于俗文学的评价方面,最明显也最有点意思的,或许这是一种实施良好、善意愿望的权宜手段,试图用新文学在文学史层面上改造俗文学的价值评估而采取的阐释策略,动机倒是为了部分证明俗文学向新文学主流靠拢而进步的与时俱进的新价值。这方面的显例之一,就是源自清末民初以鸳鸯蝴蝶派文学为主的传统市民文学(文学史上常称之为旧市民文学,是俗文学的大宗,也是新文学革命勃兴之后的主要敌人之一),在抗战大背景下投入文学抗战的创作演变。在国家和民族战争时代,这本是一种自然合理也很正常的文学反应。但我们同时也应该认识到,文学史上之所以有鸳蝴派文学的地位,不是因其后来的投身抗战大潮,而是在其市民趣味的文学主旨。后者才是市民文学的历史价值并因此奠定了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就是说,新文学(包括抗战文学)只能是市民文学流变的评价标准之一,市民文学的历史演进及其价值自有其文学生产和消费、文学鉴赏和分享的特定理由,并且,后者才是它的主要理由。不过,在新文学史的逻辑中,市民文学的评价地位一方面不高,另一方面也越来越丧失了它的正当性道义。甚至形同烙上了道德污点般的出生原罪,直到新时期后仍带有文化自卑感和历史恐惧感。(1990年代,因参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中国现代言情小说大系”出版计划,我去拜访了沪上一位现代著名的鸳蝴派言情小说家,寻求版权支持。几天后,我的导师把我叫去家里谈话,说那位老先生是和导师一个政协小组开会的,因相识就直接致信导师,称我将他的作品视为言情小说是不对的,他的小说也是关心人生疾苦、反映社会现实的,不同意出版计划的定位和丛书名称,不支持这样出版他的小说,也不欢迎我再去打扰他。)在文学价值和文体形式上,市民文学连同广义的俗文学,最终是完全被排挤出了文学史的主要叙述谱系。以至于到了1980年代末、1990年代,以琼瑶言情小说、金庸武侠小说为代表的港台通俗文学对大陆形成了席卷覆盖之势。谁会想到,只在近半个世纪前,这一套路的文学其实是大陆文学的盛产,不仅同样有半个世纪的辉煌历史,而且不失为中国现代市民文学和俗文学的正宗。
俗文学的指涉并不限于上举的鸳蝴派、市民文学之类,较长时段文学史眼光看到目前的话,网络时代的网上作品又有多少可以谓之俗文学?旁及民间文学(在学术界,民间文学和俗文学的内涵外延的范畴,深度交集,甚至还未必有共识认同的名称,命名歧义迄今存在)的领域,又有多少俗文学其实就是民间文学的正宗版本?这是新文学的主流(文体)形态和文学生产方式所不能完全覆盖的文学现象。难道都该贬低、轻视其文学价值?我只想说,新文学的价值标准很难做到对于俗文学的公平和公正的文学史判断。首先是它的标准捉襟见肘,无法量体裁衣。网络文学是在新时代将这一尴尬状况推向了极致,很明显的就是传统文学观已经对网络文学的评价和判断近乎完全失语了。最现实的挑战是,传统的文学批评方式已经完全不能应对网络文学的写作、生产和传播现状(有关网络文学的话题此处不作展开)。例举此类现象,我想说的最重要的一句话,俗文学必有、应该有其自身的评价标准,它的标准一定是和新文学的主流文学在思想观念、美学趣味、创作倾向、诉求目标等保持有鲜明区分度的距离和不同。这才是有着文学史价值地位的俗文学。另言之,俗文学使文学史具有和体现了文学的丰富性。这在古代文学史上只不过就是一点儿常识。俗文学应该、完全不需要仰仗新文学的主流价值观自证或抬升自己的文学价值。历史已经证明,俗文学本身就可以代表、标志一个时代的文学高度。如今回头看,我格外敬佩上世纪末、新世纪初,有前辈学者(并非少年新进)将崔健的摇滚歌词、金庸的武侠小说等,重评高抬跻身进了百年新诗、百年文学的排行榜前列,定评为世纪文学经典。多少人为之侧目而不屑。20年后,诺贝尔文学奖坦然授予了美国当代摇滚民谣歌手鲍勃·迪伦。你服气吗?就此比较而言,中国文学研究和学术先辈的观念实践,其实是走在了世界文学的前列。
我这样说当然并非旨在反对新文学的基本价值立场和文学史革命性,而是质疑新文学的文学史霸权建构的负面影响。如果我们考虑到、相信文学的丰富性、多样性才是合理的,那么排他性的、唯一正确性的文学史观就应该受到质疑。甚至包括文学文体的等级差别的观念也是反文学的。常说文学价值观应该是多元的。从历史上看,即便是在新文学的创始阶段,实际上启蒙文学并非一家独大,但新文学的历史建构和史著书写则将启蒙文学的价值地位确立为几乎是唯一性的正确代表。这种偏执的文学史权力地位建构看似维护了新文学的正宗和正确地位,实际上是伤害了新文学和现代文学的整体性价值呈现,削减了新文学、现代文学历史发展中的文学价值生产,无视或掩盖了新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强大生产动力和增值机制。一言以蔽之,当一种文学形态(即便是新文学的启蒙主流文学)建立了唯一性的权力地位后,文学流变及其历史演进的方式就开始进入了残酷“内卷”模式。一定程度上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的现代文学史著绝大多数会是一个模式的翻版(数量至少达几千部)——文学的丰富性已经先期被我们的文学史观念抹杀和阉割了。人为造成了资源枯竭和生态失衡的状况。俗文学不必是、也不是新文学和启蒙文学的敌人,两者应该是、实际上也是现代文学场域和文学史中的共生、共存的结构性关系。这种关系事实上无损于启蒙文学的主流地位。倒是启蒙意识形态一旦成为一种绝对正确的霸权,它就会直接消解、瓦解启蒙的精神价值观。一种哪怕是正确地体现历史进步发展的价值观,如果产生了对于自由信仰、不同立场或个体选择的限制和限定,这就走向反面成为意识形态的专制主义了。
俗文学的文学史命运涉及对其文学的思想意义及其表达方式(主要是文学文体)的判断,相对还有点复杂,一直都有歧义、不确定的言说可能,那看白话文学创制标志的新文学文体对于旧体文学(文言文学包括旧体诗词等)的颠覆,几乎就是一种天然的历史“进化”,有着正确的革命立场和不容置辩的理由作为支撑。白话新文学哪里容有文言文学的存身空间。所以,虽然一向都有旧体文学的不服抗辩之声,但都不足以撼动新文学史观的固执,无法促使其实际的改变或重构。好像所有人都愿意闭着眼无视这是对文学常识的违背,使得观念革命的困难和学术变革的懒惰长时间助长、维护了体制化的消极不作为。好在旧体文学毕竟拥有着千年以上的家世历史承传,在被压抑和剥夺权利的百年里,仍然不屈不挠地顽强接续着自己的生命脉传。而且,旧体文学还有一个相比俗文学更加值得骄傲的文化自信:旧体文学的写作成为白话现代文学时代一种文史修养、独特才艺、傲视俗流的文化资本,并无形中获得了类似“非遗”文化的特殊资格,常会被俗世眼光视为应该得到保护和尊敬的文化历史“化石”,在历史考古中惊叹于当代化石出土的稀有和名贵。实际上也就是因为现代历史造成的文化落差不期然地给文言(文学)写作罩上了一种物以稀为贵的文化光环,这才有了诸如近年几则高考作文文言写作的新闻。但这一切都无助于新文学史的学术重构。一种针对文言写作的典型“双标”现象成为常态。在道德的真诚性上,你觉得该不该把旧体文学名正言顺地接纳、安置在现代文学的历史(主流)谱系中呢?
再和新兴的网络文学的现实处境做比较的话,更可以发现历史观惰性的消极影响实在是非常可悲和令人无奈的了。因为有着主流技术条件的支持,网络文学已经形成大潮,宏观面上纸媒文学遭遇到了令人沮丧的历史低谷境遇。现在已经很难区分纸媒和网络究竟谁是主流写作媒介了,但文学权力的转换易手并没有完全发生。在这种情势下,作为亚文化方式崛起的网络写作却已经冲破了文学传统和制度的刚性压制,走出了自己的康庄大道。姑且不说市场机制,几乎每个省份都成立了网络文学作家协会之类的正式文学群团组织,俨然是在原有的作家协会制度面前扮演了自立门户、分庭抗礼的角色。这不仅是为网络文学争得了合法地位,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当代文学的生态环境。对照之下,旧体文学却还只能是现当代文学家族中的“外室”?旧体文学即便还只是亚文化的身份,但它的历史存在、现实赓续、文学影响和社会覆盖面,足以构成必须正视的文学史现象和问题,成为现当代文学的一种历史和现实的主要构成语境,成为“主流”文学关系中的一种历史有机构成和生態张力结构。现代文学在“弑父”革命的百年历史之后,如果没有这种起码的器度,那就是一种品格的缺陷和道德的耻辱。辱没的是百年前新文学的历史正义性。
概言之,我们从新文学、现代文学的起源和观念、现代文学的语言形态和文体构成来看,是可以发现一些值得重新探讨的问题的。时间流逝、时代嬗变,总会生成一些新问题,有些问题则是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发生了价值转移,问题的意义有所不同。其中最值得我们后人关注的,应该是原本的“公理”恐怕已经成了后世的谬误。这在历史观和当下关怀上,就亟须进行全面的重构。否则偿付的代价就会很大。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对一元独断论的破除,和破除迷信其实是一个意思。破除一元独断论,必然提倡或宽容相对多元多样的价值标准,好处一定会是更多呈现文学(史)的丰富性。文学的丰富性也就是文学个性的体现。文学不能整齐划一,不可丧失个性,这是立身之本。
以上主要谈了旧体文学和俗文学参与重构新文学史的问题。前辈学者中,严家炎先生等此前已经有过实际倡导和学术贡献,只是一般学术研究和史著撰述并未全面展开,仍以分而治之为主,有待于宏观面的进一步实践支持。本文动机本来不仅于此,还想一起谈的包括了翻译文学同样参与重构新文学史的问题。如何归属翻译文学的国家/民族文学身份,这是一个旧话题,但并没有解决。比如,新文学以来的汉译外国文学,如果不再是、很难说是外国文学的话,就是中国文学了吗?其中一眼看去都有点儿“荒谬性”的问题,不自寻烦恼的话,都不好意思说出来给自己添堵为难。一旦说出了口,有可能说出一点新意新见吗?换个设问方式,翻译文学如何进入中国现代文学?这一问,恐怕比较容易接受一些了,觉得还真是一个需要审慎讨论的问题。从历史现象看,翻译文学一定参与了现当代文学的建构——不仅是其影响,也是指翻译文学本身或就是新文学、现代文学的有机构成部分。这方面的显例在胡适、鲁迅这辈人的作品里就不少见,而且还非常的重要。只是有关翻译文学的观念时有变迁,就需要对历史和翻译文学实践进行更新的考察和探讨。不成问题的问题,或问题的消失,很多都是时间催生、消解的。理解过往,解决当下疑难,这是学术思考的本业。拟待下一篇再来续谈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重构关系问题吧。且借本文副题姑先留下一点(四维说)整体痕迹也好。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