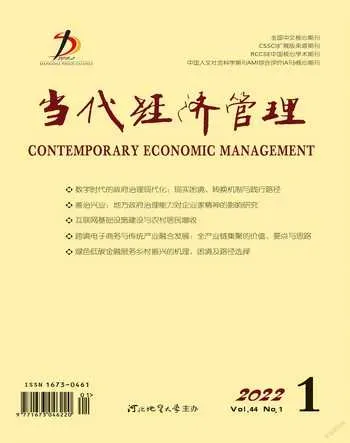数字时代的政府治理现代化:现实困境、转换机制与践行路径
张腾 蒋伏心
[摘要]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与云计算为内核的数字浪潮席卷而来,深刻重构了我国经济社会中多个运行体系与发展领域,而数字时代下传统问题异化与新问题频现是各级政府不可回避的重大治理挑战,同时也对政府部门事务治理提出更为严苛的要求与标准。在捋清当前我国政府组织治理过程中出现的主要现实问题基础之上,深层辨析显性治理难题的属性本质与根源实质,同时充分结合数字实践背景与客观环境,从源头治理视域出发,全面厘清数字时代我国政府组织与职能部门治理现代化升级的转换机制,并为其适应与引领数字新发展阶段提出针对性的政策意见与思路建议。
[关键词]数字时代;政府治理;转型升级;转换机制
[中图分类号] F49;D6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673-0461(2022)01-0001-08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随着内部资源禀赋结构与外部国际环境条件渐进式演化,我国已经迈入经济新常态发展阶段,同时进入全面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攻坚区与深水区,如何有效提振我国实体经济、保证社会平稳发展成为新阶段党中央与国务院高度重视的核心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顺应时代潮流,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须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下更大功夫。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促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成为我国政府组织理性回应客观变化与演进趋势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有力支撑。作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运行载体,政府组织治理毫无疑问成为我国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的前沿阵地。因此,优化政府治理结构,降低监督与管理成本,提升总体社会治理绩效也就成为未来长时期我国政府组织与职能部门的主要工作目标。
当今全球再一次涌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浪潮,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与云计算的数字经济的诞生与泛化催生出诸多新产品、新技术、新产业与新商业模式。作为继农业经济与工业经济之后的又一全新经济业态,数字经济深刻影响不同维度的发展领域与运行系统,已经高度渗透与深度融入于我国生产、消费、交换、分配各个环节与阶段。但任何事物均有两面性,数字时代也衍生出诸多新风险与不确定性,数字风险有着特殊的隐蔽性、突发性、跨界性与随机性等全新特征,这对我国政府治理能力与水平提出更高要求。“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提高数字政府建设水平,加强公共数据开放共享,推动政务信息化共建共用,提高数字化政务服务能力。在数字新时代,我国各级政府组织能否高效融入数字浪潮之中,加快自身数字化转型升级以有效解决新旧治理顽疾,提高电子政务能力与数字服务水平,科学促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便成为一个值得深入研究与探讨的重大议题。
二、数字时代政府治理的主要现实问题
在数字时代发展背景下,我国政府治理主要面临新问题处置不及时、传统问题治理效果低下、政府与市场边界不清、区域问题治理力量分散、晋升政策扭曲、官员行为约束低效等现实难题。
(一)新问题处置迟缓
在数字发展阶段,内嵌时代特征的新问题与新风险层出不穷,个人隐私泄露、网络谣言、P2P爆雷、虚拟币洗钱等乱象已经严重侵犯我国国民群体的基本权益,负向冲击市场主体的生产生活行为。由于我国监管制度框架具有明显的审慎包容特征,导致政府部门对新兴领域的监督与管理表现出较为宽松与放任态度,进而营造出一种软约束的“和谐”环境氛围。但过于包容的监管理念与行为诱致市场中的负面因素逐渐累积,在达到一定规模时新的问题与风险便会集体性爆发[1]。与此同时,由于政府组织从初步识别、部分理解到全面掌握社会新事物需要一个过程,且任何一项宏观措施从设计制定、公开颁布至实施落地都具有较长周期,因此我国政府部门对于社会全新问题的处理与应对则稍显“手足无措”,处置方式具有一定程度的滞后性与低效性,从而降低了我国政府组织的监管效率与治理质量。
(二)传统问题治理效果低下
改革开放40余载,基于阶段性现实特征与目标导向,我国中央政府密集颁布系列规章制度与法律法规,通过调整驱动模式与构筑动力机制促进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平稳运转,有效解决了诸多涉及温饱、民生、就业、入学等发展性难题。而对于如生态环境治理、户籍制度改革、住房市场化、医疗养老等固有传统难题,当前我国中央政府虽然从顶层设计角度科学出台多项权威性与强制性法律政策,并取得一定程度实践成效,但是现实情况仍旧不容乐观,生态环境污染、房价高企、劳动力隐性歧视、重大疾病费用昂贵等问题成为横亘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上的绊脚石。倚重过去的治理机制与方式并没有完全解决上述问题,传统难题可谓根深蒂固。老路子行不通,就应探寻新路子,我国亟须崭新的治理思路与方式破解固有顽疾,政府组织治理仍旧任重而道远。
(三)政府与市场边界不清
依据政府管理理论与市场行为理论,国家机器应当合理划分政府与市场所需治理的系统领域,充分发挥出各自的内生优势与固有特点,实现对国家全域的综合性治理。但如此理想的治理状态与治理体系并不是轻易所能达成的。虽然我国正在致力塑造现代化政府组织与市场体系,但离理论上的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仍有不小的差距,主要体现在我国政府与市场边界仍旧不明朗与不清晰。一方面局部领域出现监管空白,市场机制与竞争机制无法得以发挥,同时并没有明确的政府治理定位,缺乏针对性的组织机构与职能部门。另一方面,某些领域呈现监管重叠,政府组织多个职能部门对同一经济社会事务进行治理与监督,進而出现政出多门或相互推诿现象[2]。总而言之,由于边界划分不清与治理主体混乱,导致政府与市场对部分发展环节治理效率低下,治理绩效无法令人满意。
(四)区域问题治理力量分散
我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部分社会经济事务特别是生态保护与基础设施建设需要不同省份、直辖市与自治区共同协调与配合,但是各地方政府由于沟通机制差异、策略性竞争与“搭便车”心理等因素导致对于同一问题的处理态度截然不同[3]。例如在经济发展具有一定差距的相邻两地建设高速公路或铁路,两个地区政府组织对于建设工程的开展与推进持有区别较大的主观性,导致总体项目在两地施工进程不一致。对于区域性治理问题,由于此类事务属于公共性物品与服务,具有较强的外部性与溢出性,进而导致各地方政府的成本收益函数呈现明显区别,高度影响政府组织的主观努力程度。例如在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问题上,地处于流域上、中、下游的地方政府组织在对这一公共区域问题的治理效能会展现出显著差异性。
(五)晋升政策扭曲
在政治集权与财政分权的总体背景下,地方官员会极力显示自身执政才华与突出任期业绩。因此,中央政府的发展目标通过层层加码下沉于基层组织,而作为实施具体政策的地方政府官员,理性做法就是做出具有偏向性的财政支出与收入行为,进而顺利达成上级政府所要求的实际绩效。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官员以GDP为衡量尺度。随着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晋升体系逐渐囊括了环境保护、生态资源与科技创新等发展质量因素,这时的晋升标尺逐渐也就转变为创新投入与生态保护力度。无论任何晋升激励政策,都会在下达地方的过程中产生一定程度的扭曲与失真,这便极可能引致地方政府出现过度干预市场、懈怠监管或是政企合谋现象。
(六)官员行为约束低效
虽然我国政府已经实施行政领导负责制与责任终身制以限制地方官员干部的鲁莽性行为与自利性行为,但是这种约束机制严格而言属于软性约束,需要得到进一步调整与改善。一方面,前任政府进行“摊大饼”式发展与“一刀切”式干预,导致接任者需要为前任的各种行为进行买单,但由于我国现行指标体系、标准体系、评价体系、统计体系仍旧不完善,因此无法科学判定与合理界定现存问题的责任源头究竟属于前任或是现任,因此行政领导负责制发挥实际效用也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中央政府期望通过转移支付手段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与改善央地政府关系,但一些辖区政府会将其视为中央对地方的承诺与兜底行为,进而忽视已有约束机制与法律规定,例如地方政府组织会主动降低财政努力或者进行透支式支出,以期望获得中央政府的最终救济,这种情况毫无疑问会对辖区政府的社会经济治理体系运行产生重大影响。
三、数字时代政府治理现实问题的溯源探本
为科学与合理解决当前政府组织面临的主要现实难题,应有效寻找这些问题的真正原因,探索本质与追溯源头,方可对症下药与有的放矢。当前导致我国出现诸多治理难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根源:
(一)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第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信息不对称。一方面,在我国纵向层级治理框架下,中央政府通过向下级传达信息以明示主要的晋升标准与连任要求,但是在标准信息层层递进的传达过程之中,信息容易出现扭曲与失真现象,进而导致地方政府所掌握的信息偏离中央政府。另一方面,无论是实际地理距离或是虚拟心理距离,地方政府更能完全掌握辖区事务信息与发展诉求,而中央政府掌握关于社会大众群体的基本信息则相对有限,进而导致央地政府信息结构出现失衡。第二,地方组织内部各个部门信息不对称,我国政府组织属于条块式行政结构,不同的职能机构掌握差异化数量与质量的信息,一般情况下主管部门对于所管辖领域拥有的信息更加多元与充足。第三,政府部门与社会群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虽然近些年我国政府不断拓展交流渠道与构建沟通长效机制,但是实际效果并非特别理想,囿于主观或客观原因,群众无法完全掌握政府部门与行政组织所希冀传达的信息,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可能是政民沟通效率低下,部分渠道仍旧拥挤与堵塞[4]。另一方面是我国国民群体受教育程度偏低,有限理性与理性无知导致居民在接受政府信息过程中出现理解偏差,但无论是何种原因均会加剧政府部门与社会群众的信息非对称程度。
(二)认知行为固化
政府组织在处置日常业务与办理行政事务时容易产生心理锚定效应,延续以往的行政理念、办事流程、管理方式与监督模式,进而高度限制自身认知决策与实际行为。过度的路径依赖会大幅降低公务人员的创新动力与积极性,使得普通百姓对政府治理体系产生教条化、刻板化与僵硬化印象[5]。而在现实语境中,经济与社会环境持续演进,科技与产业不断更迭,我国政府组织的治理场景与实践情境已然不同往日,如果继续沿用傳统的治理观念与监督理念,则会严重固化自身认知行为,对一般事务办理与监督管理产生严重阻隔[6],降低国民群体对政府治理体系的好评度与赞誉度。究其深层次原因,党政组织机关单位中出现认知行为固化主要是由于公务人员转换成本过大,而实际收益较小。因此政府工作人员通过权衡利弊则倾向于“按部就班”与“一板一眼”,进而按照自己已经熟练掌握的方式方法与习惯流程开展事务处理工作。
(三)技术装备不足
世界产业变革与科技革命方兴未艾,在经济新常态阶段我国政府组织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具有复杂化、多元化与广联化等新特征。而当前我国基层职能部门的通用设备与一般装备比较陈旧老套,折旧与损坏程度较高,部分硬件装备甚至已经失去主要功能与用途。如果组织单位继续沿用传统科技装备与硬件系统将无法全面考量新问题的特点属性,进而无力解决具有时代特征的重大难题。换而言之,政府组织技术装备如果无法得到及时的更新与替换,则会产生信息传输卡顿、系统功能故障、打印重叠乱码、网站界面失效等一系列技术问题,对基层人员与前线人员办理公开业务产生客观桎梏[7],情况严重时将导致职能机构无法正常运转。因此,为顺利适应这种客观趋势性变化,政府组织的硬件设备与技术装备升级便顺理成章被提上治理改革议程之中。
(四)人才特点专一
无论对于宏观经济社会发展、中观产业结构升级与微观生产效率提升,人力资源均扮演着不可比拟的重要角色,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同样也是推动我国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发展的强大动力。我国政府公务人员与事业编人员虽然经过严格的考试选拔与政治审核,相对其它行业的工作人员而言具备较高的素质水平,但毋庸讳言我国政府组织工作人员主要呈现技术单一化与能力专一化特征,业务素养与水平仍旧需要进一步提升。随着数字经济与共享经济的递进萌发,政府组织所需解决的问题逐渐涉猎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社会多领域与数理、金融、通信、心理、法律多学科,当前我国政府人才结构则以高度单一专业化为主导,而复合型与综合型人才缺乏导致行政组织部门在处理某些交叉性与复杂性难题显得捉襟见肘,这也将会直接导致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某些问题长时间无法得到彻底根除。
(五)治理主体单调
我国治理结构主要体现为以政府为主导与社会组织和群众辅助参与,治理主体权利与责任较为失衡,且治理形式与治理手段较为单调。诚然依据公共管理理论,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权威政府可以合理提供公共性产品服务与有效处理市场失灵问题。特别是在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有制度优势基础上,我国政府组织可以科学解决与妥善处理诸多社会顽疾,并不断完善与优化自身,进而打造有为政府与全能政府[8]。但是治理主体偏向性与治理手段单调性会导致我国治理系统在如前文所述部分新兴领域的治理监督中事与愿违。以政府组织机构与事业机关为主要治理载体,则会忽视社会主体与市场主体在监督管理方面的才能与优势,无法在全域范围内汇聚多样化治理分力形成强大治理合力,进而影响我国治理主体在经济、社会、生态治理领域的统御作用。
(六)组织协调能力欠缺
我国政府组织与职能部门协调能力欠缺也是我国决策层与实务界亟须充分思考的重大议题。主要体现为地方政府之间协同能力与交互能力不足,面对具有外部性的生态污染与自然保护等环境议题,各个辖区政府“心思不往一处用”,无法“拧成一股绳”,解决生态保护问题也就成为一纸空谈。而以往的联席工作会议制度与信息传递机制起到的作用相对有限,仍然需要不断改进与适时调整。因此,对于区域公共领域的治理经常会使地方政府出现“各自为营”与“以邻为壑”现象,策略性模仿行为与逐底行为竞相出现也就稀松平常[9]。与此同时,政府组织内部各个职能部门也展现出协调无力与无序的严峻问题,由于信息不对称、职责不清晰或是权力不对等现实原因,各职能部门对于同一经济社会事务的处置具有差异化的思考范式與实施方式,大幅降低政府组织的行政效率与治理绩效。
(七)制度配套不健全
制度配套不健全一方面体现在时间维度层面上我国配套制度与法律法规衔接度有限。根据制度经济学相关原理,宏观政策组合应当严格遵从时间继起性。政府组织的前期、中期与后期政策法规理应具有较高程度的衔接度与具备较为良好的契合点,如果政策设计制定的时序性或是逻辑性较差容易出现制度混乱或是制度缝隙,进而无法获得最初预计的实际落地效果。另一方面体现在从空间场域维度观察,当前我国制度框架下细化政策配套力度不高。中央政府与决策层基于多种现实因素进行全面性考量,从顶层设计视域出发进行总体布局,但是顶层行动纲领与政策章程需要地方政府辅之出台具体细则法规与应用指南等配套关联政策才能够得以顺利实施。缺乏必要的配套制度将会限制制度红利的释放与溢出,进而在全领域衍生诸多治理与监管难题[10]。
(八)激励约束机制失效
根据激励约束行为理论,如果市场经济中没有科学合理的长效机制对行为主体进行严厉约束或强大激励,市场主体的主观积极性与自发能动性将会受损,导致市场中个体行为或是集体行为出现无谓效率损失,最终偏离于社会经济系统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具象化于政府治理语境,一方面,激励机制缺位或是失效将会引致地方官员或公务人员进行机械式与敷衍式工作,打击行政人员的工作热情与办事态度,选择性忽视甚至纵容不合理现象发生,降低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与处置效率;另一方面,缺乏有效约束与惩戒机制无法实现“将权力困在牢笼里”,政府工作人员极易出现滥用权力与违规操作行为,在部分环节预设与拓展设租寻租空间,甚至被既得利益集团轻易俘获,黑化成不法之徒的“代言人”,进而严重影响政府公众形象与治理成果。
四、数字时代的政府治理转换机制分析
数字时代的骤然来临为我国政府治理转型升级提供绝佳的机会窗口,中央政府与各级行政组织应牢牢抓住此次机会,借乘数字化发展浪潮,顺势而为转变治理方式、优化治理结构与转换治理动力,促进政府组织数字化、信息化、协同化与智能化转型升级,进而加快我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步伐。数字实践背景下政府治理转换机制可从以下几个维度予以解析:
(一)数字时代治理认知更新
数字浪潮以惊人速度有机融入我国社会经济系统的多领域与多环节。在生产维度,数字经济通过重塑厂商组织的日常决策模型与认知架构,进而影响相应经营与产出行为。在消费层面,数字经济的泛化高度影响需求者的偏好与诉求,进而改变消费者购买与投资行为。在治理领域,数字经济新业态也潜移默化与我国治理体系产生新交集。我国政府组织与部门机关应适度转换传统治理理念与思维认知,深度构建以广大人民群众现实需求为核心的互联网思维与数字思维[11],重塑新型治理认知范式,调整各级政府组织治理行为,进而提升政务能力与政府效率。传统治理理念强调以职能部门为核心,强调从供给侧划定优化治理领域,调整监督方式与管理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偏离国民个体与社会群体的真实需求,严重影响我国政府机关组织的公信力与号召力。因此,政府治理理念应进行数字化调整与转型,注重以国民群体最迫切与最真实的诉求为导向,依靠信息中心与虚拟平台收集市场异质性无序数据,借助大数据与人工智前沿数字技术对搜索记录、词条语义、地理位置、消费情况等信息进行结构化处理与整合[12],确定所需治理领域与环节,提升政府治理的精准度,进而科学制定管理条例与监督方案,提高治理结构供给需求匹配度,消弭传统治理理念下的无谓损失[13]。
(二)数字时代治理技术升级
数字科技的迭代式演进为政府部门与职能机构硬件设备跨越式升级提供完美契机。一方面,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为依托的数字科技可以促进传统硬件装备升级,改善固有设备性能与强化其工作支撑属性,盘活组织内部机器存量,促进业务信息化、办公线上化、工作协同化、反馈数字化发展[14],大幅降低运行成本与治理成本,提升政府部门的办公绩效。例如,近年来我国多个省市已经开展政务一体化系统建设,加快政府数字化与智能化转型步伐,力争实现“一网通办”与“最多跑一次”,例如浙江省“数字政府”、广东省“粤省事”、黑龙江省“数字龙江”、安徽省“皖事通办”等创新试验正如火如荼的稳步推进。另一方面,政府部门通过有意识装备最新数字科技,促进治理技术发展与进步。前沿技术与工艺的嵌入可以有效处理与解决以往硬件系统无法处理的问题与困难[15],例如超大规模数据存储、实时信息传输、反馈及时沟通与接口标准统一等问题均要求政府组织配套较高科技含量的硬件设备。政府组织将软件定义网络、数字孪生、虚拟现实与类脑计算等最新科技用于政府日常办公办事流程,可以优化材料提交、业务咨询、项目审批、证照发放、政策解读等行政环节[16],大幅提升政府治理效率与服务水平。
(三)数字时代组织结构优化
数字时代下,政府组织结构借助数字手段因势利导改变与转换以往层级化与垂直化运行框架,调整各个职能部门的相对位置,从而促进其自身向扁平化与协同化组织结构有序变迁。政府部门借助万物互联互通、数据精准分析、计算高速运转与信息瞬时传输等作用途径[17],有效打破组织内部的行政壁垒与机构分割,促进党政部门组织一体化转型升级。一方面,政府组织通过应用数据可视化与智能分级分类工具系统建立电子政务目录体系,强化政务资源的集中与分拨效能。数字组织实质是将物理上分散的组织聚集于网络世界中,构建逻辑集中与安全可靠的信息大系统,充分发挥集聚效应与溢出效应,大幅降低各个职能部门的信息非对称与非完全,避免出现数据孤岛与数字烟囱[18],进而促进数据信息实时共享程度提升,强化职能部门之间的协同与互动。另一方面,将区块链的分布式共识、智能合约、组网加密、时间戳验证等新型机理合理嵌套于政府单位内部的行政机制与操作系统,大幅提升组织本身的技术含金量。形构扁平化与协同化的数字政府组织能够减少行政纵向扭曲与失真[19],降低政府内部沟通成本与交流成本,改善机关单位组织的运行体系,优化资源配比方式与配置结构,显著提升政府组织整体行政能力。
(四)数字时代政府人才建设
数字经济有序演化为政府人才队伍建設提供崭新机会窗口。一方面,数字经济优化政府人才配置结构,提升公共政务办理效率。自动客服与智能机器人可以承担大量的机械式与流程式任务。而有些工作例如心理疏导、概念解析、服务引导、纠纷调解等行政事务需要情感、信任、认知、预期等主观因素。因此,政府组织应用数字科技能够将办公人员从繁重的物化劳动事务中解放出来,将公务人员配置到非程序化与抽象化工作之中[20],进而提升机关组织的人才配置效率,实现人尽其用与才尽其专。另一方面,以往政府雇员想要进行自行充电受到时间与空间客观限制,学习成本及相关费用较高。在数字经济时代,政府工作人员可以借助智能终端、移动设备、可穿戴工具扩充培训渠道与途径,突破固有时空约束条件,增加自身受教育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提升政府公务人员的专业化素质与数字化能力[21]。因此,数字经济发挥知识溢出与学习教育效应促进国家公务人员队伍向掌握多个学科与领域的综合型与复合型转变,同时升级组织内部公务人员的配置与分工结构,充分释放出巨大政府人才红利。
(五)数字时代政府制度供给
制度供给是一项系统性与全局性重大工程。在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时代,制度供给既要避免出于善意的政府干预过度或者不足情形,又要刻意躲避由于疏忽大意诱致的制度重叠或空白现象,同时任何规章制度与法规细则不能事前充分模拟与普化推演,也不能事后随时调停与无故废除。数字经济合理演化可以有效降低我国制度设计与确定成本,大幅提升制度供给合意性,优化我国制度结构与政策体系[22]。一方面,政府组织可以及时发现旧制度的不足与缺陷,对传统制度进一步完善。政策制定部门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超级计算与增强现实等前沿数字科技,可以优化研究与制定流程规章制度,同时预测细则法规落地成效与实施难度,极大降低制度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强与先前相关政策的衔接性与耦合性[23],进而为新制度的颁布与新政策的落实提供科技助力。另一方面,政府组织全面将数字科技纳入政策制度与法律规章的制定全流程中能够提升政府重大政策与配套政策供给的科学性与整体性,为地方政府及时出台辅助细则提供充足数据支撑[24],通过构建智能政务系统与大数据管理系统为顶层设计平稳下沉提供科学决策分析,优化制度政策供给结构,在严格遵守经济社会总体发展布局的前提下,保障地方配套体系与中央顶层制度的契合性与一致性。
(六)数字时代数据知识管理
工业互联网、大数据、量子通信与生物识别等数字科技跨越式发展可以充分挖掘与收集虚拟世界中丰富的实时数据信息,同时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将数据确认为与土地、劳动、资本、知识、技术与管理处于同等地位的生产要素,这也充分表明数据对于国民生产或生活行为的重要性已经得到党中央的高度认可。而数据元素在政府组织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扮演身份也不容小觑。一方面,政府数据池与数据库是职能机关前期细则制定、中期政事办理、后期服务改进的重要决策依据,多样化的数字手段为行政组织提供超大规模的信息原料[25],从而提升数据存储规模与备份数量,为职能机构随时调用与全面分析提供先决条件。另一方面,知识图谱、音射频识别、智能传感器与人机交互等前沿科技可以发现庞大数据潜在隐藏与不易察觉的内在联系,萃取与提炼其中宝贵精华,进而形成可读性与含金量更高的知识库存[26],为政府组织的决策认知与实践行为贡献有力知识支撑。新知识的创新发现与合理应用不仅直接精简部分中间环节与冗余环节,优化整体办事流程与升级政务供给结构,而且可以通过溢出效应与扩散效应强化政府雇员的能力素养[27],提升办事效率与服务水平,进而间接提高公共部门的整体治理绩效。
(七)数字时代监督主体调整
数字经济内生的互联网中介平台与信息平台等虚拟组织可以为我国治理主体提供交互载体,适度扩大治理主体规模,进一步丰富我国治理主体,促进我国以政府为主导的治理结构向政府、企业、媒体、工会、群众协同治理结构合理转变[28],从而促进治理体系现代化发展。数字虚拟组织的构建不仅为政府向社会主体传递政策信号与文件细则提供有力平台支撑,显著提升自上而下式信息垂直传达效率,同时也为市场行为主体与社会经济主体深度融入国家治理提供机会与可能性。平台机制与对话机制的构建可以促使政府组织有效吸收群众反馈建议与投诉意见,保证底层民众现实诉求与强烈需求在自下而上传递过程中的完整性与真实性[29],与此同时以政务微博、微信公众号、政府官网与智能客服系统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数字虚拟平台也可以有力促进媒体、企业、工会、学校、群众严格监督与约束机关单位公职人员日常行为,进而减少在编人员懒政与庸政现象,降低不作为或少作为行为发生概率。总而言之,数字经济发展可以加强政府群众互动的频率与效率[30],扩增治理结构与规模。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演进高度彰显我国治理体系的民主性与参与性,有效提升社会主体的认同感、满足感与荣誉感。
(八)数字时代外部环境营造
数字经济有序发展可以通过强化基础设施建设与文化氛围塑造,优化市场营商环境,提高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配置效率,为政府组织有机治理社会、经济与生态三元系统提供外部环境保障[31]。一方面,工业互联网、新能源充电桩、4G/5G基站、超级计算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可以降低国民群体获取市场数据的鞋底成本与搜寻成本,提高企业组织的决策效率与生产效能,进而提升全体人民的生产生活便利程度,同时人工智能、云计算、数字孪生、软件定义网络可以促进传统基础设施的转型升级,延长使用寿命与扩充覆盖面积,大幅提升实际功效。因此数字经济通过发挥基础设施建设效应夯实职能组织行政治理的硬件基础与底层架构[32],为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型提供硬环境保障。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演化营造出更为和谐与宽松软环境,在崇尚创新与自由的文化氛围之内,政策制定部门通过出台系列细则法条规范以调整市场主体行为决策的通行做法便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进而顺利引导经济社会主体形成理性预期共识,有效提升我国政府组织部门的公信力与影响力。
五、研究小结与对策建议
本文在客观分析当前我国政府组织治理过程中出现的主要现实问题基础上,深层次辨析显性治理难题的属性本质与根源实质,同时充分结合数字实践背景与发展环境,从源头治理视域出发,全面厘清数字时代我国政府组织与职能部门治理现代化转换机制。为有效促进我国政府治理顺利转型升级,现提出以下靶向性政策意见与建议:
(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外部硬件实力
首先,政府组织应加大财政支出力度支持工业互联网、新能源充电桩、云计算中心与5G基站建设,夯实政府治理的数字底座。其次,成立政府投资基金与产业扶持基金,吸引众多民间投资与社会投资,撬动市场中闲置社会资本为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数字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规模性金融支持。最后,大力促进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对参与基础设施数字化、智能化与信息化升级维修的企业主体予以贴息贷款、税收抵免、财政补贴与背书担保,充分推进传统基建的转型升级工程。
(二)塑造包容文化氛围,保障行政治理环境
首先,在政府内部树立创新与包容氛围。官員政绩与能力的综合评价体系应更多纳入供给初衷因素与方法过程因素,并非完全取决于最终政务处理结果,并采用区块链与超级计算进行科学衡量。其次,借助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数字科技塑造不同应用场域,建立崇尚创新、大胆创新、乐于创新、勇于创新的文化氛围,提升社会成员试错容忍度与宽容度,构建社会主义数字新风尚。最后,强化市场主体与政府组织的协同互动,科学塑造公平、正义、透明、平等的治理生态圈,优化社会经济治理外部软环境。
(三)提高教育培训力度,夯实政府人才基础
首先,政府组织应当强化对公务人员再培训与再教育,通过专家讲座、政企合作、项目实践、平台交流等多样方式提升工作人员的数字化办公能力,提高在编人员的数字素养与水平。其次,重视对国内外综合性与复合型人员的引进与聘用,具体从待遇薪酬、配套福利、绩效评价、子女教育等方面进行调整与完善,以提高政府组织对数字型跨学科人才的吸引力与影响力。最后,加强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厂商、工会组织的协同互动,通过外聘专家、提供兼职岗位与增添附加头衔等方式有效降低政府雇佣成本与转换成本,提升政府工作人员与数字科技的耦合度与粘合度。
(四)聚焦攻克前沿科技,强化数字政务能力
首先,中央政府应集中与配置资金、人才、管理与知识等重要资源,构建涵盖大型企业、科研院所与高等院校的综合性网络创新系统,主攻当今世界非对称技术与杀手锏技术,为行政组织机构治理现代化提供强大的“弹药库”与“武器库”。其次,各层级政府应当及时更新机器设备与操作系统,配备最新科技与工艺,促进数字科技与行政流程全方位融合,降低日常运行成本与办公费用,缩短政务办理时长周期。最后,应充分结合治理场域,创新治理新业态与治理新模式,合理采用监管科技与金融科技进行全天候监督与实时管理,促进行政机关数字政务能力与信息服务能力提升。
(五)优化政策法规体系,提升制度配套水平
首先,促进数字科技与政策制定的有机融合,形成以数据分析、数据决策、数据监管、数据评价为主导的治理新方式,提升职能部门前中后期政策的衔接性与一致性,充分借助数字科技有效释放制度红利。其次,鼓励辖区政府对顶层设计进行数字化与智能化分析,并通过应用前沿理念与先进技术合理出台地方配套细则与辅助指南,进而优化政策体系与制度结构。最后,以新问题与新难题为导向科学构建舆情分析综合系统,全面捕捉市场情报与演化动向,强化研判处置与容灾备份基础功能,提升政府机构预测精准度,进而防患于未然将非系统性风险降到最低水平。
(六)构建互动长效机制,扩大数据共享范围
首先,各级政府应系统整合专有网络,统一数据流转格式与接口标准,建立资源配置与安全可靠的政务信息大系统,促进政务数据能够在政府组织横向与纵向自由流动。其次,加快构建信息数据分享平台,加大公共数据对外开放程度与普惠程度,优化政务资源目录体系,使更多社会群体与个体能够及时获得完整与真实的公共数据资源。最后,形构政民沟通交流长效机制,加强官方网站、政府微博、电子信箱、智能通讯等数字平台建设力度,扩充老百姓反馈途径与投诉渠道,从而广泛聆听不同群体声音,提升行政单位与国民群体的互动频率。
[参考文献][1]王孟嘉. 数字政府建设的价值、困境与出路[J].改革,2021(4):136-145.
[2]戴玉祥,卜凡帅. 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治理信息与创新路径——基于信息赋能的视角[J].电子政务,2020(5):101-111.
[3]赵娟,孟天广. 数字政府的纵向治理逻辑:分层体系与协同治理[J].学海,2021(2):90-99.
[4]HA T T. Empirically testing the public value based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evaluating egovernment performance in Vietnam[J].Modern economy,2016,7(2): 140.
[5]POLITES G L,KARAHANNA E. The embeddedness of information systems habits in organizational and individual level routines: development and disruption[J].MIS quarterly,2013,37(1): 221-246.
[6]WIRTZ B W,PIEHLER R,THOMAS M J,et al. Resistance of public personnel to open government: a cognitive theory view of implementation barriers towards open government data[J].Public management review,2016,18(9): 1335-1364.
[7]刘淑春. 数字政府战略意蕴、技术构架与路径设计——基于浙江改革的实践与探索[J].中国行政管理,2018(9):37-45.
[8]鲍静,范梓腾,贾开. 数字政府治理形态研究:概念辨析与层次框架[J].电子政务,2020(11):2-13.
[9]KLIEVINK B,JANSSEN M.Realizing joined up government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stage models for transformation[J].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2009(20):275-284.
[10]张丽,陈宇. 基于公共价值的数字政府绩效评估:理论综述与概念框架[J].电子政务,2021(4):1-15.
[11]LUNAREYES L F,GILGARCIA J R. Digital government transformation and internet portals: the coevolution of technology,organizations and institutions[J].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2014,31(4): 545-555.
[12]CARTER L,BELANGER F. The utilization of egovernment services:citizen trust,innovation and acceptance factors[J].Information systems journal,2005,15(1):5-25.
[13]戴長征,鲍静. 数字政府治理——基于社会形态演变进程的考察[J].中国行政管理,2017(9):21-27.
[14]GILGARCIA J R,DAWES S S,PARDO T A . Digital government and public management research: finding the crossroads[J].Public management review,2018,20(5): 1-14.
[15]CHRISTOPHER H,OLIVER J,COLIN S.Regulation in government:has it increased,is it increasing,should it be diminished?[J].Public administration,2000,78(2):283-304.
[16]谭必勇,刘芮. 数字政府建设的理论逻辑与结构要素——基于上海市“一网通办”的实践与探索[J].电子政务,2020(8):60-70.
[17]胡重明. “政府即平台”是可能的吗?——一个协同治理数字化实践的案例研究[J].治理研究,2020(3):16-25.
[18]逯峰. 广东“数字政府”的实践与探索[J].行政管理改革,2018(11):55-58.
[19]MARIA K,ANDREW B.Digital government:a primer and professional perspectives[J].Australia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2015,74(1):42-52.
[20]李军鹏. 面向基本现代化的数字政府建设方略[J].改革,2020(12):16-27.
[21]郑磊. 政府治理的效度、温度和尺度[J].治理研究,2021(2):5-16.
[22]叶战备,王璐,田昊. 政府职责体系建设视角中的数字政府和数据治理[J].中国行政管理,2018(7):57-62.
[23]黄璜. 数字政府:政策、特征与概念[J].治理研究,2020,36(3): 6-15.
[24]高翔. 建立适应数字时代的政府治理新形态[J].探索与争鸣,2021(4):141-146.
[25]黄璜. 数字政府的概念结构:信息能力、数据流动与知识应用[J].学海,2018(4):158-167.
[26]VETRO A,CANOVA L,TORCHIANO M. Open data quality measurement framework:definition and application to open government data[J].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2016,22(2):325-337.
[27]YANG T,ZHENG L,PARDO T. The boundaries of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integration:a case study of Taiwan egovernment[J].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2012,29(1):51-60.
[28]KHAN G F,SWAR B,LEE S K. Social media risks and benefits: a public sector perspective[J].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2014,32(5): 606-627.
[29]EBBERS W E,JANSEN M G,DEURSEN A J.Impact of the digital divide on egovernment: expanding from channel choice to channel usage[J].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2017,34(3): 685-692.
[30]達雷尔·韦斯特.数字政府:技术与公共领域绩效[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15-20.
[31]徐梦周,吕铁.赋能数字经济发展的数字政府建设:内在逻辑与创新路径[J].学习与探索,2020(3):78-85.
[32]CASTELNOVO W. A stakeholder based approach to public value[C].Proceedings of 13th European conference on egovernment,2013: 94-101.Modernization of Government Governance in the Digital Age:
Realistic Dilemma,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and Practice Path
ZhangTeng,JiangFuxin
(1. Business School of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China;
2. Jiangsu Innovative Economy Research Base, Nanjing 210023,China)
Abstract: The digital wave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ig data, block chain and cloud computing as the core has swept through, deeply reconstructing multiple operation systems and many development fields in Chinas economy and society. In the digital era, the alienation of traditional problems and the frequent emergence of new problems are the major governance challenges that can not be avoided by Chinese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puts forward more stringent requirements and standards for the governance of government affairs.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main practical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process of Chinas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governance,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essence and root of the explicit governance problems.At the same time, fully combined with the digital practice background and objective environment, star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urce governance, this paper also comprehensively clarifies the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of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Chinas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and functional departments in the digital era.Finally, targeted policy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government governance to adapt to and lead the new digital development stage are put forward.
Key words:digital age; government governanc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conversion mechanism
(责任编辑:张积慧)
收稿日期:2021-11-06
基金项目:江苏省软科学研究项目《江苏建立技术交易市场的体制机制研究》(BR2017047);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数字金融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制研究》(1812000024410);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江苏交通基础设施与制造业产业链匹配效率的提升路径研究》(20EYC005)。
作者简介:张腾(1990—),男,黑龙江牡丹江人,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数字经济与政府治理;蒋伏心(1956—),男,江苏南京人,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创新经济研究基地首席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创新驱动与产业经济。DOI:1013253/j.cnki.ddjjgl.20220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