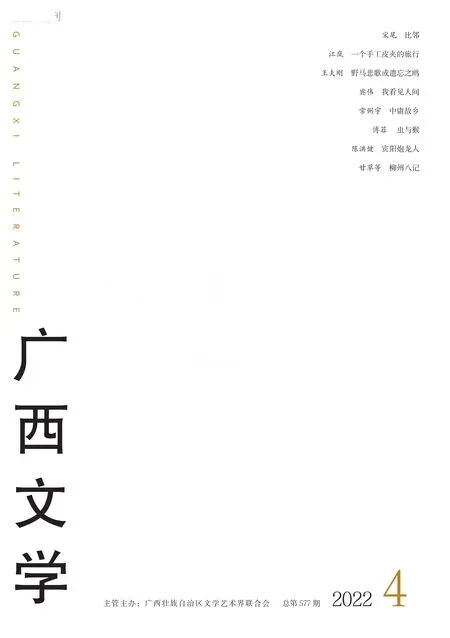奎县记忆
油 事
二嫂姓张,大个儿,大眼睛,大长腿,一说话笑盈盈。
张二嫂长得漂亮,嘴巴还甜。她不叫你点啥不说话,不先笑不说话,一样的话在她嘴里说出来就好听。人们都爱和张二嫂唠嗑,说听她说话像听“水萝卜”唱二人转。水萝卜,民国年间奎县二人转的角儿。
偏偏二嫂还不是麻鞋帮上绣牡丹——中看不中用,而是家里外面样样拿得起放得下。
张二嫂嫁到二佐,立马拉长了全村男人的目光,扯歪了全村女人的嘴。张二柱子,你小子真有福气。啧啧,老天爷,不公道,好事咋都让她一个人占全了。
张二柱子脸上带着笑,腰板拔溜直,说话都带着几分自豪与得意。村里的女人不免对自己家的男人多看了几眼。大咧咧的王桂兰从来没有经管过她男人,这回也上心了,一边站在大街上用围巾擦手,一边喊,振堂啊,回来吃饭吧!一贯大嗓门的她,语调低了许多,还多了点温柔的味道。人们听了都笑,大兰子,你这动静咋还拐好几道弯呢?桂兰一瞪眼,你们老爷们不就乐意让我们多拐几个弯嘛!
张二柱子和我家是邻居。我们两家院子中间只隔着一米多高的垡子墙,自打张二嫂进了张家门,我媳妇也温存了许多。王三冲我媳妇高声念叨:近水楼台先得月,防火防盗防对门哪!我媳妇一撇嘴,你以为我是你家那娘们,心眼跟针鼻似的?
有一天,张二嫂从院外背了半袋东西,不知道里面装的啥,但看她的样子很吃力,我回头往屋里瞅瞅,迟疑一下,还是从垡子墙跳过去,跑到她面前,但是张二嫂说啥也没让我替她背。
等我又从垡子墙跳回来时,媳妇开门出来了,说你力气挺大呀,赶快去粉料,还等猪饿得嗷嗷叫啊?我说,晚上小峰的四轮子就回来了,那么远我还能扛去?媳妇瞪了我一眼,咋不能,溜光大道,也不用你跳墙!我一听,连连点头,然后不紧不慢地说,媳妇,我去粉料,你收拾收拾锅台碗架子!
咋了?
好像什么东西坏了,咋那么大酸味呢?说完,我嘿嘿地笑了。
正笑着,一个笤帚疙瘩从房门飞了出来。
1984年的秋天到了,湛蓝的天空中,一行大雁向南斜飞。田野一片金黄。人们在金色的稻浪中,像一条条小鱼。红色的蓝色的四轮子在奔跑,像游弋在稻浪里的小舢板。二佐迎来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的第一个丰收年。
今天,张二嫂家来了不少娘家人帮忙收稻子。一大早,我们正要下地,张二嫂也跳过垡子墙,手里拿个空瓶子,她来我家借豆油。张二嫂红着脸,显得很难为情,但脸上写满了灿烂。大嫂,都说远亲不如近邻,原来只是说,这回体验到了。我也是新媳妇没经验,早应该向你学习,啥都提前预备好了,这临时抱佛脚还真有点手忙脚乱。今天人多,豆油不够了,烙饼没油哪行,丢咱二佐媳妇的手艺呀!我媳妇嘿嘿一笑,借油直接说就行,邻居住着有啥客气的!张二嫂急忙把空瓶子放到锅台上,好呀,谢嫂子。我媳妇找了漏斗,坐到瓶嘴上,拎起油帮壳倒油。张二嫂说道,好了嫂子,行了,别冒喽!我媳妇收起油帮壳,说没满呢。张二嫂笑着说,正好,满了我还不好拿,洒了,可惜了!
一个多月后,张二嫂还油。我媳妇说,你就客气,我那瓶油没满,你这浮溜的,要冒漾了!张二嫂笑,没事,我倒的时候也没把握住,啥多少的,邻居嘛,咱们之间不斤斤计较的。
张二嫂走后,我媳妇拿起她还的油,放下,又拿起我家的油,来回看了几遍,抬起頭,一脸疑惑。你咋了?我不解地问。媳妇说,你看看。我看啥?你看这油好像两样色儿。一个深,一个浅;一个发红,一个发黄。我说是吗,也歪头仔细看,然后直起身,晃了晃脑袋,我啥也没看出来!媳妇伸手点了一下我脑袋,你能看出啥?你等着我给你做个实验。说完,媳妇把张二嫂还的这瓶放在了窗台显眼的位置。
第二天,媳妇拉着我去看,结果我大吃一惊。张二嫂还的豆油在瓶子里有了明显的分界线,大部分色泽深,一小部分色泽浅。我说这是咋回事?媳妇阴阳怪气地说,掺米汤了!
媳妇对我说,她必须把油换回来,但也不和张二嫂吵吵,也不往外张扬,这件事情就咱们两家知道!不过,这女人的心眼挺辣,以后咱们离她远点。我使劲儿地点点头,但心里却爬进一只小蚂蚁。
半个小时后,媳妇心满意足地回来了。
不过,事情没出一个月,屯子人提起张二嫂,都先哈哈地笑两声之后,叫她米汤二嫂。
半年后,张二嫂家悄悄地搬走了。
去年,听人说张二嫂得病离世了,我媳妇抱着我一个劲儿地哭,她说她这辈子就做了一次丧良心的事。我问她究竟,她从始至终咬着牙,没有透露一个字。但我心里又多了一只蚂蚁。
酒 事
二佐村供销社营业室,钱二流子走进来,把一个黑乎乎的酒壶往柜台上一放,撂下两毛铜子,有时是一张蓝色的纸币。常经理面无表情,打了二两小烧倒进去,顺手在货架的匣子里准确地抓出两粒花生米,对,就两粒,一粒不多,放在酒壶的边上。酒壶是铸铁的,由于冬天长期在火盆里煨着,颜色跟个黑泥蛋一样。钱二流子一言不发,捏起一粒花生米,咔咔嚼两下,喉结嚅动一下,抓起酒壶,仰脖喝尽,然后一张嘴,哈出一丝气,捏起剩下的那粒花生米,有滋有味地嚼起来。之后照例没话,径自转身走了。
常经理像是对顾客又像是自言自语,奇怪了,这酒仙,这么喝也没把身子骨喝坏,也没把酒壶喝丢。我在二佐干了五年了,哎,细算下来搭多少花生米了!
钱二流子有家口,三个儿子。他一天离开酒就迷糊,喝上了反倒精神。他端起饭碗就必须喝酒,早晨也不例外,但每次只喝二两。倘若超过这个量,就喝麻嘴了,一斤也能下肚,但那肯定就醉了。钱二流子挺神,他家住在屯子外,可每次他都能迷迷糊糊地摸回去。
钱二流子即使醉了,也从不闹事,也从没有因为没有酒钱儿走歪歪道。这点,二佐人最佩服他。
有一次,钱二流子实在没钱买酒,一狠心拔下锅去卖铁。常经理说,我赊你一回,把锅拿回去,咋喝也得烧火做饭呢。钱二流子回来时,见家门外有只大鹅,伸长脖子东张西望。钱二流子把它抓了回去。三个小子乐了,说这下能吃上肉了。钱二流子一瞪眼,说你们仨轮番去门口站着去,见到找鹅的喊我。055F7C93-FEEA-4AB9-9A80-64A309B57588
最终,大母鹅物归原主。
钱二流子这般喝,迷迷糊糊,整日里如同睡着了一般,干不了重活,生产队拿他也没办法,就让他在队里帮老经管喂马,帮保管员干零活,自然挣最低工分,自然全队他最穷。老队长说,你这么喝,孩子咋整?不结婚哪?钱二流子说,儿孙自有儿孙福,不用爹娘做马牛。我还能把生产队喝黄喽?生产队不黄,我就能喝上酒!
没几年,生产队真黄了,钱二流子的三个儿子也长成了大小伙子。这哥仨把地扔给钱二流子,说你就可这二十亩地喝吧,我们出去打工。上哪呀?钱二流子问。南方,越往南越好。
五年后,钱二流子病死了。虽然过了七十,但二佐人还是有些惋惜,说他岁数还是小点,这和喝酒有直接关系。料理后事的时候,钱二流子的老大回来了。他说那俩弟弟照顾买卖,实在离不开。临走老大把妈妈接走了。
几年后,老母亲过世了。钱二流子三个儿子都回来了,开了三辆好车。他们给父母修了墓,立了碑。又把屯子三家超市的白酒都包了,一下子倒在钱二流子的坟上。大儿子跪下说爸呀,你这仨儿子在深圳发财了,可惜你没福啊,要不天天喝茅台都不是事。说完磕头。接着站起身烧纸,那纸堆得老高,再加上沾上酒精,火一下子蹿起来。一阵大风,着火的纸乱飞,秋干物燥,坏了,坟旁的树被烧着了。
上坟的亲友急忙灭火,有的回屯子喊人,开车拉水,有的打电话报警。屯子人风风火火地跑来了, 消防车呜呜地叫着来了。经过一个小时的奋战,火被扑灭了。但山坡上二十多棵碗口粗的松树烧得面目全非。
钱二流子的仨儿子被带到派出所,后来说要判刑。全屯子人担保,一顿折腾,他们三人最后被放了回来。老大给了村里一笔钱,让人重新栽树,又为村里的主街铺上了沙石路。
屯子人议论,说钱二流子成天泡在酒缸里,虽然成天醉醺醺的,但也没咋地,一辈子没招灾惹祸,优哉游哉度过了潇洒的一生。这哥仨滴酒不沾,却惹了这么大祸。哎,你们看看,这世上的事真是说不明白!
前年我隨扶贫工作队去了二佐,听了这个故事,也看到失火那山坡上重新种植的树木郁郁葱葱,比碗口要粗得多。村主任说,老钱家这哥仨在南方发财了,这些年只要回屯子给他爹上坟,都会给乡亲们买点米面油啥的,家家不落。据说还要给村里安路灯,过了年他打算联系一下。村主任说,现在二佐谁家也没整过钱二流子家,要不是钱二流子喝得一无所有,这仨儿子也不能破釜沉舟,在南方拼出一条路来。哎,你们看看,世上的事真是说不明白!
【于博,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绥化学院客座教授。获首届师陀文学奖优秀作品奖。有中短篇小说、散文发表于《小说月报》《海燕》《芒种》《辽河》《北方文学》等杂志。有作品被《小说选刊》《小小说选刊》转载。出版小小说集《寻找蓝色的眼睛》。】055F7C93-FEEA-4AB9-9A80-64A309B575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