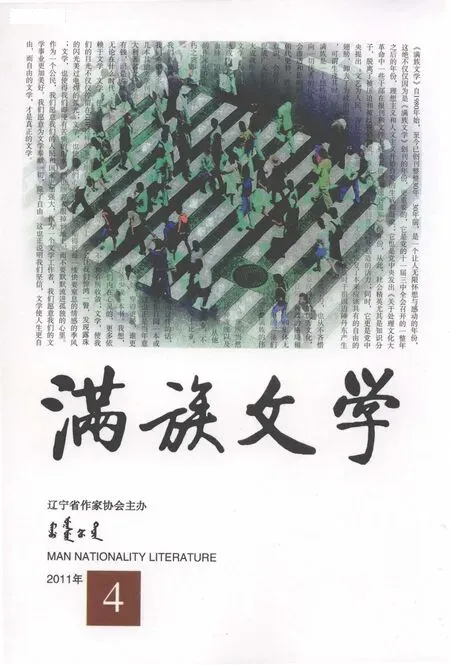私 奔
李广智
我一直对私奔充满好奇,甚至在好些年里一度渴望一次私奔,渴望一位心仪的好女孩儿为我酝酿一次。
私奔这个词,第一次进入我的记忆时,我还小。我压根不清楚私奔代表什么。满屯子的人好像都避讳这件事,也许他们私下说了,可他们不想让我知道这事,大人有大人该做的事,想说的话,他们不想让我们这些孩子知道时,有一百种理由让我们走开,我却毫无理由拒绝。我被大人的一句去菜园看看鸡,拿筐捡点柴去,支得远远的,孩子们的心让我无暇顾及大人那些我还不懂的事情。和伙伴们踢毽子、跳绳、藏猫猫儿,那些游戏一沾上我,我就忘了时间,等到大人开始经管我,让我回到他们身边时,他们说破嘴皮子的话都说完了,不想做的事也都做完了,而我却一无所知。
我是在无意中知道私奔这件事的。那时我还小,我还没一件正经事可做,大人像从树上扔下一个苹果,也许是一个梨一样,把那件事扔给了我。我在旁懵懵懂懂地听。我保持着倾听的姿态,尽管那件事不是说给我听的,我还是用心地听了。我一直认为自己喜欢倾听就是从那时形成的。大人说屯子里的一个半大小子和半大丫头失踪了。说是半大,实际上是介于成年人和孩子之间的一个年龄段。有时,二十多岁没成家的也都包括在内,其实也就是快成年了,在屯子里也该是谈婚论嫁的年龄了。早年,屯子里多半都等不到法律上的结婚年龄,他们通常习惯于老辈人的规矩,只把年龄靠近法定的结婚年龄,偷偷把婚事办了。不像现在,年龄大到父母都愁娶愁嫁了,也不着急。
屯人一定是有些时日看不见两人,失踪可是件大事。开始一定是猜,每个人心里都没准头。可屯子就那么屁股大的一块地方,向前向后向左向右,也只是前院后院左邻右舍的勾当,前脚跟能挨着后脚跟,大事小情都逃不过屯人的眼睛。院子外的一只溜达鸡真要是没有了,也会有上心的邻居搭搭话,问问原委。可现在两个活蹦乱跳的大活人,突然同时在屯子里没了踪迹,这让人很快把两个人联系到了一块儿。先是有心人试着问,后来满屯子的人都注意到了,两家大人瞒不住,不知谁漏了口风,让私奔成了满屯子一件沸沸扬扬的大事。
我记不准那时是春天还是秋天了。屯人忙过了地里的活计,再没一件像样的事可做,坐在院前院后唠嗑,嚼几件有趣的事,再嚼不出味道,就只好说私奔这事了。越隐秘的事总是传得最快的。一屯子人出出进进好像都在有意无意地说这事。可我想是秋天,尽管我同样喜欢着春天,当你进入一片土地,在一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后,你就能真切的理解春天,一粒种子萌动生命的特征,有花开放,花开的声音涌入我们的生命,那声音离心灵是那么近。可秋天的庄稼最密实,草也最深。我看见每年的秋天,风藏在绿的深处,让庄稼和草一浪一浪地涌动,我闻到大地成熟的气息,夹杂着青草类植物的味道,一次一次扑鼻而来,让人心动,或许是心醉。每次闻到那些植物清香的体味,我的心里都有一种飘的感觉,那让我感觉到生命的美好。我站在屯子的高处和低处都只有一种结果,我看不见这些植物掩在下面的任何事物,那一定容易藏住许多的秘密。我的一个初中女同学,就是在一个秋天和一个男人私奔的。他们一定利用庄稼掩护,手拉着手秘密完成一次次约会的,最后无法控制,消失在庄稼地里,成功躲避了大人的所有跟踪,并在隔年,抱回一个娃儿,完成了一次私奔的壮举。可屯子里的庄稼没能掩护住这次私奔。女孩儿家很快直接介入这次私奔事件中。
在很多天里,屯中私奔男女的家长和两大姓的家族都在争论私奔这件事。吵吵嚷嚷的声音不断响彻在屯子的上空。我家地势低,声音没拐弯,被人的嗓门轻声一送,丢到我家院子顶。我仰着头侧耳听他们争辩这件大事,屯子里以前肯定没发生过这样的事。居住在屯子里的人不愿接受这个事实,他们习惯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现在两个孩子没经过大人的同意,还有媒妁之言,他们自己背着父母做主了。或许他们压根就做不了父母的主,认为只有远离父母,他们才可以有这个权利,他们真的这样做了。父母碍于面子,互相指责,寻找弱点,赢取对方。赢家是有一定权利的,至少我是这样觉得。女方赢了,可以向男方追要一些彩礼,给女儿补做嫁妆,圆圆脸面。男方赢了,可以尽量少给,或不给女方彩礼,白捡一个媳妇。可私奔的女孩子家在这场婚姻博弈中,先失一局。
我不记得私奔男女的家长是如何化解的了,那时我还不懂。等到私奔的人回来时,没有哪一位家长不开情面地再去阻挡一场事实的婚姻,剩下的大概就只有彼此协商,让大人在屯人面前圆个脸面了。这是我看到的屯子里唯一的一次私奔。我不知道这次私奔会对屯子产生多大的影响。我始终认为敢于选择私奔的男女,一定有着很深的感情和勇气。数年之后,当成年的脚步开始走近我时,我重新对私奔充满了好奇。
我不知道屯子里那对男女私奔时走的是哪条道路,是黑夜还是白天。我管那个私奔的男人称叔,却不是同姓,这让我一直没勇气问。我还不敢确定私奔对于他们尴尬的程度。那时,私奔对于一个女性家族多多少少是一种羞辱,那让大人说话、办事仿佛矮半分,在屯人面前直不起腰。居住在屯子里的很多人,从心里还不接受私奔的事实。他们甚至死死看住院子里所有母性的动物,深怕院子里在这上面有个闪失。居住在屯子里的人一直在努力保持一个屯子的清白,死死抱住一个旧俗。这或许是一个屯子的道德底线,他们不想让任何事物打破这个底线。
在若干年后的一天,邻屯一户人家的大人没能看住自家的女儿,在花季的年龄和另一个屯子,比她大十多岁的一个男人私奔了,那个女孩儿和自己意中的男人,一个有妇之夫在外面生活了一段时间,怅然若失地回到了屯子,那个男人则回到了自己的妻儿之间团聚,没有离婚再娶的意思,只是两人好像保持着某种暧昧,女孩儿家的大人管不住自己的女儿,活了一大把年纪的母亲,人前人后的抬不起头,任死不接受这个事实,羞愤之余,一气之下投井而去。
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利用上地、割柴、上集,走遍了屯子通往外面的所有道路,可我还是不能断定,哪一条道路才是私奔时走的道路。屯子里的哪一条道路都可以最终走出屯子。一对在秋天秘密私奔的人,一定有一条更隐蔽的道路。他们或许事先探好了路,秘密约定,在屯子的某一处汇合,然后偷着消失在屯子通往外面的道路上。这条道路在白天和黑夜,他们不会走错,或许,也不会碰见屯人。这是私奔成功的唯一途径。我有充足的时间想象这件事,虽然它和我无关。
母亲曾告诉我,弟弟先前的一个女友,也曾和弟弟商量着私奔的。弟弟满足不了他那个女友家父母提出的条件,那个女孩儿想为弟弟“牺牲”一次,逃过父母的这道关口。那个女孩儿一定很喜欢弟弟,她也想利用私奔,帮助弟弟一把,那样也是在婚姻上帮了自己一把,她想利用私奔留住属于自己的幸福。屯子里私奔的女孩儿大概也是这样想的。我们都知道我称叔的那户人家的经济条件一般,真要是让媒人放到桌面上,明媒正娶,男孩家一定会为此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他们用私奔化解了这个矛盾。可我弟弟没能这样做,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放弃了私奔。总之,弟弟最终没能成为屯子里第二个私奔的人,这也让他们的感情像私奔的失败一样,没有了结果。
弟弟的失败也没能阻止我对私奔的好奇。我清楚,屯子里的人,尤其是那些没成家的年轻人,好像越来越不喜欢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了。他们从外面领来年轻的女孩儿,让她们成为屯子里新的小媳妇。我听说她们有些都是背着父母先来到屯子的。我确信这和那个我称叔的那个人当初私奔,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那时,是从一个屯子私奔到另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现在是把别的屯子的女孩儿领了回来。那时,女方家会大张旗鼓的反对,现在父母大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了女儿的选择。我的好奇让我留心了这些。
我好像一直在为另一场私奔而努力,可我始终没能成功。屯子里不会有和我私奔的人。我走出屯子,然后转回来,再走出屯子,然后再转回来,可我一直没找到能和我私奔的人。我被那些可以和我私奔的人,远远抛在一个屯子里。在更多的时间里,我被地里的活计牢牢地困住身子,不能离开屯子半步。
我肯定有过许多可以私奔的机会,我没抓住。一次,一个女孩儿把一封火热的情书送给我,我在脸红脖子粗的羞涩后,转天悄无声息地返还给了人家。还有几次,我在若干个女孩儿数次主动含情脉脉的话语中,不解真情,错过了婚姻的召唤。我是在后来知道这些的,最终浪费了可以私奔的机会。我不知道这是否和我猜不出屯子里哪一条道路可以私奔有关。我确信私奔也是一条道路,它大概和我在屯子里奔走的道路不一样。
我在屯子里走遍了所有的道路,逐渐熟悉了一个屯子,可我却不熟悉屯人,我不知道有一条道路藏在人的心里,它或许深藏在那对私奔男女的心里。我在屯子里习惯了走熟悉的道路,做习惯了的活计。我在很多年里一直习惯于跟在一群屯人的后面走路。或许,我本来就没有勇气在屯子里偷偷地为自己选择出一条道路。我在扛庄稼或扛一捆柴时,曾偷偷试着自己独自走出一条道路,可我没有更多的力气挤倒多余的庄稼,踩掉挡路的杂草与荆条,为自己开辟这样一条道路。那让我在生活中失去了另一些信心,在寻找幸福的道路上荆棘丛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