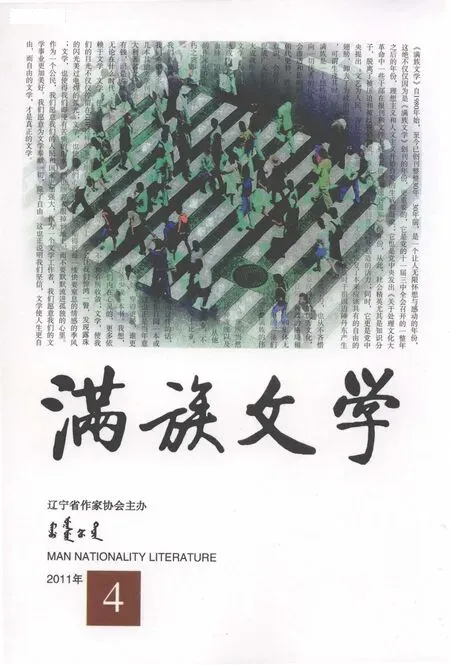目 击
刘照进
颤 动
从我居住的小区出门,往北,沿滨江路,走五百米,相遇一座桥。以前没有桥。以前是一个老渡口,一只渡河船,往返于日子的两岸。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桥修起来了,渡船便被取消,作为地理名词的“老渡口”也被取消了,“大桥”成了它的户籍修饰。
是一座复拱钢筋混凝土大桥。几只桥礅杵在江流里,像在水面行走的多足虫。我从桥头的碑文上得知,桥的修建已有些年月了,像上了年岁的老人,面部呈现出沧桑的斑纹。桥的腿脚和身子骨也像老人,每当有车辆从桥上呼啸而过,桥就禁不住颤动,伴随着轻微摇晃,哐当哐当地咳嗽。
我在桥上感觉到这种颤动和摇晃时,内心也有一种摇晃。我习惯了对生活保持探头探脑,任何摇晃都会让我疑窦丛生。有一种摇晃来自于摇晃者本身。比如树。像大风中自乱阵脚的树。可我无法剔除身上顾虑的枝桠,做一根沉稳的旗杆。很多时候,我外表坚硬,内心柔弱。风一吹,我的惶恐就会飘飞。
好多次,我站在桥上,正遇着桥在颤动,我以为桥就要倒塌。结果没有。桥修改了我对经验世界的误判。我的担忧成了生活的笑柄。
我居住的城市一直在被“改造”,沿江两岸到处是开挖的建筑工地,整天机器轰鸣,尘土飞扬。街道被切割,车辆拥堵,出行困难。橡胶管,下水道,孔桩,沙砾,像被剖开的动物内脏。
满载砂土和建筑物资的大卡车源源不断从桥上轰隆隆地碾过去,桥就剧烈颤动起来,哐当哐当地咳嗽。我在桥上听到了一种碎裂的声音,短促,急剧,像枯枝突然离开大树的身体。我想肯定是桥的某根肋骨断了,桥正经历着身体的伤痛和信念摇晃。我奋力跑到桥头,惊魂甫定,桥却安然无恙。我在心里暗笑自己庸人自扰。
断裂的生活还能修复吗?
大桥轻轻的颤动,仿如生活本身。
我不知道这样的颤动,还会波及到哪一些群体?
譬如,桥下那些暂居的面孔。剃头匠,卖书人,算命先生,残棋老叟,神经病人。我在日常的行走里与他们一一相遇。我开始了自己近距离的观察。有时我站在大桥侧面的石阶上。有时我干脆走到桥洞底下,站在他们身边,和他们说话,问一些奇怪的问题。我像一只寻找食物的蚂蚁,把细小的耳朵和触须贴到大地的表面。
他们的生活有我们看不见的背阴山坡。那里草木独自枯荣,野花为自己打扮,阳光幽微,石头沉默。这是一个公众而又极端私密的场所,他们彼此影响而又互不干扰,他们各自成为各自的个体,各自从各自的世界获得命运的阳光和阴影。
碎 屑
剃头匠在生活的表面留下一大堆碎屑。
剃头匠是个身材瘦削的老头儿,脸上永远贴着微笑的标签。也许是长期低头操作的缘故,他的背上隆起一个明显的包袱。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的手里握着一把老式剃头刀,正准备给面前的幼儿剃“满月头”。孩子躺在母亲怀中,双眼流露对陌生世界的好奇。起刀前,老头儿神情庄重,嘴里念念有词(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种“剃满月头”的封赠仪式)。唰!唰!唰!剃头刀在嫩软的头皮上轻松游走,好似闲庭信步,一绺一绺的胎发便脱落在地。短短几分钟,剃头匠就以娴熟的手艺在幼儿的哭声中完成了一次“精简主义”的启蒙教学。
桥洞外面的一块小平台是剃头匠的领地,摊子前摆着一只小木凳,木凳上斜搭着布裙,手提式旧木箱敞开,里面依次摆放着推剪、平剪、剃刀、碱粉盒、挖耳勺。墙根石壁上挂一面破旧圆镜。对自身形象的在意,使我们对镜子产生强烈依赖。
冬天,剃头匠在地上放一只小铁炉子,煤球在炉膛里烧得通红,尖嘴锑壶蹲在火炉上直冒热气,发出哧哧的声响。大部分剃头人都是那些上了年纪的乡下老人和孩子,还有进城做工的农民。仰首之间,他们就能找到符合自己标准的选择。硬皮纸壳上的潦草书法内容简洁:“光头五毛 平头一元”。省略动词的广告完全符合价廉物美的消费需求。乡村是审美主义的大众影院,尽管美容美发这些时髦名词已将人们的传统审美宪法进行了大规模修改,但依然无法在城市边缘获得完全贯彻。
桥洞下放了一把扫帚,每天收工后,剃头匠都会用扫把清理地上的碎屑,将那些零乱的碎发扫进一只破烂的口袋。他的身影佝偻在地上,扫把一挥,一挥,那些头发碎屑就慢慢团成一堆。
他能扫清生活的碎屑吗?
密 码
记忆中印象深刻的“算命先生”叫“熊八字”,肥胖,瞎眼,身体里装着众生命运的密码,背一把断柄的二胡,脚步沉缓地行走在乡村的各个集市之间,试图为那些迷惘的灵魂指示“路径”。他的二胡独奏不是《高山流水》,也不是《二泉映月》,似乎永远只有简单的过门,但是他在乡间获得了足够的尊重和信赖。他那一双眼窝深陷的瞎眼仿佛可以洞穿任何一颗忐忑的灵魂。
我的母亲曾经暗中找他给我算过“命”,她从“算命先生”手里带回来的纸片像细小的药签。己酉,丁卯,己亥,丁卯,我的“八字”端坐在纸片的四方,对我发出莫测的冷笑。母亲用五元钱的代价让瞎子先生说出了密码。那张纸片一直被母亲锁在箱子的底部,成为我此后命运的远方来信。我的妻子同样在我不知情的时候,悄悄为女儿算过一次命运。在子女通往未来的道路上,善良的母亲们总是率先一步赶往现场。
我在桥底下见到给人“算命”的是一位老年妇女,她眯缝的眼神让嘈杂的中午产生了轻微麻醉。她不给人掐算“八字”,她抽“数牌”,面前的陶瓷缸里,装着六十四张折叠的纸片,六十四种人生结论被人事先书写,埋伏在一场骗局的路口,等待迷信者心甘情愿留下买路钱。
老女人穿着陈旧的布衣,帽子上的花饰有些妖冶。她端坐在石阶上,沉默不语。她的“生意”并不兴隆,一些脑袋在旁边的剃头摊子前停下来,一些眼睛在围观旁边老者摆的残棋,一些腿从她眼前匆匆跨过。她虚坐在中午的时光里,偶尔抬起头来,和毫不相干的生活对视两眼。
我对她面前的瓷缸产生了兴趣,那是一只海碗粗的大灰瓷缸,手柄丢失,大块大块的漆皮掉落,像经风沐雨过后的石灰墙体,露出乌溜的皮肤。瓷缸上暗红的一圈字迹,依稀能够辨别出“农业学大寨纪念”,落款日期和“××公社”的名称却下落不明,像那段热火朝天之后逐渐冷却终被淡忘的历史。老女人以为我是她等待的顾客,双眼燎出瞬间的火光,待读出我的意图,火光便熄灭在眯缝的洞穴里了。
时间在以秒针的脚板往前赶路。
一秒。
两秒。
三秒。
老女人的耐心端坐不动。
男人终于在她的面前停下来,游离不定的眼神似在寻找上苍的暗示。
求财还是问凶吉?话语简短而直接,像侦察兵直插敌人的阵地,经过之处,早已窥探了对方的秘密。
男人一双筋骨突兀的手在瓷缸里触来触去,轻易不敢选择填写自己命运的那一张纸片。男人拣了一张,放弃,男人重新捡了一张,再放弃。也许对于他来说,在他的双手触摸到瓷缸里的纸片的时候,他就错过了自己希望得到的答案。
“命里有的终该有,命里无的莫强求。”女人给了他答案。似是而非。似非而是。
男人拿出两元钱交到妇人的手中,两双手掌隔着金钱相互会心一笑,像情报人员瞬间的隐秘交换。男人取到了他想要的情报,转身,很快淹没在人流里。
明晃晃的阳光下,女人挥起陈旧的袖子,试图揩去脸上的表情。一辆洒水车正从桥底下驶过,淋了她一脸尴尬。
散 落
卖书人在肮脏的地面铺上一层油纸,借助桥拱的遮掩让风雨飘在知识以外。《百家姓》、《增广贤文》、《劝孝歌》、《蟒蛇记》、《满门贤》,多是民间劝善教化的读本。书籍设计简单,印刷并不精美,薄薄的纸张,柔软,泛黄。我欣喜地蹲下身来,慢慢翻看。某些久违的记忆此刻慢慢得到复苏。“昔时贤文,诲汝谆谆。集韵增广,多见多闻。”幼时也曾在乡村的某些书摊读到,此时再见,甚觉亲切。时光飞逝,万物更迭,很多人习惯了在“艺术”面前一本正经,对于这些民间的草本书籍早已不屑一顾。
卖书人银发白须,精神矍铄,鼻梁上架着一副乌溜的老花眼镜,言谈举止显现出超凡脱俗。卖书人爱喝茶,大茶缸搁在身旁,茶缸内沿积着厚厚的茶垢,劣质茶叶浸泡的茶水泛着高粱的猩红。交谈中得知,老者是一位退休教师,感慨于现实的日下世风,于是收集编印了这些旧书。
我对文字充满无限的景仰。我曾在一篇文章的结尾中写道:“我尊重每一个词语。那些颓废的、昂扬的、愉悦的、哀伤的词语,它们原本是那么干净和纯洁……”我因此尊重那些爱惜书籍的人。书收留了流浪的文字,让文字有了薪火相传的家园。从龟甲到竹简到缎绸到纸张,文字的光焰从书籍中一路走来。
曾经一段时间,我对书店充满了彻底的失望。县城以前有一家新华书店,在我上班不远的路段,乱石砌成的老房子,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统一模样,墙壁抹了一层白石灰,人字拱形的屋顶下嵌着大大的五角星,颜色暗淡,像黑白战斗故事影片中片头出现的“闪闪红星”,书店正面还有“新华书店”的毛体大字。那时候,书店里卖很多书,像知识的大仓库。我每次到县城都要在书店里待上很长时间,尽管我没有能力购买我喜欢的所有书籍,但我会在书架前停下来,抽出我喜爱的书籍阅读。看着那些心仪的书,心想有一天我会将它们买回我的家中。那些书也仿佛在默默地看着我,等待我哪一天再与它们相遇。
到我真正有能力买书的时候,那些书却已经失踪。新华书店的楼房先是改造,修建了豪华门面,“新华书店”的毛体大字不复存在,锃亮的玻璃门上印着显目的“某某某名牌服装城”的烫金大字,那些着装妖艳的时装模具,站在玻璃背后,表情复杂地看着世界。
我心爱的那些书籍已经散落在时光的角落里,再也没有人能够找到它们居住的地址。
“河 流”
常常凝注于午夜的电视画面,看到妙美的跳水镜头。修长的两腿直立跳板,凝神,敛气,身子暗中用力上提,脚尖点地,忽然一个旱地拔葱,双手在空中转体下落的瞬间曲抱两腿,一道风车叶子旋转数周后滑落水池,洁白的莲花迅速在水面盛开。仿佛传说中的美人鱼来到眼前,掌声响过,柔滑的姿体依旧在水底游翔……
很多时候,我沉迷这样的画面。几乎每有跳水比赛,哪怕是在深夜举行,也会锁定频道,一个人静静躺进沙发,直至比赛结束。单调雷同的动作反复出现,有时并不能给人特别强烈的快感。只是喜欢比赛的节奏和氛围。恍惚感觉,很少有一项体育竞赛比跳水更加安静,旷阔的室内赛场,即使坐满观众,也丝毫不会感受压抑,除了解说和短促的掌声,很少掀起加油的高潮。运动员的表情隐藏在水中,即使未能取得理想成绩,也只是把泪水埋藏在水中,给人留下的依旧是一脸青春微笑。
人工泳池取缔了河流的深度、弯曲、滩涂、漩涡和永不停息的奔跑,最大限度地消解了户外运动带来的危险和干扰,让身体完全进入设计者的意志轨道。这时的水面总是温静而平和的,过分的安谧,与河流与身俱来的喧闹形成显著对比。
有时看到幼小的运动员,年龄不过十一、二岁,甚至更小,却有一副成年人的持重和成熟,心中不免吃惊。小小年纪便能取得如此成就,之前需要在水中浸泡多少日月?而且是那种重复不变的机械运动。一切都得按照规范的动作和要求来执行,不得出现丝毫差错。孩子的天性被规范在方寸之间,得有多少欲望的诱惑来使他们放弃想象的翅膀?
人似乎越来越充满智慧,对于山川、河流也有能力通过剪裁搬进室内,作为征服的捷径——这让我们接近自然的距离相反变得遥远。
水,在静止中证明了它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