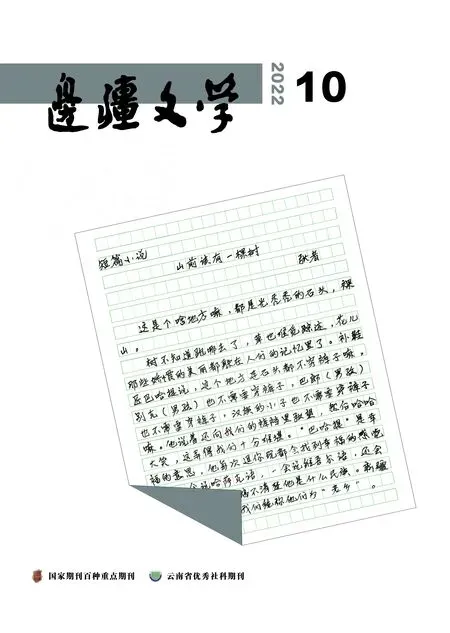天还没黑 短篇小说
巴文燕
缪兰和王栋
一辆大货车咆哮着擦身而过,缪兰感觉那个庞然大物,正洞穿自己的身体。年久失修的水泥路,像散乱的棋盘,棋子与棋子之间的缝隙,斜刺里腾起卷卷灰尘。路面传来空旷或尖锐的碾轧声,时高时低,疑似踩在年久失修的弹簧上。
缪兰左看右看,趁着路面稍显消停,搂着包,迈着碎步,迅速向马路对面移动。
街上有好几家汽车修理店,家家门脸,都像是刷了好几层汽油;门前堆着废弃轮胎、待修汽车,还有千斤顶、风炮等修理工具。一辆辆汽车席卷而过时,传来阵阵劣质汽油味儿、新鲜油漆味儿,以及厚重的泥腥味道。
缪兰走过几家店,来到一条小巷路口,拐进去,也就是百八十米,就是王栋租住的家。
这是一幢两层楼的民房,门口有个小院儿,堆满杂物。院门半开,缪兰推门而入,径直走到最里面一间,敲门,门应声而开。
王栋把她让进屋,倒了杯凉白开,放她面前的长条桌上。
像往常一样,缪兰坐在沙发上,王栋坐对面靠墙一把浅蓝色塑料方凳上,低头刷手机。有时他们一坐就是半个小时、四十分钟。这次时间不长,王栋抬起头来,看她好一会儿,才说,以后你不要来了,没有用的,浪费你时间。
缪兰看了他一眼,没什么反应。
王栋又说,我找了份工作,以后你来估计我也不在家。
缪兰说,你不给我说清楚,我还是会来的。
说不清楚。王栋嗫嚅道,眼睛瞟向门外,五官涣散。
可你说他说了,陈警官也是这样告诉我的。
王栋的双掌,紧紧握着套着黑色外壳的手机。上面污渍斑斑。
他说了是吗?缪兰踞身向前,一副虔诚的探询姿态。
你好好想想,哪怕想出一个字,我都能猜个大概,我了解他,行吗?
王栋凝视着眼前这个执拗的女人,摇摇头,又点点头。他挠几下头皮,说,他可能根本就没有说话……手机在男人的掌心被捏出汗来,他似乎下定决心似的,我是哄你的,他根本就没有说话……我真的要被你逼疯了!
我早就疯了。
声音轻柔而坚定,像一颗尖钉戳进水泥地。而瞬间凄凌的眼神,像口深井,把男人刚刚鼓起的勇气,悄无声息地吸进去。
屋子里的空气与屋外渐浓的秋色相对应,有点凉,有点薄。
有时,湿冷的空气顺着半开的屋门渗进来,如一位不速之客,在狭小的空间乱窜;有时,远处传来黯哑却霸道的汽车长鸣,让两个人的心跟着起伏。
两个人继续枯坐。二者的目光在空中游移,竭力不碰撞,就像两辆狭路相逢的汽车,小心避开对方。即便碰到,也装着不经意间滑过,继续在有限的空间游弋,与混乱的空气纠缠。某个时刻,两人的目光避无可避,撞到一起,硬生生的,干脆对视。
一个想得到某个答案,一个永远也拿不出那个所谓的答案。两个人像在一个漩涡里打转,转了好几个月,也没个结果。
缪兰和马波
对于缪兰来说,活到三十岁,如果有什么幸福的事,那就是遇到马波。马波有点胖,圆脸,戴着副眼镜,什么时候都是笑嘻嘻的,就连睡觉,两个嘴角都是上扬的。缪兰问马波,你为什么总是笑?马波说,我一见你就笑,有时还唱一两句。以后,缪兰就经常问,马波就经常那样答。缪兰心里甜滋滋的。
缪兰和马波都在一家私立医院上班,缪兰是护士,马波在药房。认识不到一年,两人领了证,在酒店办了五六桌,就算把婚给结了。有人戏谑他们租房结婚,两人不以为然,攒着钱呢,不急这一时。
婚后,缪兰一直怀不上孩子。偷偷到别的医院去检查,不出所料,她的输卵管炎症严重,宫体薄,精子不容易着床。医生用刻薄的口吻说,你这是流了几次啊,缪兰全程戴着口罩,不敢看面色冰冷的妇产医生。不久,马波知道了这事儿。问她,缪兰就吞吞吐吐说了过往的不堪。马波当时就沉默了。说,我以为你是处女。缪兰何尝不知道,马波在意这个,她费尽心思才掩盖过去。如今,她只能祈求他的原谅。
第一次,马波无视她的眼泪,像条影子似地站起来,出门,一夜未归。
自那以后,差不多两年,缪兰再难见到马波的笑容。两个人像是套在塑料袋里生活,隔隔膜膜,点到为止,相敬如宾。
有一段时间,有传闻说,马波和一个离婚女人往来甚密。缪兰几番挣扎,向马波提出离婚。马波说考虑考虑。过了段时间,某天马波似是无意提起那个离婚女人,说是他们寨上的远房表姐,从广州回来。缪兰嗤之以鼻,姐?现在很流行姐弟恋。马波扇了缪兰一巴掌。缪兰当即就哭了,哭得地动山摇。马波旋即向妻子道歉,像从前那样小心呵护,还做了缪兰爱吃的炖土鸡。缪兰撑了几个小时,还是吃了。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此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缪兰原谅了那一巴掌,以为都过去了,翻篇了,可她始终没有等到马波明明白白一句原谅的话。缪兰虽有不甘,可也不能强求,她既然软下来,也没有理由再硬起来。总得有个理由吧。
日子就那样磕磕绊绊过着。
缪兰寄希望于时间,但愿时间能疗愈所有的伤,能让她和马波回到从前幸福的生活。哪里又晓得,一辆原本不相干的一辆小货车,会毁了他们全部的生活呢。
前一天,缪兰还凑近马波的左耳朵,一字一顿地告诉他,自己怀孕了。起初,马波似不相信,圆圆的眼睛瞪着缪兰,缪兰使劲儿地点头。马波旋即过去把她抱起来转圈儿。缪兰清瘦,马波抱她,跟举一把刚刚摘下来的新鲜芹菜。马波嘴里呢喃着,我们有孩子了,我们有孩子了。缪兰甚至看见马波的眼里渗出泪来。她也忍不住流泪了,紧紧搂着他,生怕再失去。他把她放下的时候,她在他耳边怯怯地说,你不生气了呵……马波说,从明天开始,每天一只土鸡、一条鱼、六个柴鸡蛋,你可劲儿地吃。缪兰嗔笑,你把我当猪啊。马波壮实的双臂,撑在她肩膀两侧,悬空俯视她,说,我们就做一对快乐的猪,不,是三只小猪。两人开心得在床上翻滚,开心得喘不过气来。某个刹那,她鼓起勇气,再提起那个话题,老公,你原谅我了?他侧脸看她一下,说,你能不能不要再提?缪兰不再作声,虽说是含糊其词,但心里宽慰多了,失去的一些东西慢慢会回来的。
第二天,却传来噩耗,缪兰软手软脚去到现场,地上一大摊血,马波不见踪影。
再跌跌撞撞赶到人民医院时,马波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当时,缪兰就昏倒在地。等她醒来,医生委婉地告诉她,肚子里的孩子,已经没了。
王栋和缪兰
王栋走出殡仪馆时,又薄又灰的太阳,已经有两杆子高了,挣扎在尘雾后面,向人间抛洒若有若无的光晕。男人站在公交车站台上,歪着脑袋,斜着眼睛,向那团暧昧觑视。某一个片刻,他似想起那个寒冷冬天,当时天边也是这种黯淡的混沌……王栋的嘴张了张,感觉到唇颊和舌面的酸涩,一股久远的枯槁味道,游走在鼻孔和他深凹的人中间。
他从牛仔裤屁股口袋里,取出十五块钱一包的黄果树,抽出一只,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透过迷蒙的白雾,他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在十米之外,正专心致志地望着他。王栋手一抖,烟从手指滑落,他弯腰捡,白色的尸身半截浸黄——不偏不倚,那小身子骨软在一小洼污水里。彼时,14 路公交车,缓缓进站,王栋也不管了,直接跳上公交车。因为是倒数第二站,车上空位多,王栋找了个靠后、靠窗的位置,刚坐下,就看见缪兰也跟过来,躬身坐进另一边靠窗的座位。王栋侧脸看窗外,假装她不存在。缪兰的脸也对着窗外。
中间倒了两次车,缪兰一步也不落下。
第二次倒车时,王栋有座,缪兰没有,王栋也不说话,站起来让她。缪兰屁股一歪坐下,也没说谢谢。旁边有个四十多岁的妇女,翻了两次白眼。快到拱桥巷的时候,王栋进了间早餐店,要了一碗牛肉粉,想了想,多叫了一碗,推到缪兰面前。缪兰说我现在吃素,说着,一片一片,从碗里搛出来,叭叭叭,扔进脚边一个套着黑色塑料袋的垃圾桶里。
王栋抬起眼睑瞄了一眼,喉节上下滑动两下。
走出早餐店,王栋又点燃一支烟,皱眉吸了一口,回头问缪兰,你紧到跟着我有什么意思。缪兰站他后面不远,不说话。王栋往前走两步,她跟两步,王栋停下,她也停下。你晓得没,王栋倏地转身,对缪兰说,你这种行为是对我的骚扰,严重影响我的正常生活,我可以告你的。
缪兰挥手扇扇浮到面前的烟雾,说,我不告你就不错了,你告我?你凭什么告我,你有什么资格告我?自从马波走后,缪兰就很少说话,偶尔说,也是软巴巴的几个字,在王栋面前,来来回回也就那句询问,很少蹦出这么口气生硬又连贯的一句话出来。
你不早就想告了我吗,去告,我一点责任没有!
王栋把烟掐灭,像小时候在池塘里抓鳝鱼,为了降住那滑溜的身子,拇指死死嵌进它们的颈部。你知道我可以一分钱不赔的,但我可怜你,感觉对不起你,卖了我的车,我所有的钱都给你了,你还想怎么样?王栋越说越烦躁,右脚脚尖在烟蒂上碾来碾去。
我就是想知道他最后说了句什么话,你为什么就是不愿意告诉我,你这样藏着掖着有什么意思……她的双眼胀满粉色的湿气,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
我怎么藏着掖着了,他真的什么话也没说啊!王栋一张绽放的苦瓜脸,正对着缪兰,他就是嘟囔了一句,根本就不是一句话……
对啊,嘟囔也是说啊,他说了什么。
她信心满怀地注视他——再一次进入某个死循环。
四个月了,说来说去,都会绕到这儿来,从而进入无止境的循环。
无论王栋怎么解释怎么陈述,缪兰都不信,并且执拗地认为,只要他王栋好好回忆、细细回忆,一定能想起来——马波留在这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
缪兰坚信,那句话,是她差不多两年来,一直想听又没有听到的话。她相信最后的时间,他一定会给她说出那句话的。
两年前,王栋买了辆二手小货车,给人拉活儿。五成新的小货车,在他手里变成了八成新,慢慢也有了些固定的客户,每个月下来,还有节余,日子倒也过得还行。
那天,他拉了满满一车旧家具,在路上正常行驶,速度也不快。哪知道有人会突然蹿出来,也是寸,头正好撞到右边的后视镜上,后视镜撞断,撞掉,镜杆深深地插进太阳穴,再被壮实的车体撞飞三米开外。那人手里的鱼、鸡蛋、白菜、西红柿,花花绿绿,散一地。还有一只用红色编织带捆着两腿的母鸡,咯咯咯惊叫着往路中间乱窜、蹦跶,没几下就翻滚在地,怎么也站不起来。
事故认定,死者负全责,赔偿也由保险公司来承担。
很多人遇到这样的事儿,跑都来不及,可王栋听说死者家属流产住院,犹豫再三,还是拎着几大袋营养品,去了医院,还揣了两千块钱现金。
缪兰蜷缩在病床上,面如死灰,头发像刚从水底捞出的海带,粘乎乎地趺在枕上,脸上两口混浊的泉眼,冲着天花板,汩汩冒水,一会儿涌得多,一会儿滴嘀嗒嗒,没停的时候。当时王栋就跪在了床边,嘴里说着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真不是故意的……缪兰挣扎着想打他,根本起不来;等她能起来了,也不想打他了——再恨再怨,也不是人家的责任。何况,人还天天来照顾她,也算是仁至义尽。
她后来只问他,马波走之前,有没有留下什么话?
王栋想起当时的场景——马波仰面躺地上,血从太阳穴汩汩涌出,像个细小的水龙头,缓慢,又惊心。那时,他相信有一阵,他的心脏是停止跳动的——卡在时间的某个切面,挤压成没有空间的金属薄片,不能动弹丝毫。
他当时本能地去扶,一手的血,没稳住,一屁股坐地上。
那是个初夏的傍晚,天边有滚烫的红霞,气势汹汹向他们扑来。(后来,他无数次回想起那个场景,一声巨响之后,整个世界安静下来,只剩下他和地上的死者)。他喊,你怎么样,你醒醒,醒醒……那人眼睛圆睁(半截黑框眼镜挂在耳朵上),虔诚地望向血红的苍穹,嘴唇嚅动几下,发出几个奇怪的音符。
你说什么,你要说什么啊!
马波的嘴角似挂着微笑,突然涌出一大口血来,然后,眼睛以一秒一帧的速度,缓慢合上。
王栋回答缪兰,马波当时就走了,什么话也没有留下。
你是没有听到,还是他没有说?
王栋想起那几个奇怪的字音,几个模糊的音节,没有一个音是完整的。马波望向天空的眼睛,像一个超清特写,浮现王栋的脑海。
我,理解你的心情……
不,你根本就不理解,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你看我掉了多少头发,缪兰往头上轻轻抓了一把,展开在他眼前,苍白的掌心,横七竖八蜷曲十几根头发。他说,这是正常的,人每天要掉几百根头发呢。我怕马波怪我,我把他的孩子弄丢了,他多想要一个孩子啊。每次说到这儿,她都会哭,呜呜地哭。你说,如果我当时忍一忍,不要那么伤心,至少也能把孩子留下来不是……缪兰一哭,王栋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他怕听见女人哭。
昨天晚上,我好不容易睡着,马波就来了。缪兰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特别轻,像在王栋的耳朵边哈气。他的脊背发凉。是他告诉我,他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是说给我的。
那他咋不直接给你说。
他说他忘了,让我来问你。
王栋和陈警官
王栋不堪其扰,去找给他办案的陈警官。
陈警官问他,缪兰有没有对他行使什么伤害行为,王栋说那倒没有,她一个女人能对我干什么。陈警官劝他看那女人可怜,忍忍,过段时间就好了。王栋说我忍得够久了,有时我都怀疑她是不是马波派来的,故意跟我过不去。陈警官说那不会,又不是你的错,何况你还主动赔了她几万块。王栋说是不是她看我好说话,想让我再赔她些钱?但我实在是没钱了。陈警官说这个不无可能,现在的人都有点贪。想了想又说,要不你搬家?王栋说她知道我的电话,还有我的微信。陈警官说你可以不接,不行换电话。看王栋犹豫,警官跟他开玩笑,说我们想要女人跟着还没有呢。王栋苦笑一下,并不以为然。陈警官有点小尴尬,赶紧说,要不你就编一句嘛,死无对证。
王栋说,我早知道是现在这种情况,当时就编了,现在编,咋编?何况她守起一句谎话,有可能是一辈子,对她不公平。年轻的警官摊摊手,表示无能为力,又说,也怪我,当时看她可怜,多了句嘴。做笔录的时候,警方让王栋不要漏掉任何一个细节,王栋就提了马波临死前好像说了句什么话,但他没有听清楚。此刻听到陈警官这么说,王栋苦笑了一下,说,不怪你,怪我。
缪兰当时说得有模有样,王栋也不知道为什么,就顺着她的话说,马波临死前确实是说了一句话,遗憾的是他没有听清楚。当时,马波仰望天幕,眼神肃穆、虔诚。天色似乎是突然暗下来的(有可能是错觉),殷红的晚霞和几粒残星纠缠在一起。其实,当时说完,王栋就后悔了,他认为自己哄骗了这个不幸的女人——虽然是出于好意。但缪兰就此深信不疑,当时禁不住抬起下巴,看窗外的天。那时天空正准备要下雨,云层厚重,往下翻卷,压着街衢、楼宇、车流、人声。
缪兰和王栋
那天上午,缪兰又来了。不过没在殡仪馆,而是在拱桥巷,在那家卖牛肉粉的早餐店门口。王栋过马路时就看见她了,装没看见,径直进店。经过的时候,缪兰说了一句,我吃过了。一会儿,王栋捧着个大土碗过来,缪兰脚边有根小板凳,往他那边踢了踢。
你不也是夜班吗,不困啊。
你是不是为了躲着我才去殡仪馆上班的。
躲你干什么,我又不做亏心事,他声音很大地喝了一口汤,说,我战友介绍的,工资高,还有三险一金。
你当过兵?
他不想回答她那些无聊的问题。他觉得每多回应一句,对方就会更进一尺。但他又没有完全拒绝她。有时,她会让他想起在马坡岭的那些日子。
好一会儿,她说,昨晚上我又梦到马波了。
他又说哪样了。
你晓得的。
我不晓得!
你还是没有想起来?
王栋呼地抬头,嘴唇热乎乎的,四周一圈儿的红油,说,没想起来,永远也想不起来,还要我怎么给你说!他的声音有点大,店里吃粉的几个人望过来。
他根本就没有说话,是我哄你的,对不起!
你声音这么大搞哪样,我又不和你吵架。
你还不如跟我吵一盘!王栋的眼睑比平常开得更大,瞪着大土碗,轻薄的油汤里飘着残存的米粉。
他埋头唏哩呼噜连吃带喝吞了几口,转过头来说,我就搞不明白了,他说的那句话就那么重要?能说什么嘛,银行密码?还是在家头藏金藏银了嘛。你们是夫妻,死亡证明你就可以把所有钱取出来,至于屋头,你可以到处找下啊。还是,你觉得我好说话,想再问我要点钱?可我真的已经没钱了,钱都给你了。
王栋听到缪兰咯咯的在笑。他奇怪地瞅她,有那么可笑吗?你的行为才可笑,最可笑的是我,居然拿你一点办法都没得。缪兰的笑声更大了,甚至有点喘不过气来。快半年了,王栋从来没见缪兰笑过,并且还是这么长时间发出有声音的笑。他左手托着碗,右手拿着筷子,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她,希望她能注意到他的不满。当时,天气阴郁,空气中弥漫着混浊的复杂的气味,一辆庞大的油罐车哼哼唧唧驶过,掩盖了她的笑声。但她的表情还在,仰着头,左手半掩着嘴,浅绿色的方格围巾,在她的颌下晃悠,意外衬托出她微微红润的脸色……某一刹那,王栋感觉到这个令他烦恼的女人,居然也是有几分好看的。
她突然就发现了他异样的目光。
这回是她愠怒了,笑声戛然而止,也不说话,像被侵犯了似的冷冷地乜着他。王栋的目光嘀哩当啷滚一地,低下头,继续吃他的粉。只剩汤了。他一仰脖子,全倒进肚子里。站起来,回到店内。等他出来时,缪兰已经不见了。王栋站那儿发了会儿呆,似舒了口气。他点燃一支烟,吸了两口,抬头看了一眼不明所以的天,心想,两天的夜班,这回可以好好睡一觉了。
差不多有两个多月的时间,缪兰没有再出现。起初,王栋落得清静,如释重负,感觉终于可以重回正常的生活了,可很快,闲下来时他经常会想起马波,想他临死前嘟囔的那几个音节。如缪兰说的那样,使劲儿想想,或许能想起来。当时一片慌乱,神思涣散,听不清楚是很自然的。
有几个早晨,王栋下夜班,恍惚看见,那个女人又站在白雾里,冷冷地注视着他,他扇开烟雾,空空的站台,人影寥落,并没有那个熟悉的身影。
那天,他终于有机会去缪兰所在的医院。战友喝多了,酒精中毒,狂吐不止,王栋想都不想,就把战友送到缪兰所在的医院。念念不忘,必有回响,那晚正好缪兰值夜班——一袭白衣,动作轻柔、娴熟。
战友睡着后,王栋挪步到护士站,意图向缪兰表示感谢。缪兰没说话,低着头,坐在椅子上,刷刷刷在病历上写着什么。王栋站了三分钟,难耐那份阒寂,转身欲走,缪兰喂了一声,他旋即回身。
他们中间隔着乳白色的护士台面。
一钵紫竹吊兰,生长茂盛,垂挂到台下半尺。缕缕有别于医院的味道,从紫绿掺半的叶片深处渗出来,灌进王栋微微上扬的鼻孔。
不等她问,王栋就主动交代:还是,还是没得想起来……
这次说得没从前那么有底气,像是欠着她什么似的。他的一双大手搭在护士台上,接着说,不过,我会再想的,慢慢想,可能,真的能想起来。他以为她会如从前那样露出热切的眼光,照在他脸上,像有很多吸盘的八爪鱼。但是没有。等他说完,缪兰轻轻瞟他一眼,又低下头去。
黑色中性笔在她的右指间中转动,一圈儿,一圈儿,有一圈儿没转进手心,吧嗒一声,掉地上。
好像有一个星字,因为当时天上有星星,我记得。
她抬起头来,后者正冲着她笑。她有点恍惚,隐约看见马波的微笑。马波笑起来的时候,左侧嘴角也有一个针刺般的小细窝。
我记得天还没黑,哪里来的星星。她说。
有,在马坡岭,哦,我老家,经常天没黑星星就出来了。
他终于在她脸上,捕捉到一丝丝熟悉的表情,但很快就散了。她俯身捡起笔,合上病历,站起来,叹口气对他说,对不起,我也是太强人所难了。
王栋、缪兰和土鸡
之后,换成了王栋去找缪兰,而不是缪兰去找王栋。
两个人找个地方坐坐,有时也会一起吃个饭,饭后一起走很远的路,很少说话。偶尔,缪兰会说她又梦见了马波,梦见马波这样那样,那样这样,倒是越来越少提及那句话。王栋是个优秀的听众,无论缪兰说什么,他都安静地听着,很少插话,只有缪兰问他的时候,他才回答,回答得简短、中肯。
聊天或吃饭的时候,缪兰喜欢坐在王栋对面,起初,王栋没在意,时间长了,就问她缘由。缪兰就说,马波笑起来时嘴角也有个窝儿。王栋听了,冲着她使劲儿地笑(那窝更深了),还故意瘪着嘴说,是这样吗?把缪兰逗笑了。笑过后,又哭了一会儿。后来,有事儿无事儿,王栋都对缪兰笑(这让缪兰想起马波常给她唱那首歌)。有天,王栋给缪兰送宵夜,打开保温饭盒,是浓香的清炖土鸡。真是土鸡,整个护士站都灌满鸡汤的味道。从那天开始,缪兰又开始吃肉了。
又过了段时间,缪兰对王栋说,医院在招一个急救车驾驶员,问他是否愿意去,说,也有三险一金。王栋好一会儿没有吭声。缪兰说,都快两年了,你还开不了车?半天,缪兰盯着交叉的双脚说,我都不再想了……王栋就说,摸过几次战友的车,应该可以。
那我去说说?
王栋点点头。好久,又说,谢谢你!
自从王栋到医院上班后,缪兰就不再提马波临死前的那句话。但是,王栋却没有放弃,有时,他主动给缪兰说,我会想起来的,肯定能想起来。缪兰起初当没听见,说得次数多,缪兰就说,我已经不想知道了。王栋说,那不行,必须想出来,那句话对你一定很重要。王栋从来没有问过缪兰,她究竟想听到马波给她说什么。
有天凌晨,王栋出车,去拉一个车祸伤者,他帮着把人抬上救护车的时候,听到伤者嘴里咕噜了句什么。就那一刻,仿佛神启,王栋遽然想起来马波说的那句话。原来他真的说了话,不是嘟囔,不是血涌进口腔,语焉不详。那确实是一句话。想起的刹那,王栋抬伤者的手抖动得厉害,同事问他怎么了,他说没得事。坐进驾驶室,王栋的双手握住方向盘,大手上的青筋像绵延纵横的山丘。
第二天一大早,王栋就去了缪兰的家。
缪兰正在吃早饭,开门见到王栋,朝他一笑,转身回到桌子旁边,对他说,这么早,有事?不急的话,一起吃吧。说罢,盛了一碗甜酒鸡蛋给王栋,自己又自顾坐下,咬下一块果冻般晃动的蛋黄。
王栋坐缪兰的对面,清了清嗓子,说,给你说件事儿。
嗯。她没抬头。
我,想起那句话了。
什么话?
嗯,就是,他说的那句话……
咳咳咳。
她呛着了,使劲儿咳了几下。他赶紧起来,转到椅后,想拍她的后背,犹豫了一下,抽了张纸巾递给她。她接过去,揉成一团,胡乱擦了下嘴,扔进旁边的垃圾桶。
她用手抚了抚胸,憋出三个字:呛着了。
又没人跟你抢。他笑着说,又递给她一张纸巾。
她接过来的同时,抬腕看了一眼时间,说,我今天事情特别多,不吃了。
她站起来,往卧室走去。
过了一会儿出来了,眼圈微微发红。
王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缪兰浅浅一笑说,今天忙,想请你一件事。
王栋马上问,什么事?
缪兰又笑笑说,晚上想吃鸡汤,你帮我去买只老母鸡怎么样?
王栋也笑了,我以为什么事,吓我一跳。他习惯性地挠挠后脑勺,这还不好办吗,买鸡我是内行,土鸡洋鸡一眼一个准。
缪兰说,那太好了,就买只土鸡,不要太大,够两人吃的就行。说着她向门口走去,走吧,今天是周五,明天就是周末了。
王栋先出去了,缪兰关上门。
小区的路上,两人并排走着。太阳刚刚升起,四周一片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