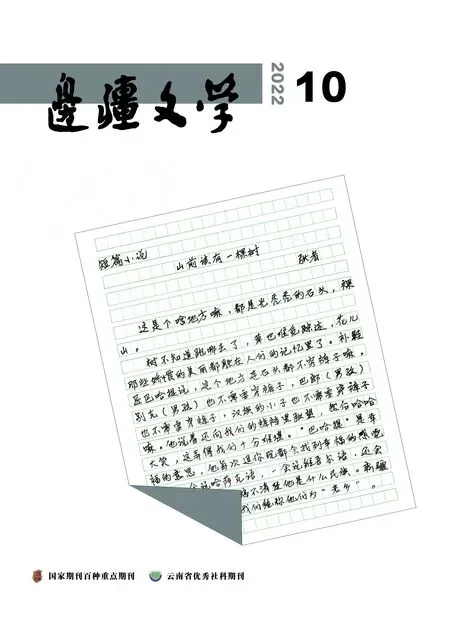从古渡口到数字港散文
黄立康(纳西族)
渡口
一个命里带着高原垭口的人,他的梦,总是流向一个河口。
那河口是个渡口。
河口两岸,橹声隐隐,船影绰绰,摆渡由此及彼,再由彼到此。漫漫岁月里,小船慢慢摇,木桨轻轻划,击出的水响,划出一首首用暗含“五音”的船歌水谣,回应着历史的呼喊。
在渡口回荡的第一声摇橹声,“宫”声,“脾应宫,其声漫而缓”,这声音似从时间的起处、遥远的夏商,长夜般缓缓盖过来,将华夏天地供奉到青黑色的司母戊方鼎前,在无声中,沁出庄严和肃穆。
秦时明月,曾照着中华大地上奔腾的历史长河,曾照着公元前被秦灭国的古蜀安阳王从古道“五尺道”“步头路”仓皇出逃,在河口摆渡向南。河水倒映出神色凄茫疲惫的蜀王,亡国之痛仍在脸上,如同后世商女隔江唱出的《后庭花》哀婉地在水面轻荡。历史的河口,将安阳王摆渡了过去,他进入古称“交趾”,后称为“安南”“越南”的地区。从此,一个渡口连接的两岸天地,开始渊源渐深。
汉时关——军事重隘和商贸要道——进桑关在河口建立。史书的春秋笔法,开始记下河口的名字:“屹峙南陲,制临交趾,山川环屏,道路四通。”
隔着南溪河和红河望向更远的南方,劝君更尽一杯酒,南下进桑,莽莽苍苍。作为汉王朝的关隘,进桑关和北纬四十度线上的阳关、玉门关一样,都曾是“玉成中国”版图上的要道关卡。当河西走廊最西端的玉门关和阳关春风不度、渡过来是铁马踏冰河的游牧马队时,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咽喉要塞,烽火边城的寒风劲雪、鸣镝尖啸在这里起伏、冲撞。神奇的北纬四十度、伟大的长城线上,农耕与游牧,战争与媾和,冲突与融合,一直充满着动荡和疼痛。直到后来,当阳关与玉门关不再是边城时,进桑关一直是南方偏远、安稳、坚固的关塞。这里的时光,如同漫长而缓慢的拖腔,在一阙词的尽头,声声慢……
那时的河口,只是一个渡口。
第二声摇橹传来,是“商”声,“肺应商,其声促以清”。
木桨划过水面,这轻盈的动作像大唐诗人白居易笔下的琵琶女抱着琵琶“轻拢慢捻抹复挑”。琵琶声声,急促清脆,嘈嘈切切间,唐王朝和南诏国的军队在河口来回摆渡。多少年过去了,摇橹的回声中,仍暗藏着纷乱的“铁骑突出刀枪鸣”。浔阳江头的渡口是不是白居易的河口?同是天涯沦落人,高山流水觅知音。白居易在这个河口摆渡过去一首千年回荡的《琵琶行》,而能容下李白旷达脚步的中华大唐,在恢宏和琐碎间,由盛世渡向衰年。
从羊苴咩城(大理)直抵安南的西南丝绸之路,开始在中华大地上弹响,西南的马帮、船影与青山绿水,遥望着西北的驼队、沙海和海市蜃楼。崎岖的马帮栈道到这里要停一停,换走红河水道,南北的商贸,从山峦到海洋,从中华到世界,在河口摆渡过去的马嘶牛鸣,摆渡回来的是珊瑚和海盐。但那时的河口,只是一个渡口。
摆渡依旧缓慢地来回于两岸,时间的记录越来越清晰了。关于过往的想象,也因清晰渐渐失去弹性。北宋与安南的交流依旧密切,但河口,仍是个渡口。在清雅宋词、马帮驼铃和江涛拍岸的声音间,河口的木船将第三声“角”声划响,“肝应角,其声呼以长”。安南的佛教徒渡过河口,去往印度求取真经。悠长的佛号在一来一回间摆渡,回响成为夜半山寺的钟声,敲响了千万信徒内心深藏的慈悲。
从天似穹庐笼罩四野的草原吹来的风,回响在第四声摇橹声中。“徵声,心应徵,其声雄以明”。元朝政府在河口设置了驿站,这个驿站连接了中华和亚洲各国。
在明代,明朝使者曾三十多次出使越南,而越南派遣使者前往中国则多达一百多次。
另一条雄壮明亮的隐秘之路,由航海家郑和统领大明船队,从江苏省太仓市的“天下第一码头”刘家港出发,七下西洋。那是一条铺满青瓷般色泽内敛、文辞清脆的中华之路,顺着郑和的航道,我们得以往返于水冷冰洁的青瓷时代,去触摸一半泥水一半火焰塑形而出的远航风暴和历史烟云。这条水路,和红河航道一样,同样载满中华山水与莫测汪洋之间的恩怨情仇,也载满藤蔓横生的古人旧事,那些人心和史书深处暗涌着的恐惧与野心、痛苦与荣耀、脆弱与坚韧、局限与浩荡,如在眼前。隔着岁月的海洋,站在时间对岸的郑和,他是无数求索者的化身,因为他们的存在,印证着流传至今的远洋传奇和中国精神。而这时的河口,仍只是一个渡口,只有几户船夫在此结庐而居。
清朝时期,边境贸易渐繁,政府在河口驻兵设卡、置建营盘,特准边民商贩来往。红河上的船队、驿道上的马帮络绎不绝,但来来往往的人,都只是在河口摆渡,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某一天,河口摆渡过一群金发碧眼的探险家,这一天,摇橹的声音是“羽”声,“肾应羽,其声沉以细”。
河口开始随着中华大地,褪去荣光,下沉到低谷。
码头
当我站在南溪河和红河交汇的河口,如同站在梦的迷津处,千年春秋、历史金戈,几个瞬息间摆渡而过,留下带着古音的摇橹回声,悠悠荡在山河间。河口湿热的空气也笼罩着我,这让一个“冷地方”来的高原人多了些黏稠的恍惚,更觉得曾经在此摆渡的一切,如梦之梦。
两河交汇处,有一个码头,我站在高处看它。码头修建没多少年头,但在风侵雨蚀的雕琢下,已显出旧色和疲惫。码头上一排拴船柱样式的铁链护栏,护栏下装饰着几个救生轮胎,空洞洞地看着台阶扇子般伸向浑黄的南溪河水。湿热阴雨,给这个码头染上了沉黑的暗色,暗色削弱了活力,拉远了时空,这让码头看上去像是睡着了,它沉到自己梦境的深处,“睡着了的身体,离世界最远”。
这个码头是个“意象化”的存在,带着图腾的气质,将一段摆渡的岁月,压缩在一首律诗的平仄和韵脚间。作为意象,“码头”牵着的意境,孤帆远影或是百舸争流,都将和渡人船客的心境映照、互喻。古人都把自己的心事藏在景物里,再覆盖上淡淡的情意,藏住了眉间事和心上人。但一定有故事发生在码头,有人在此相遇、相爱,后来相离,在相忘于江湖间,长相思。
谁能为我讲述河口码头上的往事,再现红河航道上的曾经?谁又能在宏大叙事之上,带给我一些可触肤凉的细节?
“红河,纵贯滇西南,南至越南北部最大的港口城市海防而入海,是云南省乃至中国西南至太平洋的最近水路。”那时我正查看越南水系图,想着如何绕开枯燥的史料堆叠而将自己拯救,另一条源自中国的大河,另一个与中国有着渊源的码头突然闯入我脑海,让我得以用偷换的手法、惯性的抒情,来复刻一个码头的曾经。
第一次听到“西贡”这个地名,是在电影《情人》里。错位的时空,无望的爱情,忧郁的情欲,让我一直屏住呼吸将电影看完,并在结尾处一声叹息。告别的码头,我的眼睛一直看着法国少女的脸庞,期待她露出些许的留恋和痛苦,好安抚一个观众“意难平”的对抗——这让我没有关注到他们离别的码头背景,所以说,爱情让人盲目啊,特别是别人的爱情。当我回过头再看了一遍《情人》,电影重现的昔日码头上的情景让我深受震撼,也对那段绝爱的时代背景,有了更深的了解。
离别的画面从高处俯视。在码头的弧湾里,大小航船纵横。随后切入巨轮的汽笛、黑白侧影和滚滚浓烟。游轮离岸,送别的人挥手。随着游轮移动,码头上的情景开始转换,送别的人群身后,是一字排开的标有序号黄墙大仓库。仓库前,升降的铁架林立,麻袋堆积如山,木材码放整齐,马车拉着货物,工人推着轮车。而这繁忙和嘈杂的一切都被游轮吐出的黑烟雾笼罩着,棉纱、洋火、鸦片从烟雾里来,云南的大锡和茶叶,从烟雾里运走。一个码头,唯有昼夜不息地吞吐,才能满足一个强盗世界的胃口。
让我们回到电影开头,一个法国女孩为何会在湄公河上遇到中国男子?因果之间,有时因比果更苦,这个苦果的涩因,是侵略,战争和殖民。十九世纪开始,法国以保护传教士和天主教徒的名义,逐步占领湄公河三角洲的主要城市,于1862年控制越南南部。又于1884年6月与越南签订《巴德诺条约》,控制了整个越南,正式开始全面殖民越南,并觊觎着云南。
《情人》里的虐恋,就这样痛苦地发生在畸形血腥的殖民时代里。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这似曾相识的一切可能也曾发生在河口码头。古老的红河航道上顺水或逆流的木船、汽轮机船,在昆明、蒙自、蛮耗、河口、河内、海防的大小码头上穿梭停靠,像一朵被催开的红花,闪烁着违背自然的妖艳光芒。
最开始时,河口只是个渡口,并不是码头。从越南逆流北上的航船,会在个旧市“蛮耗”码头驳岸,水陆运转,集散物资,走古道,转向蒙自昆明,后达中国内地。那时的红河航道和马帮陆运,是一条世界性的航道。
诗人冯娜有句诗,“河水是一群马,保持着船只的速度”,而她的这首诗叫《边境》。我不知道诗里的“边境”是不是河口,或者她是用“边境”,隐喻爱情这场暗战的攻伐和固守,又或者她是在隐喻一场血腥的侵略:“走得太疾,我会是你的诺曼底。走得过慢,我便是你失守的珍珠港。”不论太疾还是太慢,不论失守或是逃出生天,船只和马,正契合了中越古道水路和旱路的交通。在滇越铁路开通前,来往货物,均要通过马帮驮、商船运的方式,到中国去或到世界去。
1889年,作为中法战争后果,云南第一个海关蒙自开关,设蛮耗为分关。
蛮耗开埠几年后,中法订立约开的口岸,由蛮耗改为河口。被辟为商埠后,政府在河口设置公署,直至民国初年。从此,过往的船只必须在河口海关停船报税,才能开始航行。河口,被推着成为中国的门户,商贾往来,百业俱兴,人口暴增,城镇突起。
所以,在我的想象里,河口码头也可能是这个样子:浑黄平缓的河面上,飘过断枝残叶和肿胀牛尸。江水轻轻拍打着码头岸沿,冒着黑烟的渡船靠着码头,随水轻晃着。船上的人忙碌如蚁,他们戴着一顶顶粽叶斗笠帽,摇头晃脑的,真是像小身子的蚂蚁晃着大脑袋。工人们忙着装卸沉重的稻米麻袋。一些附近的村民,会搭船过河,他们的粗糙竹笼里关着鸡鸭和猪仔。船两边凌乱地摆放着扁担、竹篾和竹篮,放着一些榴莲柠檬。也有商贩靠着船沿,守着一个火烟飘摇的火炉,火炉上的锅里,煮着些玉米和花生,向船客售卖。人们的说话声、吆喝声、鸡鸣猪叫也乱成一团。也有穿着考究西装笔挺的商人、一脸幼稚好奇的学生刻意地站在船头,与农人拉开距离。商人和学生取道河口、河内,去往香港或者出国。在当时这是最便捷的水路。船夫打响了启航的钟声,渡船拉起一条黑烟,驶向对岸或者下一个码头。
载满殖民时代的微小细节和宏大叙事,河口码头在一条蓬勃的生命线上,将归家人渡向晨昏烟火,将云游客渡向他乡之旅,也将交易物渡向世界各地。
铁路大桥
划开皮肤和肌肉,植入一根铁。
这根“植铁”,现在就在我面前。老码头的左上方,河口中越铁路桥横过南溪河,连通了两岸、两个国家。它也曾在渡口和码头之上,摆渡了两个世界的野蛮和文明、瘙痒与疼痛、割裂和治愈。铁路大桥寂静无声,仿佛也是睡着了。和码头不同的是,码头再无泊船,而铁路大桥上每天仍旧会有一两趟火车经过米轨。火车轻轻地开过,轻到不会惊动这座老桥车水马龙的荣光之梦。
铁路大桥的枕木,一半红色,一半黑色,红与黑,是中越两国国境的界限。我想,红色与黑色,也是隐喻,隐喻着这座桥的身世和血脉,来自战争、侵略、枪炮和鲜血。这个红黑隐喻的核心、也是这座桥使命的核心里,闪动着来自列强喧嚣亢奋的脉动,一声声,一波波,都是在说:植铁,殖民;殖民,植铁!
当一个人,移植入异体,就会发生排斥反应。这是肯定的。胸闷、呼吸困难、心律不齐、肝脾肿大、双下肢水肿……一根铁从河口一直插到云南之心昆明,中华大地上种种的排斥反应,症状只是两个字:屈辱。
屈辱其实早已开始了。
从早于中法战争四十三年的鸦片战争开始,这片摩挲大地,就已经开始坠落颓败。
2021年,我去到浙江舟山。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真正的大海,虽然在我的滇西北,我们把所有大大小小的湖,都叫做“海”,但当我在跨江大桥上眺望大海,还是觉得海的阔大超出了我的预想。我如同那个“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的黄河之神河伯,在黄河入海口东望,极目却不见水端,暗自望洋兴叹。只是我“望洋”的地方,是在长江入海口。
这里也是一个大河之口。这里是此处。让我们将目光,沿着中国地图上的长江河口溯流而行,一路弯弯曲曲,到达云南金沙江中游。再南下,遇见红河,随红河水往东南,最终另一个大河之口在中越国境线吞吐。那里是彼处。由此到彼,一个在中国西南之南,一个在中华正东端,都是中国,也都是河口。
长江入海口远处的海水浑黄,出离于我对大海蔚蓝轻盈的想象。一个在长江上游金沙江边生长的人,带着朝圣的静默来到长江入海口,江海中的某一朵浪花,会不会是我对着金沙江水呆思遐想时,随水而去的心事?
来的路上,从飞机上看到许多大小岛屿。这些岛屿像一个个逗号句号。舟山群岛作为中国第一大群岛,这里的故事,肯定也是无法述尽说完的。这种苍茫感,在我走出舟山市定海城西的全国爱国主义示范基地“舟山鸦片战争纪念馆”,再次眺望东海时,突然变得愈发沉重。
1840年,英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因地处长江口和东南海岸线的优越位置,英军先后两次发起“定海之战”,入侵浙江舟山。东方古老的农业文明与西方工业扩张在定海发生碰撞,最终定海陷落。战后,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签订,黑字红印,江山屈辱:“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常远据守主掌……”“……唯有定海县之舟山海岛、厦门厅之古浪屿小岛,仍归英兵暂为驻守……”
战火由此到彼,偌大个中国,似一个火山爆发、岩浆四溢的绝地。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而早在中法战争爆发前,法越战争就已经将以河口为后方的中国黑旗军卷入其中。最后,中国赢得了这场战役,却“不败而败”,在天津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允许对越南订立条约……指定两处为通商地点,允许法国商人在此居住并设领事……日后中国修筑铁路应向法国商办……”
于是,南起越南海防,北至云南昆明,全长854 公里的滇越铁路,于1901年开始修建。中国段1904年动工,1910年竣工,自此中国西南门户洞开,殖民势力直接进入云南,并能沟通东南亚。铁路巨大的运能将滚滚财富运走,而这个火车摆渡的中国要塞,就是在河口。
一条铁路硬生生植入到故土家园日常烟火里,你会如何?不可能对此没有反应。当铺设铁轨的金属击鸣声、枕木的滚动声、开山的爆炸声、修筑铁路的异闻怪事传到你耳中,你会像石佛一样不动声色?当一个绿色的铁皮冒着浓烟从你眼前驶过,绿色盒子里一车又一车,运走了无数的锡矿煤矿锑矿,这是我们自己国家的宝藏啊,如此强盗式地被买走,你会对此无动于衷?
火车也运来了神奇的魔法:一擦即燃的小木棍,一个总有几颗长针在旋转的圆盘,一种黑色的药水外国人每天都喝。这条植铁上带来的东西,它总牵着你的眼,抓着你的心,牵疼你内心最深处最敏感的情感。
终于,我要将自己的讲述书写,从空穴来风的历史猜想,摆渡到“人”身上。
卡尔维诺说,重负之下的人们,会奋不顾身扑向某种轻。所以,愤怒是最轻易也最轻盈的吧。在被侵略、被重压、被冲击下,回应最轻易的情绪,那时的中国,愤怒且充满怨恨和绝望。河口的民间应激地发起“火烧洋关”“阻洋修路”等运动,像一个人被打了一巴掌,本能地想要回击。但愤怒并不是一个人最好的情绪状态,它缺少气度,像天上的暴雨,短暂无法持久。
面对你无法理解的东西,你或许会惊、恐、忧、悲,但这些也并不是最深最沉的情绪。最深沉的情绪,像一粒种子沉睡在泥土里,等着春雷响春雨落,然后顶开外壳,这样萌发而出生命的芽。我想,这是知觉与醒悟。一粒种子需要觉醒,才能获得生命由内向外的柔韧,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是如此,要觉醒,萌发出的生命力,从容自在且饱含期待向往。
当我在百年之后回望这段历史进程,我看到的是一个民族如何在冲击回应之后,从愤怒和怨艾的血气中冷静下来,沉到民族根骨中,用爱国情怀的历史主动精神,吸取教训,重新成长,重塑自己。
1908年,同盟会发动河口起义,被视为辛亥革命前的预演。1912年,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条民营铁路——“个碧石铁路”的开始筹资修建,这也是一个明证。而滇越铁路的通车,也让云南站在现代化的前沿,参与了中国近现代史演进。1915年震撼中国的护国运动。抗日战争期间,滇越铁路成为中国重要陆上生命线。西南联大的建立,大批著名知识分子沿着滇越铁路抵达昆明。民族意识也在滇越铁路的摆渡中觉醒,如同一粒种子在岩石缝里生根发芽。
铁鞭抽打下的土地水深火热,一代代人像一次次播种,拯救自己的是那种子里传承而来的柔韧穿石的生命之力。这是一个民族经历苦难和毁灭,仍旧顽强地生存下来的原因;这是一个民族经历千百次捶打,淬炼而出的民族精神;这是一个民族不断因势塑造自己,最终走向复兴的历程。
1997年,位于珠江河口的香港回归。那年我十三岁,跟着电视里传出的国歌唱:“中华民族到了……起来,起来……前进,前进……”
2022年,火车仍旧按时穿过中越铁路大桥。
我想,这座在今天显得窄小的铁路大桥,它的意义已经不是运送多少货物。米轨上的绿皮火车,将百年的时间摆渡到今天,它存在的意义,是提醒我们该如何看待那段历史,标记自己的成长,从低谷走上大道,然后大步往前走。
滇越铁路,这条曾经疼痛地植入云南大地上的铁,已被中华民族的血肉,熔成了国人的铮铮铁骨。
公路大桥
这是图腾、河口的图腾。
2018年我曾随一个记者队到过河口,当时的河口并没有给我留下太多印象。只记得闷热,还有中越公路大桥上的中国国门。后来,在我的回忆里,想到河口,中越边境上的国门之桥,就会跳出脑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门桥就是河口,就是河口的图腾。
蓝天下,国门矗立。国门的设计简洁大方,金字塔形,前后两条横梁支起左右的两个翅膀般椭圆,上方两道粘连的闪电,护卫着正中的国徽。气质庄严,形象生动,国门如同庄子笔下逍遥游的大鹏鸟,正奋力将翅膀下压,借力好风,振翅向天,“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
我不知道河口中越公路大桥上的国门的设计理念是什么,最初的设计者从何处寻得灵感?当我在查看河口县地图时,嘴里念叨着,指尖从左到右依次划过:莲花滩乡、瑶山乡、老范寨乡、河口镇、南溪镇、桥头苗族壮族乡……我惊异地发现,我在地图上画了个字母——“V”!
国门的设计灵感,是不是来自河口县的地图?
地图上的河口县,神似一只身形飘逸、疾坠搏兔的苍鹰。
如果拿着红河州的地图站在河口国门前,把地图倒过来,上南下北,举到眼前,那么地图上河口县的形象,和国门,有着极高的相似度。
如果设计师真是按照河口县地图倒过来的形象设计的国门,那么,国徽之下皆是国土,而国徽之上,两道闪电形的模型,将不是闪电,而是红河和南溪河,两条河交汇的最前点,就是河口。
这座公路大桥的诞生,应答了时代的呼喊、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心声。
1949年河口和平解放时,小城还没有一条公路。直至1993年中国河口—越南老街口岸恢复开通,滇越铁路已经无法满足暴增的运输需求。离公路大桥仅百米的中越铁路大桥,已经无法摆渡太多的渴望和期待,在汽车跑得比火车快的云南,河口、红河州和云南,都需要速度更快、运量更大、效率更高的运输方式。于是,横跨中越南溪河界河的公路大桥,1999年9月开工建设,2001年开始投入使用。
2009年,由中越南两国共同建设的中越红河公路大桥竣工并试通车。红河之上,还有两座公路大桥正在筹建,以适应“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红河片区”的发展需求。
日新月异,没有比这个成语更适合的词,来概括河口成长的速度,这速度也是红河速度。
曾经,从昆明到越南河内,由此及彼,走红河航道转陆地古道,需要31天。火车需要4天。现在,全程高速开车只需8 小时,而昆明到河口只需4.5 小时。2014年泛亚铁路东线蒙河铁路开通客运。2015年开通货运,河口形成了年吞吐量达800 万吨的中越国际贸易市场。2019年昆明至河口开通动车,运行时间只需3 小时33 分。
我前往河口时,坐的是“复兴号”动车。“绿巨人”从昆明出发,过屏边后,如同“机器穿山甲”,一路高速地穿过一个又一个又长又黑的隧道。在赞叹中国基建技术高超的同时,也给自己讲了个笑话:我也算是“摸着黑”到河口的。
世间伟大和渺小并存。当一条条高速路、火车路、动车路抵达河口,像人体内的动脉静脉,源源不断地将血液输送到各处时,那些毛细血管是否都能获得营养和氧气?
在去往河口乡镇和边境线采访时,那里无尽的群山给我留下了梦境的奇感。皮卡车一直在山间路上旋转,似乎没有尽头,似乎能这样天长地久地绕下去。百无聊赖中看到对面有个寨子,细细看时,发现那是早前经过的村落。在我年轻写诗的时候,我曾拙劣模仿海子,矫情地写下过一句洋洋自得许久的诗——“路是山的伤口”。挖掘机挖开山的皮肤,将碎石土推下路面,石土散开就像伤口溢出的血。那天去河口桥头乡的路,转得我都快成为山的伤口上的忧伤了。
到桥头乡中寨村时,我感叹这路难走。同行的工作队员告诉我,这路比以前是好太多了。以前都是弹石路,现在一两个小时的路程,以前要颠簸四五个小时。边民们出行都是骑摩托车,弹石路安全隐患多,经常出车祸。脱贫攻坚后,道路硬化,水泥路修到了村村寨寨,真是得感谢党和国家。
路太重要了。
我小时候不太愿意回金沙江边的老家,觉得太闭塞了,路又不好。现在对比一下河口大山里的路,觉得小时候家乡的交通已经算是便利了。后来脱贫攻坚,时常需要下乡。我们单位挂钩点是在丽江市宁蒗县翠玉乡,扶贫的村落都在原始苍茫的高寒山区里,进村的车路都是从悬崖上炸出来的。当越野车上在路上摇摆晃荡时,我看向窗外,内心惊得不由自主地叫出一句国骂。路贴着山崖,下面就是不见底的深谷,凶险得估计连这条山路都瑟瑟发抖地紧贴着山壁。我心想,车要是从这里落下去,那就不是车祸,是空难了。随后,又赶紧在心里吐口水,暗骂自己乌鸦嘴。
我写过一篇散文《翅膀之歌》,虽然叫“翅膀”,其实是写路的。我写父亲走过的路和我走过的路,写父亲走出家门口的马路,坐上弹石路上的客车,去往城镇。他在中甸县城的长征路上来来回回,求学、工作,爱怨、生死,他的一生就是一条长征路。我沿着父亲的长征路离开故乡,把他乡之路背在背上,翅膀一样,飞到了许多父亲没去过的地方。我们都在跟随时代的呼喊长征,父辈的时代,是进城时代,要到世界去。而到我辈,是返乡时代,回故乡去,田园将——兴——胡不归?
在从边境线上的边防检查站老卡回城的途中,路过一个苗族寨子。这里的边民没有修建大门和围墙的习俗,水泥路直接修到每家每户的院子里。时代的呐喊回荡在这些最偏远微小的地方,祖国的体温关照着这些最微弱稚嫩的心跳。
村口有些小孩围着一道流水玩耍,他们现在无忧无虑,一根木棍就能挑起整个世界。成长的烦恼等着他们,他们是一个家庭的希望和动力,他们的成长将牵动一个家庭的喜怒哀乐。人之常情,小家大爱,相比他们的父辈祖辈,这条修到自家院子里的水泥路,如同他们的起跑线,已经超过同年龄的父母,更远远超过祖父辈了。我想,美好的世界等着他们,虽然在这条属于他们自己的长征路上,少不了风雨艰辛。这些不知名的河口小孩,总有一天会明白“路”的意义。这些水泥路连着世界。他们会沿着这条路走出故乡,走到红河蒙自,走向昆明。更阔大的世界等着他们。也会有一天,他们会沿着这条路,回到自己的故乡。
所有的路,不再是山的伤口,而是翅膀,带我们飞翔。
数字贸易港
距中越铁路桥五十余米处,有一栋红瓦黄墙、法式风情的建筑,是“河口海关旧址”,也是“同盟会河口起义纪念馆”。红窗棂,花瓷砖,黄墙沁着水渍。有些地方墙皮脱落了,是时光悄悄经过时,不小心擦落的吗?
海关旧址前有两棵四层楼高的芒果树,挡住了后面的黄墙红窗楼。芒果树结着绿色的芒果,陪同我的老师都是河口当地人,他们说这种老品种的芒果树结的果实凉拌最是好吃,只可惜树高,摘不到。
芒果树后的大楼也是法式风格的建筑。大楼正门前有两棵棕榈树、一头威武的石头雄狮和一个大理石碑。石碑上刻着“河口邮政大楼旧址”,文字简介中说:“河口邮政大楼旧址是根据《滇越边境电报接线章程》而设,是云南省设立较早的邮政机构。”
整个河口邮政大楼,如同一封从遥远时空寄来的脱胶的信——微微张开、合不拢的红木条窗,墙根爬着黑色水痕,墙角被磨出擦痕,正门上贴着些邮票一样的告示,那只沉默的石狮,就把它看作是邮戳吧。木心在《从前慢》中写:“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个慢时代的通讯方式,一封信的书写、封存和开启,都应该是郑重而欢愉的吧。路途的疲惫,只有信封的磨痕知道,里面安放着的字迹和心事,都崭新如初。
我喜欢这个地方,我还喜欢这里的模糊感,“这封信”,寄信人不详,收信人只写着“河口”。当我站在这里,和这封信相遇时,我发现我就是那个收信人。
当然,河口邮政的存在,也是对殖民侵略的一个“冲击回应”。邮局寄信,在当时算是现代化的通信方式了。随着蒙自约开商埠,1896年蒙自海关设立寄信局。1897年在蒙自成立了大清邮政总局,同年,河口寄信局开始与法属邮政局互通信件。1898年清政府与越南政府正式签订协议,将中国河口局和越南老街局定为两国交换邮件局,从此河口邮政局成为云南第一个国际邮件互换局。
云南连通世界的国际邮路,早在1902年就已经形成。有资料显示:“河口局成为云南省主要国际邮路,邮件运输极为繁忙,河口局每天转运进出口邮件两百至三百余袋。”小小的信件,如同一座座隐形的桥,将话语和心情摆渡向世界不同地方的两个人。
但慢时代山长水遥的邮寄方式,漫长的等待还是会消耗人们的目光、眼泪和心焦。现在,发出消息,我们都等不了一分钟。
河口邮政局现在还在营业,只是谁还会去寄一封漫长又易夭折的信?
之所以费这么长的笔墨去叙述一个邮政局的前世今生,是因为当我们从河口邮政大楼去往河口老火车站时,我在中途的广场上,遇见了一个河口的“未来”。
“58 跨境数字贸易港”,这就是我在一栋仿法式风格建筑上看到的河口“未来”。
从公路大桥的国门,到河口老火车站这直线距离不超过四百米的空间,是一个神奇的存在,这里五位一体地呈现了河口发展的时空形态。如果说渡口、码头、铁路桥,是河口发展的过去时的话,那么公路大桥就是现在时,而我看到的“跨境数字贸易港”,就是河口的未来时态。
河口一直在不断地摆渡自己,将自己由此岸摆渡到彼岸,从过去摆渡到现在,它也会将自己摆渡到未来去。从进桑关渡口到红河航道码头,再转换形态变为铁路大桥,公路大桥,然后升级蜕变为虚拟的“数字贸易港”,未来的河口依旧是个口岸,只是它摆渡的桥,将隐藏在网络世界,隐藏在人们生活的暗处,不张扬,不可缺。
在“跨境数字贸易港”这几个大字下,密密麻麻地挂着一些标志:“58 同城”“天鹅到家”“前行科创”“飞件外贸”“久泰国际物流”……看着“数字贸易港”这几个字所代表的时空,我像看到《星际穿越》中的太空飞船般。我想这一次,河口将已经在跑道上了。
几百年来,红河岸边的边境城河口一直走在历史的前沿。
红河航道上的中国海关。
滇越铁路入滇第一站。
1954年开放的四个省级边境小额贸易口岸,河口在其中。
1987年至1998年,我国沿边开发开放战略启动,进入边境口岸互市贸易阶段。1993年中国河口—越南老街口岸恢复开通,河口是14 个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之一。
1999年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和实施后,沿边深化开放,河口作为我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跨境交通、口岸和边境通道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准备建设成为中越河口—老街边境经济合作区。
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沿边开发开放进入新格局,进入全面开发开放阶段。河口作为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合作的核心纽带和前沿窗口,于2017年开始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试点建设。
2019年,云南自贸区正式挂牌,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红河片区,就建在河口,中越边民贸易在“互联网+技术”的推进下加速发展。
2022年,第18 届东博会在广西南宁成功举办。“共享陆海新通道新机遇,共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作为有可能超过欧盟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的东盟,与中国的合作,将从“黄金十年”走向“钻石十年”。河口口岸,将迎接新的挑战。
写过《中国物流》的丁俊发有一个观点:“电子商务,特别是跨境电商的快速发展,将成为全球物流的新亮点……中国的垮境电商带动了全球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国际航空物流进入黄金发展期。”我在河口邮政大楼遇见了过去的河口,而在“跨境数字贸易港”遇见了未来的河口。百年前的缓慢邮路,去往世界,是一封信。百年后的国际航空物流,去往世界的是手指轻轻点击触屏,天涯海角,一点就到家。而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但充满期待。
“未来十年,将是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十年,是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的十年,是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的十年”。
面对未来,河口准备好了吗?
在河口国门和中越红河公路大桥之间,有一栋雄伟的建筑,矗立在红河岸边。这里是“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红河片区”,2019年挂牌运行,重点发展加工及贸易、大健康服务、跨境旅游、跨境电商物流四大重点产业,发展跨境金融、教育培训、总部办公、数字经济、专业服务五个配套产业。
当我抬头仰望自贸区大楼时,突然联想到第一次去故宫仰望午门的情景。轴线布局、外形简洁、气质庄严,它们不仅仅只是一个建筑,它是一个窗口,向世界呈现中国的形象、自信和气度。
大楼顶上,四个巨大方墩架起一个斗拱设计、红色立体的巨型倒三角形,它的设计理念,来自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符号——“鼎”。鼎,重诺守信,一言九鼎,它矗立在国境线上,将成为河口的新图腾,向世界展现中国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