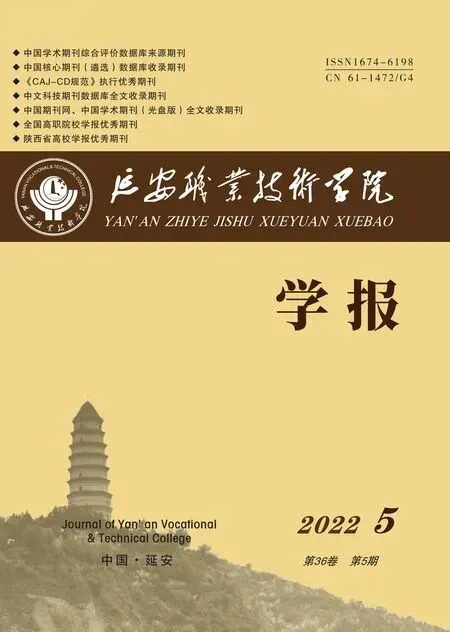晚明尘寰与文士的复杂心态分析
——以宋懋澄尺牍为例
洪月
(黑龙江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宋懋澄(1569—1620)字幼清,号稚源,松江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区)人,明后期文言小说家。他喜诗文,尤喜小说家言,其文言小说《负情侬传》《珍珠衫》后被冯梦龙重写为《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影响着此后小说创作。的确,宋懋澄的小说创作是其文学生涯的荦荦大者。但是,其小说的抒情意味淡薄,心态的呈现远不及尺牍显明。此前学界多侧重对宋懋澄文言小说的研究,对其尺牍关注不多。鉴于此,本文着重分析宋懋澄的尺牍文本,探究其尺牍中的隐微心态,管窥晚明尘寰中文士的复杂心态,一定程度上也可探微其小说文本的创作心态。
一、八股制艺下晚明文士的心态流变
八股制艺专为科举而设,对文士思想极具控制性,毁誉各半。八股文归属于一种应试文体,原不属于文学范畴,特定文化生态下却成为了左右士人命运的文体。读书人若欲入仕,便要掌握八股文的写作技巧,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八股文成为了明清文士出仕的敲门砖。可是,明清两代读书人对八股取士的认知视阈并非一成不变,具有流动性,心境亦随之流变。因此,晚明文士时常处于难以调和的矛盾之中。宋懋澄曾言:“弟少年,隆冬往来幽蓟,耳面风削,略不忘生此伧,虽少加韵,犹是正月东风。”[1]652少年之时,尽管路途颠簸,寒风侵肌,他对未来仕途却仍心向往之,殊不知科举终将成为遮蔽其一生的乌云。
宋懋澄十岁始习制艺,然而他少年意气,任由心性,专读《资治通鉴》《左传》《韩非子》《史记》之类古书,亦喜读唐诗,于其尺牍皆有直接或间接的体现。他认为“嗜古则能文”[1]660,亦坚守“以读书消岁月则乐,以之干功利则束情”[1]660与“读书不必过人,正令得其趣”[1]657的观念,宋懋澄认为读书应以兴趣作为导向,心怀好古之心,倘若仅以出仕为目的,则往往会被功利之心制约心性,可见其文化素养对读书目的及范围选择的影响[2]147。如是,种种不合时宜的主观倾向成为其科举接连碰壁的重要因素之一。
宋懋澄的心态流变存在历时性的转变与关键性的节点,二者皆与其科举经历密切相关,且不同备考阶段呈现不同状态,因而尺牍书写也显现出微妙的心态变化与情绪的反复。谈及科举经历与心态,宋懋澄言:“我二十年前,好名贪得,庚寅巳后,备尝艰辛,始信奢俭苦乐,总是一妄。然犹以进取自励,至甲午病胃犯噎,乃慨然束经,病中追思往念,悉已成空,遂并一切诸好,亦复澹然。”[1]653此言直接点明其在庚寅巳后与万历甲午两个时间点前后心态的流变,即由“好名贪得”到“备尝艰辛”,再到“亦复澹然”的转变。他一生参加科举考试十一次,除壬子年南京秋试中第,其他均落第。除万历甲午因胃病犯噎未参加秋试,他参加了有生之年所有的科考,整整十一次。因此,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宋懋澄内心其实是认同科举制度的。可以想象,一个少年在一次次的铩羽而归,不得已强行调试心态,接着再作冯妇,重新钻研八股制艺,在一次次的恶性循环中消耗了大量资产,也耗尽了所有的意气,而晚明又有多少此类蹭蹬的少年,无法定量。历经数次失意后,宋懋澄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对以八股文为功令文字的科举考试有了更为深刻而复杂的认识。他言:“此君白雪微有寒,恳请雕商刻羽衣助暖律。”[1]653此处的“微有寒”有隐喻之意,既指冬日气候的寒冷,也有对仕途不易的心境之寒,具有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寓意。可见,科举使其物质生活变得穷困窘迫,唯有向友人求援,更使其心态压抑,意志动摇,心境寒苦,精神受到束缚。因而,他感叹:“少苦羁绁,得志,但愿畜马万头,都缺衔辔。”[1]662衔辔羁绁了千里马,犹如八股文羁绁了蹭蹬士子,唯有雄鹰高飞,才能不受尘寰羁绊。此种象征性的抒情,是讽刺也是无奈。宋懋澄亦言:“吾闻‘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亦曰‘遯世不见知而不悔。’自今甘君子之疾永遯世之贞。”[1]654看似甘心实则不甘,看似轻蔑实则无奈,看似遯世实则恋世。在以八股文为功令文字的科举文化生态下,这种心态上的矛盾与流变普遍存在于晚明文士中。
二、晚明文士生存焦虑下的两难之境
尺牍作为文人抒发心绪的载体,书写着晚明文士的无奈与焦虑。生存焦虑源于生活,反作用于生活,兼具有形与无形的统一。宋懋澄尺牍中所透露出的复杂心态,很大程度上源于其生存焦虑。于他而言,家族血缘与地域文化、以八股制艺为功令文字的科举考试、“学而优则仕”的社会定见、个人的物质经济状况等是有形的;而由有形衍生的一系列诸如个人内在气质、社会责任感、同辈压力等无形之感,也早已内化为一个人的性情。有形与无形相抵牾时,人的心态便容易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这种困境在宋懋澄的尺牍中可具化为情与理和情与礼的矛盾,也意味着他必将陷入在尘寰浮沉里欲罢还休的恶性循环。
宋懋澄出身于松江的文化世家,深受儒家传统思想濡染。明代的松江府不仅是繁荣富庶的江南巨郡,而且是文教兴盛的科举重地,人才济济,这预示着他必将受到家族血缘、地域文化等人情因素的影响。从小浸润于江南浓厚的文化氛围与家族的文学传统中,昭示着家族使命终将成为其一生的桎梏,甚而不得不将其内化为生存意义。谈及家族使命,宋懋澄坦言:“弟之羁绁,夫何故哉?先人有未瞑之言,思籍一第以报命。”[1]655足以见得家族使命对宋懋澄的思想影响巨大,影响着他对人生路径的选择,甚而内化为一种无形的生存动力,乃至成为其一生的追求,以致转为终生的桎梏。此外,宋氏家族既是文化世家,亦是巨贾之家,为其提供了充盈的文化资源与物质资源。因此,当其好友钱希言遇家难,不得已放弃科考从事小说创作时,宋懋澄却因家境殷实,仍可潜心科举。祸福相依,相对充盈的物质资源却使其无任何理由放弃科考。他对稗官小说心向往之,却不能潜心于此,在对功名利禄趋之若鹜的时代大生态下,他别无选择,唯有在八股取士的道路上举步维艰。
“学而优则仕”的儒家传统陶染着诸多读书人,宋懋澄也不例外。他熟谙经史古文,自小受儒家传统思想熏染,“学而优则仕”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其潜意识里的理所应当,某种意义上也是晚明文士对政权依傍的体现,更是文士缺乏生存独立性的表现。对此,他曾直接宣称:“人生累我,岂惟父母妻子,皆为古人所累。”[1]658父母妻子的期待是有形的人情因素,但古人所遗留的出仕传统却是无形且根深蒂固的思想因素,此言显然是对儒家出仕传统的不满与无奈。不过,他持质疑态度同时,却也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他直言:“丈夫读书,欲以资通达,定经权,若惜字怜篇,儿女事也。”[1]661此处“经权”是宋明理学用语,是封建伦理纲常的具化,径直体现了宋懋澄对传统读书目的的认同。显然,一时的质疑只是其生存焦虑影响下的无奈之举,其遵循的读书宗旨完全符合儒家传统,他的不自洽行为勾勒出晚明文士的微妙心态,蕴含着入世与出仕的矛盾。
可以说,宋懋澄与阮籍、嵇康等人皆非实反礼教。谈及礼,宋懋澄直言:“仁义礼智信,终非止足处。”[1]659貌似对礼并不赞许,却表征了他深受儒家思想浸染的现状。龚鹏程言:“礼有两种,一种是能使人达到生命和谐状态的真正的礼,另一种是一般世儒所胶执坚守的那种纯然外在的名义器数之礼。”[3]21其实,此处礼的两种形式并无明确的界限,且常常共存,而多半晚明士人的郁结在于想要二者兼得,宋懋澄亦然。
宋懋澄自诩道:“世人见寻警寻,见尺警尺。他日见我,良应销魂。”[1]658出语直率,除却了传统君子的温柔敦厚与谦恭卑让。他慨叹:“自七岁以至今日,识见日增,人品日减,安知增非减而减非增乎?”[1]654显然,宋懋澄认为识见与人品之间存在着冲突,一定程度上可视为情与理的矛盾,亦是其生存焦虑的具化。谈及情,宋懋澄写道:“人生情耳,能无思乎?”[1]660他强调情是与生俱来的本能,讲求性灵,与多数晚明文士一致。另外,他在尺牍中流露出对英雄、美女和山水的向往和热衷。他直言:“士恨不生于战国,当斩张仪而咤鲁连。”[1]658可见其对建功立业的渴望与人生价值的多维审视,更是其现实心绪的折射。谈及美女,他坦率说道:“万事了不动心,惟见美人不能无叹。”[1]655其实,对美人的倾慕也只是其内心情绪抒发的窗口之一,是隐微情感的显性化。可以说,这既是一个人的情怀,也是一个时代社会风气与观念的体现,即明代中后期的江南地区,女子可以游历佛寺、参与庙会,观念相对较为开放,生活和思想皆较为丰富多元。亲近山水景物是晚明文人生活的重要部分,友人间的尺牍往来显露出晚明文士的共同关怀。宋懋澄曰:“宜水宜山一道人。”[1]661他对江南山水心向往之,但或许他更欣赏的是山水之外的至情人生。他亦写下:“深院凉月,偏亭微波,茶烟小结。墨花纷吐,梧桐肃肃,与千秋俱下。”[1]653如是,自然景物也披上了心绪的外衣,显得萧条与清冷,皆是其幽微心路的显性化表现。再者,山水亦难以亲近,即其所谓:“弹夜光于碧汉,不可以为星沉;昭华于清流,不可以为月。”[1]652两个“不”字,表面是对自然现象的客观书写,本质上却显露着他生于尘寰,累于万物的幽微心态。如是,他直言:“读书、饮酒、种树、笔削皆养生之道,然万物为其所累。”[1]658他认为闲适的读书生活,本应是性情的释放,但却累于尘寰万物,受限于礼。终究,情与礼还是互相抵牾,无法融合。
丁元荐《西山日记》写道:“愿为真士大夫,不愿为假道学;提起此心,便是天理;放下此心,便是人欲。”[4]丁元荐直接谈及“天理”与“人欲”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指明了当时常态化的社会现象。可见,情与理的矛盾心态普遍存在于晚明士大夫中。
三、晚明文士宗教观念的淡化
晚明禅悦之风盛行,宗教是一个热门的话题。然而,中国人的宗教观念,远远没有西方人那般虔诚与纯粹,显得更为理性与功利,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儒家传统思想早已先入为主。较之宗教,中国传统文士似乎更热衷诗歌,“诗言志,词言情”似乎已足够吐露他们的失意与得意。于是乎,宗教的存在似乎更像是一个备胎,只是特定时期的产物,如魏晋乱世人们心灵长期无法得到抚慰之际,宗教便兴起。战国、魏晋、晚明等时期的宗教发展各有其特征,因而文士心态皆有或显或隐的变动,如罗宗强言:“战国、魏晋和明代后期,士风与士人群体之心态,都有着较大之变动。”[5]1此言明确点出士人心态深受易代影响,与政治环境有着密切关系。
晚明历来受到学界重视,较之魏晋,晚明文士心态复杂得多。至晚明,八股取士制度固化、思想多元分化、土地兼并、流民增加等社会现象凸显,时刻影响着文士的生存。如是,太多失意科举、命途多舛、追寻人生意义无果的晚明文士选择恬退,并以宗教安抚心灵。因此,他们参禅学佛,并非随顺时风,好奇呈异,也不是要以此对抗什么“封建礼教”与“程朱官学”,他们对宗教的关注基于对生命的关怀,或许只为妥善解决自身当下的生存焦虑。晚明士人的宗教观可以具化为生死观,生死观是许多士人思想中的一个普遍存在,失意者更甚。晚明士人久困科场,对生死存亡有了更为深刻而复杂的思量。宋懋澄认为:“但愿一生受不死之疾,至四十许,杳然长逝可也。”[1]657也感叹道:“自盘古以至今日,人未尝死也。”[1]658前者将生死作为一种客观的生命现象,后者将生死上升为一种精神力量,二者的书写时间与语境存在差异,因而指归不同,但却殊途同归,皆可管窥宋懋澄不同人生阶段与境遇下的生死观。可见,宋懋澄的生死观是与时而变的,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理解,有时甚而上升为带有宗教意味的哲思。此外,他亦言:“死如月过天上,影落江河沟厕,悉无一染。”[1]661死后才能无染,恰恰表明尘世有染,有所牵绊。“染”为佛家语,其对佛家彼岸世界的憧憬一定程度上是对现实尘寰失落的体现。
不可否认的是,宋懋澄的尺牍中确实蕴含了宗教情愫与佛道教义,也隐含着宋懋澄对尘寰万物的关切与人生意义的思索,某种意义上是他回归自我的调适,但也时刻流露着其迷惘的心态。宋懋澄言:“梅花百树,枝枝善眼。仙人遥礼佳成,恍然净土,玉壶在艇。功德淋漓,敢不稽首以谢。”[1]653他认为宗教仙境为净土,高洁神圣,自己功德不足,但却心怀虔诚,心向往之,其复杂心态在“净土”的陪衬下变得显明。宋懋澄时常论及佛道之理,如“和尚不须梳镜,未免坏却剃刀。”[1]657诙谐的佛教理趣中也渗透着生活的哲思。另外,宋懋澄与佛道中人颇有交情,其好友当中亦有若干参禅悟道之人,如陈继儒、钱希言等,皆科举失意,一定程度上也是其社交语境的体现。再者,宋懋澄与友人的尺牍中频频直接或间接地渗透佛思,论及生存困境,抒发人生感慨,皆是其微妙心态的具化。他指出:“涉世不深,不知境苦;妄念不繁,不知业苦。”[1]654径直阐明其深入尘寰与妄念生成后心态的流变,点明处世不易与出仕艰辛,以及渐渐对人生有了更为深刻而复杂的认知。他言:视佛法如看天畔树,树外有天,天不限树。人竟不能于树外见天,以为天尽于树。”[1]661点明佛法的深邃,俗人对佛法的认知有其局限性,可谓径直向友人传播佛教教义,同时也暗含着宋懋澄对其时科举制度弊端的认知,更表达了他对生于尘寰的感喟。他又言:“病者小人所苦,而君子之幸。人若未死,唯病可以寡欲。某不患无得,惟恐病之不常来。”[1]657与“吾视天下犹剩物残编,不足烦我四大。”[1]654君子以病态求得无欲无念,不为外物所动,不蝇营狗苟,顺其自然,以求内心之平和与恬静,字里行间皆渗透着人生之思[6]171-176。此外,宋懋澄尺牍亦径直谈及友人好佛,如:“吾友子晋,尝言北行顾景生涕,子晋好佛,诸相未忘,虽鬓骨缁流,犹当质诸燕月。”[1]659此处“诸相”乃为佛教用语,指一切事物外现的形态,而“缁流”则指僧徒,可见晚明文士对诸多佛教用语极为熟稔,引用颇多,但“犹当质燕月”一句却仍掺杂着现实的情愫,淡化了其中的宗教色彩。然而,所有的宗教情感与生存之思终究归于一句“十年来奉教西方,而犹然以功利为戚,岂善男子邪?”[1]653宋懋澄坦率表露自己奉教西方却仍被功利之心羁绊,俗心难泯的困境。要之,宋懋澄在尘寰的功利心性与浓厚的俗世愿望面前,宗教观念亦不自觉随之淡化,显得不够纯粹,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晚明宗教世俗化的体现。
的确,佛教中深邃的哲学思考吸引了宋懋澄,使其可暂时摆脱尘寰的困扰。但是,长期浸润于儒家思想的他,无形之中早已对功名利禄产生了执念,看似云淡风轻的佛教观念背后,是愈发执着的功名意念。要之,即儒家观念并未在晚明文士的宗教观念中缄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