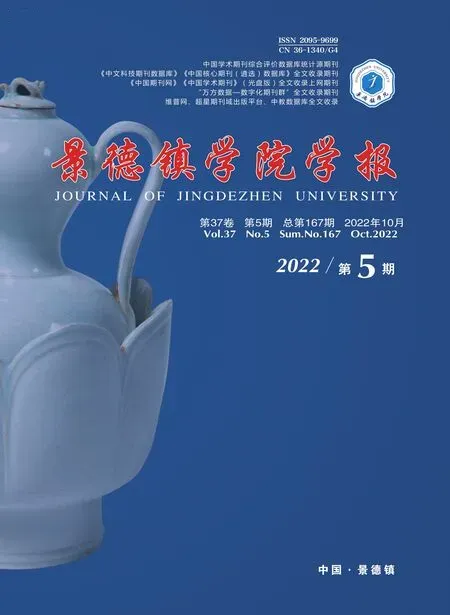陶瓷文化术语对外传播及翻译标准化
欧飞兵
(景德镇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西 景德镇 333400)
为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传承创新和对外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并得到积极落实。这给陶瓷行业与陶瓷文化的振兴和复兴带来了莫大机遇。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我国陶瓷文化对外交流将日趋频繁,陶瓷文化话语传播亦将日显重要。然而,考察国内外陶瓷文化英译,其状况委实不容乐观。作为陶瓷文化话语的核心,陶瓷文化术语首当其冲,各种翻译错误频频出现,原因之一便是标准化缺失。“话语传播,术语先行。中国特色术语翻译标准化是中国特色话语有效对外传播的前提与基础”[1]。陶瓷文化术语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文化术语,其翻译标准化是提升陶瓷文化话语对外传播效能的基本保障。为此,本文拟着力研究陶瓷文化术语翻译标准化问题,将分别以元文本与超文本为视角,探讨陶瓷文化术语翻译需遵循何种准则以及应如何遵循。
一、陶瓷文化术语翻译的标准化
我国陶瓷典籍多成于清代,最早介绍给西方的是法国传教士佩里·昂特雷科莱(Père D'Entrecolles)即殷弘绪(中文名)[2]。陶瓷典籍的早期译者也主要是外国人士,如《景德镇陶录》先后由法国汉学家斯塔尼斯拉斯·儒莲(Stanislas Julien)和英国学者杰弗里·塞义(Geoffery R.Sayer)于1856年和1951年译出,《陶说》由英国汉学家卜士礼(Stephen Wootton Bushell)于1891年译成,《匋雅》由杰弗里·塞义于1959年译毕。他们的译介对当时欧洲制瓷技术的进步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可是,在对照译本与原典之后,发现西方译者因为其文化身份,在翻译我国典籍方面有着国人无法比拟的优势,同时又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劣势。他们谙熟译文读者的阅读期望并设法予以满足,从而增强了译本的接受度,但对中国文化又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解、误解甚至曲解,进而导致漏译、误译乃至错译。这种情况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未曾消失,在中国特色术语跨文化传播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要解决这一兼具历史性与现实性的问题,中国特色话语的自主对外传播非常必要,而中国特色术语对外翻译的‘标准化’问题则是重中之重”[1]。
作为极具民族性的中国特色术语,陶瓷文化术语在由西方主导的翻译实践中处于被“他塑”境地,这既造成了西方民众对我国陶瓷文化的认知歪曲,也损害了国家文化形象。根除这一问题,需要对现有陶瓷文化术语译名系统进行梳理和审查,以“确保术语概念界定层面的准确性、语符表征层面的一致性,使之更加合理规范”[1],从而在“去他者化”中实现自我“重塑”。陶瓷文化术语不仅富有浓郁的民族性,还有着鲜明的地域性。要“提升‘地方性知识’的影响力,为其他地域人群提供普适性价值参考,是民族文化自觉与自信的体现,同时也需要相关话语体系的构建与有效传播”[1],其中,陶瓷文化术语对外翻译“标准化”是关键。
二、陶瓷文化术语翻译的元文本标准
由于术语实质上是指称概念的语符集,从陶瓷文本本身考察,其翻译标准主要源于语言学和术语学范畴。所谓“标准”,就是“对重复性事物和概念所做的统一规定”[3]。陶瓷文化术语翻译与传播具有一定“重复性”,探究其“统一规定”,有助于提高陶瓷文化对外传播效果。这种元初性翻译标准在语言学和术语学领域,又可细化为具体细微的翻译准则。
(一)陶瓷文化术语翻译的语言学准则
语言学准则是陶瓷文化术语翻译的首要基准。囿于篇幅,现仅探讨陶瓷文化术语及其译名在语言场中的功能对等与意义对等。
1.术语与译名间的功能对等
人们在译介陶瓷文化术语时,往往只顾及术语同其译名之间的形式对应,却忽略了它们在语言功能上是否对等。比如,“胆式瓶”和“美人肩瓶”常被译作gallbladder-shaped vase 和beauty shoulder porcelain vase。在这两个译例中,术语与译名只是达成了词汇表层对等。要实现本质上的功能对等,还需依据术语翻译的人类学准则、文化学准则(下文详论),将其改译为waterballoon-shaped vase 和beauty-shaped porcelain vase。
2.术语与译名间的意义对等
术语及其译名之间的意义对等是动态功能对等中最重要的语言准则。倘若术语及其译名无法达到全意域融合,那么至少要实现核心意域重叠。例如,装饰文化术语“三公图”常被译成three cocks 或three roosters,也仅做到了表层一致。“三公图”,指以三只公鸡为题材的瓷板画,作者是景德镇“珠山八友”中的花鸟画家刘雨岑。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画家感佩于抗战壮举,创作了多幅三公图。“如此厚重的文化寄寓,非cocks或roosters 所能承载,而chanticleers(意即雄鸡,尤指神话故事里的)与画家心目中如同神一样存在的英雄们在意蕴上高度吻合”[4]。
(二)陶瓷文化术语翻译的术语学准则
陶瓷文化翻译旨在让各国了解中国陶瓷文化,要使陶瓷文化术语为外国受众所知晓,除了首先考量的语惯习,还需遵从术语学的内在设定。
1.通用性:术语译名遴选准则
在文化外宣时,一个术语常对应多个译名,如“粉彩”的译名有Fencai、famille verte 和famille rose。如何抉择,实非易事。若单“从通用性看,famille rose 居三者之首”[5]。相比于“粉彩”,“建盏”的译名更繁杂,有Jian Zhan、Jianzhan、Jian ware、Jian bowl、temmoku tea bowl 等。如此多的译法显然违背了术语的单义性与简明性,也降低了建盏的翻译效度与传播质量。建盏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在日本、东南亚等地的代名词是天目(temmoku)盏[6]。既然temmoku 通用范围较广,我们拿来又何妨?
2.专用性:术语译名辨识准则
在无法确认术语译名是否通用的情况下,译者可依傍专用性准则加以辨识。众所周知,同景德镇瓷器一样,宜兴紫砂壶是中国陶瓷通行世界的名片。如此知名的“紫砂”在联合国总部、国际会议、高校教科书等不同场合,被译成Zisha、purple granulated、purple sand、dark red sand 或purple clay 等。这纷繁的译名真是“乱花渐欲迷人眼”,令译者无所适从。殊不知国际陶瓷界业已赋予宜兴陶瓷以专称“boccaro”,吾等无妨采而纳之。
3.适用性:术语译名匹配准则
在翻译陶瓷装饰文化术语时,由于一件陶瓷有时不止一种装饰,“各种技法是逐一翻译,还是择一而译,需要新的规范予以界定”[7]。只有那种与陶瓷最匹配的装饰,才是术语最适用的译名。这一准则的运用具有较大的灵活性:绘画装饰匹配时取译名painted;塑形匹配取译名shaped;雕刻匹配取译名incised 或carved;雕塑匹配译成sculpted;雕画匹配译作designed。
三、陶瓷文化术语翻译的超文本标准
陶瓷文化术语翻译在完成语码转换之后,须暂时悬搁元文本系统,从超文本视角去揭示术语所蕴含的文化符码及其象征。超文本标准由此成为陶瓷文化术语翻译的必要圭臬。确立这类标准,要求译者能够超越语言学与术语学范畴,于更为广阔的人类学、历史学、文化学乃至器物学当中,去探寻陶瓷文化术语在源语域和的语域之间的互为映射。
(一)陶瓷文化术语翻译的人类学准则
陶瓷文化翻译的主要目的是让外国民众了解我国陶瓷文化,提升陶瓷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因而在翻译陶瓷文化术语过程中,译者有必要考量翻译受体“读者”的心理期待与接受效果,遵循文化对外传播的人学准则。
1.受体的心理图式是增加术语翻译效度的基础
翻译效度关乎主体“译者”的意图和受体“读者”的期待,主体意图能否达成要看受体期待满足与否。陶瓷文化术语翻译需要考虑受体心理图式的层级性,对于层级较低的受众,因期待视野较窄,简单直译即可;对于层级较高的受众,因期待视野较宽,在直译基础上须添加注释。譬如,器物文化术语“注子注碗”被译作jug[8],有失规范。“注子注碗”是古代中国的套装酒具:“注子”即酒壶,用于盛酒,常置于碗中;“注碗”又称温碗,内注热水,用以温酒。若直接音译成Zhuzi and Zhuwan,或意译成wine-warming pot and bowl,虽顾及了普通受体的低层图式,却忽视了高层级者的认知需求。在对外的专业资料中,建议先将合体的“注子注碗”总译为wine-warming porcelain pot and bowl set,再给予分体的“注子”“注碗”以阐释:Zhuzi(wine pot);Zhuwan(bowl into which hot water is poured for warming up wine)。
2.受体的文化图式是增加术语翻译效度的阈限
翻译效度的增长常受制于受体文化图式。翻译受体作为某一族群的个体,能够复制所属文化模因,形成自己的文化图式。相比于心理图式,文化图式更深层更稳固,能阻隔或开启信息通道。当术语的源语文化具象无法投射到的语域时,术语信息会被阻隔在文化图式之外;只有将其置换成的语域中类似的文化具象,才可能突破阈限,让术语信息进入文化图式。这一准则可从器物文化术语“骆驼载乐俑”的翻译处理上得到验证。该术语曾被译为Camel Carrying Musicians[8],表面上看较为对应,却很难触动受众。“骆驼载乐俑”是一件唐三彩,表现的是乐舞伎乘坐骆驼在首都长安沿街巡演的场景。那景象不禁使人想到西方的街头表演(street performance)。如果把译名里的Musicians 置换为street performers(街头艺人),术语的源语文化具象便可以投射到的语域,换言之,汉语文化具象“乐舞伎”与“沿街巡演”将冲破受众的文化阈限,变成英语文化具象“street performers”与“street performance”。
3.受体的审美图式是增加术语翻译效度的节点
翻译效度的提高时常受控于受体审美图式。翻译受体不仅能复制本族的文化基因,而且会承袭族群的审美惯习,形成独特的审美图式。与文化图式不同,审美图式是具有想象特质的内化结构。只有当源语文化意象符合个体审美想象时,源语投射到的语域的信息才能通过节点被个体接受。这一准则可以“胆式瓶”的翻译为例。“胆式瓶”之所以不宜直译成gallbladder-shaped vase,是因为译名中的文化具象gallbladder 同受体的审美图式不符,会令其产生不愉悦想象。故须将它剔除,而代之以形似神合的其他美好形象(如water balloon)。
(二)陶瓷文化术语翻译的历史学准则
陶瓷文化翻译的目的还在于向世界宣传中国陶瓷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鉴于此,在陶瓷文化翻译过程中,要注意探察术语本源,引导受众领悟中国陶瓷历史的深邃内涵。
1.寓术语历史意涵于译名主体
前文依据术语通用性准则论述了“建盏”译名的取舍,现尝试从历史学角度重新译之。在建盏一词中,“建”音jiàn,指代窑场(建窑)与产地(古建宁府建阳县,即今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盏”音zhǎn,本意是器皿(ware),如油盏、灯盏等,此处指茶盏(tea bowl)。结合“建盏”的音义及历史,采用“种+属”的方法,可译为Jianzhan bowl。其中,Jianzhan 为一“种”器物,“属”于tea bowl。这在英语世界并不陌生,如埃博拉病毒的英文名就是Ebola virus。译名中舍去tea,不违术语之简明性特征。
2.附术语历史源流于译名注释
当历史渊源放进译名不能凸显术语特征时,宜附于译名之后。这一准则可在“景德镇窑青花折枝花卉纹碗”的译法上得到印证[9]:首行大字,为主名Jingdezhen Ware Bowl;尾行小字,为工艺源流Porcelain painted with underglaze cobalt blue。
(三)陶瓷文化术语翻译的文化学准则
在翻译陶瓷文化术语时,需要揭示和传达其潜在模因的文化象征及意义,引领世人感受中国陶瓷文化的独特魅力。
1.术语翻译需保全文化意象
文化术语翻译牵涉意象传播时,容易产生三种偏向:意象缩小、意象放大和意象异化。“美人肩”常被译成beauty shoulder,其失在于译名缩小了术语的文化意象。美人肩瓷瓶不单肩美,整个器物都形似美人,故应译为beauty-shaped porcelain vase。另一术语“鸡首壶”被译成chicken-headshaped ewer[10],失在放大了术语的文化意象。鸡首壶不是整个壶体型如鸡首,只有壶嘴(spout)形似而已,据此,应译为ewer with a chicken-head-shaped spout。而前文所论“三公图”有时还被译成birdand-flower painting[8],源语意象“雄鸡(chanticleer)”变异为的语意象“bird(鸟)”,可谓失莫大焉。
2.术语翻译需保真文化信息
文化术语翻译涉及信息传输时,容易出现三种偏差:信息冗余、信息不足和信息模糊。在中国古代酒器外宣资料中,“彩陶觚”被翻译成painted pottery gu[11]。译者不知“彩陶”有专名faience,导致冗余painted pottery。将“觚”译成gu,保留了历史意涵,但译名过简,不足以使受众接收觚的真实信息,须添加注解ancient Chinese wine vessel。前段所论“三公图”(Three Chanticleers)被译成bird-and-flower painting,不仅导致了形象异化,而且造成信息模糊。
3.术语翻译需保护文化生态
陶瓷文化术语译者在避免翻译偏向偏差的同时,不应忘记还肩负着维护世界文化生态的使命,因为平等共生是各国文化交流和发展的基础,更因为文化“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进步的动力”[12]。从文化角度看,在不影响的语读者理解和接受的前提下,译者应采用异化翻译策略,尽可能展示源语文化的本来面貌,以维持世界文化的原生多样性。
(四)陶瓷文化术语翻译的器物学准则
在翻译陶瓷文化术语过程中,还需揭开器物的神秘罩纱,以展现中国陶瓷特有的器型神韵。
1.术语翻译要表现器物所指
陶瓷文化术语译者尤其是器物术语译者,须要遵守器物学的固有本规,在译名里忠实地反映或表现器形器貌。倘若不然,译介便失信于“物”。如“人面网纹盆”被译为A pottery basin,painted with people’s faces in the Netlike Design[8]。察看原物图片,发现此译有两处悖谬:该盆不是普通陶器(pottery),而是彩色陶器(faience);盆内壁上的装饰不是网状的人面纹(people’s faces in the Netlike Design),而是网片纹和人面纹(net and person’s face)。综上,可将“人面网纹盆”译成Faience basin with pattern of net and person’s face。
2.术语翻译要体现器物能指
要在译名里准确地传达或体现器物精神,需揭示其符号意义。“中国的陶瓷开辟了人类器物领域的最高境界”[13],蕴含着深厚的中华文化。译介时不认真释读,就难免出现偏失舛讹。譬如“龙纹”是中国陶瓷的典型饰样,常见于瓶、罐、缸、尊、壶、盘、碗、墩等器物上。其译名dragon 之失在于遮蔽了源语文化意象。就象征而言,英语单词dragon 趋于贬义,而汉字“龙”多为褒义。为展示我国文化符号的真实意义,应将“龙”译成Long(Chinese dragon)。
四、结语
陶瓷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可以说,“陶瓷,对内是国之瑰宝,是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对外是国家名片,是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认知中国的重要标识”[14]。陶瓷文化及其术语“走出去”进程日渐加快,但其翻译效度亟待加强。翻译标准化可为增强话语对外传播效能提供保障。我们据此探究并提出陶瓷文化术语翻译的各类标准,基于元文本视角需遵循语言学与术语学准则,基于超文本视角应遵照人类学、历史学、文化学与器物学准则。这些准则可单独制约或协同规范陶瓷文化术语翻译过程,有利于减少陶瓷文化术语误译、增强陶瓷文化话语叙事认同以及促进陶瓷文化国际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