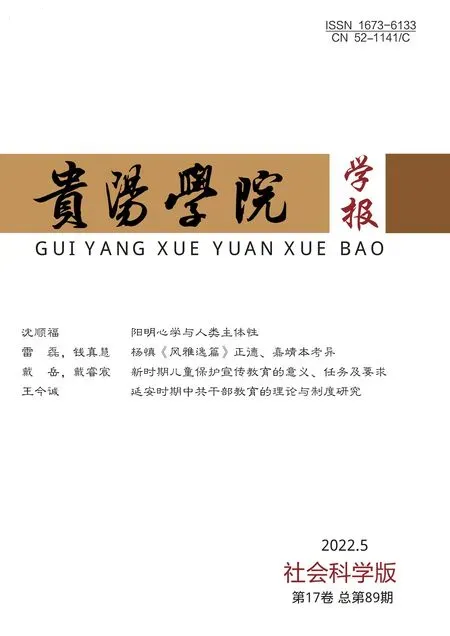阳明心学与人类主体性
沈顺福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笔者认为,王阳明不仅是传统儒家心学的代表人物,而且是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集大成者。阳明心学,一改传统理学向外穷理的路径,认为自己便是自己命运的主宰,即“止于至善岂外求哉?惟求之吾身而已”[1]1195。主宰在自身。准确地说,王阳明明确提出,这个主宰者不在别处,“身之主宰便是心”[1]6。由此,他将主宰力量由外在天理转向至内在良知,从而突出了内在良知在人类生存进程中的主导性作用与地位。这种理解,与现代哲学所强调的实践理性或自由意志的观念十分接近。故而现代学者大多将这种思想理解为主体性。如,劳思光说:“‘心’指自觉意志能力而言。”[2]312心所蕴含的良知则是人类的“最高主体性”[2]324。董平先生:“作为本原性实在之‘良知’……是真实的存在本体与整全的人格本体,也是独立、自主、自由、完善的‘主体性’本身。”[3]他认为良知体现了人的主体性。类似观点比较流行,似乎也是学术界的主流立场。本文将对此展开讨论,并试图指出:将良知理解为主体性有些简单。作为行为主体的人,其主体性应该分为两类,即人类主体性和个体主体性。阳明学突出了人类主体性,却很少关注于个体,“我”也不等于个体的自我。阳明学没有什么个体主体性观念。
一、阳明之主宰心
在程朱理学看来,决定人间事务乃至宇宙万物运行的主宰者只能是天理。万事万物皆依循天理。没有了天理,岂不是翻了天?理主宰一切,包括人心,即人心的活动只能服从天理。天理是宇宙万物包括人类生存的决定者或主宰者。这种对宇宙天理的仰仗与迷信,不仅将本心与天理分裂为二、突出了对外部事理的尊崇,而且也淡化了人自身之心在其生存中的地位与作用。对此,王阳明十分不满。王阳明曰:“心一也,未杂于人谓之道心,杂以人伪谓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谓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语若分析而意实得之。今日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并立,安有天理为主,人欲又从而听命者?”[1]7传统程朱理学认为人心不同于道心,从而造成二心说。更有甚者,程朱理学常常认为人心听命于天理,似乎一个是心,另一个是理。这便是心理为二。这些观念,在王阳明看来,都是需要反思的,或者说,王阳明都不太赞同。王阳明曰:“朱子所谓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即物穷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谓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析‘心’与‘理’为二矣。……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1]44-45朱熹的格物穷理说是将心与理分为两者。在王阳明看来,这二者应该是一。心与理合而为一,这便是王阳明的心灵学说。
阳明心灵学说主张人心是生存的主宰。王阳明曰:“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视听言动?心欲视听言动,无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1]90-91人的行为具体表现为视、听、言、动等。这些行为即身动最终听从心的调遣与安排。因此,心是行为的主宰。王阳明曰:“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1]6如果说身体活动代表了人的行为,那么,作为身体之主宰的心便是这个行为的主导者。王阳明曰:“主宰一正,则发窍于目,自无非礼之视;发窍于耳,自无非礼之听;发窍于口与四肢,自无非礼之言动:此便是修身在正其心。”[1]119人的视、听、言、动等行为皆听从于人心的指导与安排。心正自然行端。人心是行为的基础。王阳明曰:“心之发也,遇父便谓之孝,遇君便谓之忠,自此以往,名至于无穷,只一性而已。”[1]15人心是人的主宰者。合理的行为如孝、忠,无非是此心之发动。心是人类活动的主宰者。
这种主宰,王阳明常常称之为“我”。王阳明曰:“诸君只要常常怀个‘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毁谤,不管人荣辱,任他功夫有进有退,我只是这致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处,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动。”[1]101我只管自己自强不息而无关他者。我是主宰,我的一切行为皆由我定。王阳明的这种主宰说,表面来看和现代理性主义哲学比较相似。如康德说:“在自然界,所有的事物都依法运行。只有理性存在者有依据法则观念行事的能力,即依据意志原理而行为。由于依据原理的行为需要理性,因此,意志正是实践理性。”[4]412人的一切行为产生于自己的理性,并接受理性的指导。这种实践理性,康德称之为意志。意志也属于人心。意志主导论也是一种心主说,即它也主张人心做主的观念。据此,不少学者进行了类比,并认为王阳明的心主论突出了主体性,其所主张的我便是自我,其行为便是与自由相关的行为。那么,王阳明所说的我是不是自我呢?王阳明所说的主宰究竟指为谁做主呢?王阳明的心主论是不是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呢?
二、主体性:人类主体性与个体主体性
人是一个生命体。这个生命体,作为一个物理实体,也可以叫做作主体或行为主体。这个行为主体常常表现为两个主要身份,即作为种类的人和作为个体的人。从宇宙存在的视域来看,人类是宇宙万物之一员,是区别于其他生命体的特殊的生物种类。这便是人类。从现实来看,人又是社会存在者,是社会一分子。在这个社会群体中,个人不同于其他人。这便是个人。因此,作为主体的人不仅指人类,而且指个人。人的主体性因此被分为两种,即人类主体性和个体主体性。人类主体性关心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是人之所以为人并区别于别的生物的东西?这便是传统儒学所说的人性。人性论讨论了作为种类的人的性质,以及人类在宇宙中的作用与地位。个体主体性则是个体人成为其自己并因此而区别于别者的终极性依据。这个个体主体性是作为行为主体的我之所以成为我的终极性依据。依据它,行为主体成就了一个具体而特殊的我或自我。
在阳明这里,做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为人做主,另一个是为万物做主。所谓为人做主的观念和传统儒家的天命观相关。在中国文化的早期便流传着一种天命观,即:“死生有命,富贵在天。”[5]140人的生死寿命以及现实的荣华富贵、穷达遭遇等皆由苍天决定。这便是天命论。天命论的核心是天决定人的生存,即天主人从。人只能听天由命、安然待命。孔子反思了这种消极的人生观并提出了自己的独立想法,主张以人文对抗自然之天命。这一主张直接开启了传统儒家的人文主义的发展方向,并成为从孔子到王阳明的传统儒家思想历程的中心主题。孔子、孟子、荀子等别天人从而为人文主义的仁义之道发挥作用保留了一定的空间。汉代董仲舒等主张人副天数,将仁义之道提升到与苍天同等高度,从而将儒家的仁义之道等人类文明提升到了空前的高度。魏晋玄学主张天人一体,从而将人类与苍天等融为一体,首开民胞物与的思想观念。北宋张载首倡“为天地立心”[6]320,尝试着由人类来主导宇宙生存。二程主张万物一体,并以为:“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心一作体),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一日之运即一岁之运。”[7]13由此,人类成为宇宙之主宰。朱熹以为“教化皆是人做,此所谓‘人者天地之心也’”[8]2243,即人文教化为主导万事万物生存的主导力量,即“天地之心”。到了明代,王阳明也借用了《礼记》中的“天地之心”一词,曰:“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而又亲切简易。”[1]214心是生物的主宰。作为生命体的天地宇宙的主宰即天地之心便是人。这里的人包含两层内涵,即人类与人文。合起来说,人类及其所创造的文明是宇宙的主宰。这种主宰关系首先适应于人类自身,即人自作主宰。由此,传统的天命观发生了逆转。针对朱熹分裂知行的进路,王阳明分出三种模型。其中包括圣人之事是生知安行,贤者之事是存心养性而知天,而学者之事是夭寿不二、修身以俟。圣人能够做到知行合一,原因在于“自然”即必然,亦是应然而合理的,无需修身。或者说,圣人必然通天命。至于贤者、学者等,王阳明曰:“事天虽与天为二,然已真知天命之所在,但惟恭敬奉承之而已耳;若俟之云者,则尚未能真知天命之所在,犹有所俟者也,故曰所以立命。‘立’者‘创立’之‘立’,如‘立德’‘立言’‘立功’‘立名’之类,凡言‘立’者,皆是昔未尝有而本始建立之谓,孔子所谓‘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者也。”[1]44立即创立。人类自己创立自己的命运。这样,王阳明由传统的天命说转变为立命说,即人的命运在自身。这种立命说推翻了传统的天命观,并将人类命运的主宰权交还给人类自身。从由命向立命的转变不仅仅是权利的转让,更是人生观的改变。天命说倡导顺其自然、消极待命的人生观。而立命说则突出了人的主动性,即,我们不需要等待苍天的安排,而应该积极主动地把握自己的命运。这种主动性无疑体现了人的主体性。
这种主体性的基础是天人关系,即,这种主体性适用于天人关系理论中,它解决的中心问题是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等问题。早期儒家主张天命说,即苍天决定人类的命运。到了理学时期,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儒家不但认为人类的命运在于人,而且进而提出人主天地的观念。王阳明曰:“天地气机,元无一息之停;然有个主宰,故不先不后,不急不缓,虽千变万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时,与天运一般不息,虽酬酢万变,常是从容自在,所谓‘天君泰然,百体从令’。”[1]30万物生生不息。其生存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决定者。它不仅让生存成为可能,而且决定了它的合法性。“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无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1]79天地万物与人类共为一个生命体,这个生命体必然有一个主宰之心。这个主宰之心便是人,人是天地万物所构成的宇宙的主宰者。王阳明曰:“你只在感应之几上看,岂但禽兽草木,虽天地也与我同体的,鬼神也与我同体的。……你看这个天地中间,甚么是天地的心?……可知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为形体自间隔了。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1]124人与万物之间借助于感应而贯通一体,这个感应体的主宰者便是人。更进一步说,这个主宰乃是暗含良知的人心。“人孰无根?良知即是天植灵根,自生生不息;但著了私累,把此恨戕贼蔽寒,不得发生耳。”[1]101有了良知,人便能自强不息。人因此不仅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而且能主宰宇宙的生存。
王阳明所谓的主宰,包括主宰自身的命运以及主宰宇宙的生存。这个主宰者,准确地说,主要指作为宇宙一分子的人类。主宰者是人类。立命说中的人讲的是人类:人类主宰自己的命运,而不是由天来安排。同时,作为“天地之心”的“人”并不是指个人,而是指人类及其所创造的文化。这便是王阳明主体性的实质,即它属于人类主体性。
三、心主论即良知主宰论
王阳明强调的主宰,强调人不仅要主宰自身的命运,而且可以主宰宇宙的进程,最终成为宇宙万物生存的主宰者。这种主宰性地位突出了人类的主导性。不过,这种主体性只限于人类主体性:在宇宙生存进程中,人类才是最终的主宰者。它突出了人类在诸种生物中的主导性作用与地位。其表现便是号召人们自强不息、积极进取。“中间以尧、舜、文王、孔、老诸说,发明‘志学’一章之意,足知近来进修不懈。居有司之烦而能精思力究若此,非朋辈所及。然此在吾明德自以此意奋起其精神,砥切其志意,则可矣。”[1]213尧舜之道,进修不懈,奋起精神,志向高远,最终抵达圣人之阶级。这完全符合《易传》所强调的“自强不息”[9]14的积极进取精神。
这种积极进取行为的基础是人心。王阳明曰:“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1]6心是主宰,其表现为意。心意体现了人的主动性。这种主动行为的终极性根据便是良知,即良知才是心及其正确的活动的终极基础或主宰。王阳明曰:“良知犹主人翁,私欲犹豪奴悍婢。”[1]1167良知是主人翁,私欲则是使唤丫鬟,良知主宰人心活动。王阳明曰:“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其虚灵明觉之良知,应感而动者谓之意;有知而后有意,无知则无意矣。知非意之体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1]47心之所以能够做主,原因在于它内有良知。正是内在的良知使其能够明而灵,并确保了行为的合法性,即事事物物无不合“理”。为什么呢?因为良知便是天理。王阳明曰:“昏暗之士,果能随事随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则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大本立而达道行,九经之属可一以贯之而无遗矣。”[1]47良知即心中的天理。心中有良知便是心中有理。心中有理,其所产生的行为自然符合此理。“心,一而已。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义,独可外心以求理乎?”[1]43心主宰一切,而心又听从天理。听从天理的心的活动自然是合“理”的行为。
这个良知、天理具体于人身上便是人性。王阳明曰:“知是理之灵处。就其主宰处说,便谓之心,就其禀赋处说,便谓之性。”[1]34良知即天理,其在人之禀赋便是性,性即天理。王阳明曰:“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穷仁之理,真要仁极仁,穷义之理,真要义极义:仁义只是吾性,故穷理即是尽性。”[1]33-34良知不仅是理,而且是性。“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则谓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则谓之心;以其主宰之发动而言,则谓之意;以其发动之明觉而言,则谓之知;以其明觉之感应而言,则谓之物。”[1]76-77心中之性即是理。心之所以能够主宰人的视听言动等行为,最终还是因为其背后有良知即性做主宰。王阳明曰:“所谓汝心,却是那能视听言动的,这个便是性,便是天理。有这个性才能生。这性之生理便谓之仁。”[1]36人的行为不仅是血肉心的活动,而且还以人性为主导。绝对正确的人性加上动力的人心一起,必然产生合理的行为。这个合理的行为便是仁。仁即合乎天理的行为,它最终决定于人心、真己或人性。人性才是正确行为的最终极的主宰者。
这样,王阳明的心主论便转换为良知主宰说。而良知主宰说其实是本性主宰说。所谓本性如人性,按照传统儒家哲学如孟子的基本定义,乃是指人类的普遍本性或本质,即人性乃是人类之所以为人并区别于牛马的本性。这种人性主要指普遍人,或者说它主要指人类的本性。作为人类本性的人性突出了人类的性质,这种本性具有普遍性。同理,万物作为“生物”也有自己的本性,性是所有“生物”体的本性。这种普遍存在,从体用论的角度来看,可以分为体与用,即性即凝聚之体,理即流通于用。这便是二程所说的“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7]204。理之在人便为性,处置于事便是理。在人为性,在事为理。理如同恒常之日。心中的日即性与身外之日即理,其实还是一个日。故王阳明曰:“天下无性外之理,无性外之物。”[1]77万事万物皆出于性而循理。性或理皆是公性或公理,是普遍存在。从万物一体的角度来看,万物一性而一理。其中,性是体,理显于用。故,理性无二。王阳明曰:“夫理无内外,性无内外,故学无内外。讲习讨论,未尝非内也;反观内省,未尝遗外也。”[1]1273万物一体而一性,万物之间并无内外之分。故,性无内外,理无偏公。内在于身便是性,外化于事便是理。性或理皆是普遍存在。因此,所谓的心主论、良知主宰说,其实是普遍本性主宰论。
能够主宰的人心由两个部分组成,即气质的人心与纯粹的良知。人心与良知合起来形成一种可靠的心,并因此而成为人类行为的主导力量或决定者。可是,我们如果对此进一步地分解,便会发现,在这个结构体中,气质心常常是不可靠的,而良知则是纯粹可靠且善良的实体。在气质心与良知关系中,主导的天平自然滑向良知端,即,在良知与人心关系中,至善的良知才是最终的决定者。良知是天理,也叫人性。心主论其实是人性主宰论(这是先秦孟子传统的观念)、天理主宰论(程朱理学的基本立场)、良知主宰论(阳明立场)。它强调作为一个种类的本性的决定性作用。心主论以普遍本性为最终主宰者。在这个主宰者面前,人是普遍的人类,而不是具体的个人。具体的个人,面对普遍而绝对的良知时,人只能俯首帖耳地顺从,个人并不能真正地做主。这便是王阳明心主论的实质。
四、我:“私我”与我们
和传统理学相比,王阳明已经意识到,人类生存的主导权在人自身,即人的事情人做主。在现代汉语中,我具有强烈的主体性意识,人们常常将其类比于自我。由于王阳明也常常用“我”字,人们也因此常常以为王阳明具有自我观念,从而具有个体主体性意识。其实不尽然。的确,王阳明很重视我这一概念。王阳明曰:“圣人气象自是圣人的,我从何处识认。若不就自己良知上真切体认,如以无星之称而权轻重,未开之镜而照妍媸,真所谓以小人之腹而度君子之心矣。圣人气象何由认得?自己良知原与圣人一般,若体认得自己良知明白,即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今且说通于道在何处?聪明睿智从何处出来?”[1]59道在我,圣人气象亦在我,我自做主宰。阳明的这一立场似乎表明,阳明十分重视我,且具个体主体性意识或观念。那么,阳明所说的“我”的真实内涵是什么呢?
在王阳明那里,“我”有两个意思:“我”一个是行为主体,另一个是我们。“我”首先指行为主体。王阳明曰:“盖其心学纯明,而有以全其万物一体之仁,故其精神流贯,志气通达,而无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间。譬之一人之身,目视、耳听、手持、足行,以济一身之用。目不耻其无聪,而耳之所涉,目必营焉;足不耻其无执,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盖其元气充周,血脉条畅,是以痒疴呼吸,感触神应,有不言而喻之妙。”[1]55这里的“物我之间”的我仅仅指作为物理实体的行为主体,我是一个物体,他者是另一个物体。万物一体观将我和他者视为同一个生命体。这里的我仅仅指一个生命物体而已,或曰物理实体、行为主体。
作为物理实体的我是一个气质之物即气质我。王阳明曰:“凡饮食只是要养我身,食了要消化;若徒蓄积在肚里,便成痞了,如何长得肌肤?”[1]95饮食“养我身”中的“我”便是指气质我。王阳明曰:“墨子‘兼爱’,行仁而过耳;杨子‘为我’,行义而过耳。”[1]77杨朱所偏重的“我”便是气质我或肉身我。王阳明曰:“夫加诸我者,我所不欲也,无加诸人;我所欲也,出乎其心之所欲,皆自然而然,非有所强,勿施于人,则勉而后能:此仁恕之别也。”[1]149欲即人欲,我欲即气质我的活动,这便是私我。王阳明曰:“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特其间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视其父子兄弟如仇雠者。”[1]54作为行为主体的我是一种私我,我即私。这种私我即气质我常常将人区别于圣贤。王阳明曰:“夫谓学必资于外求,是以己性为有外也,是义外也,用智者也;谓反观内省为求之于内,是以己性为有内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无内外也。”[1]760有我即有私我,以私人之气质为主导。比如功利之心,王阳明曰:“使在我果无功利之心,虽钱谷兵甲,搬柴运水,何往而非实学?何事而非天理?况子、史、诗、文之类乎?使在我尚存功利之心,则虽日谈道德仁义,亦只是功利之事,况子、史、诗、文之类乎?”[1]166功利之心即我之欲,我是欲望、功利之心的行为主体。
以气解释我、我为气质我也是传统儒学的共同立场。如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10]46我便是一个由浩然之气而构成的气质体。郭象曰:“然则生生者谁哉?块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则我自然矣。”[11]16我是万物的一员,属于气质之物。二程曰:“天之付与之谓命,禀之在我之谓性,见于事业(一作物)之谓理。”[7]91人性便是苍天禀赋于气质之物上的东西,我即此气质的身躯。隋人慧远曰:“何者是我?五阴和合,假名集用,说名为我。”[12]474我即五阴和合而成肉身。这个肉体之我便是行为主体:“《诗经》中的‘我’作主语时只表示自称,但发展到《论语》时,已着重于对人自称,在他称与‘我’的对比中言‘我’,已重于相对于他称的存在而自称。”[13]这里的我和他者对立,不仅表示两个不同的物理主体,而且分属两个行为人。我是气质的行为主体。
对这种气质我,王阳明也继承了传统儒家的观念,不以为然。王阳明曰:“仆尝以为君子论事当先去其有我之私,一动于有我,则此心已陷于邪僻,虽所论尽合于理,既已亡其本矣。”[1]807一动于我便会产生私我、私欲,从而陷入偏斜而不明。王阳明曰:“此等苦心处,惟颜子便能识得,故曰‘于吾言无所不悦’。此正是大头脑处。区区举似内重,亦欲内重谦虚其心,宏大其量,去人我之见,绝意必之私,则此大头脑处,自将卓尔有见。”[1]197王阳明接受了佛教的观念,以为有“人见”和“我见”等偏执观念。其中的“我见”便是私我,“我见”即对私我的偏执。对于此类私我,王阳明也以无我来处理:“故区区专说致良知,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著实去致良知,便是诚意;著实致其良知而无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著实致良知则自无忘之病;无一毫意必固我则自无助之病:故说格致诚正则不必更说个忘助。”[1]83王阳明主张放弃对我的执着。王阳明曰:“诸君常要体此人心本是天然之理,精精明明,无纤介染着,只是一无我而已;胸中切不可有,有即傲也。古先圣人许多好处,也只是无我而已,无我自能谦。”[1]125天然之理的明朗意味着私我的断绝。对私我、肉身我、气质我等小我,王阳明不以为然。王阳明曰:“此固执事平日与人为善之素心,大公无我之盛节,顾浅陋卑劣,其将何以承之乎!”[1]1013无我之后才能实现大公,即,放弃对小我、私我的执着与追求,才能转而投身于公共事业中。这种公共事业便是大公。无我即大公。
所谓大公即指全体人,或曰“我们”。这也是阳明“我”概念的另一种内涵:我等同于我们或全人类。王阳明曰:“诸君只要常常怀个‘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毁谤,不管人荣辱,任他功夫有进有退,我只是这致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处,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动。”[1]101此处的我与其说是个体自称,毋宁说是我们或人类自称。我“致良知”完全可以被理解为我们“致良知”。王阳明曰:“天命于我谓之性,我得此性谓之德。今要尊我之德性,须是道问学。如要尊孝之德性,便须学问个孝;尊弟之德性,便须学问个弟。”[1]1168天命于我之我,完全可以作我们或人类,即天命于我们谓之性,天理在人类身上表现为性、人类得此德性便叫作德。我的德性其实是人类的德性。我即我们,泛指全人类。王阳明曰:“圣人只是顺其良知之发用,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何尝又有一物超于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碍?”[1]106“我良知”中的我完全可以当作我们的良知、人类的良知来理解。这里的良知,不是某个人的专有物,而是普遍的、人人皆有的本性。因此,良知不是说个人的良知,而是说我们的良知、人类的良知。我即我们或人类。对我的突出,不是对单个我的强调,而是对人类的推崇。这正是传统儒家的基本立场,即人类才是宇宙间最伟大的生命体。王阳明对“我”的歌颂,与其说是对自我的肯定,毋宁说是对人类的地位的高歌与宣扬。
结语:个体的缺席
笔者认为,王阳明是中国传统儒家哲学之集大成者,甚至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顶峰与终结者。阳明学的成就代表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贡献。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传统儒家关心的主题是天人之辩,即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问题。天人理论成为传统儒家思想的主要内容。孔夫子开辟了儒家人文主义思潮的方向,即用人文逐渐取代自然,最终以人取代天的主导性地位,人类及其所创造的文化才是宇宙万物的最终主宰者。这样,天人关系论由早期的“天主人从”论转变成为“人主天地”论。这便是明代王阳明的基本主张,同时也是传统儒家思想的最大贡献,即确立了人类在宇宙中的主宰者地位。人类作为宇宙万物的主宰者,不仅能够主宰万物的生生不息,而且能够主导自己的人生命运。换一句话说,人不必消极地听天由命,而应该主动地把握自己的命运,积极地应对生存。这种积极性与主动性便是传统儒家提供的智慧。
这种主动性也突出了人的主体性。主体性是主体存在的终极性质。对于主体及其性质的理解,往往有两个视域,即自然的人类、社会的成员。从天人观来看,人仅仅是宇宙一类,这便是人类。人的主体性表现为人类主体性。或者说,人类主体性指作为种类的人的主体性。它以人类为范围,而不涉及具体的个人。与此同时,人还是社会中的具体个人。因此,人的主体性还表现为个体主体性,即作为个体的人的主体性。这样,主体性便分为两类,即人类主体性和个体主体性。以王阳明为代表的传统儒家突出了人类在宇宙中的作用和地位,即人类不仅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而且也是宇宙万物生存的主宰。人不必消极等待苍天的安排,而应该积极应对生存。这种主动性便是王阳明对人类主体性的认识。也就是说,王阳明突出了人类主体性。
由于王阳明提出心做主、我做主等观点或说法,很容易让现代学者将其与现代哲学的自我、个体主体性等相混淆,以为王阳明主张自我论、弘扬个体主体性等。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在王阳明这里,心做主,表面上体现了主动性与主体性,但是实际上,真正能够做主的不是心,而是心里的普遍良知。这种普遍的良知等同于朱熹的普遍天理。也就是说,做主的心听命于绝对而普遍的天理。这个天理,不仅内在于心中,而且遍布于宇宙,因此是客观而普遍的绝对实体。对于每一个具体人而言,我们只能接受它的引导和规范,听从它的安排,却无法改变它。心听从良知或天理,从而使自己成为合理的心。这种普遍良知的崇拜表明,王阳明重视的是普遍的天理。王阳明虽然主张将天理内化于心中,成为心中的良知,但是,它终究还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我们所有人无一例外地接受它的安排。这里,王阳明突出的仅仅是普遍的天理、共同的人性。王阳明对人的主体性的恭颂也仅限于普遍的人性。这便是对人类主体性的高举和突出。这也是传统儒家的共同立场:弘扬人类主体性。
现代学者看到“我”字,便把它与自我相连,认为王阳明突出自我,在于人的个体主体性。事实并非如此。我不等于自我。在王阳明这里,我有两种内涵,其一,我即气质之我,因而有私欲;其二,我可以泛指我们。这个我们,不是现代汉语中的我们,而是通指我们人类。我即人类。这便是王阳明最关心的问题:人类在宇宙中的作用与地位。这也是包括王阳明在内的传统儒家最关心的问题。至于个体人,不仅王阳明,而且所有传统儒家,甚至是道家等,其实都无暇关注。他们很少思考个体人的地位等问题。既然无暇关注于个人问题,便谈不上个体主体性、自由、自我、尊严等与个体存在相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无疑也是人类生存的至关重要的问题之一。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解释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