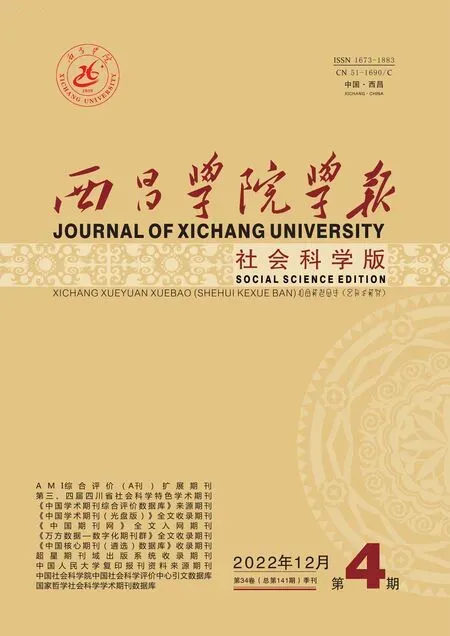以意义为中心的布鲁纳文化心理学研究
原军超,耿红叶
(西昌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四川西昌,615000)
杰罗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是美国著名教育心理学家和认知心理学家。20世纪50年代后期,布鲁纳提出以意义为中心的认知心理学体系,反对长期支配心理学领域的建立在人类行为的刺激-反应理论基础上的行为主义还原论,进而引领了心理学的认知革命。其核心观点在于认为认知的目的是发现并描述人类在与世界接触中所创造的意义,进而提出了关于意义生成过程的假设,并将理论视角关注到人类在构建与理解世界及其自身时所进行的象征性活动[1]。他认为意义由文化组成,日常意义的创造实践来源于已经存在的符号系统,扎根于文化和语言之中。文化不能被视为添加到自然上的东西,人类通过文化完整自身,人类本质上是文化的创造者。意义是心理学和人类学联结的纽带,此处所谓的意义并不是由先天的生物驱力决定,而是由文化决定,意义的建构深植于文化和语言中的符号系统,所以应倡导对文化与文化中意义的探索。如果将意义作为心理学的核心术语的话,那么心理学就需要加强和人文与社会科学相联合,所以在此已经种下了跨学科研究人类行为的种子,特别是强调心理学与人类学相结合,共同探讨意义生成的过程与机制[2]。出于对文化研究的兴趣,布鲁纳认为心理学和人类学应该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他对人类学的心理学转向中所采取的某些理论取向持怀疑态度,特别是以文化与人格学派所代表的当时人类学的主流理论。当解释人类学(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兴起之后,布鲁纳找到了双方学科对话的基础,进而促进了文化心理学的建立与发展。
一、文化心理学的诞生:心理学与人类学的跨学科整合
(一)心理学与人类学的早期交流
人类学诞生初期即与心理学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现代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模式建立的标志性事件是英国剑桥大学人类学家哈顿(A.C.Haddon)于1898-1899年带领团队远赴托列斯海峡(Torsestrait)对美拉尼西亚人(Melanesia)进行田野考察。当时参与团队的即有社会心理学家麦独孤(William Mc-Dougall)、实验心理学家迈尔斯(Charles S.Myers)、生理心理学家里弗斯(W.R.Rivers)以及对心理学和人类学都产生重要影响的塞利格曼(C.G.Seligman)。这次人类学考察以及塞利格曼对该地区土著部落的种族、文化与社会特质等方面进行分类所建立的田野工作模式,为后来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的田野工作奠定了基础。
在早期人类学家的培养中,心理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现代心理学的创始人德国心理学家冯特(Wilhelm Wundt)的学生中即有未来分别奠定英美人类学基础的马林诺夫斯基和博厄斯(Franz Boas),冯特本人晚期亦根据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结果建立了一套民族心理学体系(Volkerpsychologie)以对原始部落的思想、信仰和行为进行心理学解释。
(二)文化与人格学派的发展
20世纪20年代以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以及荣格的心理分析对英美人类学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马林诺夫斯基通过对特罗布里恩群岛的田野调查来挑战弗洛伊德理论中俄狄浦斯情结的普遍性,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通过对马努斯岛(Manus Island)新几内亚人的成长历程进行了一系列的田野调查来修正弗洛伊德的童年性理论。在这个时期心理学与人类学的交流过程中,已经开始孕育着人类学的解释倾向(interpretive),即关注与理解符号及其在意义创造中的作用,人类学开始采用心理学的结构与模式概念[3]。
格式塔心理学是早期结构主义的主要范例。人类学家爱德华·萨皮尔(Edward Sapir)、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和玛格丽特·米德都受到了格式塔理论的影响,认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他们从结构主义的心理学概念中衍生出文化模式概念,成为文化分析的有力工具,体现在《文化模式》和《菊与刀》等著作中。
人类学通过对人格的研究来理解个体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萨皮尔认为个体是文化的中心,对个体人格的研究是理解意义生成系统的手段。人格和文化共同具有动态性、结构性和系统性特征,随着不断重新诠释人格,与其相适应的文化结构也会相应发生变化[4]。萨皮尔关注的重点在于经验组织的模式和结构,受格式塔心理学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他曾在芝加哥大学开设了一门文化心理学课程,并于1931年加入耶鲁大学时开启了关于 “文化对人格影响” 的研讨会,来探讨文化的意义、文化与人格的心理关联以及人格差异和文化差异等问题。
在文化与人格学派的影响下,人类学越来越多地与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展开交流与合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20世纪30年代开始有越来越多逃离日益法西斯化的欧洲而移民美国的精神分析家参与到讨论之中,包括卡伦·霍尼(Karen Horney)、埃里克·弗洛姆(Erich Fromm)和埃里克·埃里克森(Eric Erikson)等。
人类学和精神病学的发展都受益于这一系列的跨学科对话。对于精神病学来说,人类学的视角使其不断重新定义何谓正常(normal),进而认为人格不是由一个普遍适应正常的过程所制约,而是根据出生和个体经历的偶然事件来适应尽可能多的观念模式和行为模式[5]。在人类学的影响下,霍尼和埃里克森等人开始关注文化背景的作用,并修正精神分析理论,形成精神分析的文化学派。对于人类学来说,精神病学提供了如何公正对待个体的视角,进而将个体不仅仅作为文化的代表,更是特定的被文化所塑造的思想的承载者。
(三)布鲁纳与文化心理学的建立
20世纪30年代中期布鲁纳在杜克大学本科阶段,即对文化的概念产生了兴趣,但认为当时人类学的文化概念与实验室中心理学研究的心理现象相脱节,所以选择在哈佛大学研究生院继续攻读实验心理学。他进一步接触到了人类学中文化与人格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并受到了人格心理学家阿尔伯特(Gordon Allport)的影响开始反思文化与人格的主流观点,认为主流的人格理论缺乏对于心智和意义形成过程的研究。早在美国的结构、认知和解释人类学出现前,布鲁纳就开始关注心智的进化与发展,并有意识地将发展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的结构主义和维果茨基(Lev Vygotsky)的心理发展观纳入参考的框架之中。布鲁纳认为这两位发展心理学家的区别在于,皮亚杰认识到了逻辑操作在人类心理活动中的基本作用,而维果茨基则看到了人类个体的智力与能力的发展受到文化和历史的影响[6]。
为了探讨文化语境对心智发展的影响,布鲁纳于20世纪60年代组织学生对非洲塞内加尔沃洛夫儿童和美国阿拉斯加州爱斯基摩儿童进行了一系列的认知研究,形成了《认知发展研究》这部颇具影响力的专著。同时其与迈克尔·科尔(Michael Cole)和约翰·盖伊(John Gay)对非洲利比亚克佩勒儿童的数学概念进行了认知研究,使心理学家更直接地与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进行合作以更好地理解学习和思维的文化背景[7]。布鲁纳和科尔的研究都意识到了语言和符号在认知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文化对思维和意义形成的影响。另外,解释人类学和近代文化理论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格尔兹以《文化的解释》《深度戏剧:巴厘岛斗鸡》开创了文化人类学的新局面,而《文化概念对人的概念的影响》和《文化的成长和思维的进化》两篇文章预示着人类学领域的文化心理学研究的开始。格尔兹在论述文化与思维的进化时借鉴了布鲁纳关于感知和反应中的情感选择性观点,认为人类行为需要来自情感象征模型的指导,这一情感象征模型主要包括对仪式、神话和艺术等文化的感知[8]。
布鲁纳和科尔的研究与格尔兹为代表的心理学导向的人类学家的认知研究相汇合,最终导致了文化心理学的诞生,并主要研究符号与意义在心智发展中的作用。
二、文化的认知意义:布鲁纳文化心理学的主要研究视角
布鲁纳的文化心理学强调文化行为体的活动和作用,进而关注文化形式在社会实践中的传播机制,并着重于文化对人类活动方式的调节作用,其文化心理学通过对叙事(narrative)在人类经验和行为中所发挥的中介作用的探讨,在关注经验(experience)的人类学与心理学之间搭建了一座沟通与理解的桥梁,将人类行为置于其所展开的叙事语境之中。
(一)文化与心智的叙事观
布鲁纳对人类学和心理学的重要贡献之一即是其所建立的文化和心智的叙事观,认为叙事不仅是意义建构的核心,而且是个体形成自我同一性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而认为现实是由叙事所建构的,应通过对叙事的观察来处理人类意图(intention)的变迁,而意图是人类理解和解释世界的主要思维方式,其概念本身在人类大脑中具有不可还原性特点[9]。布鲁纳通过设计一系列的人造图形运动实验来证明人类思维中的叙事倾向,即将图形视为彼此相连并以有意义的方式移动,实验中的被试通过语言描述将随机运动连接成有意义的动作与故事,表明可以通过意图来解释行为,进而布鲁纳从这些实验中的未编排的叙事转向话语叙事,以分析叙事思维的关键特征。
布鲁纳立足于建构主义视角建立文化心理学体系,其在对意义行为的研究中主要关注叙事与文化之间的联系,其认为心理科学应主要研究意义的概念及其建构过程,应将叙事作为理解人类认知的核心[10]。文化作为符号系统,为意义建构提供了场所,人类在符号构成的世界中公开与共享着意义。无论我们的话语多么模棱两可与多义,仍然可以将意义带入公共领域,进行讨论与阐释。因为文化世界的意义是公共而非私人的,文化为理解他人的意图提供了准则,并使解读他人的思想和多角度解读知识和价值观成为可能。
布鲁纳将文化比喻为戏剧,认为文化心理学应该主要关注民间心理与常识,文化领域的常识提供了关于人类社会如何运作的规范性描述[11]。常识的组织原则是叙事,而非概念或逻辑。叙事构成了故事的材料,所以讲故事与其说是一种传达意义的方式,不如说是一个意义创造的过程。叙事从生物学角度来看可以作为一种内在的心理能力,又是由历史和文化的特定叙事资源塑造的地方技能。在他看来,一个可行的文化必须有一套可用的解释性策略,这些策略在既定的信仰模式下可以为偏离规范的行为提供意义[12]。叙事在预期和反常之间建立了联系,故事提供了解释事物发展方向的视角。
布鲁纳对文化心理过程的研究受到了格尔兹的解释人类学的影响,但是又对人类学提出了挑战。他认为人类学家深描他人故事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故事,所以叙事是文化解释的核心[13]。例如格尔兹描述的那个发生在1912年摩洛哥的偷羊案件中当地人与法国当局之间的文化混乱与误解的戏剧性事件。格尔兹的深描方式既讲述了一个犹太商人科恩的悲惨故事,又将这一故事渲染成了一个黑暗的讽刺喜剧[14]。格尔兹所描述的故事是关于特殊文化类型的叙事,是人类学探索文化误读的叙事类型。人类学家的故事叙事本身亦是其所代表的文化世界的产物,叙事是解释的核心,并受当地文化的影响。叙事中的故事为自我的冲突和复杂动力提供了证据,并且记录了叙事中的感官经验。
在文化心理学的现象学方法中,叙事、认知和自我体验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相互影响着,文化被社会和历史所建构,叙事是人类主要的认知方式,个体是意义的创造者,日常经验建构了自我,借由心理理论来理解他人的自我,并根据对世界的信念采取行动[15]。文化心理学植根于日常生活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之中来探讨文化、认知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并关切那些界定和约束人类存在形式的文化实践。
(二)文化心理学的意义叙事
对文化心理学来说,在个体体验层面讨论文化就要关注意义及其形成、转化的具体表现形式,所以布鲁纳长期致力于调查文化和社会背景对个人学习和获得共同规则、价值观的影响。无论从布迪厄的习性(habitus)概念所包含的非命题和记忆形式来思考,还是从自传体记忆(Autobiographical Memory)中所表达的叙述性的过去经验痕迹来思考,个体记忆中既有对意义的追求,又有提供意义的文化资源。文化心理学通过叙事实践,在经验、记忆和社会行为的形成过程中探讨其中的文化作用与关联。布鲁纳认为集体记忆可以被安置在图式叙事模版之上,并通过图式来组织现实和历史被感知的框架,个人经验和叙事中的表达阐述了集体在时间序列上的运作方式[16]。动态、混合和多元化的文化观建立在分析实时互动的基础上,这种互动被证明是文化和个人意义的表达与转化的重要场所。
三、叙事与实践:布鲁纳的文化心理学的跨学科影响
布鲁纳的文化心理学思想不仅促进了心理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和理论化,也直接影响了教育、医学和法律领域的研究与实践。
(一)教育心理学与教育计划实施
布鲁纳对教育的影响颇为广泛。除《教育过程》(1960)《教育文化》(1996)影响教育心理学外,其参与和推动的教育计划持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学生与教师,例如其在美国学前儿童国家启智计划(The National Head Start Program)的形成与实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外,布鲁纳与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合作创建了人类研究课程(Man,A Course of Study,MACOS),将人类学引入小学教育之中,形成了一套全面的小学生科学教育方案[17]。该课程运用布鲁纳的螺旋式课程(Spiral Curriculum)模式,通过结合人类学、心理学和进化生物学的成果,形成为一套关于人类本性的课程体系。MACOS的主体概念是生命链条(the chain of life)或生命线(lifeline),包含生命的发展历史。课程首先从简单生物比如太平洋海岸鲑鱼开始,之后转向银鸥以引入养育的概念,接下来通过对狒狒的讨论来探讨社会性行为以及描述先天性行为和习得性行为的区别,最后通过对因纽特人及其与驯鹿和海豹之间关系的案例来研究人类[18]。该课程的重点在于,通过教学过程来学习特定的技能而非具体的知识,包括提出问题、讨论以及根据论点和论据形成结论的过程。
此外,布鲁纳关注到瑞吉欧·艾米里亚教育体系(Reggio Emilia Approach)重视儿童象征性语言和学前教育物理环境的创新,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儿童是有能力的学习者观点并,将发现学习理念融入学前教育,推动了瑞吉欧体系的建设和发展[19]。
(二)叙事与临床医学
布鲁纳将叙事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理念对临床医学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医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学者对于疾病和治疗叙事的田野调查中借鉴了他的工作,形成了叙事医学(Narrative Medicine)[20]。叙事医学关注患者讲述的个人故事,通过医护人员对疾病叙事更具同理心的理解和反思,可以最大限度缩短医护人员的专业知识和患者对疾病的主观体验之间的距离。另外,叙事医学可以帮助医护人员从不同角度理解疾病叙事,促进医护人员和患者之间的人际关系和相互理解,并在医护人员的同理心和理解的基础上,可以制定更有利于患者的医疗方案[21]。
在医疗保健领域,布鲁纳在医学教育的人本化(humanize medical education)尝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推动了生物医学领域的叙事伦理(narrative ethics)讨论,强调叙事在卫生保健工作中的中心地位,认为单个病人的病例只能在叙事的过程中出现,医生在倾听之中升起责任感,病人对病情的讲述以及引发的医生的感受与想法都是医疗叙事的重要维度[22]。医护人员可以通过表达道德问题上的经验来培养同理心,不仅可以提供有关道德决策的信息,也可以理解与思考个体叙事创造的道德推理方式。因此,叙事伦理在医疗保健中有着深远的意义。
(三)法律中的叙事实践
20世纪90年代,布鲁纳开始在纽约大学法学院任教,并举办文化与法律研讨班。研究美国法律实践后,他认为法律中充斥着讲故事,法律由包含一系列先例的故事的叙述模式组成。另外,客户给律师讲故事,而律师必须弄清楚他们听到的是什么,随着客户和律师的谈话,客户的故事在律师的行动过程思考下被重新塑造成关于困境与可能的叙事实践[23]。虽然法律程序的对抗性,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人们免受极端情况的影响,但是故事创造现实的力量远超三段论推理和统计的作用,所以需要进一步研究故事的真切性特点。布鲁纳通过对法律实践的研究来探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叙事和推理,试图重新确定叙事对推理的指导作用[24]。
布鲁纳在对纽约大学法律系的学生的教学过程中发现文化心理要素蕴含在律师的工作背景之中,其对法律的兴趣主要体现在考察叙事在法学和法律实践中的作用,认为法律实践中的讲故事是对智性空间(noetic space)的探索,这一类比思维模式是理论建构的基础。布鲁纳认为文化与心智是对文化的智性空间的运用,这一运用并非将图式强加于日常生活,而是一种持续进行中的想象实践。
四、启示与总结
基于对心理与文化的兴趣,布鲁纳从建构主义视角出发将文化重新纳入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其倡导的文化心理学的核心在于研究以目标为导向的、有意义的人类行为,特别是探讨文化在人类发展中的作用以及文化背景下的社会话语,其研究促进了人类学与心理学的融合。布鲁纳强调主观性和主体间性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广泛吸收人类学的民族志作为研究的方法论工具,从而可以深入分析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意义生成过程,并进一步阐述意义建构、共享和协商的机制。
布鲁纳的文化心理学研究心智的文化建构,其研究吸纳了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方法,以弥补实验心理学中生态效度之不足。另外,其强调认知的作用,以区别于以文化与人格学派为代表的心理人类学(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布鲁纳在心理学领域推动了质性研究方法论的发展,而在人类学领域则推动了认知人类学(Cognitive anthropology)的范式转变。
布鲁纳的文化心理学的研究视角对我国心理学的深入发展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应进一步促进心理学与其他学科的跨学科整合。冯特1879年在哲学和生理学的基础上建立的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标志着科学心理学的诞生,所以科学心理学本身即是跨学科整合的结果。从发展历程来看,心理学的每一次范式革命都是在吸纳了其他学科的最新研究基础上进行的自我更新。国务院学位委员会2021年印发《交叉学科设置与管理办法(试行)》,从政策层面促进跨学科的交流与发展。但从国内心理学的主流来看,跨学科整合更多地体现在心理学与理工类学科之间,缺乏吸纳人文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使得心理学成为了缺 “心” 的脑理学,限制了学科的全面发展。布鲁纳从认知心理学出发提出了意义的建构,在心智和文化之间架设了沟通与理解的桥梁,其研究不仅是研究视角的更新,亦是方法论的拓展,有利于将现象学的第一人称方法整合到心理学研究之中。布鲁纳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论,可资补充国内心理学理论与方法之不足。
其次,应大力加强心理学的经验研究。现象学影响下的人类学更多地关注主观经验问题,并从神经、感官、认知等多个角度探索文化意义的复杂性,其认识到文化的个人化过程中受到了个人的社会定位、特殊的生活历程、日常互动以及主观生活的影响。所以,文化变异、文化图式的作用以及共享文化形式的个体变化等成为研究主要关切的领域。现象学对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影响促进了意识领域的研究,形成了具身认知研究范式和神经现象学方法论。但是,国内的具身认知研究更为偏重心理学主流的第三人称方法论研究,缺乏对第一人称方法论的整合,即不重视对意识经验的主观描述的重要性。布鲁纳的研究方法论重视行动与行动中的个体的主观经验,对其研究将有利于国内心理学的方法论整合,促进心理学以经验为中心的研究领域的发展。
第三,应大力推动跨文化视野下的心理学研究。文化心理学是跨学科与跨方法论整合的结果,其强调人不仅是实验室中的个体,也是文化中的主体。跨文化比较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文化形塑了人的认知与情感,文化应是心理学的重要变量。目前国内文化心理学经历了传统文化心理学研究阶段、本土心理学研究阶段以及发展到现在的西方文化心理学的中国化阶段。国内的文化心理学还没有形成完善的中国理论,也没有形成影响力广泛的中国学派。布鲁纳将文化放在了心理学和人类学的交流之间,其视野启示国内心理学应该加强与人类学的沟通合作,在认知科学的框架内共同研究意识与经验问题,将心理学扎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
总之,布鲁纳所建构的文化心理学不仅研究人类的本性,也研究人类的存在方式。文化心理学通过观察人类高级心理功能的叙事性和规范性,为研究认知和行为提供了新的可能。各种形式的叙事是知识建构的文化工具,布鲁纳的跨学科思维方式推动了文化心理学与各学科结合,并且推动着社会实践,不仅体现在教育领域,也体现在其着力发展的法律领域,为理解文化与心智的关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布鲁纳对中国心理学界影响广泛,其多元方法论视角将为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的发展提供参考框架,为进一步推动心理学的 “中国理论” “中国学派” 的形成提供了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