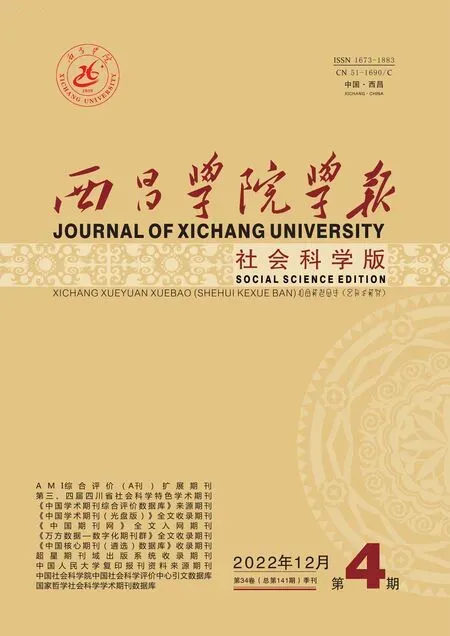《武定彝族婚姻礼俗诗》生态文化研究
令狐雅琪
(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四川成都 610000)
一、云南武定彝族及婚俗诗概况
云南省楚雄市武定县位于云贵高原西侧,云南滇中高原北部,东靠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南接富民、禄丰县,西临元谋县,北与四川省会理县隔江相望。该县有汉、彝、傈僳、苗、傣、哈尼等19个民族,少数民族众多,文化底蕴丰厚,其中彝族人口占其中少数民族人口的一半以上,保留有原始浓郁的彝族风情,被誉为 “迤东彝族文化之最高区”[1]。武定彝族擅长以口头歌谣对唱的形式记录和传递文化信息。在诸如婚礼、葬礼等重要场合,歌谣既是维系礼俗形式的手段、还是人与人情感沟通的桥梁。武定彝族婚姻礼俗诗是彝族人民的口头文学作品,在记录他们婚姻礼俗传统的同时,承载着彝族历史、宗教、生产、饮食、农耕等多方面的文化信息,不仅是彝族灿烂文化资源的体现,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集合,为今天研究古代彝族社会礼俗提供重要依据。
《彝族毕摩经籍经典译注》第二十八卷《武定彝族婚姻礼俗诗》收录了云南省武定县彝族人民口头即兴创作的婚俗诗歌作品,共计57首。这些口头诗歌最早见于武定县白鹿乡平地村的毕摩李茂森的手抄本,经李明泽、李茂森翻译整理,李继雄审定,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编印,2008年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基本包括了彝族纳苏人婚姻礼俗程序中必须吟咏的诗歌。《武定彝族婚姻礼俗诗》涉及彝族古代生活的方方面面,详细记载了古代彝族人民的婚娶习俗,包含有媒妁提亲,半路迎亲,棚内迎亲,送亲入棚,婚棚献酒,家堂献酒,屋门迎亲,赏牛飨牛,吃肝生、炒肉、牛肉、猪膀、羊膀,赏赉米饭、喝赏赉酒、赏飨马料、晒马鞍站、压地气、赏鸡看卦、招魂、锻铸银簪等。礼俗性质的歌谣在婚宴上以主客对答的形式展开,多为五言,记载详实,情感朴素真挚,带有彝族独特生活气息和乡土风情,隐含丰富生态文化内涵。
二、武定婚姻礼俗诗歌中的生态文化信息
1978年,美国学者威廉·鲁克尔曼在《文学与生态学:一次生态批评实践》中首次使用 “生态批评” 术语,提出了生态学理念与生态诗学的跨学科构想,将文学与生态学结合起来,从人文立场直面全球现代化进程下的地球生态破坏和人类精神生态危机。彻丽尔·格罗特费尔蒂、格伦·A.洛夫、劳伦斯·布伊尔等学者们,推动该理论形态趋于成熟,拥有坚实的生态哲学基础和广阔的学术视野,建构起较为完整开放的理论体系。经历了生态中心型和环境公正型两个阶段之后,进入生态中心主义与环境公正共融、多元文化互动共生的 “跨越性” 建构时期,发展成国际性多元文化绿色批评潮流[2]。作为以生存危机为驱动的文学批评范式,生态批评透过生态中心主义视野、多种族视野、性别视野,检视文学、文化与自然环境之关系,唤醒人之生态意识,认识到人类与所处环境命运与共的依存关系,探寻解决生态问题的文化和现实路径。1994年前后,中国学者一方面立足于全球化背景下的生态危机,对人类传统价值观念及审美思维进行反思;另一方面立足于国内美学界的学术瓶颈,希冀用生态学的整体性思维方式全面审视传统审美观念,走出美学理论研究的困境。他们正式提出了生态美学论题,开始了中国本土生态批评理论的构建。生态美学家曾繁仁先生受西方存在论哲学的影响颇深,以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 “此在与世界” “天地人神四方游戏” 存在论哲学观为理论基础,对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重新展开思考。曾繁仁以人处于 “在世界之中” ,与现实世界不可分割的原始生存状态为支点,系统论说了人与万物共生共在的生态存在美。他从 “人的存在” 这个根本问题出发对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重新展开思考,提出 “审美存在” 是人类生存的原初状态和人类生存的最高境界,并以人的 “审美存在” 为逻辑起点建立起生态存在论美学观,这一哲思破除了人与自然、主观与客观、身体与精神二分的机械对立,将人的价值、自然的价值和审美价值统一在一起,揭示出人的生态审美本性以及人与世界的生存性关联。本文主要从生态存在论美学理论及彝族传统生态哲学话语出发挖掘《武定彝族婚姻礼俗诗》中的生态文化信息,力图实现彝汉生态文明的沟通对话。
(一)生态存在论审美观
曾繁仁指出: “生态存在论美学观是适应生态文明时代要求提出的包含生态纬度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它是美学学科在当代的新发展、新延伸和新超越。标志着我国当代美学由认识论到生态存在论的转型。”[3]这一美学思想超越了传统认识论是一种人与世界 “主客二分” 的对立关系,打破了美与现实之间被人为割裂的存在关联,使美和审美突破传统认识论的静观推演,走向人与自然共存的现世世界。他强调审美是一种体验,是一种过程,指引人们从人类个体的生存性角度来看待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理解人与自然的一致性,将 “存在” 的范围由人本身扩展到 “人—自然—社会” 三位一体的整体系统中,指向人在自然和社会当下的生存状态,旨在阐明人不是抽象的存在物,而是切实存在于生活之中,一时一刻也离不开生态系统。作为自然生态环境中的存在者,人类与自然生态休戚与共,合和共生。《武定彝族婚姻礼俗诗》在讲述婚姻礼俗的过程中,包含着武定彝族人对自然生态的人文关注,透露出他们的生态审美观。笔者从武定彝族婚姻礼俗诗的内容和艺术形式两方面进行分析。
内容上以《路遥难行》一章为例。该章节在讲述送亲道路之艰辛的过程中,侧面反映古代武定彝族地区的原初自然环境与日常生活方式。送亲道路上 “不遇呀不遇,遇堵大悬崖。绕道崖头远,绕道崖脚远……不遇呀不遇,遇片大森林……钻来到林间,钻来到林边,钻来到林脚……不遇呀不遇,遇条大江河。绕河头路远,绕河尾路远”[3]103-104。直观记叙了武定彝区悬崖河谷众多、森林植被茂密的自然风貌,并投射出彝族人民身处自然,在生存体验中形成了主动适应环境的生态型生活方式,当送亲之路面临悬崖、森林、河水的阻隔时,他们并未选择破坏自然、战胜自然的方式以达到目的,而是尊重自然现象,守护生态环境,在有限的物质发展水平下与自然界和谐相处。人们在充分观察自然现象、把握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发挥聪明才智, “智者君大智,君使出智慧……银梯搭上崖,金梯崖头梭……剑梯搭上林,戟梯排林边……等待河水枯,等足时间后,河水枯干浅”[4]103-104,在原初自然环境下他们搭建梯子来绕崖绕林,把握河水涨落规律以见机过河。他们将人与自然放在同一平等位置,从人与自然实为生命共同体的角度来观照自然、体验自然,守护自然,饱含生态智慧,展现出武定彝族人民朴素的生态审美观念和生态文明取向。
艺术表现形式上同样投射出武定彝族人民的生态审美观念。典籍中的许多诗篇均采取由景及人的叙述方式,如《窥探真心》一章中缔结婚约双方家庭如何窥探彼此的真心时,先从自然生态着手,由景及人展开摹写。 “站在远处看,蜂飞似长云;来到近处看,蜂飞背花蜜。三对小蜜蜂,不采采花蜜,它们勤采花……山区窥什么,窥荞花黍花。什么花最美,黍花最美丽……坝区窥什么,窥谷花豆花。什么花最美,豆花最美丽……甥地窥什么,窥探公父心,窥探婆母心,窥探女婿心,窥得真心返”[4]399-400。
诗人表面上采用蜜蜂的观测视角,以蜜蜂的所见所闻为主线,由蜜蜂窥探山区黍花之美、坝区豆花之美引入窥探公婆女婿之真心,实际上观测主体是人自身。诗歌的审美主体实际上是人与动物的交叠重合,在人与蜜蜂的视域交互中打破主客二分的传统审美观,达成人与动物的平等和谐关系。诗人无形之中肯定了蜜蜂的审美眼光与审美智慧,他对蜜蜂采花的生存智慧,即主动选取真与美的采集对象由衷欣赏和敬佩,客观反映出动物窥探的真与美与武定彝族人民尊崇的真与美达成统一,具有内在一致性。《赞美婚礼》一章借用自然物象展开场面描写,烘托婚礼气氛: “屋前虫出洞,似小虫出洞;屋顶燕盘旋,似燕子盘旋;婚棚似仙境,所有客荣耀。”[4]352-353诗人采用暗喻的手法,用立夏时节雨后飞蚂蚁出洞飞舞的美感比喻婚宴气氛的活跃;用春燕在空中环绕盘旋来形容婚场歌声嘹亮,场面宏大。借自然界中动物充满生命力的场景来引发读者的联想和想象,具体生动地展现出婚宴的盛大和活跃。诗歌中暗喻喻体的选取展露出武定彝族人的生态审美倾向,诗人从真实的自然界中提取素材,将个体的生命感受、审美观念与自然相联结,创造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整体关联,相依相存的生态诗境。
(二)自然崇拜下的非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主张在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中将人类的利益放在首要地位,只有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价值评价的尺度始终掌握在人的手中,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一思想被生态批评家们看作生态失衡的罪恶之源,因此,生态批评特别强调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生态批评家们主张非人类中心主义,以生态整体性眼光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自然界与人一样具有内在价值,以维护生态整体利益来弱化人类的主体性地位,力求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平等的主体间性关系。
《武定彝族婚姻礼俗诗》中映射出了武定彝族人民的自然崇拜观,他们赋予动物神性、植物神性,将非人类自然物人格化、神圣化,赋予他们以主体性地位,突破了人与自然的主客体二元对立关系,消解了人类中心主义。典籍中多处展现出武定彝族人民的热爱自然、崇拜自然的思想观念。在《家堂献酒》一章中有赞美树木的记载: “三棵美树中,生一棵宝树。美者宝树美,宝树真俊俏。”[4]62在《拼箍马鞍》一章中马被赋予了神性: “银鞍箍好后,金鞍箍好后 ,不配其他马,抱鞍配仙马。”[4]415此外,在《赏牛礼仪》和《吃赏牛肉》等章节中森林、树木、悬崖等自然物也被神圣化, “森林头树神,树神知道我,树神看见我” , “崖间有崖神,崖神知道我”[4]131,作为神化的自然物崖神、林神和树神在武定彝族婚姻礼俗中扮演了于困境中点化民众、指引民众礼俗活动的重要角色: “阿基官员他,他不去别处,他去找树神,来到树神前,恭听树神话。树神告诉他,你去捉鸡赏,捉鸡充牛赏。”[4]131帮助人类促成婚礼宴席赏牛礼仪的顺利开展。
文本中的非人类中心主义还体现在人与自然生灵间关系平等,武定彝族视虎为祖先,自命为虎族。他们至今保留一道与虎同食的菜——肝生。《吃肝生歌》一章便追溯了肝生这一独特菜谱的来源。这道人虎同食的佳肴长久以来被保留在婚宴上,与礼俗仪式挂钩。文本采用人与虎对话的方式展开,表现出远古时期人与动物之间的亲密、平等关系, “阿乌老虎你,你要披毡吗,若你要披毡,披毡脱给你。阿乌老虎说,我住在林间,林不适披毡,我不要披毡……阿乌老虎你,你要手镯吗,若你要手镯,手镯脱给你。阿乌老虎说,我住在崖间,崖不适手镯,我不要手镯”[4]169-170。诗人采用拟人的手法,将老虎人格化,具有了人的思维和语言,拥有独立的主体意识,能够和人进行平等对话交流。文中 “阿乌老虎” 的 “阿乌” 一词注释解释为: “人名,死后则化为虎。”[4]170隐含了武定彝族人民思想观念中人与虎之间的亲缘性关系,反映出人与虎在彝族人民心目中处于在平等位置,他们打破人类中心主义,以生态整体主义的眼光,大胆抛弃人类独自发展的狭隘思想,追求人与自然生灵和谐共存的生态场域。关于人与动植物的亲缘性关系,文本中还有其他展现,《吃肝生歌》一章显示出有远古时期人与蛙的关系: “远古无人类,有人不像人,有人像青蛙。”[4]178青蛙外表虽普通,却因其内在智慧以及旺盛的生命力和繁殖力而进入彝人的审美观照视野。蛙还因其旺盛的繁殖力而形成动物崇拜的对象之一。据《勒俄特衣·雪子十二支》记载,天降三场红雪铸成十二种生物,分为无血的六种:草、柏杨树、杉树、水筋草、铁灯草、藤蔓,及有血的六种:蛙、蛇、鹰、熊、猴、人,其中青蛙居于有血的六种生物之首[4]71。在彝族《青蛙娶妻》《欧补娶妻》《天神的哑水》等民间故事中,青蛙也均以聪颖智慧的形象出现。人与蛙的亲密关联表现出武定彝族地区的生态人文意蕴。对蛙的认知,是彝族先民破除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生灵合和共生的表现。他们对蛙的崇拜感和敬畏感是借助宗教禁忌将个体生存与自然整体和谐交融,通过约束自身行为来维护生态平衡。文献中《搭建婚棚》一章展现出人体与树体的同一性: “不剖则不剖,剖开身腰部。剖身呀剖身,剖身有肉否,剖身没有肉。剖身有什么,剖身有树果,有两升树果。”[4]71文本中写到剖开人身,人体内部是自然界的树与果,直观反映出人体与自然界其他自然实体之间的生命性关联,人类的身躯实际上就是自然的身躯。体现出人与自然命运与共的存在关系,无形中打破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与生态批评的思想内核相交叠。
(三)生态整体的动态关联
生态批评家们将生命看作是人与自然万物共有的属性,从生命间的普遍联系来探索生态世界的活力,从生态整体性的角度来思考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仅作为生态整体的一部分,与自然界各生命实体合和共生,共同服务于生态系统的发展。袁鼎生先生的整生论美学关注到生态系统不可分割的整体性与系统共生性,他认为 “整体质是系统的最高规律,是各部分的关系共生的,整体价值是系统的最高目的,是各部分的价值共成的。整体中的各部分是平等的,相生互发的,并共同趋向与服从整体规范的”[6]。各生命实体以维护自然整体价值为目的共荣共生,在相生相长、相悖相克的矛盾运动中达到动态制衡,保障生态系统的稳定运转和不断上升。文本中《窥探真心》一章在凸现山区黍花的美丽、坝区豆花的美丽之余,不忘强调 “黍花虽美丽,结黍靠荞秆” ; “豆花最美丽,结豆靠谷秆,弯曲靠谷秆”[4]400。这是武定彝族人民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积累而成的生态哲学,即自然界中万事万物相互依存、不可分割,隐含着切实朴素的生态整体性思想。《吃肝生歌》一章也反映出自然整体的系统共生性及系统内部各部分的动态关联性。诗人描绘出相依相长、和谐美好的自然生态画卷, “推山叠陇山,山上则长树,山再高长草” , “推箐成深箐,深箐有河流,河中有鲸鱼,鲸鱼游河中”[4]177。山的高耸峻峭致使草木繁茂,树木丛生的山谷又利于积蓄水分,形成河流,河流又为鱼儿生存创造了条件。寥寥几笔便直观反映出了武定彝族地区立体性、整生性的生态圈层。生态系统内部逐位生发、环环相扣,在相依相长的良性互动中形成稳定发展的整体化动态结构。
据彝族古籍文献《西南彝志》《彝族源流》《宇宙人文论》,其文化元素中有 “三分” 世界的思想传统,彝族先民在远古时期将世界笼统概括为天、地、人的三部分,古籍中有关宇宙起源、人类诞生、万事万物演变规律等方面的记载均以天、地、人为原点生发而来。对这三部分关系的认识中能够反映出彝族先民质朴的生态文化思想。 “天与地吉祥,世间人吉祥,天地来保佑,来保佑人间” , “天地来到后,苍天生吉祥,苍天吉祥后,雨水降大地, “天与地相合。这样交合后,地上始文明”[4]177-178。《吃肝生歌》中交待了人类文明起始于天地人合的生态整体系统,反映出生态整体内部天、地、人三者的之间存在动态关联。他们认为,天与地之间能够依靠雨水获得沟通联络的途径。雨水能够勾连天地,从天上向地面传递福祉。武定彝族先民还关注到自然界中天与地的稳定与人类的生存发展之间的相通性,将天与地的安定看作人类吉祥平安的基础。而人类的和谐发展又反过来促进天与地的稳定运转。 “地没有天大,有人不吉祥。怎样才理好,天地才吉祥。大千世界中,有人人吉祥,人居地上吉,天与地吉祥。”[4]177在体验式的生命活动中,将人类存在与生态存在相融合。肯定自然的存在是人类发展的前提,而人类的发展落脚点是自然生态的和谐。他们秉持生态整体性的观念,认为只有天、地、人三部分真正和谐统一,才能实现生态整体的稳定运转,人类文明才有了生发的空间,体现出武定彝族人民心中的共生性生态审美范式。 “就人类存在的和谐状态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结构的相通性、双向互补性而言,生态系统若处于和谐状态,必然会带来人类和谐性的生存,而人类生存活动中对和谐自由的追寻更需要生态系统结构的和谐。”[6]彝族先民日常生存发展中与自然往来密切,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他们对自然界了解甚微,对自然神秘现象敬畏膜拜。加上人类生存发展的需求与生态系统稳定运行的需求趋于一致,因此人们形成了朴素的、不自觉的生态意识,从生态整体的视野把握人与世界的关系,将人类自身放在自然生态系统之中,作为生态循环过程的一节而存在。他们认识到自然生态整体内部的动态关联性,基于生态和谐和人类健康发展的一致目标来规范自身的行为,维护生态系统稳定。在生命的体验活动中认同自然的重要地位,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三、结语
《武定彝族婚姻礼俗诗》饱含丰富的生态文化信息,武定彝族婚姻礼俗中暗含着武定彝族地区人民良性健康的生态审美观念、生态生活范式,展现出人们超越时代局限的生态美学智慧。典籍在记述婚姻礼俗传统的同时,对自然生态环境展开充分的人文关注,将仁爱、平等的人文精神拓展到了自然领域。武定彝族人民善于发现自然生态之美,并在生态美的体验中以仁爱之心观照自然生态圈,在日常生活中保护林木、河流、山谷,主动守护自然环境,保护自然资源,形成朴素的、不自觉的可持续发展观念。在人的价值之外,武定彝族先民肯定了自然的价值,认识到自然界中的所有生灵都对维系人类生存发展及生态整体系统的运行意义重大,其价值具有不可替代性。随着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部分人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谋求经济发展,致使人类的绿色栖居生态家园面临严重危机。基于现状,人类要重新发现自然的魅力,实现自然的部分复魅。关于重新恢复怎样的 “魅” ,曾繁仁提出了三个层面:自然的神圣性、神秘性和潜在审美性[7]。人类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要合理摆正自身的位置,关注到自然秘密的不可穷尽性以及人在偌大的生态圈中的渺小性,感知到自然景象带给人类的美的感受,形成热爱自然、敬畏自然的思维方式。武定彝族先民生活在自然原生的生态环境之中,日常生产生活与自然界联系密切,对自然之魅的认识与彝族历史传统相勾连,孕育出独属于彝民族的生态文明。他们通过神化自然的方式确立自然的神圣性,彝族民间传统的树崇拜、水崇拜、山崇拜、蛙崇拜、虎崇拜等在《武定彝族婚姻礼俗诗》中均有所体现。人们提高非人类物种的地位,打破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实现了人与自然的相对平等。他们在生命体验中感知到自然之美,生动描摹武定彝族地区的山林、草木、飞鸟、鱼虫,将自然的生机活力展现出来,诗境中蕴含着人与自然相依相存、合和与共的审美关系,蕴含着人与自然的整体性关联。武定彝族婚俗诗展现出该地区人民的生态本源性,其中人体即树身、人与虎同源、人与蛙相似等观念都反映出人与自然界的一致性,人与自然生态相互交融。该地区人民还具有生态环链性。彝族古代宇宙观中以天、地、人来 “三分” 世界,如何把握三者之间关联性,如何看待人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成为他们在日常生命体验中不断思索的问题。他们从宏观视角来把握人与世界的关系,人类作为生态循环过程的重要一环而存在,与天、地共生共存。三者之间动态关联、须臾难分、处于同等地位,共同稳定平衡生态。所有生命存在于万物动态和谐的生态整体系统中的,人类离开了生态整体环链,也就离开了个体生存的土壤。彝族生态文化为全人类的生存性问题提供了深层次的思考维度。彝族先民打破人与自然的机械对立关系,确立了人与自然合和共生式的动态交互关系。在当代社会中,合理把握生命实体的关联,理解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促使我们认清人类个体在生态系统中的合理位置,形成人与自然合和共生的绿色生态观,进一步从维系自身生存发展的现实角度出发去保护自然生态环境。
——松滋礼俗——毛把烟、砂罐茶
——武定民族中学校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