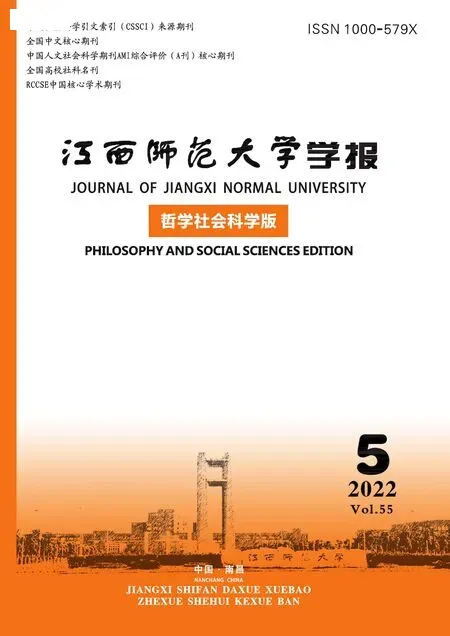美国平台公用事业管制的理论及其发展
高 薇
(北京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871)
引言
目前全球最大的科技公司控制着已经嵌入数十亿人生活的数字服务。科技大企业的垄断问题引起了全球关注。中国、美国和欧盟在近期都明显加强了对大平台的反垄断力度。而在反垄断的话语中,除主张利用竞争政策外,国际上不少学者提出还可以将大型数字企业定性为公用事业或公共承运人,采取一种类似传统上公用事业管制的方法去规制大企业的行为。这种观点开启了从平台影响公共利益角度研究垄断问题的新思路,也逐渐进入欧盟和我国学者的学术话语中。
人们在探讨公用事业在互联网行业的适用问题时首先寻求经验性的依据。研究者们往往聚焦于美国“进步主义时代”及公用事业管制在其后的发展。制度的诞生期形成了其理论内核和制度雏形,法律实用主义者的理论以及早先实践论证了现代国家和政府监管经济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基础,后续的发展时期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监管的现代版本和监管经验。本文将通过分析美国公用事业管制的历史和最新实践,说明公用事业式管制在规制数字大企业中的合理性。为此,本文首先简短回顾美国公用事业管制的历史源流并通过美国网络中立性原则的案例来说明公用事业管制的基本内容,接着通过美国平台反垄断领域的最新案件提炼出到目前为止的争论焦点,并进一步分析公用事业管制的基础即平台所具有的公共性,以此回应目前的争论。
一、公用事业理论的缘起
公用事业管制的核心逻辑是,受管制企业“影响大众利益”(affected with public interest),因而具有被管制的必要性。根据美国学者菲利普斯·索耶(Phillips Sawyer)的研究,在19世纪,人们普遍认为,合同自由和它赋予企业的灵活性确保了企业可以获得竞争性利润,这便符合了公共利益[1](p27)。而在1880年左右,具有市场力量的大公司的形成对这种信念提出了挑战。此后,政策制定者试图通过制定相关政策,一方面调和私有财产和合同自由的问题,另一方面回应竞争市场中的公共利益问题[1](p27-33)。沃尔顿·H·汉密尔顿(Walton H.Hamilton)在1930年指出,作为美国公用事业费率监管核心的“影响大众利益”的表述,起源于17世纪的英国法律,因为它出现在黑尔勋爵(Lord Hale)17世纪后半叶写就的手稿《港口论》中。这一概念是由英国法院在审理港口登陆码头的案件时提出的[2](p1092-1093)。汉密尔顿提供了这一17世纪英国法律术语被纳入19世纪美国法学的复杂而非线性的历史。是Munn v.Illinois案的判决开始了美国对“影响大众利益”的纳入,该判决是美国公用事业管制出现的一个里程碑式的判决(1)Munn v.Illinois,94 U.S.113(1876).。在这一判决中,美国最高法院认为,储存谷物的活动一旦具有“公共用途”层面,就不再是私人活动。应该指出的是,首席大法官怀特特别使用了一个原创性的术语——“商业门户”(the gateway of commerce),并以此对一项商业活动的性质进行判断(2)Munn v.Illinois,94 U.S.113(1876).。从那时起,政府可以凭借其警察权有效地规范价格。同样的推理后来被美国最高法院用来支持铁路费率管制的合法性(3)Chicago,M.& St.P.Ry.Co.v.Minnesota,134 U.S.418(1890).。
谈及美国公用事业管制的起源,就不能不提美国“进步主义时代”(4)美国进步主义时代(progressive era)一般指1890年至1920年这段时期,即南北战争到“新经济”时期。,这一直被认为是奠定了现代美国基础的时代。在这一美国社会与经济发生巨变的转型时期发展起来的公共服务企业制度和现代公用事业理念被认为是该时代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最直接地颠覆了当时美国社会既有平衡的是大企业的崛起。社会转型、大企业的兼并浪潮催生了反垄断立法,也同时导致了全国性的对公用事业管制的浪潮。但后者对美国企业控制的深远影响更甚于同时代发展起来的、也同样重要的反垄断政策。崭新的“公用事业”(Public utility)和“公共服务”(Public service)理念将经济正义和社会改革带入了20世纪美国。
美国早期的管制集中在铁路以及诸如电力、电话和城市运输等公用事业部门,随后发展到能源、通信领域。在行业划分上,美国司法实践中没有明确的指引标准。正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34年的Nebbia v.New York案中承认的,不存在一个界定这类行业的封闭标准(5)Nebbia v.New York,291 U.S.502(1934).。美国进步主义时代涉及的行业包括城市交通、铁路、机动巴士和卡车、无线电、仓储、银行、保险、牛奶、燃料和包装[3](p175)。而在当代,主要有四种基础性行业被指定为“公共服务”:远程通信业、银行业、能源供给业及交通运输业。由于这些行业在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政府必须对其作出相关调控[4](p45-46)。
当我们重新回顾美国进步主义时代公用事业思想的发展脉络,会发现在当时学者和实践者的公共利益和公用事业模型下,不公平的负担、压迫、不合理定价或有害的服务标准,所有这些均具有规制的正当性。以这种方式,公用事业管制也就超出了垄断范畴〔无论自然垄断(铁路、电话)或非自然垄断〕,并包含了许多需要法律施加必须合理服务大众义务的经济活动。商业活动也不必满足严格意义上的垄断标准。准入(access)、充足的服务和供应、合理价格、非歧视,所有公用事业法中的这些要求产生了新的、广泛的、一般概念上的政府义务,即政府是为公共福利目标去进行规制。美国现代行政法先驱,弗兰克·约翰逊·古德诺(Frank Johnson Goodnow)指出,规制企业的正当性就在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即这些事业建立在一种特权(privilege)之上,而企业并不理所当然地享有那种特权[3](p159-160)。在美国进步主义时代,铁路被认为是一种创新(正是铁路问题孕育了现代公用事业管制理念),正如互联网于我们的时代,但没有一种创新是可以以违反公共物品使用的方式发展的。
考察美国公用事业发展历史的目的在于重启一种话语,并将其与当前实践相联系。在对平台的监管中我们不必机械地适用之前的或某种现行做法,因为对不同行业进行监管必须考虑到行业特性和当时的社会背景,而共识的起点是,承认大平台的活动影响大众利益,因而存在管制的必要性。这个意义上,在下一步的讨论中继续纠缠于平台是否属于传统规制中的“公用事业”概念或类似实体,意义已经不大,因为我们首先必须更新对管制对象和经济环境的认识,必须以全新的角度去认识数字时代的大企业。而无论支持规制还是支持采取公用事业方式对互联网平台进行规制的人,都无法简单将平台装进原有公用事业监管的框架之内,而是已经开始在规范层面建立崭新的公用事业管制框架。美国对网络服务提供商(ISP)和金融业监管的案例为我们提供了两种可借鉴的监管路径,即或制定新的法律实现新公用事业式管制,或者通过一系列法律实现一种事实上的公用事业监管。事实上,伴随各国反垄断的深入、各种立法建议的出台、学者们的共同探讨,公用事业理念在平台规制中的具体适用框架也日渐清晰。这些我们都将在下文中看到。
二、网络中立性原则的实现及其经验
与近百年发展起来的反垄断法不同,公用事业管制遵循了另一种叙事。对私人商业行为进行管制的历史可追溯至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和教会的“公平价格”理念、欧洲中世纪中期行会组织的运行、法国16世纪发展起来的特定商业排他性垄断权以及英国有关管制的普通法传统[5](Chapter 3)。现代意义上的公用事业多属于国家基础建设行业,紧密联系并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具有基础性和公共性、一定的私人性、正的网络外部性和规模经济等特征。政府一般对这类行业进行较为严格的价格和准入等方面的规制。对公用事业部门进行规制是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一定程度上体现着社会公平,起到收入再分配的作用[6](p8-9)。
我国公用事业的形成与一般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国家不同,为政府主导式,最初以国有企业的形式直接经营[6](p44)。近年来,我国也在探索公用事业的市场化改革、监管与竞争政策问题的解决方案。由于我国在公用事业监管上与西方传统不同,发展也较晚,仍有若干问题需要解决,在互联网领域中国学者的研究进路并不是由传统公用事业规制扩展至互联网企业。本人在近期发表的系列文章中从公用事业这一新角度提出了国内研究平台垄断问题的新思路(6)参见高薇.平台监管公用事业理论的话语展开[J].比较法研究,2022(4):171-185;高薇.平台监管的新公用事业理论[J].法学研究,2021(3):84-100;高薇.互联网时代的公共承运人规制[J].政法论坛,2016(4):83-95;Gao W,Yang Y.Chaining cyber-titans to neutrality:An updated common carrier approach to regulate Platform Service Providers[J].Computer Law & Security Review,2015(3):412-421;Gao W.The perils of making new media the philosopher king:A Case Study from Tencent’s Weixin[J].Peking University Law Journal,2016(2):267-289.。美国学者在提出网络社会的公用事业规制时往往追溯至公用事业的诞生时期,并从传统管制理念和手段中汲取启示。
美国进步主义时代的公用事业理念和对私人权力的控制理念在互联网时代的复兴首先起始于“网络中立性”(net neutrality)原则的发展。网络中立性原则2003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吴修铭(Tim Wu)提出,核心在于防止ISP歧视建立在宽带服务之上的应用、网站或内容,即要求ISP必须同等对待来自各方的所有内容。由于ISP连接用户及内容提供商(edge providers),如Google、YouTube,它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屏蔽对手的应用程序(阻止)、令竞争对手的网站速度变慢,还可以为那些出价高的网站提供更快的速度(优先付费)并在这些过程中寻租。而它们所要做的仅仅是在网站上公布自己的政策或者告知监管机构。这里我们看到了私人权力威胁公共利益的现代版本。
网络中立性原则的提出在观念和学术上复兴和革新了公用事业理念,但美国真正将其付诸实施,利用《1996年电信法》(Telecommunications Act of 1996)第二章中的“公共承运人”(common carrier)规定监管ISP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在20世纪早期,美国公共承运人规制适用于电话和通信服务,并最终被制定在《1934年通讯法案》(Communications Act of 1934)中。这一法案针对当时市场上的不同通讯服务,区分了私有运营商与公共承运人,后者主要针对电话和电报等为“公众的利益和需求”服务的通讯行业。1934年法案要求“公共承运人”为所有用户提供无差别的服务。同时,法案授权建立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旨在对美国国内所有的通讯手段进行监管。《1996年电信法》根据1980年以来的实践,对《1934年通讯法案》进行了重大修正并作出了一个重要区分,即将依赖于网络提供的服务规定在1996年法案的第一章,将基于电话网络传输的业务(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仍划分为第二章的“公共承运人”。
在2000年以前,与电话服务相比,宽带服务仍然属于奢侈品而非生活必需品,因此FCC将ISP定义为宽带服务而非通信服务,使其不受“电信法”第二章规制。但由于美国的宽带最早是由电话公司铺设,互联网宽带服务也就具有基础设施的特性。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接入互联网逐渐成为一项基本权利。2010年,FCC发布了《开放互联网命令》(Open Internet Order),确立“禁止屏蔽、禁止流量调控、禁止付费优先”三大基本原则,提出一系列预防措施,旨在防止私人宽带提供商和ISP不正当地滥用其控制的互联网基础设施。虽然FCC并未明确援引《1996年电信法》第二章之规定或公用事业规制,但其主张代表了公用事业理念的现代版本:要求互联网管理的透明性,禁止限制用户接入内容提供商和内容的阻止行为或禁止歧视某一用户或内容。
当FCC开始对互联网运营商进行监管时,大型网络运营商以法律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为由拒绝承认FCC的管辖权。美国第四大网络运营商Verizon在2011年向华盛顿特区联邦法院提起针对FCC的诉讼,声称FCC对互联网运营商的监管超出了法律赋予的权力,并在一审败诉后上诉。2014年华盛顿特区上诉法庭作出判决,支持了Verizon的主张,承认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FCC没有权力要求运营商执行网络中立性原则。但法庭认可公开互联网的原则并明确向FCC指出,可以通过将互联网的属性从“信息服务”变更为“公共承运人”并将其纳入监管范围。作为对此的修正,FCC于2015年3月12日发布新的《开放互联网法令》(Open Internet Order),将互联网宽带归类为公共承运人,正式为网络中立性原则赋予法律效力。与2010年法令相似的是,FCC吸收了公用事业的原则,但并未要求实施全套的公用事业监管措施。2015年法令尽量避免一种“全是或全非”(all or nothing)的监管策略,将ISP排除在一些《1996年电信法》第二章规定的严格限制及传统价格管制之外,而是采取了更为务实的措施来限制私人权力、保障平等接入的公共利益。具体手段包括:
1.将《开放互联网法令》作为“防火墙式”方法,认为互联网架构作为公共品应当被整合而非拆分,但必须对所有人公开;2.法令对企业施加了公共义务,如非歧视及平等接入义务,针对屏蔽、减速或优先促进数据流动的活动。FCC的监管将确保这些义务的实现;3.美国的一些城市如田纳西州的加查塔努市(Chattanooga)开始以特许公用事业(chartered utility)的形式为大众提供价格低廉、高速的宽带服务。这种政策一开始被美国最大的互联网服务供应商Comcast Corporation诉诸法院,使田纳西州立法禁止当地政府提供宽带服务。但FCC在其裁决中引用电信法推翻了田纳西州及北卡罗来纳州的一项类似法律,指责这些法律对ISP的保护主义做法。FCC的命令和互联网公开法令,实际上开辟了当地政府提供公共宽带服务的领域[7](p1651-1654)。
一国网络中立性规则的确立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一般而言,监管机构会在自身的权限范围内,综合衡量电信和互联网两大产业的发展情况、对创新的影响、双方利益的博弈等因素,以互联网开放和创新为目标,出台符合电信和互联网行业发展利益的适度的网络中立性规则。美国能够确立网络中立性原则与行业监管机构的执法经验和能力有着密切关系。FCC丰富的监管经验使其面对大型电信运营商仍然可以采取强硬态度,其监管方式和具体措施为发展出更为一般性的现代公用事业框架提供了诸多借鉴,避免了20世纪早期公用事业管制中的问题,这体现为:
首先,监管机构认识到,由巨大的私人权力控制互联网这种基础设施存在问题并决定采取行动。这包括认识到私人企业有动机和能力利用其地位去获取私利、对公共利益带来危害,认识到市场机制不足以阻止这种危害,而利用规制工具能够实现一种在服务于公共利益目标和普遍进入与竞争之间的平衡。这些表现出和“进步主义时代”改革者同样的关切。
其次,FCC的政策说明,对互联网产业并不要求适用所有传统公用事业的规制,包括价格管制、公共承运人或国有化,而是要根据产业特点重新设计规制框架并适用于现代经济管制,这清晰地表现在聚焦于市场结构、设置防火墙、施加公共义务和通过公共机构提供服务。这些措施同样可以用于对平台监管政策的讨论。
再次,对产业进行监管的主体是FCC而非法院,通过利用其专业性、广泛的政策制定裁量权来创造出一个灵活而具有适应性的管理体制。这种体制与美国早期的公用事业理论和公共承运人法律框架的重要不同在于,早期做法过度依赖于非专业化的司法执行和模糊不清的理论测试。同样重要的是,这种管制并不是在抑制创新和经济增长,而是有效地重组宽带资源和市场,阻止ISP自己通过控制数据通道寻租。
最后,在规范层面,美国的公用事业制度还为我们提供了两种可供借鉴的路径:或制定新的法律实现公用事业式管制,或者通过一系列法律实现一种事实上的公用事业监管。网络中立性原则起源于公用事业式监管的既定法律框架。美国《1996年电信法》第二章根植于美国进步主义时代的公用事业精神,基本上可以直接恢复并更新其愿景。而美国金融业作为另一种类型的法律和政策环境代表了一种“事实上”的公用事业模型:没有任何一部法规或有关监管机构等同于电信法第二章或作为监管机构的FCC来负责发展和实施公用事业管制的理念。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人们迫切地关注如何防范金融恐慌,如何管理大型金融公司的崛起以及如何确保金融为公众和社会服务而不是变得过于剥削或引发风险。在网络中立性原则下,公用事业原则以隔离为核心,要求将互联网的基本数据传输功能与其他功能分离。而在金融业中,储蓄、中介和贷款等基本服务的筹资活动也会受到来自其他私人活动的损害。因此并不令人惊奇的是,美国有关金融改革的许多学术文献和政策辩论都涉及应用公用事业概念时引发的关于防火墙、公共义务和公共选择的相同策略讨论[7](p1657-1668)。
围绕ISP和网络中立性原则的争论远未结束。美国网络中立性原则由2014年奥巴马政府支持和确立,2017年在特朗普执政后被废除,美国民主党2019年4月11日在美国参议院引入《拯救互联网法案2019》(Save the Internet Act of 2019),试图恢复网络中立性原则(7)“H.R.1644-Save the Internet Act of 2019”,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6th-congress/house-bill/1644,accessed on 16 March 2022.根据官网,自美国参议院“二读”(read the second time)后,目前没有下一步进展。。2015 年11 月,《欧盟关于开放互联网访问的措施与修订关于与电子通信网络和服务有关的普遍服务和用户权利的指令 2002/22/EC 和条例(EU)No 531/2012 关于在联盟内的公共移动通信网络上漫游的规则》的出台标志着欧盟正式确立了关于网络中立性原则的一般规则(8)英文名称为:“Regulation(EU)2015/2120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5 November 2015 laying down measures concerning open internet access and amending Directive 2002/22/EC on universal service and users’ rights relating to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and services and Regulation(EU)No 531/2012 on roaming on public mobile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within the Union)”。值得注意的是,此项法规于2020年作了修订,最新版本为《欧盟关于2015年11月25日颁布的有关开放互联网接入和受监管的欧盟内部通信零售费用的措施(EU)2015/2120条例与修订指令2002/22/EC和条例(EU)No 531 /2012》(Regulation(EU)2015/2120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5 November 2015 laying down measures concerning open internet access and retail charges for regulated intra-EU communications and amending Directive 2002/22/EC and Regulation(EU)No 531/2012)。。时隔不到一年,欧盟电信监管委员会出台欧盟网络中立性规则实施指南,进一步推进网络中立性规则的落实,这给欧盟电信和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而与此同时,未来已经到来,人们在过去十年中已经开始探讨如何在平台层面贯彻公用事业管制的理念。曾经主张要求ISP给予它们平等对待的互联网平台,也被发现正在利用其越来越大的权力实施各种损害竞争和用户的行为。目前,平台垄断及其危害逐渐成为一个必须被认识的事实。主张平台具有公共性并将其作为公用事业予以规制及批判美国既有的互联网产业政策(包括反思反垄断法)的文献在近十年有了明显的增长,且随着平台的发展和壮大,讨论已经逐渐延伸至不同类型的平台和问题的不同方面,也同时涉及美国的四大互联网企业,即Google、Twitter、Amazon和Facebook。一场大讨论的序幕早已拉开。
三、平台公用事业管制的近期实践
较早对公用事业适用于平台问题予以探讨的领域是搜索引擎和社交媒体,并扩展到电商平台、网约车平台。社交媒体和搜索引擎较为明显地符合公用事业的特点,具有明显的规模效应,易形成集中化的垄断平台,控制信息入口,造成下游用户严重依赖平台。美国近期的两个案件即有关Twitter和Google,再次引发了关于平台公用事业式管制的热烈探讨。
(一)Twitter用户诉特朗普案
第一个案件围绕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个人Twitter账户是否属于一种“公共论坛”(public forum)展开。该案源于2017年,7名被特朗普屏蔽了Twitter账户的个人请求哥伦比亚大学奈特第一修正案研究所(Knight First Amendment Institute)作为代表向法院提起诉讼,起诉特朗普在Twitter上屏蔽那些对他持批评意见的人。初审法院和上诉法院均支持了原告的诉求。美国最高法院撤销了判决,并将案件发回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以下简称“第二巡回法院”)。在判决中,美国最高法院指示第二巡回法院,由于总统已经更换,应将案件以争议不再具有可审理性为由予以撤销(9)Biden v.Knight First Amendment,No.20-197(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这个案件引起了两方面讨论。第一个问题是有关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是否适用于总统利用其Twitter账号屏蔽用户。第二巡回法院认为,历史评论是一个“公共论坛”,时任总统特朗普利用其对Twitter账户的控制权阻止原告访问评论的历史记录,违反了第一修正案(10)Biden v.Knight First Amendment,No.20-197(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但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大法官指出,第二巡回法院关于特朗普的Twitter账户是一个公共论坛的结论,与我们经常描述的公共论坛是“政府控制的空间”等内容相矛盾。表面上看特朗普的Twitter活动在某些方面类似于公共论坛,但真正有权力控制账户的是Twitter。特朗普对该账户行使的任何控制权,与Twitter公司服务条款中规定的“在任何时候以任何理由或无理由”删除该账户的权力相比,都显得微不足道。恰恰是Twitter行使了它的权力。由于账户的无限制控制权掌握在私人手中,第一修正案的原则可能不适用于用户对于特朗普扼杀言论的投诉。原则上,私人企业不受第一修正案的限制(11)Biden v.Knight First Amendment,No.20-197(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一些评论人支持 “数字公共广场”(digital public square)的概念,指出越来越多的公职人员和政府机构现在都使用社交媒体与公众进行交流。例如,纽约民主党众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使用她的Twitter账户征求选民对她的立法议程的意见。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将其 Twitter 帐户用于分享“每日可靠的健康提示与安全更新”。又如,佛罗里达州的应急管理部门使用其帐户向居民发出飓风警告,并通知他们有关紧急救援的信息(12)Jameel Jaffer,Katie Fallow,“Official Censorship Should Have No Place in the Digital Public Square”(Knight First Amendment Institute at Columbia University,7 April 2021),https://knightcolumbia.org/blog/official-censorship-should-have-no-place-in-the-digital-public-square,accessed on 10 January 2022;See also Adam Klasfeld,“Second Circuit Pries Open Trump Twitter to Public”(Courthouse News Service,9 July 2019),https://www.courthousenews.com/second-circuit-pries-open-trump-Twitter-to-public/,accessed on 10 January 2022.。有观点认为,当官员和机构以上述这些方式使用社交媒体平台时,他们创造了一种新的、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空间(13)Adam Klasfeld,“Second Circuit Pries Open Trump Twitter to Public”(Courthouse News Service,9 July 2019),https://www.courthousenews.com/second-circuit-pries-open-trump-Twitter-to-public/,accessed on 10 February 2022.。 他们的账户可以是官方信息的来源,公民可以通过其交流信息和想法,这就使私人账号转变为了具有公共性质的论坛。
该案涉及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限制大企业的规制权。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可能并不适用于解决这一问题,而公共承运人规制可以使政府限制企业排除个人的权力。托马斯大法官提出,最终不是特朗普屏蔽了用户,而是Twitter,且Twitter可以屏蔽一切账户,包括总统的。在美国国会骚乱(14)2021年1月6日,特朗普在2020年12月14日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竞选失利后,其支持者冲击国会,国会山遭遇暴力事件。2021年1月8日,Facebook宣布将特朗普账号全部封禁。之后,几乎所有主要平台,包括Facebook、YouTube和Twitter都封禁了时任总统特朗普的账号,大多数都引用了其服务条款。如何控制企业的这种禁止权是个问题。托马斯大法官指出,今天的数字平台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量言论,包括政府行为者的言论提供了发表途径。然而,同样史无前例的是,如此多的言论被集中控制在少数私人手中。我们很快将别无选择,只能对我们的法律理论如何适用于高度集中的、私人拥有的信息基础设施(如数字平台)进行调整。托马斯大法官将大型数字社交媒体平台与公共承运人和公共通讯事业进行了类比,他认为这种集中和垄断可以使平台控制社会话语。而即使数字平台并不完全符合公共承运人的定义,立法机构仍可以将数字平台视为公共场所(public accommodation)予以管制(15)Biden v.Knight First Amendment,No.20-197(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二)俄亥俄州诉Google案
第二个案件有关Google。该案可分为两个阶段。首先,2020年12月,俄亥俄州总检察长戴夫·约斯特(Dave Yost)加入了由其他 37 位总检察长组成的两党联盟,起诉 Google违反《谢尔曼法》第2条(16)“Attorney General Dave Yost Joins Lawsuit Seeking to End Google’s Illegal Monopoly”(Ohio Attorney General Office,17 December 2020),https://www.ohioattorneygeneral.gov/Media/News-Releases/December-2020/Attorney-General-Dave-Yost-Joins-Lawsuit-Seeking-t,accessed on 5 January 2022.。各州指控Google通过一系列反竞争性的排他性合同和行为,维持其对通用搜索引擎和相关广告市场的垄断权。
起诉书中提出的论点主要有三项:第一,Google使用排他性协议和通过其他做法来限制竞争对手的通用搜索引擎和潜在竞争对手接触消费者的能力。这种行为巩固了Google作为计算机和移动设备上的首选搜索引擎的地位。第二,Google歧视专门的搜索网站(例如提供旅行、家庭维修或娱乐服务的网站),剥夺它们在搜索结果屏幕上被用户访问主页网站的权利,因为这些竞争网站威胁到Google的收入和主导地位。第三,Google的搜索广告管理工具SA360不断偏向自有平台上的广告,违背其关于搜索广告服务的中立性承诺,以损害广告商和消费者利益的方式增加收入(17)State of Colorado et al v.Google LLC,1:2020cv03715,p7-8.。
从2020年12月开始,各州开始提交自己的证据与陈述,并经历了多轮证据交换、证人出庭(18)See case file of State of Colorado et al v.Google LLC,https://dockets.justia.com/docket/district-of-columbia/dcdce/1:2020cv03715/225161,accessed on 17 January 2022.。该案于2021年2月与United States v.Google LLC一案合并(19)“Order concerning Amended Scheduling and Case Management Order”,https://www.justice.gov/atr/case-document/file/1428316/download,accessed on 17 January 2022.,在同年2月23日至8月27日间又进行了多次证据交换(20)See case file of U.S.and Plaintiff States v.Google LLC,https://www.justice.gov/atr/case/us-and-plaintiff-states-v-google-llc,accessed on 17 January 2022.。此案目前仍在审理过程中。
与此同时,俄亥俄州于2021年6月单独对Google提起了诉讼。俄亥俄州检察长提出的两个主要诉讼请求为:第一,寻求法律声明,表明Google是一家受政府适当监管的公共承运人(或公用事业公司)。第二,Google有责任以非歧视的方式呈现来自其他渠道的内容,这意味着它不应优先在搜索结果页面上放置自己的产品、服务和网站。这些平等权利应扩展到广告、增强功能、知识框、集成的专业搜索、直接答案和其他功能。俄亥俄州的此项诉讼不寻求金钱赔偿(21)State of Ohio v.Google,No.21 CV H 06 0274(Common pleas court of Delaware County,Ohio civil division),Complaint for Declaratory Judgment and Injunctive Relief.。
Google在2021年8月13日提交了一份动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并列举了三项理由。第一,“Google Search”不是俄亥俄州法律规定的公共承运人,也不是受雇将内容从一个人那里“搬运”到另一个人的网页上。第二,Google搜索不是俄亥俄州法律规定的公用事业。Google认为,“Google Search”不是一种公共服务,也不属于与公共利益相关或者属于“公众关注”类型的服务。第三,俄亥俄州和美国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障,从本质上禁止俄亥俄州试图管制“Google Search”如何回应用户的查询行为。Google认为,其为回应用户的查询而发布、显示的信息以及它呈现该信息的方式是受第一修正案保护的。另外,根据宪法规定,俄亥俄州是被禁止使用公用事业法或公共承运人法来管制受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言论的(22)State of Ohio v.Google,No.21 CV H 06 0274(Common pleas court of Delaware County,Ohio civil division),Motion of Defendant Google LLC to Dismiss Plaintiff the State of Ohio’s Complaint.。2022年5月24日,法院裁定支持Google动议中涉及公用事业的主张,驳回Google涉及公共承运人的主张,言论自由的问题由于证据不足暂且搁置(23)State of Ohio v.Google,No.21 CV H 06 0274(Common pleas court of Delaware County,Ohio civil division),Opinion and Order Granting in Part and Denying in Part Defendant’s Motion to Dismiss.。
由此,俄亥俄州的案件再度引发了平台究竟是不是公用事业或公共承运人的热烈讨论。虽然拜登政府和国会目前更倾向于以反垄断法为导向的方法来对抗大型科技公司日益膨胀的权力,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在思考反垄断方法的缺陷(24)Michelle P.Scott,“Google:A Public Utility?”(Investopedia,13 March 2022),https://www.investopedia.com/google-a-public-utility-5191176,accessed on 5 January 2022.。戴夫·约斯特发表在《纽约时报》的评论文章称,将Google作为公用事业可以使Google更加关注公共利益,不但可以为所有用户提供更公平的搜索服务,也给予所有信息提供商更平等的机会,同时更好地促进市场竞争(25)Dave Yost,“Let’s Make Google a Public Good”(The New York Times,7 July 2021),https://www.nytimes.com/2021/07/07/opinion/google-utility-antitrust-technology.html,accessed on 17 January 2022.。《华尔街日报》提到 Google通过算法改变了人们的搜索结果,从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用户的选择。同时,Google已经成为世界上访问量最大的网站、已占领全球搜索引擎90%市场份额,这种影响力无疑是巨大的。在这种情况下,当Google这样的互联网巨头利用黑名单、算法调整和大量合约条款方法来塑造用户的搜索结果时,会严重损害用户利益,同时危害健康的市场秩序(26)Kirsten Grind,Sam Schechner,Robert McMillan,John West,“How Google Interferes with Its Search Algorithms and Changes Your Results”(The Wall Street Journal,15 November 2019),https://www.wsj.com/articles/how-google-interferes-with-its-search-algorithms-and-changes-your-results-11573823753,accessed on 5 January 2022.。
反对观点则坚持认为,把Google这类大平台认为是公共承运人或公用事业不合逻辑。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芭芭拉(Barbara Cherry)教授认为,公用事业的概念是指与某种级别的政府签署协议,向广大公众提供服务的企业。作为交换,它通常会从国家获得一些利益或权力下放。Google显然没有与政府签订提供搜索引擎的合同(27)Gilad Edelman,“No,Facebook and Google Are Not Public Utilities”(Wired,15 July 2021),https://www.wired.com/story/no-facebook-google-not-public-utilities/,accessed on 5 January 2022.。但她没有说明Google能否成为公共承运人,而仅从是否与政府签订提供服务的合同来判断其是否为公用事业也略显武断。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公用事业研究中心(PURC)主任马克·贾米森(Mark Jamison)也认为Google既不是公用事业也不是公共承运人。公用事业是自然垄断企业(例如电力和天然气公司),由政府许可为公用事业,对经济生活至关重要,如果没有它们的服务会造成严重损害。反观Google,尽管它在一般搜索领域享有盛誉,但只有当它代表了提供它及其竞争对手提供的所有服务的最低成本方式,并且其竞争对手无法盈利运营时,它才会成为自然垄断。显而易见的是,Google不符合这些标准,因为在通用搜索(general search)和专业搜索(specialized/vertical search)领域都存在众多有利可图的竞争对手(28)详细参见Mark A.Jamison.Should Google be Regulated as a Public Utility[J],Journal of Law,Economics & Policy,2013(2):223-250.。
有人从Google的算法层面去证明Google本身不存在任何偏见,以此驳斥上述《华尔街日报》的文章。其认为Google的算法编写和程序较为复杂且经得住考验,Google也在不断地更新修改,它能够通过自身的治理改进和完善搜索服务,让搜索变得更加权威,不存在《华尔街日报》所指控的严重操控行为(29)Barry Schwartz,“Misquoted and misunderstood:Why many in the search community don’t believe the WSJ about Google search”(Search Engine Land,18 November 2019),https://searchengineland.com/misquoted-and-misunderstood-why-we-the-search-community-dont-believe-the-wsj-about-google-search-325241,accessed on 5 January 2022;See also Jerri-Lynn Scofield,“Blockbuster WSJ Investigation:How Google Interferes with Its Search Algorithms and Changes Your Results”(Naked Capitalism,17 November 2019),https://www.nakedcapitalism.com/2019/11/blockbuster-wsj-investigation-how-google-interferes-with-its-search-algorithms-and-changes-your-results.html,accessed on 5 January 2022.。也有观点认为,《华尔街日报》并不是带有偏见并忽略了相反的证据,但在高度紧张的政治气候背景下,更大的媒体叙事已经转向反对大型科技公司。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主流媒体出于政治需要,仅仅根据一定程度上的事实对Google大肆批评的情况也是可能的(30)Greg Sterling,“WSJ report about Google search manipulation gets a lot wrong”(Search Engine Land,15 November 2019),https://searchengineland.com/incendiary-wsj-report-about-google-search-manipulation-gets-a-lot-wrong-325190,accessed on 5 January 2022.。
四、平台公用事业的管制基础
上述两个案件以及它们所激起的激烈评论凸显了人们当前的认识分歧,它们源于发言人的不同立场,及对公共承运人、公用事业和公共设施概念的区分和解释,对竞争和垄断概念的不同理解。这些评论意见在问题阐释上未必充分,不过即便更加严谨的学术讨论也未能在这些问题上达成一致,但这些观点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在回应和作出进一步分析之前,先来看我们当前所面临的现状,特别是数字经济的特点以及当前反垄断方法实施中的问题。与美国的公用事业讨论类似,欧盟委员会的《数字市场法》(Digital Market Act,DMA)给出了对大型数字生态系统影响的类似诊断。该法反映出立法层面对竞争规则和平台特性以及规制方法的一种转变。作为对欧盟竞争规则的补充,《数字市场法》采取了更为前瞻性的结构性管制方法。这种变化涉及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涉及反垄断方法的不足。首先,反垄断规则在执行中存在无法将某些行为定性为垄断的困难。实际的损害难以用分配效率来衡量,而是更多地反映在分配后果以及对经济自由(具体表现为消费者自由选择的权利以及商业竞争的保持)的限制上[8](p21)。
其次,反垄断措施似乎不足以恢复自由和不受干扰的竞争环境。罚款不足以制止企业在追求效益之外继续确保和扩大其地位,而罚款是我国到目前为止反垄断执法所采取的最主要方法。对反垄断机构来说,又特别难以作出行为救济的裁定,它们的正确实施也很难被监测。在执行者的武器库中,仅存的救济措施是结构性救济,即拆除或剥离资产和业务。然而,这种措施将带来一些问题。有些是法律问题(如侵犯产权和是否合乎比例原则),有些是经济问题。就交易成本而言,这种补救措施将特别昂贵,也会导致显著的收益损失[8](p22)。
再次,效率是反垄断追求的目标,但其价值在整个数字反垄断中的作用降低了,因为效率问题不再是数字生态系统发展中竞争问题的主要关切。最重要的竞争风险涉及通过获得长期的、甚至是不可逆转的支配地位来抑制竞争进程,由此导致对市场准入的限制,以及占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所享有的市场架构权力。后者可以决定谁进入市场以及在什么条件下进入市场。这在获取与交易相关的租金和交易条件的合理性方面以及在福利分配方面,都产生了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平台使用其控制权来行使强制力,而它的架构和能力使它对生态系统的控制权远远超出了其产权辐射的范围。生态系统中的关键公司可以单方面决定价格、技术标准,甚至决定必须通过其生态系统才能进入市场的公司的投资。它演变为了一个私人监管者,将其交易伙伴置于经济和技术依赖的境地。
第三个问题是,美国学者担忧平台的这种经济权力和控制的集中将对美国的社会根基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经济权力的集中破坏了被认为是建立在某种条件的平等和某种程度的独立基础上的社会契约。然后,经济权力的集中为企业提供了影响政治权力的激励和能力,这使企业在竞争中获得了免受公共政策挑战的保护。另一方面,平台的控制权导致其控制信息,无论是以牺牲传统媒体的利益来获取广告资源,还是制造过滤泡沫(filter bubbles)(31)“Filter bubbles”这个概念由Eli Pariser在2010年提出,指的是在算法推荐机制下,高度同质化的信息流会阻碍人们认识真实的世界。[8](p22-23)。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来看公用事业式监管对控制数字企业权力的重要价值。源于英国普通法的“影响大众利益标准”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在具有网络效应的产业范围之外,在经济学的“效率”“竞争”“垄断”话语之外被激活。汉密尔顿本人坚持认为这一概念具有可塑性。“‘影响大众利益’这一术语的存续,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很容易适应不断变化的常识和司法意见。”[2](p1092)数字平台和影响公共利益的活动之间的关系在美国上述诉讼中越来越被突显,例如美国最高法院托马斯大法官在2021年涉及暂停前总统特朗普的Twitter账户的裁决中提出的不同意见(concurring opinion)。
激活公共承运人概念的好处是,它不依赖于对市场支配地位的证明。这个概念的适用范围并不限于网络行业,而可以扩展到以前没有被授予这一资格的活动。托马斯大法官援引了1914年German Alliance Ins.Co.一案,在案件中,法庭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根据企业自身的情况和性质,一个企业可以从私营企业转变为涉及公共利益的企业(32)German Alliance Ins.Co.v Lewis,233 U.S.,389(1914).。
正是由于有了公共利益的概念,我们才有可能以这种方式对一个公司进行定性,并使它这样一种方式受到监管,即让所有用户不受歧视地获得其服务[8](p24)。托马斯大法官还含蓄地指出了这一概念与核心设施(essential facility)概念的区别。他注意到,安东尼·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大法官在特林科案中说,在评估一家公司是否行使实质性的市场力量时,重要的是替代品是否具有可比性(33)Verizon Communications,Inc.v.Trinko,540 U.S.398(2004).。对于今天的许多数字平台来说,关键正在于没有可比性概念。因此不需要进行相关市场的支配性地位测试。托马斯大法官也使用了看门人的概念,他的推理涵盖了商品和服务的市场以及思想的市场,“(看门人)可以通过删除索引或下拉搜索结果来压制内容,或者通过手动改变自动完成的结果来引导用户远离某些内容”(34)Biden v.Knight First Amendment,No.20-197(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俄亥俄州总检察长戴夫·约斯特在2021年6月对Google提出的起诉书中也采取了同样的方法(35)State of Ohio v.Google,No.21 CV H 06 0274(Common pleas court of Delaware County,Ohio civil division).。Google在在线搜索市场上的地位,以及由此产生的自我推荐的风险,导致总检察长提议将该公司定性为俄亥俄州法律意义上的公共承运人或公用事业。他接受了托马斯大法官的论点,即“一个合理的论点是,一些数字平台足以类似于公共承运人或公共场所,应受到监管”(36)State of Ohio v.Google,No.21 CV H 06 0274(Common pleas court of Delaware County,Ohio civil division),Complaint for Declaratory Judgment and Injunctive Relief.。
一般而言,传统上对大企业进行规制的必要性在于两种失灵。一种是经济层面的市场失灵,市场倾向发展为垄断而非竞争状态,救济方式主要包括反垄断法、公用事业管制、价格控制以及政府拥有所有权。规制的目标在于实现竞争性市场通常可以实现的目标,如确保可负担性、保证产品或服务质量、保证持续的创新和投资。为此监管者通常采取价格管制。另一种是社会价值方面的失灵。由于互联网平台对消费者是免费模式,规制的正当性就必须建立在其他对消费者或用户的损害上[9](p265)。公用事业管制的重要特点在于,不以自然垄断、规模效应、不完美市场等经济标准为唯一标准,而是受管制对象在经济意义和社会重要性两方面的结合。简言之,一种行业如此重要以至于不可以仅仅交给市场去组织。定义所谓公用事业概念的关键就在于,由监管主体去认定一种行业“影响大众利益”(affected with the public interest),且监管具有“必要性”(necessities)。这种社会监管的范畴可以包含商品或服务的普遍供应、产业运行的公平或非歧视,实现文化价值、环保考量或隐私关切[9](p265)。正是公用事业管制的这种功能对平台规制具有重要价值。
与反垄断法不同,监管不以出现违法事实为干预前提,不关心企业的垄断地位如何获得,而是以消除垄断影响、促进竞争为目标,要求企业满足若干特殊义务,促使企业改变市场行为,进行一种结构性转变(37)Harold Feld,“The Case for the Digital Platform Act:Market Structure and Regulation of Digital Platforms”(Roosevelt Institute,8 May 2019),https://rooseveltinstitute.org/wp-content/uploads/2020/07/RI-Case-for-the-Digital-Platform-Act-201905.pdf,accessed on 11 January 2022.。为此,监管机构必须能够结合行业的具体情况去认定某一企业具有支配地位且进行“实时监控”。欧盟《数字市场法》第4条要求,监管机构要对“看门人”的状态进行即时审查以决定监管是否必要。而放松规制的实质就是将一些本来由政府规制的垄断企业重新划入竞争政策约束范畴来进行“间接规制”[10](p88)。
而历史上,反垄断与公用事业管制可以并行不悖,它们之间也曾存在着汇合、交替发展和相互转化的动态关系。美国AT&T公司的历史最好地说明了这种变迁。其经历了垄断的形成、受规制的垄断、反垄断诉讼直至被拆分,不再垄断,以及重新调整的市场结构和垄断重生的解除规制的监管与放松监管的循环。管制与竞争的交替受到各种因素和社会大环境的影响。经济史学家理查德·维艾特(Richard Dewitt)提出,实行管制和解除管制的迅速发展都归结于人们对经济与政府间如何相互作用这一看法的根本性变化[11](p463-466)。可以看到,管制一个行业不仅仅只是制定价格以及阻止进入,目的是使其比没有管制时更能提高效率、减少其他负面影响,提高社会福利。管制机构在决定管制的过程中有许多责任。也许其最重要的责任是,当监管当局把某一行业归为受管制的一类时,必须清楚何时这些管制不再必要。
目前,在平台反垄断这一问题上,无论是采取竞争政策还是公用事业管制,由于针对的是围绕大企业形成的权力和利益之争,其中都不免掺杂着政治的影响。无论是美国主流媒体基于一定程度上的事实对Google进行大肆批评、希望将其定义为公共承运人,还是学者们认为反垄断法仍可延伸适用于数字时代,监管时刻已经到来,而我们必须寻找符合数字时代的新理念和新方法。对于法律和政策制定者而言,应跳出反垄断法的窠臼、经济学的过度干扰,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公用事业式的法律监管规则。
五、结语
我国与美国同样拥有数字大企业,也存在类似的问题。2021年是中国互联网反垄断的“大年”,中央近期不断明确要求加强对平台的监管。但由于我国产业传统有别于西方,且在传统公用事业的监管中还存在对反垄断法与管制关系的认识模糊之处,我国学者研究平台监管的进路并不是由传统公用事业管制扩展至互联网行业,到目前为止的反垄断研究仍主要集中在如何适用反垄断法本身上。笔者以为,在我国不存在对平台进行公用事业管制的障碍,而是存在理论空白,这为在互联网领域进行理论和制度创新留出了空间。
实际上,我国近期的一些规定不断突出对平台的监管要求。如国务院2021年12月14日发布实施的《“十四五”市场监管现代化规划》,一方面强调加强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执法,同时也提到应“健全事前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制定大型平台企业主体责任清单,建立合规报告和风险评估制度”。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021年5月1日起实施的《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32条,禁止干涉平台内经营者自主经营的规定与欧盟《数字市场法》第5条(b)项的规定一致。
笔者已经撰文指出了公用事业理论在我国适用于平台规制的路径,本文的重点则在于呈现出美国的发展路径,特别是近期这一理论如何影响到美国的立法及司法实践,以期为我国下一步的平台反垄断提供进一步借鉴。
人们目前正在形成的一个共识是,以效率为基准的反垄断方法恐怕无法捕捉大平台。这要求学术界发展新的理论和规制工具,并对互联网社会出现的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公用事业理论为管制大平台提供了合理性基础和更符合当前认识的一种管制方法。认识平台在事实上的公用事业特性并以公用事业理念为出发点去设计反垄断监管框架,既符合我国一直以来审慎监管的理念,亦能够汲取历史上对大企业的监管经验,符合我国提出的保持创新和竞争活力、完善市场监管体系并能同时保护大众利益的迫切要求。
必须认识到的是,我们必须在与大企业的共存中去寻求一种经济发展和社会价值的平衡。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也是社会对大企业入侵反弹的必然。而面对控制着几乎所有人数据的大企业,政府也必须采取国家权力这道最后的屏障去控制私人权力,将平台国有化是一种做法,禁止平台数据出境是一种做法,公用事业式的日常管制也是一种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