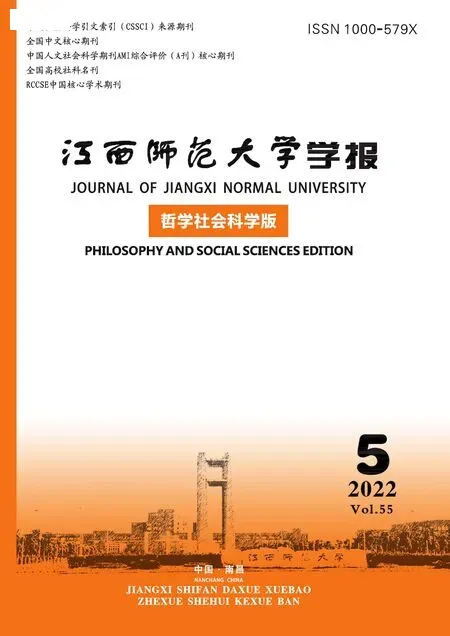《西游记》的空间观及其文化渊源
詹冬华, 孙 瑾
(江西师范大学 1.当代形态文艺学研究中心;2.文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空间是小说的重要表征对象,主要体现在主题内容与叙事形式两个维度,两者既相区别,又密切关联。作为中国神怪小说的巅峰之作,《西游记》呈现了独特而又丰富的空间观念。目前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西游记》的空间叙事。如美国汉学家浦安迪对《西游记》的章回结构、时空布局展开了初步探析(1)参见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68-120页。;韩晓从叙事空间角度确立了《西游记》“平行板块式”的结构方式(2)参见黄霖,李桂奎,等:《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三维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314-316页。。此外,也有论者从宇宙论的角度对《西游记》的空间观念展开了专题性的探讨(3)参见赵凤翔:《上天入地与时空穿梭:〈西游记〉宇宙体系的解构与探究》,《明清小说研究》2017年第1期。。以上成果均能给人以较大的启发,为该问题的后续研究铺设道路。但对于《西游记》的空间观而言,尚有可进一步深拓细琢的地方。本文拟考察的问题是,《西游记》中所呈现的空间观与中国早期思想文化之间具有怎样的关联?小说中的空间设置与时间观之间又有何种隐秘的价值观维系?这些问题的有效开掘对于深入理解《西游记》的意蕴主旨以及叙事形式均有所裨益。
一、《西游记》的空间建构
《西游记》以文学想象的方式建构了一个包含天上、地上、地下的纵横向交叉的立体空间体系,该空间体系映射了中国早期先民对天地宇宙空间的原初认知,也是早期神话时空思维在后世小说中的延续与应用。《西游记》中所建构的空间体系超越了早期空间方位辨识以及地理位置的确立诸层面,而上升到对空间与权力秩序之间隐秘关联的探寻,乃至对生命的有限性与宇宙的无限性对立与超越这一终极存在问题的集体叩问。
《西游记》构建了一个上、中、下三分的世界,分别是以玉皇大帝为最高权威的天上世界,由凡人所构成的地上世界,以阴曹地府、四海龙宫为主体的地下世界。以唐僧为代表的凡人只能活动在横向的地上空间,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白龙马以及天界、洞府、龙宫、冥界等神仙、魔怪可以在纵向的空间里活动。我们可以将自东往西的取经路线看作是“经”,这也是一个由凡(东土大唐)入圣(西天灵山)的空间变换历程。师徒四人每经一地几乎都要牵动天上或地下的纵向空间,那么孙悟空等人的上天入地可以看作是“纬”。这样一来,取经的过程也就成了横向纵向同时进行的“经纬天地”的空间网络编织。从这个意义上说,整部《西游记》实际上是以唐僧师徒取经为事由不断开拓天地新空间的过程。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这个立体的空间网络是否有观念上的源头?其与早期神话、天文、政治等文化形态之间存在何种关联?
实际上,《西游记》中的纵横网络空间植根于中国早期先民对于宇宙空间的经验感知实践。先民根据太阳在一年和一天中的运动轨迹来确认四时和四方,但这时的四方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平面四方,而是东—西与南—北垂直交叉的立体四方。其中,东—西为横向平面空间,南—北为纵向立体空间。叶舒宪先生从“旦”“昆”“昏”“昔”这四个汉字入手,从古文字学与文化人类学层面考辨论证了中国古代神话的宇宙模式系统,认为该系统包括“以‘旦、昏’构成的水平系统和以‘昆、昔’构成的垂直系统”(4)参见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0—36页。,这两个系统可以从《淮南子·天文训》对太阳运行轨迹的空间定位得到证实:
日出于旸谷……是谓晨明。……至于昆吾,是谓正中。……至于虞渊,是谓黄昏。至于蒙谷,是谓定昏。……以为朝、昼、昏、夜。[1](p145)
由“旸谷、昆吾、虞渊、蒙谷”构成太阳运动的垂直和水平模式,昆吾与蒙谷是太阳运行至头顶和地下对应的位置,旸谷和虞渊是太阳刚升起和刚落下的位置。旸谷是太阳升起的地方,为东;虞渊是太阳刚落下的地方,为西,这也是先民最早确定的方位概念:东—西。《西游记》中的长安位于南赡部洲,地处中部。在五行中,“土”恰居中央。相对西天灵山而言,“东土”也称“中土”。从《西游记》的书名便可看出,这是一次西行历程。确立了东西方向后,跟随太阳的运行再确立南北二向。太阳至昆吾,即正午时刻,在空间方位上便是南方。先民发现,在太阳的运行中,所照临之处为东、南、西三个方位,唯有北方是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北”的本义为“背”,引申为背向太阳的地方。这样,北方就与黑暗、寒冷、地下等因素关联起来了。叶舒宪认为,太阳白昼自东向西运行,夜晚潜入地底自西向东回返,所以地下即北便被想象成黑暗的阴间,这也就有了中国上古地狱观念的形成,对于阴曹地府的描述也多以“黑”“玄”“幽”“蒙”等词为主[2](p17)。《西游记》中的阴曹地府便是依据这一空间观念虚构而成的。因此,经由太阳运行的轨迹全程,世界被划分成了三个空间,在旸谷和蒙谷构成的水平方向上,区隔出地上世界和地下世界;而在昆吾之上,则是天上世界。《西游记》中人物的行动轨迹便是在这三个空间中展开的。
空间不可能脱离时间而独立存在,早期先民以太阳运行轨迹为依据划分空间,同样也以此分别不同的时间。也就是说,空间开创与时间绵延是同步的。《西游记》开篇讲述了宇宙运化的过程,第一回诗曰:
混沌未分天地乱,茫茫渺渺无人见。自从盘古破鸿蒙,开辟从兹清浊辨。覆载群生仰至仁,发明万物皆成善。欲知造化会元功,须看《西游释厄传》。[3](p1)
所谓“会元”,指的是宇宙运化的时间单位,天地完成一次大的终始循环构成一“元”,一元又可以分为十二“会”,一会分为三十“运”,一运包含十二“世”,一世包含三十年。以此累计,一会为一万零八百年,一元即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一元结束后,新的一元又开始了,宇宙又开创新的天地。此即“一元复始,万象更新”。《西游释厄传》是较早的《西游记》传本,尾句意谓:《西游记》中包含了天地宇宙循环运化的历程及规律。作者参照北宋邵雍的“元会运世”理论,详细描绘了这一时空展开过程。
盖闻天地之数,有十二万九千六百岁为一元。将一元分为十二会,乃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之十二支也。每会该一万八百岁。且就一日而论:子时得阳气,而丑则鸡鸣;寅不通光,而卯则日出;辰时食后,而巳则挨排;日午天中,而未则西蹉,申时晡而日落酉,戌黄昏而人定亥。[3](p1)
从子时到亥时,一天的十二个时辰皆由太阳运行来确定。不仅如此,小说还将宇宙的创化与十二时辰对应起来,单位不是“时”,而是“会”:戌会终,天地还是昏矇一片;到亥会初,天地间人物皆无,处于混沌状态;接近子会,天地逐渐开明,天始有根;正当子会,轻薄的清气上腾,日、月、星、辰这“四象”产生,所以“天开于子”;子终近丑,地始凝结;正当丑会,厚重的浊气下降,水、火、山、石、土这“五形”产生,所以“地辟于丑”;丑终寅初,阴阳交合,万物化生;正当寅会,人、兽、禽产生。所以,“人生于寅”[3](p2)。至此,天地人三才齐备。可见,小说开篇为后面的叙事创构了一个宏阔的宇宙时空背景,这里有关开天辟地的理论预演为后续的降妖除怪埋下了伏笔。《西游记》第三十三回,孙悟空为了对付金角银角大王的紫金葫芦,将毫毛也变作一个紫金葫芦,对小妖说自己的葫芦能装天,并念咒催动日游神等转告天庭,要借天装闭半个时辰。正当玉帝莫名其妙、不置可否时,哪吒出来相助。
那班中闪出哪吒三太子,奏道:“万岁,天也装得。”玉帝道:“天怎样装?”哪吒道:“自混沌初分,以轻清为天,重浊为地。天是一团清气而扶托瑶天宫阙,以理论之,其实难装;但只孙行者保唐僧西去取经……今日当助他成功。”玉帝道:“卿有何助?”哪吒道:“请降旨意,往北天门问真武借皂雕旗在南天门上一展,把那日月星辰闭了。对面不见人,捉白不见黑,哄那怪道,只说装了天,以助行者成功。”[3](p430)
将北天门的皂雕旗向南天门一展以遮蔽日月星辰,说明有四象的南天门代表了“天”,而北天门的皂雕旗是黑的,黑为浊,浊为地,北天门对应着“地”。用北天门的皂雕旗遮蔽南天门,也就是用北方之黑暗遮挡南方之光明。这也与前面所说的天南地北、南上北下的空间观念相一致。
早在殷商时期,就产生了东南西北中的“五方”空间观念,这是后世“五行”思想的滥觞。秦汉以后,时间、空间被纳入五行思想的整体框架中,将四时中的“夏”分出“长夏”,构成“五时”,再配以“五色”“五味”“五音”等,形成了一个统摄万物的时空大场域,这在《吕氏春秋》《礼记·月令》等文献中均有相应的记载。这一时空与万物配伍的观念在《西游记》中也得到了文学性的彰显。如在第五十一回中,孙悟空在金兜山与青牛怪大战,自己的金箍棒以及众神的兵器皆被妖精手中的圈子套去了,因苦无对策,便想到了用水、火攻击的办法:
行者纵起祥光,又至南天门外……行者道:“……我如今要到彤华宫请火德星君助阵哩。”[3](p659)
径到北天门外……行者道:“有一事要入乌浩宫见水德星君……”[3](p661)
孙悟空先到南天门请火徳星君相助。在火徳星君败下阵后,又至北天门请水德星君。这一细节可见出,这里的空间方位与五行相连,火主南方,水主北方。综上,《西游记》中的神话想象源自早期的时空观念。
二、《西游记》纵向空间的价值差序
《西游记》所构建的天上、地上、地下三分世界在各自的空间内形成了一个秩序化的政治空间。天上世界中有着各方诸神,尤以玉帝为代表的天庭空间,有三十六天宫、七十二宝殿,完美复刻了人间帝王的居住环境,而各路神仙也是各司其职,营构了一个类于人间秩序的政治空间。地上世界即人间世界,由东土大唐以及取经路上所经过的车迟国、乌鸡国、女儿国、朱紫国等多个国家构成,各个国家也遵循着自己的政治制度与风俗礼仪。地下世界的幽冥府和四海龙宫也有各自的政治空间秩序。这个从天上到地下的三分世界所构成的纵向空间也表现出一种从高到低的价值差序关系:天上世界处于最高层级,地上世界居中,地下世界最低。孙悟空出世后的一系列行为,实际上是对不同层级空间秩序的僭越与挑战。
孙悟空最初的活动范围基本是花果山,而后的拜师学艺也是在地上世界这一空间内完成的。在习得了上天入地的本领后,孙悟空开始向其他空间层级发起了挑战。他先往东海龙宫借兵器,拿走了定海神针如意金箍棒,引起龙宫水族空间的极大震动。花果山众猴设宴庆祝,孙悟空酩酊大醉后被索魂至幽冥界,在这里有一段描述:
悟空执着如意棒,径登森罗殿上,正中间南面坐下。十王即命掌案的判官取出文簿来查。那判官不敢怠慢……[3](p37)
《周易·说卦》有言:“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4](p620)孙悟空在森罗殿南面正中而坐并对十王下达命令,显然是把自己当成了最高君王,这暗含了孙悟空想成为帝王的野心。他将生死簿上的猴族一笔勾销,便是对地下冥界秩序的最大挑战。
孙悟空夺取金箍棒、勾销生死簿的事情引起了天庭的注意。经太白金星献计招安后,孙悟空也在天庭过了一段逍遥日子,直到玉帝命其接管蟠桃园,事情有了转变。他偷吃蟠桃,使王母娘娘无法宴请宾客;在得知自己不在受邀之列后,更是醉酒大闹天宫。玉皇大帝不仅管辖天庭空间,同时对地上人间以及地下世界也有最终的主宰权。孙悟空的行为挑战了天庭的权威,这让玉帝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来自凡间的石猴。在诸多天兵天将奈何不了孙悟空时,玉帝只好请如来佛祖救助。佛祖将孙悟空压于五行山下,孙悟空本属石生,与五行山同属于地上空间,所以佛祖是将孙悟空送回了他的所从来之处,这一压就是五百年。佛祖并未将孙悟空处死或押往西天,而是打回原处,实际上就是用这种“空间归位”的方式让孙悟空接受“天尊地卑”的分位意识。这种源于纵向空间层级区分的分位意识贯穿了后续取经路上降妖除怪的始终。综观取经路上的各路妖魔鬼怪,来自天上的如太上老君的青牛、童子,如来佛祖的亲戚大鹏等,最终还都是回到了天上,而地上以及地下的妖魔多半都以死亡而告终,这便是空间秩序的不可侵犯性。在《西游记》第三十二回中,孙悟空在平顶山与樵夫的对话中便有力地佐证了这种空间层级秩序的不可颠覆性。无论何方来者,皆有其去向:
行者道:“若是天魔,解与玉帝;若是土魔,解与土府。西方的归佛,东方的归圣。北方的解与真武,南方的解与火德。是蛟精解与海主,是鬼祟解与阎王。各有地头方向。”[3](p407)
那么,《西游记》中所呈现的空间分位意识是如何形成的?纵向空间的价值差序的思想文化渊源又是什么?
在早期思想文化语境中,“尊”“卑”由自然之“势”所决定,天有天势,地有地势。《淮南子·天文训》:“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清妙之合专易,重浊之凝竭难,故天先成而地后定。”[1](p103-104)天因为高而成其为天,地因为低而成其为地,两者不可析离,如此才能形成上下一体的乾坤。这是一种不证自明的自然现象。“尊”“卑”是天德和地德的象征,亦即天与地的性质与品德。天德自强不息,地德厚德载物,天地共同承担着化育生命的职责,尽管天具有高高在上的空间之势,却不能凌驾于广袤厚实的地势之上。“天尊地卑”的说法包含了两个层面的意义指涉:一是对自然现象的事实确指,二是对这一现象的价值赋予,两者相互支撑,人为的价值诉求与自然的天地之势实现了完美的统一。《周易·系辞上》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4](p527)天因为高所以尊(上),地因为低所以卑(下)。因此,原本自然成势的上下、高低的空间就被赋予了截然不同的价值等级了。事实上,在中国早期的文化进程中,将不同的空间赋值是一个渐次发展的文化重塑及建构过程。
早期先民对于空间的感知,主要是通过眼睛观察、耳朵聆察、身体觉察的方式全息性展开的。《周易·系辞下》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4](p572)伏羲氏仰观俯察,拓展纵向的垂直空间;同时又以身体为中心,远望近看,从横向打开平面空间。因此,早期先民一开始就从纵横两个向度建构一种立体的空间格局,一是上下空间,二是四方空间,连起来就是“六合”。这种天覆地载式的六合空间模型来源于先民对房舍的直接感知。有意思的是,在中国原始神话中,这两个向度的空间并不是如影随形般的同时出现,而是有所侧重。也就是说,先民在实践中可以同时感知两种空间,但在文化的二次重构时则是分途进行的。殷商的甲骨卜辞中就出现了四方观念,四方与“中商”形成密切的拱卫关系,这是当时最为重要的空间秩序。殷商尽管也有祖先神祭祀的宗教传统,但并未在观念上突出上天与地下之间的空间对应关系。这一情形到周代有所改变,这时出现的“天”的概念预示了对垂直空间的重视。纵向的天地空间观虽然也出现得比较早,但通过文献的方式将其最终定型则要晚得多,而且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创世故事出现得越晚,比如女娲补天的故事最早见于《淮南子》,而盘古开天地的故事到三国时期才始见于徐整的《三五历纪》。相较而言,纵向立体空间要晚于横向平面空间,是一种后起的带有鲜明政治价值指向的文化型空间;而后者则导源于先民对世界的原初空间认知,是确立人间秩序的最为基础的存在型空间。综上可推知,先民最先重视的是“中”这一空间,殷周之际特别是周以后,空间的重心开始由“中”转向“上”,这在“帝”“天子”这两个称谓中就可见端倪。
自殷周至汉代,人们对纵向空间的认知趋于定型,“天尊地卑”的空间分位意识最终成为一种民族文化密码,潜藏在人们的文化无意识深处,并在后世的文学艺术中不经意地呈现出来。作为一部经典的神怪小说,《西游记》无疑承载了中国早期文化传统中的原发性思想观念,并通过神话想象的方式表达出来。
三、《西游记》空间秩序的时间根因
如果将政治文化因素排除在外,《西游记》中所呈现的“天尊地卑”的空间秩序还存在更为深广的存在论基础。小说中自始至终贯穿着一个寓言式的时间主题,取经路上的大小妖精都想吃上一口唐僧肉(女性妖精或与之婚配),以求得长生不老。换言之,在妖魔看来,唐僧是永恒时间的化身,通过啖其肉的方式与永恒发生关联,自身的生命就能得到无尽的时间,以达到肉身不死、生命不朽的目的。这个隐秘的时间主题与中国古代的游仙文化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游记》可能还受到早期仙话文化的影响。本文要探究的是小说中的空间价值差序背后所隐藏的时间性根因,亦即生命的有限性与宇宙的无限性之间的尖锐冲突。
这个观念上的冲突始于天生地长的石猴孙悟空。《西游记》第一回,孙悟空便提出了这个终极性的存在论问题:
猴王道:“今日虽不归人王法律,不惧禽兽威严,将来年老血衰,暗中有阎王老子管着,一旦身亡,可不枉生世界之中,不得久注天人之内?”众猴闻此言,一个个掩面悲啼,俱以无常为虑。[3](p7)
可见,孙悟空已然意识到了生命终将消逝的危机,尽管既不归人王法律,亦不惧禽兽威服,但却依然比不了天道恒长。所以孙悟空便萌生了学习长生不老之术以躲阎君之难的念头。在菩提祖师向他传授技艺时,闻得不能长生便不学。孙悟空学成归来后,在龙宫得了如意金箍棒,森罗殿勾销了生死簿。在孙悟空的认知中,他可以与天地同寿,与日月同庚,超越了生命有死的束缚。此时,他已经不满足于仅仅据有花果山水帘洞这一狭小的家宅空间了,更不满足于美猴王这个只在猴群中才能产生威望的空间地位了,他有着更为高远的目标,即占领天宫,在他看来,玉皇大帝并不能够配以天宫之尊位,所以欲取而代之。他在与如来的对话中说道:
炼就长生多少法,学来变化广无边。因在凡间嫌地窄,立心端要住瑶天。灵霄宝殿非他久,历代人王有分传。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3](p81-82)
孙悟空对于秩序的理解是强者为尊,但佛祖对孙悟空说出了玉帝为天地至尊的真正秘密:
你那厮乃是个猴子成精,焉敢欺心,要夺玉皇上帝龙位?他自幼修持,苦历过一千七百五十劫。每劫该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你算,他该多少年数,方能享受此无极大道?你那个初世为人的畜生,如何出此大言
《西游记》开篇交代,天地之数,十二万九千六百岁为一元,天地在这一元之中诞生,而玉皇大帝已经历了一千七百五十个天地之数,超长天地时间的积淀使得玉皇大帝能居天之中央,位居众神之上,掌握众生之运命。可见,空间地位的确立最终取决于时间的累复。而这一点,也有着深广久远的文化渊源。殷人好鬼,有祖先崇拜的信仰,他们建神祠以安放祖先,“将死者放置到恰当的祭祀等级之中,而位置是由生者决定的”[7](p66),而且“这一等级结构似乎还反映了每位祖先的权能大小:越老的祖先权能越大”[7](p66)。可见,在殷商时期,祖先权力是按照时间(宗族源流)的先后来决定的,始祖处于至尊位置,往后的权能渐次减小。因为在殷人看来,祖先升天后一直存在,成为上天的诸神,他们都是上帝的臣子。依照这样的观念再来看玉帝就不难理解了,经过一千多个天地之数的艰苦修炼,玉帝才得以稳坐天庭中央之位,这不是孙悟空一个刚出世的石猴所能撼动的。在孙悟空看来,自己有七十二般变化,又有长生之术,以及金箍棒加持,认为居高位者应以强者能力为参考标准。但事实并非如此,所以孙悟空如果一定要获取在空间地位上的价值认可,更需脚踏实地认真修炼。在后来的西天取经路上,即使孙悟空可以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只消须臾便可抵达西天,但这都不能使得孙悟空修成正果,而须跟随唐僧经受九九八十一难才能求取真经,加升大职正果,成为斗战胜佛,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长生不老。
如前所述,长生不老并不是孙悟空一人之愿。不论是天魔、地魔、蛟精,还是魑魅魍魉,他们都有相同的祈愿,“吃唐僧肉以长生不老”成为他们追求生命不死的一个集体标示。此外,天庭的蟠桃与五庄观的人参果亦有延寿长生的功效。这些经过长久的天地灵气日月精华所浇灌出来的仙果也是难得的长生不老药。而孙悟空偷吃蟠桃、毁人参果树不仅是挑战权威,也是在仙家长生路上搁置绊脚石,以破坏仙家利益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故而孙悟空的“冒犯”使得自己付出了先是被压五百年而后又差点断掉取经路的沉重代价。可见,在《西游记》中,长生不老是一种永恒的集体无意识。这种无意识在早期文化中也有鲜明的体现。先民对于自然存在的一切物质包括人本身都充满着好奇、怀疑甚至是恐惧,他们无法区分睡眠的身体静止和死亡的身体静止有何区别。当他们无法科学认知生死的自然规律时,恐惧死亡、渴望长寿成为他们的集体追求,所以,“不死国”“不死民”“不死药”等就成了先民的替代性想象。《山海经·海外南经》载:“不死民在其东,其为人黑色,寿,不死”[8](p160);《山海经·大荒南经》:“有不死之国,阿姓,甘木是食”[8](p243-244);《淮南子·览冥训》载:“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恒妲娥窃以奔月。”[1](p333)这在《西游记》中也有所体现,如比丘国国王要用一千个小孩的心肝做药引子以求长生。
综上,《西游记》剖露了各个空间的存在者对于生死问题的追问,这是一种不自觉的哲学思考,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深入洞察也使我们再次审视生命有限与宇宙无限的尖锐矛盾。但是,究竟如何化解这个矛盾?《西游记》第一回中便显出端绪,猴王在路上向樵夫打听神仙的住处,樵夫告知他须菩提祖师住在“灵台方寸山”的“斜月三星洞”中,这两个空间性的地名其实都是“心”的隐喻。李卓吾评曰:“灵台方寸,心也。一部《西游》,此是宗旨。”[9](p7)也就是说,要想实现超越,必须自己修炼心性,舍此别无他法。
四、结语
《西游记》广泛汲取了中国古代神话、天文、地理、宗教、政治等文化传统中的空间观念,将其融会贯通;并通过丰富的文学想象,建构一个复合型的、纵横交叉的空间体系。其中,既保留了中国早期创世神话的时空思维,也蕴藏着道家仙话文化传统的精神内涵;既集中呈现儒家“天尊地卑”的空间分位意识,同时又掺入佛教的时空观念。比如第七回写到,孙悟空虽然一个筋斗云能飞十万八千里,但却飞不出如来佛祖“方圆不满一尺”的手掌。该情节想象奇幻,显示了佛祖无边的法力,但其背后的文化支撑是佛教大小互含互摄的空间观。在佛教视域中,一佛的化境称为“一佛土”,包含“三千大千世界”,这是佛祖释迦牟尼教化众生的世界,也称“娑婆世界”(8)参见方立天:《佛教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88—189页。。《大智度论》云:“百亿须弥山,百亿日月,名为三千大千世界。如是十方恒河沙三千大千世界,是名为一佛世界,是中更无余佛,实一释迦牟尼佛。”[11](p125)可见一佛所下辖的空间范围之大,但一佛土在无边的宇宙中只不过是沧海一粟。《五灯会元》云:“三千大千世界,日月星辰,江河淮济,一切含灵,从一毛孔入一毛孔,毛孔不小,世界不大,其中众生,不觉不知。”[12](p455)所以,如来“似个荷叶大小”[3](p82)的手掌含摄了无限大的空间。
有意思的是,这些不同文化体系中的时空观念均在文本中得到有机的统一,彼此之间并不形成明显的龃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纵向空间秩序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在这个虚拟的神话世界中,同一空间层级的圣、仙、佛可以和谐共处,甚至组成重要的同盟;但如果同一空间层中出现了扰乱或挑战秩序者,均被视作为“妖”,最终必然会被打回原处。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游记》中威胁力最大的“妖”就是孙悟空,他被收服之后保唐僧取经的降妖过程可以看作是对他的重重考验。这个过程既是他身份的转变,由戴罪在身的行脚僧变成真正的佛,同时也是其处身空间的大幅度擢升。此外,小说中处处呈现的仙凡世界的鲜明对比,特别是神与人生命寿夭的巨大差距,也始终撩拨着每个人的时间思维神经。《西游记》之所以成为经典,不仅是因为其瑰丽神幻的文学想象,而且还与其中的时空观念所激发出来的思想高度与体验深度有着密切关联。对于读者来说,这种由小说所引发的时空叩问,既是一种超越凡庸的审美体验,也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生存哲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