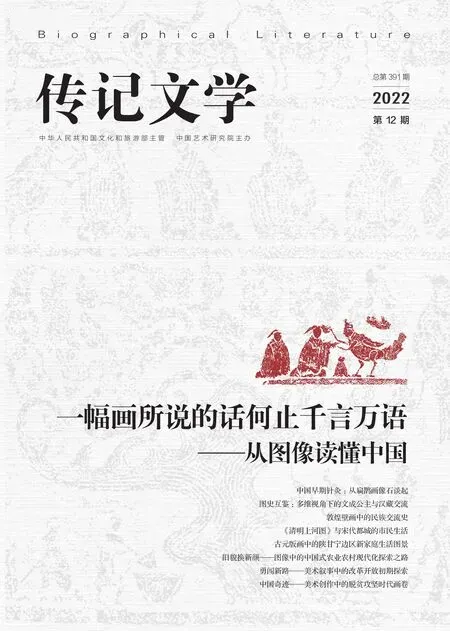一幅画所说的话何止千言万语
——从图像读懂中国
本刊编辑部
“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梁启超)现代史学将史料分为文本、口述、图像三大类,其中文本史料占据着核心位置,重量级的史学著作都以占有大量而重要的文本史料作为其优势和独特性,相比之下对图像史料的重要性,学界认识尚不一致,甚至还曾出现过围绕图像史料价值发生“可见中的不可见性”的争论。
其实,作为具有以可见的形式记载人类往昔事件、历史人物、自然万物、风俗习惯等事物功能的史料,图像在古今中外历史叙述和研究中一直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图像史料的物质性的可见视角能够弥补文字史料所忽视或阙如的缺憾,尤其为历史细节的生动再现提供了珍贵的证据。中国上古传说中“河出图”的记载,代表了人们对于图像起源和功能的认知,借助图像,人们得以认识自然宇宙的形象。唐代的张彦远认为,图像的功能是“无以见其形,故有画”,甚至能够“传既往之踪”,图像兼具文字记录的功能。宋代的欧阳修认为,图像可以“与史传正其阙谬者,以传后学”,证经补史,补订疑误。郑樵在考证“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的基础上,认为“若欲成天下之事业,未有无图谱而可行于世者”,给予图像以重要的史学价值。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作史者能多求根据于此等目睹之事物,史之最上乘也。”可见的图像是作史者“目睹之事物”,是史料中“最上乘者”。由此可见,在中国历代文人知识分子观念中,图像具有记录历史的功能,甚至能够弥补或正订文字所无法完成或谬录的一些历史细节。
公元前5 世纪,西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在其著作《历史》中讲述了关于著名的里拉琴演奏者阿里翁逃脱船上水手的蓄意谋杀,投入大海,被一条喜欢音乐的海豚从海中救起的历史故事。最初这个故事是希罗多德从科林斯人和雷斯波岛人那里听来的,后来希罗多德在特纳鲁神庙看到出土于雅典卫城的一个骑着海豚的青铜男像,这个历史故事得到了实证。西方有学者根据贝叶挂毯《国王哈罗德在哈斯廷斯战役中阵亡》(约1100 年)上叙事的故事细节,认为英国国王哈罗德因眼睛中箭而阵亡。18 世纪中叶,有批评家说,如果有更多的画家创作像约瑟夫·韦尔内的法国海港画一样的作品,他们的作品将造福于后代,因为“从他们的绘画中有可能读到行为举止的历史,还可以读到艺术史和民族史”。瑞士艺术史家雅各布·布克哈特认为图像和历史遗迹是“人类精神过去各个发展阶段的见证”,通过对图像等史料的解读,才有可能解读特定时代思想的结构及其表象。
图像是可见的历史,但图像的价值和意义并不局限于此,图像还具有艺术性,具有审美功能和叙述性。今天的图像学或图像研究这两个术语,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在艺术史学界运用。德国艺术史家欧文·潘诺夫斯基将图像的解释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前图像学的描述,主要关注于绘画的“自然意义”,并由可识别出来的物品和事件构成;第二个层次是严格意义上的图像学分析,主要关注于“常规意义”;第三个层次是图像研究的解释,关注“本质意义”,揭示图像中“决定一个民族、时代、阶级、宗教或哲学倾向基本态度的那些根本原则”。图像研究的第三个层次可称为图像文化阐释学,解读图像所隐含的文化思想内涵。图像的可见的形式是有限的,但图像所叙述的故事往往会超越有限的形式,蕴含丰富的、生动的、多元的思想,艺术地呈现漫长历史时间里发生的多重复杂的历史故事,所以,图像又被称作“可视的叙事史”。可视的图像是无言的见证者,更是能说会道的“讲故事的人”,一幅画所说的话何止千言万语。
我刊2022 年第12 期推出封面专题“一幅画所说的话何止千言万语——从图像读懂中国”,邀请重庆大学艺术学院郝斌等八位学者,选取汉代画像石《扁鹊行医图》、《步辇图》、关于文成公主的西藏壁画、敦煌壁画、《清明上河图》、20 世纪40 年代古元系列版画、关于改革开放和新时代脱贫攻坚的国家主题性美术作品若干幅,这些图像作品涵括中国历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各个方面,记述了中华文化发展史、中华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史、百姓日常生活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发展史、改革开放史、新时代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史,通过对这些图像作品的创作时间、时代背景、叙述的故事及其思想文化内涵以及影响等诸方面进行细致的梳理和研究,力图以可见的图像的形式叙述从春秋到当下的跨越2000 多年的中国社会发展简史。
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中国的故事是真实的,属于史学范畴;但讲述故事的技巧是艺术的,属于艺术史范畴。以可见的中国历代历史、社会、文化图像,艺术地讲述中国故事,既能直观历史的细节,读懂图像深层的思想内涵,又能欣赏艺术的魅力,这必定是讲故事的“最上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