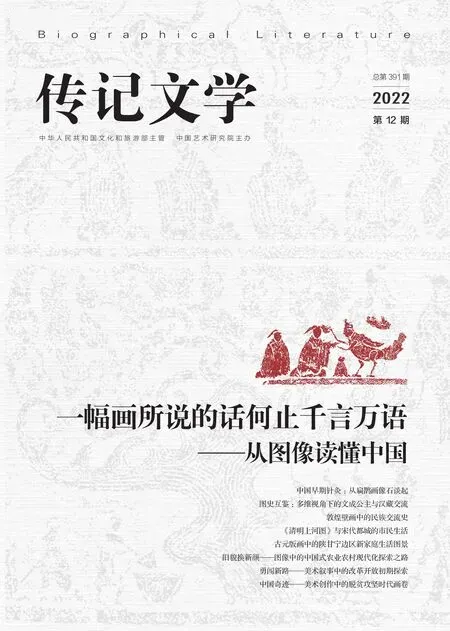“偶然值林叟”
——我进入民间文学研究的历程
毛巧晖

2019 年12 月12 日,本文作者(右)访谈郝苏民先生(张歆摄)
学术研究对于出生在20 世纪70 年代中期华北小镇的人而言,其距离不亚于地球与火星。儿时倒是经常有祖母的两位哥哥从北京、上海邮寄自己的著作回来,也是家里为数不多的几本书。我偶尔也会听祖母念叨在北京科学院工作的大哥和在复旦大学工作的二哥。祖母家一共兄弟姐妹四人:大哥贾芝,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工作,少数民族文学所(2002 年改称民族文学所)成立后担任第一任所长;二哥贾植芳,长期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工作;姐姐也是婚后跟随丈夫到北京生活;只有祖母一直生活在家乡山西襄汾古城镇。不过当时我可完全不明白,更不知道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个单位。对我而言,最开心的还是去镇上的供销社看看琳琅满目的糖果、果脯和糕点,或者跟伙伴们一起去玩耍。那个时代,家长对孩子没有要求,当然也没有期待,只要长大有个工作就行,所以我从小并没有高远的志向。父亲曾经提起,我在7 岁时写过一首石榴花的小诗,但小学、初中我都没有表现出在任何一个学科上的优势与天分,属于老师永远不会记得的中等生。我的一个小学老师也曾教过我父亲,她经常语重心长地说:“你可是跟你父亲差远了。”小镇是熟人社会,这话我听多了,也没有过多伤自尊,倒是越来越习以为常。直到中考,父亲希望我考中专,因为毕业立即就可以有工作,估计也是当老师的父亲发现我并没有读书的天赋吧。当时考中专分数非常高,我的成绩只够高中,于是也就没有加入后来经常被人们提及的“中师生”队伍。不过当时的我并没有想过读完高中之后是否能考上大学,考哪所大学,更没想过上什么专业,似乎就是顺其自然地读书。那时还是先报志愿后高考,在我填报志愿的时候,母亲只有一个要求,必须离家近,所以也就出现了第一志愿山西师范大学、第二志愿陕西师范大学、最后一个志愿北京师范大学的状况。班主任老师以为是我不懂随便填写的,所以又找我父亲商量,但结果依然没有变。后来,我多次问过父亲:“您也是老师,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他总是含糊其辞,我们都知道是母亲不愿意我走远,所以离家20 多公里的山西师范大学必须是首选。至于填报什么专业,父亲教英语,他最希望我学英语或者中文,但我当时坚持要报历史系,因为在高三时我突然喜欢上了历史。当时的历史老师说着标准的普通话,不用看教案与课本就能把各个朝代及世界各地的大小事件说得清楚明白。其实在高中,除了课本外没有其他书籍,所以我并没有看过任何历史领域的通俗或学术著作。现在当然知道这也谈不上是爱好,只是不愿意与父亲从事一样的工作。直到考上大学,才开始对学术或者说学科、专业方向有了模糊的概念。
一
1993 年我考入山西师范大学的时候,高校尚未有现在这样对学术产出的高要求,老师们更多致力于授课,但当时大学里的年轻老师很多出去读硕士、博士,获得学位后也大多调离了学校。虽然没见过他们,但是他们的“传说”经过辅导员、授课老师的“口传”,我们也有些许了解。似乎读研究生是当时青年人的主要追求,当然最核心的,就是读研究生才是我们最好的出路。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双非”高校,又是历史系,毕业生的就业并不好,再加上从我们这届开始双向选择,不再是定向分配工作。从刚上大学,辅导员王瑾老师就一再告诉我们要考研究生,不能仅限于追求本科毕业。王老师自己也致力于考研,而我当时因为害怕与老师们交往,从来没有问过老师考研的学术方向与个人选择,更不知道如何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选择,所以也只是想考研究生,但对考哪个专业方向并不知晓。
到了大三,我们开始学习世界史,当时是刚从南开大学毕业的博士徐跃勤老师讲授,他要求我们读原著、读经典。在他的课堂上,大家要逐句阅读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我们既感到新鲜也陡生了对经典著作的热爱,他介绍了很多后来我们耳熟能详的著作,如摩尔根的《古代社会》、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等。同时,他也在课堂上介绍了世界史的不同方向,特别提到目前学科中最稀缺的人才就是世界上古史,不知道为何我竟然就听进去了。估计徐老师已经不记得了,我在大学期间唯一一次课堂提问,就是问了想要学世界上古史去哪个学校比较合适?他介绍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于是我的考研方向、考研学校就这样确定了。然而,这却是我人生第一次没有被考神眷顾,此前从小到大的考试永远是擦边过,但也没有失败过,好在还有可以转到其他学校的机会。当时的考研转校不像现在对填报专业有严格要求,我有机会转到西北民族学院(后改名为西北民族大学)民间文学专业。到兰州面试之前,我从没有听说过这门学科,贾芝及其夫人金茂年老师让我找在山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民间文学的段友文老师,借一本民间文学教材看看。时间仓促,我也没机会见到段老师,更没找到《民间文学概论》。当我去面试的时候,已经是“五一”之后了,到了西北民族学院,第一次见到很多少数民族同学,当时感觉既新鲜又好奇,当然更多的是茫然。面试我的是郝苏民和郗慧民两位先生,他们问了我几个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希望我以后能够喜欢这个专业。当时并不理解,现在自己也做了导师之后,才真正明白老师们的苦心。喜欢一个专业确实不容易。
二
进入研究生学习阶段,才发现硕士与本科完全不同。记得当时硕士生导师郝苏民先生入学后给我们讲的第一节课就是如何做好学问?现在已经不记得先生当时讲了什么内容,但他讲课的形象与样貌跃然“屏”上。他对学术有着超乎常人的热情与激情,当然,当时的我对此完全不理解,也难以接受。90 年代末,还不像现在有大量的学术讲座,信息也并不是很畅通,只记得到兰州大学偶尔听过一两次博士生答辩,听得也是一头雾水,知道了答辩时老师们都很严厉,个个都是“鸡蛋里挑骨头”的行家。至于课程,阅读的很多书都是似懂非懂,弗雷泽的《金枝》、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等虽然翻过一遍,但真正理解到什么程度,很难说。那时我经常跟同学吐槽,字都认识,意思连到一起就不知道是啥了。其间做的几大本读书笔记,跟我搬了几次家,但都依然留存,每次整理完都要翻阅一遍,还是舍不得扔掉,总觉得是记忆的储存。大段大段的抄文,似乎是80 年代抄写席慕蓉、汪国真等诗作的习惯,偶尔一两句思考也是表达学习的苦闷。所以确实不像郝先生、郗先生在面试中所说的,喜欢上这门学科,似乎并未将老师的学术情感转化,民间文学对我依然很陌生。
时间并不会因为我的懵懂就放慢脚步,一转眼就到了研三。因为参与郝先生与甘肃泾川合作举办的西王母神话会议,我第一次与民间文学“学术研究”相遇。1999 年9 月,刚到学校不久,郝先生安排我和王会莹(现任职于泰国孔敬大学人文学院东亚语言系)一起到泾川县参与筹办会议。不像现在很多研一的学生都能参加各种会议的筹备工作,当时身边的学术会议很少,郝先生为了让我们能接受更多新鲜知识,邀请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的江波老师讲授一些社会学研究方法。可以说,对于学术会议我们一无所知,留在脑海里的只有作为会议场所的空旷的县城礼堂及海量的学术大咖。人生第一次见到了很多看过其著作却素未谋面的“作者”们。当时到会的有贾芝、乌丙安、柯杨、叶春生、陶立璠、杨亮才、梁白泉、潜明兹等民间文学、民俗学领域的著名学者及当时还是中青年学者的叶涛等诸位老师。这次学术会议除了知识的吸纳外,还让我第一次在日常生活中近距离接触到学者。这些在当时可能对我没有太大的影响,自己也不知道未来学术会议会成为工作、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从情感上开始对学术有了模糊的认知。会议结束后,游丝般的学术浸润似乎也断了线,但实际可能埋藏到自己的记忆深处了。多年以后,回想起这次会议,回想起自己所见到过的这些学者,后来再遇到他们时,会不经意间提起自己最早见到他们是在泾川,共同拥有的这段记忆似乎使彼此的距离更近了几分。我也因参与会议筹备结识了王知三老师,再次见到王老师已经是2018 年中国民俗学会在广州的年会,他的身影活跃在各个分会场,依然是背着相机。那一刻,我似乎又回到了1999 年秋天的泾川。人生不知道何处为起点,很少被提及的泾川却成了我学术的起点,至少是初识(当然是从我单方面而言,老师们不可能记得一个年轻的办会学生)学界很多前辈学人的开始。
硕士期间记忆深刻也是对我影响非常大的另一件事,就是毕业论文的选题。当时进入硕士阶段的学习时,最难适应的是课程不再考试,而是要撰写课程论文。由于大学期间几乎没有学习和接受过相关的课程教育,我对论文撰写可以说一头雾水。从小讨厌考试的我,当时却经常在心里祈盼赶紧回到应试教育吧,比写论文强多了。经过两年的锻炼,我慢慢可以应付课程论文了,但是硕士论文选题对我来说还是真的太难。最初因为有一门课程是郗先生讲授的“西北花儿学”,郗先生时不时还会唱上几句“花儿”,课堂气氛生动有趣,这引起了我对民间歌谣的兴趣,自己也经常翻阅郗先生的著作《西北花儿学》。当时的老先生们大多只有一两本著作,他们并不执着于学术发表,而是更关注学生的成长。我抓耳挠腮地完成了一篇有关信天游研究的习作,作为歌谣学的课程作业,拿着去找郗先生,表达了自己想将信天游作为硕士论文的选题。郗先生很高兴,跟我说:“你会唱信天游吗?”我当时就愣住了,从小最怕的就是表演,发言都紧张得声音发颤,更别说唱歌了。因为专业是民间文学,同学大多能歌善舞,他们跳着优美的各族舞蹈,演唱着各地的民歌,但我却从迎新到每年元旦的师门聚会,最怕的就是表演节目。记得刚入学,大家精彩演出之后,轮到我,只能干巴巴地讲了一则“南蛮盗宝”的故事。郝先生后来跟我说,我们这些老师到各地采录过大量的民间故事,你还给我们讲故事啊?我只能尴尬地沉默。可是在小镇出生长大的我,确实没有机会学习唱歌,更别说演奏乐器,自己又没天分,所以完全张不开口。突然被郗先生问会不会唱信天游的时候,我不自觉地嘟囔了一句:“研究还要会唱啊?”他很亲切但严肃地说:“你不会唱怎么能更好地理解民歌啊?你看,李雄飞他不仅会唱,都能当了‘伞头’。”(李师兄比我高两届,主要以陕北信天游为研究方向,出版了《河州“花儿”与陕北“信天游”文化内涵的比较研究》等著作论文,曾经执教于西北民族大学,后调到广东海洋大学工作。)我现在明白,郗先生所说的其实就是现在强调的民歌中的整体研究问题,以及歌谣与语境关系的讨论。当然,在那一时期,我理解不到这样深邃,只是很沮丧,别说唱得像李师兄那么好了,我是一首都不会,能勉强唱下来的也是曾经的流行歌曲《信天游》。与郗先生聊完后,我就只是写了一篇有关信天游的作业。最后还是郝先生指点迷津,让我以山西长治回族女性的信仰民俗为题,因为在自己家乡有调查便利,同时这一话题也具有优势,容易完成。当时,我还没有接触过“家乡民俗学”的概念[1],但学者们的思想不谋而合。郝先生特别注重发现学生的个体优势,他一直秉持因材施教的理念,发挥每个人的优长。郝先生是伯乐,但我却不是千里马。当时,我确实觉得自己没有做学术的天分与爱好,因此硕士毕业之时并未像同届的同学们那样积极考博士,感觉自己不仅是对读书失去了兴趣,可以算是出现了厌学情绪。
2000 年硕士毕业,我如愿回到母校山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最初两年主要从事教学。在本世纪初,一个省立普通师范大学的青年教师几乎没有学术交流的机会,更何况只是从事中文学科中的边缘学科民间文学、民俗学的教学,自己更焦虑的倒不是学术发表,而是为了完成教学工作量教授大量学科外课程,几年内我兼任过外事处的留学生教学、编辑出版系的出版学课程等。可能教书过于疲惫了,也是不甘心总处于“急就章”似的讲授自己不熟悉的课程,我选择了报考博士。通过查找资料,我找到了华东师范大学陈勤建教授所招的文艺民俗学方向,瞬间决定考这个,因为这能改变我的学术背景,至少可以得到中文系同事的认可。非常幸运,我如愿考上了陈老师的博士。博士期间算是我像郝先生、郗先生所希望的“喜欢”“爱上”民间文学的开端,但其中还是有曲折。
三
2002 年开始,我跟随陈老师读博士,首先感受到最大的不同就是地域文化差异。上海与自己出生、成长的区域不同,和读硕士的城市也不一样,特别是当时城市之间的差异还很大。我经常回忆初到上海时的感觉,与人类学者经常提到的文化震撼(culture shock)差不多,看到的一切都不是自己熟悉的,难免生出很多伤感,再加上当时女儿刚刚出生,这可能是很多攻读博士的女性都曾经历过的。与一些同行经常聊起这个话题,在学术研究中性别差异其实很大。那时孩子刚满一岁,我就到了上海,孩子不知道妈妈会离开很久,可能最初以为我只是像往常一样去上课了,一直看不到妈妈回来,孩子的哭闹可想而知。多亏我母亲全身心投入对孩子的养育中,似乎她又回到了做母亲的时期,不记得谁在推文中提到,中国的姥姥都非常伟大。母亲曾经担任过村里的妇女队长,对自己和孩子要求都很严格,也非常支持我的工作。当时还没网络视频、语音的条件,只有电话,家人在电话中总说孩子很好,而我听到孩子“咿咿呀呀”的声音往往都会躲在被子里哭很久。对于孩子来说,她还不能把声音与妈妈区别开,经常有人跟她开玩笑,问她:“妈妈呢?”她就指着电话。因为无法把声音与影像结合,她后来慢慢连电话都不愿意接了。当我回到家的时候,她已经不认识我了,这恐怕是作为母亲最难过的事情。我心里曾经想过放弃,准备辍学重新考个省内高校,后来还是在家人的鼓励和自我调适中才坚持了下来。
生活和学术的不适应渐渐在老师和同门的关照中度过,博士生基础课程的学习很快就结束了,其间我也听了很多讲座和中文系老师的课程,慢慢在实现接受知识与学术研究之间的转换,但面临博士选题的时候依然很艰难。导师会经常强调,博士选题不像硕士,需要更多自己的思考,且大多成为研究者未来的主要从业方向。经过硕士阶段的学习与历练,专业素养开始逐步体现出来,另外高校的教学经历也给了我很多帮助。到现在我也经常鼓励自己的学生,可能在硕士阶段学习的内容当时体现不出来,但经过时间的洗礼,一定会彰显出曾经的努力。那个时候,郝苏民先生还担任着《西北民族研究》的主编,特别注重引导我们的学术方向,关注当时刚刚出现的趋势 ——多学科交叉。记得在一次课堂上,他跟我们提到曾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跟师生们交流,当马戎介绍他是西北民族大学教授的时候,学生们几乎没有反应,但继续说到他是《西北民族研究》的主编,大家都眼睛一亮。那时的学界还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视C 刊,但《西北民族研究》在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领域都是影响力极强的刊物,研究者对其认可度特别高。正因为长期办刊,郝先生特别注重学术热点问题及学术发展的新趋势。这也影响了我们的学术选择。20 世纪末21 世纪初,民间文学研究及学科发展都陷入困境,很多学人在学术史梳理及世纪末的学术回顾和讨论中,都提到了这一问题[2],所以大家更关注吸纳了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方法的民俗学。最近,我看到王铭铭发表于《读书》2022 年第5 期《新中国人类学的“林氏建议”》一文,感触很深,他提到学者“广泛存在着对‘创新’的过高‘期待’或过度‘自信’……吾辈误以为社会科学化可等同于‘创新’本身,另一个,则通过对自然科学进行‘圣化’诱使吾辈抛弃本有的理性”。而当时的自己还谈不上是学者,只是一个学习者,但热衷于看到民俗学“社会科学化”发展趋势的成果,而对以文学为主要范式的民间文学则暗含“歧视感”。我希望自己的博士论文能以山西南部民间信仰作为研究选题,一来当时民间信仰研究是学界的热点,无论是人类学、民俗学,还是民族学、历史学都很受关注,再加上晋南历史文化悠久,民间信仰多样、驳杂,历史层累特征显著,在国内外学术界都引发了很多讨论。当时觉得这一话题既有学术价值、很前沿,并且和国内外研究都很接轨,此外也在自己的舒适圈内。我从2001 年开始就跟随山西师范大学的段友文老师在临汾、运城一带调研,特别是2002 年博士入学前夕,我们一起带着学生到万荣进行暑期实践,重点对万荣后土信仰进行调查。这次调研跟随段老师学到很多,同时我也开始觉得田野调查很有意思,曾经的硕士课程《田野调查方法论》到调研时才真正体会到所说的参与式访谈的魅力。调研很辛苦,但是同学们的欢声笑语和他们迷失在黄河滩时我打了个“三轮车”去营救他们的情形犹如发生在昨天。2022 年8 月,在参加“泰山庙会调查与研究专题研讨会”时,郭俊红博士(现在山西大学工作)也提到当时的很多难忘场景。9 月参加她主持的山西万荣后土娘娘调查汇报时,我们又共同回顾了一起参与的很多调研。现在,她已经成长为这一领域的年轻学者,我更多是向她学习,万荣、后土的影像也永久地留在了我的脑海中。

2003 年9 月,本 文作者(右三)跟随陈勤建先生(右一)到浙江宁波鄞州区高桥镇调研
2003 年,秋后的上海依然很炎热,我和陈勤建老师在对外汉语系的办公室谈自己对毕业论文的一些想法。窗外的热浪时不时扑到我脸上,我语速极快地说完了自己的想法,陈老师看出了我的紧张,安抚我说:“别着急,咱们想清楚了再说。”陈老师是上海人,但他又在黑龙江兵团呆过,所以很多学界老师说他是“南人北相”。他一直对学生都很温柔、包容。同届的三位同学周晓霞、柯玲、华霄颖读书时就已经是副教
授了,所以老师对待我们更多是研究者之间的平等交流,但我跟她们三位距离很大,她们都是成熟的学者,研究方向确定、研究成果也丰硕。与她们相比,我的学术基础不好,研究方向也不够清晰,但陈老师从来没有给过我压力。在毕业论题的交流中,陈老师说:“对于田野调查,从80 年代我就在江南一带跟着中国民协、上海民协一起调研,也与日本民俗学者合作一起完成了江南稻作文化区民俗调研。这两年你也跟着我到浙江上虞、宁波进行了梁祝调研,并参与了同济大学建筑学阮仪三主持的古建调查工作。但是我觉得你选择山西南部调研,没有对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的研究更合适。在民间文学学术史梳理中,延安这一段大家都没有关注。我当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钟敬文先生处访学的时候,他就强调要对这一时期进行细致梳理。再加上贾芝老你也熟悉,要不你关注一下延安时期的民间文学如何?”就像父母最了解孩子一样,老师也是最了解学生的。日常似乎老师也没有跟自己过多交流,但总能一下就点到自己的关键。经过老师的点拨,我开始回顾自己对学术史的关注,当时阅读了《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1918—1937)》(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对赵世瑜老师从问题史出发对学术史进行梳理非常感兴趣,但赵老师的历史功底及对史料的掌握能力是我没办法学到的,所以没敢想过以此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在2002 年至2004年间,文学史领域也非常注重对晚清以降文学刊物、社团的研究。我记得2003 年听过陈平原先生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连续讲授的两周文学史课程,每次中文系会议室都挤满了学生,间或有接触,可是自己没想过这一方向。后来,在陈勤建老师的提点和鼓励下,我开始搜集、整理民间文学学术史资料,撰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对“民间”概念的梳理。在撰写过程中,陈老师为我提供参考书,并让我关注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领域对“民间”概念的引入[3],他强调我们如何将民俗学、民间文学视域中的“民间”理念及其概念流变呈现给学界,并形成与当代文学领域的对话。当时我的能力当然达不到,但也是这个契机,让我开始学会了史料耙梳。我撰写了《20 世纪民俗学视域“民间”概念的流变》一文,并以此文参加了2003 年11 月22 日举办的“中国民俗学会成立20 周年纪念会暨2003 年年会”。在这次年会上,高丙中老师提交了《民间、人民、公民:民俗学与现代中国的关键范畴》一文,我们在同一专场,并对“民间”进行了讨论。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参加学术讨论,会上可以说语无伦次。我记得高老师以一贯犀利的风格问我,所谓“民间”与陈思和等学者在文学领域提出的概念之间的异同。依稀记得当时周星、郭于华两位老师为了缓解我的压力,紧跟着问了一些解围的小问题,老师们的友好让我自如了许多,但是依然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正如周老师在会议问答中所说:“大概等毛巧晖博士论文写完,这个结论就出来了。”如果说1999 年我第一次参与筹办学术会议,是与“学术”的第一次相遇,2003 年的学术会议我才真正开始走入“学术”。老师的谆谆教诲、学术前行者的提点让我开始对自己的博士选题有了一定的体悟。但对于这一话题的热情似乎尚未点燃。2004年上半年,我到北京访谈贾芝老。因为贾老年事已高,所以访谈及大量资料查找工作都是在金茂年老师的帮助下完成的。金老师帮助我联系中国艺术研究院,让我有机会见到吕骥当年在延安鲁迅艺术研究院调查民歌的手稿。金老师还将贾老延安时期的日记帮我找出来,看着当时年轻知识人走进延安后的生活点滴,虽然物质极端贫瘠,但是他们的精神富足;日记中记录的阅读书籍、秧歌剧等,一幅幅延安的生活画卷映入我的脑海。更让我震惊与感动的是,贾老当时记忆并不是很好了,可是只要问到延安,他就会唱起“猪啊、羊啊,赶到哪里去”及一些信天游民歌,延安的生活刻在了他的脑子里,形成了磨灭不掉的“记忆”。贾老的弟弟贾植芳先生更是经常跟我讲起三四十年代的文艺界轶事及五六十年代自己的一些遭遇。最初到上海读书,我很少去贾先生家,因为总觉得除了他是我祖母的二哥之外,跟我们家几乎没有联系,而且贾先生家里总有很多人,随便一位都是著名的学者、作家,要不就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硕士、博士生。生性木讷的我,不知道该如何跟大家打招呼。博一第二学期的某一天,突然接到桂芙阿姨的电话,她说贾先生让我周末到家里吃饭。去了后,贾先生跟我说:“你怎么不来啊,这是连亲戚都不走了?”瞬间感觉到他就是我二姥舅(老家称呼祖母、外祖母的兄弟为姥舅)。从我告诉他自己的博士选题后,他会从家里收到的各种刊物、著作中整理出我能用的资料,等周末我去了,再让桂芙阿姨打好包让我带走。贾先生这种整理资料的方式对我启发很大,特别是有一次我帮他整理过一个口述材料,他很严肃地提醒我:“你的写作缺乏历史逻辑,不注重时间序列。”所以,后来我的所有写作都非常注意行文中的材料和时间顺序。可能很多做学问的方法,都是在日常言谈中慢慢接受和吸纳的,这些不仅仅是知识的学习,更多是从事学术研究的规范和方法。其实自己是有很好的外围条件的,就是贾老提供的第一手资料,可能很多人都难以获得,以及贾植芳先生的很多历史讲述和他在闲聊中的“知识批发”,更是让我受益无穷。但博士论文的进展并不像预想的那般顺利,论文的调研、撰写都在疙疙瘩瘩中推进着,而且当时很多人不理解延安时期的民间文学,记得有学者跟我说:“延安时期有民间文学吗?”他言下之意就是当时的民间文学都是作家写出来的,这可能在很多研究现当代文学的学者眼中都是如此。延安文学,确实只有真正耙梳过资料,了解其文本内容的人才会真正认识到它的意义与价值。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论文都停滞在对何其芳《论民歌》的分析上,往往都是对着电脑一坐就是一上午,但也没写出几个字来。陈老师怕我压力太大,很少主动询问我的论文进度,宽松的环境并没有减轻我的写作焦虑,甚至一度都认为自己要延期毕业了。每次都想,自己做这个选题是不是太难了,我对文学不了解,那我写的新秧歌运动、韩起祥说书,特别是对李季《王贵与李香香》的分析是否能被学界接受?我还要继续写何其芳的民间文学研究吗?当时检索资料虽然还没现在方便,但是一到图书馆也能看到何其芳研究的书有整整一书架。我应该如何处理这些资料?如何从民间文学的角度分析?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转机就是到日本的访学。

2002 年3 月,本 文作者及女儿与贾芝先生(左二)、金茂年女士(左一)、贾植芳先生(右一)在贾植芳先生家中合影
2004 年12 月,得益于陈老师与神奈川大学的学术合作,我得到了到日本短期交流的机会,联系老师是佐野贤治,当时也第一次见到了福田亚细男。在交流期间,我和北京师范大学前往交流的韩同春一起参加了神奈川大学的博士生课堂交流,尽管语言不通,但是从展示的图片中,看到了他们民俗学的研究传统。这次交流不仅开阔了我的学术视野,更多则是了解到他们也很关注民间文学学术史,记得当时跟随福田老师读博士的王京(现任教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他的博士选题是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中日民俗学交流。这加强了我对选题的信心。从日本回到上海后,我携带着从日本复印的大量材料,又重新投入论文的撰写。很幸运,我最终克服了拖延症,在2005 年4 月完成了论文写作。当然,博士论文写得并不完美,而且当时对很多问题的梳理并未理清,但当论文写完的时候,我却真正喜欢上了民间文学。我在博士论文答辩的致谢中,除了感谢老师和同门的帮助外,我特别感恩老师把我带入到了民间文学学术史的研究领域。后来,我到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与合作导师郑元者教授协商后,决定继续完成民间文学学术史梳理,重在关注20 世纪下半叶民间文学思想史的探讨。自此,我的研究方向完全确定了下来。
我进入民间文学的经历,就像王维在林间遇到乡村父老一样,这一方向的选择有着这种小确幸,但绝没有徐志摩“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那种潇洒的情感。当然,一切偶然中都有必然。当回头再看的时候,所有的艰辛都是收获与经验,而身在其中之时确实曾很无奈和心酸。之所以愿意拉拉杂杂地将自己进入民间文学研究的经历写出来跟大家分享,并不是觉得自己在这一领域研究有多出色,而是想将自己从初涉学术到学术方向的选择的过程跟大家交流,希望年轻学子能规避我学习和科研中的一些弯路,同时也想让大家看到一位女性学术从业者的艰辛(或者有人认为是强说愁吧)。
注释:
[1]参见安德明:《家乡——中国现代民俗学的一个起点和支点》,《民族艺术》2004 年第2 期。
[2]参见刘守华:《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百年历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 年第3 期;纳杨:《让民间文学研究走出困境》,《文艺报》2001年12 月 22 日。其他很多学者包括笔者都曾撰写相关文章,特别是近年来学术史回顾中涉及者更多,在此不一一列出。
[3]一般认为,“民间”概念进入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领域是从陈思和的《民间的浮沉:对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上海文学》1994 年第1期)、《民间的还原:“文革”后文学史某种走向的解释》(《文艺争鸣》1994 年第1 期)及《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开始。之后,王光东等对文学领域的“民间”话语继续进行了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