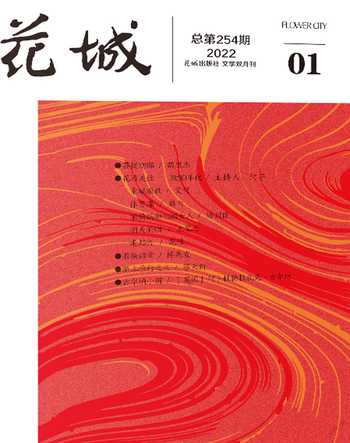古尔纳小辑
[英国]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
余静远 译
我第一次听说那幅地图,是从一个老师那里。这并不是他应该告诉我们的知识,但我觉得他有时对要做的事感到厌倦,就会转向其他话题。他是镇上一所小学的老师,且素有博学的名声,但他并不是我们正式的老师。他的名字是马林·哈桑·阿卜达拉。最近,他搬到隔壁,租住在我们邻居阿卜杜拉曼叔叔和法特玛小姐①楼下的一间房里。我们是出于尊敬才称阿卜杜拉曼夫妇为叔叔和阿姨的。他们没有子女,住在房子的上面两层,房子底层就空着。阿卜杜拉曼叔叔也是一位老师,但地位更高。他在一所英文授课的中学教书,还在坎帕拉②的麦克雷雷大学学习过。那时,几乎所有的中学老师都是欧洲人,与这些传说中的人物做同事,让阿卜杜拉曼叔叔有了某种魅力。他与马林·哈桑肯定更早的时候就彼此认识了,也许年轻的时候还一起念过大学呢。
去马林·哈桑那儿学习,是母亲的主意。我们对额外的补课没有明显的需求。我们没缺过课,也没掉过队。小孩缺课掉队的情况会时常发生,比如,陪着父母去拜访亲戚啦,或者生病啦。那时的小孩生病可不是几天的事,而是一病就好几个月,等回到学校时,已比所有的人都落后一大截了——所有的人,除了那些顽固抵制学习任何东西,并将此视为荣誉和名声的人。父母对我们的事业也未有过那种令人生畏、需要持续训练的理想,不像学校那几个印度男孩的父母,早早就将他们送去额外培训班,期盼着他们以后成为医生或律师,或者数学方面的天才。
父母从未想过我们要如此荣耀,可他们同样也没有理由担心我们的学习。弟弟哈吉毫不费力就能做到学业出色,至少老师们都喜欢他、夸奖他,他也有很多朋友。哈吉比我低一年级,老师们却督促我向他学习,脑子灵光点,而不是鞭策他以我为榜样,学习我的勤奋。我是一个辛勤认真、做事慢吞吞的人,什么事情都需要解释得清楚明白,且每走一步都犹豫不决。人们有时纳闷我们俩谁才是哥哥。
至于妹妹兰达,她才刚开始上学,当她听说我们要去法特玛小姐家补课时,她也要求参加,在她还是个婴儿时,法特玛小姐就宠着她,是她最喜欢的阿姨。
我不清楚父亲对下午去补课这事儿是怎么想的。他不止一次地告诫我,要我睁大眼睛,更善于观察,保持自己的机智。又是那套我在学校必须忍受的陈词滥调。你必须对这个世界更加警觉,他告诉我。但他可能并不指望马林·哈桑教我如何做到这一点。总之,我不再琢磨我们为什么被送到马林·哈桑那儿了。我猜,母亲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能够展现她作为一个母亲对我们教育的关心。父亲并不总是像她那么有热情,甚至抱怨过我们从学校带回家的有些知识一点用都没有。学习英文摇篮曲或听那些贪婪的探险者吹嘘到底对谁有用呢?母亲认为,学校就是知识,虽然她对什么有用什么没用有自己的看法。英语和算术是有用的,学好了它们,我们就能继续念中学了。总之呢,我们隔壁住了一个老师,据说他读过的书比这个国家任何其他人读的书都要多,而且,他还有时间。
在成为我们老师之前,我就认识马林·哈桑了。他从来没跟我说过话,但是,如果有一个陌生人问我他是谁,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出他的名字。我还知道,他有时会在一个管弦乐队里弹奏乌德琴①。有一年,父亲给我们买了节日②音乐会的门票。音乐让父亲头疼,而且塔拉布③歌曲中爱情的痛苦让他感到难为情,他就没去。马林·哈桑那晚就在管弦乐队中,与其他的音乐家一样,他身着黑西装,系着领结,穿着一套在别的时候不会有人穿的服装。这种着装模仿了埃及管弦音乐的表演,他们穿成这样来表达新潮。无论是音乐还是服装,埃及管弦音乐表演团体都對塔拉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马林·哈桑身上有一种严肃的东西。他孤僻,疑心重,说话时声音透着尖刻,却尽量不去冒犯他人。走路时他眼眸低垂,跟人打招呼时拘谨,甚至稍稍有些急躁。这与别的男人不一样,他们会不停地跟人打招呼,会为了握个手而横穿马路或从自行车上跳下来,会在大街上大声地说笑。傍晚的时候,他们坐在咖啡馆里,交谈、争辩、闲聊,与世界接轨。白天凉爽的时候,他们就住在大街上,就像住在自己家里一样。为此,出行时最好避开某些街道。与别的男人不一样,马林·哈桑不大声说话,也不夸张地大笑。父亲也是如此,因为他认为这种粗野有失体统,父亲从未对任何人任何事提高过嗓门。他最爱的就是在咖啡馆里消磨数小时谈论政治,马林·哈桑有时也会经过咖啡馆,逗留一阵,喝上一杯咖啡,然后离开。
现在,当我回忆起他,并试着描述他时,我想起了这些细节。当他搬到隔壁房子里时,我没怎么注意。人们经常那么做,租下底楼的一间房独自生活。或许是他们在镇上工作,家人住在乡下;或许是家里空间有限,兄弟姐妹、姑姑阿姨、各种堂表兄弟姐妹太多,空气中充斥着斗嘴和责骂;或许是其他复杂的原因使他们独自生活,为了更自由地呼吸,或为了以一种他们喜欢的方式生活。
我估计,有人告诉过父亲,要他负责相关事宜,且在酬劳上与母亲达成一致。像往常一样,在这件事上,他们也许有过争执。母亲是众所周知的软心肠。邻居和亲戚只要讲到他们的不幸,母亲就会哭成泪人,然后就把不该送的、送不起的东西都送了出去:她最好的肯加衣裙④、她的珠宝、我们的晚餐。父亲的反应在恼怒和难以置信的大笑间波动,可母亲就是控制不住。我一开始没意识到,后来我就想,这额外的补课对我们小孩来说是好事,对马林·哈桑是不是也一样是好事呢。无论如何,某个下午,我们去上课了。
上课的房间在房子的前面。房间有两扇上了锁、从地板一直延伸到了天花板的窗户,一扇在正前方,另一扇在侧边。两扇窗户的百叶窗都大开着,午后的光线流泻进房间。房间有四把靠墙放着的硬木椅子,一张摆在侧边窗户下的小书桌,我们到的时候,马林·哈桑正坐在书桌上面。房间更像是政府办公室,而不是起居生活的空间,极简,毫无装饰,混凝土地面光秃秃的,没有垫子,没有毛毯。乌德琴靠墙放在架子上。
我曾经很喜欢新学年与新老师见面时的忐忑不安,可是马林·哈桑低垂的目光和短短的胡子,使他看起来既悲伤又令人望而生畏。第一次上课,我心情沉重,在房间的门槛处踢掉了凉鞋。我们被要求带上学校的练习册,马林·哈桑将我们安置在房间不同的角落里,他简要地看了看我们的练习册,然后给我们布置不同的习题,我们努力做题时,他就守在我们旁边。他说话时,声音低沉、犹疑,就像好长时间没说过话一样。我们互相间不说话,也几乎没有眼神交流。这种紧张的情况持续了三节课——我们两周去一次——第四次到的时候,我们发现百叶窗放下来了一半,遮住了午后的光线。进门处还铺着一张小羊绒毯。也许强烈的光线和光秃的地板是为了给我们一个下马威,让我们不敢反抗,当一切都再明显不过了,我们很顺从,完全被震慑住了,他才让氛围柔和下来。
妹妹兰达这时已经放弃补课了,她带着无师自通的愤世嫉俗,哭诉着她遭到抛弃的不幸,母亲根本无力招架。兰达在父亲跟前从来不这样,她会用崇拜去欺骗他,父亲也会回之以宠爱。但她知道母亲无法抗拒她的眼泪和狂怒。那时,我就很想知道,如果兰达一直这么戏谑地对待悲伤,悲伤对其而言变得庸俗无聊后,那么,在以后的生活中,她要如何面对悲伤呢。那个下午,兰达得逞了,可以不用去补课。反正补课对她来说也只是一种消遣,因为她不愿意落下任何事情。
那天下午的课上到某个地方时,马林·哈桑决定来一个拼写测试。我喜欢拼写测试,不是因为我很擅长,而是因为拼写测试花的时间很长,而我喜欢交换练习册给别人打分的场面。哈吉非常擅长拼写测试,但他那天也被马林·哈桑给的一个单词打败了,像我一样。那个单词是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哈桑对我们的无知报以微笑,说,伊斯坦布尔。在被称作伊斯坦布尔之前它被称作君士坦丁堡。他让我们正确地写下这个单词并大声念几遍。这座城市是以一个伟大的罗马皇帝命名的,他告诉我们。这就是那个名字的意思:君士坦丁的城市。然后他告诉我们,这座城市于1453年陷落了;防守者们如何英勇抵抗,抵抗持续了多长时间,他们如何阻止奥斯曼的海军进入博斯普鲁斯海峡,他们在海峡的入口处,修建了一排水栅栏;“征服者”苏丹穆罕默德如何将船只放在涂油的圆木上旋转,经由陆地把船只运送到黑海,从后面把这座城市拿下了。哈桑告诉我们,这座城市的陷落既是胜利也是悲剧。那次上课之后,我们每堂课都去,企盼着马林·哈桑会厌倦英语和算术,陷入博学的沉思当中去。
他并不经常给弟弟哈吉讲他的故事,几周之后,哈吉开始逃课了,我和他都没告诉母亲。马林·哈桑问起哈吉的时候,我就扯一些勉强说得过去的谎。就我俩时,他似乎更自在一些。他皱眉的时候少了,当我做着他布置的作业时,他就坐在书桌上看书,有时候练习乌德琴,一旦我表现出很感兴趣的样子,他会立即停下,所以我低着头,假装没注意。一边磨蹭着做他给我布置的冗长的作业,一边听他练琴,真是愉快的时刻。他把好书都放在另一个房间,上课时,在书桌上放着一本,有空了就读几页。他笑得更多了,谨慎的、不情愿的微笑让他的表情有了变化。他叫我名字,并问一些跟我相关的问题。问我参加什么体育活动啊,他曾经非常热衷于游泳,他说,不过那都是年轻时候的事了。当我告诉他,我很喜欢上学时,他对着我笑了。
我与马林·哈桑越来越熟悉后,他对我也不再那么嚴厉,我试着从他嘴里撬出点故事。海洋经常出现在他的故事中。那天,他跟我说了那幅地图。第一天上课,我就注意到了那幅地图,地图是棕金色的,镶了框挂在墙上。那幅地图和一些看起来像是毕业班级的照片,是那间炎热又空荡的房间里唯一的装饰品。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知道地图上那凸出来的轮廓和小旗帜是什么意思。世界充满了图像,它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可以解释的,我猜,虽然不是很确定,它们大部分都跟人的信仰有关。裁缝店里,有一幅大象头的胖男人画像。理发店里,有配了框的乌尔都语文字,文字鼓起的地方放着星星和月亮的图片。宗教书店里有带翅膀的种马和交叉弯曲的军刀的图片。日历上,有八条胳膊的女人、大胡子的男人、巨大的建筑,还有用不同字母组成的单词和数字。一幅美丽的、凸出的地方是棕金色的图画不算什么。我想,总有一天他会告诉我的。10月一个炎热的下午,我正读着他给我的一篇文章,一桩无法忍受的任务。我诱导着他,推动话题朝那个方向发展。我全神贯注地盯着地图,头左右摇摆着,想搞明白它的意思。我知道他在看着我,盼着他会忍不住告诉我。
“你知道那是什么吗?”他问。
那时,我一个人上课已经好几周了,也有了一些小小的自由。我站起来,走得离墙更近了些。我在地图前驻足良久,突然,我认出来,那是一幅粗糙的、挂反了的世界地图。是非洲的形状给了我提示。“是一幅地图,”我说,“为什么它是反着挂的?”
看着我急切的样子,他笑得很开心。“他们那个时候就是那么制作地图的,”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地图制作者名叫弗拉·马洛,一个住在威尼斯潟湖岛上的修道士。他哪儿也没去过,就在岛上制作了这幅地图。那时,我还没有听说过威尼斯,不知道潟湖是什么,也不知道修道士是什么。我跟马林·哈桑说了这些,他往后仰了仰头,对我的一无所知笑了。然后他跟我讲威尼斯和弗拉·马洛所在的穆兰罗岛。他讲起这些地方,似乎对这些地方很熟悉的样子。根据旅行者们的描述,弗拉拼凑出资料,制作出了这幅准确率比之前所有地图都要高的世界地图。我那时就觉得,弗拉·马洛肯定与马林·哈桑有一些相像之处,虽然我的老师并不知道如何制作世界地图。但就像弗拉一样,他也是一个生活在想象中的人,一个在自己的思绪中游走的人。我十分肯定,马林·哈桑从未到过威尼斯。如果他去过的话,我们一定会知道的。别说威尼斯了,如果说他到过温古贾岛以外的其他地方,我都会大吃一惊。人们来来去去,你总是能知道哪些是旅行者,从他们自信、不露声色的神气、他们的言谈中看出端倪。你也总是能一眼就看出哪些人从未到过外地,马林·哈桑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虽然他讲的很多故事都与海洋有关。
下次再说到地图时,他告诉我上面的标注上写着从各种渠道得来的关于遥远地方的信息。在这张复制的地图上你看不清楚,因为地图太小了,标注又是用拉丁文写的,他说,他也不懂拉丁文。然后他想起我是为何而来,就又让我接着去做那被打断了的、冗长的除法练习了。
可他总忍不住提起地图,第三次提起地图的时候,他告诉我其中一条标注的内容。关于一艘被暴风雨吹到黑色海洋的轮船,阿拉伯人称那黑色海洋为大西洋。轮船从穆卡拉①驶向黑色海岸的那个上午10点左右,他们看见天上挂着一轮灰白的月亮。船上的乘客,有去那边与丈夫团聚的女人,也有想去那片绿地发财的男人。其中一个女人说,灰白的月亮预兆着不好的事情。每个人都知道预兆的力量,那个女人说,智者们最好注意点。需要做的事情千万不能不做。那些听到她说这话的人尖叫着要她闭嘴,不要把坏运气带给他们。但是一切都太晚了,预兆已经出现了。几天后,狂风将他们吹到了遥远的海面上,他们没法把轮船掉转向海岸的方向。他们能做的只是往南越漂越远,祈祷着风会转向,让他们掉转西行。等到终于掉转过来后,他们才意识到,轮船航行得太远,把陆地远远抛在了后面,早已过了非洲西南角了。那时,没人确切地知道,非洲还有一个西南角。命运抛弃了他们,40天,除了天空和海水,他们一无所见。根据船长②的推测,他们朝西航行了2000英里,无疑将面临毁灭的结局。当天气的高压渐渐平息后,他们掉转船头,往回又航行了70天。回程中遇到了寒流,寒流把他们逼到了波涛汹涌的海岸处,直到他们奇迹般地被冲刷到了海洋中间的一个群岛上。整个地平线都是这个岛地。这时,只剩下五个人还活着。其他所有人都依照神的旨意,在饥渴和疾病中死去了。存活者中有那个看到了预示着凶兆的、上午10点的月亮的女人。她在旅途中疯掉了,也许是假装疯掉了,她害怕自己会因为带来了厄运而被丢到大海里去。剩下的四个人是水手,他们习惯了海上的艰苦。那个女人总是不停地讲到一个小男孩,她把小男孩留在了穆卡拉的邻居家,她为他的命运哀悼痛哭。他们着陆的那个群岛,很可能就是科摩罗岛①。没人知道这五个人上岛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但肯定是他们中的某个人把他们苦难的遭遇流传了下来。
“我一直在想着那个画面,天上挂着一轮上午10点的月亮,一艘从穆卡拉出发的轮船,载着担惊受怕的船客。”马林·哈桑说。
“一条小小的标注能告诉我们那么多吗?”我问道。马林·哈桑皱了皱眉头。我没想到还有存活者,我说。在波涛汹涌的海上漂泊110天是史诗的素材;什么样的轮船能够经得住呢?一艘桑布克②,他说。船舱里有多少乘客呢?他们吃什么?他们怎么能在一艘只有部分甲板的船上存活那么长时间?如果没有存活者,弗拉·马洛又怎么知道在黑暗之海上的40天和回程的70天呢?想想看,要是他们没有回头,而是一直航行穿过黑暗之海呢?
但是,我看到马林·哈桑已经心不在焉了,也许对我乏味的疑问不耐烦了。也许他期待着我对他的故事有不一样的反应——他似乎对我着了恼。他皱着眉头,看向了别处。“你最好在走之前完成概要③。”他说。
他糟糕的心情并没有持续很久,那天下午下课之前,他又聊起了地图:中国和阿拉伯地图上的印度洋;基督徒地图上的西亚总是将耶路撒冷放在世界的中心。我想问他,他是怎么知道这些的,但我不想再引起他的不快。肯定是他博学的一部分。我走的时候,他递给我一张便条。便条折成了一个小正方形,边角都折进去密封好了。“把这个给你的玛索达姑姑。”他轻轻地说,垂下了眼睛。“但不要当着别人的面。”
玛索达姑姑并不是我的姑姑。她是我父亲的侄女,所以算我的表姐,父母都将她看作我们的姐妹。几个月前,丈夫与她离婚,她搬来了我家。她的父母也离婚了。她父亲租了一间底楼的房间,一个人住着,母亲再嫁,搬到坦噶④去了。我父亲是她母亲的哥哥,从我记事时起,她母亲和她就经常来我家做客。每隔几个月,她们中的一个就会过来住一段时间,一连几日或几周都不走。玛索达这次来住,也不例外。这意味着不同的生活作息、新的八卦、客人餐食——至少短时间内。然后是等待客人离去,你可以要回自己的床,恢复正常的生活作息。我们喜欢玛索达姑姑,我们从小就一块儿玩耍,她总是说一些邪恶的事情,在背后笑话别人,有时还说脏话粗话。她看起来特别健美,黑色的皮肤发着光,走在街上时,男人们有时会多看她几眼,她也不遮挡着脸。离婚时她肯定已经二十出头了,但是在那之前我们就知道她的婚姻有麻烦,因为她来我们家,跟母亲讲起有暴力倾向的丈夫时,经常把我妈弄得泪眼涟涟。最后,夫妻无法忍受彼此,在事情处理好之前,玛索达搬来我家暂住一段时间。
我知道马林·哈桑给了我什么,一张让小孩转交给其女性亲戚的秘密便条只可能是一封情书。即使是像我这样驽钝的小孩都知道。我没看马林·哈桑,把便条放入衬衫的口袋就走了。我回家放下书,谢天谢地,哈吉不在家,要不然我肯定会告诉他便条的事了,他也肯定会飞奔着去告诉母亲。我需要点时间想想该怎么做。如果我把便条交给玛索达,她又写了一封回信要我转交的话,我会扮演一个可恨的角色。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知道这个的,但是我知道一旦我被发现了,父亲会鄙视我,母亲则会一连几小时地训斥我。除此之外,我不明白为什么马林·哈桑给玛索达写便条并要我转交有什么不合适的。如果我把便条交给母亲——这也正是我非常想做的——我自己就能从这责任中解脱。母亲可以决定是把便条给玛索达呢,还是把它交给父亲,让他将之撕碎。我把便条藏在枕头里,然后出门去了,看看有什么我能够参与的事儿。
我觉得最安全的做法是扮演无辜者,尽量随意地把便条塞给玛索达,就好像我根本不知道这事有什么好禁忌的。可是,最终我却搞砸了。晚饭后,母亲和玛索达在前厅里聊天,父亲到他的卧室里去读书或听广播了。那天晚上,有那么一小会儿,我看到玛索达一个人坐着,我想,我的机会来了。我回到卧室,从枕头里拿出便条,飞快跑到前厅,我胳膊朝着玛索达半伸着,她看着我,被我的突然的动作吓住了。当我听到身后有声音响起时,我知道母亲回来了。我收回胳膊,试着用手掌把便条遮住。
“那是什么?”母亲问,伸手过来抓我的手腕。在母亲抓住我之前,我把便条递给了玛索达,用的正是马林·哈桑提醒我不要用的方式。玛索达从我手中一把抓过便条,把它放到了裙子的口袋里。我想,她们俩都知道了,我递给玛索达的是某个男人的情书,我几乎能听到她们的头脑在思考,在推演。“谁给你的?”母亲问。
过了一会儿,玛索达笑了起来。她把手伸进裙子的口袋,展开了便条。她一边看一边笑得更厉害了,当她看完后,她大笑起来。那种嘲讽的大笑,只有女人才笑得出来。我不知道该如何形容那种笑,当我在街上经过一群女生时,经常听她们那样笑,这会让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可笑的男人。玛索达对着马林·哈桑的便条也是这样笑的。
这时,母亲抓住我的衣领,逃跑是不可能了。“谁给你的?”她问,从玛索达的笑声中她已经猜到了便条的内容。我不吱声,母亲突然给我的后脑勺来了一记猛击,我毫不犹豫,脱口说出了马林·哈桑的名字。母亲坐下来,仍旧抓着我。“他想干什么?”她问玛索达。
玛索达耸了耸肩,笑了:“胡言乱语。你能想象吗?谁想与那个可怜的男人有关系啊?他还有他的那些书。他怎么敢?简直是疯了。”
然后她将便条撕了又撕,碎纸屑落在她的脚边。做这一切时,她脸上那种嘲讽的神情让我觉得自己是個浑蛋,就好像我是故意要这么对马林·哈桑似的。母亲更用力地抓着我的衣领,我能感受到她的紧张。母亲想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而且要知道每一个细节。她想知道马林·哈桑是否对我说了一些不合适的话,是否碰过我,他教了我什么,那天下午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给我便条时说了什么。这些问题被母亲催促的敲击和玛索达嘲笑的旁白不时打断,在这期间,玛索达还去把门拴上了,这样我们就不会被打扰了。当我告诉母亲那幅地图,还有那艘出发时天空挂着一轮上午10点的月亮的轮船,以及它的悲剧结局时,她松开了抓着我的手,似乎我最终解释了什么事情。
我再也不被允许去马林·哈桑那儿了。当我在街上看到他时,他像往常一样,严肃地回应我的问候,但没有问我为什么不去上课了。便条事件几天后,玛索达搬走了,去了坦噶她母亲那儿。离开的那天,她用右手捏着我的下巴说:“你知道便条里写着什么吗?尽是些胡言乱语,他从书中看到的某种污秽的歌曲或魔咒。你要保持自己的机智。”她说,“小心别人给你的东西。”
几个月后,母亲告诉了我其他人都知道的一件事。很多年前,在一次从蒙巴萨①到科摩罗岛的航行中,马林·哈桑的全家都在海上淹死了,他的父亲是唯一的幸存者,因为还未从高烧中恢复,他被留下来交给邻居了。后来,他很年轻的时候就死了,他的妻子改嫁后搬到岛的南边去了。马林·哈桑从十几岁就开始一个人生活,对任何人都没有用处了。亲友的逝去让他人生中所有的舒适都变得苦涩,母亲说。
他还有书呢,我说。
书有什么用,母亲说。孤独让他生病了。
玛索达走后不久,马林·哈桑也搬离了租住的房子。我不知道母亲是否跟法特玛小姐说过什么,即使她说过,我也不会惊讶。我觉得她也深感不安,因为她允许自己的孩子跟一个会写便条给一位体面的女士的男人接触。一个月后,我参加中学的入学考试,考出的成绩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父亲说,我应该问问马林·哈桑搬到哪儿去了,要我去感谢他,所以我估计,父亲还不知道被拦截下的便条这个小插曲。
责任编辑 李嘉平
①原文为斯瓦希里语Bi Fatma。
②非洲国家乌干达首都,位于坦桑尼亚北部。
①原文为土耳其语ud,是北非、西亚和中亚等地区使用的一种传统拨弦乐器。
②原文为阿拉伯语Idd,节日的意思。
③原文为阿拉伯语Tarab。在阿拉伯语世界里,Tarab指的是让人听了精神愉悦的音乐,是和神沟通的音乐。
④非洲东部妇女的节日服装。
①阿拉伯半岛西南端国家也门的最大港口。
②原文为nahodha,斯瓦希里语。
①非洲一个位于印度洋上的岛国,位于莫桑比克海峡北部,莫桑比克和马达加斯加之间。
②中型阿拉伯轻快船,较大,船体相对偏薄,窄长。
③原文为法语pre’ cis。
④坦桑尼亚东北部一港口城市。
①肯尼亚第二大城市,东非最大港口,位于肯尼亚东南部沿海,东临印度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