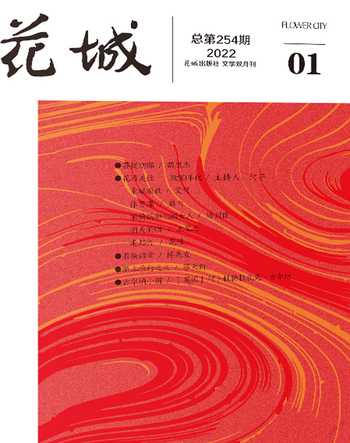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非洲性”
访谈选自《英国穆斯林小说:当代作家访谈录》(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11年版)。这本访谈集的作者是英国约克大学全球文学教授克莱尔·钱伯斯(Claire Chambers)。这个集子里的采访对象主要是出自伊斯兰教信仰或文化背景,旅居英国,用英语创作,小说具有较高艺术价值和影响力的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是受访者之一。采访话题涉及古尔纳早年从事写作的经历,文学创作主题,对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的批判,对东非社会的反思,自己所受的文学影响,对自己作家身份的定位,等。古尔纳强调文学写作的复杂性,不愿意将自己归入某种理论立场或流派,他的批判矛头不仅对外朝向前宗主国的种族歧视和殖民主义话语,更是对准了多民族、多种族地域普遍存在的问题,包括思想偏见与社会隔阂。古尔纳尤其强调要警惕关于非洲性的本质主义话语,认为非洲人在既有的历史事实面前,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今天,应当具有广阔的世界意识,以包容开放的姿态面对各种文化影响。
钱伯斯(以下简称“钱”):你能先从你写作中的迁徙和流离主题谈起吗?
古尔纳(以下简称“古”):我对移民流动不居的状态非常感兴趣。我对它有兴趣,并非因为它是远在天边的反常现象,而是因为它就是我的人生经验,当代世界的主导经验。我认为这种经验就是居住在一处,但在别处却有着自己的想象生活,甚至幻想生活。对那些只曾在自己国家境内迁徙的人来说,这也是可能的:你可以居住在伦敦,但在格拉斯哥过你想象中的生活。《离别的记忆》是我相当年轻那会儿写的,我试图描写主人公想离开的挫败感,只不过我当时并不想透露过多个人兴趣给读者。我一直感兴趣的是人们的孤立感,即使身在故乡也会产生的孤独感。不同地点、不同时代之间的距离和隔阂赋予迁徙境況某种悲剧性。这种令人痛心的维度是不可避免的,它关乎失去,关乎遗憾:有些事情未完成,没做好,却难以补救。在写作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常在这片区域四处翻找,目的是将移民经历的不同维度戏剧化,获得更深的理解。
钱:你关于迁徙、丧失,以及想象生活的论说令人想起萨尔曼·拉什迪《想象的故土》中的一句话:“过去是家园,却是失落的家园,位于失落的城里,位于失落时间的迷雾里。”这多大程度上适用于描述你与桑给巴尔的关系?
古:拉什迪14岁就离开了印度,而我差不多18岁离开了桑给巴尔,所以他想象中的故土会比我的更加模糊。他可能不同意这一点,但我想说,他14岁离开孟买相对富足的生活,进入英国公立学校,与我以成年非法移民的身份离开桑给巴尔,是有很大区别的。当时以及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桑给巴尔都是恐怖之地。我以为自己知道英国会有多么不同,但到了当地后的体验比我预期的更强烈。而且,我来得不是时候,那是1967—1968年,当时伊诺克·鲍威尔等人正在煽动关于“种族”的狂热情绪。移民问题似乎令人人惊惧。根据新闻报纸,伊迪·阿明①开始驱逐亚裔乌干达人,或强迫他们离开,因此,对数十万来到英国的外国人感到恐惧,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经过很长时间思路才开始清晰起来。尽管我有自己的困难,但仍要应对将他人抛在身后的负罪感,因为我知道身处桑给巴尔有多么艰难。一旦开始不间断地思考,我就想看看关于桑给巴尔,自己还能记住多少,理解多少。这不是浅显的练习,而是需要全身心参与,我意识到有些事情自己记不得了,但不得不虚构出来。当时的写作主要关于曾经的生活经历,“人们试图回忆过去”是我的作品里反复出现的主题。还有一些问题一直盘踞我的内心,包括如何在不疏远读者的情况下书写悲剧,当然,还包括在一种语言和文化里如何再现另一种语言和文化。沉默一直困扰着我。因此,最主要的活动不是回忆,而是与方法和形式有关的问题:你要讲述多少?你要压制多少?我能想到的任何读者,不管是英国人、毛利人还是非洲人,都会对我的读者有望知道的种种抱有期待:我希望人人都能读到我写的东西。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促使我写作的动因,无疑对拉什迪也是一样,所以这一切不仅仅与记忆有关。
钱:既然提到了伊诺克·鲍威尔,你能不能详细描述一下你在20世纪60年代抵达英国的经历以及遭遇种族主义的早期经历?这些经历在以英国为重要背景的书中得到深入表现,比如《崇拜的沉默》和《朝圣者之路》。
古:我对很多关于种族主义的小说和电影都很熟悉,但我在想象中将它定位在某些地方,比如南非和美国各处。然而,到达英国时,我惊讶地发现种族主义是生活如此重要的部分,与它的相遇如此难以预料,又如此接连不断。种族主义并不必然意味着言语侮辱;通常它意味着更微妙的东西,比如侮辱的表情。很难解释这类反应有多么普遍、常见,多么始终如一。距离赋予你驳斥它的能力,但如果你是个年轻人,经常遇到人们在大街上对你大喊大叫,在教室里、工作岗位上、公共交通工具上辱骂你,它会让你疲惫不堪。
钱:你一直在使用过去时,可见,种族主义在多大程度上已经消失或改变了?
古:我跟过去不一样了,所以这个问题说不准。我想,这类事情有一些会落到你头上,是因为你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如何控制自己,如何或何时发怒。也许今天,一个身无分文的陌生人,来自不同的文化,就像当初的我一样笨拙,语言技能同样生涩,他仍然至少会经历一些我曾遭受的种族主义。种族主义并不一定意味着有人朝你扔东西,紧拽你的衬衫或推搡你。但是,当人们的语调、言语或手势流露出怨恨、嘲笑或轻蔑时,我是知道的。我现在没有遇到这种暴力,但不相信它已经消失了。它还在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延续着。
钱:回到拉什迪,你认为“《撒旦诗篇》事件”在多大程度上是对待穆斯林的方式的转折点?从1989年起,宗教和文化,与肤色相比,是否在种族主义话语中占据了更显要的位置?
古:变化是翻天覆地的。过去文化和宗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肤色。有人会听到“巴基佬”这样的侮辱性词汇,但那些人谈论的不是“穆斯林”。我认为你是对的,“拉什迪事件”改变了这一点,尽管这可能只是这些问题上的第一次风波。由于2001年对美国的袭击和反恐战争,现在所谓的“伊斯兰恐惧症”是无处不在的。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之前,穆斯林“令人惊恐”,或是“恐怖分子”,而现在他们已经成为“敌人”。这使得西方人将穆斯林视为危险和不稳定的人群时,毫无愧疚感。各种图片和新闻报道持续汇聚,不可避免地——即使以含蓄的方式——把穆斯林,显然激进的穆斯林——描绘成狂热或极端一族。这使得世人毫不顾忌地说出“他们又来这一出了”之类的话。你也许会认为英国和欧洲知识界大多数自由派会站出来支持《撒旦诗篇》以及创作这种小说的权利,但我想这群人绝不会挺身而出声援伊斯兰教。
钱:你在一篇文章中强调“有些社会……在某些情况下保持伊斯兰教信仰大约千年之久”,你所有小说里都有“伊斯兰之家”的意象,那是高度文明的地方。你反驳沃尔·索因卡的论点,即伊斯兰教在非洲是一股压迫力量,你也驳斥了他的意图,即试图恢复“真正”的非洲性,并表明伊斯兰教长期以来在东非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古兰经》对你写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天堂》中你以互文方式化用了《优素福》。伊斯兰主题和艺术形式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你的写作?
古:嗯,我从小就是穆斯林,所以,想象伊斯兰世界并非了不起的成就:我只需把自己带回那里就可以。正如你所说,我在《天堂》中大力探索这些主题,也许这是我头一回为一本小说展开实质性研究。我想表现“位于人间的天堂式花园”理念,探讨这为何不仅仅是一种表达方式,更近乎一种愿景:一个社会有可能缔造这样的花园。我当时读了不少书,沿着东非海岸旅行了几个星期,只是为了观察一些简单细节,像清真寺和人们的生活方式。我感兴趣的不仅是伊斯兰教这个宗教,还有它在东非海岸文化中扮演的关键角色,而东非海岸一直是我有兴趣书写的地域。我表现穆斯林这个群体时,倒没有一定强调他们是虔诚、遵纪守法、有信仰、务实的,而是突出他们的文化是穆斯林文化。像索因卡那样指责东非人被宗教殖民了一千多年,是没有道理的,毕竟,他们曾主动利用宗教来满足自己的用处和目的。索因卡和其他人常为某种“真正”的非洲立场辩护,而这意味着压制成为非洲人的其他方式,我与这些人的观点屡屡不合。在我看来,把非洲的伊斯兰教说成是外来的殖民势力,几乎可以说是19世纪话语。整个争论表明一种殖民话语试图取代另一种。欧洲殖民主义通过宣称穆斯林不过是奴隶贩子而站稳脚跟,现在听到同样的话语被非洲人自己捡起,多少有些令人惊讶。作为一名作家,我也试图谈论一些通常不被讨论的话题,就像詹姆斯·鲍德温书写关于非裔美国人的著作,或者V.S.奈保尔创作关于加勒比海的小说。据我看来,非洲写作把生活在非洲东海岸的穆斯林排除在外。我无法在小说的镜子中找到自己。因此,我对有关伊斯兰教的写作感兴趣,无关乎宗教本身,而关乎这一点:再现我想书写的那群人的生活。
钱:你在肯特大学的正式头衔是“后殖民文学教授”,你对“穆斯林写作”或“后殖民写作”这样的文学类别有什么看法?
古:我从不认为自己是穆斯林作家,也不认为自己属于任何其他范畴。如果有人对我说——这种情况有时会发生——“你是英国作家吗?”我会说:“你一定是在开玩笑,我怎么可能是呢?”然而,如果人们从某个角度看我,觉得说得通,那也不要紧。我不想就这些类别争论,也许有些类别比其他更适合,但我不这样看自己。我知道作家们总是这么说,但我这样说,倒不是因为不想被束缚手脚,也不是出于某种艺术自由理念,我只是把自己当成阿卜杜勒拉扎克,他住在英国,在大学里教书,写书。
我也不认为自己是后殖民主义者。从后殖民主义角度思考如何组织自己教授的文本,显然是有用的方法。我们发现,关于这些文本,我们可以有共通的表述,但后殖民主义不是一种虔诚的信仰,也不是你可以相信或不信的对象。你可以说,“我是女权主义者”,表明你在性别及其表征方面持有特定的立场,但我无法想象有人會以同样的方式说:“我是后殖民主义者。”不过,在这个节骨眼,我们能够用一个范畴将某些文本聚拢在一起,找到共同的修辞和关注点,也许还能以某种方式建立理论并展开分析,这或许不失为有用的方法。后殖民主义不是身份的一部分,而是一个不错的、包容的术语,它的外延十分宽广,如今可以把它用在任何地方。
钱:天堂意象大量存在于你的作品中,最明显的是在《天堂》中,在你所表现的七重天堂中。卡拉辛加将克什米尔和赫拉特称为人间天堂的说法具有讽刺意味,因为这两个地区如今饱受战争蹂躏,暴力不断。在小说结尾,阿米娜说,“如果人间有地狱,那它就在这里”,讽刺了莫卧儿王朝的皇帝贾汗吉关于克什米尔是人间天堂的名言。所以,你能不能来谈谈那本小说对天堂近乎康拉德式的阴郁描写?
古:小说往往是复杂的,没有单一的视角,但我写《天堂》时感兴趣的一大对象是“一战”前的时期。我对这个背景感兴趣,因为欧洲殖民主义很晚才出现在东非及其沿海地区,大约在世纪之交。1890年,桑给巴尔成为英国的保护领地,1895年肯尼亚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我想看看自己是否能再现那个时期的经历,即让陌生人僭取了对自己社群和政权组织的管控权。我感兴趣的是当时的人们如何理解和应对那时的情势。
我想表现的另一个方面是什么样的社会竟然允许或无法阻止殖民活动。为什么那里的人几乎没有以暴力来拒绝外人的管控?几十年来反抗暴力一直在暗中积聚,不过,如果外人已经证明他们有极其强大的军队,就不需要将它派遣进来了。不管如何,没有抵抗战争的事实表明东非是个支离破碎的社会,因为当地人来自不同的地方,说着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宗教。他们一直致力于协商相处之道,我相信这是宽容的,甚至令人艳羡的社会,没有占据主导地位的群体来决定一切。然而,在这部小说里,天堂却以反讽的手法呈现出来,因为它被压制了,被挫败了。此外,我想表明,这个天堂看似充满善意和礼貌,其间的人显然也有共同生活的能力,但在其表面之下却是丑陋的现实,表现为对其他群体的压迫。
钱:你在《抛弃》中着重表现了来自不同文化的民族混居时会发生什么事情,以及与另一个民族的人交往产生的偏见如何体现在与女性的关系中。
古:乔治·华莱士在1963年到1987年间断断续续当了多年的亚拉巴马州州长,他拒绝让非裔美国人进入曾是白人专供的亚拉巴马大学,并因此出名。法律改变后,他被迫让步,但1963年,他确实曾站在大学门口,阻止一位年轻黑人女性进入。他成为一个全国性的人物,并在多次选举中竞选总统。我记得他接受过大卫·弗罗斯特的采访,后者问了他最关键的问题:“你会允许自家的女儿嫁给非洲裔美国人吗?”这个问题涉及家庭关系,其实是“你的种族歧视到底有多深?”的委婉说法。女性承受着种族歧视的首要伤害,因为她们被视为男性的财产。女人也是你的男子气概的象征,因为保护女人的能力体现了你的荣誉和雄风。是否能确保你的女人们不会做她们一直想做的“恶心”事,反映了你是不是真正的男人。
钱:你很敏感地处理了本族内部的人参与奴隶压迫这个严肃问题。在《离别的记忆》中,有个角色被描述为“原奴隶监工的孙子”,这意味着他是一个“地位显要的人物”。欧洲奴隶贸易的暴力显然超过了任何本土机构,但你也描述了不同社群里反印度、反阿拉伯、反非洲的偏见。
古:的确,如果你要在某种程度上忠实地描写东非,就无法避免这一点。本族内部的紧张关系不是人们喜欢谈论的话题,因为我们喜欢认为自己是彬彬有礼、文明开化的。我并不是要提出震天动地的批评,而是要完整地描绘我们真实的面貌。彬彬有礼的外表,就像《天堂》中的阿齐兹一样,常常掩盖或隐藏了一种冷酷,甚至残酷的心态。任何人要抱着一定程度的诚实心态描写自身所处的社群,必然会将批评的矛盾对准它,而这通常是不受欢迎的。作家们总是主动希望壮足自身的胆量去刺痛别人:这可能取决于谁活着,谁死了,以及他们能承受什么代价,但这是不能不做的。
钱:为什么对印度洋及其沿海地区的共同历史感兴趣?
古:我研究得越多,就越清楚地发现,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和他们讲述的故事通过大洋联系起来。我想从东非的角度看世界,与从南阿拉伯或印度西部的角度看世界,并没有惊人的不同。似乎海洋缔造了一座座文化之岛,它们漫布在更广阔的列岛之中,通过海路和商业贸易联系在一起。即使在我的孩提时代,听人们说要去附近的蒙巴萨,甚至孟买或毛里求斯,也丝毫不足为奇。来往于这些地方并不稀罕,但仍然相对危险。有一点对你自己的文化身份意识很重要:你不仅仅来自桑给巴尔,还属于另一个世界。你还共同享有印度洋的故事:例如,我读到《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时很诧异,因为这些故事是我的母亲和祖母等人讲述的,感觉就像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我当时从来没有想过要问,为什么我们互相讲述中国、波斯和叙利亚的故事,但这些地方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世界,因为海上航线使我们成为更广阔世界的一部分。
钱:你描述了印度洋上共有的“列岛”,你能谈谈其中的岛屿状况吗?
古:我们公认有些地方是历史上和今天东非文化的中心,它们几乎都是岛屿,这是东非一个有趣的特征。桑给巴尔、蒙巴萨、基尔瓦、拉姆都是岛屿。非洲大陆是岛民获得物质财富的地方。奴隶只占他们贸易的一小部分。大部分是黄金、兽皮、木材、象牙。你几乎可以步行,当然也可以游泳,穿越蒙巴萨岛和非洲大陆之间的海峡,因为那道海峡不是很大,也不是很深。然而,就像壕沟一样,这道窄窄的海峡仍然提供了安全保障,使蒙巴萨岛保持岛屿状态。桑给巴尔岛和拉姆岛同样靠近大陆。此外,由于这些岛屿是海上殖民地,它们面向大海并拥有港口。我对“列岛”的理解是:拥有海岛心态——害怕出海但也随时准备出海——而非定居陆地、建造大城市的心态。说个题外话,我还在上学的时候,班上有印度、阿拉伯、非洲的孩子,我们已经司空见惯了,因为无论你沿着印度洋海岸线走到哪里,都有同样易于辨认的混杂人群。这反映了社会交流的程度,而且我认为它的源头在于人们来自同一个海洋的周边地区。
钱:在一次采访中,你犹豫是否使用“混杂性”一词,你认为它赋予了这种现象“一种能量”,从而模糊了背后的暴力和压迫。霍米·巴巴认为“混杂性”,即他所谓的“第三空间”,具有赋能、变革功能,“打破了自我与他者、内在与外在的对称和二元性”,而你对此的看法似乎比他更悲观。
古:许多后殖民主义者在讨论“混杂性”时没有承认的是各式各样的种族主义。在《崇拜的沉默》一书中,我暗示,我们自以为是“我们”,但其实都被锁在各家的院子里。我说的是学童,但即使在成年人中,某些社群与其他社群没有任何往来。例如,穆斯林和某些其他团体,如天主教徒和一些印度族群,不会与其他团体联姻,也不会有很多互动,他们还坚持学校教育分开。这不是“混杂性”,因为这些人群没有广泛交融,从中生成新的东西。各种隔离是存在的,如果你没有专门研究桑给巴尔和沿海地区的“种族”和社会政治态势,你会发现这类问题很复杂,难以深入而细致地讨论。这不是一幅清晰的图景。
钱:在你的作品里,一个常见手法是主人殷勤款待客人,而客人被主人的女儿或儿子诱惑,或者主动引诱了他们。这说明你对好客之道、性和性别抱有什么看法?
古:我想我要表达的意思是,如果你把殷勤待客当作社会体面的表现形式,其他人就会立刻产生冒犯的恶意。当然,《抛弃》里的英国人物马丁·皮尔斯不大可能清楚这种价值观,也不会出于这个原因而这样做。不过,《海边》里的侯赛因之类的人物会选择勾引主人儿子,一大原因也许正在于此。同样,如果你认为女人的行为对你的自尊或声誉是一种打击,这无关乎事实本身;相反,它的意义被卷入一种并非宗教意义的虔诚中,我想大量不幸由此而生。即使主人出于好心款待客人,如果没有以深思熟虑或发自真心的方式进行,而只是遵循礼俗或成规,那么,照我看来,那就是好心办坏事。
钱:我前面说到你为了互文性引用了康拉德、拉什迪和《古兰经》。另外,在你的作品里还有与19世纪人物相关的典故。你在《崇拜的沉默》的标题和卷首语里援引了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在《海边》里,还能见到梅尔维尔的《抄写员巴特比》。请谈谈你所受的影响。
古:某些作家有一阵子对你来说很重要,但多半很快就过去了。我经常翻阅J. M.库切和V.S.奈保尔的书,我想,我现在可能已经不再阅读奈保尔了,因为我阅读他近来的作品,并不觉得很喜欢,他以前的作品因此更读不下去了。他的思考路径中使你意识到,你之前认为是讽刺的言论,在如今的感受里,比你当时想象的更强烈。我曾离开英国一段时间,回来后他出版了《河湾》和《信徒的国度》。我差不多是同时读到的,觉得这两本书有不少共同之处。由于他过分自信,《河湾》关于非洲的说法通常是错误的,从《信徒的国度》对伊斯兰教,对伊朗、巴基斯坦和其他伊斯兰国家的描述可见,他的印象似乎也是错误的,尽管我对那些地方所知有限。不过,我并没有太过介意,因为我认为这是他写作的特点:他放出的炮火有些你能接受,有些不能接受。然而,奈保尔变得越来越不宽容,让我觉得也许我对他太宽容了。在他后来的作品《不止信仰》中,有很多令人错愕的言论,皆是他的由衷之言,而不仅仅是为了煽动人们的情绪。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他的写作开始离客观分析更远,而更像是争辩或谩骂。如今他的喉管里就像装了把尖刀,不断讨伐伊斯兰教,当然,激怒他的问题不止这一个。
我也阅读其他无论就名气还是作品而言都不那么有分量的作家;这些人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写了一两本书。我广泛阅读,人们以不同方式影响我,如果用“影响”这个词恰当的话。我每写完一本书都会重访梅尔维尔,这样做,倒不是因为我受到他的影响,而是因为我觉得他很有趣、迷人,有时还很睿智。有时候,你写了点东西,发现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只不过不知道它从何而来。也许你最终会想起契诃夫笔下的某个瞬间,一个人看着镜子或什么东西的意象潜入你的字里行间。我不会声称《天堂》是对康拉德《黑暗之心》的刻意改写,但人们时不时发现二者有相似之处。莎士比亚是《海边》的关键参照,包括他对爱情的理解。还有,萨利赫·奥马尔在机场时,心想,移民官凯文·愛德曼是不是犹太人。这段文字从这句引言开始:“但愿这一具太坚实、太坚实的肉体会融解、消散,化作一滴露水。”这里提及的“肉”和“犹太人”令读者想起《威尼斯商人》,但这句话其实来自《哈姆雷特》。这些都是有意为之的互文关系,而互文正是写作,甚至阅读的部分乐趣所在。互文并不总是意味着重大关联。事实上,它属于将诸多观念混合的方法。比如说,萨利赫·奥马尔为什么不该对莎士比亚有浓厚兴趣呢?不管什么原因,他确实兴趣浓厚,但这与他的身份并不必然有着深刻关联。
钱:最后,请谈谈写作和历史的关系。你在《对过去的认知》一文里联系德里克·沃尔科特对加勒比奴隶制的愤怒以及对英语的热爱,探讨了这个议题。你是否也跟沃尔科特一样,相信某种“赋能的传统”①?
古:我认同“赋能的传统”这个理念,但对沃尔科特来说,有所不同,因为除了英语之外,他没有其他现实渠道获得世界归属感、文学归属感。在那篇文章里,我谈到了思考我们所属的传统以及过去赋予我们的观念的两种方式。一方面是索因卡式的理念,即清除障碍,丢弃所有堆积物,复原真实面貌;另一方面,像沃尔科特一样,拥抱出现于我们面前的一切。我更认同第二种观点,即不试图净化任何东西,只是理解和接受任何影响。
责任编辑 李嘉平
① 伊迪·阿明为乌干达第三任总统。
①相信“赋能的传统”,即把传统看成活跃、灵动、与当下同步,而非死板、固定的东西,将它转变成为释放积极创作能量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