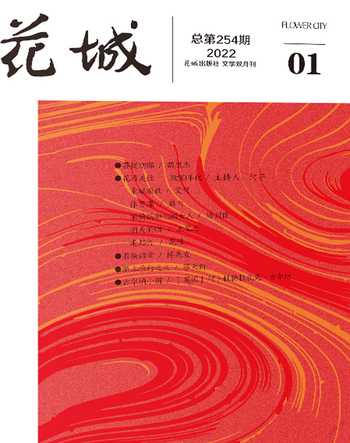体育课
路内

谁能想到呢,我们化工技校,著名的流氓学校,在1990年被称为戴城十大不敢惹的单位,与日晖桥派出所齐名的地方——竟然没有操场。
这年9月开学,教学楼推平重造了,我们背着书包在楼下看了好一会儿,问明白了才敢进去。化工系统有钱,这些单位长年向运河排放各种污水,向居民区喷射各种毒气,一分钱都不会赔给老百姓,它们当然富裕。它们要做的跟黑社会没大差别,就是交钱给市里、局里。局里觉得化工技校太破啦,影响到局长的形象,终于决定拨下资金,把一排红砖房子推平了,造了四层高的教学楼。进去一看,墙面雪白,钢窗锃亮,每层楼都有男女厕所。我们感动得不得了,跑到阶梯教室的电视机前看世界杯的录像,踹开每间教室门往黑板上乱写老师的名字,我们发现目前只有三个班级的学生在上课,而教室有二十四间,一楼以上完全没人,于是我们又跑进顶楼的女厕所里看了看,把大飞反锁在了那里。那一整个下午大飞就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向远处挥舞着汗衫。
但这个鬼地方仍然没有操场,因为地皮不够。教学楼后面有一块很小的空地,一个只剩半块篮板的篮球架,其他啥都没了。这对我们来说太过狭窄、乏味。门房老乌龟一激动,还种了很多蓖麻,傻逼也不收蓖麻籽,就种着,图个开心。那里面有蛇!

我们的体育老师姓汪,50多岁一个秃头男人,开学以后,他看到这操场就发出了一声娇喘。这意味着他仍然不用带我们做任何球类运动,非常省力。这是一个没什么自尊心的体育老师,他打乒乓球不如黄毛,打羽毛球不如花裤子,打桌球不如我,跑步跑不过我们大部分人。我们顺便问了一句,有没有室内运动场所,造这么大的房子给弄间乒乓球室总可以吧?老汪说他们忘记了,造楼花费很大,没余钱买任何体育器材了。
亚运会要开,化工局觉得钱太多,也想搞搞,把各单位喊到一起说咱们弄一场田径比赛吧。这消息传到我们学校,校长特别重视,让老汪带着我们去街上跑圈,选几个能跑的,长跑短跑,跑不死的可以马拉松,老汪只得照办。我们上了街可就不再是池中之物,沿着运河,铁三角一马当先跑出去,他还穿着皮鞋。老铁是区田径队的,因为打架被开除了。由于老铁跑太快,我们不得不狂奔着紧跟,老汪不知道我们想跑到哪里去——按路线应该在城东大桥转弯,然后绕回来,但老铁钻进了涵洞,一溜烟往火车站去了。我们也全跟着。老汪急啦,他想吹哨让我们回来,一摸胸口发现哨子没了,哨子在阔逼手里呢。老汪不得不发疯一样追我们,如果我们成群地跑丢了,那确实会对社会造成很大危害。可是他一个50多岁的秃头老男人,跟我们比跑步,那不是跟比性功能一样吗?他可能赢得下来吗(除了猪大肠这样极个别的超肥怪胎)?跑到纺工职校那儿,我们还停了一下,因为我们有一半人的女朋友都在那里,打个招呼还是应该的。大飞一回头看见老汪扑倒在地上。
“老汪摔啦。”
我们哈哈大笑,等着看老汪爬起来。等了好长时间,我们的女朋友全都从学校里出来了,缠着我们去买冷饮,我们买了冷饮,女朋友们舔起了冷饮,猪大肠从街道远处气喘吁吁跟上来——老汪他妈的还是没爬起来。贱男春稍微有点医学常识,他老妈是护士,他说坏了,老汪可能挂了,这病叫马上风。我们跑上前,把老汪翻过来,他面色发紫,气息全无,一只手还打在我腳背上,让我起了一层寒栗。接下来我们一群人抬着老汪往医院狂奔,后面跑着我们舔冷饮的女朋友,再后面追着几个警察,警察后面跟着一群看热闹的老百姓。
我们就这样把体育老师给跑死了。
老汪去世以后我们才意识到,他挺好的,他的体育课尽管没有球类运动,但也不会安排太多的队形操练,让我们在蓖麻丛里愚蠢地晒着。他喜欢给我们讲人生哲学:你们将来做工人,做工人要学会偷懒,不然你会累死。这类朴素的道理被我们深深地记住,尚来不及实践,他就把自己累死了。
体育课必须上,还有那个化工局的田径运动会。第二任体育老师是我们的机械制图老师,他能胜任这个教职据说是因为他老爸当年做过体育老师,但他本人,结巴、瘦弱、近视、迂腐,看上去是他老爸质量最差的那颗精子制造出来的。为啥质量最差的那颗跑赢了其他的,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他给我们安排的唯一的运动,是跑楼梯。老天,这学校终于有楼梯了,可以用来跑了。
这项运动确实锻炼耐力,但它让我们所有人发疯并失去耐性。这么上去下来的,跑一节课,到头来他发现我们班40个男生全都躲进了各楼层的女厕所,在里面抽烟骂街呢。对的,我们班没有女生,40个,全男的,每次我都得把这件事说上三遍别人才能理解。如果你不理解,你可以去监狱里体会一下那滋味。这件事最后的结果是:老师跑上跑下,反复不停地把我们从四个楼层的女厕所里揪出来,第二个星期他膝盖积水了,他给自己报了个工伤,连机械制图课都没人上了。
后面连续两个星期,我们校长无耻地让门房老乌龟来代课。不得不说,老乌龟是能镇住我们的,他会武术,他还有两个儿子也会武术。他的下盘功夫不错,马步一扎连200多斤重的猪大肠都推不倒他,然后他一脚就把猪大肠蹬进蓖麻丛里去了。昊逼曾经跃跃欲试想拜他为师,因为昊逼有点瘦弱,他希望自己能强壮起来,追得上纺工职校那个跑得贼快的芳芳。后来大飞一脚把昊逼踹进了蓖麻丛,他就断了这个念头,专心做大飞的小弟了。
我们班四十个人并不齐心协力。纺工职校的芳芳经常对我说,女人多的地方,是非多。她将来会进纺织厂,那地方女人很多很多。然而事实是,全是男人的地方气氛也很尴尬,男人喜欢拉帮派,认小弟,吃豆腐。我们班主要三派人:一派是团干部,可以不用提他们,他们将来会分配到效益最好的硫酸厂,在一堆腐蚀物和腐蚀性气体中享受光荣;一派是以大脸猫为首的黑脸帮,他们的主要战绩是打平过第八中学(俗称野八中)、烹饪职校、园林技校、轻工中专,他们极其蛮横,极其无知,在面对美好的事物时会茫然;最后一派,当然就是我、大飞、花裤子、飞机头组成的白脸帮,有时阔逼和黄毛也会加入进来,有时还捎带上刀把五和昊逼这种不成器的东西,我们的主要特点是长得白,不爱被晒黑,我们的战绩是进了纺工职校以后——女生会掏钱请我们吃冷饮!
老乌龟的体育课上得有声有色,他太沉醉于这一工作、这一额外的奖励,居然要求每星期三下午的固定休假也调整为体育课,让我们跟着他扎马步,校长居然同意了。太阳炽热,到9月底我的脸已经被晒成了咖啡色,很快将是褐色。同志们,那是“做六休一”的年代,我们所有的欢乐都指着星期三下午去纺工职校约女生玩,我们不可能在星期天冲到她们家门口去,她们的爸爸和哥哥会打死我们,因为我们来自该死的化工技校。总之,我们得把半天的假期夺回来。
我们的基本原则是不能在上课时打老师,请记住,这是天条,朝他脸上吐唾沫也不行,这种肢体冲突会把警察招來。老乌龟在上体育课时就是我们的老师,没人敢动他,等到下了课,他就是一个低贱的门房。在接下来的一星期里,他先是发现自己小间里的枕头不见了,又发现起夜用的痰盂被人扣在了床上,最后,他新买不久的一套运动服,居然是白色的,他还不知死活地晾在食堂边上,被人用红色粉笔画了个大乌龟。尽管粉笔很容易洗掉,但他心里应该知道,我们只是给他留了点面子。
老乌龟的老婆是一个讲话谁都听不懂的外地大娘,星期三下午她提着那套白色运动服,已经洗干净,似乎变大了些,她骂骂咧咧地坐在篮球架下面,一边晾衣服,一边看着我们扎马步,还有她丈夫。我快累昏过去了,过了一会儿老乌龟站直了身体,走过去劝他老婆回家。于是我们全都喊了起来,老乌龟你不要偷懒!他老婆听不得这个绰号,从地上爬起来,照着我们轮番扇耳光,打得又准又狠。我们四散而逃,并且意识到,老乌龟这身功夫可能是跟他老婆学的。后来老乌龟自己都看不下去了,冲过来拦腰抱住他老婆,企图将其搬出学校,他老婆使了个鞭腿,一脚把他掀到蓖麻丛里去了。
他种的这一大片蓖麻终于救了他,但即便这样他也没有悔改。星期三下午,我需要这半天的休假。
我17岁的时候,天天觉得饿,但这不是国家造成的,是我发育了,无论吃多少,两三个小时必能消化干净,我是一个强壮的工人阶级的儿子。当时我妈心脏病住院,我每天放学直奔她的病房,就为了吃医院里提供的下午餐,有时是面包,有时是袜底酥。我妈对我挺好的,坐在病床上看我吃完,会在心里默默告诉自己不能死,要是她死了,我的营养就跟不上,身高就会停在一米七二,而我爸的秃头也会从前额蔓延至颅顶。作为一个时髦、正派、有志气的工人阶级的妻子,这是她不能承受的痛。
还有一个对我很好的妹子是纺工职校的芳芳,前面说过,跑得贼快,她有一双匀称的大长腿,肺活量惊人,短跑能和我打个平手,长跑我们没比过,主要原因是我讨厌长跑这种神经病一样的运动,我跑着跑着会做白日梦,看见饭岛爱。大飞他们经常嘲笑芳芳,因为她长得不够好看,黑黑的,因为她单方面喜欢我,而他们都认为我喜欢的是财经中专那个美艳不可方物的姗姗,更因为她曾经失恋过,她爱上了第一中学长跑队的周志亮,而周志亮跑着跑着就跟第三中学的黎丽娜勾搭上了。
爱情这种事情,我爸讲不清,我也讲不清。那时因为我妈病着,我只能在学校食堂吃午饭,我爸给了我每餐两元的预算,而我每餐必须吃掉四元才够饱。我校食堂是校长亲戚办的,他们搞了一套复杂的价格体系,老师一个价,团员一个价,轮到我这种人,菜价贵到天上去了,一份豆芽两元,一份饭一元,我吃上了饭就吃不上豆芽,吃上了豆芽就吃不上饭,全都吃上了又当如何?一片肉都没有。有一天中午我吃得实在太不爽了,冲到蒸饭间打开蒸柜,顾不得烫,随便拿了个搪瓷杯子揭开就吃,后来被机械制图老师揪住。那是他带的菜,他也挺可怜的,一碗红烧豆芽,也没有肉。我感到非常绝望,去食堂赔了老师两份豆芽,然后吃光了他的豆芽。中午骑车乱逛,我在纺工职校门口遇到了芳芳。
“你好像不开心?”她说,“失恋了吗?”
“我没有肉吃!”
她把我带进了纺工职校,在操场边的一棵大树下,让我安静地坐着等,并提醒我不要抽烟,抽烟会被赶走。我说不用担心,我和我爸最近都穷得买不起烟了,我爸在家找烟屁股抽结果他发现我已经抢先一步抽光了所有的,我们爷儿俩商量着今后每天只吃一顿,余钱用来买烟,我们不这么干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怕我妈心脏病发作。我这么絮絮叨叨,芳芳已经跑远了。我在树下找了根枯枝放在嘴里吸了两下,过了一会儿,她跑了回来,手里端着一个饭盒、一个搪瓷茶杯。她走到围墙边掰了两片蓖麻叶子,铺在地上,打开餐具。我看到米饭和红烧肉,还有一个鸡蛋。我快昏过去了,她递给我叉子说:“吃吧。”
“你吃什么?”
“我吃你吃剩下的。”
老天做证,周志亮你应该去死。我蹲在树下吃了两块肥肉,感觉自己又开心了起来。我是个有志气的人,不能吃光妹子的午餐。“你妈做菜手艺真好,就像我妈一样好。”我赞美道。
“这是我自己做的,你再吃一个鸡蛋。”
我是个没志气的人,我吃下了鸡蛋。她捧着饭盒在树下吃,我看着她,帮她赶蚊子。过了一会儿她从耳朵后面拔出一根弯弯曲曲的香烟给我。“我课桌里就剩这一根了,”她说,“少抽点,出去了再抽,你的肺,迟早有一天跑不过我。”
我就这么爱上了她,我忘记了财经中专那个美艳不可方物的姗姗,事实上,我从没跟姗姗搭上过半句话。
9月的最后一堂体育课,一场细雨落下,没完没了。这种天气没法再扎马步,我们应该早点散场回家,但这天老乌龟被校长通知,立即选拔出800米、200米、100米以及跳远、跳高、跳绳的选手,因为,化工局那场倒霉的运动会,国庆节之后就要开始啦。老乌龟完全蒙了,他毕竟只是一个门房,领会不了文件精神,经他调教之后这个班上有40个能扎马步的男生,而运动会并没有扎马步这项比赛。
这天下午老乌龟让我们举手,谁愿意参加,立即报上名来。我们全都对着他奸笑,只有铁三角举手,他要参加马拉松。老乌龟松了口气,后来他发现也没有马拉松这项,局里不想再发生跑死人的事故,他让铁三角去参加800米,那看起来也挺远的。老铁摇头说去你的吧,800米我才不想跑,我就想跑马拉松,过瘾。老乌龟没办法,跑去楼上请示校长,过了一会儿跑下来说:“校长说了,没有人报名就一个都别想回家。”
坐在我身后的大飞已经极其不耐烦,在1990年的9月,我们这位嚣张跋扈的大飞变成了一个浪漫而沉默的人,有时会突然发情。他正在经历一场恋爱,对象是旅游中专的明明,一个明眸皓齿会讲几句英文的长发少女,她几乎是白脸帮的女神,不过六个月后大飞将会栽在沟里,被她永远抛弃。当时他并不知道这一结局,他将自己的每个星期三下午都许给了她,并发誓在毕业后一定会离开化工系统,到酒店系统去陪着她刷浴缸。大飞坐在我身后,双手在桌板上做着一串刷浴缸的动作,晃得我前后乱抖。我一回头看见他眼中的火焰,左眼是明字,右眼还是明字。我知道他绷不住了。
“星期三下午应该休息!”大飞跳了起来,“我要回家。”
“他是要去旅游中专找那个叫克里斯蒂安娜的女人。”大脸猫在教室另一边大声嘲笑,克里斯蒂安娜是明明的英文名字,但这个名字并不应该从黑脸帮嘴里说出来,它是一个秘密。这个城市里没有其他女人有英文名字。大飞很是惊愕,花裤子比他反应快,立即指出,是昊逼投靠了黑脸帮,泄露了我们所有的心事。
“是的,”大脸猫把昊逼搂了过来,用胳膊夹住了他的少白头,“因为你们抢了他的女人,那个叫芳芳的,跑得贼快的。现在昊昊是我的小弟了。”昊逼横着脑袋冲我笑了笑,冲花裤子挥了挥手。我猜想花裤子前阵被丹丹给吻了这件事,也已经传到别人耳朵里。
“上课不要讲话!”老乌龟拍讲台。
大飞站了起来。“你知不知道自己只是个门房?他妈的你只是个门房你知不知道?”他走向老乌龟,飞机头拽了他一把,没拽住。“我们在讲什么你听得懂吗?”大飞指着老乌龟的鼻子。我替他捏把汗,手快点的捏住他的食指就能把他掰得跪下。老乌龟果然出手了,不过大飞更快,他的手只有克里斯蒂安娜能握住,其他人休想。他及时地缩回了手指,让老乌龟抓了个空。我们鼓掌。“我要去找妹子。”大飞扭脸走出了教室,又撂下半句话,“星期三下午应该休息!”
“我应该怎么处理他?”老乌龟问。
“旷课,”大脸猫回答,他还夹着昊逼,后者已经翻白眼了。“一学期累积旷课三天就可以开除了。”
“旷课半天呢?”
“那就是旷课而已。”
老乌龟被我们绕晕了,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在这个学期里,都拥有五次拂袖而去的机会。这当然不是事实,但如果我非要这么干,他也拦不住。这当口有一个化工局的干部敲门,后面还有两个警察,问校长室在哪里。以往这种级别的干部都应该是老乌龟开路引道,但他现在不是在上课吗?他不得不撂下我们,带着干部去找校长。干部对老乌龟很不满意,说你们学校怎么这么乱,门房是个女的,还在跟学生打架。这么一说,我们听到大飞从校门口传来的惨叫,因为下雨,窗都关了。我打开窗,大飞的叫声变得连续、凄厉,好像还在喊我和花裤子去帮忙。
我们冲到校门口。这天下午全校就我们一个班在上课,老乌龟代课后,他就让他老婆来充当门房,也就几小时的工夫。他老婆把大门锁得紧紧的,抱着胳膊守在信件柜那儿,大飞没废话,要求她开锁,她要求大飞拿出她老公签署的出门证,说了三遍大飞没听懂,校门还是锁着,大飞急了。克里斯蒂安娜在雨中等他,在雨中,等他。我要缓慢地讲出如下这句话——没有一个男人能受得了这种煎熬。他扑进门房,打开抽屉找钥匙。钥匙当然在那婆娘手里,他翻了很久,一回头看见干部和警察走了进来,婆娘又锁上了门。大飞在原地待了片刻,只等警察走远,又扑过去抢钥匙,老乌龟的老婆往他下体踢了一脚。我们的大飞,他仍然躲开了,除了克里斯蒂安娜没有人可以踢中他的下体,但他被激怒了,他还了一个鞭腿,因下雨地滑,踢出去半脚就摔倒在地,老乌龟的老婆立马骑到他肚子上,往他脸上乱打。大飞朝这婆娘连连吐口水,然后他像摔跤运动员一样翻过身,用屁股拱翻了老乌龟的老婆,往抽屉那儿爬去,后者虽然倒地,一只手还拽着大飞的裤带。大飞往台阶上爬了三层觉得屁股很凉,昂头一看,雨水正落在他的内裤上,臀部还有两个洞。大飞惨叫起来。
“如果你去约会,你应该穿条好一点的内裤。”花裤子抱着胳膊说。那当口大飞正在哭,他的裤子一半在腿上,一半在老乌龟的老婆手里。
后来发生了什么我已经不知道了,那天太乱,我还看见我们校长爬到了窗台上,然后被警察拖了下去。我趁这工夫翻墙出去,连自行车都不要了,徒步跑向纺工职校。细雨落在我眼睛里,那滋味就像我有很多伤感的情绪无处倾倒。在化工技校,如果你表达这种情绪,你会被笑死,但当你踏进纺工职校,你会被它包围。
我看到芳芳在操场上奔跑,我看到了一个从未看到过的她。假定在此后失散的岁月中我会忘记她,那么只要我走在细雨中,闭上眼睛,就会看到一个穿田径服的妹子从我眼前跑过。她短发,长腿,黝黑,脸上沾满汗水和雨水。她在1992年进入某纺织厂做女工,三年后工厂关门,人们散去,她以这一姿态跑出了我的世界,再也没有回来。
“你为什么要练跑步?”我对着她喊。
“我们纺织单位,也要举办运动会。”她喊道。
“你参加哪项?”
“800米。”她沿着跑道又跑了一圈,来到我眼前,回答我。
“有奖金吗?”我跟着她跑了起来。
“如果跑出纪录,他们说,我可以去市田径队。”她说,“虽然是业余的,虽然还要做女工,但也许还有别的机会呢?”
“你他妈的真的是个进步女性。”
她停了下来。她有点伤感,是的,我曾经在她面前说过,那个将要去涉外酒店上班的克里斯蒂安娜是进步女性,我从未将这一用词送给其他任何妹子。“你呢?”她问,“你打算参加哪项?”
“我不想参加任何一项陪着傻逼跑跑跳跳的运动。”我说,“这件事你做有意义,我做的话可能正好相反。”
“你应该参加,做進步男性。”她天真地说。
“世界上从来没有进步男性这种说法。”我说,“把我当一个瘫子看待吧。”
“饿了?”
“还没跑就饿了。”
她就穿着这身田径服,披着件衬衫,带我走出学校,沿街找了个小摊吃馄饨。雨落在馄饨汤里,9月末的天气正在变凉,到了10月,你又能去哪里?我吃完了馄饨,她一口没吃,看着我。我从裤兜里找出香烟给自己点了一根,把烟灰随意弹在湿漉漉的街道上。摊主走过来收碗,对她说:“你怎么穿着胸罩出来?”
“这是田径服。”我说,“全世界都是这么穿的。”
“你怎么这么黑?”他又多嘴。我把一截烟屁股扔进他手中的碗里,我当然不能回答他全世界的女人都这么黑,或者世界上还有比她更黑的女人。这他妈的都是什么屁话?“你觉得我一个人打不死你,是吗?”我拉起她离开。
在陪她走路的时间里,我说起1990年世界杯,巴西队压着阿根廷打了80分钟,马拉多纳晃过三个巴西队员传球,“风之子”卡尼吉亚一蹴而就,然后,大半夜的,我所在的农药新村远近发出一阵欢呼,我爸激动得把我妈给摇醒了,我妈激动得尖叫起来:啊,那个长头发的。卡尼吉亚,我也想留这么一头长发,给自己取个绰号叫作风之子。我讨厌跑步,但我喜欢足球场上的奔跑,告诉你为什么——在足球场上,你可以匀速跑、变速跑、向前跑、侧身跑、跳着跑、微笑着跑、扭过头跑、挥舞着双手跑。只有这样你才配叫风之子。
“你根本不理解跑步。”她说。
“无所谓,等我技校毕业了,我就给自己留一头长发。”
“像个硬汉?”
“像个内心软弱的人。”我想起克里斯蒂安娜对大飞的评价,我借来用用总是可以的。
我们直走到化工技校门口,这时我才想起应该换条路走,不过无所谓。我们班的人散落在各处,有些在墙头,有些在窗台,有些在门口。“校长被抓走啦!”飞机头高兴地对我喊,“造房子贪污钱了!”
“大飛呢?”
“他还在为裤子哭。”
我向他挥挥手,也向墙头另一边的昊逼。黑脸帮居高临下看着我,过了一会儿他们全都笑了起来:“你找了个黑妹。”
我没理他们,继续带着她往前走。然后我觉得有人拽了我一把,老乌龟从学校里跑了出来。“回去上课!”他对我喊道。我叉了他的脖子,老乌龟朝我腰里撞了一膝盖,这老东西疯了,接着他老婆又冲了出来。我把芳芳拽到身后,顺手从旁边甘蔗摊拽了把刀过来,指住这对雌雄双煞的鼻尖。花裤子和飞机头跑了出来。
“你不再是人民教师了,”花裤子对老乌龟说,“你从来也不是教师,只是门房。你的课结束了,星期三下午我们应该放假。”
我不去看老乌龟失落的眼神,到了10月,你又能去哪里?我扔了刀子,带着芳芳向远处街道走,细雨仍未停。他们还在喊她黑妹。
“你知道吗?皮肤黑的妹子,在我家那片街上,人们都会喊她‘黑里俏’或是‘黑珍珠’,她身边应该是一条浑身雪白的汉子,最好是长发,有浪里白条那么白,胳膊上再刺一朵牡丹花。到了夏天,妹子穿一身肚兜,汉子赤膊,肩并肩走在街上那叫一个好看。”
“如果是很黑的汉子呢?”
“那他妈不就像两个乡下来的傻逼吗?”我脱了汗衫,光膀子走在她身边,“怎么样?”
“好看。”她把衬衫也摘了。我们沿着街道走去,接着我听到后面一阵脚步,是花裤子和飞机头。“脱。”我招呼他们。这两人也脱了,白花花三条赤膊汉子,我想起还有大飞。
“不要喊他了,如果他也脱了,只穿一条三角裤在街上走,我们真的会被人耻笑的。”花裤子说。
“我被你说服了。”我说。
责任编辑 许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