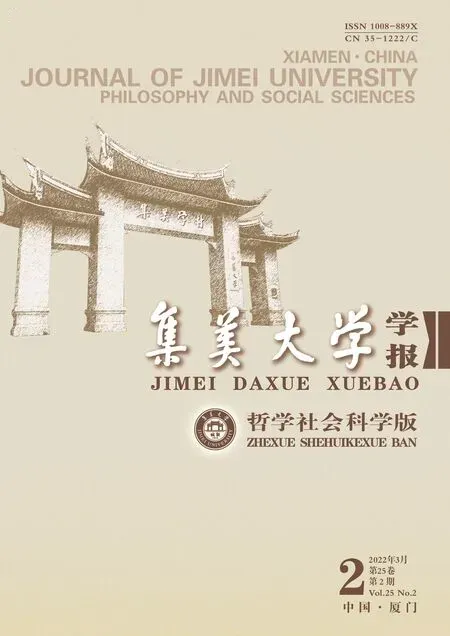惠安“南派石雕”艺术风格的形成及演变
张朝阳
(集美大学 美术与设计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中国石雕艺术历史悠久,北方石雕以京津、鲁豫、晋陕为主,南方以江浙、徽赣、闽粤最具特色。福建石雕尤其以闽南惠安最为著名[1],惠安“南匠”(1)根据《乌山石记》记载,清光绪年间,当年乌塔倾斜,“南匠”蒋学心曾应邀讨论处理办法,蒋学心建议采用灌水法来纠偏,未被采;所以至今乌塔仍未矫正。“南匠”称谓可考的较早文献可参见:福建日报社工商处、福建日报社农业处,编写.福建特产风味指南[M].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13;罗翰,等,编著.福建旅游指南[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1987:136.历经千年不断探索,渐成独特风格体系,如今被业界谓之为“南派石雕”(2)“南派石雕”的提法源于行业民间习语。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由文化自觉意识较早的惠安政府和文联提出,广义上与北方(曲阳)传统石雕相区分。这也是很少有以“北派石雕”为名研究石雕的原因。现有资料显示,南派石雕,其概念主指惠安石雕,虽有异议,但已为业界所默认。可以这样理解,这种提法是惠安石雕产业发展的产物,是传统工艺文化振兴的时代需求,体现了中央提倡的文化自觉。目前,“南派石雕”的代表就是“惠安石雕”,两者相互指代。可考的最早文献可参见:施宝霖.崇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215.。相较于北方及其他地区石雕,惠安石雕在工艺上更精细,造型更活泼,趣味更丰富,总体风貌一如“惠安女”般的形态和特征,既显得绮丽秀雅,又不失纤巧灵动,不仅成为一种文化气质和象征,而且在其蕴涵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中,彰显出东南地区耐人寻味且亟需研究的文化共性。
一、惠安石雕艺术的历史分期
历史上惠安共修过6次县志,有关建筑、石雕记载的文字难得吉光片羽,以致人们对一些建筑、石雕的历史难以稽考(3)林瑞峰:《惠安方志通讯》,惠安县地方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内部资料),1994年。。经对明清以来有关石雕艺人、作品的口头传说和只言片语文字记载的考辨以及现时学人相关研究的梳理(4)黄永胜:《中国惠安石文化》,93中国惠安石文化节组委会(内部资料),1994年。,笔者以为,有关于惠安石雕艺术的历史分期和划分大致有以下几种:
1.从历史考古的角度,分为6个时期:曾经的辉煌期(唐以前);初兴期(唐五代);鼎盛期(宋元);繁荣期(明清);衰退期(民国);复兴期(现代)[2]。
2.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分为5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萌芽时期(东晋至明后期);第二阶段为奠基时期(明后期至清咸丰年间);第三阶段为成熟时期(清光绪年间至20世纪60年代);第四阶段为繁荣时期(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第五阶段为点石成金时期(改革开放以来)[3]。
3.从石雕发展的历程,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孕育阶段(清以前);第二阶段为振兴阶段(清),代表事件为李周的出现、南派风格的形成及石雕专业村的确立;第三阶段为成熟阶段(建国初期);第四阶段为繁荣阶段(改革开放以后)(5)汪峰:《崇武石文化》,惠安县文学艺术联合会(内部资料),2000年。。
4.从产业变迁角度,划分为5个时期:萌芽期(石雕产业初现中原风格);发展期(石雕产业技法写实);成熟期(石雕产业形成精雕细琢的南派风格);创新期(石雕产业推陈出新);繁盛期(石雕产业链全球化)[4]。
5.从工艺学的视角,分为3个阶段:即工具性、工艺性和艺术性阶段。平石、雕刻、影雕分别是三阶段中标志性的产品[5]。
以上几种划分方法对惠安石雕艺术特点虽有提及并较为笼统,但都在规律和原理上为惠安“南派石雕”艺术风格流派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参照。换言之,惠安“南派石雕”必然也会经历其孕育期、发生期和发展期(6)“艺术风格”是指艺术作品语言相对稳定的整体性艺术特色,是艺术家创造个性成熟的标志。理论上通常将思想倾向、美学立场、创作方法和表现风格相似的艺术家划归为一种流派。“艺术流派”则是特定地域、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其成因很复杂,概括起来大致有2种:(1)自觉形成;(2)不自觉形成。参见:刘钊,庞国达.艺术概论[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8:199.,不同之处在于,各个阶段具体的历史节点与断代依据各不相同。
二、惠安石雕艺术风格的历史演变
单就惠安“南派石雕”而言,孕育期是指风格形成之前的准备阶段;生发期是指作品风格的肇发过程,体现为代表作的产生和面貌的形成;发展期是指其风格要素的集体无意识的认同或有意识的自组织、有系统的传承。本研究重点从“南派石雕”艺术风格的形成与演变角度,力求勾勒出惠安石雕艺术的发展脉络。
(一)惠安石雕艺术风格的孕育期
福建石雕工艺源远流长,可上溯至石器时代。惠安石雕艺术据说从北方传入,惠安境内史料记载最早的作品为晋安郡王林禄墓“前有石冠石纷,后有石羊石马”(7)明天启丁卯年(1627),林齐圣赴任惠安教谕时,重修莆林始祖墓,所撰《重修始祖晋安郡王墓记》称:“晋安之茔域历几百年为沧桑物改,翁仲明器犹有存者。”。唐末王潮墓的文官、武士、马、羊和莲花浮雕石砖,宋代洛阳桥守桥四介士、月光菩萨及《万安桥记》碑刻,洛阳龙船尾山老君造像,黄塘岩峰寺弥勒佛、菩萨像,元代的惠安孔庙龙柱、浮山塔与平山塔佛像浮雕等遗迹,足以体现惠安石雕的悠久历史。
惠安东桥东湖村《鉴湖张氏族谱》记载:鉴湖十二世张仲哥(1123—1194年),是“泉郡名匠,善雕浮图花卉,晋(江)南(安)同(安)宫阙泰半着手”;鉴湖十四世张仕志(1211—1291年),为泉州南少林寺石狮子的雕刻者;鉴湖十五世张日臣“力攻雕刻艺术,所活人物图像呼之欲出”;鉴湖十六世张同善(1338—1426年),“政务之余攻习雕刻漆绘成术益精”。可见,有文献记载的惠安雕刻工艺,最迟可追溯至宋代(8)《鉴湖张氏宗谱》是一本手抄本,共91页。建谱于宋淳化壬辰年(992)。张良始祖第三十五世张椿寿辑,明永乐任辰年(1412)重修。记载大量有关张氏重要人物的生平。族谱揭开泉州开元寺飞天乐伎的雕刻者张仕逊,并记载泉州少林寺石狮的石雕名匠张仕志,还记载晋江安海龙山寺文殊普贤塑像是东湖村人日臣所作。。此外,泉州开元寺石雕佛像、清源山老君岩老子造像、德化九仙山弥勒佛像、漳州唐咸通四年(863)的石经幢、漳州陈元光墓以及南安韩握墓神道石刻等闽南境内众多历史遗迹均离不开惠安的雕刻工匠。
尽管如此,与其他省份相比较,闽南石雕在明代以前遗存的实物并不多。古代文献《石刻刻工研究》收集的福建碑刻及工匠姓名也很少,最早为清代李周。但是,自宋元时期,却又是闽南石雕发展迅速的阶段,尽管自身的形制、风格依稀萌芽,却大体仍与北方中原传统样式相仿,尚未形成自己的艺术面貌和特征,没有出现风格清晰的特色作品。
(二)惠安石雕艺术风格的生发期
明清以来,惠安石雕的发展日趋成熟,能工巧匠人数剧增。这些雕匠大多为亲戚关系、师徒关系或同行关系。一个个匠师社群,在长期的实践中不断摸索,凝练出独特的艺术语言。这种艺术观念、艺术表达的相近性是群体风格形成的重要原因。群体风格中代表人物的出现、代表作品的认定至关重要,这也正是一种艺术风格形成的关键之所在。
据惠安崇武镇五峰村道光壬寅(1842)整修的蒋氏族谱中记载:其祖峰前村蒋眉峰公之孙蒋景荣、蒋景明兄弟于明正德、嘉靖年间先后前往云南大理拜金盛学艺,学成后传授乡里,一时蒋氏雕刻技艺“冠绝福泉”。明嘉靖至万历年间蒋景明作惠安孔庙龙柱及麒麟石壁堵、崇武三玄宫石狮子及石牌坊、张岳墓的石将军、石马、石虎、石羊;清康熙年间,蒋树台作鼓山灵源洞祖师像,蒋树台、蒋树仁作青山宫魁星像;清雍正年间,蒋树台、蒋树义作于山法雨堂三狮戏绣球石鼓;清乾隆年间,蒋经强作惠安白石亭,蒋世强作惠安奉宪立碑,蒋经强和其子蒋世英作安溪文庙翻云盘龙柱,蒋志益、李周作于山法雨堂一对龙柱,李周作涌泉寺绣球狮(见图1)、侯官县万寿桥18只拳头大小的石狮、福州泉漳会馆一对石狮。这些作品均体现了当时较高的石雕工艺水平,李周无疑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

图1 福州涌泉寺绣球狮
李周(也写作李州)俗名“瓮仔周”,清乾隆和嘉庆年间人,崇武人氏。作为福建青石雕技艺发展史上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人物,历来被视为宗师。他在惠安石雕技艺上有两大创新:(1)将绘画技法与石雕技艺结合,独创“针黑白”的工艺,利用黑白成像原理,创造了一种崭新的艺术表现形式,这就是成熟于现代的影雕艺术。(2)在传统雕刻技艺上大胆创新,一改北派狮子正面蹲坐、形象凶猛的传统形象,创造性地雕出摇头摆尾、玲珑可爱的“南狮”风格,这种“巧”与“趣”的特点,奠定了惠安石雕的精神内核[6]。
艺术竞争是流派产生及发展的动力,惠安石雕艺术风格的形成与发展,正是闽南地区行业充分发育、业内技艺竞争的必然结果。以地缘、姻缘、亲缘等社会关系组成的惠安匠师群体,近似的心理结构和审美性格、密切的社会往来和长久的合作,往往会形成相近的艺术观念。此后,惠安石雕冲破旧规,技艺大进,石雕艺人开始走出惠安向外发展,以石狮和龙柱为核心,发展出了石鼓、石堵、人物以及牌坊等诸多工艺类型,艺术进一步趋向精巧、欢愉之美,艺术特征上突出天真活泼、婉转流利的视觉效果。
(三)惠安石雕艺术风格的自成期
惠安石雕群体艺术风格的生成,往往通过匠师之间的社会关系来实现,一般来说,地缘关系仍然是艺术家形成群体的主体。在惠安五峰村以蒋姓为主的石匠与溪底派大木匠师相互配合,形成闽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匠帮集团,以致有“无蒋不成场”之说。如,清嘉庆庚申(1800)蒋志恩作惠安城西龙泉寺龙柱,清嘉庆癸亥(1803)蒋志云、蒋明兴作惠安沙格宫花鸟石柱和人物石柱各一对,清嘉庆戊辰(1808)蒋明心作侯官文庙龙柱一对,清嘉庆丙子(1816)蒋志云、将明心作漳洲白礁学甲慈济宫龙柱五对(见图2),清嘉庆戊寅(1818)蒋志恩作厦门南普陀寺石狮一对,清道光乙酉(1825)蒋国衡作仙游东门外石碑坊,清道光甲辰(1844)蒋明堂和蒋寿豪作海沧保生大帝庙龙柱一对、青礁慈济宫施公典故浮雕、晋江陈林村“四不象”墙堵,清光绪戊子(1888)蒋双家作峰尾东岳庙龙柱等等。当然,不同的匠师群体在竞争中也会强化自身的艺术特点,打巧斗技依然是闽南石雕的拿手好戏。而敢于尝试、善于灵活变通则是闽南人的精神在石雕艺术领域的具体表现。这种变化在盘龙柱的风格演变中可见一斑。

图2 漳州白礁学甲慈济宫龙柱
凡经惠安艺匠精心雕制的龙柱统称为“福龙”,蟠龙柱作为惠安“南派石雕”作品中的精髓,“据不完全资料统计,省内外、国内外共达110多对”[7]。这些文物大多为清代时期的作品,从石雕的装饰内容上看,早期龙柱布局疏朗,画面较为简单;中晚期则较为繁密,朵云中增加人物、海兽等元素,营造出云遮雾罩、神仙出没的感觉。从雕刻技法上来看,早期龙柱以高浮雕为主,中晚期后透雕增多,镂空的龙体常常游离于柱体之上,几近圆雕,有的出现了二层、三层,即俗称“二透”“三透”。与北派古朴苍劲的龙柱相比,南派龙柱的刻画更为繁缛细致,动感通透[8]。这一时期,“南派石雕”艺术风格在“巧趣”的基础上逐步转向对“繁褥”的追求。
清末、民国时期,惠安雕匠已名扬全国,这时的石雕工艺与建筑艺术珠联璧合,在海内外大量宅第、祠堂、陵园的建造中得以彰显。例如,蒋仁文作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合龙柱,王神赐作仙游保和堂石雕,蒋瑞生作晋江侨乡“甘露寺招亲”壁雕等。在台湾,惠安净峰名匠张火广及弟子张木成作木栅指南宫、八德三元宫、八里天后宫、新庄大众庙及三峡清水祖师庙;蒋馨作南瑶宫、鹿港天后宫等数座大庙。鹿港天后宫的石窗人物细部刻画入微,神态栩栩如生,是台湾寺庙石雕的经典之作。特别是1918年被誉为“八闽首席木雕大师”的王益顺,他主持台北万华龙山寺的修建,与石匠师傅蒋金辉、庄德发、杨国嘉、蒋细来、蒋连德、蒋玉坤、辛金锡、辛阿救与王云玉等名家一起制作出刻画精良、结构细密、富丽堂皇的石雕作品,在台湾名噪一时。惠安石雕正是依托海内外宏伟壮观的建筑群落,尽显俊俏秀雅、精致华美的艺术风采,也是这一时期“南派石雕”重要的审美特色。这种艺术风格在集美鳌园的修建中达到了极致。清末、民国时期是惠安石雕的大发展阶段,也是闽南石雕向外扩大的时期,今天的中国台湾、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的许多寺庙、民宅都保留着“南派石雕”的精粹。
(四)惠安石雕艺术风格的自觉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创办了惠安石雕厂,把石雕艺匠集中在一起,先后参加集美鳌园、北京“十大”建筑、毛主席纪念堂、南昌“八一”纪念塔、井岗山纪念碑等重要工程的建设。集美鳌园作为传统石雕与现代石雕的转折点,1953年始由蒋友才、蒋瑞生、蒋丙丁、蒋佛源、张来富等200多人历时6年完成。其数量之多、品种之全、技艺之精、内容之新,实为我国传统石雕所罕见,堪称惠安石雕艺术之博物馆。鳌园600余件作品涵盖了政治、经济、历史、社会、文化、教育、艺术等领域的内容,在传统文化底蕴中,石雕艺人创造性地汲取西方透视学与构图学经验,运用民间的造型语言描绘现代人物活动场景。如,工业矿山交通机电、舟车农具武器、奇禽异兽海产动物、文教卫生体育日常生活等。现代生活极大地丰富了传统石雕的表现题材。值得关注的是,鳌园的石雕手法几乎囊括了惠安所有的雕刻工艺,有圆雕、线雕、浮雕、透雕、影雕、嵌沉雕等等,工匠根据不同的表现对象,运用凿、镂、刻、锯、锉、磨等不同技法,因材施艺,各显其态,达到宏伟华美、秀雅精致、栩栩如生的艺术效果。此时的惠安石雕逐步汲取了现代工艺美术的属性,从传统单一的审美向度逐渐走向形式多样的现代审美向度,这为惠安石雕的当代发展指明了方向,也是惠安传统艺人对于艺术创新的理解。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建设的蓬勃发展,石雕产品应用场景也从传统民居、寺庙走向现代园林、建筑和广场雕塑等场域。面对巨大的市场,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陆续强化“南派石雕”这一概念,近些年来恰逢传统工艺振兴之时,这种提法也被大家默认,这也是惠安石雕文化自觉的重要表现。2000年以后,惠安雕匠作为南派石雕艺术的主要创造者和传播者[9],连续6届在“中国雕刻艺术节暨雕刻大赛”与现代艺术深度对接,这种交流不仅扩大了惠安石雕的生存空间,也拓宽了“南派石雕”多元化的风格特征。2015年“心造天成——中国惠安南派雕刻艺术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展出了55位雕刻家108件作品,集中体现了惠安当代南派雕刻的整体水平[10]。2019年“中国当代南北石雕艺术巡展”,61件作品以“文献+作品”图文并茂的方式,勾勒出中国南、北派石雕的历史发展演变及当代创作方向。无论是注重历史继承的北派作品,还是重视“形式多样”的南派作品,基本呈现了中国南北雕塑从材料、技艺、造型、创意上的各自特征与差异[11]。这一时期,受现代新观念、新标准、新创意、新视点的影响,当代惠安石雕逐步走向形式多元化的审美道路。
惠安石雕在整体上呈现出“灵动纤巧、绮靡繁缛、秀雅华丽、形式多元”的精雕细刻艺术风格,其形成并非一蹴而就,也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代的审美而变化。“南派石雕”肇始以李周所刻南狮为代表,尽显灵动纤巧、喜庆欢愉之态。至清中晚期,风格呈现绮靡繁缛的特征,这种变化在龙柱的发展中可寻征兆。现代以集美鳌园为代表,总体追求俊俏华美、秀丽雅致的艺术风采。改革开放后,惠安石雕的当代发展逐步走向丰富多彩、形式多元的审美特色。倘若追究南派石雕艺术风格演变的根源,则离不开其独特的地理区位、社会民俗及经济文化环境。
三、惠安“南派石雕”艺术风格的成因
作为一定时代、地域中的艺术个体与社会群体审美心理的典型特征和反映,艺术风格的生成、传播与流变,往往受到社会诸多因素的影响。纵观惠安“南派石雕”艺术风格的形成,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民俗风情及社会文化氛围分不开。
(一)人文地理的底色
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的地域性。每个地区的文化在其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各自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艺术是人类情感外溢的物化形态,是人类主动的创造行为,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山水画自唐以后就分为南北两宗,分别以北方景色和江南景色为蓝本,各自创造出美妙动人的艺术境界。
国内石雕界素有“北曲阳,南惠安”之说。其背后,更有“骏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之意涵。因四季分明,北方景观宽广辽阔,秋冬雄浑苍茫,更有“大漠孤烟”与“长河落日”的人生体验,造就了北派艺术雄浑壮美、简约粗犷的风格特征,而秀温润平、四季如春的闽南地区,孕育了秀雅精致的人文风韵,形成了惠安南派石雕艺术舒缓雅致、细腻通透的温婉韵致。受地理环境的影响,曲阳盛产汉白玉,惠安盛产辉绿岩。辉绿岩又称青草石,其石质地细腻,韧度极高,非常适宜雕刻挑空结构,不易折断且易于保存,这就为轻盈灵动、复杂难工的技艺提供了最重要的材料保障。可以说传统石雕中,北派端庄、素朴、劲健,崇尚恢弘、雄伟气势;南派则清丽、潇洒、流美,石雕大多呈现细腻秀丽、含蓄灵动的柔媚情态[12]。
(二)社会风俗的作用
嘉靖《惠安县志》记载:“吾惠为地蕞尔,半属海需,山地则逼惬烟郁,可艺之土或寡矣。”(9)明嘉靖《惠安县志》共13卷。明嘉靖八年(1529),惠安知县莫尚简聘请张岳箓,翌年成书,为惠安第一部县志。惠安虽然地贫,但石材资源丰富,石匠作为主要谋生手段之一,历经千余年的积累,形成了发达的手工业传统。另外,闽南一带较少发生战乱,海上贸易发达,社会相对稳定。和平安康的社会环境,往往需要宏伟华美的建筑,也会造就华丽细腻的工艺品,这种工艺品制作工序繁杂、用时长,在圆雕、浮雕、透雕、线雕、沉雕中均有体现,尤以镂空雕、多层透雕最为突出,堪称一绝。
自古以来,泉州地区远离中原传统思想的束缚,民间世俗文化盛行,相对于正统的中原地区,在文化上呈明显的边缘形态。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造就了闽南人随性喜庆的世俗文化底蕴,在审美追求上,呈现出艳丽、热烈、奔放、奇趣的民间美学特征。明清时期,闽南沿海一带“习俗之趋尚为豪奢”,凡商贾、胥役之辈广修豪宅府邸,宅邸建筑之要求极为严格,大到整个府邸规模,小至建筑中的某个石雕细节,均要严格把关,建筑装饰既不是北方地区之雄伟庄重,也不是江南地区的尚文儒雅,大多体现为色彩绚丽、俊俏华美之特色。石雕作为建筑的装饰品,极尽精雕细刻之能事,绮靡繁缛的艺术特点,正可体现惠安民众对“富”和“劝”的崇拜[13]。
(三)文化交流的影响
惠安原属百越之地,越人普遍信巫,及至秦汉两晋,道教、佛教渐入闽地。唐宋以后,又有天妃妈祖、保生大帝、清水祖师等具有本土特色的宗教神灵产生。宋元年间,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中国与小亚细亚、中东、非洲以及欧洲的联系交往日益密切,泉州港发展成为世界性港口,摩尼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天主教等多种外来宗教陆续登陆,闽南地区成为各种宗教相处最为融洽的地方,当时天主教神甫安德烈佩鲁亚斯在一封信中这样描述:“天下各国人民,各种宗教,皆依其信仰,自由居住。盖彼等以为凡为宗教,皆可救护人民……吾等可自由传道,虽无特别允许,亦无妨碍。”[14]发达的对外贸易创造了巨大的财富,造就了诸如千年古刹开元寺、伊斯兰圣墓和清静寺、草庵摩尼教寺等宗教文化建筑无以伦比的木雕、石雕、砖雕艺术。
从广义的角度讲,惠安石雕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融合了闽越文化和海洋文化,近代又受到华侨带回的西洋文化、南洋文化的影响。从狭义的角度看,福建石雕长期受竹、木、牙雕工艺的熏染,在艺术观念、审美趣味、创作题材、表现手法等方面,相对于“北派”大气粗犷、善用大錾大斧而言,“南派石雕”更喜欢用小斧小錾进行创作。惠安雕匠巧妙融合各种文化元素,在形式上不断追求丰富性与多样化,在装饰上强调精致与细腻,逐渐形成了复杂多元、丰富多彩的艺术特色。这正是多种文化因子相互碰撞、融合的结果。
正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泉州地狭人稠的自然环境与移民的生存意识,造就了闽南人冒险进取、敢拼爱赢、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远离政治中心的社会风气及崇尚商工的传统,培养了其活泼自由、喜庆奢华的民间美学特征。开放多元的文化孕育了惠安人豪爽团结、兼容并包的性格。这种边缘文化形态外化的最有价值的民性,从惠安“南派石雕”的当代发展中可见一斑。
四、惠安“南派石雕”艺术风格的当代发展
时代更迭会导致人的价值意识转换,艺术审美也会随之改变。艺术语言的变迁是艺术风格演变的重要内容。传统惠安石雕作为区域性的地方工艺,其当代发展可以理解为是通过吸收最新的技术和审美思想的转变来适应现代社会的过程。在文化全面渗透、市场多元发展、信息快速传播的当下,惠安“南派石雕”无论艺术风格还是审美观念,都表现出从地域风格到多向度发展趋势。这种风格多元化的艺术转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题材内容与艺术形式的拓展
传统惠安石雕源于本土的生活方式,表现题材偏重于乡土风情、民间传说、宗教故事、美德典故、山水花鸟、吉祥纹样等方面,这些作品在满足现实需求的同时还担负着人们的精神寄托。如今人类已经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代,社会的发展直接影响着工艺美术的表达。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艺术内容方面,随后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艺术形式,以鳌园为代表的惠安石雕就集中体现了这种现象。惠安石雕的题材内容种类繁多,其大致可以归为: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描绘、对各种艺术语言的探究、对思想观念的实验。例如,张华达的青石雕《乐在其中》,以具象手法刻画了憨态可掬的儿童形象;张建奎的自然石雕《石破天惊》,以虚实对比的艺术表现,强化对主题意境的营造;阿尾的观念石雕《橱窗人》,是作者对当代社会“人”的理解。
形式与内容的融合拓展是当代惠安石雕发展的基础。形式包含作品的内部结构和外在形态,内容则指向题材、主题、细节、情节、情感等要素的总和。新的艺术形式带来的新形态进一步阐释了作品的内容,对新内容的挖掘亦有利于诞生更多的艺术形式。新内容新形式为惠安石雕的当代发展开启了多元、丰富、自由的前进方向。
(二)工艺技术与雕刻材料的延伸
进入工业社会,技术的进步成为生产的主要助力,如今惠安石雕也不可避免地走上了机器生产的道路。随着人工智能、数控技术、3D雕刻的发展,大部分工艺美术师已由传统手工制作时代进入到半机械化、机械化、智能化的创作阶段。手工与机械并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存在着一种优势的互补。非遗传承人王向明通过自己研发的工具,尝试把传统镂空雕做到极致。《生生不息》雕刻出细如发丝的蜂窝状细节,《海嬉》中高难度镂雕多达几十层,《团队的力量》密密麻麻的蚁群有数百只。这些作品通过工艺的进步挑战技术的极限,创造出最为精细的惠安镂空石雕作品,这是传统手工技术难以达到的境地。
惠安石雕过去大多采用本地出产的辉绿岩或花岗石,随着现代市场需求的多样,石材应用场景的扩展,诸如汉白玉、大理石、玉石等新材料开始不断运用到石雕的创作之中。近几年惠安玉雕异军突起,以技巧的灵活及色泽显贵,改变了过去人们对惠安石雕的印象,石雕不仅能成为建筑装饰,还可以出现在人们的桌几案头。江美才制作的《青龙》,利用玉石色彩鲜素一体的特点,构思巧妙且精雕细琢尽显“南派石雕”的特色。和大型石雕一样,玉雕界也不断研发新的工具,牙机便是借用了牙医的医疗设备,具有很强的灵活性,满足了匠师对玉器精度的要求。另外,郑国明“木裹石”巧雕作品独树一帜,为我们展现出多种材质融合的魅力。俏雕与影雕则拓宽了石雕在色彩表现上的局限性,特别是影雕将绘画、摄影的创作方法引入其中,进一步拓宽了惠安石雕的艺术视野。这些新材料、新技术的应用,极大丰富了“南派石雕”的表现力,为石雕语言风格的多元提供了基础保障。
(三)思想观念与认知方式的转变
艺术理念是艺术创作的思想观念,不同的艺术理念产生不同的认知方式,认知方式的变化又会导致艺术理念的变化。随着惠安石雕从宫观庙宇、传统民居逐步走向现代建筑与城市景观,石刻产品也从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惠安匠师的认知方式与艺术理念也从传统走向现代。匠师开始突破单一的传统工艺思路,强调个性、强化自我。有些人对传统艺术进行重新梳理与解读,有些人运用了学院派的艺术表达方式,有些人吸收了现代主义的观念,有些人则走向了设计之路。王荣海写意石雕《残荷》《秋山幽居图》看似简单几笔,却蕴含了悠远的意境;蒋丙丁作品《游击队吹号员》采用现实主义创作理念;龚祖荣、李军官、毛景秋的作品在《五月石动——当代石雕艺术展》上尽显惠安石雕的新观念;吴德强、辛小平充分吸收现代设计理念,通过多年的努力,他们的作品逐步完成了现代审美、功能形式、思想情感、材料质感等方面的协调与转换,最终为自己构建了一套突破传统、化用传统的思想方法和观念体系。
传统艺术体现艺术世界和日常生活之间的和谐关系,现代艺术则走上了依靠审美经验进行不断“创新”的道路。与现代艺术不同,后现代艺术不再是那种“精英”式的存在,它把艺术作品和现实生活的界限混淆起来。这些不同的艺术理念及创作方式造就了惠安石雕丰富的艺术风格。风格多样性又是思想观念多样性、认知方式多样性的共同结果。
(四)文化价值与审美标准的丰富
相比之下,早期的惠安民间艺人在审美自觉性上主要趋向“雕缋满眼”的气质,代表大众化的世俗审美趣味。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变革,惠安匠师的审美标准与艺术价值也发生了深刻的转变,既有传统工艺审美观念,也有现代艺术审美观念,总体呈现出传统和现代共存、东方和西方共生的审美现象。王经明的《听萧对月图》风格传统,给人一种静谧和谐、淡泊深远的古典之美;张文山、孔武战的作品转向东方的沉静之美,这种具有东方人文精神的作品,不再是简单的传承与创新,而是对当代生活方式的从容思考。近年来受过高等美术教育的艺术家积极投身惠安石雕的创作中,例如,陈玉坤作品《开着一座山》《41℃》《心电图》、王向荣作品《来自大地的礼物3》《非自然伤害》都具备后现代批判性精神,其关注点已经转向对现实问题的思考,诸如消费文化、物质欲望膨胀以及以生存环境为代价赢取的“物质文明”等等。惠安石雕从早期较单一的审美观念开始向多样化、多元化、碎片化、平民化审美观念发展,各种题材、形式、风格的作品被创作出来,呈现出百花齐放的面貌。这种石雕语言的新探索,也许正在成为“南派石雕”的新符号。
对于石雕继承人来说,时代的审美变化要求手艺人必须从传统思维定式中走出来,在传承中注入现代观念、融合科学技术、融汇时尚元素、追求形式的多样性等等,这也是传统工艺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的必然结果。尽管当代惠安石雕艺术风格种类越来越多、艺术化水平越来越高,但是“南派石雕”灵巧、娟繁、秀雅、多元的精雕细刻作风以及传统工匠创作时的艺术感觉却没有因此而丧失,正是这种文化的根本属性,贯穿了整个“南派石雕”的发展路径。
五、结 语
一部惠安石雕的风格史,在艺术学意义上,也是“南派石雕”及其艺术流派的发展史和传播史。艺术风格的历史演变,往往不只是其自身单线的延续与成长,更多的是地理位置、政治影响、经济发展、技术进步、身份认同、文化自信之间相互交叉和影响的结果,是动态的发展。正如《文心雕龙·通变》中所说:“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可文,通则不乏。趋时必果,乘机无怯。望今制奇,参古定法。”[15]一在通,二在变。在全球化背景下,尽管惠安石雕与当代文化不断地碰撞,然而,直到现在,其风格总能展现出一脉相承的特点,“南派石雕”的特色依然明显。这说明全球化对人的影响,不会因为交融而消弭。当然,这种特色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在动态生成中不断更迭,在交流融合中不断变化,这种嬗变,既构成了惠安石雕艺术风格的发展路径,同时也为“南派石雕”艺术的研究提供了资源和依据。
——以《珠江纪事》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