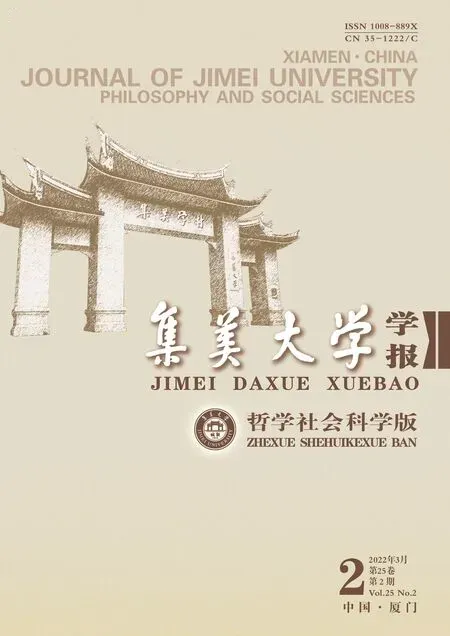中华文化共同体形成研究
熊建军,单晓云
(河池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西 河池 546300)
一、引 言
习近平同志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1]近年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成为中华民族话语体系表达中的重要内容。如果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我们就要承认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存在,这是一个先决条件。什么是中华文化共同体?根据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我们将其界定为:中华文化共同体是在中原文化与四方文化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交流、沟通、濡化、涵化,最终形成的一个以汉文化为主、“四夷”文化为辅的既具文化共性又有文化特色的文化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里,主流文化作为自我存在,具有历史的和现实的影响力,而曾经的他者,在文化的交流与演变中,逐渐进入文化共同体成为内部的他者:一方面,成为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又与主流文化存在差异。或者说,曾经作为远方的文化存在,在以华夏文化作为参照体系的观照中,成为既不是纯粹的他者,也无法完全归入到自我文化系统中的另一种文化,于是“内部的他者”似乎成为一个可以指称的更为贴切的归类选项。“四方”文化与“中心”文化的不断发展变化、交流传播,最终形成了一个具有明显政治意味的“自我”。在这个“自我”里面,因为多元性和差异性的存在,“内部他者”成为中华文化的独特景观。而这一景观的形成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从最初的中国与蛮夷戎狄文化平等、各自为据到后来中心从自我角度出发,审视他者的存在从而带来文化交流与冲突,再到历经政治改造、文化理解,使得文化互融互通,最终形成了庞大的中华文化体系。
中华文化在历史的早期除了主流(中原文化)之外,存在两条主要支流:一是华夏远裔,这一支流的文化演化经历了由自我而他者再到内部他者的过程;一是文化他者,这一支流是渐次归入中原政权政治统治的远方文化,经历了自他者到内部他者的转化,其转化时常受到中央政权用无思想的影响。无论是华夏远裔还是中原文化的他者,在其演变过程中都存在着跨文化的冲突、交流、适应与融入。在主动与被动、适应与冲突、分裂与整合的文化传播过程中,不同文化在阻拒与协调间最终统合成了中华文化共同体。在这里,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中华文化共同体不单纯是大家普遍认为的以儒家文化为核心,融合了法家、墨家、阴阳家、道家、佛教等文化的文化综合体,这实质上只算是“中原文化”而非“中华文化”。同时还需要清楚认识到,三代时期形成的文化仅仅是后来汉文化的主流,而非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华文化的全部。
本研究以主流文化和西、北支流文化作为主要对象,以正史内容作为主要材料,分析中华民族体系下,不同文化身份在中央政权的价值取向、文化观念及其视角转换下的跨文化传播,以期更好地认识中华文化共同体的演变与形成。
二、文化的主动融入
华夏远裔曾经与炎黄子孙同源同种,随着空间迁移,从中心而边缘,又历经时间变迁,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但是,在中心文化的激荡下,最终又选择了回归。在回归中心的过程中,面对远祖文化与后生成文化的碰撞,他们大多持一种积极主动的心态,其中匈奴、鲜卑、契丹最为典型。匈奴、鲜卑、契丹都属于炎黄远末子孙,因为居所不同,所以文化有异。“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2]2879;“魏之先,出自黄帝轩辕氏。黄帝子曰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3]1;“辽之先,出自炎帝,世为审吉国,其可知者盖自奇首云”[4]24。也就是说,匈奴、鲜卑、契丹等族,追根朔源,均为炎黄后代。
作为炎黄后裔,有意识地吸收中原文化成为其文化发展的重要环节,最为典型的就属鲜卑。魏太宗拓跋嗣“兼资文武,礼爱儒生,好览史传,以刘向所撰新序、说苑于经典正义多有所阙,乃撰新集三十篇,采诸经史,该洽古义云”[3]35。除了魏太宗,魏高祖拓跋宏对中原文化的喜好更是前无古人:“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受师,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在兴而作”[3]121。拓跋宏对于中原文化的学习不止皮毛,而是深入骨髓。儒家《五经》,过目即讲;史传诸子,遍历兼览;老庄之义,明晓通达;诗赋铭颂,即兴而作。此足见中原文化对其影响之大。正是在这一前提下,才出现了迁都、易姓、更服之举。孝文帝即位的第二年,即延兴二年(472),发布诏令:“顷者,淮徐未宾,尼父庙隔非所,至令祠典寝顿,礼章殄灭,遂使女巫妖觋淫进非礼。自今有祭孔庙,制用酒脯而已,不听妇女杂合,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违制论,其公家有事,自如常礼。”[3]88在重视儒家先圣的基础上恢复汉家礼制,自此寝顿殄灭的祠典礼章又得到重视。延兴三年(473),“诏以孔子二十八世孙鲁郡孔乘为崇圣大夫,给十户以供洒扫”[3]89-90。这当是自汉尊儒术以来,少数民族政权对孔子后人加封第一人。随着社会发展,孝文帝文化整合的力度加大,在婚姻制度、官制结构等方面都倾向于汉制。在社会生活中,尤其是在下层社会管理中,尊崇乡饮之礼,认为“乡饮之礼废,则长幼之序乱。孟冬十月,人闲岁隙,宜于此时,道以德义,可下诸州、党、里之内,推贤而长者,教其里人父慈、子孝、兄友、弟顺、夫和、妻柔”[3]102。他甚至学习孔子删诗之法,“诏定乐章,非雅者除之”[2]102。就孝文帝而言,因为他对主流文化秉持了一种积极适应的态度,因此他的文化改革实质上是一种文化身份的回归。太和十九年(495)六月,又下诏改变工作语言:“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违者,免所居官。”[3]114这是有历史记载以来,少数民族政权第一次对于使用汉话作为官方语言或者工作语言的统一要求。对语言的改变目的当然是改造文化,而这种文化改造实际上是对优秀文化的吸收,是一种融入社会主流文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主动同化。作为鲜卑的代表,拓跋宏的这一系列举措无疑是大胆且需要勇气的,即便在今天,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依然有借鉴意义。一方面,支流文化要思考如何向主流文化妥协;另一方面,支流文化融入靠拢的同时,主流文化如何有条件让渡,以确保多元性的成长。很难想象,一个文化多元,但缺乏主导文化统领的社会能够和谐、稳定的发展。
除此之外,与华夏文化同根同源的契丹文化也表现出了对中原文化的亲近,对儒家思想、礼仪文化、音乐文化的吸纳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辽初,尊孔子为圣,并时时拜谒祭祀。太祖神册四年(919):“秋八月丁酉,谒孔子庙,命皇后、皇太子分谒寺观。”[4]15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文化动脉,被当时的少数民族政权所尊崇,足见其文化生命力和影响力。在此基础上,辽还杂用汉朝礼仪、服辇,“辽本朝鲜故壤,箕子八条之教,流风遗俗,盖有存者……又有辽朝杂礼,汉仪为多”[4]833。“太宗皇帝会同元年(938),晋使冯道、刘昫等备车辂法物,上皇帝、皇太后尊号册礼。自此天子车服昉见于辽。太平中行汉册礼,乘黄令陈车辂,尚辇奉御陈舆辇。盛唐辇辂,尽在辽廷矣”[4]901。“定衣冠之制,北班国制,南班汉制,各从其便焉”[4]905。“会同中,太后、北面臣僚国服;皇帝、南面臣僚汉服。干亨以后,大礼虽北面三品以上亦用汉服;重熙以后,大礼并汉服矣。常朝仍遵会同之制”[4]908。此时,礼乐、车服尽在辽庭。契丹对于中原文化的主动接受,音乐是另一个重点:“自汉以后,相承雅乐,有古颂焉,有古大雅焉。辽阙郊庙礼,无颂乐。大同元年(947),太宗自汴将还,得晋太常乐谱、宫悬、乐架,委所司先赴中京”[4]883。“辽雅乐歌辞,文阙不具;八音器数,大抵因唐之旧”[4]884。最初,辽无雅颂之乐,其来自中原,除此之外,辽国大乐、散乐,亦均来自中原:“辽国大乐,晋代所传。杂礼虽见坐部乐工左右各一百二人,盖亦以景云遗工充坐部;其坐、立部乐,自唐已亡,可考者唯景云四部乐舞而已。”[4]886从文献记载看,契丹关于政治管理尤其是官制方面效仿中原文化的不多见,但是他们却自觉地在接受礼、服、舆、乐等文化,并表现出主动融入的姿态。在这种融入中,契丹一方面没有放弃其主要文化,另一方面对于新文化体系中的一些做法和规定性开始自觉的学习,显然这促成其跨文化适应,也导致新的文化体系形成的可能性增加,这可以视作文化的濡化。
在文化的接触中,匈奴是一个渴望融入但又受到阻碍的特殊个案。匈奴老上单于稽弼初立之时,汉朝延续了高祖时期的和亲政策。汉文帝使宦官中行说傅公主之匈奴和亲,中行说拒绝了朝廷安排。汉室强使之行,至则降单于。当时,因为已经存在物物交换和双方物品互赠,匈奴知道中原物产富饶、物品精细,对中原之服饰饮食多有羡慕,稽弼更欲变民俗好汉物。稽弼这一文化思想受到被其重用的中行说的明确反对。他认为匈奴的文化特色千万不能丢弃,否则会失去对汉朝的“文化优势”,最终必将与汉人无异:“‘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也。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其得汉缯絮,以驰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汉室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于是说教单于左右疏记,以计课其人众畜物。”[2]2899《史记》的这段记载可以说是历史上较早对跨文化认识的记录。首先,他认为文化应该自信,所谓匈奴所以强,是因为“衣食异”之故,这是匈奴文化的优点;其次,能看到文化的差异与不足,认为匈奴所不足不在衣食,而在文书计算方面,这是需要改变的;再次,他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不要自觉被同化。他认为单于变民俗而好汉物,最终的结果是尽归于汉,这种“尽归于汉”当然不是归降归顺,而是被同化,从匈奴而成为汉人。因为中行说的存在,导致了匈奴文化与主流文化适应与冲突的双向选择。
关于汉人对匈奴文化的批评,尤其是对“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取其妻妻之。无冠带之饰,阙庭之礼[2]2900”的乱常行为的批评,中行说强为之辩:“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恶种姓之失也。故匈奴虽乱,必立宗种。今中国虽详不取其父兄之妻,亲属益疏则相杀,至乃易姓,皆从此类。且礼仪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极,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筑城郭以自备,故其民急则不习战功,缓则罢于作业。嗟土室之人,顾无多辞。令喋喋而占占,冠固何当?”[2]2889他认为,匈奴之所以有父子兄弟死而继承王位者妻死者妻的传统,是因为受到客观条件的影响,担心种姓消失。其所分析的汉文化特色和匈奴文化特色,自然带有明显的狡辩的故意。中行说辩称匈奴君臣关系相较于汉室更为简易,虽然伦常混乱,但是宗种却延续。他认为礼仪虽然重要,但一旦衰败,则会导致君臣上下怨恨,言下之意礼仪虽然有用,但不可能一直秩序井然,一旦凋敝,不如没有。他还认为汉人耕桑以求衣食,筑城郭以自用,虽然衣食无忧,遮蔽风雨,但易耗尽民力。在中行说看来,汉人习俗不如匈奴的人食畜肉,畜食水草,人习骑射。从文化的角度来讲,匈奴的妻父子兄弟妻,贵壮健、贱老弱不符合汉文化一直以来的人伦关系和道德观念,但是中行说能够站在他文化的角度来看待和分析文化,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当然,对于匈奴的贵壮健、贱老弱的做法,中行说的解释显然非常牵强。
中行说作为一个“政治叛徒”,他在民族大义上可能颇为人诟病,但是他在保存文化多元性、保存自身(匈奴)文化、传播先进文化方面应该是一个先行者。正是他阻止匈奴毫不保留地对汉文化的吸收,才保证了匈奴文化的特殊性,也才保留了文化激烈碰撞的可能,从而使得文化参照得以更明显的存在。而匈奴作为中原文化的一个参照存在,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匈奴国家的两种模式——经济上依赖于中华帝国,军事上对付中华帝国——并非是完全相互排斥”[5]135。而正是这样一种排斥又依赖的关系,一方面增加了文化间的冲突,另一方面使得双方不得不相互适应。
除了华夏远裔主动融入和吸收主流文化,在文化传播中,还存在主流文化收缩而外部文化积极进入的情形,这一文化传播现象主要发生在宋朝。宋初,出现了四方来朝来献、中心文化主动龟缩的局面。据不完全统计,单是太祖年间,就有40余国来献、来贺、来降抑或内附,呈现出文化交流的繁荣景象。但是史书对宋朝外出却鲜有记载。或者说,宋朝甫一建国,就奉行一种收缩主义的文化交流方略,很少主动对外开展文化传播。太祖年间,有记载的宋人去境外使或考察屈指可数,规模较大的一是乾德四年(966),行勤率团游西域:“癸未,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各赐钱三万,游西域,”[3]23还有就是开宝八年(975),“庚辰,遣阁门使郝崇信、太常丞吕端使契丹”[6]44。这与络绎不绝的来献、来朝显得极为不对称,可见宋朝对外联系很不主动。当时,宋周边权力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前朝留下来的四分五裂的割据政权;一是周边存在的少数民族政权。面对权力四分五裂的情形,宋朝统治者采取了较为内敛的方式维系与周边各政权的关系。这一方面和当时的政治形势相关,另一方面大概和宋太祖本人奉行的“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6]51的治国方略不无关系。也正是如此,在史学家们看来,“宋于汉、唐盖无让焉”[6]51。宋与汉唐如何相比?论国力、论疆域,显然都无法相提并论,唯一可比的大概是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也就是说有宋一代,文化的发展甚至超过了汉唐,除了内部文化蓬勃发展,这种超越也当然地体现在跨文化传播的层面。如果从跨文化的角度而言,华夏文化的内涵因为“万国来朝”的局面得到了充分发展,或者说,宋初文化输入明显,而文化输出不足。太祖之后,宋太宗的政策虽稍有变化,但整体来看,还是沿袭了太祖传统,其中文化往来依然不改太祖时代的面貌。南渡之后,与西、北诸少数民族政权交往愈稀,虽有至者,不过寥寥。甚至可以说,有宋一代,汉文化向外发展与传播进入了一个低潮,但给中原文化吸纳其他文化成分,进一步获取旺盛的文化生命力创造了机会,因为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实力逐渐南移,文化的交融、碰撞也日益频繁,导致了文化间的沟通与融合,从而为主流文化注入了更多的新鲜血液。
在中华文化的历史上,虽有“胡”“华”之隔,但华夏远裔还是以“中华”为荣,因为这之间存在着文化血脉的联系。“所谓的‘中华’,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不是以民族集团为标准,而是重视接受和具有何种文化。当一个人接受了中华文化之后,从民族的角度来说也就自然变成了华夏”[7]。主动融入既是少数民族文化、四方文化对于中心文化的朝圣,也是主流文化内涵增加的过程。虽然在这个过程中难免出现诸如中行说那样的特殊情况,但并不妨碍中原文化的传播、延伸和新鲜血液的融入。可以说,作为早期中华文化的重要支脉——华夏远裔,对于主流文化的学习大多显示了主动积极的一面。与之对应,那些缺乏根脉,但又因为时代变迁在政治上受到统治的远方他者在接受主流文化时往往受制于中原政权用无思想影响。
三、用无观念支配下的文化传播
在商朝时期,文化中心区域在今天的河南商丘、郑州、安阳、邢台等地。四周,则有东边的人方、淮夷,西边的犬方、骊山氏、祭方、羌方、熏育,北边的鬼戎、鬼方、土方、危方,南边的南巢氏、虎方等不同文化存在 。整体来看,这些文化是处于商文化之外的。到了周朝,疆域扩大,中心文化势力范围也随之外延,大家熟悉的“中国”“夷戎”文化区分的含义也就更趋明显:“中国戎夷蛮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皮,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鞮,北方曰译。”[8]359-360这是中国较早谈论文化异同以及文化沟通的文献。《礼记》虽然成书于汉,但是记载的却是先秦礼制。从记载中不难看出,当时的五方之人,各有习俗,而不同主要体现在衣食住行等方面。所谓东夷披发纹身,不吃熟食;南蛮头有纹饰,也不吃熟食;西戎也是披发,以野兽之皮为衣,只吃肉,不食五谷;北狄穴居,以飞禽走兽的羽毛为衣,只吃肉不吃五谷。中原、夷、蛮、戎、狄,居于五方。五方之人虽各有习俗,但是并不孤立存在,大家都有沟通交流的愿望。而沟通的完成依赖于具有熟悉他文化的人的存在,在当时,寄、象、鞮、译是东、南、西、北跨文化交流的使者。这段文字至少表明了三点:(1)在当时还不存在文化的先进与落后的区别,既没有故意区分出“中国”文化比蛮、夷、戎、狄的文化优秀,也从另一个角度表明,早些时候,“蛮、夷、戎、狄”这些指称是没有贬义色彩的。(2)文化之不同是因为“五方之民”之故,亦就是环境不同,乃有区别。物理环境的差异导致居、味、服、用、器各有差异。(3)早期文化交流目的是“达其志,通其欲”,即最初的文化交流目的有二,一为情感交流,一为欲望满足。可以说,“中国”与“四方”的文化交流一开始就建立在有用与否的基础上的。传受双方更主要的是权衡利益需求,“用”“无”成为考量交流是否达成的重要依据。在华夏文化的传播过程中,这种实用主义的传播倾向常常出现,其中在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交流中甚为常见,可以说,用无之争成为中原与西域文化通绝的重要因素。
汉武之世,始通西域。初通西域目的非常明显,那就是“欲事灭胡”[9]2687,也就是希望寻找战略伙伴而灭胡。自此开始,向西通道逐渐打开。张骞西使归来,言于武帝西域大国众多,多奇物,这使得武帝兴致盎然,以为如果得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徧于四海”[9]2690。显然,基于实用主义目的的对外联系成为开端。也正是如此,历代定边疆尤其是西域之策,常在用无之间徘徊。当然,就统治者而言,他们清楚西域与中原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距离,得弃无损:“与汉隔绝,道里又远,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9]3930但这不妨碍盛世中原的对外传播。不过,此时的西域在中原统治者眼里更多的是器物一样的存在,是一个炫耀威德的对象。而稍后的范晔以为,定西域之策,不外两途:“自兵威之所肃服,财赂之所怀诱。莫不献方奇,纳爱质,露顶肘行,东向而朝天子。”[10]2931或以武或以物成为羁縻之策,而和亲、质子则是在此基础上的关系加深。不过汉朝与西域交流虽然出现了“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觉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10]2931的繁荣景象,但这种繁荣更多地体现在商胡往来、政治博弈上,基本价值取向依然是用无。因此,直接的文化交流,不是取决于远方文化的主动,而是取决于中原政权的用无思想,很多时候用无思想的主导直接延宕了文化间的传播,而过于强调是否有用成为中华文化融合的障碍。
用无思想最正式的提出大概是杜钦。是时,西域罽宾国以汉军不能至而剽杀汉使,引起朝廷震怒,至汉成帝时,罽宾国遣使献谢罪,汉欲遣使者报送其使,大臣杜钦以为:“前亲逆节,恶暴西城,故绝而不通……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蛮夷之贾,劳吏士之众,涉危难之路,罢弊所恃以事无用,非久长计也。”[9]3886在杜钦看来,罽宾国所以派使者前来,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为了通货市买。“献”只是表象,目的是为了通商,而正是基于此,杜钦认为没有必要行险行远而事无用。从国家利益考虑,杜钦所言不无道理,但是从政治一统和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杜钦的“用无”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文化交流空间。
北魏时期,文化交流与联系依然受到了统治者用无观念的直接影响。北魏太祖道武帝拓跋珪时代,有司奏通西域,以为通西域“可以振威德于荒外,又可致奇货于天府”[3]3205。当时的官僚认识到通西域既可振威德,又可致奇货,请通西域。这依然是实用主义思路,而拓跋珪以另外的实用主义思想驳了回去:“汉氏不保境安人,乃远开西域,使海内虚耗,何利之有?今若通之,前弊复加百姓矣。”[3]3205“利”成为是否通西域的重要因素。而对于彼时西域诸国遣使来献,太武帝拓跋焘也认为:“有求则卑词而来,无欲则骄慢王命,此其自知绝远,大兵不可至故也。若报使往来,终无所益,欲不遣使。”[3]3206拓跋焘和拓跋珪的意见是一致的,都徘徊在有用无用之间,以利益角度衡量相互关系,这在文化传播史上算得上一个挫折,这个小挫折并不妨碍后来中华文化的形成,但对当时的文化传播的影响却是明显的,出现了长期以来与中原政权有联系的西域一方面与南边政权断绝了联系,另一方面又受到北边政权的冷对的情形。虽然民间传播依然进行,但是政府间缺乏使节这个重要的联系环节,直接导致中原文化对西域文化影响的减弱。后来虽然与西域关系恢复,往来亦甚为频繁,但是较之于有汉一代,显然是衰微的。
隋朝时代,中原政权恢复了与西域的联系,与高昌的关系最为紧密。而以史臣观点,中央之于远方,用无观念依然明显:“自古开远夷,通绝域,必因宏放之主,皆起好事之臣。张骞凿空于前,班超投笔于后,或结之以重宝,或慑之以利剑,投躯万死之地,以要一旦之功,皆由主尚来远之名,臣殉轻生之节。是知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也。炀帝规摹宏侈,掩吞秦、汉,裴矩方进《西域图记》以荡其心,故万乘亲出玉门关,置伊吾、且末,而关右暨于流沙,骚然无聊生矣。若使北狄无虞,东夷告捷,必将修轮台之戍,筑乌垒之城,求大秦之明珠,致条支之鸟卵,往来转输,将何以堪其敝哉!古者哲王之制,方五千里,务安诸夏,不事要荒。岂威不能加,德不能被?盖不以四夷劳中国,不以无用害有用也。”[11]1859-1860史家对隋以前通西域的是非功过做了简单的总结,整体上是反对通西域的,认为自古以来远通绝域多为好大喜功之主、好事之臣、轻生之士,而维系与西域关系的方式大概不过两种,或者利诱,或者征服,原因在于帝王的天朝心态和臣子的轻生之念。在史臣看来,真正的贤明君王,不是做不到威加德被,而是清楚不能以“四夷劳中国,不以无用害有用”。但史家们恰恰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正是自汉以来的喜功之主、好事之臣、轻生之士,才有了中华文化的壮大。非此,则无今日之文化共同体。当然,我们必须承认,用无观念的博弈,使得跨文化传播的自觉性减弱。
唐朝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四夷联系密切,文化在适应与冲突间得到长足发展。虽如此,朝廷对于通远方的态度仍然处于用无之间。魏徵以为:“陛下即位,高昌最先朝谒,俄以掠商胡,遏贡献,故王诛加焉。文泰死,罪止矣,抚其人,立其子,伐罪吊民,道也。今利其土,屯守常千人,屯士数年一易,办装资,离亲戚,不十年陇右且空。陛下终不得高昌圭粒咫帛助中国费,所谓散有用事无用。”[12]6222作为政治家的魏徵,面对远方,没有看到文化交流的意义,没有考虑文化的扩散与影响,仅仅是站在政治功利的角度来看中原与四方的关系,以为散有用事无用不可取。紧随魏徵的还有黄门侍郎褚遂良,他说:“古者先函夏,后夷狄,务广德化,不争荒逖。今高昌诛灭,威动四夷,然自王师始征,河西供役,飞米转刍,十室九匮,五年未可复。今又岁遣屯戍,行李万里,去者资装使自营办,卖菽粟,倾机杼,道路死亡尚不计。罪人始于犯法,终于惰业,无益于行。所遣复有亡命,官司捕逮,株蔓相牵。有如张掖、酒泉尘飞烽举,岂得高昌一乘一卒及事乎?必发陇右、河西耳。然则河西为我腹心,高昌,他人手足也,何必耗中华,事无用?”[12]6222无论是魏徵还是褚遂良,看待主藩关系都是站在“用”与“无”的角度,缺乏更为远阔的“大一统”视角,更缺乏文化传播与交流的视角。从文化的角度来说,魏徵以为“物”不我用,耗民伤财,断不可取。褚遂良则以为古之先例就是先包容华夏,再考虑经营夷狄,而高昌诛灭,李唐天下威动四夷,但同时也存在很大问题,那就是因为征伐导致河西一带,十室九匮,这种现状长时间难以恢复,再加之征伐之后,年年遣人屯戍,更致陇右、河西虚空。如此,实在是耗中华事无用。褚遂良的说法其实和魏徵相同,落在了物不我用则是无用的价值取向上。从二人所论不难看出,文化接触引起了社会变迁,但与此同时也给主流文化带来了压力,导致了一些人对外部文化意义的质疑,从而拒绝沟通与交流。持这种观点的人强调沟通的价值,强调用无观念,希望与他者的交流可以让自我满足或者获得利益。这种文化传播价值取向使文化交流变得被动,实际上延宕了文化的传播与创新,“没有一个研究变迁的当代学者,会不同意说传播或借用是创新的最普遍的形式,由此得出结论,在文化内涵中绝大部分的因素是借用来的”[13]26。简单地站在用无基础上的传播无疑对华夏文化的创新起到了一定的阻碍作用。在中国古代文化变迁的历史上,文化传播因为存在过于真实的实用主义思想,从而导致了文化内涵的生长缓慢,延缓了文化内涵的增加,今天,这依然是我们必须警惕的。
华夏文化之初存在的中原-远方的空间概念,在文化意义上而言,是平等的。但是随着社会发展,不同文化间的斗争日趋激烈,这时候文化优劣论渐趋明显,在优劣论的指向下渐生出用无论,而用无思想的交锋使得文化传播常常处于被动的语境之中,它促使我们形成了一个“远方”印象:“一直将西域视为远方,不独是地理上的远方,也是文化的远方,是认同的远方,是交流的远方。”[14]从而使得文化传播落入被动一面。在这里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唐朝的时候,用无思想虽然交锋激烈,但是因有为用常常成为主流,与此同时,统治者以声色犬马羁縻诸藩的实用主义恰恰成为文化传播的无心之柳:“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升平,而玄宗以声色犬马为羁縻诸王之策,重以蕃将大盛,异族入居长安者多,于是长安胡化盛极一时,此种胡化大率为西域风之好尚。”[15]这大概是基于用无思想牵引下文化获得的一个令人欣喜的结果。
四、天朝心态与文化整合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一种文化对他种文化的吸收总是通过自己的文化眼光和文化框架来进行的,也就是要通过自身文化屏幕的过滤”[16]。在华夏多元文化的传播与交流过程中,不同文化的比较成为必然,他者在比较中出现,我族中心主义者也随之诞生。随着社会发展,中原政权日益强盛,中原文化开始自觉地与相邻的游牧民族进行文化上的区分。统治者认为自我文化天然是优秀、先进的,其他文化体系是落后甚至野蛮的。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天朝心态愈发强烈。历史上,关于四方民族文化的书写大多是站在汉文化角度——我族中心主义的视角进行的。书写者对文化的定义与中心视角直接相关,于是书写前的价值判断实际上已经很明显地带有“他者化”的色彩。汉使也好,唐臣也罢,看轻四夷文化也就不奇怪了。而站在他者角度理解文化并不常见,以天朝心态对付天朝心态也不常见,中行说是其一。因为了解汉朝的天朝心态,他依其道而行之,用汉文化的方式帮助单于建立文化自信,并渴望借此打破中心视角。《史记》记载:“汉遗单于书,牍以尺一寸,辞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中行说令单于遗汉书以尺二寸牍,及印封皆令广大长,倨傲其辞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2]2899中行说的做法看上去有一些孩子气,有些自欺欺人的意味,但这正是中行说对汉朝天朝心态的一种回应。他很清楚,中原政权自周以来,各种规矩礼仪繁复严苛,这繁复严苛的礼仪规矩实际上是权力秩序、身份高低的象征。中行说之所以这样做,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消解汉朝统治者的中心视角。他利用汉朝看重的“规矩”从气势上来反制对方,目的是从心理上占据优势。这种看上去更像斗气的行为,暗含了中行说的报复心理,实际上也是对汉王朝逐渐诞生的天朝心态的回应和嘲讽。但是,这种较量并不能消除具有地域、心理、文化优势的汉王朝统治者的天朝心态。汉武帝之时,因为中原向匈奴提供物产繁多,且匈奴希望获得与中原平等的地位,从而激起了中原反击。在统治者看来,“对中原标志性秩序的违背,不管是表现为灾异,还是体现在人类行为的规范方面,都有着直接的政治意义,他们敏锐地意识到抗击这种标志性秩序所带来的威胁”[17]。于是,维护天子的天朝心态逐渐明显。
汉元帝时,大将陈汤任西域都护副校尉,矫天子令攻杀郅支单于:“天下大义,当混为一,昔有唐虞,今有强汉。匈奴呼韩邪单于已称北藩,唯郅支单于叛逆,未负其辜,大夏之西以为强汉不能臣也。郅支单于惨毒行于民,大恶通于天……犯强汉者,虽远必诛。”[9]3015“犯我强汉,虽远必诛”的誓言体现的是汉文化为主宰的心理,是典型的“我族中心主义”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帝王时代,正是这种民族主义的价值取向造就了华夏文化的整合。如果说汉朝在西域设置都护、设置校尉是对西域行政管理之始,那甘延寿、陈汤的上疏则可以视为“我族中心主义”的强化,表达了一统天下的观念,也表达了对自我行为方式的肯定与认可,对他者行为的否定与贬低。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汉武帝在北方实施徙民戍边政策,在江淮实施越人内嵌策略,从而使得中原文化的四周扩散、文化的传播与影响变得更为活跃,尤其是人口迁移增加了不同区域、民族、文化接触与交流的可能性,文化的理解与变迁速度加快。
彼时,中央政权在与边地和藩国交往时都会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对待这些从地理和心理距离上都下意识地被我们认为是 “远方”的人与物,也正是这种思考使得天朝心态渐盛:“夷狄之人贪而好利,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群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涉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也。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靡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9]3834中原政权的统治者们选择了一种表面上有效但实际上简单的方式。之所以说方式简单,首先是天朝站在“我”的角度对“他者”的异化与偏见,这种方式导致了对“他们”的消极观念的产生。或者说,这种基于“我的”视角的形象塑造是华夏历史上少数民族负面刻板印象形成的主要原因。正是在异化与偏见中,我们越来越肯定了自己态度的正确性和正当性;其次,从汉朝开始,我们一直在强调少数民族之于我的不同,也就是探求差异性成为重要视角,对共性的寻找与归纳从来没有站在主流文化的舞台上。因为自视甚高,我们很难从人的层面去审视对方,我们需要的是“权力”与“物”,是对于我们需要的“权力”掌控和对缺少的“物”的欲求;与此同时,天朝心态促使我们站在高处俯视对方,希望他们“慕义”而来。也正是在天朝心态的指引下,汉文化中心意识得到加强,防范文化差异成为常态,“世界被‘我们和他们’的概念所组织,个人的自身文化高于一切,而其他文化处于次要地位”[18]。这种俯视既增强了汉文化的高度,也使得他者身份转变成为必然。
国力越是强大,天朝心态越是明显。唐初,天下尚未完全安定,突厥时常袭扰,至贞观八年(634),突厥使者来访,预示着唐帝国拉开了统一华夏的帷幕。当时,面对突厥来访,高祖叹曰:“当今蛮夷率服,故未尝有也。”[19]17李渊此说,当然带有明显的炫耀成分,但也表明大一统走向深入,天朝心态更趋明显。太宗时期,唐朝不再立来奔者突利可汗为“可汗”,而是授右卫大将军,封北平郡王。李世民的这一做法实际上明确了突利可汗一部为唐朝直接所属,从他告诫突利可汗的话里也可以看出端倪:“昔尔祖启民亡失兵马,一身投隋,隋家翌立,遂至强盛,荷隋之恩,未尝报德。至尔父始毕,反为隋家之患,自尔已后,无岁不侵扰中国。天实祸淫,大降灾变,尔众散乱,死亡略尽。既事穷后,乃来投我,我所以不立尔为可汗者,正为启民前事故也。改变前法,欲中国久安,尔宗族永固,是以授尔都督。当须依我国法,整齐所部,不得妄相侵掠,如有所违,当获重罪。”[19]5161太宗这段告诫的起点是“恩”,“报恩”是天朝心态的基础,“恩,在用之第一位和最大的恩情,亦即‘皇恩’时,是在无限忠诚的意义上使用的”[20]。这大概是东方文化固有之义。从表面上来看,这是一个君王对藩国的训诫,但是却包含着几层意思:(1)借史鉴今,突厥有荷恩忘德的传统,权力给予越大最终背德的可能性越大。(2)由国而族的话语转换,也就是自突利可汗之后,原来的藩国身份发生了变化,成为唐之宗族。(3)从此以后,突厥一族当依唐朝律法,这是从政治层面的又一种关系界定方式。而这里,我们觉得最为重要的也是对后来影响最大的是国族宗族的话语转换。唐太宗以其雄才大略和高瞻远瞩充分认识到了欲中国久安,突厥宗族永固的方法就是身份转化。只有使之成为中央王朝的所属,他者成为自我的一部分,内部他者成为他者的归宿,如此,一统才能实现,天朝才会成为可能。当时统治者对于民族政策的看法并不统一,朝议意见有别。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因其归命,分其种落,俘之河南兖、豫之地,散居州县,各使耕织,百万胡虏可得化为百姓,则中国有加户之利,塞北可常空矣”[19]5162,这种做法最直接的效果就是将其“化为百姓”,此之所谓“化为百姓”实际上就是打散其群居群动的习惯,同时改变其游牧习惯,使之成为中国百姓。魏徵的态度则代表了另一种观点。他以为周边民族的天性是“非我族类,强必寇盗,弱则卑服,不顾忠义,其天性也”[19]5162。站在自我文化的角度认知与理解他文化是一种文化惯性,魏徵的态度恰恰是文化自我属性具有先天优越性的表现,也是文化排他性的具体体现。在很多人看来,“中原-四夷”文化表象是空间的区隔,实质是“先进-落后”的文化体现,最终成为我们对四围文化认知和“中原-四夷”文化比较的极为稳固的定式。这种定式是一个历史形成的过程。在这个形成过程中,“他者”对于“自我”空间的侵入是不被允许的,这不但会损害“自我”文化的整体性,同时还会带来心腹之疾。所以说,如果将少数民族置于河南之地,带来的影响是无法接受的,后果也是无法想象的:“数年之间,孳息百倍,居我肘腋,密迩王畿,心腹之疾,将为后患,尤不可河南处也。”[19]5162魏徵作为肱股之臣,他从中央政权稳定的角度考虑问题是恰当的,但是因为“中原-四夷”的二元话语表达在当时已经被人们普遍接受,因空间距离而存在的文化距离被魏徵放大,于是文化认知差异带来了空间想象——有对现实空间的控制意识,又有对想象空间的排斥意识。魏徵对于自我控制下的文化空间因为外来文化的可能介入增强了控制意识,而对于“他者”文化的解读实际上不是全部的真实,更多的是建立在想象的基础上,或者说建立在自我文化优越性的基础上的。这种控制实际上早已萌芽,甚至深入群体内心,成为很多人的共识,看轻四夷文化成为惯性:“奈何以天子之尊,与匈奴约为兄弟,帝女之号,与胡媪并御;蒸母报子,从其污俗?中国异于蛮夷者,有父子男女之别也。婉冶之姿,毁节异类,垢辱甚矣。汉之君臣,莫之耻也。”[12]6024天朝帝国很多人认为以天子之尊,和外族结为兄弟;以帝女之名号,与胡女同事一夫是一种耻辱。最主要的是,论者认为,对于蛮夷之族,班固所谓的“接以礼仪”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礼让以交君子,非所以接禽兽夷狄也”[12]6025。在礼仪之邦的汉族人看来,夷狄缺乏君子之风,多的是禽兽习性,这是一种自古以来的先进与落后的对比。因此“圣人饮食声乐不与之共,来朝坐于门外,舌人体委与食之,不使知馨香嘉味也。汉氏习玩骄虏,使其悦燕、赵之色,甘太官之珍,服以文绮罗纨,供之则增求,绝之则招怨,是饱豺狼以良肉,而纵其猎噬也”[12]6025。显然,作为撕裂文化的代表人物,刘贶的观点也是建立在天朝心态基础上的,他对远方文化的态度是建立在历史遗留的刻板印象基础上的。当然,需要注意一点,刻板印象虽然往往是一种文化偏见,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它常常成为主流文化改造支流文化的重要动力,也就是说,文化的改变往往基于刻板印象的推动。
在天朝心态的影响下,在大一统的观念中,华夏文化传播呈现出集体意识与个人书写、权力传播与个体认同同时存在的景象。最为明显的就是唐代诗歌所表现出来的胡天、胡地、胡人、胡舞、胡乐的个人书写。随着唐代诗歌书写增加、流寓长安的胡人人口增加,文化交流进一步深入,个人认同也渐次多了起来,民间传播成为文化整合最为强大的磁场:“又使户奴数十百人习音声学胡人,椎髻剪彩为舞衣……又好突厥言及所服。选貌类胡者以羊裘辫发”[12]3564,“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着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19]1957-1958。此时,西域人华化、长安人胡化,西域美术、乐舞、技艺尽在长安,文化交流一片繁荣景象,由他者而内部他者的转化成为必然的文化景观。
自汉朝以来,中原政权的统治者就逐渐形成了天朝-远方、自我-他者二元对立的政治与文化观念,也正是这种观念的存在,使得中原政权在文化外向传播与吸收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中心-四方、先进-落后、天朝-蛮夷的思维。因此,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俯视的文化接受与传播成为常态,文化融合成为必然,而天朝心态实际上是中华文化共同体——一体化形成的重要动因。现代研究大多认为天朝心态是封建社会的糟粕,但是,我们如果将其植入历史语境中,会发现如果没有主流文化的天朝心态,没有封建统治者大一统思想,就很难形成有如此旺盛生命力的中华文化,所以说天朝心态实际上促成了文化整合。
五、结 语
自先秦而汉,自汉而唐,中华文化共同体在濡化、涵化、冲突、适应、交流与理解中逐渐形成并焕发出强大的光芒,即便后来受到元蒙、满清文化的冲击,最终也未改本色,反而愈显靓丽,形成了蔚为浩荡的中华文化洪流。在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用无观念”“天朝心态”和“刻板印象”等常常被大家认为是对支流文化的漠视、俯视和歧视,从本质上来看,中原文化确实存在这样的心态。但是,我们仔细分析会发现,在文化的交流过程中,如果缺乏文化间的优劣之分,缺乏对文化差异的认识,也就不存在跨文化的交流了。所以说,这在支流文化看来的负面恰恰是推动中华文化共同体形成的巨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