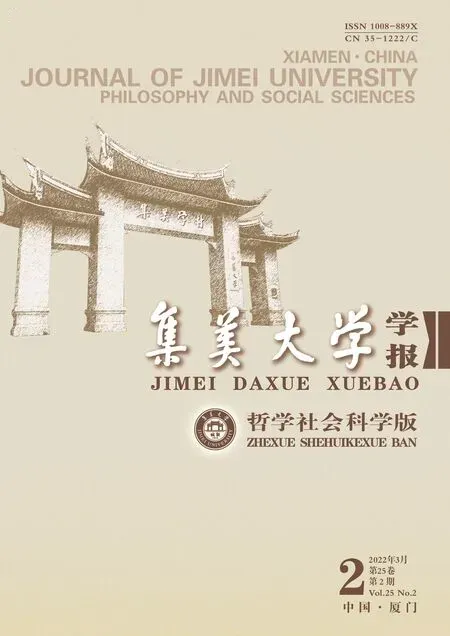西域流人庄肇奎的情感世界与流放心态
——以《胥园诗钞》为中心
杨 霖
(湖州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
乾嘉时期,新疆成为主要的流放地,大批获罪士人谪戍于此。谪戍期间,西域流人多作有诗歌记录其戍守边疆时的生活,如纪昀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获罪流放西域,作《乌鲁木齐杂诗》160首,涉及地理、农事、物产、风俗等方面,同时谪戍的徐步云有《新疆纪胜诗》记录风物、兴屯、山水等,之后曹麟开、陈庭学、祁韵士等人都有竹枝词吟咏西域的风光风俗、历史文化。乾嘉西域流人多以新奇之眼感受异域带来的新鲜感,却很少述及流放期间的情感起伏。庄肇奎谪戍西域十年,期间情感几经变化,诗歌创作也随之而异。他既作有《出嘉峪关纪行二十首》《闲云二首》等抒发流放之苦的诗歌,又有《伊犁纪事二十首效竹枝体》等客观反映西域社会状况之作,在西域流人中独树一格。笔者以庄肇奎戍守西域期间的情感变化为线索,考察其诗歌创作,通过把握其从流放初期受到地理环境的差异造成的冲击与不适以及流人身份所带来的愁苦,到逐渐适应西域,转而以欣赏的眼光看待西域的情感变化轨迹及其在诗歌中的反映,也可窥见乾嘉西域流人流放期间被隐藏的心理状态与情感世界(1)关于庄肇奎流放期间情感的转变,星汉《清代西域诗研究》一书第十三章第二节《八年不减亲情和乡情的诗作——庄肇奎》中略约提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庄肇奎(1728—1798),字星堂,号胥园,浙江秀水人。乾隆癸酉(1753)举人,历任广东布政使,有《胥园诗钞》十卷。《胥园诗钞》中记录其流放生涯的诗歌占大部,主要收于五至八卷,题曰《塞外稿》,另有流放途中所作诗歌,收于卷四《黔滇稿》中。庄肇奎塞外诸作不仅在数量上占优势,也是其诗歌之精华所在,长洲顾曾序肇奎诗曰:“先生为诗务以精意相融结,不袭蹈前人句律,而其生平仕宦又冒历艰险,迹其出处,有可慨者,然其诗于塞外诸篇为尤奇。”[1]1顾承也极力称赏肇奎西域诗歌,认为其足迹几遍天下,历经艰难险阻,所以其诗能“陶写性灵,别开一格”,而“若塞外诸篇,才力雄放,襟怀洒脱,虽古之作者无以过也”[1]2。谪戍期间,肇奎情感几经起伏,其诗歌创作心态也随之而变。流放途中,肇奎总体心情沉郁,而以嘉峪关为界,此前其借咏史怀古诗以抒发罹罪的不满,出关之后,异域之地带来的强烈冲击使其陷入巨大的不适与感伤之中。在西域生活期间,强烈的乡关之思时刻盘踞在肇奎的心头,成为他愁苦情绪的主要来源。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西域日渐熟悉,肇奎的情感逐渐发生了转变,能够主动欣赏西域的景色,转向乐观的心态,其诗歌风格也一变为明快之音。
一、空间转移与情感起伏
中京兆试后肇奎被选为瑞安县令,之后又被举荐为贵州施秉令,摄正安牧。因执法公正升松桃同知,还未赴任,即以有才奏调至滇,移补永北同知。云贵总督李侍尧十分赏识庄肇奎,令其入幕,倚重非常。乾隆四十五年(1780),李侍尧贪纵营私被举报,逮捕回京,被判斩监候。庄肇奎被李案牵连下狱,被判遣戍伊犁,同年五月,自滇出发前往京师诏狱,次年赴伊犁戍所。
流放途中,肇奎经过山西寿阳县、介休县、灵石县、赵城县、洪洞县、太平县、夏县,面对当地留存的历史文化遗迹,作有多首咏史怀古诗,藉以书写其获罪的悲愤心情。如《过洪洞县师旷墓》一诗赞扬目盲而心不盲的乐师师旷,认为盲与不盲不在于视听而在于心,真盲的人是其心被视听所蒙蔽,讽喻的意味不言而喻。《过韩侯岭行并序》一诗写其经过灵石县韩侯岭见韩信之土冢,惋惜其赤诚之心被历史所歪曲,真相不得而明,所以作诗以发明之,所谓“世人谁识韩侯忠,我今为侯一发蒙”[1]25-26。诗中极力赞颂韩信在楚汉之争时叱咤风云的英雄形象与忠诚之心,而叹惋其被吕后设计杀害的悲剧结局,在一唱三叹的感怀中不难见出其借此以抒己愤的心情。又如《过赵城县有蔺相如故里碑》《过皋陶墓》《过夏县有司马温公故里碑》等诗或感慨世变,或感怀英雄人物的不幸遭遇,无一不是其内心情绪的投射,在慨叹中抒发自身罹难之悲苦。
乾隆四十六年(1781)季夏之初,庄肇奎行至嘉峪关。嘉峪关是进入西域的唯一关口,作为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化地标,“这一空间对于士人而言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是一个节点,这个空间的内外代表着不同的社会关系,产生了文化身份认同的差别”[2]。因此,嘉峪关这一隐喻符号,其所代表的夷夏之别、内外之分的观念极大地影响了肇奎心态的改变,入关之前的咏史怀古诗托古而隐晦地书写获罪之不满情绪,入关之后,在对塞外自然环境的隐喻书写中则表达着身处边疆蛮夷之地所带来的身份与文化方面的失落感。
入关之前,肇奎穿过山陕,到达甘肃,行进路线为历会宁县往北,经兰州、安定、永昌县到嘉峪关,出关后再向西行进。甘肃北边的自然环境和社会风物与内地有极大的差异,而与关外相接近。肇奎经过甘肃时,已有身履异域之感,路过永昌县时有诗句曰:“到此忽惊称邑号,由来天尽塞西头。”[1]29诗中永昌县位于甘肃河西走廊东部,祁连山北麓,隶属凉州府,而云南亦有一永昌,为府,位于边境,南临缅甸,肇奎任职云南时,每年年末会巡察此地,所以车行至甘肃永昌县,肇奎会有“忽惊称邑号”之感。由永昌县以西穿过河西走廊,即到达嘉峪关,由于地理位置的偏远与自然地貌的迥异,肇奎已将此地称为塞外、天尽头。而此前途经会宁时所作《会宁道中》一诗,更是详细描绘了甘肃北部的自然地理特征:
黄尘十丈眼双昏,五月披裘气未温。万叠土山谁放牧土山并无寸草,谁家陶穴自成村。边民不识丰年乐,眢井难寻苦水源民间无水井,水既苦,晴久亦涸,俱掘窖藏雨水以饮。过客停车避烽警,征夫深夜打柴门[1]29。
会宁县位于甘肃中部,是丝绸之路北线的要道,也是军事重地,素有“秦陇锁钥”之称,而其地处腾格里沙漠与黄土高原交接处,自然环境恶劣,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诗中也写到此地气候严寒、沙尘严重、干旱少雨、寸草不生,诗人以边民指称当地居民,在其看来,此地已与西域无太大差异。
季夏之初,庄肇奎出嘉峪关,并作《出嘉峪关纪行二十首并序》,八月十三日抵达伊犁城,乘马配刀谒见伊犁将军。出关之后,即便有会宁、永昌等地见闻的铺垫,庄肇奎对于西域最直接、最巨大的感受还是自然环境的极大差异造成的心理冲击。西域自古作为塞外荒蛮之地,尚永亮先生认为外贬意味着对于政治中心的疏离[3]90,遥远的距离与迥异的自然环境时刻提醒着流放者其政治地位与文化身份的失落。流人对于塞外自然环境的感知不仅是生理层面的感官感受,在生理感知的背后,更是埋藏着流人精神方面的失落与苦痛。嘉峪之雄关是严别内外的关口,又是皇权的隐喻,即便此地在京师万里之外,面对雄关,亦能感受到天子的威严。然而,“出关回首即门关,关吏无情未许还”[1]30,甫出关外,城门即被关严,这一仪式化的举动斩断了流人与华夏文明的联系,自此之后,朝向西域,面对的便是“沙碛遍留鸿爪印,塞云遥引马蹄还”[1]30的景象。荒凉而与世隔绝是肇奎对于西域的第一印象,《出嘉峪关纪行》诗序曰:“出嘉峪之雄关,指伊犁之绝域,过羌戎而投荒戍,当暮齿而别中原”[1]30,可见西域作为绝域荒蛮之地,是与中原相对的概念。诗中更是用“洪荒”“大荒”“荒土”“天涯”等词来描述西域的环境。
荒凉的印象落到实处,空间视觉方面首先是无边无尽的沙漠戈壁。戈壁沙漠寸草不生,一望无际,无论是“草木不生秋影阔,桑榆欲晚暮云沉出安西州即戈壁”[1]30,还是“萧萧白发三千丈,莽莽黄云一万程”,带来的都是“未知何处天方尽”的无望[1]30。林则徐亦有同感而曰:“天山巉削摩肩立,瀚海苍茫入望迷”[4],祁韵士亦云:“行径瀚海难为水,渡向恒河但有沙”[5]139。历尽艰辛,于漫漫沙漠之中忽见绿洲的惊奇亦是振奋人心的,“几重大碛盼斜晖,征汗终宵透葛衣。点水不生波万叠遥望戈壁如海翻波,三泉忽涌草初肥”[1]31一诗中叙述终于从如万叠波涛般连绵翻滚的戈壁中走出的欣喜。诗中小注曰:“自吐鲁番西行一百六十里皆戈壁,至三个泉,水甚甘美,此去戈壁渐少。”[1]31
巨大的风沙亦是荒凉印象的另一个方面。风有狂风:“揽辔欲停无荫树,飞轮忽起有狂风”[1]31;有悲风:“明月琵琶泪暗吞,悲风吹起劫尘昏”[1]31;有急风:“捲沙风似归心急,积雪山争夜月光”[1]38;有盲风:“上有黄云下白草,盲风乱卷霾龙沙”[1]41。悲风分明是诗人悲伤情感的投射,急风以比归乡之心。诗人以我观物,在移情的作用下,西域的风都具有了情感色彩,不同形式的大风将西域荒凉恶劣自然环境描述殆尽的同时,也将诗人面对异域之地的情感展现无余。
西域为典型的大陆性气候,温差很大,夏天酷热难耐,冬季寒冷无比。对于气温的感觉加剧了肇奎对荒蛮之地的体验。甫出关外,肇奎即在诗序中言:“戈壁滩边秋阳尤其烈”[1]30,自注:六月十八日立秋。即便已经立秋,而戈壁滩边的阳光依然酷烈,又无草木以遮荫,行路之难,可想而知。正如诗中所言:“几重大碛盼斜晖,征汗终宵透葛衣”[1]30,在望不到边际的戈壁中辛苦盼望日落的到来,然而夜晚的到来却并没有减少热气,葛衣终宵都被汗水所浸透。对于从南方来的流人,与江南温暖的自然环境相比,对于塞外寒冷的感知更加深刻。肇奎八月十三日抵达伊犁,此时正处仲秋之季,新疆的气温已经十分寒冷。“永夜角声寒不寐,透簾新月又初高”[1]31、“晓寒旃帐催残月,呜咽西风剑欲抽”[1]35,寒夜更添角声,忧愁无法入睡。旋而入冬,肇奎对寒冷的感知主要来自于对雪天的记忆,有不少诗作于雪天,如“晓风吹雪满篱垣,犬吠声敲冷巷门”[1]36、“去年残雪补残垣,曾记呼童冷候门”[1]36、“残敲晓柝灯初灺,冻洒孤棂雪正骄”[1]36。在冰天雪地中,“呵冻”书写的场面是肇奎对寒冷冬天生活最深刻的记忆。“呵冻”为嘘气而使冬天砚中凝结的墨汁融化,元代洪希文《春寒无炭》一诗有“吟成呵砚冰尚坚,毛颖蹇涩非张颠”[6]之句。洪亮吉诗曰:“心交海内今余几,呵冻裁书手自封。”[7]肇奎有多首诗歌写到其“呵冻”书写的场面,如“盘花卷烛流乡泪,呵冻成水断客书”[1]37一句写其不断呵冻的动作打断了家信的写作,在思乡的情绪之上更添一愁;“闭门呵冻独吟叹,忽然翻作狂歌行”[1]39一句写其在呵冻哀吟之时忽然兴起而歌;“流年如水人如戏,呵冻聊凭退笔书”[1]40,呵笔作书,感慨人生际遇。
总之,入关之后,迥异于江南的自然环境时刻提醒着肇奎身在异乡的处境,而西域特殊的环境与文化意义又加重了流放期间的失落感。在对西域恶劣自然环境的具体书写中肇奎抒发出他的苦痛,这种苦痛尤其强烈地表现在其对江南的记忆与书写中。
二、感官感知中的江南记忆
人的回忆通常会被味觉、触觉、视觉所触发,从而勾起连绵不绝的往事。身处于西域的陌生而艰苦的环境之中,流人对于江南故土的记忆更容易被不同的感觉所激起。被触发的故土记忆看似在当下给予诗人以慰藉,实则在回忆的过程中往往进一步加剧了昔是而今非的感知,在时间与空间的维度中,今与昔、西域与江南的强烈对比强化了诗人的痛楚与悔恨。庄肇奎的诗歌中,视觉与听觉是触发记忆的两种主要感觉。
在迁移频繁的社会中,语言的相对稳定性使得乡音成为故乡认同的重要方式。唐代贺知章脍炙人口的《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8]展现的即是在时光变迁中游子回乡时容貌老去,而乡音犹存的场景。在西域异乡之中,乡音无疑是激起故土回忆的重要方式。出关之后,西行途中,庄肇奎作“经月何曾展布衾,夜骑羸马走天阴。黄泥壁起黄鸡舞,白雪山寒白发心。酒可为生偏不嗜,梦能归去却难寻。老夫世累多抛却,剩有痴情是越吟”[2]30。这首诗叙述日夜兼程、累月前行的辛苦,而外在环境带来身体上的疲惫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流放”所带来的精神方面的打击,也即诗中所言“白雪山寒白发心”。在身心俱疲的状态之下,肇奎重新反思人生,抛却了诸多世累,而唯一不能放却的是痴情所在的“越吟”。“越吟”在此诗中有双重意旨,庄肇奎为浙江秀水人,表面看来,“越吟”实指其家乡方言。再者,“越吟”又称“庄舄越吟”“庄舄思归”,此典出自《史记·张仪列传》,传中陈轸引庄舄虽富贵不忘故国,病中吟越歌以寄乡思之典向秦惠王表明其忠心。因此诗中“越吟”的转喻运用,在实与虚两方面共同指向肇奎的江南记忆与思乡之心。
“越吟”的感知和记忆与当下境遇及自然环境的对照中形成的故土怀恋在行进途中看似带给肇奎以短暂安慰,如在伊犁时肇奎所作《晓雪莼涘招饮赋谢》一诗中所云“君自高歌吾老矣,乡音诗话共温存”[2]36,而美好过往可忆而不可得的体验实则加剧了肇奎的苦痛。在西安,肇奎得以与前往伊犁省亲的王鸣周偕行出塞,肇奎所作“挈伴青门笑语温,思亲征袖湿啼痕。有朋濯濯如春柳,嗟我蘧蘧剩蝶魂。塞雁重来谙道路,越禽相对语乡园。世间那得中山酒,潦倒先抛老瓦盆”一诗首联“笑语温”之后立即接以“湿啼痕”,“笑语”的存在引发了肇奎更强烈的思亲之情,而“越禽相对语乡园”一句可见诗人对声音的感知到了极端化的状态,越鸟相对而鸣被认为是其互相言说着家乡的消息,与首联呼应,越鸟的鸣叫引导肇奎进入思乡的情绪。于是,诗人想要借助中山酒一醉解除思乡之愁,中山酒又名千日酒,典故出自《搜神记》,刘玄石于中山酒家沽酒,酒家与千日酒,归家醉倒千日,家人以为其死也。经三年,酒家开棺呼之,醉始醒。又如《雪朝约同人晓餐,徐溉余因病不至,走笔问之》一诗中回忆昔年永嘉风雨之夜两人共话清宵的场面,此次极塞重逢,盼望共同回乡,归弄浙江之潮。徐溉余,名烺,字昆衔,号溉余,浙江钱塘人,因事流放伊犁。在“永嘉风雨话清宵”与此刻“残敲晓柝灯初灺,冻洒孤棂雪正骄”[2]36的景象比照之下,杯酒也不能浇灭心中之块垒。声音的感知又抒发了流放生涯中相逢的偶然与旋而即别的伤感,肇奎与方丞、张提举、杨明府三人一同获罪,肇奎被遣戍伊犁,而三人被发往乌鲁木齐,西行途中偶然相逢,共话遭遇,肇奎诗曰:“难里相逢亦枉然,暂留灯火话尊前。古人半在阳关外,老我孤悬伊水边。到此那堪还远别,归来难定是何年。萧萧征马催行色,鸿雁哀鸣又各天。”[2]32短暂的相逢与挑灯夜话的场景并没有为流放的旅途带来多少喜悦,反而更衬肇奎的孤独,匆匆的离别也强化了这种“相逢亦枉然”之感。
“越吟”是听觉上对江南的记忆,图像则是从视觉方面对江南的再度感知。祁韵士“西北云山看欲饱,独怜东望梦魂亲”[5]146从视觉疲劳的角度反向阐释思乡之情,肇奎则从图画的角度正面抒发怀乡之感。题画诗本无特别,但画中内容(江南)与展示背景(西域)的结合,对于肇奎则有特殊意义。在对江南风景不厌其烦地细致刻画与描绘中,肇奎如痴如醉,将其对江南故土的情感全部投入其中,而现实中的景象也即江南图像所展现的大背景——西域——时时将诗人拉回现实,在强烈的比照中肇奎不时发出无奈的喟叹。如《题春耕图》一诗详细地展现了牧歌式的江南春耕的典型图景,又在与眼前环境的对比中忧思感慨:
江南江北春水肥,稻胜麦陇摇烟霏。农夫相唤集南亩,如膏泥滑连云犁。曾孙至止田畯喜,村歌响答迎晴晖。曷来苍莽走天末,烟霞痼疾心事违。忽然展卷见风景,淋漓泼墨开愁眉。树涵宿雨罨绣野,人驱健犊来荆扉。白云深处自怡悦,谁与招邀入翠微?何人掉头不肯早,当年悔泣眠牛衣。雪山层簇寒成围,画中有路无从归。闭门僵卧看不厌,强起呵冻撚枯髭[1]33。
此诗中对江南春耕图景的描写与诗人当下的情感交织而行,诗歌开头春江、麦陇、云犁、农夫答歌在客观展现出“春耕图”图画中的场景的同时,传递出一片祥和的气氛。接着,肇奎叙述自己在身处边疆抑郁苦闷的状态中看到此图,心情舒畅。感慨之后,继而再一次详细地审视画面,对树木近景、人驱健犊的描绘中产生了归思,然而“雪山层簇寒成围,画中有路无从归”一联在与现状的对比中,诗人明了了无从回归的现实,产生出无奈与悔恨的情绪。再如,共同戍守伊犁的侍御炳焕其作《风雨归舟图》,请肇奎题诗,肇奎《题炳侍御焕其〈风雨归舟图〉》一诗在描绘图中所呈现的江南图景的同时,将更多的笔墨放在了对自身当下所处西域环境的书写中,旨在于对比中发泄其愁苦的情绪:
雪山高并青天高,莽莽四望穷周遭。伊江水流西不极,诸蕃屏息销弓刀。屹然此间一都会,黄沙争逐红尘嚣。我闻塞外太萧索,恰称闲心养冲漠。汉家都护万里侯,奉扬天命绥边略。奔走群下无弃遗,乘轩厄脱仍羁鹤。道旁握手逢王孙,轩然眉宇春风温。手持一纸索长句,披图泼墨淋漓痕。天末无情烟水梦,江南何处风雨村。水光潋滟山空濛,反怜深谷攒青枫。野舟恰受二三子,一生欸乃追冥鸿。归云渡口片帆月,诛茆崖际半亩宫。不知尘世有底事,但祝年间蝦莱丰。置身图外发长喟,王孙与我同秋塞。堞螺牧马互悲哀,黄云白草空叆叇。短衣挟策矜雄豪,相逢低首儿童辈。何当把臂入此图,吟瓢野笠长酬对[1]33-34。
此诗以西域之风景起,塞外雪山、青天、莽莽黄沙为日常司空见惯的景物,单调而萧索。图中所画正是庄氏情思所寄之江南,空濛的山色、深谷之青枫、荒野之冥鸿、渡口之片帆月与塞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相比之下,眼前的牧马、黄云白草更加索然无味,思乡的愁绪更加深重,于是诗人喟然长叹,遂生“把臂入图”的愿望。诗以现实之景起,以现实之景结,中间夹之江南风景的描绘,让人有种置身虚幻之感。诗末将视线从图画中拉出来,回到现实。对比之下,眼前的秋塞、牧马、黄云、白草的环境与“低首儿童辈”的屈辱让庄氏喟然长叹。末联“何当把臂入此图,吟瓢野笠长酬对”,“把臂入图”的奇愿将思乡心切的情感和盘托出。
除了在对水乡之图景的描绘中暂时抒发自己的江南之思,身处黄沙白雪之地,肇奎对江南水云之乡的记忆,常常存在于自己想象的画面之中。想象中的江南并非凭空虚构,而是基于过往经验的重新组构,是其对江南记忆的变形书写。塞外与江南景观为数不多的相似之处为天空之景,塞外的白云能激起诗人对于故乡的联想,如《闲云二首》其一曰:“龙漠黄沙里,天山白雪装。如何吟钓客,不共水云乡。坞曲停舟梦,峰高采药香。伊人自怡悦,欲赠远难将。”[2]37面对着塞外的黄山、白雪,诗人感慨为何这位吟钓客不在水云之乡,思绪回到江南,想象中故乡舟泛湖上,曲绕桥梁,伊人欲赠送所采之药,却因途远而难以实现。
再者,身处西域的肇奎时常登高望远,并将江南记忆抽象为“青一发”,这种极其强烈的夸张和比喻将其对江南的具体记忆抽象成了“青”这种江南的代表颜色。但其诗中“中原”实际转义指江南故乡,如其《秋感》一诗云:“凉云叆叇苦低垂,木叶萧森谢故枝。天且悲秋何况客,虫能鸣夜岂无诗。笛声杨柳依依怨,泽国芙蓉渺渺思。万里中原青一发,黄沙白草望迷离。”[1]35颈联中的“泽国芙蓉”之句已经表明“万里中原青一发”所指为江南。戍守闲暇时,肇奎常与同人登鉴远楼望远,希冀望见故乡所在,《次韵陈莼涘同人招饮鉴远楼二首》其一曰:“一发中原夕照斜,青山何处是吾家?倚楼有客吹羌笛,杨柳边声怨落花。”[1]38登高望远,却被连绵的环山阻挡住了视野,所谓“环山不断乡魂断,戍客难回野鸟回”[1]35,在夕阳夕照中,远方青山连绵,而何处是乡关。
三、再现江南与探索西域
庄肇奎带罪戍守伊犁8年,期满之后又留任2年,共10年。如此漫长的时光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初来时的惶恐与不适逐渐消退,而代之以苦中作乐的情怀。西域荒蛮之地,自然不比江南,肇奎一方面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尽力改造边塞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使之富有江南气息。另一方面,他也逐渐能够带着赞赏与惊异的目光欣赏西域独特的民俗与风物。适应西域的过程带给肇奎精神上的慰藉,抚平了其愁苦的情绪,使其能够安心地戍守边疆。
面对西域与江南环境带来的巨大反差,肇奎热衷于改造所处的环境,移花植草,使其成为“塞上江南”。初春季节,肇奎采摘回野外的桃花,将其插入瓶中,放于室内,仿佛看到了江南的影子。《对瓶桃有感》组诗通过隐喻写出其苦中作乐的心理过程:
其一:刘郎去后泪双红,此日嫣然到眼中。谩道马前都是雪,芦簾草阁贮春风。
其二:一笑浮生那有涯,蘼芜山下忆胡麻。桃花莫讶人为客,除却天台不是家。
其六:玉壶水里一枝斜,醉墨吟窗护碧纱。门外泥深人不至,闭门风雨独怜花[1]34。
第一首写与桃花久别之后重逢的惊喜,在四周大雪苦寒环境的背景下,芦簾草阁中瓶桃所铸造的春日的风景正如世外桃源般地存在于塞外,为诗人在寒冬带来许多慰藉。第二首自嘲流放生涯的漫漫无期,又用拟人化的手法劝慰桃花安心西域,莫要“除却天台不是家”,虽为规劝桃花实则自我安慰。第六首为瓶桃在室内的特写场景,碧纱窗前,醉墨案上,桃花一枝斜插玉壶水中。门外风雨交加,人迹罕至,独与瓶桃为伴,记忆中可望而不可即的江南此刻成为实景,欣赏眼前这幅瓶桃书案图即是享受其精心营造的江南春景。
瓶桃虽好而易谢,且其受空间的限制带来的观赏效果十分有限。肇奎将再现江南的范围由居室扩大到了庭院,在院中开辟了一片荒地,起名叫“西圃”,将别地的植物移植到自己的庭院以观赏。《西圃观桃二首》记其欣赏亲自栽种的桃花时喜悦的心情,诗下小注曰:“予于丁未之春植桃数株,是冬缘事入关,戊申夏季始回,今乃见花故云。”[1]50西圃中的菊花是肇奎移栽的植物中最多也是其最喜欢的花卉,带给他极大的慰藉,让他笑口常开:“去年曾赏菊花回,分种移将处处栽。隐士羁魂凭月唁,老夫笑口向秋开。”[1]35西域荒地本无菊花,“好事者”带来以伴孤独,而肇奎诗中菊花也化身为女子伴随其左右:
嫩凉鸿影角声愁,姹紫嫣红晓露稠。青女忽矜秋富贵,碧翁犹许客风流。翻从绝境怜生色,似向羁窗笑宦游。谩讶远移多好种,明妃较胜绿珠楼[1]38。
肇奎在诗中更是用夸张的手法记录了秋天各色菊花开放的盛况:“忽惊五色目欲迷,缃枝缥带成芳窟。颗颗珊瑚出大川,片片白玉种在田。黄金布地作幻相,紫茵铺径欲藉眠。恍疑群仙骑凤凰,蹁跹翠羽摇明珰。彩云满空飞不去,一朝谪堕下大荒。”[1]41盛开的菊花带来巨大的喜悦,十月之后,肇奎因公赴惠远城旬月,归来时花已全部枯萎,作《余于惠宁城寓中艺菊数十株,因公赴惠远城,旬月而返,花已尽槁,慨然作歌》一诗:
菊花乍开人已违,菊花睁开人未归。一朝策马排双扉,巡篱顿讶花容非。举头但见黄云飞,山木尽脱雪四围。我闻遐荒本无菊,好事携来伴孤独。去年收种付健仆,今年分种满茆屋。正拟开时深闭门,吟眠一榻倾芳樽。朝餐夕佩聊与安,羁魂呜呼紫塞人。依然逐红尘,冷香易销歇,寂寞江水滨。不学陶渊明,不肯折腰争虚名。不学康风子,服食得仙贪不死。与花同贬万里塞,花似怜人仍故态。呼童酌酒浇一杯,花如有知魂其来,长歌未已心转哀。吁嗟乎怀故乡,中原一发空苍茫。回首南山旧径荒,颓然醉倒空篱旁[1]36。
诗中肇奎错过菊花的盛开,等回到惠宁城中时,菊花已经枯槁殆尽,“正拟开时深闭门,吟眠一榻倾芳樽”的美好期待转瞬成空。肇奎对菊花的感情极深,有同病相怜之感,将其视为同贬边塞的伙伴,所谓“与花同贬万里塞,花似怜人仍故态”,能给予自己以江南故乡的安慰。菊花已逝,安慰不在,酌酒祭奠菊花之魂魄,且作诗长歌以书怀。
再现的江南风景局限于较为封闭的居所环境,居所之外,流人亦能逐渐对于西域景物持以欣赏的态度。洪亮吉诗中曰:“风光谷雨尤奇丽,苹果花开雀舌香”[7]127、“游蜂蛱蝶竞寻芳,花事初红菜甲黄”[7]129。肇奎《伊犁纪事二十首效竹枝体》采用竹枝词的形式,以新奇的眼光书写异域的见闻,风格明快疏朗,异于前作。《伊犁纪事》中涉及西域植物、食物、文化遗迹等方面,也是较为全面地反映西域物产、文化的组诗。西域风物的书写体现了肇奎对西域关注点的转移,也反映出其对西域态度的转变。西域虽然荒芜,但并非寸草不生,在戈壁沙漠中往往生长有奇特的植物,如芨芨草只生长于沙漠,可以用来制作簾子,在日照时间十分漫长的西域夏季,为流人们带来了一片荫凉:“午余苦热更斜阳到晚尤热,想夕阳西沉为更近耳,偏较中原昼景长自寅至戌日长八时有余。芨芨草簾风细细,青蝇也怕北窗凉。”[1]51果子花也只生长在西域,其“花嫩红色,枝条甚柔”,肇奎有诗曰:“果子花开春雨凉,垂丝斜亸嫩条长。一枝折赠江南客,错认嫣红是海棠。”[1]51又有一诗咏虞美人与佛茄花曰:“虞美人开遍小园,千层五色彩云屯。佛茄偏向黄昏放,别种幽香欲断魂。”[1]51虞美人与佛茄花也生长在内地,但西域的品种更加奇特,“虞美人花萼高三寸,色浓艳,中原所不及,佛茄花香独幽烈”[1]51。除此之外,肇奎又有《西圃罂粟花有大红及纯白色者大如牡丹鲜丽可爱诗以美之》《佛茄花》等诗咏西域之花。
西域的食材虽不及中原丰富,但也有新奇别致的特产,如蒲笋实为蒲根,颇鲜嫩可食,因竹笋为中原所产,伊犁不产笋,故起名叫蒲笋。哈密瓜为西域特有的水果,常年居住于伊犁的肇奎已经精熟于识别哈密瓜的品级,曰“瓜以白瓤者最佳”,又有诗曰:“六月争求节署瓜哈密瓜惟将军署中后圃所产最佳,移之他处种即变,剖开如蜜味堪夸。白居第一青居次,下品为黄论不差。”[1]51由诗可知,哈密瓜成熟于六月,有白、青、黄三个品级。伊犁所产大头鱼颇为肥美,每年二月中旬,于河畔即可捉得。林则徐在《回疆竹枝词三十首》中写道:“河鱼有疾问谁医,掘地通泉作小池”[4]127,肇奎亦曰:“伊犁江上泮水初,雪圃才消未有蔬。齐向鼓楼南市里,一时争买大头鱼。”肇奎在其他诗作中也流露出享受西域美味物产的情思,如友人于梅谷筑小亭,肇奎受托起名为寄亭,夏日相聚于寄亭,享受葡萄和野桃,诗曰“晚凉小酌釀葡萄,冰水堆盘浸野桃”[1]33-34,沉浸在如此良辰美味中,若非偶然抬头看见雪山高耸,肇奎竟然忘记了自己为客的身份。
除自然物产之外,肇奎对伊犁城的文化建置也颇为在意。《伊犁纪事》组诗第二首即通过伊犁城中西汉张骞留存的石碑来说明新疆的地形,“新疆形势地居巅,量度曾经初辟年。高过京师八百里得伊犁后量地约有此数,去天尺五古碑传。”[1]51之后又述及筑城中掘井之事,刚得筑城时,城中无水,计欲迁城,而将军伊伯传令昼夜掘井,遂得泉,城乃不迁,“戈壁滩头已驻兵戈壁即瀚海,城中无水欲迁城。试传军令齐开井,掘处皆泉万斛清。”[1]51
四、庄肇奎诗风形成与情感转捩的原因
相比其他西域流人的诗歌,庄肇奎西域诗歌的情感表现十分明显,且呈现出鲜明的阶段特点,这在西域流人中别树一格,而其形成则有内在原因与外在契机。总体来说,流放初期肇奎的诗歌充满了背井离乡的痛楚,这种阴郁情感在诗歌中的强烈表现是其他乾嘉西域流人所缺乏的,而其形成也是由多方面的原因促使的。
首先,主要来自于其自身的性格与初期人生经历。早期经历的不顺利造成了肇奎性格方面的压抑与忧愁。他曾自叙读书经历曰:“八岁读谟诰,九岁经笥便。十岁辨四声,学吟骚雅篇。十一始远游,飒沓千山巅。”[1]3如此勤奋刻苦,希冀将来能够大展宏图。弱冠之年,肇奎前往京师,但因其性格疏略耿直,不屑于阿谀奉承,所以不被王侯公卿所重。几回应试,终得科场获荣。在志得意满之时,却遭逢家难,祖父与父亲同时亡故,竟不得最后一面的机会。从此,一家8口的重担肩负于肇奎一人身上,“区区百劫身,轻如叶一片。生不识饥寒,何以处贫贱”[2]33-34。父祖为家中的顶梁柱,在父祖的辛苦经营下,肇奎从小过着优渥的生活,没有体验过饥寒之苦。家难后,家境直转而下,养家糊口的重担落在了肇奎身上,突然的转变,让他不知所措,感慨“生不识饥寒,何以处贫贱。”在这种自我过高的期许与在京师中的遭逢的落差,加之突然的家难的打击,使得庄肇奎性情变得沉郁。
其次,与同时流放及其他流放西域的文人相比,肇奎的官职较低,且任职于黔滇边陲,远离皇权中心。政治地位并不高,这给了他在政治氛围紧张的仕宦时期以喘息的空间,官职越低,离开皇权中心越远,其自我展现也越多,故其诗歌中能较多地抒发自己的愤懑情感。同样,乾隆六十年(1795)觉罗舒敏因父事被判流放伊犁时年仅十九岁,其《适斋居士集》中《惨别离》《述哀》等西域诗歌也充满哀戚之音。相反,官职较高或者任职于京师的流人,由于其政治处境的敏感,政治氛围的紧张,加之罹罪的惊恐,往往倾向于隐藏自身的哀怨之情,转而书写流放地的奇异物产与风光,歌颂皇帝开疆辟土之功绩。纪昀获罪时为大学士、徐步云获罪时为候补内阁中书学习行走,他们或者身居高位,或者任职于京师,对政治氛围的敏感促使他们善于隐藏自己的不满情绪,流放途中多作客观书写西域风物人情的诗歌。
再次,与流放时间的长短也相关。乾嘉时期西域流人流放时期大多较短,如卢见曾、纪昀、徐步云、蒋业晋、舒敏、韦佩金等人为二三年,更短者如方受畴、和瑛、成林、铁保等人为1年左右,洪亮吉甚至流放不足百日便被释回。时间较长者寥寥,如王大枢与舒其绍为10年左右。庄肇奎带罪流放8年,之后又补抚民同知2年,在西域总共生活了10年,是相当长的时间,由此也造成了肇奎不一样的心态。《胥园诗抄》中《送色司马心斋报满入都》《喜冯蓼堂放还作诗赠行》等多首送别友人期满回归的诗歌足以见其自我伤悼的情绪。
在伊犁流放地,肇奎的情感再次发生转变,除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逐渐适应西域的环境之外,转变的契机为与妾室碧梧的团聚。肇奎有一妻一妾,在黔为官时,其妻妾相伴。乾隆三十九年(1774)肇奎调至滇省为官,即遣其妻归乡,料理两代四榇营葬之事,此后,其妻一直居于嘉兴故乡,打理家事,妾室碧梧随宦滇中。乾隆四十五年(1780)五月,庄肇奎自滇北上时,碧梧就已身怀有孕。孩子尚未出世,便要生离,遣戍途中,肇奎作一诗,写其伤感之情:“一索初占八月临,笛梅悽绝小楼阴。绯桃将实枝离荫,紫藕方花叶卷心。刚得梦时灯耿耿,更无人处月深深。抱离他日重牵袂,应有啼痕洗翠襟时碧梧怀孕。”[1]23以植物作比,隐喻八月即将临盆的碧梧无法得到夫君的关爱。行至西域,面对恶劣的环境,对亲人的怀念更加剧烈,常有此生再无相见之日的担忧,“忧患何堪值暮年,雪霜无赖踞毛颠。阮咸独侍人俱散人瑞侄相随出关,苏过才生客已迁去年被难后得一子。蛮徼早应烟瘴死,昆明未尽劫灰然。只今八口飘何处,不信终成梦里缘。”[1]31生值暮年而遭此祸端,家人八口四处飘散,只恐与亲人的再度相见会终成梦里之缘。在伊犁戍所,庄肇奎也无日不被远离妻儿的哀伤所包围,乾隆四十九年(1784),流放已有五年之久,元旦日,肇奎作《甲辰元旦即事书怀》:“……锻翮落天外,岁月忽已徂。遥忆首如蓬,离銮抱孤独。儿生未识父,向母啼呱呱。偻指今五龄,拜母红氍毹。应嗟垂暮人,绝塞羁孱躯。谁怜母子心,形隔神与俱。顾予未龙钟,努力收桑榆。引领金鸡竿,欣欣复嘘枯。团圞祝椒酒,归卧云水区。”[1]37元旦应为团圆之日,肇奎却与家人天各一方,新得之子已有五岁,终未识父之面,只能将团圆之愿望寄托于酒中。
清代“流放官员除连坐发遣外,一般都是单身发遣,亦可携仆僮,但严禁携眷”[9]。妾侍的身份在此方面获得较大的自由。乾隆五十年(1785)十月十五日,碧梧自南而来,肇奎喜不自胜,难以相信此生竟能与亲人重逢于塞外,“敢信难中非死别,何期天外忽生逢”,在肇奎看来,男子尚未肯离开家乡,而碧梧一介女流竟然来到西域荒芜之地,他被这种万里相从的行为所打动,“笑汝痴情真过我,独轻万里远相从”[2]40。碧梧的到来缓解了肇奎强烈的思乡情绪,此后,其诗情绪方面明显好转,《元夕口占二首》作于乾隆丙午年(1786),此时,碧梧到来已有三月余,肇奎仍沉浸在重逢的感概之中,其二曰:“个人絮说梦中缘,盼断刀环已六年。破镜忽飞天外合,今宵也与月争圆。”[1]41
另一方面,肇奎情绪的好转与其流放归期近也有很大关系。乾隆五十一年(1786),已是肇奎在新疆的第七年,肇奎时时不忘归期将近,送别友人,也想到自己,“我亦明年归去来。”[2]42乾隆五十二年(1787)二月,肇奎因公事入关,次年四月六日再次出关,夏季始回伊犁。此次出关,其情感状态与首次出关时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西行的路途中,肇奎不再如上次般尽情抒发哀愁的情绪,而是将注意力更多停留在西域事物的书写上。《过玉门县》一诗中诗人想到了自己初次出关时思乡之啼涕痕犹在,此次重寻陈迹,却与此前情感不同,倾向于客观地书写西域的风物,如瀚海、雪山、疏勒河、赤金峡,在赤金峡后有小注:“自赤金峡至玉门县一百里,雍正五年曾置赤金所,今属安西。”雪山句后注曰:“出嘉峪关即瀚海,距雪山转远。”[1]48《戈壁》简述了自唐以来西域的历史之后,转而歌颂当今皇帝对西域开伐之功绩。本年七月二十六日肇奎卸篆,二十九日即出发。《生还二首》中流露即将归乡的狂喜之情“诗书乱卷待朝晖,感泣焚香拜紫薇……扶上征鞍忘老病,送行人见马如飞。”[1]51《伊犁纪事二十首效竹枝体》《纪伊犁事》都作于此后。
总之,庄肇奎流放期间的诗歌是其心路历程的真切反映,从初期流放途中以嘉峪关为界前后的情感起伏,入关之后强烈的乡关之思,到安守边疆,改造与欣赏西域的过程的展现,与其他西域流人相比,其西域诗歌较为全面与真实地记录了其在西域期间的生活与情感状态,借此也可管窥乾嘉时期流人群体的流放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