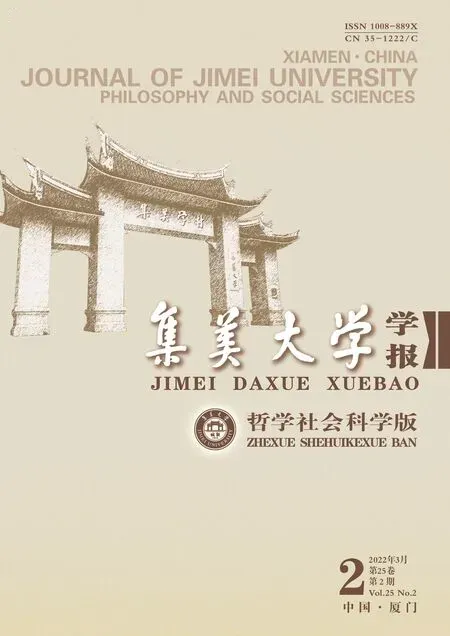20世纪80年代以来符号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黄文虎
(华侨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符号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议题。不少前辈学者对这一问题都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如王铭玉和宋尧将符号学在中国的传播分为起步期(1980—1986年)、平稳发展期(1987—1993年)、全面展开期(1994—2000年)[1]13-21;严志军和张杰将西方符号学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分为3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语言学阶段(20世纪80年代),第二阶段是超语言学阶段(20世纪90年代),第三阶段(21世纪)是中国学术界对西方符号学理论的“中国化”时期[2]138-141;赵毅衡分别从符号学与结构主义(20世纪80年代)、中国古典符号学(20世纪90年代)、符号学与文化研究(21世纪)为主线进行了论述[3]146-155。综合各家之说,笔者将符号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分为萌芽期(1980年之前)、起步阶段(1980—1989年)、发展阶段(1990—1999年)、深化阶段(2000年至今)4个主要阶段,重点梳理20世纪80年代以来符号学在中国的基本发展脉络。
二、萌芽期(1980年之前):西方符号学的传入
西方现代意义上的符号学(Semiotics)大致产生于20世纪初期的欧美,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奠基人物主要有索绪尔和皮尔斯。早期的符号学与语言学关系密切,并受到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深刻影响,后逐步扩展到文化领域,成为一种具有专业性和跨学科性的方法论和聚焦“人类意义活动”的系统性学说。
早在20世纪初,中国学者已经关注到语言符号学的相关内容。1926年,赵元任发表《符号学大纲》一文,他在该文中指出:“符号这东西是很老的了,但拿一切的符号当一种题目来研究它的种种性质跟用法的原则,这事情还没有人做过。”[4]此处暗含了两个重要观点:(1)符号自古有之,不分国界和地域。也就是说,无论东方或西方,都有“关于符号的研究传统”。(2)符号学作为一门专业性的知识理论,在当时还尚未得到东西方学界的充分重视。赵元任这一说法基本符合史实,因为索绪尔和皮尔斯虽然在20世纪初就提出了符号学基本理论,但当时并未引起东西方学界的充分关注。直到20世纪60年代,符号学理论广泛的应用前景才逐渐得以显现。
此外,赵元任的这篇文章区分了“理论的符号学”和“应用的符号学”,探讨了符号的概念、符号的成素、符号的组合、符号的边界、符号与对象的关系等基本理论问题,可视为20世纪中国符号学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开山之作”。因此,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符号并不是“洋玩意”,而符号学也并非“舶来品”。符号学“中国化”进程的开端是“化西为中”,而绝非“全盘西化”。
但由于各种历史性客观因素所限,此后近40年间,符号学在中国并未引发实质性的影响,甚至一度出现“断层”,在中国,仅能找到极少数有关符号学的研究资料。总的来看,建国之后到新时期之前,符号学在中国的影响极为有限,仅仅是作为点缀语言学、逻辑学和哲学的一个“附属品”,并没有体现出广泛而深入的学术影响力。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其重要意义才得到中国学界的普遍认可。
三、起步阶段(1980—1989年):“西方化”为主导的时期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符号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兴盛和新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扩展和深化,符号学得到中国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20世纪80年代,有关西方符号学理论的译介和研究开始得到稳步发展,符号学理论也被应用到文学、电影、艺术以及文化研究之中,这一时期可视为符号学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的起步阶段。该时期的主要特点是注重推介西方具有代表性的符号学思想,其所奠定的主导性学术话语体系为“以西阐中”,西方符号学的“光环”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中国符号学”自身的本土特质,因而这一时期可以被视为符号学“西方化”为主导的阶段。
具体来看,这一时期符号学在中国的传播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
(一)符号学受制于结构主义思潮
早在1978年,杨熙令在《结构主义是什么》一文中就说道:“结构主义又名符号学(Semiotics)。”[5]不可否认,符号学与结构主义具有不可忽视的渊源关系,甚至可以说,结构主义是西方早期符号学的主导性范式。赵毅衡指出:“中国学界在80年代基本上把结构主义当作符号学的同义词。”[3]148这一将符号学置于西方结构主义阴影下的观点贯穿于20世纪80—90年代的中国学界,具有代表性。这说明符号学在引入中国之初并没有被当作是一门独立的理论体系,其研究边界不够清晰,因而使符号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合法性备受质疑。
(二)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派占据符号学的理论核心
1980年,胡壮麟发表《语用学》一文,其中涉及语言学与符号学的内容。这一时期,涌现出一批研究索绪尔的相关论文。比如徐志民的《索绪尔的语言理论》(1980)、刘耀武的《论索绪尔的语言哲学》(1981)、徐盛桓《组合与聚合》(1983)、许国樟《关于索绪尔的两本书》(1983)等。总的来看,以索绪尔为中心的研讨往往重心在于语言学与符号学之间的关系,或者是注重用语言学的方法来研究各类符号现象。有关符号学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被限制在语言学的研究框架和话语体系之内,尚未体现符号学的学科独立性。
(三)结构主义符号学作为一种普遍的范式应用到文学、哲学、艺术学、人类学、电影学等领域,体现出鲜明的跨学科色彩
在文学领域,有安和居的《“符号学”与文艺创作》(1985)、安迪的《短篇小说的符号学》(1985)、周晓风的《朦胧诗与艺术规律:对于现代诗歌的一个符号学探讨》(1987)等。在哲学领域,较早涉及符号学的论文有史建海的《符号学与认识论》(1984)、陈波的《符号学及其方法论意义》(1988)、章仕荣的《符号的理解与解释》(1989)、刘宗棠的《〈指物论〉与指号学》(1989)等。在艺术学领域,代表作有杨春时的《艺术符号与解释》(1989),此书创建了一套系统性的艺术符号学理论,并试图克服和超越以结构主义为本位的西方符号学的局限;胡妙胜的《戏剧演出符号学引论》(1989)则尝试将符号学与结构主义引入戏剧研究,是中国第一部戏剧符号学领域的专著。在人类学领域,俞建章、叶舒宪在《符号:语言与艺术》(1988)一书中结合符号学理论来阐释中西文化中的神话思维模式,奠定了中国早期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范式。李幼蒸的《电影符号学概述》(1986)和徐增敏的《电影符号与符号学》(1986)则较早将西方符号学理论与电影批评相结合。
(四)关于符号学理论的推介
早在1983年,金克木就在《读书》上发表《谈符号学》一文。该文从广义(文化学)和狭义(语言学)两个维度讨论了符号学的研究范围。同时,金克木认为符号可被定义为“传递信息的中介”,而符号学是“一门发展中的科学”[6]。1987年,毛丹青在《符号学的起源》一文中对西方文明早期的符号研究传统进行梳理,并介绍了索绪尔、皮尔斯、莫里斯等现代西方符号学的代表人物[7]。在1988—1989年,李先焜等学者在《逻辑与语言学习》连载了符号学系列讲座,对符号学的代表人物、重要概念和基本范畴进行了介绍,并涉及语言学、逻辑学等相关领域。
总体来看,在起步阶段,符号学“西方化”的倾向十分鲜明。西方符号学在中国可谓是一种“单向度的传播”,即仅仅表现为“理论输入”,但缺乏中西方符号学界之间的“双向对话”。中国学界尚不具备自觉的学科“主体意识”,因而,对西方符号学的整体态度是被动地“汲取”与“迎受”,其背后的学术话语体系为“以西阐中”。尽管不少中国学者运用西方符号学理论,尝试打通不同学科之间的边界,扩展研究视野和深度,但“以西阐中”的话语体系有可能会遮蔽跨学科之下的文化多元性和异质性,潜藏着“西方中心论”的危险。
四、发展阶段(1990—1999年):“西方化”与“本土化”并行的时期
20世纪90年代,符号学开始向“国际接轨”,其重要表现是由以“西方为中心”的单向“散播”逐渐转向跨中西文明视野下的双向对话与碰撞,这一时期可视为符号学在中国的发展阶段。总的来看,一方面,国内学界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以西方符号学理论为中心的话语体系;另一方面,中国符号学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符号学资源,并通过“创造性的转化”呈现出“本土化”的端倪。
(一)注重整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符号学资源
通过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符号学资源来呈现中国符号学的学术话语特色成为这一阶段符号学“本土化”的重要表现。
1.尝试挖掘中国古代符号学传统。如李先焜在《中国:一个具有丰富的符号学传统的国家》(1990)一文中将训诂学、儒家的正名学说、《易经》中的符号理论、《墨经》中的名实理论、《公孙龙子》中的指物学理论等归纳为中国古代符号学的源流,同时还对索绪尔的符号学思想与中国古代符号学理论进行了对比,体现出一种自觉的“主体意识”[8]。邓生庆在《传统文化典籍的符号学特征与典籍阐释》(1993)一文中,从符号传播的角度,指出了传统典籍中“诗学编码”的解码规律,试图将符号学、阐释学、逻辑学理论用于解释传统典籍[9]。
2.从跨学科视角来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化符号。如朱炳祥的专著《伏羲与中国文化——关于中国文化发生的符号学研究》(1995)融合了符号学、考古学、民族志等方法探讨了伏羲神话的内涵和象征意义,是中国第一部将符号学与人类学、神话学相结合的理论专著。孙新周的《中国原始艺术符号的文化破译》(1998)则结合了符号学、神话学、宗教学来探讨岩画、彩陶等原始符号与巫术的内在关联。
3.从中西比较视野看待中国传统符号学的独特价值。如李幼蒸在《从符号学看中国传统文化》(1995)一文中,明确提出“中国符号学”的概念,认为中国符号学能够跨越中西学术话语的“鸿沟”,有助于打通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现代思想之间的“隔阂”[10]。此外,不少学者还从逻辑学和语言学的维度来探讨中国古典典籍中的符号问题,如许艾琼的《荀子正名理论的符号学意义》(1993)、周文英的《〈易〉的符号学的性质》(1994)、高乐田的《〈说文解字〉中的符号思想初探》(1997)等,此类研究中也体现出符号学的色彩。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国内学界对于中国传统符号学的关注度仍然有限,多为“浅尝辄止”,尚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
(二)符号学成为重新认知中国文学与艺术话语本土价值的新维度
1.符号学视角下的中国文学研究。1990年,张颐武发表系列论文《张颐武的本土符号学研究——二十世纪汉语文学的语言问题》,在文中,作者结合符号学理论探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白话文学所面临的口语化与欧化的两难问题[11]。与此同时,符号学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全新的阐释视角,典型代表有赵毅衡的《文学符号学》(1990),该书是国内第一本运用西方符号学原理与叙述学理论系统性阐述文学现象与文艺理论的著作,为中国文学符号学的开展奠定了基本的研究范式。此外,作者还较早指出符号学文论与马克思主义文论之间的内在关联[12]。
2.艺术学与符号学的跨学科研究。丁和根在《戏曲演出的符号化特征》(1990)一文中从符号学视角阐述了中国戏曲中的各种典型符号。他认为,戏曲演出中的听觉符号包括戏曲演出中的唱、念以及音乐伴奏,视觉符号包括戏曲服装、舞台道具、布景和灯光等,动作符号则涉及演员的角色和人物性格,体现出鲜明的“本土”特色[13]。此外,不少学者还尝试从比较文学的视野探讨中西戏曲的差异和特色。张生筠认为符号学对于阐释中国戏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分析了中国传统戏曲舞台设计中的各类具有美学功能的符号[14]。杜隽在《符号学与当代戏剧理论》(1991)一文中梳理了西方戏剧符号学发展史,并指出构建中国戏剧符号学的必要性[15]。
(三)尝试从跨文化视野来融合中西符号学理论
在这一阶段,不少学者开始以西方现代符号学思想作为参照来构建符号学体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凸显出本土话语的特色。代表作有李幼蒸的《理论符号学导论》(1994),该书为中国第一部从跨东西方比较视野下的符号学理论著作,提出创建中国符号学的理论构想;孟华的《符号表达原理》(1999)则从比较符号学的视野,对周易符号与二进制算术符号进行了对比,体现出了中国传统符号的独特性。此外,这一时期的符号学相关专著还有鲁枢元的《超越语言——文学言语学刍议》(1990)、董小英的《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1994)、吴文虎的《广告的符号世界》(1997)、孙新周的《中国原始艺术符号的文化破译》(1998)、陈治安、刘家荣主编的《语言与符号学在中国的进展》(1999)、荀志效的《意义与符号》(1999)等,涉及语言学、文学、人类学、传播学等多个交叉领域。
(四)提倡中国符号学的本土性与独立性
这一时期,不少学者从宏观视角对符号学在中国的发展和困境进行了论述。如丁尔苏在专著《超越本体》(1994)中对西方古代与现代主流“意义理论”进行了解构和重构,涉及符号学的主体性建构问题,他在《符号学研究——世界与中国》(1994)一文中则指出,中国符号学界与世界符号学界存在一定差距,要缩小差距,需要整理中国古代的符号学思想,以便使中国符号学界能够与国外符号学界进行平等对话[16]。苟志效在《回顾与展望——中国符号学研究5年》(1994)中认为,中国本土拥有丰富的符号学传统,完全有可能形成一个具有“中国风格和气派”的符号学新派别[17]。同时,苟志效等编写了《中国古代符号思想史纲要》(1995),该书是第一本尝试从符号学的视角分析中国古典哲学的编著。此外,关于符号学到底是属于一门学科还是一种方法论也引发了学界的争议。王宁在《走向文学的符号学研究》(1995)一文中则肯定了符号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合法性,并指出不能用传统的学科分类来限制符号学的发展[18]。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可被视为符号学的“西方化”与“本土化”并行的阶段。在这一时期,符号学体现出鲜明的“跨文明性”。符号学不再被视为西方科学话语体系所独有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一些中国学者逐渐意识到,中国传统的符号学资源、东方诗性话语体系与西方所构建的现代符号学具有内在的“可通约性”,中国符号学本土资源的独特价值开始凸显。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符号学界由被动的“以西阐中”的话语模式逐渐转向了更具有主动色彩的“以西适中”的话语体系。
五、深化阶段(2000年至今):“中国学派”的探索期
近20年以来,符号学在中国的传播从量的积累逐渐迈向质的飞跃,这正是符号学“中国化”演化的必然结果,也是符号学在中国的深化阶段。根据中国知网搜索关键词“符号学”的统计数据来看,1979年至1999年符号学相关文献只有627篇,而2000至2019年符号学相关文献却高达6 482篇(1)通过中国知网“符号学”关键词所搜集到的数据,访问时间:2020年10月22日。。根据超星读秀搜索关键词“符号学”的统计结果来看,1979年至1999年符号学相关著作为58部,而2000至2019年符号学相关著作为312部(2)通过超星读秀“符号学”关键词(选取书名一栏)所搜集到的数据,访问时间:2020年10月22日。。由此来看,新时期40年间,符号学相关文献后20年和前20年相比在数量上得到快速增长。正是在这种爆发式的发展和推进之中,符号学由“西方化”逐渐转向了“中国化”,而符号学的“中国化”正是构建“中国学派”的基础。
在这一阶段,不少有见识的学者都提出了构建“中国符号学”的重要观点。总的来看,可分为3个层面:
(一)阐释中国符号学的总体特征
王永祥、潘新宁在《从三个角度看中国符号学的发展趋向》(2016)一文中分别从学科理论框架体系、学科学术发展规律、学科发展的现实状态进行了阐发。同时,作者对比了中西符号学,指出相对于西方符号学的逻辑性和理论性,中国符号学更偏重于感悟性和应用性。若中国符号学能够融汇中西方的符号学思想,将有利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号学基础理论[19]。王铭玉、宋尧在《中国符号学研究20年》(2003)一文中认为,从宏观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符号学将逐步走向国际化,而且中国传统文化领域的符号学资源具有广阔的开发前景[1]13-21。严志军、张杰在《西方符号学理论在中国》(2010)一文中更加明确地指出:“中国文化的丰厚底蕴使得中国符号学界对西方符号学理论的阐释表现出自己的独特性。”[2]138-141顾嘉祖在《迈向特色创新阶段的我国符号学研究》(2003)一文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强调中国符号学已经从单纯地引进西方理论转向了建构具有民族话语特色的新阶段[20]。
(二)界定中国符号学的研究范畴
王铭玉在《中国符号学的理论依归和学术精神》(2016)一文中,将中国符号学学术资源分为13大类,分别是易学符号学、名学符号学、训诂学符号学、汉字符号学、《文心雕龙》符号学、佛教哲学符号学、术数符号学、典故符号学、古典文学符号学、艺术符号学、音韵符号学、人类符号学、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此外,论者还认为,中国符号学应以一种“合治”的包容观念来借鉴西方符号学理论,并从大符号的概念来突出中国传统符号学的研究特色[21]。
(三)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符号学话语体系
李幼蒸认为,从学科划分的角度,有必要构建“中国文学符号学”学科与“中国古典文学符号学”专业,并将语言学类、叙事学类、诗歌类、文体类、艺术门类、语史类综合语义研究(考据学研究)都纳入其研究领域之内,并从学科构建的角度指出了文学符号学作为一门特定学科和专业的必要性[22]。苏晓军在《符号学在中国的三个发展进路》(2016)一文中则从认知符号学、教育符号学和文化符号学3个角度进行阐述。作者认为,要挖掘中国符号学思想,意味着需要建构一套中国本土的符号话语体系。龚鹏程在《文化符号学:中国社会的肌理与文化法则》(2009)一书中,就曾尝试建构一个独立于索绪尔与皮尔斯的中国符号学话语体系[23]。
事实上,不少学者正通过学术行动来构建不同于西方的中国本土符号学话语特色。不少高校成立了专门的符号学研究中心,并定期出版符号学刊物或开设符号学专栏,如四川大学的中英文版学术集刊《符号与传媒》、南京师范大学的英文期刊《中国符号学研究》、苏州大学英文期刊《语言与符号学研究》,《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开设的“语言符号学”专栏等,在国内外学界均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力。
(四)具有地域特色和规模效应的中国符号学阵地正在成型
符号学研究阵地的“地域化”是中国符号学兴盛的重要标志。在西南地区,以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中心”作为主轴,形成了在国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川大符号学派”。该研究中心成立于2006年,在赵毅衡符号学团队的引领之下,主编符号学系列专著和“当代符号学译丛”多达60余部,涉及文学艺术、语言学、民俗学、传播学等人文社会学科的多个领域,得到了学界广泛的关注,并体现出中国符号学鲜明的地域色彩。
总的来看,“川大符号学派”至少体现出3个重要特点:
1.通过翻译与推介国外具有代表性的符号学者或符号学流派来推动中外符号学界的互动和交流。如赵星植编译的《皮尔斯·论符号》(2014)一书对于国内读者了解皮尔斯符号学的基本框架提供了一扇重要的学术“窗口”;同时,其研究专著《皮尔斯与传播符号学》(2017)进一步对西方符号学界影响深远的皮尔斯符号学体系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研讨。赵星植在新著《当代符号学新潮流研究(1980-2020)》(2021)一书中,更是系统、全面地介绍了生态符号学、认知符号学、传播符号学、社会符号学、文化符号学等在西方符号学界最具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符号学派。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也得到了国内学界的广泛关注,如唐小林、张碧在主编的《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派》(2016)一书中,就选译了一批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代表人物的著作,有助于国内学界从符号学的视角来了解马克思主义。无疑,此类有关西方当代符号学理论的翻译和研究对于中国符号学界了解世界符号学界的最新发展动态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2.出版了一大批极具原创性、民族性、跨学科特色的学术专著,大大扩展了中国符号学的研究广度,并凸显出鲜明的本土特质。这些著述既借鉴了西方具有代表性的符号学原理,但又不是亦步亦趋,而是能够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符号学资源与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实践来挖掘契合时代需求的议题。例如,胡易容的国家重大项目《“巴蜀图语”符号谱系整理分析与数字人文传播研究》(2018)就以中国传统符号“巴蜀图语”作为研究对象,深刻体现了“川大符号学派”的地域特质。该研究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系统性地整理巴蜀符号谱系;第二部分是通过“数字人文”的技术手段,通过计算机建模来构建巴蜀符号数据检索和巴蜀符号演化模拟系统,这无疑是对中国符号学话语体系的一次有益探索。正如胡易容所指出:“中国符号学要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必须要加强基于中华传统文字与文化符号对象研究。”[24]
“川大符号学派”推出了一系列具有民族特色的著述,如张淑萍的《陇中民俗剪纸的文化符号学解读》(2014)、祝东的《先秦符号思想研究》(2014)、孙金燕的《武侠文化符号学》(2015)、王俊花的《皮尔斯与中国古典美学》(2018)、苏智的《〈周易〉的符号学研究》(2018)等。这些极具中国特色的符号学论著尝试将现代西方符号学思潮与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特色紧密结合,从而与世界符号学研究形成互补与互证。
“川大符号学派”还体现出鲜明的跨学科特色,并尝试运用符号学的视角和方法来打通固有的学科体系和传统的知识分类,大大扩宽了符号学的研究范畴。比如,宗争的《游戏学:符号叙述学研究》(2014)、李玮的《新闻符号学》(2014)、闫文君的《名人:传播符号学研究》(2018)、贾佳的《打扮:符号学研究》(2018)、石访访的《饮食的文化符号学》(2019)、陆正兰的《流行音乐传播符号学》(2019)、薛晨的《日常生活意义世界:一个符号学路径》(2020)、饶广祥的《品牌与广告:符号学叙述学分析》(2020)等符号学研究著述,都超越了狭义符号学所限定的学科范畴,为中国符号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新的学术空间。
3.通过创办《符号与传媒》这一学术集刊推出了一系列视角独特、理论内涵丰富且极具时代感的学术热点话题。以《符号与传播》2020年、2021年出版的4辑为例,在这4辑中,刊物分别推出了哲学符号学、精神符号学、传播符号学、广义叙述学、汉字符号学、中国俗文化符号学等内容涵盖广泛、多元的议题。在符号学理论层面,既有关于西方经典符号学家和符号学派的研究,也有中国符号学思想如礼乐文化符号、唐宋佛学中的符号学思想、禅宗公案中的空符号、《文心雕龙》与符号学等的研讨。在符号学应用层面,涌现出不少时尚新鲜的话题,其内容涉及表情包符号、“盲盒热”、国潮品牌、人设现象、熊猫符号等极具时代感的符号传播现象。此类旨在凸显中国元素与时代元素的符号学研究不仅仅是“川大符号学派”的特色,而且也愈来愈成为当前中国符号学界的主流趋势,这可谓是符号学“中国化”的重要标志。
总的来看,近20年,随着符号学在中国的深化发展,显示出新的时代特征,尤其是涌现出像“川大符号学派”这种极具地域特色与民族特色的本土符号学研究阵地。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符号学的专业性、独立性和合法性逐渐得到中外学界的认同。从中外交流的视角来看,西方符号学界与中国学界形成了广泛而深入的“双向对话”。从学科建设的维度来看,中国学界逐渐具备了自觉的学科“主体意识”,在国内已经形成具有地域特色和规模效应的本土符号学阵地,呈现出了一种更为多元的国际化视野,并在国际符号学界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些都是符号学中国学派构建学科主体性的有益探索。
六、未来展望
纵观20世纪以来的符号学发展史,符号学绝非“舶来品”,它并非西方学术话语所独创的外来产物,中国自古以来就拥有丰富多元的符号学资源和符号学研究传统。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新时代背景之下,中国符号学与国际符号学界逐渐形成了良好的互动与平等的对话关系。越来越多的中国符号学者得到了海外学界的关注,独立于西方符号学体系的中国符号学开始在国际符号学界崭露头角。中国符号学从“理论口号”逐渐迈向了具有实际影响力的“学术实践”。
回顾近40年来符号学在中国的发展史,中国符号学的传播脉络表现为从单向的文化输入转向文化输入与输出并举的新态势,从“西方一元话语”为主导迈向“中西杂语共生”的新局面,从以追随“他者”为中心的西方符号学演化为以彰显“自我”特色、促进平等对话的中西比较符号学,这正是中国符号学在新时代发展的新趋势。在这一新的时代背景之下,“中西比较符号学”的目的不仅要凸显“中国学派”自觉的学科主体意识和学术话语创新理念,更要努力展现出一种多元、包容的学术胸怀和国际视野,切实推动世界符号学的进步和融合。
从发展的眼光来看,中国符号学无疑将成为世界符号学未来发展的轴心力量之一,它兼具西方理性话语和东方人文传统,兼容特殊符号学与一般符号学,兼顾符号学的认识论意义与方法论意义。符号学的“中国化”意味着我们既需要保持一种开放包容的比较视域,又必须立足于中国本土话语,将中国传统符号学资源与现代符号学话语有机融合,力图构建一种跨文化、跨民族、跨语言、跨学科的符号学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