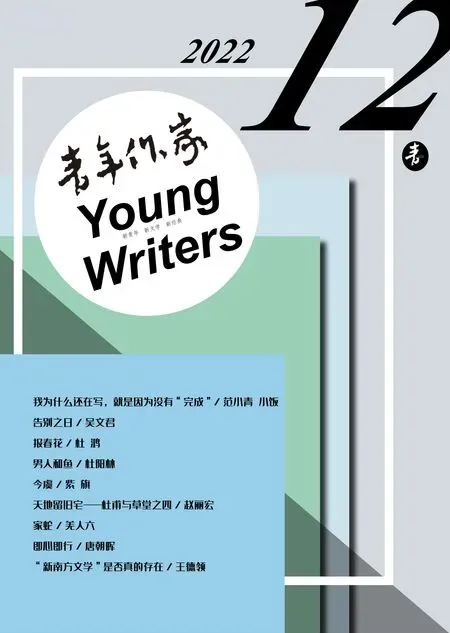家蛇
羌人六
一
断裂带,我自小长大的那个腊月里梅花总是遍山盛开的村子,如果谁不热爱劳动,整天一截树桩似的待着闲着,无所事事、好吃懒做,漠视双手和劳动价值,视勤劳务实为做人本分的乡亲就会说,“真是懒得烧蛇吃。”其实,懒得烧蛇吃的人,未必真的存在,人即使真的懒惰,也未必胆敢吃蛇,句子混着唾沫星子飞出嘴唇缝隙,连同懒人的名字和脊梁骨一起被人踩在脚下。说人懒得烧蛇吃,就是用语言打脸,这样的人,朽木一块,很难在村子里立足,更不要说抬头做人。二十世纪末梢的断裂带,被群山手帕一样裹住视线的人们,物质生活要求不高,过着相对简朴的生活,穿衣打扮也不像城里那样热衷,在老一辈人眼中,不能当饭吃的“臭美”就像懒惰一样令人厌弃。衣物可以破破烂烂,只是绝对不能脏,否则就会被人笑话。儿时,我那瘦骨嶙峋的竹竿似的身板不知被多少破破烂烂的衣服、裤子和鞋子包围过,坐在身体里的自卑和恐惧总是比天上的星星还亮,但母亲总有办法抚平它们,她常常安慰我说:“笑脏不笑烂。”爱说“长一双手样啥都有”的外婆也经常这样说,给我的感觉是,话语也有自己的生命,能够遗传似的。过了很多年,我渐渐明白母亲们的话里边不仅住着一种智慧,并且也隐匿着一种断裂带人骨子里永远迸溅着生命火花的倔强与尊严。同时,我还发现,“笑脏不笑烂”与“懒得烧蛇吃”就像断裂带河谷两边永恒对峙的高山,中间隔着一条河。
关于“懒得烧蛇吃”这个说法,民间流传一个故事,说是在古老的年代,万物关系和谐,人与花鸟虫鱼可以毫无障碍地交流,那时候,有牙齿的人与原本没有毒牙的蛇是极好的朋友,但凡上山背柴,蛇都要主动给人搭伴陪同,并且力所能及地帮下忙,蛇总是把自己变成一截绳子,充当人捆柴的绳子使用,结果有次一个懒人因为肚子饿得发昏,就将捆柴用的蛇搁在柴火上烧来吃了,于是蛇上天向神告状,控诉人的罪行。天神同情蛇的遭遇,使其长出毒牙,允许蛇见人就咬,而人也由此立下一个与蛇势不两立的规矩:见蛇不打七分罪。在断裂带,与“懒得烧蛇吃”还有个类似的说法,“懒得烧虱子”。含蓄克制、言简意赅,又不失荨麻一样的尖锐,也颇有恨铁不成钢的意思。“烧蛇吃”“烧虱子”只是说法不同,异曲同工,将蛇与虱子这些不能吃的东西作为食物只是比喻,意味着“饥不择食”,指向的则是人的懒惰。不得不说的是,“懒得烧蛇吃”的人也是想让自己摆脱重负,活得轻松一点,只是和勤快人选择的方式不同。在人什么都吃什么都敢吃的当下,“懒得烧蛇吃”和“懒得烧虱子”早已铁锈斑斑,或许,仅是一种语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蛇,冷飕飕、冰欠欠的家伙,身形柔若无骨,行踪诡谲;蛇,没有腿脚却能走遍大地、孤独纵横大地的浪子。在断裂带的那些年,在我的脚印曾经涂遍过所有角落的村子,蛇是隐秘的,很少露面,深居简出,但几乎人人都能说出与蛇相关的“缘分”,讲述时,脑袋里的恐惧就会从眼睛、心跳和呼吸里滑出来,像蛇穿过堆满寂静的草丛、树林和山岗。在城里这些年,我已经很少见到蛇,很难见到蛇,正如我很少在当下生活中使用断裂带乡亲父老使用过的语言,在他乡,我过着普通的生活,活着普通的人,与此同时,我如同秘密蛰伏在断裂带的那些蛇类,远远打量着观望着自己土生土长的断裂带,在距离和流年中感受着这片土地的生机、命运和绚烂。如果我说,蛇并未消失在我的脑袋里,那么,这个句子其实还可以像日子一样继续延长,比如,人即便消失在断裂带的空气中,也能通过自己的回忆,在那些散乱的细节、人事和文字间隙安放内心的情感,安放故乡,安放那些一去不返的时光。
儿时记忆中,蛇总是带来恐惧、不安。
二十世纪末的某个夜晚在我的记忆中就像断裂带夜空里沸腾的星光一样闪亮,一条皮肤斑斓的菜花蛇赫然出现在我家灶屋,蜘蛛一样紧贴着墙壁,尔后,又熟面条似的在我家灶台上大大咧咧地逛了一圈。从容、威严,细长、柔软。父亲不在家里,在场的母亲、我和弟弟万分恐惧。镇定下来,母亲用一种她从未那样对我有过的温柔语气跟蛇说了些“好话”,那蛇听懂了似的,很快温顺退出我们的视线,滑向无边的夜晚……与见蛇不打七分罪相悖的是,家里显形的蛇是不能打的。断裂带有个沿袭已久的说法,那就是,家蛇不能打,打不得。家蛇,顾名思义,即出现在家里或者房子周围的蛇。并不是所有的蛇都是家蛇。在断裂带,行踪诡秘、风度翩翩的蛇一旦闯入家头,蛇便脱离自然的行列,变成禁忌,不但不能打,且须敬畏三分,任其晃晃悠悠毫无畏惧地来,也任其亮着自己跟人一样“扑通”响的心脏平安离去。家蛇为什么不能打?家长们的说法是,家蛇类似于故去的某位祖先或者神灵,地位颇高,岂能蓄意伤害?“见蛇不打七分罪”的民间传说,因为家蛇有了对立面,变得形同虚设。
群山绵延、地震频发的断裂带,在时序中依然保持着蓬勃生机与存活率的断裂带,乡亲父老世世代代耕耘、厮守的断裂带,多少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化作齑粉后仍在心跳中热气腾腾“活着”的断裂带,我的童年和少年时光的摇篮,如今,一切仿佛早已从那里长进岁月的岩层,只有恍恍惚惚的记忆似乎并未像断裂带家门前终年流淌的河水那样注入下游,注入遗忘,而是秘密地驻扎在我的灵魂深处,驻扎在我的记忆深处,如影随形。如此深情告白,也许有些过头,有些夸张,并非真实的想法。其实,挣脱这片土地的种子在儿时便已萌芽,因为她的贫瘠,因为她的泥泞,因为她的单调,因为她给予我的人生履历。生命穿过岁月的长廊,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丧失,于是我在作品里一遍遍写道:人,永远去不了的地方就是过去。然而,就像早年偶然邂逅从此牢牢冻结在记忆枝头的家蛇一样,如今,我与早年相依相伴的家乡渐行渐远,但“家蛇记忆”并没有消失,而是断裂带家门前河流一样始终盘桓在我的内心深处,在时间里,在断裂带群山的褶皱之间。
对本地人而言,当我们身在断裂带,村子里的某座房子就是我们的家;对异乡人而言,当我们离开断裂带,那里的一整片土地就是我们的家了。当我写下“家蛇”,指向的其实是与蛇相关的记忆,它们拴着我生命上游的很多部分,拴着我对家园、家庭和家人们的回忆,如同最初变成帮人捆柴的蛇,它们恍若一截截绳子,串联着我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二
壬寅年四月,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的四月,重新长出枝叶的草木在空气皮肤上亮出胳膊、脑袋的四月,无数彼此相连的命运在同一根铁轨昏昏欲睡的四月,我就像个懒得烧蛇吃的人一样,浑身石化般动弹不得,不想动弹。终日宅家,蜗居在绵阳园艺山100.1平方米的房子里,与久违的锅碗瓢盆、柴米油盐为伍。如今,和弟弟一家仍然生活在断裂带上的母亲,早在我儿时的记忆里边,就种下过这样一个叫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词:“挺尸”。简洁、直白地描述人睡懒觉的样子,而不是有谁真的一命呜呼。药可以治病,这个词却能够以毒攻毒,排除人精神上的毒素,懒惰或者懈怠。在断裂带,在母亲那里,在一辈子汗水多半留给庄稼地留给劳动并且最终被自家庄稼地的泥土吃掉的乡亲父老那里,如果已经日上三竿,如果人还懒洋洋待在床上,遑论睡或醒,这个词就像“懒得烧蛇吃”的亲戚似的,准会从家人口中,钉子钉在墙上那样钉入你的耳膜,撕破土壤一样撕开土地的花朵那样撕破你的耳朵。其实,这个词何止是对“懒惰”的讽刺羞辱,简直就是咒骂了。挺尸,一个与“躺平”类似或者意思挨边的词。城里生活多年,我的骨子里依然流淌着断裂带以及祖先父辈予以我的勤快血液,而不是“懒得烧蛇吃”。岁月生长,与断裂带的距离不断拉长,距离包括空间、包括情感。而今,除了逢年过节,我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归心似箭,频繁穿梭于城市与断裂带之间,好在,横亘在断裂带与城市间的宽阔马路并没有因为我的“懒得烧蛇吃”而荒废。
诗人艾略特在《荒原》中用预言般的句子向人类揭示一个“秘密”:“四月是残忍的季节。”我充满怀疑,对于没有答案没有真相可言的生活,覆盖在我们这些普通人身上的冰欠欠的生活,是否只有诗人早已洞悉、早已参透?读聂鲁达《我坦言我曾历尽沧桑》,看到一段掌故,诗人曾主编过一部刊物,名曰《绿马》,有人觉得莫名其妙,为什么不是红马?诗人却不同意给这匹“马”换颜色,认为“世上有足够的地方容纳彩虹般色彩各异的马匹和诗人”。疫情当下,护身符一样的绿马,胜过色彩各异的马匹。
拦不住色彩各异的马匹遍地飞奔的四月,曾经乐此不疲的音乐、书籍乃至肉体之欢连同美味的蔬菜、水果和食物,心有灵犀似的不约而同失去本来的味道、色彩和形状。如今,生活缩水一般变得皱皱巴巴,脑袋透着荒凉与冷清,一言难尽,叫人很不自在。儿时,在断裂带读小学和初中那会儿,但凡遇见苦难、尴尬或者屈辱,我常常会在作文里天马行空,无所不能,不是“长出一副翅膀远走高飞”,就是“钻进一道地缝”。整天待在家里,枯坐书房,无所事事,浑浑噩噩,任凭思绪的钟摆在我生活的城市与出生地断裂带之间摇摇晃晃。往事点滴,历历在目,形如早年在断裂带的家门前那场滔滔洪水中看见一群“水蛇”晃悠着脑袋,密密麻麻、浩浩荡荡地从上游而来,追赶着什么似的,游过我的眼睛,游过我的面前,尔后随着水雾缭绕、汹涌狂野的洪水款款而去。
我就像一条不需要腿脚的蛇类,在记忆里追赶着断裂带人的生活,却身不由己地陷入一个毫无出路也毫无退路的怪圈,就像断裂带的群山一样固若金汤的怪圈,一个目光永远够不着边的怪圈,即便借助望远镜、显微镜或者透视仪也都无济于事。毫无疑问,终于挣脱断裂带的“那身农皮”和泥腥味的田园生活,远离家乡的天空、大地、炊烟、农事和过往,我再也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断裂带人,连同我名副其实的户口和身份证也不能说明我的本地人身份。当我兴致勃勃地提出爬山锻炼身体,去山林里挖野菜……亲戚们就会用一种半是同情半是讽刺的眼神挖苦我,好像在挖我的什么苦难似的。一出眼睛看不见的追赶游戏,在我和亲戚们之间频频上演,我追赶着他们恨不得晾在一边的生活,他们也在追赶着我们恨不得晾在一边的生活。但是我并不为此感到悲哀,我只是难过,我难过的是,我们之间仿佛早已有了界限,甚至某种敌意。
事实上,感官早就远离了自己、疏远了自己,再也不属于自己,就像儿时吃下太多青涩的无花果,舌头是僵硬的,沉默是僵硬的,思绪是僵硬的,脆弱而麻木的肉身是僵硬的,整个人石化一般,荒废、孤独、愤怒、无助和乏力的感觉让人仿佛是从它们那里膨胀幻化出来的一团泡沫,在嘀答作响的时间里等待天亮,抑或自生自灭。
如今的日子,我的精神萎靡不振,仿佛冬眠的蛇类,或者一株人形植物。中旬,阳光斑斓的午后,我才如梦初醒似的想起在上海工作的堂哥,之前问候关心过好些上海的朋友,似乎都没有想起过自己的亲人,远在他乡的堂哥刘强一家——大伯在断裂带去世两三年了。给堂哥刘强发去问候消息的时候,我感到深深的内疚。堂哥是大伯的儿子,我们都一样,在断裂带的刘家院子一起长大,在岁月里各奔东西。堂哥的翅膀明显更硬一筹,飞得最远,从闭塞贫苦的大山飞到了繁华富庶的上海滩。堂哥很快回了消息:“已经回家,一切还好。”堂哥的回复如同我干巴巴的问候。问候,代表的是一种关心。其实,我知道,眼下根本无法为堂哥提供任何实质性帮助,或者说有心无力。但仍然真心实意问他,是否需要给他快递些腊肉香肠之类?堂哥回复,不用,快递、美团外卖之类早就毫无用武之地。“早就毫无永用武之地”,堂哥的话语仿佛不是来自当下,而是来自我们远离的家园——断裂带,那片我们都曾经了如指掌的土地。我的关心问候不是因为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或者心血来潮,一个意图在我的问候里生长,就是想把多年来我们彼此间的淡漠和疏远一笔勾销。毕竟,无论天涯海角,我们之间还有父辈们给予我们的血脉,还有那尽管早已褪色早已黯淡早已无味的亲情。
距离使得亲情“毫无用武之地”。只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下,亲人间都漠不关心,不闻不问,我想,那真是只有拿“懒得烧蛇吃”形容才够。
三
“骨头碎了,筋还连着。”这是断裂带人对亲情的“认识”,表述看似抓住了本质,实则过于感性,弥散着一股豆腐眼儿的陈腐气息,底气十足却又经不起推敲,因为细节和过程已经在句子的脚后跟上被结果抹去和掩盖,就像蛇与蛇皮之间,始终隔着一层生命,并不能等同,捡到蛇皮的人也不会说他抓住的是蛇。事实上,只有在亲人因为某些利益冲突互相交恶之后,奉劝当事双方冰释前嫌、重归于好的情况下,人们才会使用这个说法,唾沫飞进空气,仇恨吞进肚子,握手言和。“骨头碎了,筋还连着”也可以用“亲情碎了,筋还连着”这个直白的句子替换。在我看来,亲情其实可以理解成碎裂残缺的过程,也许,只有碎裂的过程才能让亲情有生长、呼吸和弥补的空间,像一个人吃饱喝足,他就不会感受到饥渴,也不会意识到亲情的存在和意义。亲情是相斥的,也是相互的。对于堂哥的关心,其实是对于我自己的关心,如果闭上眼睛装瞎子,我的内心就不会得到安宁,更不会变得轻松。因此,与其说是我花了一小块时间安慰问候在上海某个小区的堂哥,还不如说是在“打发”自己,形如过去母亲用一堆好话“打发”并且成功打发掉贸然闯入我家灶屋的那条家蛇一样。
潜意识里,我其实更容易读懂和理解堂哥的生活与人生,因为我们都在多年后实现所谓的理想,完成与断裂带的告别,成了“自生自灭”的异乡人。就是说,我们都变成了断裂带的过客,相对被泥土吃掉的父辈以及还在那片土地打发时光的乡亲父老,我们已然搭上命运的班车,开启新的旅程。然而,不可否认,无论飞得多高、走得多远,也无论岁月如何生长,我们的现在与过去始终连在一起。与天各一方已经很少往来的堂哥联系互动的原因,其他只是引线,亲情当然是主要原因。
在日常生活中,似乎很多现象无法得到科学或者确切地解释,就像从断裂带嫁到李白故里江油青莲镇桃花山下的三娘告诉我,外公去世那年,她的牙齿一直莫名其妙地痛,撕心裂肺地痛,吃药也无济于事,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大半年,外公去世后,她的牙也不疼了。
提及堂哥一家,“家蛇”就会作为某种意象在我的脑袋里盘旋。莫非,是我心心念念,或者是我的“自以为是”,又或者一厢情愿的“结果”?堂哥一家的故事,还有断裂带村里人对堂哥一家的“只言片语”,就像那条大伯当年在自己家里“结果”了的家蛇,总在我的记忆里闪烁,挥之不去,呼之欲出。想说的是,将过往写成文字的基础也许就是这样一种“挥之不去”,并非刻意渲染和故弄玄虚,也不是奔着稿费,而是为了释怀,为了看清我们这些断裂带儿女的过去和当下,“打发”脑袋里那些不断纠缠的画面,任凭它们去该去的地方。时光来了,时光走了,时光一去不返。人,永远去不了的地方就是过去。我不知道“挥之不去”意味着什么?可以肯定的是,大地有自己的筛子,时间有自己的筛子,记忆也有自己的筛子,平常的事件在脑袋里无法储存,而“破例”的经历却可以逃过岁月筛孔,在脑袋里持续一生,在我还没有被弹弓弹出断裂带的岁月深处,与堂哥一家或者那条家蛇有关的记忆从未枯萎,不曾凋谢,时隔多年,那条出现在堂哥家里的家蛇,似乎仍在岁月深处某个角落凝视着,沉默地凝视,深深地凝视。
二十世纪末的断裂带,刘家院子屋后的那条水泥路还在泥土间沉睡,压路机、挖掘机、筑路队尚未抵达我们那个村子而大片庄稼也未被人从日子里撵走,乡亲父老的汗水总是被泥土当做肥料包裹,孩子则像麻雀一样乱飞的日子,除了操心自己,我也总是整天帮父母操心,想象家里的房子如果倒过来的话,能否倒出我和弟弟新学期的学费。野樱桃熟透的五月,家门前的河流便饥渴地亲吻我们乌梢蛇似的身体,在我们的皮肤上歌唱,而父母总是能够在我们的胳膊上划出一道白线洞悉我们偷偷下河洗澡的秘密,我们害怕棍子的惩罚,常常浑身爬满了虱子一样痒得无可奈何。为了预防我们偷偷下河洗澡,家长们时常告诫我们,河里住着水鬼,会将洗澡的小孩子拉下去。对河流的信赖与枯燥生活的厌倦,让坐在心头的恐惧大打折扣,因此家长的话总是从我们的一只耳朵进来,又很快从另外一只耳朵出去。其实,我们也早就意识到,动不动就拉孩子下水的水鬼并不存在,无非是长辈为了管束我们而生出的另一双眼睛和手。我们都不喜欢家长管得太宽,也不喜欢管得太宽的家长。
接下来就是要讲述的事情,那是早年断裂带一个闷热的午后,知了声在房前屋后聒噪,一根肥硕粗大的乌梢蛇爬过粗糙的水泥院子,雄赳赳气昂昂地闯入刘家院子最东边的大伯家里去了。浑身裂缝的水泥院子坐着我们的等待,那天,我们没有像平时那样跑去河里游泳,将我们晒得就像乌梢蛇一样的胳膊和腿继续晒得闪闪发亮,就是为了等待。冥冥之中,这一天我们是在等待这条乌梢蛇的到来。不知是谁通的风报的信?让我们马不停蹄地快速向大伯家集结,向这条胆大包天、突如其来的乌梢蛇靠拢。恐惧和兴奋的感觉让我们跑得迅疾如风又摇摇晃晃,空气因此留下更大面积的擦伤。那根冒冒失失的乌梢蛇恐怕不会想到,从它出现的时刻起,残酷的命运已然雪花般地落在它摇摇晃晃的脑袋上面。
一场惊心动魄的人蛇大战已然拉开序幕。
用了一小块时间,堂哥刘强的父亲,我那身强体壮的大伯就已经死死地逮住乌梢蛇,黑黢黢的尾巴像一截闪电,在我们的眼睛里扫来扫去,拼命地挣扎着、摇晃着。家蛇至少有半截命运掌握在大伯手上了。蛇在挣扎,我们这些旁观者的头皮也在阵阵发麻,心脏因为兴奋、紧张、刺激还有恐惧的挤压,似乎就要从身体的某个部位跳出来。时间凝固一般,空气凝固一般,我一会儿看着大伯,一会儿看着那截蛇尾,一会儿又瞧着那些老鼠洞,眼睛都要忙不过来了。蛇鼠一窝,一个成语快速闪过我的脑海。家蛇与大伯的手在沉默中对峙,沉默是一块磁铁,牢牢吸着蛇尾和大伯的手,也吸着我们的眼睛。家蛇有半截身子已经钻进一个老鼠洞,大伯家卧室墙角的一个老鼠洞,老鼠的眼睛在大伯家的墙角滴溜溜转。在断裂带,贫穷人家的墙角总是会长出这样的眼睛来,而富人不会。谁都能看见,大伯家卧室的老鼠眼睛不止一只,而是好多只。老鼠洞,我们家也有不少,但数量远远不如大伯家。
老鼠用它的眼睛秘密注视着人的生活,注视着大伯一家人的生活。我甚至没心没肺地相信,这么多老鼠洞开会似的聚集在大伯家,已然把大伯家变成一个老鼠窝、一个根据地,一个繁衍生息的家园。旁观者的眼睛在滴溜溜转,大伯的眼睛也像老鼠一样滴溜溜转。“这条蛇是家蛇,打不得,等它走了算了!”大伯凶巴巴的,脸色阴沉,始终不愿松手,像是在与墙拔河,更加卖力地想要把家蛇揪出来。就在我们为胜负难分而捏着一把汗的当口,汗如雨下、满脸通红的大伯,竟然眨眼间将一条好好的家蛇活生生地挣断了!一条家蛇断成两截,失去半截身子的家蛇终于逃之夭夭,留下蛇尾在地上跳舞似的苟延残喘般拍打着粗糙的水泥地面,拍打着卧室里昏暗的光线,拍打着我们的眼睛,然后陷入了永久的沉默。
屋子里留下一片死寂。
至于大伯后来如何处理剩下的半截家蛇,我早已忘记。所谓“家蛇不能打”的民间禁忌,某些不可言说的念头,似乎也在那一天截止,在命运或者意外落在家蛇头上的那一刻截止。失去半截身子的家蛇早就一命呜呼,与其想象它已经逃之夭夭,不如说它是逃进了我的眼睛,逃进了我的记忆,一个岁月始终无法将其清除的死角。
四
穿过当下,咀嚼往事,当我默念“家蛇”这个字眼,不免思绪万千,感慨万千。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在《白色城堡》里如此写道:“在生命的某一时期,当他们回头审视,发现多年来被视为巧合的事,其实是不可避免的。”
我对早年堂哥家那条被大伯残忍毁掉的家蛇“记忆犹新”,是因为,在岁月里,我已经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审视的目光,审视的对象并非家蛇,而是过去、当下、未来之间的渊源,一个过程——命运迁徙的过程,我看到了,也见证了,并且感同身受。在我眼底,家蛇和过去的点滴,包括堂哥一家的生活,同样在我如今的审视中有了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深意。当我试图用“家蛇”保留这些记忆,苍白的文字其实远没有过去清晰,因为对我们而言,时间早就一去不返,我们早就一去不返,站在原地的只有记忆,只有家蛇那幽暗、神秘和哀伤的眼眸。
相比在大伯家那条一分为二的家蛇,当年出现在我家灶屋的那条家蛇实属幸运,我们非但没有让它受到一丝伤害,还好言好语、战战兢兢、恭恭敬敬目送它悠然离去。出现在大伯家里的那条家蛇就没有这种待遇,虽说也算离开了,不过只逃脱了它的一半,留下一半。当年,在母亲那里,我感受到的是恐惧,人对蛇的恐惧,或者说是对恐惧的本能反应,母亲的好言好语是一种示好、一种巴结,或许还有对生灵的敬畏,恐惧因此得到释放,我们得到释怀;大伯则无须担心这些,他也不必害怕什么。身强力壮的他走起路来像只螃蟹,没人敢惹,有谁敢惹?大伯又怎会放过一条蛇呢?俗话说,见蛇不打七分罪呢!
关于“见蛇不打七分罪”,在断裂带,在我外婆出生的北川一带,还流传着一则故事:
很早很早以前,蛇是不会脱皮的,因而会死,而人老了脱层皮就又变年轻了,那时有对夫妻已经八百岁了还没死。活着就要生计,就要干活,有一天夫妻二人干活累了,妻子就抱怨:“干活就像脱皮一样恼火,要是人不用干活,不用脱皮才好呢!”丈夫却问:“不干活吃啥?”他们的话被蛇听进了耳朵。有一天男人出门干活,半夜还未归家,当妻子的就在家里等啊等啊。蛇就假装上门问女人:“是不是在等你丈夫呢?”女人就回答:“就是,这都半夜了,人还不见回来,也不晓得跑哪里去了!”蛇就说:“你别急,我晓得他在哪里,只要我们换一样东西,我就去帮你把他找回来!”女人问蛇:“换什么?”蛇说:“你把脱皮的办法告诉我,我把死的办法说给你。”女人于是答应了,与蛇各自交换了各自的办法。从那以后,人就不脱皮要死,蛇就会脱皮不死。见蛇不打七分罪,那是因为恨蛇呢!
故事的名字叫《人脱皮》,我在一部民间故事集里偶然读到。
见蛇不打七分罪。那条在大伯手上断成两截的家蛇,厄运里是否包含着人与蛇之间古老的敌意?家蛇能不能打呢?任何民间故事,多是过去年代人们枯乏生活的调味品,是人对自然现象的一种感性思考、认识、想象和杜撰。在大伯家里变成两截的家蛇确有其事,并非凭空杜撰,不过这条家蛇也只是串联起当下与过去的一截绳子,将那些场景、人事和记忆捆在一起,置于断裂带的框架之内。
很多时候,想起大伯就会不由自主想起那条家蛇的遭遇,想起他的咒骂,想起他不苟言笑透着凶狠的脸孔。在断裂带,大伯算是个狠人、断裂带罕见的狠人,归根结底,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民。据说,年轻时候的大伯就已经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物了,他的世界没有道理可言,拳头就是道理,拳头就是命令。我们还知道,怪脾气、坏脾气于一身的大伯,早就无法用连自己亲爹都敢打来形容,而是真的打过。
这样的人,还有什么不能打?不敢打?那些年,大伯的拳头总是雨点一样落在堂哥身上,落在堂妹身上,落在伯娘身上。在断裂带河边,我亲眼见过被大伯打得遍体鳞伤的伯娘跳河的场景,大伯不但不心疼,还在一边冷嘲热讽:“去死吧!大河又没盖盖子!”也见过洪水暴发的季节,想必是因为大伯看见钓鱼的堂哥刘强一无所获,就怒气冲天地施出连环腿将弱不禁风的堂哥踹倒在地,事发突然,我们吓得不敢吱声,明白也更加不明白大伯为何打人?
岁月生长,人是会变老的,大伯也不例外。
大伯没有来得及老,就已经得到了自己的因果报应。
好些年前的一个春节,大概就是除夕当天,再也无法忍受的堂哥、伯娘和堂妹多年的委屈终于火山爆发,用村里人的描述,是一家三口联手将喜欢酗酒并且撒酒疯的大伯在家里毒打一顿。曾经拿拳头打过自己父亲的大伯,被自己的妻子和儿女痛打一顿。这件事,我们那个村子的风知道、虫知道、鸟知道、草知道、树知道,人也知道,但无人前去当和事佬,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谁也说不清!就在当天,已经在上海工作刚刚回断裂带过年的堂哥收拾起尚未打开的行囊,带着在家熬了多年的伯娘到上海去了,临走,堂哥丢下一句绝情的话:“等他死了我再回来!”堂哥走后,大伯的遭遇很快引燃诸多乡邻和亲戚的同情,虽说只是马后炮,但毕竟是同情,与堂哥有关的负面评价很快在村里传开,比较直接的是“白眼狼!”相对委婉的则是“书白念了”“书念多了!”“脑袋给书念出问题了!”说得就像读书会给断裂带引来什么灾难似的,不过,村里人就是这么说的,针对的仿佛不是堂哥,而是那些读书人。总之,留在村子里的人,对堂哥没有一句好话,也没有任何人深究大伯多年来如何折磨堂哥折磨伯娘的那些陈年旧账和斑斑血泪。
五
无数次,驱车从大伯门前路过,都看见大伯一个人可怜巴巴地坐在自家门前,一动不动,仿佛一株人形植物。我不敢打开车窗,不愿车内涌进那隐匿在空气中的空旷和悲凉。
断裂带的内部和外部,纯粹的本地人和只是逢年过节回来的本地人,看法和想法似乎都不在一个人生频道。即便同一件事情,也会产生歧义,歧义就是偏见,偏见之下隐匿着人性。如同对于家蛇,每个家庭每个人会有截然不同的态度。也许,因为那条家蛇,因为我和堂哥类似的经历——读书、就业、异乡生活——如今我们都把各自的命运移栽到断裂带之外,移栽到异地他乡,我对堂哥其实没有家乡人言语间的那份刻薄、疏远乃至排斥,我同情堂哥胜于大伯,有时,我甚至能够想象堂哥、伯娘那些年内心的苦涩和忍气吞声,看见他们曾经日复一日忍受过的暴力、野蛮和绝望。
大伯生命的最后几年,在酗酒、恶疾和孤独中度过。就像早年被他终结命运的那条家蛇一样,他的家也一分为二,儿子妻子都不愿跟他一个屋檐过日子,他只好孤家寡人独自生活,自己洗衣做饭,自己穿过白天夜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2020 年夏天某个日子,不记得是上午还是下午,抑或傍晚?在断裂带老家的弟弟忽然打来电话,语气平淡地告诉我:“大伯走了。”喘了口气,他又告诉我,“大伯是自杀的,刚刚才发现,脖子上缠着一圈绳子,脚下还有瓶已经喝光了的老白干,估计夜里上吊走的。”
堂哥带着伯娘去上海一起生活之后,大伯一直独自在家,孤苦伶仃,无人照看,又身患恶疾,这样的结局,也是意料之中。
不过,在我看来,大伯并非死于病痛,而是死于痛苦、死于孤独。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弟弟打来电话说到绳子的时候,当年被大伯首尾断裂的家蛇,忽然就在我脑海浮现出来。我产生一种幻觉,大伯脖子上的绳子,冥冥之中与当年那条可怜的家蛇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比如样子,比如姿势……
今年春节,堂哥刘强一家从上海开车回断裂带过年。“手上戴了个金镯子,眉飞色舞的,简直洋昏了,刘强买的,说是要值一万多!”母亲添油加醋说起伯娘“衣锦还乡”的盛况,羡慕不已。听说,堂哥刘强在上海混得不错,出手阔绰,回来后还特地在断裂带的农家乐请客吃饭,坐了六桌。“客”,都是些村子里的亲朋好友。
其实,堂哥回断裂带过春节的那天下午,我也在家,就在他家斜对面的大娘家。我、弟弟、波哥、玉哥四个人刚坐在牌桌上“找朋友”,打牌,几乎是每年逢年过节的传统节目。除非天塌下来,坐上牌桌似乎谁都不想挪一下屁股。忙着端茶递水的大娘跟我们说:“刘强娃回来了!”弟弟眼睛看着牌,语气轻蔑地说:“自己老子都不认的人……”我纠正弟弟的说法:“在外地工作,除了双手无依无靠,不容易!”
我的声音隐含着一丝羞怯、一丝愧疚,像是在帮自己说话。之前一天,和弟弟一起到坡上挂坟,经过大伯坟地,特地驻足烧了些纸钱。大伯坟地周边杂草丛生,荒凉落寞的身影,透着命运的那些不甘心。坟前的酒杯浑身泥土,仿佛旧时的文物。弟弟说:“大伯啊,你看,大过年的,你娃都不看你,草都长得比人高了!”弟弟话里带着话,无非是说,远水救不了近火,远亲不如近邻……
刚刚驱车千里迢迢回到断裂带,回到家门口的堂哥就出了点岔子,因为常年在外,或许是已经忘了路况,将车一下子开进了他家门前的排水沟,出不来了!大娘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波娃子,你们快去帮帮忙!”波哥听完,自言自语似的抖出一句出人意料的话:“才拢屋,老太爷就给来了个下马威!”
断裂带有句老话:“天都亮了,还把尿屙在裤子里!”刚从上海驱车回断裂带过春节的堂哥就是这样,路上顺风顺水的,在家门口却栽了跟头,把车开进门前水沟。久违断裂带的堂哥,居然在本地人闭上眼睛也能走上好几里路的家乡,自己把车开进了水沟。
确实有点不可思议,有些匪夷所思,有点说不出的味道。
我们没有起身擦亮经年累月早已锈迹斑驳的亲情,向仅仅隔在一道卷帘门外的堂哥伸手相助,仿佛碰面是在耽搁时间。我们继续沉浸在纸牌的游戏之中,沉溺在一场时输时赢其乐无穷的欢乐之中。记得那天,平时很少打牌的我数次发错牌,与发牌行云流水的亲人而言,我更像是一只笨手笨脚的菜鸟,捏着手上的纸牌如同捏着过去的一个个片段。出牌慢,还老是走神。事实上,我无心打牌,也不在乎输赢,想着隔着一道门外的堂哥一家……每一张打出去的牌都是过去的一段经历,每一张打出去的牌都有去无回,因为牌会被更好的牌吃掉。四个人的纸牌游戏却简单明了,除了地主,谁都要暗里较劲,因而过程总是迷雾重重,一波三折,除非有人打完,否则胜负难分。
那天,我总是赢,一直在赢,赢得越多,我的脑袋就越发虚空,越发沉重。“快拿回去,又不是三岁小孩!”回家路上,我无所谓地想把弟弟输的钱交给他,弟弟拒绝,弄得我很尴尬。
六
断裂带,早年的刘家院子早已不再是原来的模样,几户人家就像一块碎掉的玻璃,在地震后把影子留在原地,然后各奔东西。幺爸房子建到镇上,我家的房子、大娘家的房子和大伯家的房子则各自修在九环线的公路边。
大娘家的房子就在大伯家的斜对面。据说,大伯临走前的那段时间,行为已经开始反常。有天半夜,他惊恐万状地跑到大娘那里敲门,说河里边有几个人正在喊他到河边去,说是要好好收拾他。“帮我看看他们是哪个?”汗水淋漓的大伯一脸恐惧,几乎是在哀求。深更半夜,大伯的一番话,听得人汗毛倒竖。翌日,大伯似乎仍然惊魂未定,缓过神来的他举着拳头,喊我弟弟跟他一起去河边跟那些人“拼命”……
儿时跟大伯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大娘说,那些日子她最提心吊胆的就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大伯。每天一日三餐前后,她的脸孔和脖子都像定过闹钟一样,习惯性地朝大伯家的房子那边张望,看看大伯家的房子是否有炊烟升起。望炊烟本身是一种等待,需要耐心和时间的填充。而炊烟无疑则是一种信号,说明大伯肚子里的饥饿还在,说明大伯脑袋上的天空是明亮的,说明大伯还是好好的一个人……
2020 年夏天,孤苦伶仃的大伯不再留恋什么,再也爱不动什么,于是选择以一种近乎残酷的方式离开,不过,这符合他的一贯风格,一了百了。有时,我忍不住怀疑,当年从他手里挣断尾巴的家蛇,为了逃离,是否也带着一丝故意?
现在是2022 年春天,断裂带的炊烟仍在继续升起。透过城市的喧嚣,透过文字的缝隙,远远的,我在绵阳的园艺山上望见断裂带那熟悉又陌生的炊烟,乡亲父老的炊烟,儿时的炊烟,充满辛酸苦辣却无以言说的炊烟,祖祖辈辈世世代代在这片土地延续的炊烟,默默守望着断裂带的悲欢离合,守望着断裂带的春夏秋冬,守望着断裂带的人间烟火……我,远离了的炊烟,远离了的断裂带,远离了的家园。
壬寅年四月中旬,因为问候远在上海生活工作的堂哥,很自然地想起过去,想起成长中的那些琐事,想起那些与家蛇相关的点滴。家蛇,真的存在吗?我是说它具备的魔力与神性。谈及家蛇,断裂带的大多乡亲父老总是心生恐惧满怀敬畏,我也一样。一晃多年过去,家蛇似乎早已销声匿迹。或许,销声匿迹的其实并非家蛇,而是过去的“我们”,整个只属于断裂带的“我们”。如此一来,我就略等于销声匿迹的家蛇,家蛇略等于一个隐喻,敬畏与恐惧同在的隐喻或者象征,包括我对家乡的眷恋与灰心。当我在文字里把过去重新走了一遍,自己回到自己身边,记忆中的家蛇,似乎正亮着心脏穿过断裂带,穿过涂白了树梢的寂静,穿过无边的大地,穿过层层岁月和空气,朝着我的方向滑动,隐隐的,耳畔传来一句充满智慧和力量的不朽箴言:
“古花古谢,今花今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