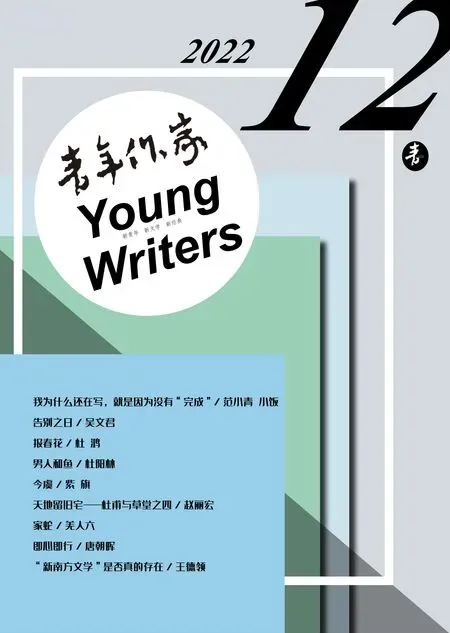今虞
紫旗
上篇
母亲说,记清楚没有。我把垂到胸口的脑袋点了点。
她拔高音量,又重复了一遍:“不准搞忘,晓不晓得?”
我大声地说:“晓得了。”
母亲满意地点头。
她把我拉到身边,正了正我的衣领,手越过前额,落在头顶,从头发到发根,她一下一下地撸,像是在撸羊毛。起先她力气很轻,然后越来越用力,我想喊痛,母亲说:“看你老汉还咋个编。”我于是不敢喊了。
今天之前,我就来过乐阳县的法院,爷爷是这么告诉我的。
他说上一次是打离婚官司,母亲早早先去,他和婆婆带着小姨,出发时,见我趴在玻璃上看鱼,他走出去,又走回来,走到看大鱼小鱼依次扎进水底的我面前,最后抱着我出门了。爷爷说,今虞那阵才点点大,肯定没得印象。
爷爷不知道,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记忆,只是那些很小时候的记忆全都模糊难辨。每次我想回忆,都像站在水面之下往岸上看。但越是这样,我越想探头,这种心情,和我后来在半黑不黑的夜晚走到楼底,看见楼上只亮了一盏灯的房间,温温地放出昏黄的光,映在玻璃窗上吸引我进去,其实是一样的。
再来,就是今天,爷爷说,你现在可以记清楚事了。我想尤其是,我现在可以说话了,所以母亲让我来当证人。
起先,我告诉母亲,我不知道说什么,母亲一下就愤怒了。她愤怒时,眉头聚成层叠的山峦,窗外吹进的热风不能把它拂平,我更不能。屋里的光线很暗,我必须更加仔细地分辨母亲的表情,才能揣摩她是什么样的心情。幸好,母亲拔高了说话声,每个字清晰地传进我的耳朵里,但随即我就意识到,不妙的事情发生了。
“他不管你,也不拿钱,这么多事情你哪件不晓得?”她说。
每次母亲升高了语调说话,我都感觉像是铜炉里烧开了水,再多一秒就要迸裂。于是我马上说,我害怕,我不想上法庭。这次是实话了,但母亲仍摇头,她说:“你不想,未必我想。你老汉不拿钱,我有啥子办法。”
母亲不再撸我的头发,我目睹她的眼眶变红,火光在里头哗哗地燎,它越烧越旺,好像在管我要什么东西。我终于感到无处可逃,说,我去。
回到乐阳,我还穿着校服。在车上的时候我想脱,母亲不准,她说,这样好,让法官看下覃一鸣他个狗日的一点良心没有,女儿还在读书就不管了。但我很讨厌穿校服,惨白,肥大,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我像套进了一件囚服。天气燥热,车子却没有开窗,一股混杂着汗渍和脚臭的味道冲进鼻腔,我把头偏向左边,又偏向右边,还是摆脱不了它的禁锢。母亲骂,板命啊。我于是不再动弹了。
今天是星期三,上学天,我本来该在简中,不该在乐阳的。但我背上书包的时候,母亲突然跨着两条细长的腿走到门边,她说,今天不去学校,去车站,我们回乐阳。每个月底的周末,母亲都要回乐阳,也没有什么事情要办,只是待着,待到上班的头天晚上她再回来。母亲说,乐阳才是她的家。她带着我,每次搭同一辆脏兮兮的小车回去,次数多了,司机都认得我们。但是今天才周三,所以我很惊讶,这是我第一次从母亲嘴里听到“请假”两个字,以前哪怕是我发烧,母亲也会在我吃药后马上把我送到学校。所以我问,回去干啥子,她说,打官司,顿了顿,她又补充:和你老汉。
我走进车站时,闻到了熟悉的酸臭。十米见方的大堂被汗津津的人堆挤满了,厕所的味道不断飘来,填满我的呼吸。我向母亲投去一瞥,她浑然未觉,大步流星地走,母亲好像总能无视那些令人难受的东西。我只好屏气,飞快地跑,穿过大厅和大厅旁边的厕所,回乐阳的小车停在尽头,树底下光秃秃的,连块草皮也没有,我藏进阴暗的角落,和堆在过道边的大包小包一起等买票的母亲回来。很快,母亲来了,我们坐上车,卖东西的婆婆也过来了,她们站在外面敲窗,问,油条买不买根?报纸呐,报纸来不来一份嘛?我每次隔着车窗看,她们的脸都是一张瀑布下的岩石。
母亲说,不要。其实我想吃。婆婆一定是看出来了,她说,娃娃想吃,买点嘛。母亲又说,不要,说了不要。这次已经不耐烦了。婆婆嘴边的纹路抖了抖,然后走了。
我问母亲:“婆婆好可怜,每次车上都没人买,东西好久才卖得出去呀?”
母亲说:“你操心别个,车站一天到黑多的是人,你操心就操心你自己,你这回期中考试又没考进班上前三。”
我不说话了。
车子缓缓驶出,起先路面宽阔,等开过长长的滨江路,后面都是小路,颠了两个小时,我们到达六十车队。现在我不会再往党校走了,最开始的时候,每次回家我都想回党校,因为党校的房子我们住得最久,从我有意识开始,我和母亲,还有父亲就住在那里。但自从它卖掉,后面再回老家,我们只能住爷爷婆婆的屋子。母亲说我们最早是住房管局,到我一岁的时候才搬到党校。我记得,院子里有一种紫色的花,年年很热闹地开,母亲说那是紫荆,我搞不清楚,一直写成紫晶。二楼住着表叔家,正上方就是我家。爷爷在楼外面的花坛里养了三棵铁树,每棵都长得特别高大,比周围所有的花草都要高大。我读六年级的一个晚上,有人抹黑偷走了一棵,早上母亲发现气得跺脚,在小区门口贴了告示,铁树没有回来,也没有人再偷剩下的两棵铁树,它们平平安安地长大,直到我离开乐阳。还有一棵枇杷树,它长到了三层楼高,正对我家阳台。她们谁也不知道,那是我种的,是我有次从父亲那里回来,门口孃孃给我的种子。她当时看我在哭,问我咋个了,我说,他们骗我的糖吃。她就给我一个枇杷,说:“钟孃孃给你糖吃。”我把枇杷吃完,核留下,种在家门前的土里。后来它拼命长,枇杷果长了一树,黄澄澄的,特别好看。
党校的房子也是我住过最大的房子,它有上下两层。书房和三个卧室在上面,下面一层都是客厅,除了厨房和厕所。我和姐姐每次比赛,比谁的胆子大,最喜欢闭着眼睛跳舞。我们从客厅跳到阳台,闭着眼睛转很多很多圈,怎么也不会撞到家具。但跳舞只能悄悄进行,母亲每次看见都会生气,她不好意思骂姐姐,只能骂我,骂我“点都不让人省心”。我好像总让母亲生气。刚搬家的时候,我和姐姐跑到主卧室蹦床。我说,你们屋头没得这么大的床吧?蹦起来,又说,我爸爸讲有一米八宽。姐姐问,一米八是好宽喃。我答不上来,想了想自己,有六十厘米长,就说,我给你比一下嘛,然后两下蹦到床边,往后一倒。我忘了痛不痛,有多痛,只记得母亲大声斥责:“覃今虞,你又在搞啥子!”
其实,如果不是母亲发现得太快,我自己就能爬起来。每次母亲刀片般的嗓音从我身上划过,父亲就会过来,用他温水一样的声音说话。他说,小娃娃都是爱闹的,或者说,先检查下有没得问题再说,父亲最常说的就是这两句话。父亲和母亲完全不同,我写作文的时候,写我的父亲,他是一块棉花,可以揉来揉去,没有固定的形状。像是母亲问他,“你是不是藏私房钱”,他就说,“你不信去单位上问”,母亲骂他,“没得我哪有你们今天”,他就说,“所以我是百依百顺”——他什么都能接住。父亲也从来不会和我发火。有一次,我把放在书柜最下面的墨水瓶刨出来,想玩,没拿住,墨水从我的手上爬进地砖的缝隙,红艳艳的,和鲜血一样。我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为什么不让它就是鲜血呢?父亲这时候过来了,我赶紧远离那个柜子,把手举得高高的,喊:“爸爸你看,我流血了!”我像炫耀战绩一样。
父亲细长的手指拧着毛巾,一遍一遍地擦我指间的红,他说,咋个弄到的。我高兴极了,心想:爸爸好笨哦,我说流血他就信了。
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很多回,能记起来的,还有父亲给我订《幼儿画报》,每期都订,里面有东东、西西、南南、北北四只小动物,每看一次,父亲就重复一次: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要分清楚。但是直到他离开,我仍然分不清东西南北。到后来,我开始疑心记忆是不是欺骗了我。我想,如果一切都是我记忆中呈现的那样,那么当我央求他不要和母亲离婚时,我记忆中的父亲,不会把我像扔垃圾一样地扔走。
那是我第一次发现,原来我那么小,小到他扔出我,就像弹走一粒没有重量的灰尘。
我很早就预感到,他们会分开。最早的一次,是我读幼儿园小班的时候,白天,老师教我们唱歌,下午母亲来接我回家。我喜欢沿方格的边缘线走路,先迈左脚,再迈右脚,稍微倾斜一点,就要摔倒,但那几乎不会发生:我的平衡感从小就很好。我会边走边唱,那天也是,我唱《捉泥鳅》:“池塘里水满了,雨也停了。”唱了两句,我说,我唱得好嘛。母亲猛地把我抱住。
她埋头在我肩膀,不说话,手臂撞进我的眼中。下臂依然洁白,自手肘起,红焰流动,爬满上臂,宛如一场冰火交融。我觉得过于刺眼,问她,身上咋个又红又青。母亲说:“你老汉打的。”顿了顿,她又说,“你装不晓得。”我说好。
一周过去,它们还是那样,哪种都没有变淡,我告诉了爷爷,它们反而越来越浓,成了母亲身上常见的颜色。我开始希望父亲不要出现,仿佛听见我的祈祷,父亲果然不再回家,他越来越频繁地夜不归宿,但这时,我又希望他回来,我想或许那样母亲会高兴一点。忘了是从哪一天开始,父亲再回到家时,几乎喝得酩酊大醉,酒气冲天,我不得不离他喷气的鼻子和嘴巴远远的。他喝醉了就吐,不吐在家里,总爱吐在楼梯的过道上。母亲说:“你这样让邻居咋个办。”他说:“凉拌。”他还是什么都能接住。
最后母亲拿着拖把,像把仅有的那些一点不剩地拖得干干净净。
再后来,我从他们的嘴里听到两个字:离婚。没有任何人和我解释那是什么意思,但奇怪,我就是知道。那时学校已经开学,我睡得很早,小孩都睡得很早,七点,或者八点,最多不超过九点,我被吵醒时,天出奇地黑,窗外大雨瓢泼。我先听见了打雷的声音,然后才听见门外面的争吵,好多人的声音。我扒开门,见客厅里所有灯都被打开了:黄的白的,红的紫的,亮得烫眼睛。母亲站在客厅中间,一个人,父亲在她对面,和爷爷奶奶挨在一起。他说话,声音还是那么轻,我听不清,只听见母亲的声音,永远锐利而响亮:老子早就晓得你们一家人都是白眼狼!我又听见她说:给老子滚!
父亲突然拎起音响上的花瓶,砸向母亲,当啷一声脆响,花瓶在母亲背后的墙上绽开,粉末四溅,飞向天空、地板和母亲的后脑。我没有套棉服,很冷,胃里那只湿冷的小动物又开始哀鸣,我一溜烟儿地跑下去,抱住父亲的小腿。他整个人陷进沙发,自上而下地看我。
“爸爸你莫和妈妈离婚,我害怕。”我说。
我记得,他拎起我,使我不得不蜷起四肢,像一支冷箭般猝不及防地射了出去。再往后呢,我是什么反应,母亲有没有和他厮打,父亲是什么表情,这些之后的事情就像被什么东西抹掉,一概没有在我的记忆中留下。我问婆婆,她说:这是记忆在保护你。或许因此,我关于父亲的记忆总共也没有多少。记事以来,父亲在我记忆里留存下的,不过是一些坍缩的、单单调调的剪影。
那之后,父亲没再出现,又或者是,我的记忆里不再有他。
十二月,元旦前夕,县城张灯结彩,姑婆接我回家。她是临危受命来照顾我。母亲不再每天接我放学,她太忙了,她说事情只剩她一个人做。渐渐地,我和吴晓叶结伴回家,她和我一样,也是大人没有时间接送。但我比吴晓叶幸福很多,她回家帮奶奶做饭,我到家的时候,已经有做好的晚饭在桌子上等我。母亲最会做韭菜粑粑和凉面,炒菜就不太好吃,做粑粑和凉面我就多吃点,做炒菜我就少吃点。只有那天晚上,我什么也没有吃。还在门外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劲,我想,居然没有电视的声音。母亲永远开着电视,她说有电视的声音家里就有人气。
我没有敲门,用拴在脖子上的钥匙拧开门锁,进屋,望望楼上,又望望楼下,然后我往里走,看见敞开的冰箱,像一只张开獠牙的野兽,蛆虫从它嘴巴里爬出,一股股的,像白色的液体流了一地。我从来不知道自己可以发出那么像母亲的声音,我挤出一声尖叫。这时我看见了母亲,她缩在角落里,整个人单薄得像被床板压过。我跑过去,像汇入一条大河,泪越流越多。我说,怎么办,我们怎么办。母亲抬头,眼睛像浸在水里的玻璃珠,亮晶晶的,里面什么也没有。好半天过去,她说,妈妈把姑婆接来。
两天后,我见到了金顺老家的姑婆,背着比她半个人还大的背篓,声音洪亮,说话像吵架一样,她说,今虞都长这么大了啊。她笑起来,露出粉红色的牙龈,母亲也笑着回她,是嘛,日子挨起来也快得很。声音是难得的低沉。我听了不说话,心知自己很瘦,但姑婆比我更瘦,眼眶凹进去,眼球突出来,看得久了,我怀疑她眼珠子都快掉下来。正发呆时,她伸出手,摸了摸我的头顶,手上泛着密密麻麻的黑斑,我有些害怕,听见她说:“小园怀你那阵就是我照顾,你生下来的时候我还抱过嘞。”我就忽然不感到害怕了,只是用很小的声音说话。
“姑婆,我五点钟放学哈。”我说。
之后,每天下午五点,出现在校门口的人从母亲变成了姑婆,那天也是。我奔向姑婆,她接过我的书包,挂在她只有几根骨头的身体上面。姑婆说,今天咋出来这么暗。我说,黄老师说我笔画不对,她说我拼α 是画蚯蚓,写对二十遍才准我走。姑婆点了点头。我说,姑婆,妈妈这几天回家都好暗哦。姑婆没说话。我摇了摇她的手,她说:“你爸爸妈妈离婚判下来了,你妈妈在忙。”
在忙,忙什么呢,姑婆没说,我也没问。
晚上,母亲把已经睡着的我叫醒。我喊困,想睡觉。母亲摇头,脸色灰得像烧过的纸钱,我想。这时听见她说,起来,给舅舅烧纸。她的声音很轻很慢,随时都会哽咽一样。我爬起来,往火光大盛的地方走,走到阳台。母亲摆好小板凳,说坐,我就乖乖坐好,她说,烧纸。我就接过纸钱,模仿她的动作。她观察火焰,每当火舌回缩她就喂入一张粗糙的黄纸。烟雾很快熏满了整间屋子,我满眼是泪,央求母亲:“我们烧好多了,舅舅够用了嘛。”但母亲仍在投纸,她说,再多烧点,让舅舅保佑我们以后过好。她一遍一遍重复,任何东西,风、黑夜、烟雾,都无法吞没这盆熊熊燃烧的大火和母亲的话。那晚我最后的记忆,是母亲的话,她说:如果你舅舅还在,我们不会这么被欺负。
中篇
父亲和母亲离婚的头两年,我还会去到父亲家里,印象中,去过两次。一次是在暑假。天气热起来,在一个异常闷热的雨夜里,我梦到自己坐在车上,车子摇摇晃晃,一直开到省城。醒过来时,母亲坐在我的床边,她说:“你爸爸想带你去成都耍。”
如在梦里,我真的到了省城,那是我第一次去成都玩,夏天的颜色是鲜亮的,风不大,天很蓝,雨天过后,空气都清爽起来。我和父亲,还有覃皓然一起,我们在动物园来来回回地走,看熊猫、猴子、金丝雀还有狮子,父亲的脖子上挂着黑沉沉的东西,砖头一样,问我们,要不要拍照留念。他又回到我记忆最深处的样子,声音和动作,都像一条小溪,缓缓地流出不大不小的声响。我在父亲的指挥下,把饲料投进池塘,鲤鱼竟像蜂群,不断从水里往外冒。我说,它们好能吃哦,我都看饿了。覃皓然说,我也饿了。于是父亲说,想吃啥子嘛?我大声说,想喝牛奶。父亲说,牛奶,尾音往上扬,然后降下来,说,牛奶是不是贵了点?我说,妈妈每天早上都给我牛奶喝。他哈地笑了一声,嗓子突然吊起来:“你妈硬是讲究得很,我们屋头天天早上喝稀饭,她金贵,天天喝牛奶。”我想说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喝,但我终于什么也没说。
那也是我第一次发现自己晕车,回去的路上,我吐了一次又一次,我问覃皓然,为什么还不到家?他说,那是要得久,成都到乐阳有三百多公里。父亲拍拍他的脑袋,笑说:“皓然你莫跟妹妹乱讲,哪里来的三百公里,只有一百多公里!”他扯起脸皮,嘿嘿笑。我想,皓哥哥咋这个样子,说起谎来眼睛都不眨。
到乐阳的时候已经八点过了,父亲说,先送表哥回屋。
掀开门的是幺妈,抱着堂弟,看见我,很热情地招呼:皓然和今虞今天耍安逸了嘛。门打开,弟弟的腿耷拉下来,她把手臂往上耸了一下,我又闻到她身上浓烈的香水味。幺妈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女人,个子高高,细瘦,白得像剥开皮的甘蔗,发尾卷成一朵朵小花。父亲说,可惜骐跃太小了,不然跟到我们一起。幺妈说,没事,二天有的是机会。她瞥我一眼说,今虞还没见过骐跃,来抱一下嘛。我有点紧张,想拒绝,幺妈多半是看出来了,她笑眯眯的,把弟弟递到我的面前。
“不怕,幺妈盯到的,不得摔到弟弟。”她说,声音甜得像苹果。
我接过来,抱着弟弟,感觉像抱着一只奶猫,柔软、蓬松,干净得像是沾不上灰尘。我忽然想,等他长大了,能跑能跳的时候,我们再一起去成都。这时父亲说,行了。
“我把今虞送回去,慢点她妈又要冒火。”父亲说。
回到家,我开始分享我一整天的快乐。我对母亲说,动物园还有狮子!母亲说,动物园肯定有狮子的嘛。我说,大熊猫在啃竹子!母亲说,熊猫本来就啃竹子。我说,我们喂了鲤鱼!母亲说,喂鱼有啥子稀奇的。
她那么平静,完全没有被我的故事打动。我不服气,心想,我一定要说一个母亲预料不到的事情,我绞尽脑汁地想,想啊想,终于福至心灵。我说,我今天去爸爸屋头遇到幺妈了,她还让我抱骐跃弟弟耍。母亲在厨房洗碗,我站在外面,听见哐啷一声脆响,是碗碎的声音,太突然了,我吓了一跳。刚要进去,母亲已经从厨房出来了,她直勾勾地盯着我,问:“你抱了覃骐跃?”我说,啊,对啊。我还没反应过来。
“你说,你抱了覃骐跃?”母亲又问了一遍。
我想,是我声音太小,所以听不清楚吗?于是我大声说:“是啊,你没看到,弟弟好乖哦!”
一瞬间,我以为火烧到了脸上。
我捂住脸抬头,下意识地辨认母亲的表情,但没有成功,又是一掌甩在我脸上,我痛得哭了出来。母亲说:“我让你抱覃骐跃。”现在母亲不平静了,她像一头被触怒的牛,喘着粗气,五官拧成我认不出的形状。我喊痛,她说,我让你抱覃骐跃。我喊,好痛。她还是说,我让你抱覃骐跃。母亲好像忘记我是她的女儿,只顾发狠打我。我捂住脸,她打我的背,我捂住背,她打我的脸,她一直打啊打,好像一点也不累。我快要感觉不到疼痛的时候,她说:“你记清楚,你长大以后要是敢认覃家的人,我就是死了下九泉,都不会原谅你。”
从那一刻起,我每天暗暗地告诉自己,千万不能让母亲觉得我记挂父亲他们,那会挨打。此后,我习得了说谎的技能,并渐渐地谙熟于心,我习惯在每句话出口前揣摩母亲的脸色,尽最大的努力减少触怒母亲的机会,减少我挨打的可能。
二月末下了一场很大的雨,那之后,春天很快绿遍了田野。我坐在教室里靠窗的座位,往外看,每下一场小雨,油菜花就冒出一点点,再冒一点点,心情也随阳光充沛起来,我喜欢把一切点亮的春天。眼看三月的桃花,马上就要装满县城,母亲说:“你老汉想接你去覃家耍。”
但那天来接我的不是父亲,是幺妈。她出现在我家楼下,踩着高跟鞋,整个人还是往常那样,眼线浓黑,脸皮也搽得雪白。她说爸爸还在办事,先到幺妈屋头和哥哥弟弟耍会儿。于是我被接到幺妈家里,光线昏昏,墙壁惨白,已经有人在玩,他们转过头时我认出来了,一个是覃皓然,一个是覃骐跃,他们齐刷刷地看我,我竟然觉得紧张,想要解释,是爸爸让我过来的。
幺妈这时进屋,飘飘然的,像个仙女。她手伸过去摸覃骐跃的头,他站在地上,像个倭瓜,偶尔摇摆,但总体已经可以直立行走。幺妈说:“妈妈出去一会儿就回来,你跟到哥哥姐姐好生耍哈。”他咿咿呀呀,说不清楚,说话多是含混无意义的音节。幺妈笑了,睫毛晕成一把黑色的开扇,她说:“糖搁在抽屉头,你们要吃自己拿。”我一眨眼她就消失了。
覃皓然说:“吃糖不安逸。”我瘪瘪嘴,没说话,心想,吃糖才安逸。他戳了戳我说:“你想不想吃锅巴?”我一下振奋起来,锅巴,香脆脆的,我最喜欢吃了。母亲不准我吃零食,也不给我零花钱买,每次罗倩倩放学买锅巴,我想让她分我,说“下次大扫除我替你扫厕所”,她就慷慨地匀我两块。我忍不住,说想吃。于是覃皓然下楼买了一包锅巴,他说他只有五毛钱。每吃两把,他就给我一把,吃了一半,小倭瓜来了,跌跌撞撞,撞到我们跟前。他说,要,声音颤巍巍的。覃皓然嘴里嘎嘣嘎嘣响,浑然没有听见一样。小倭瓜急了,身体一颠一颠,像托在浪上,他又喊“要”,这次声音变大了点。我看向覃皓然,他气定神闲,满眼锅巴。我说不给吗?他说不给,小娃娃吃不得锅巴。我想也对,就不再吭声。
最后一点,覃皓然倒在掌心,抖了抖,龇着牙齿笑:“骐跃,最后一把,哥哥给你。”说完,他眼神飘着移过来,手一翻,全给了我。
当我意识到下游处的河床已经垒得很高,随时可能决堤的时候,已经晚了。覃骐跃的眼睛原本是一条细缝,当我一口咽下,它突然瞪圆,我只愣了一下,就见从里往外,不断地发着大水。
一个尖细的女人声音在喊:幺儿。
突然间,我像又回到了那个张开獠牙的冰箱面前。幺妈冲过来,把小倭瓜搂在臂里,哄他:“不哭啊,哪个把我们幺儿整哭了?”覃皓然第一个回神,他说:“幺弟没吃到锅巴,就哭。”幺妈说:“哪个把锅巴吃完的?”覃皓然没说话,说话的是覃骐跃。他指我,手臂随抽泣声抖了又抖。我后退一点,他往前一点,我再后退一点,他几乎要挣脱女人的怀抱了。他终于说了一个她字。
我想,怎么他说一个字,就有那么大的力量呢。
高高瘦瘦的女人飘到我的身前,扬起手,替我挡下了一片日光。我想,每次我和姐姐吵架,母亲都只骂我一个,如果在小姨那里,挨骂的那个就会变成姐姐,为什么在父亲这边就不是这样呢?
“幺妈。”覃皓然喊。
女人中断了动作。
她吊着细长的喉咙说:“以后不要到我屋头来。”
她说完这句我就明白了,哦,原来只对我不是这样。爷爷早就说过,父亲这边不是我的家,他们和我不是一家人。于是我就回我的家了,我对母亲说,我再也不去覃家,再也不见我爸了。可是母亲拒绝了我。她说,不去覃家可以,但必须见覃一鸣,因为,“你必须找他要钱。”
说话时,母亲用手捏住了遥控器,摁一下,音量区的红光就灭一格,一格又一格,直到整间屋子都没了声息。我忽然就理解了母亲曾经说过的那句话:有电视机的声音,屋子里就有人气。
现在,屋子里只有母亲的声音了。她说:“你老汉从离婚开始到现在,一分钱没有拿过,我一个人养不起你,要么,你就去找你老汉要钱,要么你就跟覃家过,不要跟我。”
从那天开始,我偶尔会疑心自己,突然变成一只动物园里的狮子——如果长出痛苦的心情和长出爪子一样。
上周,杨老师的语文课讲吃苦,她说,前几年刚工作的时候,工资低得简直莫法生活,现在的娃娃啥子苦都没吃过,哪里会有概念嘛。我埋着脑袋,坐在第一排,小声地说“六百”,杨老师听见了,低头看了看我,说:“向今虞还晓得嗦。”
我晓得,是因为母亲说过很多遍。心情好的时候,母亲会说她一个月只有六百块钱的工资,温言劝我,跟着父亲过日子算了,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废话,只说,滚。但我不想住在父亲家里,所以我去要钱。五百,或者一千,具体多少,母亲说了算。后来我也摸索出了规律:平常时候少要,逢年过节多要。所以母亲喜欢春节,还有我的生日,她说,过年和过生最适合要钱,“这阵不要,还有啥子办法能把你老汉的嘴巴撬开。”说这话的时候,母亲正在剪纸。从离婚后,母亲最爱做的事情就是剪纸,剪刀的嘴巴张开又闭上,咔嚓、咔嚓,把大大的白纸咬成一条一条碎片,像没有了黑键的钢琴。
我确实再也没有去过覃家了,要钱也不去,有时我约在外面,有时去父亲的工作单位。如果是上午要钱,时间充裕,我就走路过去,走一个小时能到。如果着急,我就坐两块钱的三轮车去,告诉师傅,到灯光球场、灯光球场,次数多了,梦中都会出现一片球场,阔大,挂满灯,场内是风和笑语人声,人们聚在一起说话,外面下雨,雨声潺潺,有人在水边洗脸,哗——哗——哗。
醒过来,灯光球场还是那样,没有灯、光或者绿草,只有一片焦黄的土地,日复一日裸露着空虚。我要先从球场旁边走过,右拐,从两壁中间穿过,左边有石头台阶,往上伸,就是最后一段路。我只要跟它一起上伸,一层一层地,伸向没有光的所在,就能走到父亲面前。父亲说,没钱。眼珠上翻,直通额头,眼白泛出令我害怕的冷漠。
那天出发之前,母亲再三和我强调,这是提前要我的学费,她说我马上要升乐阳中学,上了初中,开销就会很大。所以我不能害怕,我把腰杆挺得笔直,大声说:“我妈讲了,你有工资,还有津贴。”
“你晓得啥子叫津贴不?”父亲说。
我当然不晓得,我晓得他是在故意为难我,但我答不上来。于是声音低下去,我小声说,爸爸给点钱嘛,妈妈一个人养我很困难。父亲哈哈地笑起来,把眼角都笑出了一尾鱼,他说:“你妈困难,我们家更困难,我没得钱。”我盯着他,盯得眼睛都痛了,他还是说,没钱,没钱。
父亲的眼睛蒙着一层薄薄的水雾,像是刚下过一场雨,冷得人迹罕至,只有我浑身发烫,热烈得像陶壶里的开水,连声音也颤抖起来。来的路上,我在脑子里预演了回家后的场面,咚咚的敲门声后,脚步声越来越近,门一开,墙上的影子由窄窄的一道变成宽厚的一片,母亲就出现在我面前。她肯定会先问:钱呢?那时,我会把钞票一张不差地从我的口袋里塞进她的手里,且最好是高举,像得胜的将军一样呐喊:在这里!所以我说:“你不给,我没办法回去见我妈。”
父亲摇了摇头,说:“我给你,我也没办法回去见我屋头的人。”我不管,只说:“你必须给。”我翻来覆去地重复,父亲终于无奈了,他慢慢地说:“这样子嘛,给你两娘母五百块钱,我是仁至义尽了。”
我好半天不言语,把仁至义尽四个字在心里默念了几遍。然后我说,不行,一千,十张,一张都不能少。抬头的时候,我瞧见了书柜玻璃里的自己,竟然哭了,又红又胀的脸,像是被人狠狠打了一拳。我说:“你不晓得,我妈会打我的。”我用尽全力地说话,但父亲平静极了,他从我身边走过,像是从一条河边走过。
“你是她女儿,她能把你甩了还是咋样?”他说。
突然,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崩塌了,只有脖子梗着,像只急红眼的公鸡,我几乎是喊了出来:“你今天的一切都是我妈给的,我要你这么一点又算啥子!”
他跳起来,椅子往后猛倒,惊天动地的巨响中,他大吼:“你妈你妈,开口闭口都是你妈,你妈就是个疯子!”
我看着父亲狰狞扭曲的脸,想起小时候:我和父亲,还有覃皓然一起,我们在动物园来来回回地走,看熊猫、猴子、金丝雀,还有狮子,父亲的脖子上挂着黑沉沉的东西,砖头一样——现在我知道了,那是相机。他问我们,要不要拍照留念。我停在通体金色的小狮子面前,高声喊要。后来他把照片拿给我看:寸头,虎牙,笑眯了眼,我还戴着红领巾。心脏猛地一阵绞痛,仿佛有人伸过一只粗暴的手,毫不留情地把照片撕得粉碎。
我想,我们好像两条抢食的恶狗。
下篇
六月的小升初考试,我考了全县第十,乐阳中学免收我一年学费。母亲脸上露出稀罕的柔和,她说好啊,就要证明给覃家那些龟儿子看,女娃娃照样能干得很。但我只在乐阳中学读了一个学期,十二月底,母亲的工作调动,她说把党校的房子卖了,给我转学到简州中学。我改变不了她的决定,只能眼看她卖掉了那间住过十年的房子。那个午后,我和吴晓叶吃完最后一包锅巴,跟着母亲离开了乐阳。
车子从六十车队出发,大约两小时后,我们停在一个路口,面前的巷子挤在两栋衰老的矮楼中间,越往里,光线越暗。母亲说,房子是租的,只有三十平方米,以后我们就和爷爷婆婆一起住了,今虞要懂点事,晓不晓得。我说,晓得了。我跟在母亲身后,看到母亲的后背被胀鼓鼓的布袋盖住,身子歪斜,在木板搭成的楼梯上小心翼翼地行走,像一只走在钢丝上的山羊,我惊讶地发现,母亲几乎和我差不多瘦了。
爬到五楼,母亲停下来了,我跟着停下,大口喘气,一股令人作呕的酸臭味冲进我的口鼻,我说,啥子味道。母亲说,厕所。她示意我看旁边,一间水泥砌成的小屋,门板发黑,我稍微走近些,腥臭味一下沁进了脑子里。母亲说,我们一层楼共用这个厕所,记到,以后上完厕所,自己回屋舀了水出来冲。
说完,她掏出钥匙开门,我先进去,把背包放在水泥地上,一路拖到了窗户下面,窗户大喇喇地开着豁口,我坐在那里,风吹进窗框,后背上的汗很快被风干。等一道道数完墙壁上的裂缝,我说,我想进屋吹风扇。母亲说,没得,我们卧室没得插座。母亲进了右边的屋子,我立马跟着进屋,把灯打开,又关上。母亲说,早晚把电源弄烂,讲了无数百遍,这个习惯要改。我从小就喜欢连续按两下开关,灯光乍现又退散,像一道闪电划过的奇景。但这一次没有闪电划过,我抬起头,看见用钢丝悬在天花板上的灯泡,孤单单的一只,橙黄的微光一闪一闪,摇摇欲坠,带着点随时都会崩溃的危险,这下我不敢再戏弄它了。我说,晓得了。
“以后就在这高头晾衣服。”母亲说。
她说完我才发现,一根细细的麻绳穿过我脑袋上空,系在绿漆剥落的窗框上,母亲取出几个衣架,挂上去,一张床和木柜紧凑地挨在一起,除了这些,屋子里没有其他陈设。我走近看,木柜的门帘上不知道被谁用圆珠笔画了很多个“正”字,歪歪斜斜的,横过鸳鸯戏水的图案。
我问,有没得电热毯呐,晚上好冷哦。母亲说,没得,被子盖厚点晓不晓得。我说,晓得了。
晚上母亲做饭,我在左边屋子陪爷爷婆婆看电视,好小的一台电视,比我的脑袋大不了多少。爷爷说,条件嘛,比起以前是艰苦点,今虞克服一下哈。婆婆说,我们今虞最懂事了,晓得体谅妈妈的。我点点下巴,说,晓得了。
母亲给我和爷爷婆婆做了南瓜稀饭,一大把青菜下在里面,青菜和南瓜烂成一锅,摆在板凳上。我又想起母亲手臂上的颜色,于是我吃不下了。母亲说,这个屋子只通水电不通气,炒菜不方便,可能不咋好吃。爷爷说,嗨,莫得事。我说,以后我们都在板凳上吃饭了吗?母亲说,桌子摆不下,以后吃饭就用板凳。我低下头,她用筷子戳戳稀饭说,快吃,慢点饭冷了。我只好憋气,埋头苦吃。
吃完饭,爷爷婆婆说出去散步,他们叫我一起,一起“欣赏一下大简州”。但我拒绝了,我说我要洗头,没有跟去,溜进厕所,发现没有淋浴,只有一个长着塑料水龙头的洗手池,母亲说,以后热水都拿壶烧,洗头弓进盆子里洗,晓不晓得?我说,晓得了。母亲把水烧开,我兑了满满一盆温水,沉得几乎端不住,等我终于抬进厕所,发现一些小动物已经抢在我前面占据了它,几只红棕色的蟑螂蹲在墙壁低处,在我抬脚的瞬间飞奔出一段。我想了想,决定与它们和平共处,它们自由爬行的时候我打好泡沫,用红色的水瓢往头上浇,第一下没对准,偏了,水浇在右边肩膀,我换左手,再来一次,水浇在左边肩膀,反复几次,我浑身发抖,于是我举起水盆,整个倾倒过来,然后我从厕所出来了。我看见坐在客厅的母亲,佝偻着背,眼皮凹下去,眼球凸出来,仿佛我是个陌生人般直愣愣地盯我。她说,今虞,你过来。
我过去,站在她的面前,一段时间以来,母亲脸上的黄斑像蚂蚁一样,越爬越多。她说:“我知道你一直不愿意跟你老汉要钱,但是这回确实莫得办法。”我顿时有了不好的预感,没吭声。母亲不理我,继续往下说:“我没用,自己过苦日子就算了,连累你爷爷婆婆,辛苦一辈子,一把年纪了,还要来吃这种苦。”我这才发现,她没有像往常那样尖着嗓子说话,声音很低、很小,轻言细语,像是生怕吵醒了什么。我想说,不消卖关子,想说啥子就直说。忽然看见傍晚的红霞,一缕缕地在她眼睛里漫开。
我一直以为,母亲早就删除了哭泣这个能力,因为她是一个悍然无匹的斗士,从来只会高高地昂起脖颈,谁敢挑衅,就气势汹汹地拼命,一次不够就两次,直到对方认输,我反复想,她怎么会哭呢。上一次见母亲流泪是什么时候,我忘了,但肯定是很早很早以前,早到我现在面对她的眼泪,竟吓得呆若木鸡。“爷爷想让你转到简州中学读书,”母亲终于说话了,“校长说,要交六千块钱的择校费。”
我被这个数字吓到,我说,可是我考了全县第十。她说,考第一也没用,校长说交六千块钱,就一分钱都不能少。我明白母亲的意思了,我说:“你想让我,找我爸要钱是吗?”母亲没有马上回答,过了一会儿,才说:“我也不占他的便宜,你和他说,我们一人出一半。你是他女儿,这三千块钱本来就是他该给的。”
母亲说得字正腔圆,我也觉得很有道理,所以这次,我坚定地拨通了电话。父亲说,搞笑,你们母女两个除了要钱还会啥子。我以为可以控制自己,让自己像一个大人那样说话,但到后来,我又开始哭,我想起母亲眼里发烫的晚霞,边哭边说,我们家现在真的很困难。隔着电话,我看不见父亲的表情,但可以猜想,他一定笑了,声音好像很近,又像很远,忽大忽小地说:“你们是好日子过惯了,晓得啥子叫苦日子哦。”然后他迅速地挂断了电话。
我告诉母亲,她不再哭了,眨眼之间,她又变回了我熟悉的那个样子。母亲说:“有两件事我早就想做,怕你接受不了才一直没去。”我问,哪两件事?她说,第一件事,我们去改名字,以后今虞不姓覃,姓向。
第二天,我跟着母亲去派出所,一进屋就闻到空气中有种金属的味道。人很少,每个人都步履匆匆,我紧紧跟着母亲,走到穿蓝衣服的警察面前。母亲递上几张纸,又接过几张纸。她摸摸我的头说,几分钟就好。然后旋开笔盖,摁住纸,很认真地写字。中途,母亲偏头看了看我,她说:“以后你就是向今虞了。”母亲说得没错,从那天开始,往后遇见的所有人都叫我向今虞,“向今虞交作业了”,“向今虞起来回答问题”,于是覃今虞,连同和覃今虞有关的一切,就像从来没有在这个世界出现过。
第二件事情,母亲没说,后来我就忘记了。直到今天早上她叫我,我走到车站,才想起那天她说到一半的时候,那阵突如其来的沉默。
已经立秋,天气却丝毫不见凉意,日头还是很晒,沥青地软成一块席梦思床垫,我踩在上面,感觉随时都会踩空。车子开出去一会儿我就困了,睡得正香的时候,我被母亲叫醒,她说,到了。拉我下车。母亲走在前面,她的步子很大,两只宽阔的裤管卷进气流,像两只跃跃欲试的白鸽。我想起曾有一次,母亲也是这样,领着我闷头往前,大包小包,翻山越田,最后钻进一片树林。脚下是被人踩出的土路,母亲爬上又爬下,蹲下又站起,衣服被树枝挂破了都没发现,兜兜转转,她终于停在一个小土堆前,说,燃香。这是对我说的。我就打开半透明的红色塑料袋,掏出水果、零食、香和纸钱,看母亲把菜肉摆好,倒酒、点香、烧纸。然后她用空出来的手按住我的头顶,我像被人摁住了死穴。母亲说,看一眼,记清楚了,这是舅舅。我心想,这么小一点点,咋可能是舅舅,怕是找错了。但我抬头看她,眉间山峦起伏,眼角渗出红来,我说不出口,只是埋下头合掌,喊,舅舅,舅舅保佑我们。
母亲说,到了。我就停下。我的方向感从来不好,走哪儿都不认路,只管埋头跟着母亲,等她停下,我就停下。如果母亲不说这是法庭,我一定不会相信。好小的一间屋子,四四方方,像个密不透气的盒子,屋子里摆着木头长桌、几把椅子,零星坐了几个人,衣服就是平常穿的衣服,没有什么特别,角落还堆着发灰的布。
父亲出现的时候我不敢看他,我怕母亲生气,于是假装我在观察这间屋子,偷偷地打量父亲。他好像变了,阴影里站着的父亲和我记忆里的很不一样,矮了一截,头发也短了一截,脑袋上却多冒出一块头皮,油光光的,顶着半黑半白的发丝,走起路来,上身冲在前面,有种刻意的矫健。我看他一眼就低头,不敢多看,怕母亲发现。脚步声从我的右耳走向左耳,从远处走到近前,唰唰两下,停在我对面的长桌背后。一个留胡子的叔叔和他说话:“想不到在这儿碰到起。”父亲笑了笑,说:“哪个想得到喃,晚上一起吃个饭嘛。”胡子叔叔说:“可以是可以,你请客哦。”他们并成一排,身体摇摇晃晃,哈哈笑个不停,像在酒桌上碰见了彼此。
“郭老师,我请教你个事哈,法律是不是规定子女满了十八岁,父母就没得赡养的义务了哦?”父亲骤然拔高了音量。
我知道,父亲是专程讲给其他人的耳朵听的,尤其是我和母亲。我想,母亲又要发怒了。
果然,母亲一巴掌摔在桌子上,她站起来,隔着桌子开骂:“覃一鸣你又开始装模作样,你少在这儿给我指桑骂槐,我告诉你,不拿钱不可能!今虞没工作之前你想都不要想!你天天在外头装得文质彬彬的,心肠黑得很,我今天就把你女儿带到你面前,让她好生看下你都干些啥子事。”
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戴眼镜的阿姨已经开始说话了,哇啦哇啦,她说完,母亲开始说话,哇啦哇啦。我坐在母亲旁边,一动不动,只有眼珠子在转。然后是父亲,这时,那道熟悉的、实际上又很陌生的声音漫过来了。我立起两只耳朵,捕捉到一些数字:两千七百块钱,百分之二十五,第十三个月。
我屏住呼吸,用力地听,想要理解更多他们口中的词语,听了半天,听见知了的叫声。每次穿黑衣服的叔叔和阿姨们讲话,知了只听,不叫。一到母亲和父亲哇啦哇啦讲话的时候,它就跟着吱哇吱哇地怪叫,它们越叫越久,越叫越响,盖过了所有的声音,电扇转动的风声、脚步声、大人们说话的声音,还带动更远方的知了一起。整间屋子的上空好像有一个更大更无形的吹风机在旋转,到处荡着回响——母亲说,喊你说话。它就停了,好像它也晓得了,很识趣地停了下来。
满屋的人看向我。我的喉咙在烧,无数簇火焰从我的胸腔蹿上脸,手脚却冰冷。
我说,是,是这样的,我妈讲的都是事实。
母亲用手肘碰了碰我,我明白她的意思,这不够,她还想让我说出更多。戴眼镜的阿姨也问,证人,还有没得啥子要说的。我看见母亲放在桌子下的手臂颤了一下,分明是种极熟悉的征兆。我打了个激灵,说有,他不给钱,哦还有,也不管我,还有。
还有什么,我用力地想,来之前母亲是怎么教我的,我竟然全都忘记了。现在没有人说话,我破碎的声音荡来荡去,清晰得简直刺耳。母亲拿肩膀撞我,像是要撞开一扇坏死的门,我的脸更烫了。我突然想起那些要钱回家的夜晚,在路上,一束一束车灯扫过,白天乌黑平整的路面就像翻起波浪,一个大坑连着一个大坑,打桩一样地刻进我的脑子。那时我才觉得,原来白天的路和晚上的路差别那么大,白天让我得意洋洋的东西忽然被车灯扫成另外一种颜色,发灰、发青,是我站在父亲的办公桌前歇斯底里的样子,和每天在家中,面对母亲时虚张声势的样子。我好像头一次发现衣服里面的我只有一副瘦的胸骨,生出脚气的脚,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完全没有办法好好往前走。
知了又开始叫了。我看向父亲没有表情的脸,就在这时,看见跪在阳台的自己,正睁大了眼睛,看大年初二的烟花照亮整座县城,只除了我跪着的地方,我看见那张被撕碎的照片,模糊难辨,浸泡在鲜红的墨水当中,看见每一个无力却狂叫的自己,大火终于烧遍了全身。我被烫得跳起来,不可抑制地跑,向外,向有凉风涌来的方向跑。栏杆那么高,几乎高到我的胸口,我竟然轻轻一跃就翻过去了。
风吹到我的脸上,站在栏杆和天台边缘之间的空地,我想:站得越高,风吹越烈。忽然之间,那些在明在暗的记忆都在这时一个一个地浮出了水面。它们探出头来,我想起了那个火舌如龙的夜晚,母亲也是这样,将手中所有的纸钱,一点不剩地投进那个火盆,从此它永远冰冷,永远无人问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