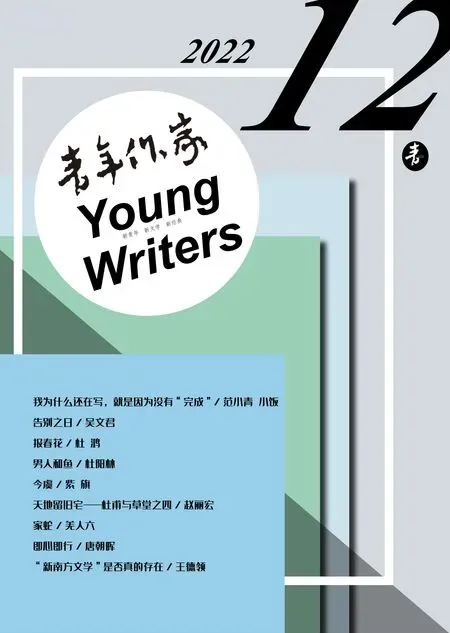归程
吴洋忠
凌晨五点半的样子,一串鞭炮响起,赵凯民晓得代云峰死了。他没动,瘫在床上闭着眼睛叹了一口气,打算继续睡。代明君会来敲门的,即使不来敲门,睡到天亮再去也不迟。这几天,实在太累了,这是不到一周里死的第五个人了,没准第六个也快了。想到这些,赵凯民呼吸沉重,窒息感进一步加重了浑身的疲惫,他叹息一声,翻身爬起来,抓过外套走出院子,往代明君家走去。
半路上,两个人撞在了一起。见代明君走来,赵凯民挥手让他回去。代明君没说话,随即转身往回走,赵凯民紧跟其后。这样的场景,每年他少说也会看到十几次,每当这时,逝者的亲人们,总像给抽去了真气,身子松散无力,走路歪歪斜斜。
下葬时间选定第二天上午十点一刻。从死到下葬,仅一天时间,似乎太仓促了,可时间一旦选定,便不得有半点含糊,风水先生选的好时间,关系到逝者入土为安,更关系到子孙后代前程远大,如若有半点闪失,小则破坏风水,大则犯煞伤人命。既是命运使然,对赵凯民选定的时间,代家人纷纷表示赞许。当然,这也不排除内心暗藏尽孝道又期望早点下葬早点结束这桩葬礼,大家都尽快轻松下来的心理。
在坟地里,赵凯民就打电话让田娃组织丧葬队。
代明君、赵春蓉两口子和代月娥、刘春山两口子以及旁亲近邻跟着赵凯民从坟地回到院子。代明君和刘春山抬来八仙桌,赵凯民铺开白纸写祭文,由赵月娥全程陪同。尽管是邻里乡亲,赵凯民对代明君一家也算了解,但是对代明君祖上三代的名字如何写,许多需要赵月娥提供和补充。
作为唯一一个儿子,跪礼迎客,代明君只得一个人担着。见有来客,代明君赶忙小跑上去,本已哀痛的表情上,再添一层悲恸和泪水,扑通一声跪倒在来客面前,磕头致谢!
院子里一边喇叭、铜锣、铜镲喧天响,一边锅灶忙碌,蒸笼重得像通天塔。
田娃刚坐下,一个抬匠便跨进院门来。田娃赶忙喊上,各扛一把锄头,顺着明天出殡线路,即把起灵到落棺之间那一段路细细巡视一遍。总体来说情况良好,小路两侧全是邻里各家的菜地,田间道路狭窄,即使踩坏谁家一点菜,也不会招来谩骂。这不足一千米路程,最困难的地方是出门左转抬过一个水坑后需要爬的第一个坡坎,二三十米长的坡,斜度至少在30°以上,最窄处不足一米宽,两根抬杠一头一尾分别两个人总共四个,哪怕四个人都使劲挤在棺材上,也很难通过,且下边那个水坑,一旦滑下去就完蛋了——田娃捡起一块石头扔进去,听石头落水的闷响,估计至少一两米深。把路挖宽一点,田娃说。田娃靠坡里侧挖,另一个靠外侧挖,不一会儿陡坡被挖宽敞了一些,两人狠劲连跳带蹦上下来回走了两三趟,确定路面稳固后,继续往前巡查。
坟地在半山坡的树林里。第一排第一座就是代云峰的坟,左边那一座是代云峰老婆的。代云峰两口子后边的是梅支山的,梅支山老婆的空坟在他左边,她的西边是代月娥两口子的空坟。这一片坟头,田娃几乎能背出所有名字,跟师傅学艺这几年,谁家有几头牛几个钱他不清楚,谁家什么时候死了人什么时候下的葬,他一清二楚。久而久之,每一片坟地、每一个坟头,他如数家珍。起初看着一家老小哭得死去活来,免不了跟着落几滴泪,时间长了,习惯了,连安慰的习惯也丧失了,看着一个二个哭娘喊爹眼泪鼻涕的表情,反倒从中瞅出许多乐趣。
我寡人一根儿,上没天,下没地,没人要我哭,也没有人哭我!他经常叹息。
不足半小时,全路程都修过一遍,田娃带着抬匠从坟地回来,又原路返回再巡查一遍,下山路过一家菜地,顺手扯一根红萝卜,在锄头上刮两下泥,塞进嘴里大口嚼。天将晚,其他抬匠陆续赶来聚到一张桌子上吃酒,八仙桌上七个人,空着一双筷子。
哪个没来?田娃问。
赵康民!一个抬匠说。
你好久来?田娃打电话问。
闪了!腰闪了。电话那头说。
他说腰闪了,田娃挂下电话说,他妈的,这下咋整?差一个人总不能让他自己走进去?
今天早晨把腰闪了一下,当时他说不严重的嘛?另一个抬匠说。
不严重就坚持一下,田娃又拿起电话,抬86岁的喜丧打牌光赢钱哦,这菜好吃,酒也好喝,快来,给你多留两口,嗯嗯呀呀只配趴在桌子下头啃骨头。电话那头说,实在不行了,腰肿硬了,躺在床上都翻不动!一听这话,田娃放下筷子跑了,大概十分钟,又跑回来,抓起筷子海吃。
咋个的?坐右上方的一个问。
硬是闪到了,有点严重,肿得像猪肚皮,我刨几口把他送医院去,再找个人顶替他,要不然明天咋个抬?你们也都问一下。
你喝醉了撒,除了我们八个,全乡哪里还有人!
往昔人丁兴旺,几乎各村一个丧葬队,现在年轻人全出去了,外地打工的,城里定居的,村里头的人越来越少,死人却越来越多,全乡只剩他们八个。这传统手艺难找继承人咯,赵凯民说,这个月生意尤其好,像他妈的鬼赶七月半,一个接一个,这是第五个。
一个人忍不住哈哈大笑说,下一个不是抬你就是抬我啰,都老球啰,赶快吃,吃一顿少一顿,多吃两口赚两口。说完拿起筷子在肘子里抄两下,嫌剩下的全是肥肉,转又在夹沙肉里挑一块塞进嘴里。赵凯民从隔壁桌过来,用筷子指着大声说话的说,你小声点儿,以为结婚啦?那人咧开嘴,对田娃挑个白眼,低下头继续吃。赵凯民伸筷子越过肩膀,夹起一块粉蒸肉。田娃赶忙站起来,把自己的酒杯递向赵凯民,说,师傅,喝酒!赵凯民没有理睬,又夹起一块夹沙肉,转身回到原桌坐下接着吃。
田娃顾不上喝酒,胡乱吃饱,匆匆跑了。
去康民家的路上,田娃给镇医院打电话,一个中年妇女接电话说可以。听声音像那个胖护士,那婆娘长相一般,却风骚得很,走路左摇一下屁股右摆一下屁股,除开抖音上扭胳膊甩腿儿的女人,田娃没有见过比她更风骚的了,想到这个,田娃心头充满欢喜,劲儿杠杠的。在康民老婆协助下,田娃把康民扶上摩托坐好,骑上去说,抱紧啰。一脚踩燃油门,不忘回头对康民老婆说,嫂子,吃醋不?你男人……紧紧地……抱着我!
抱紧点儿,给老子摔死了,我不得放过你!康民老婆说。
你婆娘说把你摔死了她不得放过我是啥子意思?田娃边开边回头戏谑康民。
摔死了我也不得放过你!康民说。
身后半山坡竹林里,锣鼓喧天,喇叭里那个男人哭得声嘶力竭。朦胧月光下,公路一会儿清晰一会儿模糊。摩托车钻进竹林下边那一片漆黑的时候,总有一种失重感,那种感觉就像摔下悬崖可是总落不到底,一直在深渊的漆黑里往下坠落时手脚胡乱抓腾的感觉,这种感觉多次出现在他梦里,这让田娃既恐慌又兴奋。
师傅,死的时候,是不是那种感觉?!田娃多次问赵凯民。
等老子死了给你说。赵凯民异常愤怒。
既然你说死了给我说,那就等你死了再去问你。田娃放肆地哈哈大笑。
田娃对师傅的回答很满意,如果死像梦里跌落悬崖那种感觉也不错,这种感觉一会儿在镇医院看到那个胖护士的时候,又会在心里重新燃起。想到这里,田娃心里悸了一下。
镇医院在正街西头一个岔巷里,三层小楼带一个院子,院子中间杵着一根旗杆。灯光下,旗杆若有若无,像一道影子。把康民扔给医生后,田娃顺着一楼找了一圈,胖护士没见人,便顺着楼梯爬上二楼,在二楼走道里走个来回,又顺着楼梯爬上三楼。三楼过道一片漆黑,只有尽头窗框缝里投进来一点微光。一股冷风缩成一个人影倏地扑向田娃,撞进他身体,穿过去分散开,化成一股冷雾漫在空中。田娃血管像被灌进了冰块,全身顿时冰凉。
眨眼间,田娃冲下楼梯,跳进院子,默念,鬼啊,阿弥陀佛!
那诡异的瞬间,越想越离奇,田娃怀疑自己那天晚上是否爬上过三楼,但那阵冰凉扑过来的风,每到夜里都在他身体里摇——耳朵在抖、牙齿在抖、手指冰凉、脚趾冰凉,几乎浑身上下都在抖动——那冲天灵盖冰凉的恐惧,紧密地包裹着他,大半年没有消散。
从医院逃出来,田娃骑上摩托在冷风中拼命驾驶,他冲进代家院子,差点撞翻围墙根下装冥币纸钱的背篼,右脚蹬在围墙上才刹住车,围墙明显晃动了几下,像在地震中。田娃翻身下车,将摩托往后一拽停好,趔趄走向酒桌。他颤抖的心,急需要一口酒。
找到没?赵凯民问。
找啥子?躲开师傅的眼睛,田娃才想起找人的事。
闯你妈个鬼,你不是找人去了啊?!赵凯民说。
我是闯了个鬼,师傅,魂都给我吓脱了!田娃说着抓起师傅一只手,摁到自己额头上,你摸一下,你有没有摸到鬼!
赵凯民差点给气晕过去,缩回手,呸地一泡口水吐在地上,坐回灵堂前的凳子上点着一根烟。今晚必须找到,还要赶过来熟悉路线,把规矩给他讲清楚,二十多年从来没有缺过人,这必须由田娃搞定,人生无常,哪天我突然死球!
隔壁乡有,一个抬匠说,明早也有人要抬。
现在找个人,突然这么麻烦了。一个抬匠说。
大口喝两口酒,吃过几筷子肉,田娃推上摩托打算再去一趟乡上。如果康民不严重,让医生简单捣鼓几下,把他接回来;如果不行,就去镇上把朱二老表接来,抬死人他没经验,年轻时候干石匠他总是抬头杠。这时正巧康民老婆打来电话问情况,田娃本想说没事,结果一慌张说:没死,你放心!
没死就是快要死了,或者差点儿死了没死成。
电话那头呼天抢地,田娃赶紧逃跑,消失在院门里投出去的光里。
在儿孙、外侄、女婿轮流值守下,小院平安度过一夜。天将破晓,道场结束,众人按分工分散开,各自忙碌,清点物品的清点物品,掌火的掌火,扫地的扫地,几个年轻人,以几个外姓女婿为主,轮流着睡上一会儿。
这一夜,田娃几乎没睡,先是在医院伺候康民,又去镇上找自家老表。朱二当即拒绝,怨恨道,相亲做媒成功一次还要干两次,干不满三次都要倒霉,抬死人这种夯活你就想起我了,给我滚远点。之后,田娃接连跑了好几个地方,把能想到的多少有些熟的几家敲了一遍,有两次被扫把赶了出来:没有见过半夜鬼敲门,只见三更敲门鬼,呸,晦气!
快天明时,田娃才找到人载着往回赶,不巧半路碰见康民老婆。那婆娘人傻心亮,挡住摩托,一只手拽着方向盘,另一只手发疯似的去抓田娃找来的那个人的脸,三下两下把那人抓跑了。她坐到摩托上,揪住田娃腰上的肥肉往死里拧,人没有死你就去找别人,给我走,要不今天跟你拼命。惹得起阎王,惹不起康民婆娘,大伙调侃道。康民像头吹胀肚皮刚杀出来的白生生刨光了毛的年猪,圆滚滚翘在病床上,曲一根手指在侧腰上一弹,他就能滚起来。看见婆娘跟着田娃走来,康民马上闭上眼睛直哼哼。那婆娘跳上去,对准康民脑壳狠狠两巴掌,不顾医生阻拦,拽过康民右手往肩膀上扛,死活要拖康民走。
田娃见势不可挡,摇摆着双手像只肥鹅追上去。他实在不晓得康民娶这个疯婆娘来干啥子,有时候想一想光棍儿有光棍儿的好处,打个麻将喝个酒没人管,调戏一下别家婆娘也没人管,开心自在。唯一是死了没有人披麻戴孝送终。他追上去,康民和他老婆已经坐在他摩托上,康民抱紧田娃,康民老婆抱紧康民,摇摇晃晃驶出去。
就这样,人,终于凑齐了。
小院安静下来不久,天光彻底打开了。随着各路亲朋赶来,小院重归喧闹。开棺时辰已到,赵月娥拿着礼信簿,一个接一个点人头。赵凯民站到屋檐下,对着院子里喊,开棺时辰已到,众孝子孝媳孝女孝女婿家孙外甥孙媳孙女婿外侄外侄女及各位亲人,想看代云峰老人家最后一眼的,请赶紧上前来。
众人按照预先排好的顺序,围着棺材瞻仰后,顺次站进送葬队列里。
棺材被盖上了。几个抬匠围过来,用绳索拴好棺材穿好抬杠,动作麻利,半蹲下去撅着屁股等鞭炮点响。
所有人都担心康民撑不起腰,他一往下蹲,他老婆立即跑过去,举着手时刻准备接杠。赵凯民把她拽开。鞭炮响,全体起。康民表情痛苦,不过精神抖擞,腰板打得笔直,看上去没啥大问题。康民走一步,他老婆跟一步。此时,赵凯民走在前边主持仪式,无可奈何,顾不上驱赶,田娃抬头杠也顾不上驱赶,只得由了她放肆。走过水池,第一个坡坎差点儿出了问题,倒不是康民,头杠一脚没踩稳,脚下泥土松动,摇晃几下没稳住,退了回来,后边几个被后坠力一推,一个一个顺次往后退,幸亏两个小伙子反应敏捷,冲上去顶住压尾的两个抬匠的背,另两个人在棺材下方一头一尾各塞进去一根条凳顶住棺材,这才稳住。
之后,一路朗日清风,除踩坏几颗莲花白和几笼韭菜,一切顺利。
一个孝子背着背篼走在最前边,每隔七八米点响一串鞭炮,躬身捡来一个土块压上一张黄纸插上一根香。赵凯民或停或起地呐喊着,同时向天空撒大米、黄豆和水,十多分钟时间,代云峰就给抬进了坟地。抬匠放下棺材,各自歇息。田娃抱起一大坨纸钱,跟着赵凯民和代明君,给坟地里的每一个埋了人的坟头烧上一沓纸钱,其后代明君、代明君姐夫、代明君女婿、赵家大哥等几个男人,受赵凯民的指示,纷纷冲向山坡,将各自手中二指宽的红布条找根树干系上,跑得越远系得越高,意味着生活越好,做生意的财源广进,搞事业的步步高升。
准备工作结束,赵凯民召集众孝子挤到坟前,下葬仪式正式开始。
每当这时,田娃总坐在坟旁仔细聆听赵凯民主持仪式,同时以与人打趣为乐。
除了是一根光棍之外,他堪比康民老婆的毒舌,也是人尽皆知。久而久之,知晓了解他的人,无论他说什么,权当笑话一乐,每当丧事,田娃倒成了开心果,跟哭丧的高音喇叭一唱一和,对于葬礼上喜悦气氛的制造变得必不可少,也正是这泼皮嬉闹的性格,导致这些年来赵凯民尝试将人工哭丧的绝活传授给他的愿望一直无法实现。
只要赵凯民头一歪、眼睛一闭、嘴一张,喊上一声爸爸呀……喊上一声妈妈呀……儿子呀……我不孝敬嗯嗯嗯……嗯嗯嗯……你呀呢……怎么舍得也……招呼也不打啊……你就出啊门啊远行……倏忽间,沙泥走尘,悲从地起:跪在灵堂前的人东倒西歪,哭得千姿百态,有的相互抱着哭,有的抱着棺材哭,有的扶着墙壁哭,有的忍住不出声只掉眼泪,有的在地上打滚,看热闹的人也被感动进悲情中来,纷纷上前,搀的搀、扶的扶。尤其那些倒在地上、躺在地上、歪在墙根里的七老八十的老人,在赵凯民主持的葬礼上,就曾经哭死过两个。下葬时,赵凯民再一声,爸爸呀……今天你竟狠心将我们弃……狠心跟我们永别离……哪怕也……儿啦啊呀……只有再世来谢……恩情……风起树鸣,恸天悲地——跪在坟头前的孝子们捶胸的捶胸、跺脚的跺脚,哭得一片狼藉,抱坟头的抱坟头,扑棺材的扑棺材,儿子抱着媳妇,姐姐抱着弟弟,就近的不分长幼,只要从泪里看见一个人影来,便冲上去抱在一块儿放声大哭。此外,独个儿哭的也不在少数,站着哭、跪着哭、抱着树干哭、斜靠在坟头上哭、使劲儿哭、放声哭,哭得越大声越动情越悲伤,悼念之情越浓烈,孝顺之后代的未来必然更加顺遂、安康、富有。
这些年,赵凯民曾无数次向田娃教授人工哭丧的绝活,见单人一对一的教授没有效果,有几次赵凯民闲来无事,索性请来邻里老头老太太在院子里晒太阳嗑瓜子喝茶,田娃则在正前堂屋台阶上学唱。
假情假意入不了戏,真情真意拼回忆。田娃绞尽脑汁想不出自己一生有什么值得哭啼,浑浑浊浊傻里吧唧度日,从来风平浪静,一年就像一日。
哦,有了,田娃说,师傅,要是你死了,我肯定哭得出来!
台下人,一片起哄,掌声四起。
这冷不丁冒出来的话,好似被阎王爷一爪子抓碎了心,赵凯民好几秒钟回不过神,骂道,日你仙人,老子死了,你也哭不出来,我死了你吃屎。
吃屎就吃屎,哪里有说死就死的。田娃说。
赵凯民转念一想,这也不失为一个办法,索性搬来两根长木凳,跑进堂屋间隔一米分别横在中央放下,满怀期待躺上去,扭了扭身体调整端正,一根板凳枕颈下,一根板凳搁膝后。他说,好了,现在我死了,看你哭不哭得出来!
哭得出来!田娃喊道。
面对这简陋却无比逼真的场景,田娃当真恸哭了一场,妈老汉死得早,从来想不起他们的模样,也从来不记得他们有什么好,更多是怨恨他们早早丢下自己没儿没女没婆娘,可是生我一场,我也该哭他们一场。
田娃当真哭了,哭得真真切切,上气不接下气,一把鼻涕一把泪,却把唱词忘了。作为一具尸体,赵凯民对这莽子恨铁不成钢,咬牙切齿,又不能立起来及时教训。台下无比兴奋,有人呐喊道,田娃,你在哭你老子还是哭你师傅?话音未落,赵凯民儿媳妇举着扫帚冲了进来,在田娃最动情最伤心最投入的时候,一扫帚砸在他脑壳上,好不容易找来的泪水一扫把给打散了,否则大家真以为赵凯民家死人了,如果真是那样,大家首先想到的一定是赵凯民死了。
田娃回头看到代云成牵着小孙子挡在代月娥面前,说,隔代亲往后边站,要是把你挤下去了,两铲铲一起埋了。这下言重了,代云成气得上眼翻下眼,撒开小孙子的手,伸拐杖向田娃剁过去。你龟儿子,活该当孤寡户!第一拐棍儿没打着,代云成追上去打第二下,小孙子一直拽着他衣袖,打田娃没打着却把孙子给抡进了土沟里,小家伙撅着屁股头窜在土沟里只顾哭。代月娥跳下去抱他起来,从地上捡来一粒哑炮逗他玩,同时骂田娃,你个没良心的,他得了癌症你还气他!一个抬匠起哄道,云成大爷死了田娃免费抬杠!田娃红着脸转身去打那个抬匠,躲避掉刚才的尴尬。这时,代云成又冲上去,一拐棍冲田娃头顶砸过去,看样子不给他打一下,这事儿没完。田娃把头一偏,却不躲身子,拐棍重重砸在他肩膀上,他说:
把我砸死了,怕你要把我埋了才行呢。
代云成气在头上,要继续打。代月娥拽住他,要他严肃一点。
坟头下,众孝子在赵凯民带领下正在举行仪式,或起立作揖或跪拜磕头,或围着火堆跑圈圈,一段念词一段仪式。
那边哭哭啼啼一片哀伤,这边嘻嘻哈哈一片打闹。
你一个寡人,打死丢了喂狗!代云成继续追打。
打不得,打死了没人抬你上山。田娃边逃边逗。
没人抬老子今天也要打死你!代云成喷着唾沫咆哮道。
田娃和代云成躲来追去好一阵子,老头体力不支,脸上瞬间煞白,停下来走到抬匠中间抱住田娃的抬杠直喘粗气。田娃站在一旁,看着代云成白纸一样的脸说,大爷,我错了!
打死你狗日的!我打不死你,我儿来打你。代云成说。
好好好,我先死,只要你开心,我让你打死!
你不能先死哦,一个抬匠说,你最年轻,按年纪也该我们几个先死。其他几个哈哈大笑。另一个说,我年纪最大,该我先死,抬了一辈子人,也让你们几个抬一下我,不晓得当爷爷被抬是啥子感觉!
抬个屁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康民,你会不会最先死,腰肿得那么严重,你要是死了,我们就散伙了!田娃说。
你把他咒死了,要你当我幺儿给我送终!康民老婆说。
那我喊你一声妈,妈,我要吃奶奶!田娃从来嘴不饶人,能舔上一嘴算一嘴!
嫂子的脸绯红,你是害羞了啊,还是火烤的啊?一个抬匠说。
康民没有说话,他老婆也没有说话。
代云成接过去说,田娃先死,背时娃儿咒我,我一定要他死了我才死!
哎呀呢,老先人,你儿孙满堂,你长命百岁,你死了不像我一个孤寡户,随便几个儿孙都把你抬进山埋了。代云成给气哽了,说不出话,直打嗝。人越老越怕死,一个抬匠安慰说,你看我们都想先死,后死的没人抬!
哪里那么复杂,死了扔进锅炉呼啦一声烧成一把灰,装进铁盒子随便找个地方扔了就是,那还落个轻松!火葬也有火葬的好处,哪里需要担心死了没有人抬啊!另一个说。
田娃说,好好好,等会儿你们先把钱交给我,明天起你们一个二个的挨个死,我想尽一切办法把你们抬进坟山里去,抬不进去拖也拖进去,绝不把你们烧成一把灰!我要是要死了,就自个儿把山门撬开,钻进去从里边关上。
坟前烈火熊熊,天堂屋燃得尤其旺盛,火苗嗞啦一下从一楼蹿到二楼烧进三楼,两层楼板和屋顶瞬间烧开一个大洞,孝子们把各种纸钱祭品通通蓬上去,代家女婿抓过法拉利递给代家女儿,示意她扔进去。代家女儿接过来一笑,嗖地把法拉利扔进天堂屋的堂屋里,法拉利呼啦一下引出一团火苗轰隆隆燃烧,代家女婿又递过去那匹汗血宝马,马儿块头比法拉利大许多,代家女儿只得小心地将它蓬在天堂屋上烧,之后女婿又递给她一个美女,忍俊不禁说,我看这哈你往哪里扔,一扔进去你奶奶从坟里钻出来甩手给你两巴掌。女儿横女婿一眼,捏在手里不知如何是好,烧一个纸人儿这么简单的事情,经这么一说竟有了毛骨悚然的味道,脊背上生出一股凉意,她顺手递给代明君,说:
爸爸,来,你给爷爷烧个美女。
代明君一脸茫然,接过去似乎明白了什么,笑呵呵走上去,把纸人的头伸进火焰里,火苗瞬间吞噬掉她的上半身,代明君把下半身也扔进火里,老汉,给你烧个丫鬟!他边说边蹲下去,把未烧完的纸片往火堆里推。
这时,赵凯民呐喊道,某年某日佳辰,赵云峰老大人葬礼已毕,急急如律令,带孩子的先行!只见一群人,解下裹在头上的孝帕,扔进火堆里,从冲天火光中争先恐后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