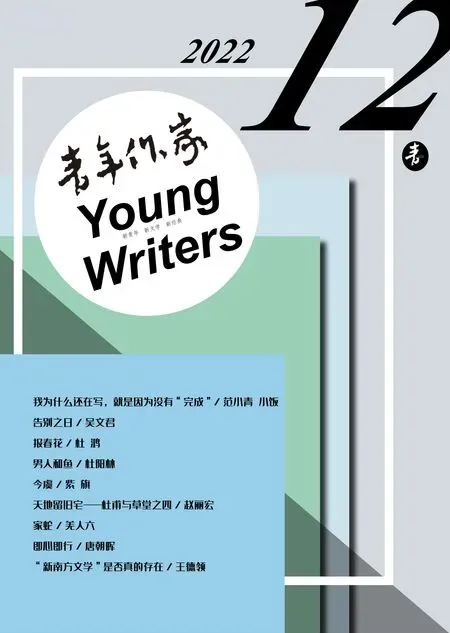水老虫
王才兴
王才兴
一
空气里漫腾着一撮一撮的雾霭,时隐时现,飘忽不定。冷寂的街市,空空荡荡。点心店、大饼油条店最先敞门,开始点火升炉,准备生意。三两个农妇手里挽只竹篮,脚踩露水来赶集市……寺北街渐渐露出它灰白的轮廓。
水老虫两手各提一桶柴油,迈开沉沉的步子,走在坚硬的青石路上。妻子杏芬紧随其后,一手牵着5 岁的男孩,一手提竹篮,竹篮里放着淘好的米、几把蔬菜,半碗腌菜。男孩睡意蒙眬,垂着眼皮,嘴巴不停嘟囔,他的鞋子不停去踩他娘的脚后跟。
水老虫,真名叫姚露,幼时长得尖头尖脑,眼小如豆,身体削瘦矮小。从小随爹娘生活在船上,风吹日晒,皮肤黧黑,蜷身躺船舱,活脱脱一只水老鼠。土话里,老鼠喊老虫,周边人就赐他外号——水老虫。
三人来到北边的河滩。水老虫将油桶放在石阶,一个蹲身起跳,登上岸边的木船。他从船舱抱起跳板,搁在船与石阶间。待妻子携男孩小心翼翼跨过跳板,他拎起油桶,一步一晃上船。
杏芬手脚伶俐,引燃行灶里的稻草、木爿,从河里舀水,与生米一起置入铁锅,然后偎守行灶旁,推柴进膛,煮着早粥。
水老虫解开船缆,快步来到船尾,左手紧握橹绳,右手来回推拉橹桨。欸乃欸乃,清冽的橹声在水中回响。船徐徐行进,橹桨犁出的浪花,向后渐行渐去。江南的四月,东风拂吹,夹杂丝丝凉意。两岸树枝绽出新芽,黝黑的泥地冒出一滩一滩嫩草,油汪水亮,惹人欢喜。春江水暖鸭先知,季节的轮换,对常年漂泊船上的水老虫家,这话实在最贴切不过。
前些天,几个农户通知水老虫,准备戽水,落谷下田。他翻阅皇历,今天是黄道吉日,诸事皆宜,百无禁忌。五点左右,他起床忙碌,点烛、焚香、化锡箔、烧元宝,然后虔诚跪拜,向祖宗叩三个响头,心里默默祈祷,保佑人船平安,戽水顺利。
第一站是黄泥夅村,紧挨的是冷水湾村、张村、姑里村。他决定以接洽时间为准,按照先来后到的次序戽水。经验告诉他,凡事都得按规矩办。去年戽水,没按时间顺序,以地域为序,结果招致预约在先的农户十分不满,他们与他争吵、闹情绪。年底收包水费时,被他们各家活生生赖掉二斗米。想起此事,他心头隐隐作痛。
他用缆绳固定好船体,将几节铁管拼接起来,旋紧螺丝。长长的管子从船头翘到沟渠。整条船像龙躯,铁管如高昂的龙头,出水口便是龙嘴。嘭嘭嘭,嘭嘭嘭,机器声响遍附近村庄。龙嘴吐出湍急的水花,哗啦哗啦,跃入水渠。
洋龙船来了,洋龙船来了!闻见响动,村里孩童高呼着,赶来凑热闹。寂寞的河岸,一时喧嘈起来。
见了人群,儿子姚亮神情变得兴奋、活跃、不安分。他几次想跳上岸,与村童玩耍,被杏芬紧紧拽住。水老虫似乎通情达理,抱起他,跳上岸,将儿子往人堆一搡,说:玩一会儿,就上船。
水老虫懂孩子的心。孩时,他随父母上船。父母常将他晾一旁,自顾自忙活。整日整日,抬头是天,俯首是水。仰望天空,棉花似的白云一撮撮、一堆堆,有的像雄鹰,有的像大象,有的像鸡鸭,有的像猪狗。远处飞来一群大雁,一会儿一字形排开,一会成了人字形,一会儿又成了丫字形,实在好看。云儿看腻了,便低头凝视水面。河水碧青,鱼儿自由自在游弋,一会喁喁,一会唼喋。不时,噼啪声起,鱼儿蹿出水面……村里孩子牵狗来河边耍。他跟母亲嚷嚷,船上也养一条。母亲说不行,家里不宜养狗。理由是水老虫属龙,龙狗相冲。他以为母亲小气,是为省米饭。他不懂啥叫相冲,只隐隐觉得,相冲就是犯大忌,不许违逆。初夏时,一只学飞的小麻雀跌落船头。他捧住小鸟,别提有多高兴。用饭粒喂,给水喝。可小鸟合紧嘴巴,不吃不喝。次日,小鸟头一歪,闭上眼,死了。饿死的。他心痛,伤心,淌着眼泪……那时他多想上岸,与村里孩子一同嬉戏。可爹娘不允。几年下来,他变得孤僻、木讷,不喜与人交往。
水老虫十七八岁时,爹娘四处为他物色姑娘。说了五六回,他都相不中,要么嫌鄙人家丑,要么说女孩长得瘦,干田活不中用。其实,他心里有人。戽水时,爹娘守船上。水老虫肩扛铁铲,在田间转悠。谁家包水的,他用铁铲掘开水口,水缓缓流入农田。田埂上发现鳝洞,他用泥土封住,避免漏水。那时,不少人家用龙骨水车,有的靠人力,有的借风力,有的凭畜力。那次在姑里村戽水。水老虫发现,一对母女脚踏水车,在车水灌田。女孩才十四五岁。春寒料峭时分,她穿着薄衣,裤管卷过膝盖,露出藕白似的小腿;绯红的小嘴紧咬着,一双橄榄大眼盯住远方,双脚一起一落,奋力踩着水车,呱嗒呱嗒,踩啊踩,不知疲倦。他心里估摸,单凭母女俩的四条腿,非得踩个几日几夜。一时起了恻隐之心,他挥铲挖开她家的水口,悄悄灌水进田。
田埂上,水老虫遇见女孩。日光里,她的脸汪汪一碧,贮满春色,柔声细气对他说:大哥,谢谢你,替我家放水浇地。说完,显出羞赧的神色,稚嫩的脸上洇出一团红晕,樱桃小嘴嚅动着,头垂得很低很低。可怜又可爱。后来他知道,女孩叫蔡杏芬,父亲死得早,母女俩相依为命。自见面的那刻起,他的心底涌出男人的神圣感、庄严感。他铁定心,要呵护、照顾眼前的女孩。以后遇到戽水灌田时,他总是悄悄地为她家铲开水口。机船抽水,河里的鱼蟹常被卷入岸上。他在沟渠口安上网兜。网到的鱼蟹,他瞒着爹娘,送一部分给杏芬家,与她家分享……
爹娘摸透了水老虫的心思,央人去杏芬家提亲。几年后,爹娘为他们举办了一场寺北街最热闹的婚礼。一般人家结婚,娶亲队伍走田埂,穿村庄;十多个小伙子拿着扁担麻绳,去新娘家挑运嫁妆。而水老虫娶亲,却是木船。船沿彩旗猎猎,船头船尾盛满五彩的棉被、大大小小的木桶、樟木箱。伴娘和小伙子端坐船舱,谈笑风生,风光无比。据说,杏芬家丰厚的嫁妆,都是水老虫让自己娘筹备的。他爱场面!
二
夜幕垂降。水老虫拉上儿子姚亮,钻进船舱,倒头便睡。夜里十一点刚过,他就从被窝中爬出。
他对杏芬说:你去睡吧,我来看守。
杏芬说:你不多睡一会儿?我还能坚持。
女人边说边进了船舱。
清寂的月光下,河面泛出微薄的银光;附近村庄、两岸植物都陷入茫茫的暮色中,朦朦胧胧,似有若无。眼前只有机器的轰鸣声、流水的哗哗声,不知疲倦地陪伴着他。
他点燃桅灯,提着铁铲,脚步轻快地跃上岸。借着桅灯黄晕的光线,一脚深一脚浅,行走在坑洼的田埂上。每晚他要去田间检查两次。哪块田水满了,他铲挖泥土,封住水口;哪块地流水不畅,他就将缺口掘得宽些,让水快速流进稻田。伫立田岸,静心谛听,流水汩汩,仿如淌入心田。他感到踏实,甚至得意。这些年,他似乎对水格外倾注感情,白花花的水,就是白花花的大米、白花花的银子!这是他的饭碗、他的营生、他生命的依赖。
水老虫爷爷辈时,家境贫寒落魄,一家人挤在一间破败的老屋,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父亲二十好几,还是光棍一条。当时寺北街最阔绰的要数薛家。薛家风光显赫,长子在朝廷为官,是鼎鼎有名的外交大臣。次子、三子在浙江、安徽跑运输,生意昌隆,富甲一方。薛家老妈孤身一人,在家无人照顾。水老虫奶奶和薛家是远房亲戚,她被雇到薛家,帮助照料老人,打理家务。那年春节,薛家长子一行浩浩荡荡,回寺北街省亲。眼见母亲在水老虫奶奶的悉心伺候下,饮食起居,样样称心。于是在几十间老屋中,挑选最西边的一间平屋,馈赠给水老虫奶奶。
水老虫爷爷如获至宝,满心欢喜地住进薛家赏赐的平屋。春日里,他搬来锄头铁耙、扫帚,拾掇院子,平整地面,准备栽种花草。清理土堆时,咣当、咣当,从泥堆滚出几个金属玩具。整土完毕,点数玩具,共有十几件。他端来清水,拭净玩具的泥屑。玩具露出金光,熠熠生辉。隔日,爷爷将一件藏入鞋底,悄悄去城里的金店探问。老板将玩具融化,测定,含金五成。老板告诉他,那是仿照皇帝銮驾缩小铸成的玩具。爷爷将銮驾一件一件送至城里的金店,换得大洋一千。意外之财,如天上掉下馅饼,爷爷惊喜惶恐,反复叮咛金店老板,此事不足向外人道,要他严守秘密。
穷得叮当响的父亲,正愁没钱娶老婆。爷爷花费部分大洋,给父亲添置家具、彩礼,置办婚宴,娶上老婆。剩余的钱,怎么处置?爷爷思虑再三,决定替水老虫父亲寻找一条生计。当时苏州吴江、浙江湖州一带,机船戽水十分流行,利润可观。爷爷到本地名闻的泗堡桥船厂,向老板订购了一台戽水机船,耗费大米两百石。
鞭炮声声,披红挂彩的机船抵达河滩时,整个寺北街沸腾了。围观的人像看“西洋镜”,挤得水泄不通。有人啧啧称赞,有人显出羡慕的眼神……坊间传说,当时街上算命的老瞎子听闻此事,感喟万千,心有戚戚道:财为命中注定。命里无财,捡到黄金就变铜!
多年后,老瞎子的话,一语成谶。
三
风调雨顺,日子静好。
拥有戽水机船,在寺北街是开天辟地第一回。机器戽水省力、省时,见效快,得到农户广泛认同。第一年,父亲的生意发展到近千亩。他仿照别处的收费标准,一个种植季节每亩收取包水费大米一斗,先交定钱二至三成,其余秋后算账。结算收钱时,却遭遇麻烦。几个刁蛮之人竟然赖账,不肯付钱。父亲向他们诉怨,诉说白天黑夜、风里雨里戽水的困苦、心酸。好说歹说,终因口说无凭,无法佐证,讨不回欠账。次年,父亲吸取教训。他与每个戽水户签订契约,并邀请地方绅董做证人,在契约上画押签字。遇到纷争,由绅董出面,斡旋解决……这些往事,是他从父亲口里获知的。父亲的创业经历,让年少纯粹的他感受到,生活的底色由黑白构成,人性善良的反面便是丑陋;也让他早早体悟到生活的沉重、人生的艰难。
父亲的生意愈益发达,戽水面积扩展到二千多亩。白花花的钞票进账,钱袋子一天天鼓胀。父亲野心勃勃,不断开疆拓域,扩大家业。他收购十多亩水田,雇佣多个长工、短工帮他种地;还在街上购置两间宅基地,就是现在的上河西街130 号。当时,寺北街流行矮脚楼。父亲摇船去吴江,运回整船上好的木料。木梁、木柱、木椽子都用桐油漆得锃亮。新屋从动土到竣工落成,耗时整整二年。楼屋门楣器宇轩昂,室内宽敞明亮,水老虫家俨然成为街上的大户人家。
生活滋润,日子富足。父亲除了喝酒、抽烟,没其他嗜好。喝的是农户自酿的土烧酒。小时候父亲诓水老虫,说,酒是酒酿做的,甘甜可口。父亲用竹筷蘸了酒滴,塞他嘴里,让他尝吃。一抿,又苦又辣,他舌头伸伸,直摇头。呵呵呵,父亲见状,纵情畅笑。自此,水老虫见了酒,便远远躲开……父亲的烟瘾特别重,抽的是水烟,嘴边好像从没掉过烟筒。蜡黄的烟丝装在铜制的烟筒里,用洋火卷纸点燃,噗噜噜、噗噜噜,父亲沉浸在腾云驾雾中,惬意、满足。一次,父亲将烟筒递给水老虫,让他品尝。他憋气紧吸,烟筒里的苦水一下子涌入喉咙,呛得他哇哇直吐……
水老虫结婚的第二年。盛夏午后,烈日炎炎,在张村戽水。父亲坐船尾,一边看机一边啜酒。从日照当头,一直喝到日头西坠。一瓮头白酒下肚,人已醺酣,脸呈酡红,吐话口齿不清,舌头囫囵……他仍不肯消歇。发现酒瓮见底,令水老虫上街添酒。父命如山,水老虫提着酒瓮,晃荡晃荡向街头走去。
回船的路上,轰隆,轰隆,传来两声巨响,随后闻见大呼小叫的哭喊声。抬眼望见,机船上空蹿起一股青烟。不好,出事了。他心一慌,腿脚酥软,一个趔趄,瓮头摔出老远。他跌跌撞撞,拔腿奔向戽水船。
眼前惨状令他窒息、呆愕:机船千疮百孔,遗骸漂浮水面,机器燃成一坨废铁。父亲被几个农户抱到岸上,像一具焦木,蜷躺在岸边。
事后他猜测,父亲酒多了,神志不清。不慎将火星溅落船板,引燃擦船的揩布,揩布上沾着油渍。火势快速蔓延,灼烤桶里的柴油,温度急剧升高,油桶爆炸……
四
飞来横祸,将鲜活的父亲夺走。父亲一向是水老虫心目中的主心骨,人生的精神大山。失去父亲如同丢了魂魄,他的身体像死鱼一样漂浮起来,独自怔怔窝在椅子上,空洞的眼眶黯淡无光,不时唉声叹气。他进食很少,身子一天天消瘦。夜晚经常噩梦连连。惊醒时分,背脊冒着冷汗。他的人生陷入茫茫的沼泽……
半年之后,他仍没步出荫翳,时光在迷迷沌沌中延伸。杏芬默默陪伴他。她知道他的心思,他心里盛满苦水。
她心平气和,开导他说:姚露,父亲已去,生命无法挽回,可生活还得延续。他要是在世,肯定不愿见到你现在的模样。咱们还是从长计议,找点活干,日后东山再起。
他蔫蔫朝她一瞥,淡淡地答道:做啥呢?
杏芬将酝酿长久的念头告诉他:你不谙农活,但熟悉戽水,对戽水有感情。不如重操旧业吧?!
水老虫眼里倏地闪出一簇火光,沉吟一会儿,说:戽水,好是好。只是购船支不出这么多现钱。
妻子沉着淡定,将拿定的主意和盘托出:与船厂商量,先交部分订金,余款用家里的地契房契作抵押,以后逐年偿还。
水老虫听闻,心犹迟疑,觉得将所有家产抵押有极大风险。但转而想,做啥没风险,还不如趁此搏一回……
往昔的日子死水一潭。妻子劝慰的话,让他重获新生。周边世界对于他变得陌生而新奇,沉寂半年后的他又听见了体内血液重新流动的声音,他真的听到潴留的血突然汩汩流动起来……
夫妻俩去了二十里外的泗堡桥船厂。船厂老板已听闻水老虫家的厄难,他清楚他们的家底,便一口应诺他们的请求。水老虫对戽水机船提出新要求:在船上添置碾米、磨粉、榨油的设备。在戽水的空当,他准备扩展生意,摇船去村子,接做碾米、磨粉、榨油的生意。初夏时,新船运回。择日便开机运营,生意一天比一天忙碌。水老虫变得充盈、踏实,精气神大振。
那年,遇到虫害,农田稻禾大半枯萎。秋收时,大多人家收成减半,严重的甚至颗粒无收。有几家农户交不出水费,上门与水老虫商量,包水费能否赊欠到明年。望着农户绝望的神情,他慷慨答应说:免掉你们今年的包水费。但你们得给我守住秘密,不要外传。否则,每家都不交包水费,我可承受不了!
农户纷纷作揖,感激地说:谢谢,谢谢你的大恩大德!待以后我们富裕了,本金利息一起偿还。
次年春季,青黄不接时,不少农户已经断炊。走投无路的农户纷纷上门,向水老虫家赊粮。他二话不说,吩咐手下人,开仓借粮。那年,好多地方都饿死人,寺北街附近饥饿的农民,在水老虫的帮助下,都撑过了难关。
儿子姚亮到了读书的年纪。水老虫将儿子送到私塾老师家,教他识字念书。平时水老虫常与乡里绅董比照,后悔自己年少时没念书,不如他们知识渊博,成不了大事。他期望儿子日后能知书达理,出人头地。私塾老师是个老秀才,他知道水老虫素有善心,崇尚礼义,便提醒他,说:祠堂东边有一块荒地,你可以买下来,造三间平屋,办一所学堂,我来当先生,让寺北街的小孩都能上学。
水老虫听人讲,远近乡贤有了钱财都乐于助人、乐为善事,有的还开办义庄,帮助病寡孤独之人,义助穷苦孩子读书成才。自从范仲淹在苏州创办范氏义庄后,数百年间,江南大地创办义庄的热潮不减,各地乡绅礼贤纷纷仿效,办起自己的义庄。像本地的荡口华氏义庄、石塘湾的孟氏义庄、鸿声七坊桥的怀海义庄等。水老虫曾暗暗发誓,待自己发达后,要效仿他们,创办义庄,名字就叫姚氏义庄。而今,秀才的一席话,一下点亮了他的心灯。
两年后,一幢崭新的新屋,在祠堂边落成。每日清晨,姚氏义庄里传出了朗朗的读书声。
五
姚氏义庄建成一年,日本人侵占中国。一时遍地狼烟,百姓生灵涂炭,哀鸿遍野……
那日,杏芬忧心忡忡,对水老虫说:街上传遍了,东洋人要进驻寺北街。
水老虫蹙眉锁脸,低沉地答道:嗯,听说了,狗日的矮鬼子一来,恐怕生意做不成了。
他们都说,鬼子动不动就抢东西、杀人、放火、糟蹋妇女。
你没事多待船上,别上岸,少抛头露面。
嗯,晓得。
没几天,日本兵一个六人小分队,来到了寺北街,为首的叫木村。他们在乡保长的指引下,去街上转悠,寻找住所。当一行人来到姚氏义庄时,木村一眼相中了簇新的义庄,翘出拇指说:这个地方,好。大大的好。他命令乡保长通知主人水老虫,明天起小孩不许进学堂上课,把屋子让出来,供他们驻军。
水老虫接到通知,无奈地望着乡保长。刚建成的义庄要被霸占,小孩将失学,他心里难过、疼痛。他想说不,但不敢,只得忍气吞声。六个日本兵住进了姚氏义庄。
那天上午,乡保长唤来几个壮劳力,搬来木柱、木板、绳子等,在祠堂门前空地搭建戏台。中午时分,乡保长提着铜锣游走街头,边敲锣边高声叫喊:各位乡民,听好啦,木村小队长有令,今晚六点在祠堂前看戏,锡剧《珍珠塔》!各家老少都得参加,不得缺席。铛、铛、铛……
秋风频频,一阵紧过一阵。祠堂前的梧桐叶子开始脱落,不时发出簌簌的声响。晚饭后,戏台四周燃起数盏桅灯。灯光忽明忽暗,台下黑压压寂静一片。男女老幼忐忑不安、心神不宁地枯坐着,似乎失去了先前看戏时的激动与兴奋……晚上六点钟,五个士兵荷枪实弹站立台前,眼睛不时窥视全场。小队长木村昂首挺胸,迈着赳赳步伐,走上戏台中央。他面含微笑,扯着嗓子向台下喊话。他喊一句,翻译叫嚷一句。看戏后的第三天,乡保长带着木村和一个士兵以及翻译,来到水边的戽水机船上。
杏芬见后,心里咯噔一声,惊慌万分,手足无措站立船尾。水老虫慌里慌张,颤颤悠悠到船头迎接。
木村翘出拇指,夸赞水老虫说:你的良民,大大的良民!然后对他说:皇军急需运输工具,要征用你的机船为大日本帝国效力,皇军付你工钱。你的,好好考虑考虑,三天后听你答复。
木村下完命令,吊起三角眼,朝船尾的杏芬投去一瞥。他好像发现了什么,有滋有味盯看良久,脸上不时露出一丝猥琐的奸笑。
水老虫一时思维混乱,嗯嗯啊啊应答着。
鬼子走后,水老虫铁青着脸,一言不发。他和杏芬隐隐觉得,此事福少祸多。两人栖栖惶惶,商量对策。答应吧,戽水生意将荒废,对客户无法交代。不应呢,日本人肯定不会轻易放过,全家恐将遭遇不测。这群畜生!刚霸占学堂,现在又要霸占他的机船。他越想越觉得憋屈、窝囊……实在没法,拖到第三天,水老虫被迫答应了木村的要求。
木村交付的第一道任务,去城东的陈义茂木行运回木材。那天,鬼子派上两个士兵登船看押,雇佣一位村民帮衬水老虫摇船。天光微曦,机船出发;回到寺北街,已是日头西下。木材被送往寺北街的小南山。据说,鬼子要在小南山建立军事基地。
第二道任务,去缥缈山运载水泥。缥缈山在远处的太湖边,路途往返需两天时间。天蒙蒙亮时,水老虫卷了铺盖,准备出门。妻子扯住他衣角,送他至门口,满含忧郁,吩咐他:路上注意安全。行事多留个心眼。
水老虫别过头,深情款款望着妻子,说:你放心,我会小心的。他转而叮嘱妻子:你没事别出门,待在家里。晚上早点关门歇息,闩牢门闩。
机船在运河中徐徐行走。到底是秋晨的河水,有一种凝稠的、金属的黑,在无声地流淌。两岸村庄、树木、植物渐渐向船后隐去。吱呀吱呀,橹桨声声。水老虫摇橹谛听,往昔悦耳的橹声,今日却显得特别陌生、刺耳。他心悸,不踏实。一会儿惦记着自己的戽水生意,一会儿又牵挂起妻子儿子 ……
六
次日傍晚,水老虫踏着夜幕,匆匆回到寺北街。
进入院子,感到阴冰冷气的。杏芬肩倚着门,怔怔站立着,两眼呆滞。在黄昏幽暗的光线下,她的脸折射出凄惨的白光。一见丈夫,她泪水涟涟,呜呜抽泣。
水老虫心里猛地哆嗦,一阵惊怵,赶紧发问:出啥事了?
哇的一声,妻子爆发出锦帛撕裂般的哭声……
昨日子夜时分,木村趁着酣醺,率两个士兵,夜色中翻墙潜入水老虫的宅子。他闯进杏芬的房间,两个士兵把守房门。失去人性的他兽性大发,不顾杏芬死命反抗,将她奸污、蹂躏。
夫妻俩抱拥一起,呜呜哭泣。学堂、机船被霸占,现在老婆又被欺辱,水老虫悲恸欲绝,伤心彻骨。万念俱灰的他,想到了死……一股怒火从心底蹿出,仇恨从每个细胞中滋生,牙齿咬得咯咯直响,牙龈在淌血……
他走在街上,恍恍惚惚,好像后背有无数双眼睛在盯视他,灼灼的眼光让他抬不起头,使他无地自容。他分明感到,体内多出了一个器官——可恶的木村似乎附着他,植入了他的肌体,拂之不去,形影不离。还不时跳将出来,伸出锋利的爪子朝他狂抓,抓得鲜血淋漓;张开血盆大口,死死封住他的喉咙,他几近窒息,透不过气。夜晚,他噩梦连连。梦里,魑魅魍魉包抄他、追逐他、吞噬他……
那天,他悄悄安排杏芬带了儿子,携上家里所有银两细软,投奔浙江临安山坳里的姑姑家……
水老虫被派去上海郊区,运载枪支、弹药。
日照当头,晴空朗朗。机船回程经过阳澄湖。湖水辽阔,渺渺茫茫;微风徐徐,水波荡漾。两个鬼子一会儿监视湖面,一会监看摇船的水老虫和村民。
水老虫撂下手里的橹桨,让村民独自摇橹。他从容走进船舱,端出备好的鱼肉菜肴、一瓮白酒,笑嘻嘻对两个日本兵说:太君,你的,米西米西的干活。
鬼子兵心生戒备,将信将疑,要水老虫先尝吃。
水老虫大口咀嚼着鱼肉,将满碗白酒一饮而尽。鬼子露齿大笑,称赞说:你的良心大大的好。
两个鬼子蹲身开吃,狼吞虎咽。水老虫继续摇橹前行。
半个时辰后,酒瓮已空。鬼子喝得面红耳赤,醉眼迷离。其中一个摇摇晃晃走到船沿,拉开裤裆,向湖里撒尿。另一个见了,仿佛被传染,也立身去撒尿。两人叽里呱啦,比试谁射得远、射得高。
说时迟那时快,水老虫迅捷将油桶内的柴油倾入船板,用火柴引燃纸片,扔到木板上。嗤嗤嗤,火苗如一条火龙从船尾飞速窜向船头,熊熊大火迅速覆盖了机船。鬼子兵惊醒,慌忙端起身边的长枪瞄向水老虫。还没来得及开枪,轰隆,轰隆隆,几声巨响,鬼子的弹药爆炸了,人、船全被炸成碎片,葬于湖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