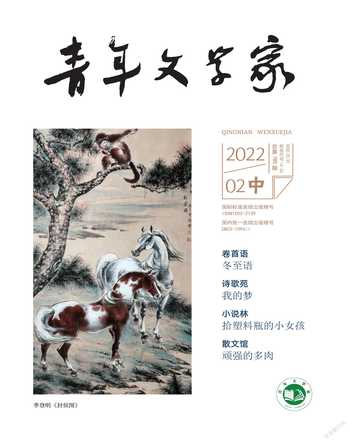香橼
赵宏建

秋风萧瑟,风过处黄叶漫天飞舞,便觉一股凄凉袭上心头。真希望仰望天空写意画般的枝头还能寻觅到几枚果子,或柿,或橘子,或白果,可白果早跌进绵密厚实的落叶堆里了,踩一地金蝶,沙沙声里,忽听得“啪”的一声响,白果被踩碎,像听到一声叹息,又恐是呓语。跺跺脚,鞋底上沾一股臭味,有些煞风景。
我家屋前有一棵香橼树,屋后还有一棵香橼树。屋前香橼树旁还有一棵桂花树,桂花树有些年头了,比我三十岁的女儿还大,独杆,树冠如伞,如膀大腰粗、孔武有力的汉子。香橼树经冬不凋谢,浓绿枝叶间挂着一枚枚果实,恰如少妇浑圆的乳房,优美的形态真叫养眼,令人浮想联翩,可我以为只能远观而不可亵近。
我家香橼树是母亲在世时种的,我起先以为是棵自然长出的橘子,然而看到它有刺,母亲说是她种的。香橼树长得太快了,第二年,母亲便将它们分开,移植两处,屋前一处,屋后一处。它们仿佛比赛似的往上长,很快就高过了我的头顶。
春天,香橼树开花了,细小的、洁白的,在绿色的树叶间,星星般点缀在绿叶丛中。有蜜蜂飞来访花,也有一对黑色的蝴蝶翩翩而至。母亲对我说:“今年要结香橼了,你要好好地照看它呀!”
然而,就在香橼树开花的季节,母亲故去了。秋天,香橼树果然结果了,两棵树都是硕果累累,满院里都清香四溢。香橼先是墨绿的,而后成长为淡黄的,像橘子一样,我摘了几只最大的香橼供在母亲的像前。
汪曾祺在《鉴赏家》中说叶三“还卖佛手、香橼。人家买去,配架装盘,书斋清供,闻香观赏”。大观园中探春的秋爽斋里也有,“左边紫檀架上放着一个大观窑的大盘,盘内盛着数十个娇黄玲珑大佛手”。我把香橼陈立在茶几上,让它与妻子网购的百合、玫瑰、满天星为伍,自由自在,各香各的。妻子则喜欢放于条桌清供,再燃上一枚小小的水沉香,青烟袅袅,云山雾绕。
前些日子,相约去苏州女儿家看望外孙,便早早摘了数枚香橼,用井水泡着,然后轻轻用抹布拭擦,晾干。怀揣一兜香橼上车,摇摇晃晃中,酣然入睡,一帘幽梦都帶着甜香。到了苏州,可小外孙一点不解风情,拿着香橼在客厅当皮球踢,还发出一阵阵尖叫。第二天游拙政园,遍寻不见香橼,心中有点落寞。我记得有一首写香橼的诗:“你栖居在江南水乡/被时间染色的白墙黑瓦之间/像江南的水洗浴过的江南女子/古典 美丽 忧伤/高垣冷峻 竹篱枯寂/围成一个孤独的角落/你住在这个角落里吞吐日月/温婉 娴静 坚强。”我越发感觉到,诗歌是理想的,现实是真实的。
一树的香橼,竟成了我的牵挂。从苏州回来,午夜醒来,黑暗中一片安宁。似听得到院里“啪”的一声,一枚香橼从枝头坠落下,打两个滚儿,歇在菜地的青葱上,或者是躺在辛辣的芫荽上,怕是偷偷藏着冬眠的蝴蝶也会吓一惊吧!
今天看了天气预报,初雪将至。真不愿香橼再落果了,想象中,雪花纷飞,绿叶点缀明黄,依稀一抹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