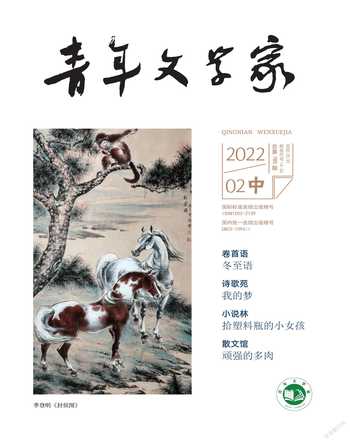《文心雕龙·知音》中的批评系统及缺失
王艺桥
作为一部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地位显著,《知音》篇中所提出的“知音”鉴赏论也一直被沿用,刘勰所提出的“六观”说,也提醒人们在鉴赏的过程中,注重性情的同时也要关注外在形式,但《知音》篇中也存在“音”可知与否、过分要求客观等问题。
一、知音系统
《知音》篇是《文心雕龙》中的最后五篇批评论之一,主要表达刘勰对于文章鉴赏问题的看法,包括“知音其难”的问题以及具体鉴赏文学作品的方法。清人纪昀认为“难字一篇之骨”,刘勰也确实感叹“音实难知,知实难逢”,但难只是《知音》篇前半部分提出的问题,这一篇的后半部分不但分析了“知音”这一问题的内在原理,他所认为的达到“知音”的方法,向人们展示了如何做到“知音”。《知音》一篇的根本目的是教会人们如何成为一个“知音君子”,《文心雕龙》最后的五篇批评论都是围绕对于文学的接受和鉴赏展开的,共同的落脚点也都是要培养人们成为“知音君子”。
“知音”是刘勰的一种重要批评模式,在这种批评模式中,“知音君子”就是其中的理想型人物,也是刘勰主张的批评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这种批评的理念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不断出现发展,孟子主张“知人论世”,提倡把目光投向创作的起点,从作家的人生经历和遭遇出发,从根本上把握作者创作的内涵。知音批评可以通过了解作者的心路历程,通过文章去推测作者内心真正想要表达的情感,这就是知音批评在批评系统中的优势。
想要“知音”首先要观察作品的外在,刘勰强调要先弄清楚文章的文体风格,即“才性异区,文体繁诡”,文章体裁不一,且风格多变,想要对一篇文章“知音”就要先搞清这个问題。刘勰认为《离骚》之奇在于它不同于《诗经》之正的文体风格,中国古代的文学风骚同祖,“奇”和“正”就是文学风格的两大源头。刘勰关于通变的看法,即当代人写文章,“通”就是强调继承,优良的写作传统不可背弃;“变”是强调今人的创新。刘勰认为在行文中必须“变”的地方是“文辞气力”,“文辞气力”是指文章具体的辞采和风格,这些都是因人、因时、因作而异的,没有具体的内在规律可言,那么在创作过程中对于语言的修辞和运用就值得注意了,而且刘勰提出通变的观点也是为了改变当时文学创作的弊病,这个出发点是难能可贵的。
二、知音系统中的缺失
(一)知音其难的原因
刘勰对于“知音其难”的原因概括为不够充分,“知音其难”的原因除去刘勰所提及的三个情况外,还有其他原因,如作品内容的抽象,使读者陷入迷茫,无法理解,陷入误区而不自知;再如读者的偏好或能力不足,使对文章的鉴赏和评论变得困难,无法做出较为公正的裁断。刘勰对于这些原因的探寻和总结很精辟,但不够全面和完备,许多其他“知音其难”的原因刘勰都未能论及。古代文人文学素养普遍较高,作品水平以及表现出的文化心理和水平也都未必会被当时的文人所理解,这种先进而超前的思维也可能是“知音其难”的原因之一。当中国古代文人在作品中表现出超越同时代人的认知和审美水平时,他们的感情得到了充分的宣泄,个性得到了充分的张扬,但未必会得到同时期文人的理解,甚至还会招致世俗异样的目光,就像《古诗十九首》中“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中表现出来的寻求认同却不得的感伤和忧患。
司马迁遭遇坎坷后发愤著书,不避黄老,直抒胸臆,但这样的做法却遭到了班彪、班固父子二人的斥责。“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这种包含着激烈情绪的措辞反而印证了司马迁所表现出来的思想高度远超过当时与他同时代的人,司马迁也渴望有知音来欣赏和肯定他的付出和创作。在《报任安书》中写“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这就是思想巨人不被时代所肯定的体现。陶渊明在中国的山水田园诗中有着独一无二的地位,但是他的诗在当时并未受到肯定,在钟嵘的《诗品》中也只位列中品。早年的陶渊明还想要在官场中有一番作为,但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性格,注定他要在仕途上无大建树,无法被人认同,不得不寄情于山水田园,他在自己的诗歌中也展现了对知音的期盼。精神上的超前是一个民族文化创新和进步的标志之一,他的超前性必然会带来这样的后果,即作者的思维无法被同时代的人所理解,表达与理解之间产生隔膜的现象也在所难免,这种原因也会导致“知音其难”的现象,这些原因是刘勰所忽略的。
(二)“音”可知与否
想要真正的“知音”,单注重内或外的某一方面是不可行的,要做到内外兼修,又要观察到文章的形式、文辞特点,又要能够体会文章作品中深层的情感,这样才能真正地鉴赏一篇文学作品,做到“知音”。刘勰所说的“情”是相对于文章外在形式而言,与之相对的内容,但“六观”的内容和要求是无法真正深入地理解文章所表达的深情的。刘勰所追求的文章,是一种内容与形式的平衡,受到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在探寻文章情志的时候总是融入儒家教义的东西,总是将文章的核心回到圣贤之说上去,他在研究文章内涵乃至文字含义的时候也遵照儒家的积极态度,儒家的一些文学观点也体现在《文心雕龙》中。儒家认为文章的作者可以通过语言完整准确地将自己的思想完全表达出来,同样读者也可以通过阅读文字来感受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这种观念有其深刻合理的一面,但这个观点的普适性真的能够做到覆盖吗?也未必见得。如庄子就认为有些不可知的东西是无法用文字来表达的,就像古人留下来的经典不过是末流,真正的“道”早就随着先人的消失而消逝了,这也就是道家的“言不尽意”,刘勰自己虽然也在《神思》篇中有过这样的困惑,但他并没有对这个问题做出自己的理解和解答。
在创作的过程中,作者的思维是属于个人的,在落实到文字之前并不会被外人所知,但用于表达这种思维所使用的语言和文字却不独属于某个人,是整个社会所通用的。这种一般性和特殊性之间有一些部分是无法做到统一的,也就是说语言和文字在某些时候并不是全能的,可能无法表达出作者内心深处真正想要表达的情感。既然无法借助文字来进行表达,那么作为读者也就无法单纯从文字中获得作者的体悟。除此之外,中国的传统创作观点讲究“含蓄”,讲究“言外之意,味外之旨”,这些根植于文人思想中的创作观念不仅在不经意间给读者的阅读带来了困难,也大大加深了“音”不可知的方面。读者与作者之间进行情感交流的桥梁就是文字和语言,而作为表达工具的语言和文字本身也有他不确定的两面性,一方面文字是否能表达出作者想要表达的意义,另一方面读者从文字中体会到的东西是否又与作者想要表达的东西一致,这两点外还有语言文字在传播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纰漏和问题,这都会影响到作者的情感表达和读者的情感接受。因此刘勰在讨论“知音”问题时,并没有关注“音”到底是不是完全可知的,就在默认“音”可知的情况下形成了“知音”理论,并留下了一个鉴赏的天花板,这就是从两面性角度去思考“知音”这个问题本身时,命题中所存在的问题。
(三)批评鉴赏中的主观与客观
刘勰在《知音》篇中强调人会因为个人的喜好导致鉴赏结果出现偏颇,这样的理论有其合理性,但其也有不合理性的存在,即可能会走向绝对客观而忽略在文学鉴赏中主观的合理性和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知音》中的刘勰是站在作者的角度来教读者如何鉴赏作品,并没有关注读者的角度和情感因素,这种角度充分肯定了客观对于文章鉴赏的重要价值,却将文学鉴赏这一活动中读者所占据的主体性忽略了。与每位作者都有其独特的个人性情一样,每个读者也拥有自己的性情,每个人性情的独特性一定会体现在他所创作的语言文字中,而读者在阅读这种情感体现时,是不可能完全避免个人性情的影响的。刘勰在《体性》篇中也提到了作家的个人性格与作品之间的这种关系,“才性异区,文辞繁诡”,但对于这种关系的思考并没有很好地体现在这一篇鉴赏论之中。
个性越加鲜明的作家,其在文章作品中的体现就越发突出,如果读者或鉴赏者的性情能够接近作者的真实性情,那么就越发的能够真正地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内涵。这种体现在性情上的异同是在文学批评中一个很重要的现象,但刘勰认为这是“私于轻重,偏于情爱”,这样的态度在鉴赏过程中是需要摒弃的,但如果一味地追求鉴赏的客观性,那么许多“妙鉴”也就无从得来了。在许多古人的诗文评中都可以见到主观因素的合理性,如元好问喜欢慷慨苍凉的写作风格,因此就大力推崇刘琨的清刚之体,而对费心锤炼的孟郊评价就相对一般,“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这种评价听起来虽然有些刺耳,但确实能够概括出孟郊的创作风格;又如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谈唐宋诗的问题,“唐诗多以丰神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夫人禀性,各有偏至。发为声诗,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将唐诗与宋诗放在一起,本就是两种不同创作风格的比较。历代文人也都根据自己的性情喜好来进行评判鉴赏,无法进行客观的评判,不同的人根据性情所选来鉴赏的诗作不同,每个人的评判标准也都不尽相同,许多拿出来评判的诗作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水平上都是水平极高的作品,但每个人又会根据自己的性情喜好加以选择,这就是主观因素所起到的作用,也不能将之完全忽略抛弃。
客观性在文学鉴赏中确实有它自己的优势,理智且逻辑严谨,思维深远,但过分追求这种客观性,就会由于过分理性而忽略文学作品中“情”的力量,这就会在文学鉴赏时束缚住思维的发散,如果依照某种客观思维订立一套鉴赏标准的话,那么文学鉴赏又会陷入刻板呆滞,意味全失。如果作家在创作的过程中刻意秉持这种客观的思维,那么写出来的东西很难会是他内心想法的真正表达,文学批评也同样适用,一味地刻意追求客观,忽略根据自己的真性情做出的评价,这种文学鉴赏必然也是空洞的。
因此在文学批评的过程中,既要避免过分主观带来的个人偏颇,又要避免过分客观导致的空虚乏味,如何把握好这个尺度,在批评中做到一种态度的平衡,大概只有在不断的实践中才能够获得经验了。
(四)“六观”的功用
从内容上看,“六观”是针对“文情难鉴”的问题所提出的,虽然含有一定的原则性和规范性,像是在教授读者如何去分析作品,分析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布局谋篇、语言修饰等,也就是说读者可以从“六观”的六个方面入手分析作品。但“六观”并没有说明评价文学作品优劣的标准,没有说明什么样的“位体”“置辞”“通变”“奇正”“事义”“宫商”是优还是劣,读者没有办法将之作为标准来运用,去进行文学的批评活动。所谓“标准”是指评论文章的依据,即根据怎样的标准去评价一篇文章,但刘勰口中的“六观”则是从实际的操作角度去讲如何品鉴一篇文章。“观”从语义上来看有“看”“示人”“观赏”的含义,“六观”中的“观”即所谓的“观察”“考察”,而所谓的“六观”就是从六个方面来考察作品的方法。刘勰对于“六观”的描述中,并没有出现说明标准和准则的词,但是却用到了许多对于优劣好坏的品评词汇,例如“风清”“体约”“文丽”“诡”“诞”“芜”等词汇,这些词既是对于文学创作的要求,也是对文章批评鉴赏的要求,在這个含义上《知音》篇对于《宗经》篇有补充的内容,即文学批评与鉴赏的方法和途径,使整个《文心雕龙》的批评系统更为完备。
综上所述,《文心雕龙·知音》篇对我国古代文学鉴赏和批评形成的较为客观的、科学的批评方法产生了较大且积极的影响,虽然也存在着一些不够完善和强求的问题,但这些理论问题在千年后的现在也没有被解决,与《文心雕龙》的成就相比还是次要的,这就是《文心雕龙》在文学批评鉴赏上沿用至今且不断更新发展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