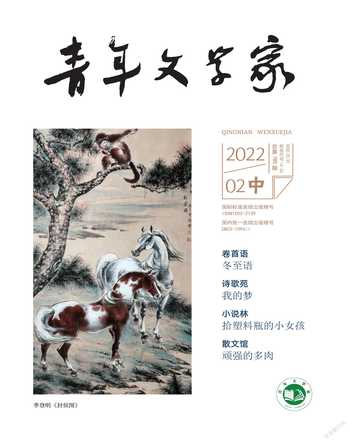小叙事模式下汪曾祺《徙》的人物形象探析
王晴阳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高度发展,引发出“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等文学模式。但是宏大叙事模式已然慢慢丧失了可以为人具体感知的审美特征,真实的个体生存中无时无刻不在的“小文化”“小话语”“小叙事”反而具备了可体验的艺术魅力。汪曾祺对中国当代文坛的独特贡献,在于他专注于从司空见惯的、平平淡淡的凡人琐事中汲取诗情,叙写了身边的“凡人小事”之美,他聚焦于个体生存境况,呼唤了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汪曾祺笔墨淡雅,怀着溫厚的心境自小其“小”,因小见大,极少抒写惊天动地的大事。他的作品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神韵之所以产生强大的阅读魅力,就在于他对凡人俗事的细致描摹,既是体现了人本主义思想,又再现了悲悯情怀的情感理论体系。
一、“小叙事”对“宏大叙事”的消解与颠覆
“宏大叙事”是一种追求完整的叙事模式,尽可能达成包容万千的叙述,以目的性、主题性、统一性以及连贯性,建构气势磅礴的基地,用以表现宏大的历史和现实,密切联系意识形态和抽象概念。宏大叙事往往与总体构建、宏观理论、全面共识等概念有部分相同的内涵,与细节、结构、分析、差异性、多元性、悖谬推理具有相对立的含义。
“小叙事”又名“个人叙事”,采用小范围的话语,从个人角度和个人体验出发,以坦诚开放、个人化的叙述方式,认识、理解和阐释历史的叙事模式,以普通个体的体验与集体大话语对抗,其意义在于解构主流话语强调的整体的、一元化的叙事模式,从而构建丰富多样的历史。后现代权威理论家利奥塔主张用局部叙事取代总体叙事,用“小叙事”取代“大叙事”。利奥塔认为,当下如果我们仍然探索后现代科学化的有效度,不能再根据精神辩证法,甚至也不能寄希望于人类精神的解放。换言之,就不能再依仗着“大叙事”的策略,这一方案被排除了。因此,现代叙事风格逐渐向“小叙事”风格靠拢,尤其是富有创作生命力的作家。然而由于风格较为独特,和传统高评论家过去推崇的叙事模式截然不同,“小叙事”在初入文坛时,往往得不到理解和共鸣。所以汪曾祺继承沈从文延续了这个风格流派,在文学史的意义也尤为重大,以至于变成一种持久而稳定的精神辐射。
京派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读书传统更是薪火相传,演绎到小说理论中便凝结成了“希腊小庙”“纯文学”等文学理论。汪曾祺的小说风格简约粗疏,大多篇幅短小,形式不拘一格,介于随笔和小说之间;行文流露着中国古典笔记体小说的风韵,践行了一个长久讨论的议题:中国现当代文学如何守正创新,从传统中真正传承古典遗韵,进而丰富传统。汪曾祺传承了正宗的京派气质,把高北溟作为中国传统文人的缩影,自有直通人性深处的魅力。
“大叙事”以分析“当下”、关注“现在时”为己任,而汪曾祺反其道而行之,解释灵感常常来源于过往,托梦于“四十年代”,汪式小说的内容与题材大部分都取之于旧社会,取之于故乡高邮的乡村市镇生活,取之于过去时,以过去时态叙述故事,“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汪曾祺,1993)。
二、《徙》中高北溟、高雪等人物形象与塑造
汪曾祺的小说里没有高大的英雄形象,没有跌宕起伏的动人情节,有的只是现实生活的琐碎小事,以及平凡人物面临现实生活生存的窘迫和妥协。主人公多是“善良的,有古风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们柔弱得安时处顺、谦逊宽容,不声不响地给予人间温情。
(一)教书先生高北溟
汪曾祺用“小叙事”的风格描写了普通人平凡的生存状态,肯定了不完整的、庸常的人生。汪曾祺小说《徙》中的传统读书人和教书先生形象—高北溟,平凡人物的形象被勾画得栩栩如生,成为一个历史迭代的人物缩影,一个时代更替的代表符号。
高先生的天资,“虽只是中上,但很知发奋”,多么诚恳的一笔,若是放在“大叙事”里,为了突出天赋异禀的独特,加之主人公光环,恐怕要被写成方仲永的“指物作诗立就”的才能。面对世事变迁,高北溟曾踌躇满志也曾茫然无措,他还是被历史抛弃,和千千万万读书人一样惊悚不安地寻找出路,像地震前恐慌不安的飞鸟走兽,终究没有成为史诗巨著里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的英雄。
“高先生性子很急,爱生气。生起气来不说话,满脸通红,脑袋不停地剧烈摇动……高先生很孤僻。他不吃烟,不饮酒,不打牌,不看戏……高先生家的春联都是自撰的。”一长串的高先生如何如何,都在展现一个真正的读书人,一个性格上不够完美,但凡事郑重其事、一丝不苟的教书先生形象。或许,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让人变得深奥,而是让我们重返天真。
高北溟身上流露出道家主张的随缘自适、自足自保的悠然的意趣,但又有别于魏晋文人的清谈和颓废。高北溟喜欢给学生改作文,“只有在这样的时候,他觉得不负此生,做了一点有意义的事”。虽然高先生不像看起来的那么薄情寡面,但对得意的学生也从不喜形于色,只把热情倾注在教学中。高北溟追求的是顺其自然的无所依,他最终获得了无穷的自在自由。
在一个平淡无奇的教书先生的人生经历里,读者被轻轻地戳中了泪点,先生之态栩栩如生,高先生的脾气很“方”,他“很孤僻,不通人情,不随份子,从不请客,从不赴宴”,固执得有些傻气。
高北溟以平淡的心态感受和认识世事艰难,与传统文人的忧患意识相通,在压力下孕育出超然的精神自救方式。他对现实的痛苦感受在不断地发酵、酝酿,平息着激情,平息着愤怒,平息着对学生的喜爱。
如果正如孙郁所说,汪曾祺是“革命时代的士大夫”,那么高北溟可堪称是“士大夫里最后的教书先生”。高北溟认真着,他教书时极其认真甚至执拗,除此之外的生活是混沌而“糊涂”的。“糊涂”是旧社会多数文人的毛病,连汪曾祺也不例外,没有那么多的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替他们分析利害关系,他也不愿意钩心斗角,玩弄远交近攻的把戏,而是过着自得其乐的生活,本真地栖居,做一个诗人而不是一个教书匠。宏大叙事里往往自以为是地把社会分析解剖,用辩证法的显微镜拨开人的内心世界,自作聪明地把人物安置在某个阶层,把他们固化、标签化、脸谱化。
汪曾祺小说的魅力在于能把叙事情感倾注在平静如水却暗流涌动的叙述中,多数读者能读出自我镜像,围绕在爱憎的人物形象上,在故事的流动中不知不觉地共情共鸣,被弥漫其间的酸苦氛围笼罩,咂摸出淳朴厚重的乡愁,生出些许悲凉。《徙》宛若一则博学、沉潜的寓言,描述出个体生命的脆弱与孤独。人物写到最后不是一种个性的表现,而是一种个性的脱离,具有了普遍永恒的意味。
(二)高雪
高北溟的兩个女儿差别很大,姐姐高冰知书达理,懂事识大体;妹妹高雪飘逸灵动,志存高远。这个高先生“欢喜团”似的小女儿,恰如一支芙蓉涉水而来,她意态高扬、自由自在地度过青春年少,娴静处有娇憨之态,流转时妩媚可人,欲笑还颦,温顺里夹杂着些许倔强,沉静中露出锋芒,忽然灵动起来却又是另一番明光流丽。但是她也没有等到“海运”,“则将徙于南溟”。最终的结局是高雪被迫出嫁,成了静默地走向死亡的花蕊。
作为《徙》中最浓墨重彩塑造的女性形象,高雪最后的离去不是单纯意义上生命的终结,于高雪,这或许是一种解脱,她活在自己的理想世界里,仿佛与现实格格不入,只好以死来反抗。更像是一个反诘,拷问了高北溟和镇上的其他人,逼迫他们去反省:为什么要用自以为是的世界观强加在一个未经世事的少女身上?两个女孩形象显露了汪曾祺对人物塑造的功底,而且显示小叙事的审美效果,具有“洞庭始波,木叶微脱”的清远静美之意。
《徙》的前面部分主要展示了高北溟跌宕起伏的经历,或许可以认为,他受过太多的约束与限制,出身、家境、制度、年龄……所以,汪曾祺此处也是想在高北溟女儿身上做些补偿,纵容高雪有个酣畅肆意的童年,但是没有条件继续让她随心所欲—想飞、上大学,不只是金钱短缺,更有来自世俗力量的压迫。无缝不入的压迫才让人觉得窒息,无法逃脱。试想,即使高雪飞了出去,上了大学又如何,最终还是要回归柴米油盐的家庭生活,苏州师范的“《茶花女》的饮酒歌,肖邦的小夜曲”,都会淹没在锅碗瓢盆的琐碎里。
三、《徙》的深度题解与内涵探析
《徙》开篇即引用庄子中《逍遥游》的一段文字,显得意味深长,“小叙事”的张力就在于其发掘和表现的普遍性能创造巨大的艺术效应。“徙”字意味深长,《说文》中认为“徙,迻也”,动词常作迁移和移动之意,小说题目也意味着不断地适应新变化,不停歇地被迫改变,持续地与时俱进。
高北溟随着世事变迁不断地迁徙。若直接取“迁移”,就可将主人公高北溟的每一次的转弯都看作“徙”:“家世业儒。祖父、父亲都没有考取功名。”高北溟天资不足却遇到谈甓渔这样的用心的教授,“怒而飞,由鲲化而为鹏”,十六岁时高高地中了秀才,一徙也;第二年停科举、兴学校,功名道断,谈先生寿终,高北溟去读被人看不起的师范,二徙也;在“五小”任教免于冻饿,不至像徐呆子似的死在街上,但总受同事挤迫,三徙也;“未徙者将徙也”,辛未年的春联撰后第二年,高先生来到了本县最高学府“初级中学”,教书顺了,“翼若垂天之云也”,传播人道主义,泽被学生,搬家了,心境很好,人也变得随和,四徙也;省长易人,人事更代,高先生又回到第五小学,谈先生的书稿再无可以出来的希望了,高雪走了,五徙也。
最后,高先生也走了。以慢移的镜头和瞻前顾后的剪辑,给人以汩汩清泉般的冲击。章与章之间,节与节之间,甚至一节之内,自由转换,跳跃自如。“随遇而安”隐藏着深深的无可奈何之情,他的性格依然如故—“方”,不通人情世故。
若按照第二种理解,“徙”意味古代流放的刑罚,始终是一种流放,始终未至南溟。北溟无边无际,水深而黑,古有“六月海动”之说,海运之时必有大风,因此大鹏可以乘风南行。“北溟之鹏终将徙于南溟”,这是谈甓渔对高北溟的嘱托,或是文化传承的希冀。可是科举废止,谈甓渔寿终,他的“后人很没出息,游手好闲,坐吃山空,几年工夫,把谈先生挣下的家业败得精光,最后竟至靠拆卖房屋的砖瓦维持生活”,他的高足高北溟想刻印先生的文集也不能至。
“小叙事”里的“以小媚大”的确是“四两拨千斤”的功夫。我们现在又何尝不是在拆卖先辈留下来的房屋呢?如果用宏大叙事的手法讲述同样的故事,可能远远不如《徙》的张力。汪曾祺让我们看到,传统文化已经是谈家门楼,“门楼倒还在,也破落不堪了”,又有“惯于欺世盗名”的李三麻子这样的文化汉奸,“很多歌消失了,许多歌的词、曲的作者没有人知道了”。高北溟这样的先生也死去很多年了。这是一次宏大意义上的“徙”,我们的文化被我们自己流放了。
从《徙》的细节处理、修辞的运用乃至自居推敲中,“小叙事”体现着特定的审美意识形态本质特征。推断汪曾祺的人文意识,究其根源,汪曾祺的文学观厚植于中国传统文论中,又于西学东渐时吸取西方哲学中的有益成分,形成自己独特的书写风格。他曾经强调,文学应当“于世道人心有补,对社会人生有益”。读者在汪氏小说中可以尽情感知日常生活中琐事的温暖,在世事的苍凉与沉沦中擦干眼泪,即使未来被历史轨道揪扯或抛弃,也自知甘苦,凭着一双勤奋的手,从容熬过,期待春暖花开。
“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汪曾祺,1987)的汪曾祺,采用中国传统文人的情调和视角,试图将整个自然、社会甚至人类融汇进自我的生命意识中,《徙》凝聚了特定文化形态,具有了跨越时空的文学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