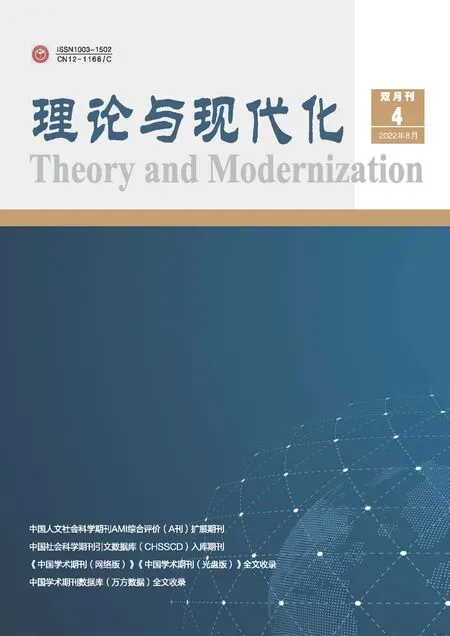柏拉图的定义理论
吕纯山
一、引言
对于柏拉图哲学,研究者喜欢讨论他的政治哲学、伦理学、形而上学和知识论等,而在知识论中,多会讨论知识与意见和感觉的关系,以及真假等问题,对他的定义理论,却很少有专文展开讨论,即使有,也只在他的哲学体系内部,或只是联系苏格拉底的相关理论进行研究,甚少有人联系亚里士多德的定义理论,从二人定义理论的相关性这一独特角度进行思考。柏拉图的定义理论甚少被讨论,也有其文本上的困难之处——虽然他对定义的对象和方式问题都有里程碑式的理论贡献,都为亚里士多德后来的深入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但是他有关定义的理论分散于不同的对话之中,而且他的很多灵光乍现式的真知灼见往往和相关上下文的语焉不详相伴。更重要的是,他的定义理论终究没有十分明确的结论,不成体系,因此研究者也难以展开深入细致的讨论。然而,如果我们能联系亚里士多德对老师相关理论的发展,从学生的哲学来重新审视老师卓越的思想闪光点,相信我们一定有意外的收获,或者说,只有从这一角度入手,才能挖掘柏拉图定义思想的深邃之处。
现当代的研究者有关柏拉图定义理论的研究文献寥寥,而不多的文献也以单篇文章为主,因此对定义的论证并不细致。理查德·罗宾森(Richard Robinson)在一本名为《定义》(Definition, 1954)的专著中,按照定义目的的不同,把定义分为两大类,一类称之为物—物定义(thing-thing definition)或真正的定义(real definition),另一类为名义性定义(nominal definition)。他认为定义这个概念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发明的,并且只想到了真正的定义,即所定义的对象理念是真实存在的[1]。对于罗宾森的观点,笔者很难苟同。所谓真正的定义和名义性定义的划分是值得商榷的,理念固然是真正存在的,但它同时是一种类概念,换言之,虽然柏拉图在文本中都用,但未尝没有区分存在论上的理念和知识论意义上的种/类,而且从苏格拉底开始,定义就是对普遍对象的描述。另外,说“定义这个概念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发明的”,恐怕也不符合事实。后来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概念明确、讨论丰富的“定义”()这一概念,在柏拉图哲学中尚未形成统一的说法。正如一些柏拉图哲学专家颇有见地地指出:“亚里士多德曾告诉我们苏格拉底是最先关注定义的人,但柏拉图的早期苏格拉底对话没有使用表示‘下定义’或‘定义’的术语,亚里士多德所用的‘’在柏拉图对话中始终没有出现,但出现了‘o'ρο ’及其相关动词‘’,原意是空间性的边界。‘’在对话中出现了6 次,仅《理想国》(331c1-d3)最接近于‘定义(definition)’,其他几处则保留‘boundary(边界)’或‘mark(界标)’的意思;‘’出现了15 次,意近英文的‘mark off’、‘separate’、‘bound’;所以有学者认为‘distinguish’或‘determine’是比‘define’更为恰当的翻译。”[2]120-121“‘o'ρο ’及其相关动词‘oριζειν’正是通过苏格拉底对话才开始向哲学术语过渡,从‘边界’或‘划界’走向‘定义’,而这意味着,‘定义’观念本身则尚处于建构的过程之中”[2]121。事实上,柏拉图用以表述后来的定义概念的词经常是λογο (描述),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的叙述中清楚地看出来。查尔斯(David Charles)主编的一个论文集《古希腊哲学中的定义》重点在于对亚里士多德分类法定义的讨论,仅个别论文涉及柏拉图的二分法定义,讨论虽细致却因为缺少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视角而显得大众化。赛德利(David Sedley)专门为柏拉图的《泰阿泰德》写了一部注释,但他对于其中的苏格拉底的“梦论”和描述的三种选择的讨论,却值得商榷,他不仅把柏拉图前后相续的思想打断,把元素理论解释为两种,而且把“元素”解释为四元素火、气、水、土,还误解了“可知的复合物”,更否定了后来亚里士多德对相关理论的发展[3]。可以说,缺少亚里士多德定义理论的维度,无法准确把握柏拉图定义理论的真知灼见。
哲学史家策勒有这么一句著名评语:“在希腊哲学历史发展的全盛时期,苏格拉底是其孕育的胚芽,柏拉图是盛开的花,亚里士多德是成熟的果实。”[4]在笔者看来,这句话准确而深刻地刻画了三代哲人在概念理论和西方理性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在传统的哲学史中,因为苏格拉底是在伦理学概念中寻求普遍者,也被后世尊为希腊哲学从自然哲学转向伦理学的里程碑,于是后人更多强调他们在伦理学方面的继承关系。但是,仅肯定苏格拉底的伦理学创始人的地位,远远不足以刻画他在哲学上的贡献。实际上,三代人对概念理论中最为核心的定义问题的讨论及形成的丰富理论,既是他们哲学中最基础的部分,也是他们每个人殚精竭虑思考一生的问题。毕竟,如后来亚里士多德所言,定义是知识的本原(),他们的定义理论是他们各自知识论的中心。而柏拉图的定义理论,上承苏格拉底对“是什么”的描述和“归纳论证和普遍定义”的追求,下接亚里士多德在逻辑学著作、《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著作中深入而广泛地对属加种差定义和质形复合定义的讨论,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二、定义的对象
(一)定义是对“是什么(τι εστι)”和理念/种(ειδο /ιδεα)的描述
亚里士多德曾明确告诉我们,苏格拉底是第一个讨论普遍定义的人,他在《形而上学》A6, 987a29-b14 中这么评价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本人正忙于伦理问题,忽视了整个自然界。他在这些问题中寻求普遍者,第一次把思想集中到定义上。”[5]648他在《形而上学》M4,1078b9-1079a4 中更详细地谈到苏格拉底的贡献:“苏格拉底当时正专注于道德品质,并且与此相联系,成了第一个提出普遍定义的人。——因为在自然哲学家当中,只有德谟克利特接触到这个问题,并且勉强地给‘热’和‘冷’下了定义,毕达哥拉斯学派在此以前曾联系到数来说明少数几种事物,如机会、正义和婚姻。——但是,(苏格拉底)要寻求事物的‘是什么()’。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还寻求理性的推导,而事物的是什么正是理性推导的本原()。……有两件事可以公正地归给苏格拉底:归纳论证和普遍定义。这两点都是与知识的本原有关的()。但是,苏格拉底并没有使普遍者或定义分离地存在”①。在这两段话中,亚里士多德充分肯定了苏格拉底在定义理论上的功绩:作为哲学史上第一个追求普遍定义的人,他以伦理概念为主要讨论对象,并进行归纳论证,从特殊的事例中寻求普遍对象及其描述。同时也提醒我们,苏格拉底虽然是严格意义上第一个追求普遍定义的人,却也并非首次接触这个问题的人,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中的德谟克利特和毕达哥拉斯学派曾在这方面都有贡献,但还没有成熟到对普遍物的追求上,当然更没有归纳论证的方法。
熟悉柏拉图以伦理学概念为讨论对象的对话的读者,一定知道苏格拉底在对话中一直在寻求各种伦理概念的“是什么”和定义,如在《欧绪弗若》中讨论虔诚②,《卡尔米德》中讨论节制[5],《拉克斯》中讨论勇敢[5],《美诺》中讨论德性③,《理想国》第一卷讨论正义是什么[6]……不过由于我们只能通过柏拉图的对话来理解苏格拉底,有时候两人的思想又是纠缠在一起的,我们不太容易分辨。例如在一般公认是柏拉图早期对话、代表苏格拉底思想的对话《欧绪弗若》中讨论虔诚时,苏格拉底和欧绪弗若讨论了好几个定义,讨论由于最后的定义又回到原点而结束。不过,最主要的结论其实是第一个定义之后给出的,那就是当欧绪弗若给出“虔诚就是告发那些犯有杀人罪或者盗窃庙产罪的人”(《欧绪弗若》5e)时,苏格拉底认为这个定义不充分,因为这个定义不过是虔诚的一个特殊实例,但所追求的虔诚的定义不是对特殊的虔诚的事的描述,而是对虔诚的理念的描述:“那么请你想想,我向你提出的请求,并不是从许多虔诚的事例里给我说出一两件来,而是说出那个使虔诚的事情虔诚的理念本身()。因为你说过,有一个理念使不虔诚的事情不虔诚,使虔诚的事情虔诚。”(《欧绪弗若》6d-e)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理念是柏拉图的创造,“他引进理念是由于他要研究描述”(《形而上学》A7, 987b31),并明确了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区别:“苏格拉底……在各种伦理性的事情里面寻求普遍的东西,首先把心思放在定义上面。柏拉图接受了他的观点,但是认为定义不能下在可感事物身上,只能给另外一类东西下定义,因为可感事物不能有共同的界限,而总是变化不定。他把这另外一类东西称为理念(),说它在可感事物以外(),可感事物都是按照它来称呼的。”(《形而上学》④A6, 987b1-9)因此,《欧绪弗若》中对虔诚的讨论,或许已经代表柏拉图的思想,对“是什么”问题的追求,就是对“理念”的描述,对一类特殊事物的类的描述,描述中不涉及特殊,追求的是普遍的东西,包括对象的普遍和描述的普遍。
还有如苏格拉底在《美诺》中讨论一般的德性是什么,美诺首先给出男人、女人的不同德性,并认为儿童、老人、自由人和奴隶的德性都不同:“每一种行业、每一种年龄、每一种活动都有它各自的德性。”(《美诺》72a)苏格拉底不满意这个说法,认为:“各种德性也是这样。它们虽然很多,而且多种多样,却共有一个理念,正是由于这一理念,它们才是德性。回答我提出的问题的人要密切注意这个理念,就是:德性本来是什么?”(《美诺》72c)因此苏格拉底强调要考察的是这个理念,随后给出的一个定义是正义的定义,但苏格拉底认为,正义是德性的一种,德性还有勇敢、节制、智慧等,我们只寻求那统一的德性,却找到了许多德性。因此,用属于德性的不同的具体德性来定义作为整体的德性本身,这样的说法依然是不成立的,要完整地说出德性是什么。
不止苏格拉底在柏拉图早期对话中追求事物的“是什么”,其实柏拉图的大部分对话都是对“是什么”的讨论,如他在《智者》中讨论智术是什么,《高尔吉亚》甚至讨论高尔吉亚是什么,《斐多》讨论灵魂是什么。在柏拉图的《泰阿泰德》⑤145e 中,苏格拉底提出问题:知识是什么?泰阿泰德的回答是:包括几何学、算学、天文学和自然哲学等在内的知识,还有制鞋术和其他各种工匠的技艺(《泰阿泰德》146c-d)。苏格拉底马上反驳,我要求一个简单的说法,你却给了很多复杂的内容,而且,你说的是制鞋术和木工技艺各自“属于什么”,前者属于制作鞋子方面的知识,后者属于制作木器方面的知识。问题不是知识属于什么,有多少种类,而是希望认识知识本身究竟是什么。例如,要回答泥是什么,回答有陶工的泥、灶工的泥、砖工的泥,是不对的。对于知识是什么的问题,当某人用某种技工的名称来回答,答案很可笑,因为回答了知识属于什么。泥是土混合了液体。他举了正方形数和长方形数的例子,说明平方根是什么。因此,要对知识进行描述,并且是给出统一的、单一的描述。
当然,因为被柏拉图强调所有的理念都是一个个“本身”,“每一个在本身中都是一”(《理想国》476a),如美本身、正义本身、智慧本身、节制本身、勇敢本身,甚至还有躺椅本身。“我们说存在很多美的东西,存在很多善的东西,并且存在很多其他的东西……现在,反过来,我们都把它们置于和它们每个相应的单一的理念之下,因为这理念是单一的,我们说它们每一个就是存在。”(《理想国》507b)理念,就其根本而言,是知识的对象,这些说法明确理念是一种存在,虽然不能通过视觉被看到,但却是我们思考的对象,它们本身在可感事物之外存在。正像后来亚里士多德所批评的那样:“所以不难明白,普遍不能在个体之外(παρα)分离存在()。那些主张理念的人,说理念是分离的()时,这是对的,假如它们是实体的话;但他们又是错的,说理念是众多之上的一。其原因在于,他们不能指明,在个别可感事物之外(παρα),这些不可消灭的实体到底是什么。”(《形而上学》Z16, 1040b26-32)理念虽然与可感事物分离存在,是一种与个别事物相似的独立存在物,但它根本上是一种类概念种。就一般概念而言,善、正义、节制、勇敢、智慧、虔诚、美、知识、德性、描述……当然是一种类概念,是集合。
亚里士多德后来把“是什么”与“本质”概念等同了起来,在逻辑学著作中认为,定义就是对种的描述,属加种差构成这种描述,其中属是标志性的,例如我们问:“人是什么?”回答:“人是动物。”这一回答就给出了人的本质。可以说,逻辑学著作中对定义的讨论最大程度地发展了柏拉图的分类法定义思想。亚里士多德不仅讨论如何正确划分,讨论如何给出属,如何给出种差,还详细评价过或许是学园成员给出的一系列分类法定义。后来,他在《形而上学》Z4 中把这些概念与“定义”和“存在”相联系,认为存在的首要意义是实体,是“这一个”。因此,定义的首要应用就是对这一个实体,“是什么”和“本质”的首要意义也是“这一个()”的是什么和本质,如苏格拉底的是什么和本质,呈现出存在上本质的个别性和定义或知识上对本质的普遍描述之间的张力。
(二)可知的复合物种(ειδο /ιδεα)
与亚里士多德和后世哲学对柏拉图在《政治家》中提出的“人是两足动物”这一著名定义的反复使用相比,柏拉图知识论的代表著作《泰阿泰德》在其定义理论中的重要地位被严重低估了,甚至一些《泰阿泰德》的研究者的理解都很是偏颇。如上文提到的赛德利,他把文本中提及的元素理解为火、气、水、土四元素,而没有把握实际上是亚里士多德后来用“终极质料”表述的质料,把“梦论”和第二种描述分隔开来,认为是两种元素理论,没有理解到实际上是同一种元素理论,只是因为与其他两种描述相比更为复杂,柏拉图提前用比较多的笔墨进行阐释罢了[3]。事实上,柏拉图《泰阿泰德》的核心思想就是寻求“知识”的定义,谈到了“描述”的三种选择,没有提到他典型的伦理学概念,如美、善、正义等。这一点也被格思里注意到了,不过很奇怪的是他认为柏拉图在这里强调的是对个别事物下定义:“全篇的主要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够有对物理世界的个别事物——泰阿泰德,太阳等——的知识,而非关于事实的知识,也非关于像勇气或正义这样的普遍概念的知识。这可能是整篇对话最奇怪的地方。当然对柏拉图而言,知识的标志是有能力说‘X 是什么’,即定义它……但他的X 总是一个普遍物或类概念:正义,勇气,或就像接下来的对话中的‘智者’或‘政治家’,而非普罗狄克斯或伯里克利。这里他徒劳地花时间追求个别事物的知识,但……注定只能失败。”[7]这样的理解其实是误解,柏拉图在文本中的确提到音节、马车等这样的事物,但何以这些事物一定是个别事物,而非个别事物的集合或类呢?毕竟也正是在这一文本中柏拉图说道:“我们必须这样来表述个别的东西以及许多东西的集合,所谓集合就是指人或石头或每一种动物以及种/类()。”(《泰阿泰德》157b-c)这句话也明确地解释了ειδο /ιδεα 本来就是类概念,“人”是指个别人的种,“动物”是指个别动物如个别的人或马的类。
因此,在定义问题的发展上,《泰阿泰德》对亚里士多德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第一,柏拉图在《泰阿泰德》中根本没有提及他一般提及的典型的伦理学概念,而提及的是人、石头、马车后来被亚里士多德称为质形复合实体的东西,或许已经暗示实体与其他概念有不同的定义方式,当然文本所强调的是知识论上的可知的复合物,也就是后来被亚里士多德强调的作为定义对象的普遍的质形复合物;第二,柏拉图把元素和可知的复合物直接对照,并把后者称为种,也或许影响到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Z7-9 中的观点,这一观点认为复合物是种和可感质料构成,如苏格拉底是人和个别的躯体构成,成为亚里士多德思想发展的一个独特阶段;第三,柏拉图在《泰阿泰德》中的叙述并没有明确究竟我们要描述的对象是元素和路径的可知复合物这样的种或类概念,还是只对路径进行描述,后来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Z10-11 中即专注于讨论实体定义的对象,不是质形复合物,而是形式,或许在这个阶段他倾向于对类似于柏拉图的路径的描述;第四,《泰阿泰德》暗示复合物是各元素与贯通路径构成,并以字母和音节为元素和复合物的典型代表,后来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Z17 中也以字母和音节为代表强调字母就是质料,形式就是使字母成为整体音节的原因,与柏拉图的路径的功能是一致的;第五,《泰阿泰德》讨论有一种描述是对“差异”的描述,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H 卷径直讨论差异类比于形式,事物无论排列、组合、位置还是什么的差异,都相当于质料的形式的不同,差异即形式,从而对复合实体的描述,也就是对质料和形式的描述,也就是对普遍的质形复合物的描述,也就是柏拉图的可知的复合物。一句话,柏拉图《泰阿泰德》中有关复合物、路径、差异的思想,为后来的亚里士多德以普遍的质形复合物概念为定义的理论铺平了道路。
三、定义的方式
(一)二分法定义
柏拉图不仅追随苏格拉底的思路,把定义的对象从“是什么”进一步定位到类概念之上,而且在定义的方式上,也给出了分类法定义,并在《智者》[8]《政治家》[9]等对话中要给“智术”和“人”下定义。《智者》中为了给“智术”下定义,从“技艺”开始,进行二分,一层层划分下去,而且每一层的每一种技艺也都可以二分,分别得出了几个有关智者的定义,但是智者是一个,定义却好几个,显然不符合定义是单一的描述的特征。最后在讨论了“非存在”“假判断”等问题之后,重新讨论智术的定义,又一次从“影像制作术”开始两分,然后逐层划分下去,得出结论:智术是属人的而非属神的制作,在言论中玩弄魔术的部分,属于影像制作术当中幻像术的类型,也就是自以为是的模仿当中伪装的、制造悖论部分的技艺。这一划分,从最高的“属”技艺开始,最后得出智术是“XX 的技艺”,是一个统一的描述,也为后来抽象出属加种差的定义方式奠定了基础。而当我们详细考察柏拉图的二分法,虽然每一次具体的划分都是二分,但却也是多次的二分,无疑也给后来亚里士多德的“多分”提供了改善思路。
《政治家》中要对“人”下定义,从“知识”开始进行二分,待分到“指示性的知识”时,又分为传令官这样的传达他人命令的和发布命令者自己的命令的两类,而发布命令的对象,可被划分为无生命的“动物”或者有生命的“动物”;有生命的动物的类型中,又有野生的和驯服的之分;驯服的进一步分为单个喂养的和群养的;群养的类型又进一步分为水生的和陆生的;陆生的分为有角的和无角的;无角的分为杂交的和不能杂交的;不能杂交的分为四足的和两足的;两足的分为有翼的和无翼的。总之,一层层分类下来,得出一个人的定义——陆生无翼两足的群养动物,有时被简称为两足(无翼)动物,或称为两足(陆生)动物,或更简称为两足动物,这一定义经过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中反复不断地引用和解释,成为哲学史上最为著名的一个定义⑦。当然,我们看到,这一定义的划分不是从最高的属开始,划分过程中从“知识”突然转到其对象,颇为随意。后来亚里士多德虽然接受了“人是两足动物”这一定义,并且在逻辑学著作中经常把它当作经典的定义来使用,但对柏拉图的“两分法”却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他在《论动物部分》I.2-3 和《后分析篇》《论题篇》甚至《形而上学》Z 卷中都对这一定义方式进行了讨论,明确肯定了“划分”的可行性和“二分”的武断性。在他看来,首先,“二分法”意味着分离和拆散,是不可能的:“有些人试图借助把物种划分为两个不同的种差系列来把握动物的绝对形式,这种方法既不容易,也是不可能的。”(《论动物部分》⑧I.2,642b5-7)其次,“二分法”必然导致缺失性词项如“无足的”或“无翼的”这类词项(这类词项不是种差)的产生,应用“多分法”(《论动物部分》I.3, 642b23-24)。总之,“用二分法把它们划分成相互对立的两类种差系列更是困难重重,实际上也是不可能”(《论动物部分》643a1-2)。甚至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两足动物”,既属于鸟类,又属于人类。因此,既不应当把同一个不可分的种置于两个以上的被划分的种差系列,也不应当把不同的种归于统一被划分的种差系列。每个种必须被置于某个合适的种差系列。但是,按二分法进行划分的人是达不到这样的要求的。坚持二分法的人还武断地自由组合,比如,他们把动物划分为“有翼的”和“无翼的”,又把“有翼的”划分为“驯服的”和“野生的”,或划分为“白色的”和“黑色的”。但是,“驯服的”和“白色的”都不是“有翼的”的种差,而是另一系列种差的开始,出现在这里纯粹是偶然的。因此,这样的划分是十分武断的,缺失性词项也不能成为有效的差异。而且,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存在一个包括所有种类的种差系列是不可能的。例如,我们对人进行划分,唯一的种差要么是单一的,如分趾足的,要么是复合的,如有足的、两足的和分趾足的。如果人只是分趾足的动物,那这是一个由正确方法找到的唯一种差。但人并非仅仅如此,必然会有许多种差,它们不能被一种划分单位所包括。同一种动物的多种种差不会被二分法的两个分支系列的任何一个所容纳,因为任何一个系列都以一个种差而终结,所以对于使用二分法的人来说,要想借助这种方法来把握或发现全部动物的种类是不可能的,这实际上从一个方面否认“人是两足动物”这一定义是对人的合适定义。
当然,虽然亚里士多德批评了二分法,却肯定划分的必要性,强调正确的多分,并且在《后分析篇》《论题篇》等文本中详细地讨论了属加种差的定义方式,如何正确地进行属和种差的寻求,和众多的定义是否正确。只是,属加种差这一定义方式,究竟是柏拉图给出的还是亚里士多德给出的呢?柏拉图的对话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证据,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直接对这一定义进行讨论,唯一可以证明是柏拉图学派提出这一定义方式的文本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Z14 中:
显然,由同样这些,这一结论也适用于那些主张理念是实体和分离物的人,以及那些使种由属和种差构成的人。 (1039a24-26)
亚里士多德的这句话表明,属加种差的定义方式不是他本人提出的,不过,究竟是柏拉图本人提出,还是柏拉图学派的人提出,就无法得知了。无论如何,柏拉图提出“智术”和“人”的定义,已经为这种定义方式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属加种差的定义方式显然是柏拉图学派和亚里士多德共享的定义方式,一般的概念都可以这种方式被定义。
(二)为质形复合定义奠定基础
柏拉图及其学派给我们留下了“二分法”的实践记录,肯定了定义的对象,提出著名的“属加种差”分类法定义,还提出“人是两足动物”这样的著名定义,但绝不仅如此,柏拉图也为后来亚里士多德提出另一种定义方式提供了充分的思想资源,而这一点似乎更不为研究者所重视。
柏拉图在《泰阿泰德》中试图给“知识”下定义,在给出第三个知识定义时,他认为是“给出描述的正确信念”,最终因为“描述”和“正确信念”都是对“差异”的掌握,因此是同义反复,从而否定了这一定义,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定义尝试都失败了。其实,对如何“给出描述”给出三种选择:第一,“通过由动词和名词组成的语言让自己的思想显示出来”(《泰阿泰德》206d);第二,“贯通各元素而达整体的路径”(《泰阿泰德》208c);第三,“能够说出所问的东西区别于(διαφερει)其他所有东西的某个标识”(《泰阿泰德》208c)。其中的第一种选择比较容易理解,肯定了描述是由动词和动词构成的陈述句;第二种选择,是对苏格拉底“梦论”的进一步发展,柏拉图在文本中也对这一选择进行了很详细的讨论。他举了音节和马车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例如ΣΩΚΡΑΤΗΣ(苏格拉底的希腊语名字)这个音节,就前两个字母ΣΩ 而言,是什么?回答:Σ 和Ω。那么Σ 可否有描述?回答:没有,因为“Σ 是一个不发声的字母,只是一个噪音,就像舌头嘶嘶作响;再比如Β,它既不发声也算不上噪音,其他许多字母也是这样。所以,说它们本身缺乏描述是很对的,即使七个最清晰的字母也只有声音,没有任何描述”(《泰阿泰德》203b)。同样,当人们在写任何一个人名字的时候写错了字母,一定不能说是有知识的,比如当有人在书写ΘΕΑΙΤΗΤΟΣ(泰阿泰德的希腊语名字)或ΘΕΟΔΩΡΟΣ(塞奥多罗的希腊语名字)时写错了字母,那么他就没有知识;而“当他在书写ΘΕΑΙΤΗΤΟΣ 的时候,只要他按照顺序写对了,那么他在正确信念之外还掌握了贯通各元素的路径”(《泰阿泰德》208a)。因此,描述中的“路径”是很重要的,有了它,才能使各元素成为一个统一的事物。
除了对贯通路径的强调,他还提出一种说法——列举所有的元素和组成成分:
对于我们正在考察的这个知识的定义的主张者, 我们不要轻易地指责他在说废话。 因为很可能这个主张者不是这个意思。 他的意思可能是:当被问及一个东西是什么的时候,能够列举它的诸元素从而对提问者做出回答。 (206e-207a)
比如我们要给出对“马车”的描述,有人或许能说出轮、轴、车身、栏杆和轭,但是要达到对马车的完整描述,亦即,我们要正确地描述马车,必须能够给出上百个部件而详细解释马车,“通过诸元素成全整体”(《泰阿泰德》207a)才能具有对马车的知识,否则只能说拥有正确信念而无法具有知识,因为“除非某人在真信念之余还能够完全列举出那个东西的各个元素,否则他不可能带有知识地做出说明”(《泰阿泰德》207a)。这样,组成事物的元素本身虽然可感而不可知,但复合物是可知的,当然对复合物的描述必须把所有的元素完全罗列出来。除了对“路径”和所有元素的强调,柏拉图还强调要对事物和事物之间的差异(διαφορα)进行描述。
亚里士多德对质形复合物也提出了不同于分类法的定义方式。在他看来,“人是两足动物”这个定义中的“两足”和“动物”都并没有描述人的实体灵魂,从而否定了这一定义,可以认为这是上文提到的人是多种差而非单一种差划分之外的另一个否定理由。在他看来,既然质形复合物由形式和质料两个部分组成,极力在定义中排除质料是徒劳无功的。如我们在上文简单提及的,后来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H2 中把柏拉图在《泰阿泰德》中讨论“差异”理解为形式,类比于原子论者的形状、位置和次序的质形复合物中的形式的“差异”。当然,对柏拉图完全罗列元素的说法,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发展,毕竟,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他强调定义中必须包含对质料的描述,他给出的例子有灵魂、房屋、斧子、锯等,对灵魂下定义需要提及潜在的躯体,对房屋下定义需要提及砖瓦,对斧子和锯下定义需要提及铁,这种质形复合定义在《物理学》《论灵魂》《论动物部分》《论天》等文本中都有讨论和应用。因此,亚里士多德的质形复合定义,其实在柏拉图定义理论中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论准备。
四、结束语
苏格拉底是开创定义理论的哲人,柏拉图完全继承了老师对归纳论证和普遍定义的追求,并在这一领域有了长足的发展,无论是在定义对象还是定义方式上,都为亚里士多德后来进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首先,在定义对象上,他对苏格拉底提出的“是什么”的问题进行了发展,指出“是什么”就是理念或种,就是个别事物或特殊事例的集合或类或典型;并对由元素构成的复合物也进行了定义尝试,或者说,ειδο /ιδεα 既指善、正义、知识、德性这样的单纯的类概念,也包括人、石头、马车这样的复合物概念。在定义方式上,提出多次进行的二分法定义,给出属加种差的定义方式,并提出对后世有极大影响的“人是两足动物”定义;对复合物也进行了专门的讨论,只是,其定义方式究竟是全部罗列元素还是描述路径和差异还是其他,并没有明确结论。亚里士多德后来发展出庞大的定义理论体系,都是在柏拉图定义理论的基础上发展的。亚里士多德也从“是什么”开始讨论,但他进一步给出“本质”概念,认为定义就是对本质的描述,在逻辑学著作尤其《后分析篇》II 卷和《论题篇》VI 卷中详细讨论了属加种差的分类法定义,肯定了这种定义中属的重要性,只是在《形而上学》Z12 中又强调了种差的重要性,还对“人是两足动物”这一定义进行了反思;对于柏拉图提出的元素与路径的可知的复合物,亚里士多德用了质料和形式的普遍的复合物来表示,并进一步明确,对这样的对象,其定义既要提及形式,又要提及质料,是由现实的形式和潜在的质料构成的。一句话,亚里士多德的定义理论是在柏拉图的定义理论基础上发展和深化的,柏拉图的真知灼见都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了肯定,并最终有了非常合理的结论,二人是一脉相承的。
注释:
①柏拉图.柏拉图对话集[M].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参考《形而上学》的希腊文本:W JAEGER.Aristotelis Metaphysica[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个别字词的翻译有修改。
②柏拉图.柏拉图对话集[M].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参考的希腊文本是E A DUKE,et al.Platonis Opera:Tomvs I [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个别字词的翻译有修改。
③柏拉图.柏拉图对话集[M].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参考的希腊文本是IOANNES BURNET.Platonis Opera:Tomvs III [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03., 个别字词的翻译有修改。
④如无特殊说明,本文所引用的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文本为作者对希腊语版本的译文。本文《形而上学》《泰阿泰德》《理想国》等文本标出相应译本的标注编码。
⑤柏拉图.泰阿泰德[M].詹文杰,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参考的希腊文本是E A DUKE,et al.Platonis Opera:Tomvs I [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英文本是JOHN M COOPER,etal.Plato:Complete Works[M].Indianapolis/Cambridge: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1997.。个别词句的翻译有修订。
⑦不过,在笔者看来,柏拉图除了提出“人是两足动物”这样的定义,也提出一种描述的方式:如果你掌握了一个东西区别于其他东西的差异,那么,就像某些人说的,你就掌握了它的描述。但是,如果你把握到的是某种共性,那么你的描述就会属于全体具有该共性的东西(《泰阿泰德》208d)。这段话表示,描述或者是对差异的,或者是对共性的,只是这差异和共性究竟是什么关系,我们不得而知。只是,亚里士多德后来的“种差”也是用了διαφορα,并强调种和属是一种共性。因此,我们不知道种是属加种差的说法有没有受到这段话的影响。
⑧希腊文本参见(古希腊文影印本)伊曼努尔·贝克,等.Aristotelis Opera(《亚里士多德全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7.;英译本参见JONATHAN BARNES.The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M].Princeton/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汉译参考亚里士多德.论动物部分[M].崔延强,译//苗力田.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五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引文有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