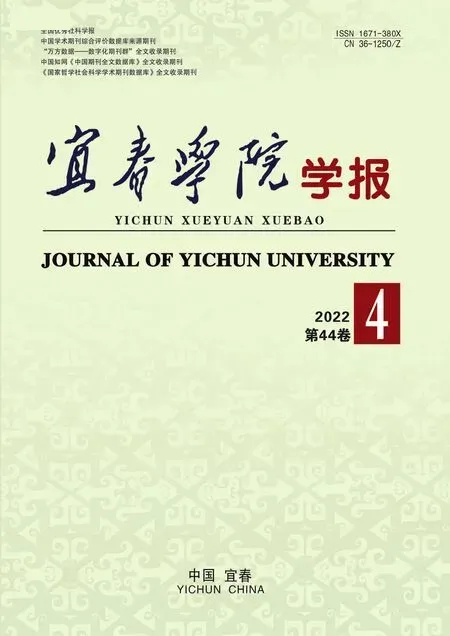何为译:翻译定义的嬗变与走向
皮伟男,蓝红军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高级翻译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0)
“何为译”“译何为”“如何译”“译如何”等四个问题勾勒出了翻译研究广阔的疆域。而“何为译”则是翻译研究最基本的问题,是翻译研究的逻辑起点,“是对翻译研究元理论的思考”,[1]对该问题的不断追问能帮助翻译研究者对翻译研究的问题域有一个逐渐清晰的认识。通过对古今中外的翻译定义做爬梳整理,笔者发现翻译研究问题域的拓展也始终伴随着翻译定义的更新。
翻译定义具有历史性,因此我们需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一核心概念。古往今来,许多翻译实践者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对“何为译”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有些见解在翻译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例如“翻译就是媒婆”等;同时也有许多哲学家和翻译研究者从多角度考察翻译并对翻译下了定义。但是现阶段大部分翻译现象无法从现有的翻译理论中得到解释,现有的翻译定义也始终无法囊括所有的翻译活动,无法涵盖现有翻译活动的内涵及外延,出现了翻译定义和翻译活动的逻辑不自洽之处。谢天振[2]呼吁学者结合当下的历史语境对翻译进行重新定位和定义。胡开宝、[3]蓝红军、[4]穆雷、邹兵[5]以及仲伟合[6]等学者也响应了翻译研究领军学者的号召从新的角度对翻译现实做出理论上的回应,对翻译定义进行了思考。然而,自那时起,五年已经过去了,科技迅速发展,AI+时代已经来临,新的翻译现象和活动层出不穷,机器翻译的质量出现了质的飞跃,越来越多的人在面对跨语障碍时会选择诉诸机器翻译,“2018年欧洲语言行业协会(ELIA)的一项调查显示,来自55个国家回复调查的1200人都强调2018年有超过50%的公司以及语言专家声称使用了机器翻译”。[7](P1)相应地,翻译研究也已经是另一番风景,翻译研究的信息化程度正在不断加深。因此,站在翻译新时代来临的起点上,我们有必要对古今中外的翻译定义做一次爬梳整理,理清翻译定义发展的脉络,并试图回答未来翻译定义发展的问题。
侯林平[8]将翻译定义分为传统语文学研究阶段的翻译定义、现代语言学研究阶段的翻译定义、当代多学科研究阶段的翻译定义等三类。该分类方式主要是从历时的角度根据翻译研究范式对翻译定义进行分类。蓝红军[4]在总结了前人从翻译的形态和功能等二维视角进行翻译定义的基础上从发生维的角度进行翻译定义的第三维思考,该分类方式具有十足的创新性。吴长青[9]认为翻译定义经历了附着于语言的翻译定义阶段、翻译定义的文化转向阶段、哲学视角下的翻译定义阶段以及翻译定义的开放包容阶段等四个阶段。然而这一分类有模糊和混乱之处。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是在解构主义思潮风靡的学术背景下出现的,吕俊认为“由于解构主义思潮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解构、语言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破除,文学研究和翻译研究中的文本结构与语言研究让位给了话语研究,让位给了文学文本和翻译文本产生过程的研究”,[10](P94)而解构主义本身就是以德里达为代表的一种对西方形而上传统进行反叛的哲学思潮,所以将翻译定义分为文化转向阶段和哲学视角下的翻译定义阶段有重合之处。向鹏根据思想特征将翻译思想分为了传统翻译思想、现代主义翻译思想以及后现代主义翻译思想等三类。[11]所以本文拟借用向鹏的分类,根据定义的思想特征将翻译定义分为以实践为导向的传统翻译思想的翻译定义、现代主义翻译思想的翻译定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翻译思想的翻译定义。
一、传统翻译思想的翻译定义
向鹏将传统翻译思想定义为:不论古今中外,凡是那些没有明显学科意识和理论意识的经验式和感悟式的的翻译思想皆为传统翻译思想。[11](P103)
下定义指描述一个概念。在传统翻译理论时期,中国的古典典籍中有许多零星式、片段式关于翻译定义的叙述,这些定义带有朴素的学理化特征,认为翻译就是“传”或“易”,即传达、传递异族语的活动(的人),例如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言部》中写道:“译,传四夷之语者”,[12](P148)孔颖达疏曰:“通传北方语官,谓之曰译者。译,陈也,谓陈说外内之言”,[13](P3)唐朝的贾公彦在《周礼义疏》中也提到:“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14](P1)宋朝初年的高僧赞宁总结译经理论并主持编纂了《宋高僧传》,在这部书中他写道:“译之言易也,谓以所有易所无也。”[15](P31)
古今中外还有一些特殊的翻译定义在译史中发出了耀眼的光芒,广为人们熟悉,那就是翻译比喻,例如“翻译就是戴着镣铐跳舞”,将译者比作“仆人”等。谭载喜从理论层面将翻译比喻作为一个专门的领域进行全面、系统地考察和研究,将翻译比喻分成了绘画、雕刻类、音乐、表演类、桥梁、媒婆类、奴隶、镣铐类、叛逆、投胎转世类、商人、乞丐类、酒水、味觉类、动物、果实、器具类、竞赛、游戏类以及比喻本身及其他类等十类。[16]
下定义最常用及最具代表性的方法就是种概念的实质定义,即用属加种差的方法,也就是把某一概念包含在它的属概念中,并揭示它与同一个属概念下其他种概念之间的差别。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编写的《形式逻辑》,“下定义必须用明确的概念。一是要求下定义必须用概念;二是要求下定义的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必须是明确的。违反这条规则所犯的逻辑错误,常见的有‘用比喻代替定义’和‘定义模糊不清’两种”,[17](P38)因此以上的翻译比喻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定义。但是这些翻译比喻使人们认识到“翻译在本质上是一种具有多面特性的活动”,[16]翻译并不存在一个唯一确定、形而上的本质,因此也不存在一个“非此即彼”的翻译定义,人们可以从多元视角来考察翻译并据此下翻译定义,以加深我们对“何为译”的认识。
我们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来谈论传统翻译理论时期的翻译定义,要站在历史语境中看待这些朴素的翻译定义以及翻译比喻。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出于与周边国家沟通交流的现实需要出现了译者官职,于是古典典籍中也留下了古人对“何为译”阐发的粗浅、简单的认识,且与周边国家民族交流大多是口头翻译活动,所以对翻译下的定义大多出现了“传”“易”以及“陈说”等语汇。中国翻译有两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就是东汉末年到宋朝1100多年辉煌的佛经翻译。在这期间,有的译经家也留下了关于翻译定义的思考痕迹,但是佛经翻译时期大多数译经家都是基于自己的佛经翻译实践留下了关于“如何译”,即翻译方法以及个人在翻译时遇到的问题进行的主观感悟式的探讨,例如支谦的《法句经序》、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玄奘的“五不翻”以及彦琮的《辩证论》等。佛经翻译在宋朝因为政策而走向衰亡,直到明末清初因西学东渐中国才迎来了第二次翻译高潮。在这次高潮中,最著名的人物当属徐光启,在意识到翻译的重要性后,他发出了“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的时代最强音。然而,他关注的是“译何为”,道出了翻译的功用和目的,也没有对“何为译”留下自己的思考。第二次翻译高潮的第二波是在清末民初出现的,那时以梁启超、严复等为代表的仁人志士为了救亡图存而翻译了大量的西书,这也拉开了中国世俗文学翻译的序幕,也是在这时中国才出现了大量的翻译比喻,因为“文学翻译有如文学创作,是一种比其他翻译类型如宗教、科技翻译都更需要创意、更需要使用形象语言的翻译,文学翻译家们既然更需要并更擅长用诗的、形象的语言来从事翻译,也自然更能使用诗的、形象的语言来谈论翻译”。[16]然而,这一时期人们关注的也是“译何为”,而不是“何为译”,“翻译之用也是当时学者们对其他翻译问题的思考和研讨的起点所在”。[18](P65)总的来说,在传统翻译理论时期的中国,由于翻译都是为了政治和社会服务,人们更注重实用而不注重概念,所以关于“如何译”以及“译何为”的探讨占了主流,缺少了对“译为何”的哲学性思辨。
二、现代主义翻译思想的翻译定义
传统翻译理论时期,翻译没有成体系的理论,缺乏翻译本体意识、翻译研究意识以及翻译研究方法意识,因此翻译一直处于前学科时期,不过这一局面在20世纪50年代结构主义语言学发展起来后就得到了改善。向鹏将现代主义翻译思想定义为:“现代主义翻译思想是对传统翻译思想的反叛和发展,它力图让翻译研究摆脱传统经验式、感悟式和碎片化的形态,让翻译研究走上理论化、系统化的科学发展道路。”[11](P109)结构主义语言视角下的翻译定义最具有代表性,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认知视角下的翻译定义较结构主义语言视角下的翻译定义有所突破,避免了后者定义的缺陷,但却少有学者进行探讨,所以在此,笔者将以结构主义语言学、认知语言学以及跨学科视角下的翻译定义来进行探讨。
(一)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的翻译定义
翻译研究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作用下走上了“语言转向”,许多语言学家也据此下了翻译定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奈达(Eugene Nida)、卡特福德(John Catford)以及豪斯(Juliane House)等人,这些人对翻译下的定义也广为人们所熟悉,例如:
1.翻译是把一种语言中的篇章材料用另一种语言中等值的篇章材料加以代替。[19](P20)
2.翻译就是在接受语中复制出与原语信息最贴切与自然的对等物,首先就语义而言,再者就风格而言。[20](P12)
3.翻译就是用语义及语用对等的译语文本对原语文本的代替。[21](P20)
4.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即话语)在保持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为另外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22](P4)
5.什么是翻译?通常来说,虽然并不总是如此,就是把原文作者在一个文本中所想表达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23](P5)
在结构主义语言学推动下,翻译开始走向了学科化与科学化的道路,使翻译研究拜托了传统翻译理论时期主观式和经验式的弊病。而且,也是在这一时期,学界也有了翻译本体意识,开始思考“何为译”,不再仅仅就宗教典籍翻译或者文学翻译而谈论翻译的功用与方法,所以这一时期的翻译定义相较传统翻译理论时期的翻译定义更为客观与学理化。
但是结构主义语言学视角下的翻译定义也有其缺陷之处。首先,结构主义语言学只关注语言内部,认为意义具有确定性,认为翻译就是对一种语言进行解码再用另一种语言进行编码的活动,翻译可以达到等值的效果。所以纵观以上翻译定义,几乎都以寻找对等为中心,虽然表述不同,但都传达出了同一个中心思想:“翻译是将源语文本转换为意义对等的目的语文本。”[4]但是翻译并不是在不受外界环境干扰的真空中发生的,不只是单纯的语言解码和编码的操作,而是一种具有动态生成性的复杂社会活动。既然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那就肯定会受到意识形态、权力、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因此,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的翻译研究后来受到了来自文化学派翻译研究的抨击。再者,纵观以上的翻译定义,我们会发现,译者一直是处于缺席的状态。结构主义语言范式的翻译研究派认为语言具有共性,一种语言能够表达的内容另一种语言也能够表达,因此“任何人只要遵循语言的规律,制定出语言转换的规则,就能做好翻译,甚至机器都可以取代人”,[24]最终译者丧失了其主体性。翻译作为社会活动离不开人的参与,即便是机器翻译越来越受到人们青睐的今天,译后编辑也需要人的参与。但是结构主义语言学视角下的翻译定义人为地忽视译者的存在而造成了长期译者的隐身,导致了译者地位的底下,最终受到了解构主义的抨击。
(二)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翻译定义
以往的学者往往只停留在对结构主义语言学视角下的翻译定义进行探讨,而忽视了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翻译定义。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翻译定义强调“对等”,而忽视了如何做到“对等”,这一点,认知观的翻译定义给出了答案。
1.翻译是解决问题和选择策略的行为。[25](P19)
2.翻译是基于知识的决策行为。[26](P187)
3.翻译是一个推理以及决策的交际行为。[27](P8)
认知观的翻译定义没有突出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以上定义的进步之处在于道出了翻译不仅仅是语言转换的问题,而是一个要根据遇到的问题进而根据知识选择相应策略的行为。在做翻译时,每位译者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不仅仅是语言对等上的问题,还包括文化问题、相关垂直领域知识的问题、意识形态的问题等等,不一而足,因此译者要根据遇到的具体问题来选择解决问题的策略。
(三)跨学科视角下的翻译定义
有学者(威尔斯)认为“翻译理论史实际上大致相当于对‘翻译’这个词的多义性的漫长争战”。[28](P19)20世纪80年代后越来越多其他学科的学者加入到了这场漫长的争战当中从他们各自学科的角度来考察翻译、研究翻译,表征出对翻译进行多元化的理解,于是出现了翻译的多学科定义,推动了翻译定义的繁荣发展。Sager创造性地从符号学地角度对翻译进行定义,认为翻译就是“用其他语言对言语符号的解读”。[29](P182)蓝红军站在翻译作为语言服务的立场上从发生学的角度将翻译定义为“为跨语信息传播与跨文化交流过程中遭遇异语符号理解与表达障碍的人们提供的语言符号转换与阐释服务”。[4](P29)李瑞林将翻译定义为“以知情意为内容、以语言为媒介、以认知为途径、以求真为导向的动态社会心理过程,旨在协调差异,传通信息,建构关系”。该定义是一种综合观,将翻译的“属”定位在“社会心理过程”,还道出了实现翻译的途径,即如何做翻译。还有值得称道的一点就是该定义将翻译的功用也纳入其中,翻译除了传递信息外,还能协调不同文化和种族之间的差异,最终能建构人与人、文化与文化、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实现和平与发展。
除了结构主义语言学、认知观以及跨学科视角下的翻译定义外,以弗米尔、诺德等为代表的德国目的论学派的翻译定义,以图里为代表的描写翻译学派的翻译定义也属于这一类,笔者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三、后现代主义翻译思想的翻译定义
上文我们讨论了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翻译研究及其定义的不足之处。后来解构主义以摧枯拉朽之势将翻译研究从机械语言转换的桎梏中释放出来,将文化纳入到翻译研究当中,于是发生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研究者的目光从语言内部转向到了文本之外,“从文本的语言分析,转向了与文本传播有关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环境”,[30]于是新的翻译定义出现了。勒菲弗尔认为“翻译不仅是语言层次上的转换,更是译者对原作所进行的文化层面的改写”。[29](P181)王克非将翻译定义为“译者将一种语言文字所蕴含的意思换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述出来的文化活动”。[31]这一定义除了将翻译的“属”确定为“文化活动”外,还有一个进步之处就是突出了译者的主体性,让译者“显身”。除此之外,该定义没有像结构主义语言的翻译定义一样强调“对等”这种时常对译者而言可望而不可及的要求。
四、对未来翻译定义的展望:技术及跨学科导向
如上文所述,定义旨在揭示一个事物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而概念的形成是人类对具体的事物进行抽象认识的结果,下定义会经历一个从“本体”到“认识”再到“语言”的过程,因此定义的更新迭代会落后于事物内涵和外延的改变。所以对未来翻译定义的展望首先要明晰现阶段翻译定义无法囊括的翻译活动以及预测未来翻译活动的走向。
上文已提到,翻译研究历经了“语言转向”和“文化转向”,每次转向都增进了人们对翻译本质的多维认识,并且催生出了新的翻译定义。不过Chan Sin-wai认为“翻译一直都是以传统的方式进行定义的,即基于人们对翻译目标、翻译性质、翻译实践以及与翻译相关学科的理解,这催生出了许多翻译定义,不过这些定义要不就是太笼统,要不就是植根于技术出现前人们的观念”。[32](P268)随着技术的突飞猛进,近几年翻译技术成为了热点,越来越多的科研机构、高校以及科技公司成为了机器翻译、人机交互翻译开发大军中的一员,这对翻译实践以及翻译研究都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许多学者认为翻译的“技术转向”已经来临。张成智、王华树将翻译技术转向定义为“指随着信息技术、计算语言学、术语学等学科发展,翻译实践发生了从纯人工翻译到人工翻译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的变化,从而引发翻译理论研究的变革”。[33]在1949年机器翻译出现之前,翻译仅仅是由人(译者)完成的,翻译的主体是人(译者),不过“现在所有的翻译几乎都是在计算机的辅助下的翻译行为”;[34]口译的模式也发生了改变,“作为强化或支持译员的AI口译辅助技术也已在国内外会议上初露锋芒”。[35]现在人工翻译、机器翻译和机辅翻译三者并驾齐驱。在翻译语言服务本质日益凸显的今天,翻译技术的出现与人们追求效率的目标不谋而合。翻译仅仅由人(译者)主导的本质已经发生了改变,因此慢慢的在翻译定义中技术的主体性会凸显出来。Chan Sin-wai将翻译定义为“在技术的帮助下将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32](P269)不过我们还需要明确一点,那就是人(译者)的作用绝不会被代替,因为翻译作为一项有意识形态、权力、文化等因素参与的社会性活动没有发生改变。即便现在机器翻译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广,但是人(译员)依旧是翻译产品的最终责任人,机器无法承担(民事)责任。因此,技术会加入到翻译定义当中,但是人(译者)的作用依旧是无法代替的。
第二点与翻译定义中的行为主体“译者”相关。如上文所述,有学者在翻译定义中加入了译者,让译者“显身”,提高了译者的地位。传统上,人们都会认为“翻译是一种刻意习得的技能,主要和专业的和内行的方式联系在一起”,[36](P19)因此人们也常常认为译者具有很强的专业性、职业性,甚至有学者认为“所有的译员都具有优秀的语言能力,优异的写作技能以及对专业性的东西充满兴趣”,[37](P87)不过人们对译者都具有“专业性”的观念正慢慢被打破。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充满着大量的“非专业性翻译(non-professional translation)”活动。非专业性翻译活动的主体都“没有接受过特别教育或/和翻译训练”,[38](P7)非专业性翻译主要包括“众包翻译”和“在线合作翻译”。现在非专业性翻译正逐渐侵蚀翻译的专业性,甚至包括文学翻译,因为“从文学文本到非洲非政府组织使用的医疗教育视频,几乎所有类型的文本都可以外包”。[36](P33)今后翻译活动有可能会越来越大众化,因此翻译定义中“译者”这一暗含“专业性”的主体可能会被普通大众弱化。
第三,翻译的跨学科性会进一步加强,这将拓展翻译活动和研究的边界,因此越来越多其他学科会给翻译下相应的定义。上文我们已经讨论了多学科视角下的翻译定义。翻译何以会出现这么多学科视角下的定义?这是因为翻译学究其本质就是一个综合性学科。未来翻译研究会进一步打破学科间的藩篱,与工科、法学等学科进行交叉,新的翻译定义也会相应出现。Chan Sin-wai讨论在翻译技术的作用下,翻译匠会成长成技术工作者,并论证机辅翻译人员的数量会急剧增加,而且随着翻译的职业化今后会有证书证明译者的翻译技术能力。[32](P270)以往的翻译工作者、翻译研究人员大多都是文科出身,技术化也对译者、翻译研究学者带了不小的挑战。不过在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背景下,翻译与工科的交叉融合也与当前新文科建设需求不谋而合。随着时代的发展,翻译与工科的结合会带来译者身份的改变,带来翻译内涵和外延的改变,因此也会创造出新的翻译定义。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何恩培在2021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人工智能与暑期工作坊中提到区块链技术能推动翻译成果IP化、价值化,译者第一次创译成果能成为一个IP,后人如若要使用则需要付费。因此今后翻译会与知识产权法形成交叉,进一步推动翻译研究的边界,推动翻译定义的出新。
“一个定义只能揭示事物某个或某些方面的本质,并不能完整地反映具体事物的全部本质”,[17](P42)所以目前还没有也不需要一个能一统天下的翻译定义。翻译活动持续了数千年,翻译研究也持续了数十年,无数译者和翻译研究者从各自的角度来考察翻译并据此下定义,以达到对“何为译”更深入更全面的认识。在传统翻译理论时期,人们对“何为译”有一个朴素的认识,并通过比喻来表达自己的见解;在现代翻译理论时期,翻译定义走上了学理化以及客观化的道路,但也有其缺陷;后来在解构主义的作用下,人们从外部环境来审视翻译,贡献了更全面的翻译定义,推动翻译定义走向繁荣;在未来翻译技术和新文科学科交叉的催化下,会有跟上时代发展的翻译定义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