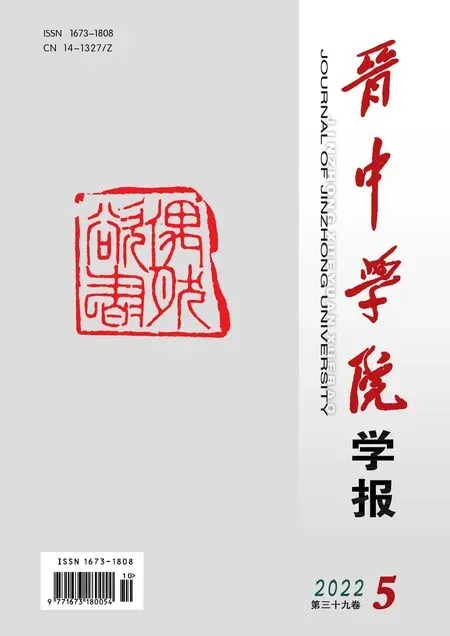儒家“天人合一”观念的确立路径及基本内涵
郭 鹏,常馨元
(1.山西大学文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2.伯明翰大学政府与社会学院,伯明翰 B152TN)
“天人合一”观念,不只是儒家,道家以及其他诸子也都曾阐发过,不过阐发的角度与阐述目的均有不同。“天人合一”是在古代“天人感应”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而成的。从“天人感应”到“天人合一”,其中蕴含着儒家对原始的宇宙认识论进行人文化解读的意旨。即是说,儒家对“天人感应”进行了人文化解读,并将其升华为以人文社会理念为核心的“天人合一”理念。这一演化过程充分彰显了儒家重视社会礼义秩序构建和主体人格塑造的理论关切。这一过程,同时也是儒家提高自身理论尊严与权威,并借以继承三代文明,打通当代与古代的务实的努力。
一、“天人感应”与“天人合一”观念的由来
“天人感应”之说起源很早。先秦典籍中具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述。许多记述也涉及到了早期的感应论思想。如《国语·周语》载,周幽王二年,三川皆震,史官伯阳父云:“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柔,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1]26伯阳父以自然现象解读社会发展的前景,从阴阳消长的角度阐发对自然与社会的认识,其基本思路就是早期的感应论思想。而《吕氏春秋·应同》所谓“类固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鼓宫而宫动,鼓角而角动。平地注水,水流湿;均薪施火,火就燥。山云草莽,水云鱼鳞,旱云烟火,雨云水波,无不皆类其所生以示人”[2]251,也是从“水流湿”“火就燥”的自然现象中总结出了“类固相召,气同则合”的道理。先秦典籍中类似的内容很多。应该说,早期的感应论源自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关联性解读。“类固相召,气同则合”是认识基础,而与人类社会的联属观照则是根本的思维特点。这其中蕴含着的就是以自然理性解释社会理性,甚至是以自然理性替代社会理性的阐发目的。在这个理论演进的过程中,阴阳家以五行始终解释社会发展规律的述理方式很值得关注。
《吕氏春秋·应同》有云:
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2]251
这里所说,显然是以阴阳家五行相生相克的自然逻辑去解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目的正在于释读过去的历史以确定现实和未来的合理性。同样,先秦典籍中也保存着许多反映感应论的观点,但却将关注重心移至社会演化视角。如果说,《周易·乾卦·文言》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3]17还是原始感应论的话,那么,《尚书·洪范》的“曰肃,时雨若;曰义,时旸若;曰晰,时燠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曰咎征,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旸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风若”[4]320-321,则已然表现出了将自然现象与社会政治相联系的述理倾向。到《礼记·中庸》就明确地讲:“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5]1449这实际上就是儒家对古代感应论思想的一种延承与发展。
实际上,《尚书·泰誓》中就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4]277的观点,将“民视”“民听”的地位上升到“天”的高度,借以提高“民”的政治权威和文化地位。以“祖述尧舜,宪章文武”[5]1459为己任,旨在继承三代文化的儒家以此出发,一方面吸取了早期感应论或天人感应论的思想,另一方面则将人类社会的政治文化举措与之对应,树立了既合乎自然理性,又合乎人文理性的社会规则。反映这些规则的就是儒家构建的思想与社会行为的规则体系。
二、儒家对“天人感应”的改造和“天人合一”观念的确立
上文曾说过,先秦感应论资料很多,要么对应人的吉凶休咎,要么对应国家的否泰前景,总之是出于将自然规律与个人遭际和社会发展间的关系置于类同思维的前提下考虑:前者与后者同质,适应于同样的规则。因自然规律存在难以索解或无法索解的问题,而使得这种思维方式在解释社会规律时充满着不可知的神秘性和人在规律面前的无力感。规律成为一种必须遵守的权力。那么人的作用呢?人的思想、情性和实际作为在自然——社会规律面前真的就毫无作用吗?这一点,儒家就能充分地强调人的作用,强调人在遵守自然与社会规律时的积极意义。儒家认为只要人有德行,就能获得扶助,就能将不利的规律转化为对自己有利的规律。重视人的因素,尤其是人的德行的能动作用,是原始的天人感应向人文化的天人合一过渡的重要节点。所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4]452“黍稷非馨,明德惟馨”[4]491就是将人的德行看作是天道自然规律影响人类社会的最重要依据。感应中道德指标的注入,是天人合一观念形成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一步。儒家沿用的感应论,也因这种德性指标的存在而具有了“惟德是辅”的意涵。这为后来以德性内涵为核心构建天人合一思想体系做好了充分的铺垫。
儒家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们对自然的观照细致入理,又能直接比附于承载着人文社会理念的“礼”。这样就可以在解析自然现象时将其对应为“礼”,以便导向对“德”的强调。如儒家“三礼”之一的《礼记》,其中的《月令》就颇具典型意义。它将一年分为四季,每季又分为孟、仲、季来阐述。其阐述又先罗列自然现象,进而对社会人事予以规范,其规范又以规范君王的行止为纲领。这就是“礼”的思维方式的构建逻辑,如在述及孟春时,《月令》云:
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大蔟。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鸿雁来。天子居青阳左个。乘鸾路,驾仓龙,载青旗,衣青衣,服仓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齐。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还反,赏公卿诸侯大夫于朝。[5]442-458......是月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王命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经术,善相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道,民必躬亲之,田事既饬。先定准直,农乃不惑。是月也,命乐正入学习舞,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毋聚大众,毋置城郭,掩骼埋胔。是月也,不可以称兵,称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从我始。毋变天之道,毋绝地之理,毋乱人之纪。[5]463-466
这里,既详细罗列了天象、物候的特征,又从对“天子”的要求开始,阐发了对于社会生活(包括礼义制度和政治措施)的具体要求。如“布农事”“田舍东郊”“修封疆”“审端经术”以及“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等等,这些对人事的规范,儒家认为是天地自然之道的要求,是以德行反馈天道的表现形式。所谓“毋变天之道,毋绝地之理,毋乱人之纪”云云,就是将天、地、人统一整合成一个带有规范性的思维结构,这个思维结构的核心就是“天之道”、“地之理”与“人之纪”。其中的“人之际”实际是儒家化的、蕴含着德性内涵的“仁”及“仁政”思想。可以说,善于继承、汲取前代文明成果的儒家总是能够将自身的理论主张与价值观融入旧的思想观念之中以发挥作用。这就如同西周继承了夏商文化,尤其是商文化的祭典形式,又将其完全听从“天命”的传统改造为以德为先一样。孔子说“周监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6]36就是以德从周,跟从周的人本化的礼乐文化。
在思想传统上能够使得儒家顺应时代,并借助国家权力确立儒家式的“天人合一”观念的是董仲舒。与《礼记·月令》的思维方式一样,董仲舒进而明言“天不变,道亦不变”,[7]320这倒不是在提高“天”的权威,实际上是借助无须争论的“天”的意志以提升儒家之道的权威与尊严。从这种意在提升儒家之道的述理策略出发,董仲舒倡言“天道”,将儒家的理论和思想升至“天道”的地位。他在《天人三策》中说:“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遣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习,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有效者也。”[7]304“天心仁爱”“天道”的禀赋可明。“人道”受制于“天道”,而“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则人事可为,治国者必须“强勉学习”“强勉行道”,这样,就可在“天道”的制约统辖之下开辟出腾挪的空间。可见,儒家“天人合一”不是消极地顺从所谓“天道”,而是积极地跟从,是“强勉”为善、“强勉”为仁,这样的“天道”,就是具有绝对意志的儒家之道。即使是占卜这类诉求“天”垂训和指引的行为,儒家都绝非被动。夏商周都有卜筮,儒家也不反对,但如同董仲舒的“强勉”,儒家的卜筮观也充斥着诉诸人的德行的意味。《汉书·艺文志》在论及卜筮文献时说的“人失常则訞兴,人无衅焉訞不作。故曰:德胜不祥,义厌不惠”。[8]1773消极的卜筮来源于人的“失常”,但卜筮的结果是可以通过“德”“义”去改变的。前提是人本身在德行方面有好的作为,做到“无衅”。儒家的听从天命和天人合一一直都有德行的贯穿,这大不同于消极被动地在对天人感应和“天命”的完全依从中趋利避害。儒家构建的“天人合一”思维模式和基本观念始终都包含着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包含着对人本身尤其是人的德行的强调。“天道”与“人道”在德行基点上绾合一处:“天”是德行的“天”,“人”是顺应道义至善的“人”——由此构建的“天人合一”观念,汇成滔滔汩汩的历史洪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三、“天人合一”观念体现的儒家智慧
儒家一直比较注重“和”。所谓“和”,就是协调各种对立关系,在不失原则的基础上找到利益的共同点,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发展。“和”观念的提出,也是在“格物”的基础之上总结出来的。所谓“声—无听,色—无文,味—无果,物—无讲”,[1]471就是看到了没有对立事物的相辅相成作用,是不会有客体存在的协调、均衡和发展。《国语·郑语》中史伯所说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1]470,其实也是强调对立统一的意思。这种思想后来被儒家继承,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6]179便是就人应该具备协调各种人际关系的素质与能力而言的。儒家认为人应该能听取不同的意见,也能谋求更多的人的理解和支持。在面对天道自然时,儒家能够发挥这种“和”的理念,能够在坚持自身道义追求的同时极大限度地顺应客观普遍规律。儒家顺应规律并能坚守自身立场的灵活态度也与他们注重顺应自然的生生之道并能在坚持自身德性原则的基础上谋求“通变”的思想紧密相关。[3]294可以说,因重“和”而讲“通变”是源于天人合一观念的一种理论发扬,它成为一种理论和实践的智慧,这种智慧使得天人合一观念充满了灵动性,也使儒家思想具备了因应环境得以长久发展的内在活力。
我们分析天人合一观念的由来时曾说过,儒家将自己注重德行的理论关切羼入其中,改变了这个观念本身的消极性,而使社会人事能够在德行前提下发挥更大的作用。其实这种改变,体现的正是儒家的理论与实践智慧。孔子的时代,礼崩乐坏,所谓“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9]178在这样的境况下,孔子始终自信,对未来人类社会的文明始终抱有自信的态度。他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6]113那种自信豪迈,隔纸可见。春秋时期,异端思想甚嚣尘上,对孔子倡导的三代文明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孔子愤慨地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矣。”[6]20他要求儒家研究其他诸子,以便提高自身的理论素质和对应能力。我们知道,孔子认为行胜于言,尤其反对“御人以口给”[6]56的“巧言令色”。[6]4他用自己的切身行事作为表率而不去空骋口舌之辩。卫灵公问以军旅之事,孔子直接回答“未之学也”,[6]206随即便离开了卫国。他不屑于辩,而力求以切实的行为去化成天下。然而,到了孟子时代,天下悖乱更甚于孔子时代,“诸侯放恣,处士横议”的局面也更为严重。儒家受到其他学派的催迫也更为严峻,“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则归于墨”。[9]178
在如此的境况下,孟子一改孔子的做法,他投身到与其他学派的论辩之中,目的正在于捍卫儒家思想,为儒家争取文化上的制高点。但他也同孔子一样周游列国,与各国君主和辩士展开了激烈的论争。他以孔子反对的“巧言”据理力争,从不落下风,还往往使人无从辩驳。他口舌敏利,析理透辟,以辞锋之矫励和逻辑之精严慑服论敌,但究其根本,则在于他能养“浩然之气”。他不只是养自己的“浩然之气”,而是整个儒家的“浩然之气”。这就是孟子“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9]176的内理所在。经由孟子的改造,儒家不仅没有式微,而是进一步得到了壮大。至荀子时代,诸子间的相互攻讦更甚于孟子之时,形势的催迫使荀子明言:“君子必辩。”[10]70《荀子》一书中有许多长篇大论,其逻辑论证的气势与思维的缜密程度有逾于孟子,也更多地有了专题论文的性质。
从孔子不屑于辩,到孟子善于取譬为辩,再到荀子的专论之辩,儒家因应社会文化与舆论环境的自身调适机制得到了强化。在复杂而又险恶的文化舆论环境中,随着政治文化氛围的改变而不断调适着自身的理论,不断致力于捍卫自身的思想阵地。在儒家顺应时代文化并调适自身的过程中,秦王朝的打击对于儒家而言,可谓教训惨痛,但这却进一步促使儒家认识到获得最高权力这个“天”的支持与认可有多么的重要。因此,当汉文帝下令收集天下图书,表现出重视文化建设的态度之后,儒家谋求与权力之“天”合作就成了强烈的内在诉求。这个“天”必须在依循中改变,必须将其与自己的理论和思想糅合起来:既是为了宣化道义,也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至董仲舒,他终于以万言规模的《天人三策》而得到了汉武帝——这个“天”的采纳。
建元五年(公元前136)汉武帝下令设五经博士,从此儒家独尊的地位终于得到了确立。在儒家从诸子之一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顺应、依循环境并不懈地在顺应依循中坚持自己,这样的结果是无从出现的——这也就是《周易·系辞下》所说的“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3]300的道理。
四、“天人合一”观念的包容性与内涵的丰富性
上文曾说过,天人合一观念来源于古代原始的“天人感应”思想。而这种思想也被儒家以外的其他诸子所吸取,道家、法家、墨家等的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表露,尤其是阴阳家,可以说强化了“天人感应”对人间社会的主导意义。他们的五行相生相克论就是用自然理性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以天命观作为绝对意志,认为人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听从“天命”的安排。这种理论本身并没有太强的逻辑性,但其尊崇绝对的“天”的思路却被后来的权力系统所看重。秦王朝就以此来构建自己的历史哲学。到了汉代,同样因为大一统的政治文化需要,希图尊崇权威,服从大一统的政治及文化。那么,将王朝权威释读为天意,就成了可行的选择。已经对“天”做了道德改造的儒家式的天人合一理念就很容易与王朝合作,所以董仲舒的建议得到了采纳。因为王朝明白,运用这样的思想和理念,既能在历史维度上尊奉前朝正脉,又能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强化权力,维护政治文化的大一统。而儒家式的天人合一之所以能超出其他的天人合一,就在于它的包容。其天人合一的内在涵义,既可以找到道家、法家对绝对规律的顺服,也能寻绎出阴阳家、名家对规则秩序的崇奉。但天人合一的关键——道与德行,则源自儒家自己对三代文明的总结与发展。因此,天人合一作为古代思想发展的一个成果,其实是颇具集成性的。正因为它具有这样的集成性,它在思想史上就表现出了极强的理论活力。同时,因为儒家对天人合一理念做了德性的改造,其理念本身在具有包容性的同时,也具有了鲜明的德性色彩,有着其他诸子较为驳杂的天人合一观念所难以企及的严肃性与纯粹性。比如,董仲舒汲取阴阳家理论改造儒家,终于获得了王朝的认可,但阴阳家的思维方式和一些观点也会反噬着儒家思想本身,导致思想领域充斥着妄诞的天命论,甚至妄言天命,夸诞地以自然现象比附现实政治。这些都与早期天人感应还未完全完成儒家化有关。本身不谈天命的儒家在吸收天命论后产生了很强的排异反应,直至出现了谶纬神学,儒家自身的严肃性受到了冲击,其纯粹性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在这种局面下,儒家自身源自先秦儒学的作用便适时地发挥了出来。桓谭、尹敏、王充、张衡等等,都是如此。他们坚守了儒家的学术伦理,顶住了排异反应巨大的催迫,终于逐渐激浊扬清,使得儒学回归了“实事求是”的传统,而以儒学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也得到了极大的廓清。因此说,天人合一理念在儒家那里才得以理论化,才得以称之为理念——天人合一有包容性,是因为有儒家思想作为根基与基本矩矱。
儒家倡言“比德”,就是在观照外部世界时注重汲取其中的德性因素。《礼记·聘义》有云:“(孔子曰)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5]1670从中可见,孔子将玉直接比附于人的德行,君子应该以玉为鉴,积极颐养自身道德,像玉那样兼具十一种优秀品德。儒家的天人合一理念也是如此,人作为“三才”之一,只有不断从德性方面参天法地,才能犹如天地一样生生不息,才能既葆有积极进取的精神,又能有负载万物的仁厚。由“比德”意识生发,人面对天地自然的一切感受都带有道德性,都是伦理化的情感。由“比德”而来的这种情感化的发展,终于在古代文学乃至整个艺术领域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金谷园的山水,寄寓着抽身宦途的念想;兰亭的林木曲水,承载着疲于名利应对的愁思;陶潜之桃源与村烟,掩不住对世事的愤慨与无奈;谢客山景,蕴蓄着跳脱出尘网的意愿;江淹春绪,庾信秋情,无不蕴涵人间愁恼,无不以山水为知己,以自然为俦侣。摩诘竹林之啸,襄阳岘山之思,哪一个不是饱含人间情愫和人间情怀?米芾酷爱的怪石,王冕笔下的墨梅,又哪一个不是有着对世俗功利的拒斥;朱耷无目的幽鸟,板桥怪石似的手迹,也都充斥着对某些不可抗拒力量的逃避与叛逆......所有这些古代艺术的自然书写,都得力于天人合一的理念,也都得力于这个理念中的人间关切与德性内核。尤其是后来由王国维先生集其大成的意境论,完全可以说是古代天人合一理念在中国美学史上结出的最大、最重要,也最具民族性的硕果。
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天人合一理念在当代仍然具有积极的文化价值。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现代化科学技术的运用,使得人与自然之间,乃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充满着矛盾和对立。一方面是对环境无尽的攫取与破坏,一方面又是沉浸在利益纠葛中不能自拔。人口激增、环境恶化、资源短缺、气候变暖、灾害频发,人人似乎都陷入到普遍的焦虑之中,人类几乎难以改变的诸多世界性问题重重紧逼。作为“三才”中的一员,无视自然规律,任意掠夺资源,“天”“地”成为可以蔑视的存在,而人的各种欲望却在无限地膨胀......在这样严峻的问题视界之中,我们回望我国古代曾经发挥过巨大作用的天人合一理念,它流溢着对“天”“地”和人本身的充分尊重,荡漾着“三才”应协同发展的理性认知。天地间充斥着的是正气,自然是人永远的道义上的朋友。它们不应被遗忘,不应被冷落。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自强不息”,才能“厚德载物”、生生不息地使我们的文明延续下去——与天地友好,与自然和谐,“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3]105。天人合一带给我们的正是人类要实现永续发展的根本理路之所在。
——由刖者三逃季羔论儒家的仁与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