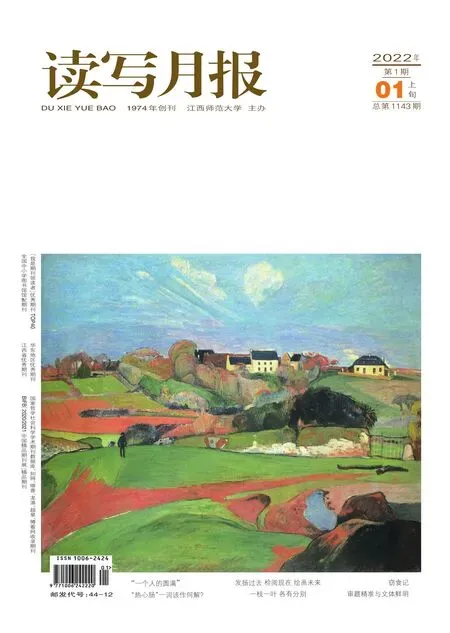“一个人的圆满”
——读《峨日朵雪峰之侧》
涂薇

峨日朵雪峰之侧
昌耀
这是我此刻仅能征服的高度了:
我小心地探出前额,
惊异于薄壁那边
朝向峨日朵之雪彷徨许久的太阳
正决然跃入一片引力无穷的
山海。石砾不时滑坡,
引动棕色深渊自上而下的一派嚣鸣,
像军旅远去的喊杀声。
我的指关节铆钉一样揳入巨石的罅隙
血滴,从撕裂的千层掌鞋底渗出。
啊,真渴望有一只雄鹰或雪豹与我为伍。
在锈蚀的岩壁,
但有一只小得可怜的蜘蛛
与我一同默享着这大自然赐予的
快慰。
1962 年8 月2日初稿
1983 年7 月27 日删定
这首诗是一位攀登者的自述,它看似激情豪壮,其实纹理细腻,几乎遍布全诗的隐喻则使其具有了纯粹的抽象性与某种精神的高度。
让我们从诗歌的标题开始。
“峨日朵雪峰之侧”,向我们指明了这位登山者所处的状态:他已然登上了属于祁连山脉的不出名的雪山“峨日朵”的侧边——用诗和哲学的语言来说,这是“在路上”:他已经出发,却尚未抵达。
全诗呈现了这位攀登者在攀爬过程中停滞的一个瞬间:他因为“惊异”而“探出前额”——他为什么要“停下来”?在停下的这个瞬间,他看见了什么?又想到了什么呢?
他停下来是因为“这是我此刻仅能征服的高度了”。“仅能”意为“我”已经达到了自己的极限,或者换一种说法,对于自我而言,“我”此刻正站在自己的生命之巅。
“此刻”是一个副词,它修饰限定“达到”,意思是“我”此刻正等于自己过去一切的总和,但并不等于“我”未来的总和:“峨日朵雪峰之侧”是“我”拼尽既有能量所能达到的一种极限,但它是“此刻”的“极限”,当“未来”到来,“我”仍有可能继续攀升。所以这是“无限”中的“有限”,是理性“自我”的一次评价与展望。
接下来这位攀登者便开始向我们描绘他在峨日朵雪峰之侧的所见所感。
“惊异”于太阳之决然跃入山海
“我小心地探出前额,
惊异于薄壁那边朝向峨日朵之雪彷徨许久的太阳正决然跃入一片引力无穷的
山海。”
让我们先来看看这“太阳”——
它朝向“峨日朵之雪”——这是一个向上的视角,说明此刻太阳的位置是朝下的,所以这是夕阳。
夕阳正仰望着雪峰峨日朵,并“彷徨许久”——因为它不想下坠,它想留在山巅。
但结果是“决然跃入”——夕阳坠入山谷,这是自然规律,是非如此不可。
强大的太阳没能守住留在峨日朵雪山之巅的梦,它最终选择了“顺应”。那迫使它屈服的力量是什么?
是“山海”的“无穷引力”。
“山海”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
“海”永远处于下位,而“山”是居于上位的——可见“山海”这个意象本身就充满了冲突与张力:什么样的“山”会如“海”一般呢?
是被俯视的群山,比如山谷——这再一次提示我们攀登者“此刻”已然“征服的高度”:即使不在巅峰,也足以“一览众山小”。
山海的“引力”也许便代表着“非如此不可”的一切世间法则,它不容置疑地要将一切向上之物拉下来,使之隐没于自己的怀抱。
这力量让“我”惊异——即使强悍如太阳,也不能避免被它拉下去的命运。
那么“我”呢?作为攀登者的“我”在这似乎难以战胜的向下的“引力”面前,将如何自处呢?
像铆钉一样揳入巨石的罅隙
在“太阳”决然跃入“山海”之后,“石砾不时滑坡,/引动棕色深渊自上而下的一派嚣鸣,/像军旅远去的喊杀声”——表面上,这里描写的似乎是太阳这个庞然大物的“决然跃入”引发的山石滚动,但末句“军旅”二字似乎在寓示着某种对抗与争斗。
谁在对抗?又为什么而对抗呢?
“我的指关节铆钉一样揳入巨石的罅隙。/血滴,从撕裂的千层掌鞋底渗出”,这应该是攀登者对自我状态的一种描绘,整个画面充满了力量感——既有主体的努力,更有客观环境带来的吃力感:为什么“我”要如此用力呢?
“我的指关节铆钉一样揳入巨石的罅隙”,这是一个竭尽全力将自己固定于山石的动作。为什么要固定住呢?当然是因为不愿坠入那“引力无穷的山海”——“我”作出了和“太阳”不同的选择:尽管同样面临“非如此不可”的山海,“我”却不愿意坠入,“我”要向上,要攀登,要登顶。
这正是对首句的一个回扣:“这是我此刻仅能征服的高度了”——“我”来到这里是为了“征服”,这注定了“我”将与“决然跃入”的太阳相背而行:“我”是一个叛逆者,要与那无穷的山海的“引力”交战——
“我”要抗拒引力向下的拉拽,朝着山峰的方向,决然向上。
而作为征服者的“我”,无疑为此付出了代价:“血滴,从撕裂的千层掌鞋底渗出”——当你选择与“非如此不可”的力量相抗,你就可能流汗、流泪、流血,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比如此刻的“我”,千层掌的鞋底已因用尽全力地攀登而撕裂,凌厉的石块割破了“我”的脚底——而“痛感”,正是一切叛逆者从肉体到心灵必然的体验。
流着血,将自己牢牢揳入此刻仅能征服的高度的“我”,在想些什么呢?
梦想中的雄鹰和现实里的蜘蛛
“啊,真渴望有一只雄鹰或雪豹与我为伍。/在锈蚀的岩壁”——“我”为什么渴望有一只雄鹰或雪豹?
雄鹰和雪豹是自由与力量的象征,也是生而属于雪山的生命。那么此刻,位于“峨日朵雪峰”之侧的“我”为什么会突然渴望起它们呢?
“渴望”意味着向往却未能拥有的状态:很明显,在“我”此刻仅能征服的高度——峨日朵雪峰之侧——并不曾出现过雄鹰与雪豹的身影。
它们是能够傲视群山的生命,所以山巅,才是雄鹰和雪豹应该出现之地。“我”对它们的“渴望”,既是对自由与力量的向往,更是对“未来”的畅想:如果有一天,“我”能够登上雪山之巅,那么雄鹰和雪豹就将成为“我”的伙伴吧。
只是此刻,“我”还“在路上”,那么“我”的视野里可能出现的同伴是什么呢?
“但有一只小得可怜的蜘蛛/与我一同默享着这大自然赐予的/快慰。”
在峨日朵雪峰之侧,与“我”为伴的是一只小得可怜的“蜘蛛”——它的“渺小”当然是得之于与雪山的对比,它同时也映衬出“我”的渺小:在伟大的自然面前,任何生命恐怕都是“渺小”而微不足道的。
但这“小”中也有“大”——他们都是试图登顶雪山的“征服者”,他们都是试图对抗“非如此不可”的“叛逆者”。某种意义上,他们也是坚定的梦想践行者——尽管“尚未抵达”,但大自然已经对他们有所赐予——
赐予了他们在山脚无所见而只有站在“此刻”的高度才能见到的壮景,比如太阳面向山海的“决然跃入”;赐予了他们牢牢站立于峨日朵雪峰之侧的征服的快意;赐予了他们彼此一个“一同默享”的伙伴——当你忍受着千层掌鞋底的撕裂、忍受着脚底流血的疼痛独自攀上峨日朵雪峰之侧后,你将遇见一位同道者、一位战友——他和你一样渺小、一样艰难,但你们能消解掉彼此的孤独——此刻你们静默无声,却拥有同样的快乐与欣慰:也许随着高度的增加,你能遇见越来越多的同伴呢。
这时一个疑问会出现:为什么诗人要让一只蜘蛛出现在这里?渺小的生命有无数,为什么在峨日朵雪峰之侧出现的必须是一只蜘蛛呢?
一个可能的答案是,在古老的文化中,人们认为蜘蛛是可以预兆吉祥的虫,并叫它“喜虫”——这预示着未来光明的蜘蛛,也饱含着诗人对自己、对一切向上的攀登者的祝福吧。
…………
在《峨日朵雪峰之侧》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奋力向上的人,他既是一位攀登者,更是一个“叛逆者”——他要对抗的力量甚至连太阳也无法战胜。但他克服着艰险,忍受着疼痛出发、上路,并终于登上了雪峰之侧——虽然他渴望登顶却尚未登顶,却在自己的现实中感受到了征服的快感,并愿意将更多的希望寄予未来——对于这样的一个人,这样一种人生,这样一类精神的本质,圣·埃克苏佩里也许会表述为:
“只有这样的人我感兴趣,他在登山时运动自己的肌肉,即使只登过一座山,他有了准备去了解今后所有的风景……我还要说一遍,当我说到山,意思是指让你被荆棘刺伤过,从悬崖跌下过,搬动石头流过汗,采过上面的花,最后在山顶迎着狂风呼吸过的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