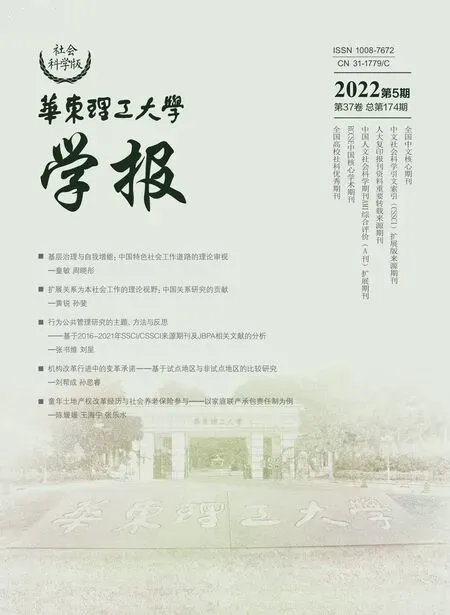基层治理与自我增能:中国特色社会工作道路的理论审视
文/童敏 周晓彤(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13 年民政部正式把社会工作与社区和社会组织并列提出“三社联动”以来,社会工作被视为我国社区基层治理的一支重要专业力量,逐渐得到社会的认可。特别是在党的十九大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以及十九届五中全会倡导“畅通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等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之后,社会工作被当作我国基层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专业力量之一受到政府各部门的重视。近年来“五社联动”的提出则进一步推动中国社会工作融入社区基层治理的实践中,使之成为我国基层治理的重要创新力量。①夏学娟、王思斌、徐选国、任敏、金美凤、任艳萍:《打造现代化的基层治理服务新格局(下)——解读〈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中国社会工作》2021 年第24 期。2022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十四五”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再一次强调在我国城乡社区建设中发挥社会工作的专业力量。显然,基层治理实践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的主要场域,也是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的现实依据。这样,社会工作如何融入基层治理实践,推动我国基层治理的创新,就不仅是一个实务问题,而且是一个急需中国社会工作者回答的理论问题,它关乎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的道路选择和理论建构。
值得注意的是,一旦人们把社会工作视为一支创新基层治理的专业力量就会发现,这样的专业实践不同于传统的社会工作,它至少出现了三个方面的转变:从关注社区弱势人群转向关注社区普通人群,甚至社区能人;从注重居民的困难帮扶转向注重居民的参与和议事;从强调人和环境的不足修补转向人与环境的协同改变。显然,在这样的转变下中国社会工作弱化了传统社会工作专业实践开展所需要的对社区弱势人群的困难帮扶,而需要专注于普通人群的社区参与和议事以及其中要实现的个人与社区的能力提升,这是一种增能实践。为此,中国社会工作者就需要考察西方增能实践的历史演变,以便能够明确社会工作基层治理实践中的增能要求,找到中国特色社会工作道路的理论基础,创建社会工作的“中国学派”。
二、社会生活中的增能
在社会工作专业实践中,第一次正式使用“增能”这一概念的是美国黑人社会工作学者芭芭拉·索罗门(Barbara Bryant Solomon),她在1976 年出版的《黑人增能:受压迫社区的社会工作》(Black Empowerment:Social Work in Oppressed Communities)一书中,聚焦美国黑人在社会生活中普遍感受到的无力感(powerlessness),并由此出发将导致无力感的社会层面的直接影响因素(资源分配不公)与个人层面的间接影响因素(负面感受内化)联系起来,倡导一种能够改变黑人种族社会地位的社会工作。②Barbara B. Solomon,Black Empowerment:Social Work in Oppressed Communitie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p.127.进入20 世纪80 年代之后,增能社会工作得到迅猛的发展,增能的内涵也因此变得更加明确,它倡导一种能够把个人层面的临床治疗与社会层面的资源分配整合起来的整全实践。①Helen Northen,Clinical Social Work(2nd ed.).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4,p.2.到了90 年代,美国另一位国际知名的社会工作学者朱迪斯·李(Judith Lee)就是在这种整全实践的基础上建构增能社会工作的理论逻辑框架的。她把人与环境之间的生态联系作为人们增能的基本观察维度,强调任何社会层面的改变都以人们的生态联系为基础,是对人们生态联系的深化,目的是增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应对周围环境挑战的能力。②Judith A.B. Lee,“The Empowerment Approach to Social Work Practice,”In Francis J. Turner,Social Work Treatment:Interlocking Theoretical Approaches(4th ed.). 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6,p.220.尽管朱迪斯·李在不同时期对于增能的理论逻辑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框架,但是她始终把社会资源分配不公导致的压迫作为考察的核心,来建构增能概念的内涵,并且认为历史视角、生态视角和社会视角是增能实践不可或缺的三个观察维度。历史视角是指从纵向的时间演变维度考察社会资源分配不公对弱势群体造成的影响,生态视角则是从横向的人与环境交互影响维度分析资源分配不公对弱势群体的生活造成的困扰,而社会视角则是从社会结构维度探究资源分配不公给弱势群体造成的困境。这三个视角分别从纵向的时间演变、横向的人与环境关系、广度的社会结构维度探究资源分配不公对弱势群体造成的困扰。③Judith A.B. Lee,“The Empowerment Approach to Social Work Practice,”In Francis J. Turner,Social Work Treatment:Interlocking Theoretical Approaches(4th ed.). 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6,p.220.进入21 世纪之后,增能概念的内涵呈现出多样化、动态化和个别化的特点。④Kenneth McLauglin,“Empowering the People:‘Empowerment’and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1971-99,”Critical and Radical Social Work,Vol.2,No.2,2014,pp.203-216.之前一直强调的社会变革性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对个人主体性的强调,导致增能这一概念未得到普遍认可,有时甚至出现含混不清的问题。⑤Adinda T. Muchtar,John Overton and Marcela Palomino-Schalscha,“Contextualizing Empowerment:Highlighting Key Elements from Women’s Stories of Empowerment,”Development in Practice,Vol.29,No.8,2019,pp.1053-1063.
与问题解决模式不同,增能社会工作始终把对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现象的分析视为个人问题解决的关键。它假设,每个人都具有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都能够影响社会生活的改变,不局限于个人现实生活困扰的解决。⑥同②,p.229.这样,人们的增能也就有了多个层面的改变要求,是人们整个社会生活状况的改变,既表现为个人层面的自我成长,如自我主动参与能力的加强、自我决定能力和行动能力的提升以及自我信心的增强等⑦Lorraine M. Gutiérrez,Kathryn A. DeLois and Linnea GlenMaye,“Understanding Empowerment Practice:Building on Practitioner-based Knowledge,”Families in Society:Journal of Contemporary Social Services,Vol.76,No.9,1995,pp.534-54.,也表现为社会环境层面的改善,如人际互助关系的建立、分享式学习方式的培养以及社会资源公平分配方式的倡导等⑧Malcolm Payne,Modern Social Work Theory(3rd ed.).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p.295.。尽管增能的内容涉及很广,手段也很多样,但是其核心就是增强人们对社会生活的掌控能力,使人们能够充分挖掘自己的潜能,改善社会生活的状况。①Robert Adams,Self-help,Social Work and Empowerment.London:Macmillan,1990,p.43.简单而言,人们的增能包括三个方面的改变:(1)拥有更为积极、更有力量的自我;(2)对现实环境始终保持批判的意识;(3)学会寻找资源和策略实现预定的目标。②Judith A.B. Lee,The Empowerment Approach to Social Work Practice:Building the Beloved Community(2nd ed.).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1,pp.34.相应地,人们的增能也就涉及人们生活的三个相互关联的不同层面,即个人层面、人际层面和政治层面。③Ibid.,p.51.显然,这种理解增能内涵的逻辑框架已经拥有了后现代建构主义的视角,因为它反对把人与环境割裂开来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强调人的任何自我改变都是发生在社会环境中的,都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同时也影响着社会环境。④Robert Adams,Social Work and Empowerment(2nd ed.). London:Macmillan,1996,p.11.
增能社会工作把意识提升(consciousness-raising)视为增能内涵中不可缺少的核心内容,认为只有借助与社会环境的对话,了解人们生活困难背后社会层面的问题,才能找到对抗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的办法,消除人们的无力感。⑤Paulo Freire,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Harmondsworth:Penguin,1972(reprinted 1986),p.15.这样,帮助人们建立与社会环境的对话交流机制就成为实现意识提升的关键。它需要人们对社会现实进行重新命名和重新理解,这才有了重新建构社会现实的要求。⑥Robert Adams,Social Work and Empowerment(2nd ed.). London:Macmillan,1996,p.61.可见,社会生活中的增能具有两个方面的核心改变要求:(1)意识提升,表明人们观察视野的拓展,拥有了参与社会生活并且影响社会环境的能力;(2)行动反思,表明人们参与社会生活的深入,拥有了探究社会生活要求和重构社会生活经验的能力。⑦Ibid.,p.39.实际上,增能社会工作倡导的是一种新的“本土”知识观,这种知识观与人们的在地参与经验有着密切关联,是人们融入社会生活并且推动社会生活改变能力的体现,而其中对自己所处社会环境的批判意识也就成为这种知识的核心内涵之一。⑧Mary E. Kondrat,“Concept,Act,and Interest in Professional Practice:Implications of an Empowerment Perspective,”Social Service Review,Vol.69,No.3,1995,pp.305-328.显然,这种新的“本土”知识观具有三个方面的显著特点。(1)场景化(contextualization)。它以人们的在地经验为出发点,需要围绕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到的“社会事实”展开对话交流,呈现人们的整个社会生活状况。(2)过程化(processing)。它涉及人们在特定社会生活场景中做出的行动选择,以应对社会生活中面临的问题,是一种不断寻求社会生活改变的知识,始终与人们的应对行动联系在一起,能够帮助人们提升社会生活的掌控能力。(3)集体化(collectivization)。它需要人们与身边的他人联系起来,一起寻找社会生活问题的解决方法,摆脱原子化、碎片化的社会生活现状,形成互助关系。⑨Stephen M. Rose,“Advocacy/Empowerment:An Approach to Clinical Practice for Social Work,”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Welfare,Vol.17,No.2,1990,pp.41-52.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强调社会生活中变革性的增能实践在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不仅内容变得越来越宽泛,而且越来越注重个人成长改变的要求以及个人对现实生活掌控能力的提升。①Phylida Parsloe,“Empowerment in Social Work Practice,”In Phylida Parsloe (ed.),Pathways to Empowerment.Birmingham:Venture,1996,p.8.
三、现实生活中的增能
在全球化运动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增能社会工作从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开始拒绝从社会环境维度理解增能内涵这种单一的解释,而是把现实生活中的多元化、复杂性和变动性等特征也纳入对增能内涵的考察中。②Adinda T. Muchtar,John Overton and Marcela Palomino-Schalscha,“Contextualizing Empowerment:Highlighting Key Elements from Women’s Stories of Empowerment,”Development in Practice,Vol.29,No.8,2019,pp.1053-1063.这样,增能这一概念也就不再局限于社会领域的服务,它被广泛运用于社会工作的不同服务领域和不同服务人群,既有微观领域的精神障碍患者③Zlatka Russinova,Vasudha Gidugu,Philippe Bloch,Maria Restrepo-Toro and E.Sally Rogers,“Empowering Individuals with Psychiatric Disabilities to Work:Results of a Randomized Trial,”Psychiatric Rehabilitation Journal,Vol.41,No.3,2018,pp.196-207.以及社区生活的病人④Laura A. Faith,Jen O. Collins,Jenna Decker,Amber Grove,Stephen P. Jarvis and Melisa V. Rempfer,“Experiences of Empowerment in a Community Cognitive Enhancement Therapy Program:An Exploratory Qualitative Study,”Psychosis,Vol.11,No.4,2019,pp.319-330.的疾病康复,也有宏观领域的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妇女⑤Adinda T. Muchtar,John Overton and Marcela Palomino-Schalscha,“Contextualizing Empowerment:Highlighting Key Elements from Women’s Stories of Empowerment,”Development in Practice,Vol.29,No.8,2019,pp.1053-1063.和流浪者⑥Max A. Huber,Louis D. Brown,Rosalie N. Metze,Martin Stam,Tine Van Regenmortel and Tineke N. Abma,“Exploring Empowerment of Participants and Peer Workers in a Self-managed Homeless Shelter,”Journal of Social Work,Vol.22,No.1,2022,pp.26-45.的能力提升,甚至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弱势人群实践⑦Charlene Tan,“A Confucian Interpretation of Women’s Empowerment,”Journal of Gender Studies,Vol.30,No.8,2021,pp.927-937.和中国的社会治理实践等⑧袁方成:《增能居民:社区参与的主体性逻辑与行动路径》,《行政论坛》2019 年第1 期。。显然,增能已经不是某一种理论流派的概念,而是理解服务对象以及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一种独特视角,它成为社会工作者实现“助人自助”专业服务目标的普遍诉求。⑨Rigaud Joseph,“The Theory of Empowerment:A Critical Analysis with the Theory Evaluation Scale,”Journal of Human Behavior in the Social Environment,Vol.30,No.2,2020,pp.138-157.
作为变革性的增能的内涵中有一个基本假设,认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会遭遇来自社会结构因素影响而导致的成长受阻现象,使人们的基本权益受到剥夺,让人们感受到“失权”的无力感。在这样的基本假设下,权力的抗争也就被视为增能的重要实践策略,它能够保障人们的基本权益不受侵害。女性主义不赞同这样的假设。她们发现,一旦人们把权力的抗争作为保障自己权益的基本手段,就必然涉及从有权力的人手里争夺权力的过程,让自己从无权变成有权,最后增能就会演变成权力斗争。①Adinda T. Muchtar,John Overton and Marcela Palomino-Schalscha,“Contextualizing Empowerment:Highlighting Key Elements from Women’s Stories of Empowerment,”Development in Practice,Vol.29,No.8,2019,pp.1053-1063.实际上,人们的权力争夺很多时候并不会自然而然出现增能,增能也并不只是人们掌控感的增强,它同时还包含人们对现实生活处境的深入理解,以及与周围他人协同能力的增强。②Bob Pease,“Rethinking Empowerment:A Postmodern Reappraisal for Emancipatory Practice,”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Vol.32,No.2,2002,pp.135-147.有学者直接引用福柯的权力观点,强调权力不是一种社会结构,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一种说“不”的能力,它实际上是一种生产事务的能力,涉及人们的行动能力、主体性和影响力等。③Kevin J. Heller,“Power,Subjectification and Resistance in Foucault,”Substance,Vol.25,No.1,1996,pp.78-110.因此,增能的内涵不能被狭隘地理解为权力的抗争,它涉及人的主观心理状态的复杂变化过程,除了包括掌控感和力量感的增强之外,还包括参与现实生活能力的增强④Lars Hansson and Tommy Björkman,“Empowerment in People with a Mental Illness: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Swedish Version of an Empowerment Scale,”Scandinavian Journal of Caring Sciences,Vol.19,No.1,2005,pp.32-38.、自我主动性的提升以及自我满意感的增加等⑤Ching-Man Lam and Wai-Man Kwong,“Powerful Parent Educators and Powerless Parents:The‘Empowerment Paradox’in Parent Education,”Journal of Social Work,Vol.14,No.2,2014,pp.183-195.。
实际上,增能是无法给予的。一旦人们在增能实践中缺乏批判反思的能力,就会不自觉地通过增能把自己认同的价值标准和责任要求转移给对方,做着增能形式的去能工作,让对方感受到的不是增能,而是失能。⑥Judith A.B. Lee,The Empowerment Approach to Social Work Practice:Building the Beloved Community(2nd ed.).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1,p.206.这也意味着,增能不能采用“需要—满足”这种传统的问题解决框架来考察,它不是给予和接受这种单向的影响关系。⑦Rigaud Joseph,“The Theory of Empowerment:A Critical Analysis with the Theory Evaluation Scale,”Journal of Human Behavior in the Social Environment,Vol.30,No.2,2020,pp.138-157.显然,增能需要打破这种“非黑即白”二元对立的交往关系,建立一种相互影响、共同学习的沟通方式。它需要人们在这种交互影响过程中重新定义彼此的位置和角色,从而找到更有利于自我成长的改变空间。⑧Katharina Hölscher,Julia M. Wittmayer,Flor Avelino and Mendel Giezen,“Opening up the Transition Arena:An Analysis of (Dis)empowerment of Civil Society Actors in Transition Management in Cities,”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Vol.145,2019,pp.176-185.这样,个人的主动性就成为增能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人们只有主动寻求自己认定的现实生活目标并且感受到自己的主动影响能力时,才能够保持自己行动的积极性,远离顺从、取悦、被动,甚至疏离的生活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增能的这种主动性并不是人们借助某个方面能力的变化来实现的,而是人们对自己生活状态的重新理解和调整,是一种自我的改变,涉及复杂、多维的内涵变化。⑨Laura A.Faith and Melisa V. Rempfer,“Comparison of Performance-based Assessment and Real World Skill in People with Serious Mental Illness:Ecological Validity of the Test of Grocery Shopping Skills,”Psychiatry Research,Vol.266,2018,pp.11-17.
显然,增能不是一种被动接受指令的单向学习过程,而是主动融入现实生活处境中并且呈现自我主动性的交互影响过程。它拒绝那种从单一角度出发的分析、理解和定义,因而也就需要人们把自己放在具体的现实生活场景中来理解个人的成长改变要求,不能脱离具体的现实生活场景来考察人的成长改变过程。①Douglas D. Perkins and Marc A. Zimmerman,“Empowerment Theory,Research,and Application,”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Vol.23,No.5,1995,pp.569-579.相应地,限制社会弱势人群成长改变的现实生活场景中的社会问题才能够呈现出来。例如,社会污名化就是社会问题的常见形式之一,它迫使社会弱势人群陷入更为弱势的处境中。②Haya Itzhaky and Alan S. York,“Showing Results in Community Organization,”Social Work,Vol.47,No.2,2002,pp.125-131.值得注意的是,一旦人们从单一的角度来理解增能,就会不自觉地忽略人类现实生活的两个基本事实:第一,人是社会人,人们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他人,无法脱离他人而存在;第二,人类生活处于社会物质环境中,依赖物质的生产和分配。正因如此,增能的内涵就需要场景化,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一方面能够避免陷入个人主义的窠臼中,只关注自己的感受,不关心他人的要求;另一方面,能够避免掉入道德主义的陷阱中,只强调生活的意义,不考虑生活的现实要求。③Dag Leonardsen,“Empowerment in Social Work:An Individual vs. a Relational Perspectiv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Vol.16,No.1,2007,pp.3-11.这样,对于增能而言,场景化具有了哲学层面的意义。它是一种新的知识观,要求人们放弃决定论和相对主义的知识立场,从人们所处的现实生活场景出发寻找个人成长改变的空间,它既涉及场景化的现实生活要求,也涉及人们在特定场景中的主动性。④Adinda T. Muchtar,John Overton and Marcela Palomino-Schalscha,“Contextualizing Empowerment:Highlighting Key Elements from Women’s Stories of Empowerment,”Development in Practice,Vol.29,No.8,2019,pp.1053-1063.否则,人们的成长改变就无法与他们对现实生活场景的理解联系起来,人们的增能也因此变成“无本之木”,必然走向失能。⑤Martine J.H. Coun,Pascal Peters,Robert J. Blomme and Jaap Schaveling,“‘To Empower or not to Empower,That’s the Question’. Using an Empowerment Process Approach to Explain Employees’Workplace Proactivity,”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Vol.33,No.14,2022,pp.2829-2855.
增能的实现绝不可能是自动发生的,它除了需要人们拥有一定的动力和能力之外,还需要给予人们实现能力的机会。⑥Eileen Appelbaum,Thomas Bailey,Peter Berg and Arne L.Kalleberg,Manufacturing Advantage:Why High-Performance Work Systems Pay Off.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0,p.23.正是有了这样的机会,人们才能够在能力的实现过程中尝试那些具有前瞻性的行为,使人们真正拥有推动环境改变的能力,增能的主动性也因此得到延伸,而且能够成为人们生活经验的一部分,内化为个人自我成长的推动力。⑦Sharon K. Parker and Chia-Huei Wu,“Leading for Proactivity:How Leaders Cultivate Staff Who Make Things Happen,”In David Day(ed.),The Oxford Handbook of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s .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p.401.实际上,心理增能的实现依赖人们对环境的态度。只有当人们不再把环境视为“给定”的条件时,他们才能够在现实场景中有所创新,呈现出更强烈的主动性和更有效的问题解决能力。①Gretchen M. Spreitzer,“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in the Workplace:Dimensions,Measurement,and Validation,”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Vol.38,No.5,1995,pp.1442-1465.显然,这里所说的机会不是定好目标让人们去行动的机会,这种从单一角度考察的指令性的实施机会只会让人们变成行动的工具,失去自我的主动性。这里的机会是让人们学会在具体现实场景中寻找问题解决方法并且能够推动环境一起改变的机会,这种机会就有了授权的要求,它能够提升人们的自我决定能力,使人们真正拥有主动性。②Martine J.H. Coun,Pascal Peters,Robert J. Blomme and Jaap Schaveling,“‘To Empower or not to Empower,That’s the Question’. Using an Empowerment Process Approach to Explain Employees’Workplace Proactivity,”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Vol.33,No.14,2022,pp.2829-2855.
显然,增能不同于人们常说的能力提升或者特长的发挥,它包含了人们的自主性、自决能力和自我效能等方面的改变,有了“由内向外”的主动性。③Merle Varik,Marju Medar and Kai Saks,“Informal Caregivers’Experiences of Caring for Persons with Dementia in Estonia:A Narrative Study,”Health & Social Care in the Community,Vol.28,No.2,2020,pp.448-455.这样的变化是无法仅仅依靠个人单方面的努力就能够实现的。它存在于人们与周围环境的交往关系中,是一种特定交往关系呈现出来的特征。④Cristina P. Albuquerque,Clara C. Santos and Helena D.S.N.S. Almeida,“Assessing ‘Empowerment’as Social Development:Goal and Process,”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Work,Vol.20,No.1,2017,pp.88-100.这样,伙伴关系的建设就成为人们实现增能的重要策略之一。这种伙伴关系不仅涉及服务对象与社会工作者之间的专业合作,而且涉及服务对象与周围他人之间的日常交往。⑤Lai-Ching Leung,“Empowering Women in Social Work Practice:A Hong Kong Case,”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Vol.48,No.4,2005,pp.429-440.其核心是尊重和保护人们的自决权,特别是社会工作者因为在专业服务中具有了“专家”身份,他们就需要在专业服务与人们的自决权之间做出选择,维持两者的平衡,以保障社会工作专业服务能够真正推动人们自决能力的提升,而不仅仅是问题的消除。⑥Ole P. Askheim,“Empowerment as Guidance for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An Act of Balancing on a Slack Rope,”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Work,Vol.6,No.3,2003,pp.229-240.其中,使用合作语言进行沟通就变得非常重要,因为这种对话方式能够让合作伙伴的感受和想法被听到和看到,有了得到尊重和理解的体验。也正是因为如此,人们常常把参与和包容视为增能的前提,这让人们的合作关系真正拥有了促使自我成长的功能。⑦Maja L. Andersen,“Involvement or Empowerment-assumptions and Differences in Social Work Practice,”Nordic Social Work Research,Vol.10,No.3,2018,pp.283-298.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需要面对的关系通常是多元的,涉及人们生活的多个不同层面和多个不同对象,不仅仅是单一的“我与你”的关系,因而增能也就具有了交叉性,它是人们在多重相互影响的复杂关系中所做的选择。⑧Celia Kitzinger,“Feminist Approaches.”In Clive Seale,Giampietro Gobo,Jaber F. Gubrium and David Silverman(eds.).Qualitative Research Practice(pp.125-140). London:Sage,2004,p.138.这样的选择必然具有在地的场景性特征,与在地的历史、文化以及人们的生活习俗有着密切的关联,是在地生活的人们根据自己的现实生活要求所做的改变努力。①⑥Adinda T. Muchtar,John Overton and Marcela Palomino-Schalscha,“Contextualizing Empowerment:Highlighting Key Elements from Women’s Stories of Empowerment,”Development in Practice,Vol.29,No.8,2019,pp.1053-1063.它需要人们融入在地的现实生活中,依据在地的现实要求并且通过多方协商的方式给自己的生活赋予一定的意义,让自己能够有效应对现实生活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挑战。显然,增能是个别化的、独特的。②Enrique Alonso-Población,Alberto Fidalgo-Castro and David Palazón-Monforte,“Ethnographic Filmmaking as Narrative Capital Enhancement among Atauro Diverwomen:A Theoretical Exploration,”Development in Practice,Vol.26,No.3,2016,pp.262-271.它是人们个人自我的改变,不仅涉及人们对自己所处的在地现实生活环境理解的深入,而且涉及人们主动性的发挥以及与周围他人合作伙伴关系的建设。可以说,这是一种自我增能。③Ping K. Kam,“From the Strengths Perspective to an Empowerment-Participation-Strengths Model in Social Work Practice,”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Vol.51,No.4,2021,pp.1425-1444.它让人们拥有更为清晰的在地的主体意识④Cristina P. Albuquerque,Clara C. Santos and Helena D.S.N.S. Almeida,“Assessing ‘Empowerment’as Social Development:Goal and Process,”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Work,Vol.20,No.1,2017,pp.88-100.和理性自决能力⑤Merle Varik,Marju Medar and Kai Saks,“Informal Caregivers’Experiences of Caring for Persons with Dementia in Estonia:A Narrative Study,”Health & Social Care in the Community,Vol.28,No.2,2020,pp.448-455.。
可见,增能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具有多维性,特别是在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之后逐渐转向自我增能,关注个人在现实生活场景中的增能。⑥Adinda T. Muchtar,John Overton and Marcela Palomino-Schalscha,“Contextualizing Empowerment:Highlighting Key Elements from Women’s Stories of Empowerment,”Development in Practice,Vol.29,No.8,2019,pp.1053-1063.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增能这一概念目前仍缺乏一致的认识,导致在它在研究和实务领域运用中存在诸多困难。⑦April Mackey and Pammla Petrucka,“Technology as the Key to Women’s Empowerment:A Scoping Review,”BMC Women’s Health,Vol.21,No.1,2021,pp.45-78.
四、西方自我增能内涵的不足
显然,自我增能是在人们失去面对现实环境挑战能力的情况下实施的服务策略,它的目的是帮助人们提升对现实生活的掌控能力。这样的自我增能只有在人们出现了明显的失能感的时候才发挥作用,平时根本无法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当然,它也就无法推动人们日常生活的改变,导致自我增能极容易陷入批判意识的强化和权力抗争的纯智力游戏中,看不到它对现实生活的改变能力。实际上,人们的主动性是在日常生活的问题解决过程中形成的,只有当人们能够把自己所学的新知识运用于现实问题的解决过程并且看到其积极的成效时,才能对抗无力感,主动融入现实生活,增强自我的主动性。⑧Laura A. Faith,Jen O. Collins,Jenna Decker,Amber Grove,Stephen P. Jarvis and Melisa V. Rempfer,“Experiences of Empowerment in a Community Cognitive Enhancement Therapy Program:An Exploratory Qualitative Study,”Psychosis,Vol.11,No.4,2019,pp.319-330.自我增能与日常生活的割裂恰恰来自对问题概念的忽视,因为人们一旦在现实生活中遭受到环境的挑战,首先感受到的就是由目标无法实现所产生的问题,只有当人们经历过多次尝试仍旧无法改变现实环境时,内心才会出现无力感。其次,在实际日常生活中,人们面对更多的是应对行动成效不佳的问题,即人们知道怎么做,而且也有办法应对,但是应对行动的成效不如自己的预期。显然,此时人们需要的是问题解决方面的帮助。即使面对无力感,人们首先也需要考察问题,了解是什么问题导致了人们无力感的出现。因此,与增能相比,问题的使用更为日常化、生活化。相应地,自我增能要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就需要与对问题的考察结合起来。
除了无法融入日常生活之外,自我增能的内涵始终镶嵌于西方的个人主义和自我改善的文化传统中,与有着不同文化传统的非西方社会之间会产生冲突。①Phylida Parsloe,“Empowerment in Social Work Practice,”In Phylida Parsloe (ed.),Pathways to Empowerment.Birmingham:Venture,1996,p.8.为此,有学者提倡在地化的服务,呼吁人们关注在地的生活方式以及自身拥有的理解框架,建立一种与西方增能内涵不同的东方范式。②Tzuyuan S. Chao and Huiwen Huang,“The East Asian Age-friendly Cities Promotion-Taiwan’s Experience and the Need for an Oriental Paradigm,”Global Health Promotion,Vol.23,No.1,2016,pp.85-89.实际上,在具体的增能服务中,中国人的自我观直接影响着增能服务的内涵。由于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人更为关注家庭关系和重要他人的作用,因而在增能服务中也就强调对生命意义的自我批判意识,注重检视个人的行为和品格,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而不是使用激进的变革手段。③Kam-shing Yip,“The Empowerment Model:A Critical Reflection of Empowerment in Chinese Culture,”Social Work,Vol.49,No.3,2004,pp.479-487.有学者直接从儒家文化的视角出发审视中国女性如何增能,强调这是女性发挥个人能动性并且主动修正权力关系的过程,受到在地文化习俗的影响。④Charlene Tan,Confucian Philosophy for Contemporary Education. London:Routledge,2020,p.142.在道家文化和禅宗思想的影响下,增能被视为根据自然的节奏和发展要求寻找真我的过程,它需要人们停止一切不自然、不和谐的行动和想法。⑤David Brandon,“Zen Practice in Social Work,”In David Brandon and Bill Jordan(eds.),Creative Social Work. Oxford:Basil Blackwell,1979,p.32.尽管人们渐渐意识到发展中国家的增能内涵应当不同于西方的自我增能内涵,有着自己独特的要求,但是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和实践尚远远不足,仍有很长的路需要人们去探索。⑥Mary Daly,“The Long Road to Gender Equality,”Social Politics: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Gender,State & Society,Vol.26,No.4,2019,pp.512-518.
自我增能的内涵之所以遇到这样的困境,既无法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无法与在地的中国文化精神资源相衔接,是因为增能的内涵在从社会生活的变革性增能向现实生活的自我增能转变过程中,人与环境的交互影响成了自我增能实现的关键,而在这种交互影响中对于如何保证人们的意识提升超越个人经验的局限却没有清晰说明,导致人们不自觉地陷入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中审视自我增能的内涵。这样,西方的自我增能内涵也就无法摆脱西方个人主义单向视角的局限。这种单向视角要么把问题视为人们现实生活中的不足,等待人们去解决,这是一种向外的问题解决的探寻过程;要么把问题当作人们在环境压迫下呈现出来的无力感,等待人们去自我觉察,这是一种向内的自我增能过程。因此,问题解决与自我增能也就成为两种“水火不容”的社会工作实践策略。可以说,自我增能的专业实践困境反映的恰恰是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困境,尤其是在有着与西方个人主义不同文化传统的中国本土环境中,这一专业实践的困境显得更为突出。
五、中国文化视角的自我增能
为此,中国社会工作者就需要放弃从个人主义的单向视角审视自我增能的内涵,而需要坚持在地的中国文化立场,采用一种人与环境交互影响的双向观察视角,注重个人如何在超越单向观察视角局限之后发现生活之“道”,进而产生提升个人自决理性的需求。一旦中国社会工作者采用这种双向观察视角考察社会工作专业实践就会发现,与自我增能相对立的问题解决也就具有了新的内涵,此时的问题解决总会遭遇环境的挑战,需要人们在问题解决过程中明确环境提出的挑战,并且在对环境挑战的考察中拓展人们问题解决的观察视角,由此使人们在问题解决过程中获得自我增能。这样,基于双向观察视角,人们的问题解决与自我增能不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人们解决问题过程中的两面,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一旦人们采用双向视角的自我增能,不仅能够让自我增能这一概念与问题解决结合起来,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让人们的每一次问题遭遇和解决过程都成为能力提升的过程,而且西方的自我增能这一概念也能够与中国文化注重的理性自决衔接起来,为中国本土社会工作注入中国文化的精神元素,使中国社会工作能够真正实现本土化。这样,这种双向视角的自我增能也就能够在融入人们日常生活的同时,与在地的中国文化精神资源联结起来,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的发展道路。
尽管中国社会工作已经广泛参与到我国的基层治理实践中并被视为我国基层治理实践的一支重要创新力量,但是实际上它的专业位置和专业功能是不清晰的,常常与社会组织的公益慈善服务以及居民的志愿服务混淆在一起。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国社会工作在基层治理实践中找不到可以实现专业改变成效的专业手法。如何促使社区居民在基层治理实践的社区参与和社区议事中发生有效的改变,这不仅是一个社会工作的实务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工作的理论问题。在西方传统社会工作的问题解决和自我增能两大实践策略失效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工作需要走出自己的专业化发展道路。这样,双向视角的自我增能也就具有了明确社会工作基层治理实践的专业位置和专业功能的作用,因为这样的专业手法不仅能够帮助中国社会工作者在推动居民社区参与和社区议事过程中找到他们遇到的现实问题,而且能够协助居民通过现实问题的解决及其自我增能的过程提升其在社区生活中的理性自决、互助和自治能力。显然,此时中国社会工作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真正拥有了无法替代的专业位置和专业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双向视角自我增能的逻辑框架中,中国社会工作的基层治理实践有了传承中国文化精神资源的现实要求,不再仅仅停留在居民现实生活问题的解决和能力的增强等物质生活层面,同时拥有了运用中国文化精神资源改造现实生活这种文化精神层面的需求:一方面,要求中国社会工作者在基层治理实践中,推动这种基于人与环境协同改变的双向视角的中国文化精神资源走进居民的日常生活,转化为居民在现实生活中的理性自决能力,让中国文化精神资源通过问题解决和自我增能的过程适应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要求;另一方面,要求中国社会工作者在帮助居民促进现实生活的改善过程中,能够展现中国文化的精神资源,使中国的现代化生活拥有自己的文化内涵和伦理价值,避免陷入西方个人主义的窠臼中,最终迷失发展的方向。因此,可以说,双向视角的自我增能让中国社会工作的基层治理实践拥有了文化实践的内涵,是中国社会工作者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寻求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六、结论
随着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转型,中国社会工作自2013 年被政府视为基层“三社联动”中的专业力量之后,逐渐融入基层治理中,成为我国基层治理实践中不可或缺的创新力量。然而,在基层治理实践中,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位置和专业功能是不清晰的,不仅没有明确的专业成效,而且也缺乏有效的专业手法,特别是在国家进入“十四五”规划建设时期,中国社会工作面临高质量发展的挑战,亟须回答如何在基层治理实践中通过推动社区居民的社区参与和议事来实现居民的成长改变。本文通过回顾西方社会工作的增能实践策略发现,这种促进人们成长改变的增能内涵经历了从社会生活的变革性增能向现实生活的自我增能转变的发展阶段。前者关注不公平的社会资源分配对人成长改变造成的无力感,这是一种社会结构性的无力感,需要变革性增能;后者注重多元、变动的现实生活环境对人成长改变产生的无力感,这是一种环境差异性的无力感,需要自我增能。
实际上,西方自我增能的内涵依据的是个人主义价值观,采用人与环境二元对立的单向视角。这样的单向视角必然导致自我增能内涵与问题解决的对立,不仅无法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而且无法与中国文化精神资源倡导的人与环境协同改变的双向视角衔接起来。为此,中国社会工作就需要摒弃西方个人主义的单向视角,采用融入了中国文化精神资源的双向视角来审视自我增能的内涵。这样能够在问题解决的过程中融入自我增能,使中国社会工作的基层治理实践拥有专业的服务成效,同时能够将中国文化精神资源贯穿到中国社会工作的基层治理实践中,让中国社会工作真正拥有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化实践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