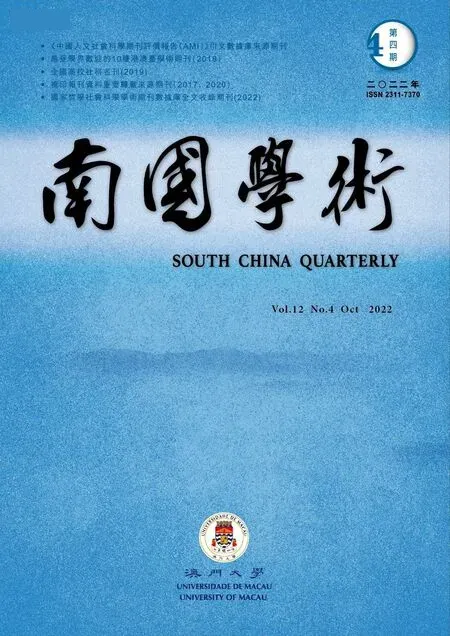中西美學與詩學關係之比較
楊春時
[關鍵詞]中國美學 中國詩學 西方美學 西方詩學
美學、詩學都是古老的學科,但兩者的關係,在中國與西方有所不同,從而形成了中西美學、詩學各自的特性。這個問題雖然重要,但相關的研究吉光片羽。爲此,本文擬從學科的發生、學科的性質、學科的演化等角度,探討中西方美學與詩學的關係。
一 學科的發生: 異源異體/同源同體
一個學科與另一個學科的關係,首先是由各自的起源決定的,美學與詩學的關係也是如此。中西美學、詩學各自起源不同,決定了二者的差異。
西方美學與詩學起源不同,具有二元性,從而造成了美學與詩學的分立。西方美學從屬於哲學,而哲學是“愛智慧”,所以美學也是愛智慧的學問。美學的研究對象是美的本質,這種對美的思考不是藝術經驗的總結,而是一種抽象的哲學思辨。柏拉圖是西方美學的始祖,他的哲學以理念爲實體,認爲美是理念的光輝。柏拉圖提出,在具體的美的事物之後,有一個美的理念作爲本源,它不是感官經驗的表象,而是靈魂對理念的洞見。柏拉圖還認爲,現實中的美衹是塵世之人對上界理念光輝的回憶,不是美本身,而美本身衹在理念世界:“有這種迷狂的人見到塵世的美,就回憶起上界裏真正的美。”①《柏拉圖文藝對話集》(重慶:重慶出版公司/重慶出版社,2016),朱光潛 譯,第117、116、207頁。這樣,美就具有了超越性,而柏拉圖美學開啓了西方美學的形而上學傳統。
古希臘美學是一種形而上的思辨,它不以藝術(“詩”)爲研究對象,美也不是藝術的本質(雖然某些藝術如繪畫和音樂帶有美的因素),故美學也不是藝術哲學。古代西方美學與詩學的分離,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當時的美學觀無法把敍事藝術列入審美對象。古代哲學是實體本體論的客體性哲學,美學作爲哲學的分支也是客體性美學,因此美被規定爲實體的屬性。這樣,作爲實體屬性的美,必然以“物”的形式呈現出來,如人體、器物、自然物等,而不會以敍事藝術的形式存在。當然,作爲這些物體的“摹仿”的美術等表現藝術也有美的因素。柏拉圖追問美的本質列舉了四種審美對象,包括美的姑娘,美的水罐,美的母馬,美的竪琴,並沒有列出藝術。這不是出於疏忽,而是由於藝術沒有成爲美學對象,或者說藝術不是美的。實體本體論的美學不能把語言藝術“詩”作爲對象,而古希臘的“詩”是敍事性的史詩和戲劇。由於敍事藝術的對象是人的行動,其本身不是“美的”,它被認爲是摹仿的對象,因此敍事藝術無法納入美學的研究範圍,而衹能成爲詩學研究的對象。
在柏拉圖那裏,美學與詩學是兩個學科,詩學不以美學爲本,美學不統領詩學。柏拉圖認爲,美是理念的光輝,美屬於真理,美學研究的是“美本身”“真實本體”。他還認爲,詩摹仿現實,而現實摹仿理念,故詩是對理念的雙重摹仿,是虛假的幻象,與真理隔着三層;詩人煽動情慾、亂人心性,應該逐出理想國。這意味着藝術(詩)本質不是美,而且美高於藝術(詩),故美學不是詩學。柏拉圖抬高“愛美者”而貶低“詩人或其他摹仿的藝術家”,他提出,塵世的人如果其靈魂洞見了真理,就會投生爲“愛智慧者,愛美者,或者是詩神和愛神的頂禮者”,而其他人則依次爲:第一流、第二流是君主、戰士;第三流是政治家或經濟家、財政家;第四流是體育家或醫生;第五流是預言家或執掌宗教典禮的;而“第六流最適宜於詩人或其他摹仿的藝術家”。②《柏拉圖文藝對話集》(重慶:重慶出版公司/重慶出版社,2016),朱光潛 譯,第117、116、207頁。柏拉圖把美與愛聯繫在一起,認爲美源於愛神,而不是源於藝術女神。他說:“衹有驅遣人以高尚的方式相愛的那種愛神纔是美,纔值得頌揚。”③《柏拉圖文藝對話集》(重慶:重慶出版公司/重慶出版社,2016),朱光潛 譯,第117、116、207頁。這也說明了美與藝術的區別,因爲藝術是歸藝術女神繆斯管轄的。在中世紀,美學歸屬於神學,詩學歸屬於修辭學;美被當作上帝的屬性,認爲世俗之美(包括藝術)不是真美。這同樣肯定了美的超越性,把美與藝術分別開來。直至近代,美學纔與詩學聯繫起來,最後成爲藝術哲學。
西方的詩學不是起源於哲學思考,而是一種知識學的研究,是關於早期語言藝術“詩”的理論。“詩”專指韻文,與日常語言相區別,而詩學也與一般的技藝知識區別開來。詩學是在古代藝術門類沒有充分分化的情形下的語言類藝術理論,體現了藝術脫離早期宗教後的理論自覺。在當代中國的語境中,詩學概念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詩學等同於文學理論,狹義詩學則是詩歌理論。其實,當代的詩學概念衹是對古典詩學概念的借用,但二者的內涵並不相同。因爲,詩學在近代已經解體了,轉化爲包括各種具體的藝術門類的藝術理論。在古代西方,藝術門類還沒有充分分化,“詩”指總體性的語言類藝術,不僅指詩歌(史詩和敍事詩),也指泛詩化的藝術(如戲劇是“劇詩”)。在《詩學》中,亞里士多德把韻文分作兩類,戲劇與長篇敍事詩。在詩學後來的發展中,抒情詩也成爲詩的一種,列入詩學研究的對象。古希臘藝術主要有說唱性的史詩和表演性的祭祀儀式兩個源頭,前者演化爲詩歌,後者演化爲戲劇(悲劇和喜劇),成爲古希臘藝術的主要樣式。古希臘詩歌脫胎於史詩,講述歷史故事,主要是敍事詩,也帶有抒情性。古希臘戲劇有角色朗誦、表演,還有歌隊的吟唱和伴奏。戲劇與長篇敍事詩都屬韻文藝術,都具有敍事性,都是“詩”。於是,關於詩歌、戲劇的理論探討形成了詩學。
亞里士多德不認爲美是詩的本質,而認爲詩的本質是“摹仿現實”,故詩學與美學分屬不同的領域。雖然亞里士多德對詩歌和戲劇也有美的評價,但主要指這些藝術的形式和修辭學的因素,而非本質的評價。他在談論悲劇時說:“再則,一個美的事物——一個活東西或一個由某些部分組成之物——不但它的各部分應有一定的安排,而且它的體積也應有一定的大小,因爲美要靠體積與安排。……因此,情節也須有長度(以易於記憶者爲限)……”①[古希臘]亞里士多德:“詩學”,《詩學,修辭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羅念生 譯,第45 頁。在《形而上學》中,他提出“美的主要形式是秩序、勻稱和明確”。在這裏,美是結構、形式因素,而非藝術的本質。亞里士多德所使用的“美”的概念,在許多地方衹是“最好的”意思,所以,現代美學家比厄斯利說:“他並不一定認爲美是一種不同於藝術的優秀特質,但對這種優秀特質有貢獻的特殊的性質。也許對他來說,‘美的悲劇’與‘藝術上好的悲劇’是同義詞。”②[美]門羅·C.比厄斯利:《美學史:從古希臘到當代》(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高建平 譯,第87頁。這表明,在古希臘,詩學不是美學,而美學也還不是藝術哲學。
總之,西方美學與詩學的起源不同:美學發源於哲學思考,是對“美”的理念的研究;詩學發源於對“詩”的知識學研究,而“詩”的本質不是美。因此,美學與詩學不相關聯。
在古代中國,究竟有沒有詩學?或者說,古代中國的詩學概念是否合理呢?余虹認爲,中國沒有詩學,衹有“文論”,但“文論”不是文學理論,更不是詩歌理論,是關於“文”的理論;而“文”不僅包括文學,還包括其他文體,如應用文等。因此,他把詩學視爲西方獨有的理論形態,中國“文論”不能與其相提並論。③余虹:《中國文論與西方詩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這種說法,忽略了根本的一點,那就是:中國“文論”論及的“文”,包括人文與天地之文,都帶有審美屬性;“文”的概念本身就有“華彩”的意思,因此帶有美的屬性。所以,文即美文,關於美文的理論就是詩學。
“文論”是對這種審美對象的研究,故可以定性爲一種文化詩學。“人文”,主要是指講求辭采的韻文,如詩賦等文體,也包括一些修辭化的應用文體。它們都具有修辭學的特性,總體上可以歸爲詩學對象。“天地之文”,則是具有審美屬性的自然現象,作爲自然美可以歸爲美學對象。《文心雕龍·原道》說:“文之爲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叠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這裏的自然不是物理對象,而是審美對象,具有審美屬性,所以也是“文”的範圍。因此,中國的“文論”既具有了詩學性質,也帶有美學的屬性。作爲一般文化的“文”衹是早期“文論”的概念,主要體現在《文心雕龍》中,但那個時期已有文筆之分:“有韻爲文,無韻爲筆。”筆作爲韻文,已經成爲詩學對象,衹是劉勰沒有嚴格運用這一原則。後來,蕭統編《文選》,嚴格區分文筆,“事出於沉思,義歸於翰藻”,以韻文爲主要形式特徵,專選具有詩性的語言作品,而排除了經史子集等文類。這樣,“文”的概念不斷演化,審美屬性越來越鮮明,並逐步向文學靠攏,而“文論”也日益詩學化。在以後的歷史中,“文論”演化爲詩論、詞論、戲劇論、小說論等各種具體的藝術理論,於是“文論”就充分詩學化了。中國詩學沒有形成純文學、純藝術的概念,而是雜文學、雜藝術的概念,這是以早期藝術爲對象的詩學本身的特性。
古代中國的詩學與古代西方的詩學之不同,還在於:西方詩學是關於史詩、敍事詩和戲劇的理論,主要是敍事詩學;而中國詩學是關於抒情詩、文的理論,主要是抒情詩學,衹是在元代以後纔形成了敍事詩學即關於戲曲、小說的理論。但這衹是中西詩學的特點不同,不能據此否定中國詩學的存在。
中國詩學發端於對重建“樂”的思考。中國藝術發源於禮樂文化,是禮樂文化解體後的産物。周代的禮樂文化是早期國家的文化禮儀,是中國理性文化的源頭。其中,“樂”是藝術的源頭,但還不是獨立的藝術。禮是融合宗教、倫理、法律等文化形態於一體的思想行爲規範,而“樂”是配合禮的儀式。詩、樂、舞合一,禮樂一體,“樂”是爲禮服務的,所謂“禮別異,樂合同”,禮樂共同達成了“尊尊”“親親”的宗法倫理秩序。在春秋戰國時代,宗法貴族社會變成了後宗法平民社會,禮樂文化解體,儒家要重建禮樂文化,以恢復社會文化的秩序。一方面,“以仁釋禮”,重建了倫理體系;另一方面,重新闡釋樂,建立了詩學。這時的“樂”已經從宮廷走向民間,從宗教、倫理儀式變成了一種娛樂活動,而且詩、樂、舞從禮樂文化中分離,獲得了相對的獨立,具有了審美的性質,成爲早期藝術形式。詩、樂、舞等一旦脫離禮樂體系,原先承擔的宗教、政治、倫理功能便相對淡化,而藝術價值突出。面對這種演變,孔子要重新界定藝術的性質,他反對把禮樂庸俗化、形式化,而要賦予其新的意義,所以發出這樣的疑問:“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論語·陽貨》)這樣,新的藝術的本質、特性、功用等問題就被提出來了,而對新的藝術的闡釋就形成了詩學。由此,經過孔子選定的詩成爲經典《詩經》,而對這些詩歌的解釋和評論就産生了中國的詩學。孔子對詩的闡述成爲中國詩學的思想綱領,而《詩大序》就是最初的詩學著作。作爲禮樂文化的組成部分之一的“樂”,也有了自己的理論體系《樂記》。而後,又有衆多的詩學著作産生,如《文賦》《文心雕龍》《滄浪詩話》《原詩》《藝概》《閑情偶寄》等等。
古代中國的美學與詩學有共同的源頭,共存在一起。中華文化具有實用理性的性質,中國人不擅長哲學思辨,對抽象的美的問題不感興趣,故沒有獨立地提出美的本質的問題,沒有産生獨立的美學;但是,中國詩學的起源中包含着美學問題,故美學與詩學同源同體。因爲,在詩學問題的思考中,不僅包括詩的倫理性質和教化作用,也包括詩的感性、動情的性質和作用。在藝術實踐中,僅僅用倫理標準來評價藝術並不全面,藝術作爲動情之物,除了善的品格和理性內容以外,還有情感內涵和形式的特徵,這就是美。於是,對美的思考就形成了美學思想。《論語·八佾》記述了孔子在聽完《韶》樂、《武》樂所說的話:“子謂《韶》:‘盡善矣,又盡美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這裏用了“善”“美”兩個標準評價藝術,這意味着詩具有善和美兩種品格,於是詩學中就包含了對美的研究,形成了美學思想。在詩學論述中,美和善共同成爲藝術的本質特徵,如荀子就得出了“美善相樂”的結論。中國的詩學和美學思考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産生的。由於哲學思維不發達,對美的思考沒有形成理論體系,美學沒有獨立,美學思想主要在詩學中得到闡發,因此美學詩學化,詩學通美學。
總之,中國詩學起源於對禮樂文化演變生成的早期藝術的性質和作用的思考,包含着對藝術的倫理屬性和美的屬性研究,因此,中國詩學和美學具有共生性,詩學中包含着美學思想。
二 學科的性質: 形上形下二分/體用一元
不同學科的性質,決定了學科之間的關係,美學與詩學的關係也是由各自的性質決定的。因此,中西美學與詩學各自的性質決定了它們的相互關係。
在西方,美學歸屬於哲學。哲學是形而上學,是“愛智慧”,而美學就是對抽象的美的思辨,它一開始就與哲學本體論結合在一起,美被界定爲實體(本體)的屬性。也就是說,西方美學從本體論出發,考察美的性質,是一種形而上學。柏拉圖認爲,理念是實體,經驗對象是理念的摹仿,而美是理念的光輝,審美是超驗的對理念的洞見。這就提出了美的超越性觀念。這個觀念在中世紀就演變爲美是上帝的屬性——超越世俗之美,在現代就演變爲審美的自由性。西方美學體系是自上而下的邏輯推演,就是從哲學本體論出發,把美當作實體的屬性,演繹出一個理論體系。這個傳統在德國古典美學中得到典型的體現。康德劃分了現象領域與本體領域,這兩個領域不能溝通,具有二律背反的性質,而審美則成爲溝通現象領域與本體領域的中介。他由此推導出審美的四個契機,即“無利害的愉快”“無概念的普遍性”“無目的的合目的性”“共通感”,並且得出了“美是道德的象徵”命題。黑格爾則從理念出發,經過邏輯—歷史的行程,確定美是理念向絕對精神回歸的感性階段,推導出了“美是理念的感性顯現”的命題。現代西方美學也繼承了這個超越性傳統,以審美作爲自由的生存,肯定了美學的形而上學性質。
西方詩學是關於詩藝的知識學,是對詩的經驗的概括,因此,詩學不具有形而上的性質,也不能與美學溝通。古代詩學理論認爲,詩的本質是摹仿,而不是“美”。亞里士多德以摹仿的更高的真實性(普遍性和可能性)把詩與歷史相區別。詩學的研究對象是“詩”,詩學是一種關於詩的“技藝”的知識,具有經驗性,因此與形而上的美學分離。亞里士多德不同意柏拉圖的理念本體論,也不同意其藝術間接摹仿理念的觀點,而是從經驗的維度研究“詩”。亞里士多德把“詩”的本質規定爲“摹仿現實”,認爲詩的本質在於能夠摹仿普遍的事物以及可能發生的事物,因此與敍述個別事物和已經發生的事物的歷史相比較更具有本質性和普遍性。他說:“詩人的職責不在於描述已經發生的事,而在於描述可能發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發生的事。歷史家與詩人的差別不在於一用散文,一用韻文;希羅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寫爲韻文,但仍然是一種歷史,有沒有韻律都一樣;兩者的差別在於一敍述已發生的事,一敍述可能發生的事。因此,寫詩這種活動比寫歷史更富於哲學意味,更被嚴肅地對待,因爲詩所描寫的事情帶有普遍性,歷史則敍述個別的事。”①[古希臘]亞里士多德:“詩學”,《詩學,修辭學》,第41頁。他還認爲,惟妙惟肖的摹仿産生了快感,從而形成了藝術的趣味性。可見,西方詩學對藝術的定性,在於其真實性,而不在審美屬性。
美學研究抽象的美的本質,詩學則研究具體的藝術特性,如對悲劇、喜劇的研究。亞里士多德具體分析了悲劇的六個要素,如悲劇的成因、悲劇的淨化心靈功能等等。古羅馬的賀拉斯繼承了亞里士多德的詩學思想,對詩藝做了廣泛的研究,如對悲劇做了這樣的定義:“藉引起憐憫與恐懼來使這種情感得到陶冶。”中世紀的文化是宗教主宰的,詩學歸屬於修辭學,喪失了獨立性;也沒有獨立的美學,真善美成爲上帝的屬性。因此,比厄斯利說:“詩與三學科中的修辭學相聯繫,音樂列於四學科之中,而美的問題是神學的一部分。他們沒有專門的關於美的藝術的概念,也沒有將諸種美的藝術組合起來,同樣,也沒有使之形成一種獨特的哲學問題的意識。”②[美]門羅·C. 比厄斯利:《美學史:從古希臘到當代》,第167頁。文藝復興運動之後,詩學得到重建。17世紀,新古典主義詩學達到了一個高峰,布瓦羅對戲劇的思想內容、結構形式、語言風格做出了嚴格的規定,制定了嚴整的藝術規範;同時,新古典主義的理性化傾向也導致了古典詩學最終被浪漫主義詩學顛覆而走向終結。
西方古代詩學提出了獨立的詩學範疇,最初這些範疇還不是美學範疇。古希臘羅馬詩學考察了“悲劇”“喜劇”等戲劇類型,並且對二者的性質、功能做出了規定,使之成爲一種詩學範疇。古代詩學還提出了“崇高”範疇,古羅馬的朗吉努斯首次論述了“崇高”概念,將它作爲一種詩學的風格。以後,新古典主義詩學以崇高爲主要範疇,以崇高來闡釋悲劇。在古典時代,悲劇、喜劇和崇高衹是詩學範疇,還不是美學範疇。古代西方美的概念僅僅指“美好”,大致上相當於現代的“優美”,而不包括其他審美範疇,如醜、崇高、悲劇、喜劇等,因此不能涵蓋所有藝術,美學也因此不能成爲藝術哲學。
在古代中國,美學與詩學在特性上沒有分離,美學思想寓於詩學之中。
首先,古代中國的人文學科沒有充分分化,美學學科也沒有獨立。在春秋戰國時期,雖然美學問題提出了,也有美學論述,但並沒有發生現代那種真、善、美充分分離的狀況,而是有限的分離,它們仍然聚合在一起,互相關聯。在中國學術理論體系中,文、史、哲、倫理、政治各個領域雖然有了初步的分化,但始終沒有充分分離,保持着緊密的關聯性。其中,哲學也沒有獨立爲一個專門的學科,仍與神學、倫理學等混雜在一起,形成了關於“天命”“道”的論說。這樣,作爲哲學分支的美學學科,更沒有形成和獨立出來。中國美學思想沒有形成獨立的理論體系,而是包含在對世界人生的總體論述之中。諸子百家多有關於美的論述,但大都包含在對社會人生的思考之中,沒有形成獨立的藝術哲學。例如,孔子把詩歌、藝術納入禮樂文化的總體建構中,與對社會人生的思考聯繫在一起。《論語·泰伯》云:“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在這裏,藝術(包括詩、樂)是人生總體志趣以及人格修養、社會教化的一部分,是道德修養的途徑。錢穆認爲,孔子這一論述說明,詩、禮、樂是心性養成的過程,不能分割開來。①錢穆:《論語新解》(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第207頁。也可以這樣理解:“興於詩”,是說詩可以喚起人的情感、志向;“立於禮”,是說要以禮處事,規範情感、行爲;“成於樂’,是說在樂中達到理與情的和諧統一,養成完美人格。《禮記·樂記》云:“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這裏談論的是整個政教制度,而樂是其中一個方面,是爲社會教化服務的。孔子教導後代:“小子何莫學夫詩?夫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論語·陽貨》)還說:“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這裏所說的興、觀、群、怨以及言,都是藝術的社會作用,包括審美作用,但不止於審美作用。
其次,古代中國的美學思想沒有形成體系,沒有成爲一個獨立的學科,此即所謂“有美無學”。這與中國哲學的“體用不二”性質有關。中國有哲學思想,先秦的道家哲學品格較爲鮮明,提出了“道”爲本體論範疇的哲學論說;漢代,董仲舒建立了一個儒家的神學哲學;魏晉時期,形成了帶有哲學思辨性的玄學;宋明理學則建立了一個以“理”爲本體論範疇的儒家哲學體系。至此,中國哲學走向成熟。但是,在這個哲學體系中,並沒有形成一個獨立的美學學科。這是因爲,中國哲學建立在“天人合一”觀念之上,具有“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的特性,也就是非形而上學的特性。這種哲學與倫理學沒有充分分化,是一種倫理化的哲學。中國主流哲學即儒家哲學主要是爲倫理做論證,而美學問題是作爲倫理學的附屬問題提出來的。由此,美學衹能依附於倫理學,作爲倫理學的附屬問題展開論述,當然就不可能形成獨立的美學。儒家對美的性質做了比較多的論述,主要集中於文道關係問題,道作爲本體,展開了美學論述。但是,道有兩重性,既有超越性,是作爲哲學本體論範疇的天道;又有現實性,是作爲倫理學範疇的人道,故文道關係包括了美學論述,也包括了倫理學論述。由於道的倫理性,文道關係就側重於美善關係,美成爲善的形式,所以荀子說“美善相樂”,朱熹說“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②〔宋〕朱熹:《四書集註·論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上冊,第86頁。。這導致了美學思想依附於倫理思想,故很難形成獨立的美學學科。
古代中國的美學也有哲學性論述,主要從本體論上考察美和藝術的根源,揭示美和藝術的本質。先秦諸子在關於道的論述中推演出了美(文),也做了關於美的本質的論述,使中國美學具有了形而上的源頭。道家美學擁有哲學思辨的特徵,如老子對道的論述就是一種哲學思辨,而由此得出的美就具有了形而上的品性。老子認爲,“無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世俗之美非真美,故很少使用“美”的概念,而常用“妙”“玄”表達真美。他將“妙”“玄”視爲道的屬性,認爲體現了自然天性。莊子也對美做了哲學思考,認爲真美不在異化的世俗世界,而在自然本體,“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至樂無樂”,因此要“原天地之美”。儘管如此,道家的美學思想並沒有展開,它被同化在哲學表述中,美幾乎是自然的同義詞,沒有獲得獨立的考察,因此也沒有形成獨立的美學學科。儒家美學也有一些哲學論述,但這種論述是爲了克服詩學的經驗性局限,爲藝術的本質做終極論證,故從本體論角度論述美的性質。由於道具有體用不二的性質,道作爲倫理範疇被規定爲善、仁,因此,美與善、仁同源。孔子說,“里仁爲美”;孟子認爲,道體現於人性之中,而人性的充實就是美即“充實之謂美”;荀子說,“美善相樂”。這種哲學論述並不充分,更多地是一種倫理學的思想表達。甚至在儒家著作中,“美”“善”概念往往是不分的,許多“美”的概念和判斷,實際衹是一種“善”的概念和判斷。衹是在《文心雕龍》中,劉勰以道爲本體,論證了美是道的體現即所謂“道之文”。這是帶有哲學性的論述,但這種邏輯論述沒有充分展開,衹是在《原道》《徵聖》《宗經》三篇中得到貫徹。由於邏輯的推演和證明的薄弱,關於美的本質的論說沒有形成嚴謹的邏輯體系,也沒有産生專門的著作,而呈現爲片段化的狀態。美學論說多散見於各種典籍之中,不成體系。嚴格地說,作爲獨立學科的中國美學並沒有形成,它還缺乏完整的哲學論述。
古代中國的美學論述主要體現在詩學論說中,美學與詩學同體。儒家在吸收了道家、佛家思想後,建立了系統的詩學理論。劉勰接受了印度的“因明學”也就是邏輯學,因此,《文心雕龍》具有一定的邏輯性和哲學思辨性,但並不充分。《文心雕龍》前三篇即《原道》《徵聖》《宗經》,演繹了從道到文的邏輯行程,即“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得出了“道之文”的美學觀。這種關於美的本質的推演和論述,帶有邏輯性和思辨性,屬哲學—美學論述。但是,這種哲學—美學論述僅僅限於前三篇,而其餘各篇的內容主要是闡述各種文體的特徵以及具體的藝術規律,如文的演變、風格、創造、接受等。這些論述主要出自藝術經驗,與哲學論述脫節,屬於詩學範圍。在《文心雕龍》以後,産生了多種詩學著作,但關於美的本質的直接論述很少,也沒有形成系統的美學體系,更多的是關於詩歌特性的詩學論述。也就是說,思辨的美學傳統並沒有發展爲主流,而僅僅成爲詩學的一種形而上的補充。
古代中國的美學論述雖然不成體系,但詩性思維發達,美學詩學化,美學思想寓於詩學中。中國詩學發端於先秦諸子,奠基於《詩大序》《樂記》,成體系於《文心雕龍》,以後進一步得到發展完善。中國詩學與西方詩學有一個根本的不同,即它沒有與美學分離,而是與美學融合在一起。中國詩學不僅僅是藝術經驗的總結,還包含着美學思想,具有形而上的維度。中國美學與詩學是兩個不同的論說模式,一個是自上而下的推演,一個是經驗性的概括,但它們往往結合在一起。美學論說是從道本體出發,演繹出文的本質,如《文心雕龍》的“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就是一種美學性的論說,它得出了“道之文”“文以明道”的結論。詩學論說是從藝術經驗出發,得出詩的情感特性。中國的詩學基本上是圍繞情感論展開的,情成爲以詩爲代表的藝術的基本屬性,也成爲詩學論述的主題。《詩大序》把“言志說”做了情感論的闡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禮記·樂記》認爲,音樂之美源於感物生情:“凡音之起,由人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與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在六朝時期,禮教衰微,審美意識覺醒,情從志中獨立,興情說發生。陸機《文賦》云:“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揭示了詩歌的情感特性。劉勰以道爲文定性,認爲文是道形式;同時又認爲情是文的本性,提出“情文”概念,從而使情與道並列而具有了本體論的地位。《文心雕龍》在總體論上是理性化的明道論,偏於哲學—美學論述;而在具體展開時又是感性化的主情論,偏於詩學論述。劉勰在《原道》《徵聖》《宗經》以後各篇中主要講言志、緣情,他在《文心雕龍·情采》中說:“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也。”這種論述向情感論傾斜。以後的詩學言志說轉化爲緣情說,成爲中國文論的主流,而“情”成爲中國詩學的基本範疇。宋代嚴羽在《滄浪詩話·詩辨》中已有藝術獨立於意識形態思想的萌芽,強調詩歌表達的主題、情趣與世俗倫理的區別:“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這個“別材”“別趣”是以情感爲主綫的。
古代中國的詩學論述與美學論述結合在一起,構成了美學、詩學一體化的形態,但還是以詩學論述爲主。《文心雕龍》前三篇是一種形而上的哲學論述,但以後各篇也沒有展開對美的本質、美學範疇的系統論述,沒有把“文以明道”推演到藝術的各個環節,而是離開了美學論述,展開了詩學論述。其卷二至卷五主要論述諸文體的特性,如《明詩》《樂府》《詮賦》《頌贊》諸篇;卷六則闡述風格和創作手法等文的內在特性,如《神思》《體性》《風骨》《通變》《定勢》諸篇;卷七則主要闡述了文的形式特徵,如《情采》《熔裁》《聲律》《章句》《麗辭》諸篇;卷八則主要論述創作手法,如《比興》《誇飾》《事類》《練字》《隱秀》諸篇;卷九則主要論述創作經驗,如《指瑕》《養氣》《附會》《總術》《時序》諸篇;卷十則主要考察創作和欣賞等方面的問題。總之,《文心雕龍》用主要篇幅做出了詩學論說,建構了一個詩學體系。以後的詩學著作,直接的美學論述更少,多在詩學論述中表達美學思想。
由於詩性思維發達,邏輯思維薄弱,古代中國成體系的詩學理論不多,衹有《樂記》《文心雕龍》等少數著作,更多的詩學著作是藝術鑒賞和藝術批評,包括詩論、畫論、戲曲評論、小說評點等,著名的有《詩品》《二十四詩品》《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第六才子書王實甫西厢記》等。在近代,王國維吸收了西方美學思想,但也沒有寫出純粹的理論著作,而多採取藝術批評的方法,如《人間詞話》就以詩詞鑒賞、評論的方式表達其詩學、美學思想。
總之,古代中國的美學與詩學融合在一起,是特殊的美學和特殊的詩學。中國比歐洲更早地用美學觀念來闡釋和評價藝術,也比歐洲更早地把美學當作藝術哲學。由此,中國詩學就具有了美學的品性,成爲一種美學的形態。
三 學科的演變: 藝術哲學統領藝術理論/詩學美學化
不同學科各自的歷史決定了學科之間的關係,美學與詩學的關係也是由各自的歷史決定的。但中西美學與詩學的關係是發展變化的,特別是近代以來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西方詩學是在古希臘形成的關於史詩、敍事詩、戲劇等語言類藝術的理論,亞里士多德是詩學的奠基人。在亞里士多德之後,詩學傳統由賀拉斯、朗吉努斯等繼承發揚。在中世紀,詩學成爲神學的附庸,隸屬於修辭學。文藝復興運動之後,詩學得到復興,並且在新古典主義時期達到頂峰。18世紀之後,詩學與美學溝通,最終轉化爲包括各個門類的藝術理論。
在近代,西方古典詩學面臨着三大挑戰,最後走向終結。第一個挑戰是主體性的現代藝術觀念和藝術思潮的興起,顛覆了詩學的“摹仿現實”的基本理念。在文藝復興、啓蒙運動發生之後,古典藝術向現代藝術轉化,傳統詩學的“摹仿”說不再能合理地給以闡釋。這時主體性的藝術觀念發生,打破了建立在客體性哲學之上的傳統詩學理念。亞里士多德的“摹仿現實”觀念被重新闡釋,變成了“摹仿自然”。它既包括了摹仿外在的自然,也包括了摹仿內在的自然。這意味着摹仿說的變質,帶有了主體性。新的藝術理念以創造取代了摹仿觀念,倡導想象、激情、靈感、天才,從而瓦解了傳統詩學的客體性原則。啓蒙主義藝術具有平民精神,以市民爲主體的喜劇、小說、正劇等瓦解了傳統詩學的貴族精神,趣味性取代了崇高性,從而顛覆了傳統詩學的理性法則。赫爾德以創造性否定了摹仿說,而席勒提出了“素樸的詩”與“感傷的詩”的區分,實際上把後者劃到“摹仿”說之外,成爲主觀思想情感的表達,這使得傳統詩學失去了部分的解釋效力。浪漫主義反對藝術的現實性、規範性、權威性,倡導象徵性、幻想和彼岸性。這些新的藝術思想都與古典詩學不合,於是,傳統詩學走向衰落。第二個挑戰是“詩”的分化。近代以來,作爲語言藝術的“詩”分化爲更爲具體、複雜的形態,如詩歌分化爲抒情詩和敍事詩,戲劇分化爲歌劇、話劇、舞劇、歌舞劇等,而且傳統的悲劇、喜劇之外,産生了正劇,它們之間有巨大的形式、內容差異,整體性的“詩”不復存在,傳統的詩學不再具有解釋效力,於是傳統詩學解體,具體的詩歌理論、小說理論、戲劇理論、散文理論等取代了傳統的詩學。第三個挑戰是新的語言藝術樣式産生,突破了詩學的範圍。近代以來,史詩成爲陳跡,小說、話劇、散文等新的藝術樣式産生,特別是小說成爲現代文學的主要體裁,它們使用生活語言,脫離了韻文傳統,難以爲傳統詩學所容納。最初,詩學排斥小說,批評其低俗性;後來,又試圖容納小說。但這樣一來,傳統詩學就被突破,變成了廣義的藝術理論。基於以上原因,傳統的詩學解體了,變成了現代的藝術理論。
由於傳統詩學的解體以及藝術門類的分化,摹仿說已經喪失了解釋的功能,但藝術本質需要有一個新的規定,這個新的藝術本質是什麽呢?衹能是美。於是美的理念向藝術領域擴展,美成爲藝術的基本屬性,産生了“美的藝術”概念。比厄斯利考證出,夏爾·巴圖神父的《歸結爲同一原理的美的藝術》一書,最早提出了“美的藝術”思想:“藝術是對‘美的自然’的摹仿。巴圖將詩歌、繪畫、音樂、雕塑和舞蹈包括進來,這也許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將‘美的藝術’定義爲一個特殊的範疇。”①[美]門羅·C.比厄斯利:《美學史:從古希臘到當代》,第261頁、第259頁。於是,藝術統一於美,美是藝術的本質,“美的藝術”的理論應運而生。
與傳統詩學解體以及“美的藝術”概念産生的同時,西方美學也不斷向藝術領域擴展,最終把藝術列入美學的主要對象。柏拉圖時代,開啓了美學的形而上維度,排除了形而下的藝術。但是,到了18世紀,隨着哲學的認識論轉向,近代美學以主體論代替了客體論,“美學之父”鮑姆嘉通給美學命名爲“感性學”,審美成爲感性認識的完善。這個定義,使得美學可以向一切藝術開放,因爲藝術被認爲具有感性特徵,而且是“完善的”感性認識。不僅傳統的“詩”,而且“詩”以外的一切藝術都可以成爲美學研究的對象,它們都具有了美的品格。這也就是說,作爲感性學的美學可以以感性的名義把藝術納入美學範圍。鮑姆加通說:“詩指一個完善的感性話語,詩學指一首詩所遵循的一套規則,哲學詩學指詩學的科學。”②[美]門羅·C.比厄斯利:《美學史:從古希臘到當代》,第261頁、第259頁。這裏把詩作爲完善的感性話語,成爲一種美的形態。此外,他還提出了“哲學詩學”即美學的概念,用美學來統領詩學。與此同時,悲劇、喜劇和崇高範疇從詩學進入美學,與美一樣成爲美學範疇,這在康德美學中得到確認。這就導致美學成爲藝術哲學,並且統領了藝術理論,
在中國,美學與詩學的歷史走了一條與西方不同的道路,二者的關係也發生了與西方不同的演變,這就是詩學美學化。古代中國美學的論述主要體現在“道”與“文”的關係方面,如《文心雕龍》論述的“文以明道”,是說美是“道之文”即道的形式。但道具有兩重性,就是作爲形而上的本體論範疇和作爲形而下的倫理學範疇,二者沒有明確地分化,故美學思想並不獨立,還依附於倫理學思想。宋明理學建立了道(理)本體論哲學,這個哲學把道理性化,提出了“存天理,滅人慾”的主張,甚至表達了“文以害道”的思想,這使得感性和藝術的合法性受到了威脅。這表明,以“道”論“文”的路徑走向反面,道學具有了反美學的性質,不能再爲美和藝術做終極論證,從而導致了傳統美學論述的終結。
但是,中國美學思想並未消失,而是在詩學中發展壯大。它避開了文道關係的論述,專注於藝術的情感性論述,進一步建立了情本體論。在古代社會後期,在程朱理學之外,陸王心學提出了“心即理(道)”的思想,以心爲本體。據《陽明全書·答季明德》載,王陽明重新解釋了天人合一,把萬物歸結爲心:“人者,天地萬物之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這種主觀論思想本意是爲了約束人心,把心理性化,以達到“去心中賊”的目的,但其內在邏輯卻使心偏離了理,而導向了情。王學左派開始使心性脫離“理”的羈絆,轉化爲感性本體。於是,作爲心性的體現的情就擺脫了理的桎梏而獲得了獨立,成爲宇宙本體和藝術的本質,從而建立了情本體詩學。明中葉以後,詩學思想大變,審美意識獲得獨立。徐渭以“摹情”論藝術,使情具有了本體論的意義:“人生墮地,便爲情使。……迨終身涉境觸事,夷拂悲愉,發爲詩文騷賦,璀璨偉麗,令人讀之,喜而頤解,憤而眦裂,哀而鼻酸,恍若與其人即席揮,嬉笑悼唁於數千百載之上者,無他,摹情彌真則動人彌易,傳世亦彌遠。”①〔明〕徐渭:“選古今南北劇·序”,《中國古典戲曲序跋集》(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90),第67頁。袁宏道在《序小修詩》中提出“性靈”說,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湯顯祖在與達觀法師的信《寄達觀》中,把情與理對立起來,認爲情不受理法約束,爲藝術所獨有:“情有者,理必無;理有者,情必無,真是一刀兩斷語也。”他在《牡丹亭題辭》中認爲:“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盡。自非通人,恆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無,安知情之所必有也。”這就宣告了審美之情與意識形態(理)的分離。程允昌《南九宮十三調曲譜序》記載湯顯祖駁斥張位對其“言情不言性”的責難:“公所講者是‘性’,我所講者是‘情’。離‘情’而言‘性’,一家之私言也;合情而言‘性’,天下之公言也。”這就駁斥了理學家揚性而抑情的觀念,把情與性同列爲本體。馮夢龍在《情史敍》中,認爲情乃宇宙本體:“天地若無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無情,不能環相生。”“萬物如散錢,一情爲綫牽。”他甚至提出了“立情教”的主張:“我欲立情教,教誨諸衆生。”“願得有情人,一齊來演法。”以“情教”代替“禮教”,使情取代理(道)而成爲本體,成爲審美和藝術的依據。袁枚在《與程蕺園書》中倡導性靈之說,也以情爲本:“且夫詩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後又必不可朽之詩。”劉熙載主張寓義(理性)於情,寓情於景,是爲文之本,他在《藝概·詩概》中寫道:“詩或寓義於情而義愈至,或寓情於景而情愈深。”
古代中國後期的詩學建立了情本體論,這個情不是日常之情,而是真情,也就是人的本性的流露。徐渭在《西厢序》中提出“真我”說,這個“真我”即人之“本色”,而與之相對的是假我即“相色”,因此主張要“賤相色,貴本色”。李贄反對理對人性的戕害,收錄於《焚書》中的《童心說》認爲,天下之至文莫不出自童心:“夫童心者,真心也。……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童心既障,於是發而爲言語,則言語不由衷;見而爲政事,則政事無根底;著而爲文章,則文辭不能達。非內含以章美也,非篤實生輝光也。欲求一句有德之言,率不可得。所以者何?以童心既障,而從外入者,見聞道理爲之心也。”明確指出童心與見聞道理的根本衝突——童心是未被世俗污染的真心、本心,而見聞道理就是“從外入者”的宗法禮教,是對童心的障蔽。黃宗羲在《論文管見》中還把至文與至情聯繫起來,認爲至情是至文的根據:“蓋情之至真,時不我限也。斯論美矣。……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這些論述均反映出,中國詩學的後期發展,建立起情本體論,提出了“真情”“至情”說,使之超越現實情感,成爲本體。這意味着,詩學發生了革命性的改變,具有了自己的哲學基礎,形成了超越性的美學思想,從而具有了美學性質。可以說,在中國詩學身軀之內,躁動着一個藝術哲學的靈魂。由此表明,中國詩學的發展,最後形成了一個美學化的詩學。
進入現代以來,古代詩學解體,從西方傳入的現代美學和藝術理論成爲主流。但是,中國古典詩學、美學思想並沒有消亡,它在與現代美學和藝術理論的對話、融合中將彰顯其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