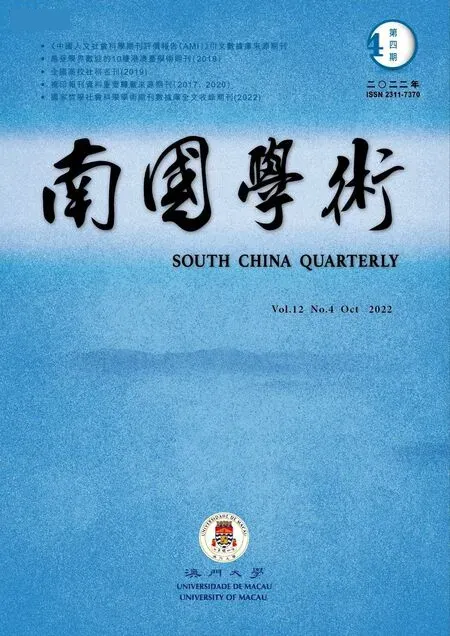精神人文學論綱
胡偉希
[關鍵詞]精神 人文理性 天人感應 人文學文本 審美教化
精神人文學是研究“人是什麽”的學問。這種關於“人”的研究之所以稱作“精神人文學”或“精神的人文學”,在於它是從人的“精神性”存在立義,從而與通常的人文學科對人的理解區別開來。①本文所說的“精神”,是指具有超越性的宇宙之終極實在;而人的“精神性”,則指人的具有超越現象界生存的形而上學本性。本文視“精神性”爲人的本質規定。關於以人的“精神性”爲研究對象的“人文學”與一般作爲學科概念的“人文學科”的區別及其論證,見胡偉希:“論人文學作爲‘精神科學’”,《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2016):119~128。精神人文學從作爲宇宙的終極實在的“天理”之處尋求人的超越的精神性存在之依據。在這方面,它與強調有宇宙之最高存在者和造物主的“上帝”,以及人的超越精神性亦是來自上帝的基督教神學思想有相通之處。但是,“精神人文學”對人的精神性的理解又是“人文的”而非“神學的”。這樣一門既是“精神”又是“人文”的關於人的學問如何可能,其對人的精神性成長與教化來說意味着什麽,這是本文所要探討的。而這一切,都要從對這個問題的歷史溯源開始:即“人的科學”的研究爲何要關注人的精神實在性?如何理解以人的“精神性存在”作爲研究對象的“精神科學”?
一 《實用人類學》與現當代的“精神科學”研究
無論從何種意義上說,康德哲學對現當代哲學的影響都不容低估。這表現在:無論同意康德哲學的具體觀點與否,但所討論的哲學問題或者哲學話語都與康德思想有關。然而,即便如此,康德哲學對後人最值得重視與發掘的思想遺産是什麽,卻也成爲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不過,儘管康德哲學的內容恢宏龐大,似乎囊括了天地宇宙以及世界一切問題,但他畢生關注的問題其實衹有一個,即“人是什麽”?爲此,他曾將他著名的“三大批判”視爲對“人是什麽”的一種奠基性研究。②1793年,康德在致卡·弗·司徒林的信中總結他一生從事學術研究的關切時說:“在純粹哲學的領域中,我對自己提出的長期工作計劃,就是要解决以下三個問題:1.我能知道什麽?(形而上學)2.我應做什麽(道德學)3.我可以希望什麽?(宗教學)接着是第四個,最後一個問題:人是什麽?(人類學)二十多年來,我每年都要講授一遍。”〔鄧曉芒:“中譯本再版序言”,[德]康德:《實用人類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2頁。〕海德格爾對康德的“三大批判”到底“言說”的是什麽也作過專門的討論〔孫周興 選編:《海德格爾選集(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第98~99頁〕。而到生命的晚年,他終於身體力行、花費心力撰寫了《實用人類學》一書,系統地展示其“人類學”思想。該書在開篇寫道:
在人用來形成他的學問的文化中,一切進步都有一個目標,即把這些得到的知識和技能用於人世間;但在他能夠把它們用於其間的那些對象中,最重要的對象是人:因爲人是他自己的最終目的。所以,根據他的類把他作爲具有天賦理性的理性生物來認識,這是特別值得稱之爲世界知識的,儘管他衹佔地上的創造物的一部分。③[德]康德:《實用人類學》,“前言”第1、3頁。
這說明,康德是將“人類學”的知識視爲最高的知識,甚至是理解其他一切“世界知識”包括哲學知識在內的“鑰匙”。他接着寫道:
人能夠具有“自我”的觀念,這使人無限地提升到地球上一切其他有生命的存在物之上。因此,他是一個人,並且由於在他可能遇到的一切變化上具有意識的統一性,因而他是同一個人,也就是一個與人們可以任意處置和支配的、諸如無理性的動物之類的事物在等級和尊嚴上截然不同的存在物。甚至當他還不能說出一個“我”時就是如此,因爲在他的思想中畢竟包含着這一點:一切語言在用第一人稱述說時都必須考慮,如何不用一個特別的詞而仍表示出這個“我性”。因爲這種能力(即思考)就是知性。④[德]康德:《實用人類學》,“前言”第1、3頁。
這段話點明了康德在《實用人類學》一書中對“人是什麽”的基本看法,即認爲“人之爲人”的核心元素是“自我”;而人之所以能夠産生出“自我”意識,在於他具有一般動物所缺少的“知性”。這說明:《實用人類學》是從“知性”出發來對“人之爲人”加以界定的。如果說開篇這段話與康德《純粹理性批判》的思想內容還銜接得上的話,那麽,書中接下來對“實用人類學”思想的具體發揮與論證,就與前面康德所說的對“三大哲學問題”的思考完全無關了。
關於“人類學”的著作應當如何撰寫,康德本人其實有着清醒的意識。他認爲:“一種系統地把握人類知識的學說(人類學),衹能要麽存在於生理學觀點之中,要麽存在於實用的觀點之中。生理學的人類知識研究是自然從人身上産生的東西,而實用的人類知識研究的是人作爲自由行動的生物由自身作出的東西,或能夠和應該作出的東西。”①[德]康德:《實用人類學》“前言”第1頁。這裏,儘管康德提到“實用的人類知識研究”要以“人作爲自由行動的生物由自身作出的東西”,但事實上,從《實用人類學》的內容來看,它衹是一種從經驗現象的角度出發來對作爲“社會人”的“人”所作出的描述與說明,而非像他所說的是關於“世界公民在人類學方面”的“總體知識”。②本文儘管認爲康德的《實用人類學》稱不上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哲學人類學”,但依然肯定他從“哲學人類學”出發來尋求“人是什麽”這一問題的思路;同時,也充分肯定海德格爾從康德的“三大批判”出發來尋找“人是什麽”答案的問題意識。
這就帶來一個問題:在《實用人類學》中,爲什麽康德不沿襲他寫作“三大批判”的思路,從先驗而非經驗的角度來對“人”作爲地球上的“類存在”加以審視,卻沿着傳統的或者說一般的經驗描述甚至通常人類學的經驗收集方法,滿足於實證的甚至簡單的材料歸納的方法來對“人是什麽”這個他關心的重要問題加以論述呢?顯然,這個問題不能簡單地歸結爲他的哲學思考的方法論原則發生了變化,而衹能說是他晚年關於“人是什麽”這個問題的看法與寫作“三大批判”時候的觀念相比發生了變化。對於晚年的他來說,“人”已經不是那個具有“形而上學”衝動的“有限的理性存在者”,而純粹成爲一種雖然具有“知性”,甚至也具有“愉悅”情感以及“道德慾望能力”的社會人的存在,但這種從社會人的視角來透視或者說認識人之行爲、心理與意識的看法,與“三大批判”中強調人之自由精神的觀念相去已遠。一句話,雖然《實用人類學》也仍然襲取了“三大批判”中的一些名詞用法,但其含義與“三大批判”中的思想觀念已發生了斷裂。可以說,後期康德在對“人是什麽”問題的認識上,已有了轉變:如果說在“三大批判”中,康德設想的“人”是“有限的理性存在者”,是一種追求形而上學的動物,是具有超越的精神性向度的人的概念的話,那麽,在《實用人類學》中出場的“人”,卻是一種在知性水平上不同於地球上其他動物,而其生存狀態完全處於現象界之生存中的關於人的概念。
後期康德關於“人”的這一看法,對後來追隨康德思想的研究者來說影響深遠。一方面,他們繼承了康德關於“人是目的”以及人是具有自由意志的動物的這一早期思想路綫,強調哲學是關於人的哲學,重視道德哲學以及實踐哲學的研究,並且開創了以研究人的精神性爲主題的“精神科學”的新康德主義哲學路綫;另一方面,這個學派同時亦繼承和發展了康德在《實用人類學》中將人之“精神性存在”理解爲人之心理過程或者意識活動的這一經驗現象性描述的研究方法與路綫。這方面,影響頗大並且被視爲具有學術“典範”意義的有卡西爾、狄爾泰。他們兩人雖然分別從“符號學”與“精神科學”的角度深化了人們對“人”的認識,但終極地看,這種對於“人”的研究之前提假設,卻依然以康德《實用人類學》的問題意識與學術範式爲限,即將人視爲“現象界的存在者”,而非真正的“精神性的存在者”。從這種意義上說,儘管以狄爾泰爲代表的新康德主義者開創了一門以研究人的精神作爲對象的“精神科學”,但這種“精神科學”卻未必是“三大批判”中的關於人的精神性存在,而僅成爲康德《實用人類學》中的思想觀念之延伸或餘緒。這種關於人的精神性現象的研究,無論其內容與角度如何多變,卻無一例外地是滿足於對於經驗現象層面的實證式的資料收集與概括之類的研究。即便像狄爾泰一直強調精神科學在方法論上與自然科學的方法有別,但在具體研究中其實也衹是一種改頭換面的自然科學研究方法及其擴展,這與從哲學高度對人的精神性研究的維度相差甚遠。
也許,海德格爾算得上是當代少有的從哲學意義上對康德“三大批判”作尋根式追問的學者(這一點與新康德主義者衹知追隨康德的《實用人類學》思想不同)。在他看來,康德所謂的《實用人類學》其實算不上是真正意義上的“哲學人類學”:
哲學人類學之所以能被稱爲哲學的,是因爲它的方法是哲學的,例如在對人的本質考察這個意義上。所以,這個考察的目的是把我們稱爲人的這個存在者與植物、動物和其他存在者的領域相區別,並以此來強調這一存在者的特定區域的特有的本質狀況。這樣,哲學人類學就成了一種人的區域存在論,而它本身仍然是和其他那些與之分享着存在者之共同領域的存在論相並列的。
人類學也可以成爲哲學的。衹要它或是規定哲學的目的爲人類學,或是規定哲學的開端爲人類學,或是同時規定兩者爲人類學。如果哲學的目的在於世界觀的制定,那麽一種人類學就會有必要去界定“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並且,如果人被卸任這樣一個存在者,他在建立某種絕對確定的知識時在次序上是絕對最先給予和最確定的東西,那麽這樣設計的哲學大廈就必定會把人的主體性帶進自己核心的根基之中。這第一個任務與第二個任務是可以結合起來的,雙方都能作爲人類學的考察而利用人的區域存在論的方法與成果。①孫周興 選編:《海德格爾選集(上)》,第102頁。
這兩段話的要義是:從哲學角度對“人類學”的研究,其實就是尋找“人之爲人”的本質根據問題;任何離開了關於人的本質的探討而去著手關於“人是什麽”的研究,都會陷入其他各種實用人類學。因此,關於“人是什麽”的問題首先是一個存在論的問題,然後纔是其他。
可惜的是,當海德格爾放棄康德的《實用人類學》的寫作思路,並且看到《純粹理性批判》其實是“給形而上學奠基”之作,試圖要從中挖掘出康德真正的“哲學人類學”思想時,卻竟然將《純粹理性批判》中包含的“人的精神性”這一思想精髓徹底拋棄,還將人的本體性存在歸結爲“時間性”。而所謂“時間性”,其實就是將人的存在視爲個體的“偶在”,將人理解爲變動不居的現象界中的偶然之物。這樣一來,海德格爾從存在論角度對康德《純粹理性批判》中哲學人類學思想的挖掘,雖然路徑、方法與新康德主義者不同,但其將康德的人類學思想理解爲現象界中的有限性存在,實乃殊途同歸。即言之,海氏本來是想通過對《純粹理性批判》的“批判”來展開關於“人是什麽”這一問題思考的,結果卻將“人”的“精神性”定位於現象界之偶然的“定在”。這與康德關於人是“具有超越的形而上學追求的動物”這一“精神性現象”的研究相距更遠。
二 世界是“精神的存在”
事實上,康德的“三大批判”並未正面回答或解釋“人是什麽”這個問題,而是將它蘊涵於“三大批判”的一系列問題討論之中。具體來說,在“三大批判”中,康德關於“人”的規定展現爲三個向度:知性的、意志的、情感的,它們分別對應於人的知覺能力、道德理性、審美批判力。但值得注意的是:與《實用人類學》僅從人的現象性生存的經驗層面來挖掘與考察人的這三種“精神能力”不同,“三大批判”是從人的形而上學層面來追溯人的這三種精神能力起源的。即康德將人的知性能力歸結爲先驗的感性與範疇,將道德理性歸結爲人的自由意志,將人的審美愉悅追溯到其無目的的合目的性。也就是說,“三大批判”是從人的先驗以及超驗的精神層面對人的經驗知性、道德理性、審美批判力予以分析與論證,從而說明,人從其天性上具有超越的精神性存在。這其中,核心的觀念是自由。故拋開其關於人的理論知性、道德理性、審美鑒賞力起源及其本性的具體論述,“三大批判”應當是康德關於人的精神性存在的極好論證與闡明。即人作爲不同於地球上其他生物體的本質規定——科學理性、道德理性、審美批判力皆屬於人類所特有的一種精神性。這種精神性,也就是衹有人纔會具有的超越於現象界生存的精神性維度。對康德來說,一切科學,包括自然科學、道德科學,乃至於藝術審美以及其他人文科學之産生及其本性的研究,皆須沿着“人類特有的精神性現象”這一思路進行“尋根式”研究。
然而,儘管“三大批判”包含着“人是精神性的存在”這一問題的思考,但康德關於這一問題的全部哲學論證遠未徹底地完成(像後來的《實用人類學》甚至走了彎路)。因此,“人是精神性的存在”這個問題還需重提。這與其說是對康德的哲學人類學思想的重新梳理與解讀,不如說是從康德的“三大批判”中關於人的“精神性存在”的思想出發,看看一種真正意義上關於“人的精神性存在”的科學建立是否可能?即言之,康德未能建立一門真正意義上關於“人的科學”,其哲學思維中究竟缺少了什麽?
康德展開其哲學視域以及進行哲學論證的根本出發點或者說哲學基礎,就是關於人的自我意識以及自由意志。而且,他的自我意識尤其是自由意志的概念包括先驗與超驗的維度,屬於人之超越的“精神性存在”範疇。更重要的是,他明確將人定義爲“有限的理性存在者”。但是,還應看到,康德不僅在“三大批判”而且在後來的研究中,並沒有據此思想觀念建立起“人的精神性存在”的思想體系。之所以如此,在於康德將人的精神性僅僅局限於人的知性能力以及自由意志。然而,將一門關於人的精神性存在的思想體系僅僅建立在自我意識、自由意志基礎之上,是無法建構起關於人的精神科學的學問來的。
“自我意識”在哲學史上的出現相當久遠,但自從笛卡爾以後,它纔作爲哲學認識論討論問題的出發點。儘管康德不滿意笛卡爾將自我意識視之爲“經驗的自我意識”,認爲它是一個關於“先驗統覺”的概念,但說到底,它在康德哲學語境中,始終還是一個“反思理論”的概念。在這種反思理論的框架下,康德強調自我意識超出了單純的知性認知的範圍,並通過“知性的限制”,知道還有那作爲“不可知之物”的“物自體”。從這一點上說,人對知性的限制的認識,體現了自我意識具有超出經驗現象的超越性。然而,這種超越性始終限制在先驗哲學的範圍,還說不上是純粹的人的精神性,充其量衹是人的超越的精神性的一個維度。爲了將人的超越的精神性存在的另一個維度——真正超越的精神性維度加以區分,本文將這種從人的自我意識出發呈現出來的精神性存在稱之爲“科學理性”,而將與之並立的另外一種不同於科學理性的人的精神性稱之爲“人文理性”,即從“人文”的視域來看待與理解世界的一種眼光與見識。之所以說它是“理性”的,因爲它是對“世界”的一種理解與認識,並且具有普遍的方法論與認識論意義,而非出於想象的或者偶然的“靈感”,甚至於純粹的“直覺經驗”。由於它與知性一樣是人類特有的心智性的思維活動,具有一定的理智思維結構,因而代表着人類特有的一種理性能力。這種人文性的理性思維能力,與僅僅訴諸於人類的知性能力的知性思維的區別是明顯的。它們二者之間的差異,並非在心智思維器官上有着根本的不同,而是在運用與駕馭這些心智思維器官的方式和方法上有着根本的不同。爲了深刻認識這種不同的表現,需要先從何爲人類的認識這個基本問題說起。
首先,人類的任何真實的認識活動都是指向對“世界”之“真實”的認識。這意味着,瞭解人類的認識活動,離不開對世界是怎麽回事的瞭解。但是,對世界是什麽的瞭解或知識,又反過來須追問人類的認識到底是怎麽回事。那麽,如何打破這種認識活動與認識“對象”之間的彼此纏繞與循環論證呢?海德格爾提出“沒有世界,衹有世界化”這個觀念。而世界化意味着什麽呢?所謂世界化,其實就是人在“認識”世界之前,對於人與世界之關係的一種“先行籌劃”。這種先於任何認識論的對世界的一種“籌劃”,決定了人如何去理解世界的方式。從這種意義上說,它屬於存在論而非認識論的領域。它先於人類對世界的認識而又決定人類關於世界的知識及其認知活動。爲了與通常的認識論的認識區別開來,這裏將這種關於世界的認識稱之爲世界“觀”。這種關於世界的認識,或者說世界觀,對於世界的認識具有總體性。所謂總體性,是說它不是關於外部世界之個別的、零碎的知識,而是從根本上決定世界全體是什麽的認識。
其次,這種對世界的總體認識還具有“人格性”,也即由人的“精神性存在”所決定。因此,爲了與通常作爲科學認識論之前提與出發點相聯繫的“自我意識”相區別開來,這裏將這種決定人的認識論與思維方式的關於世界之觀的先行領悟稱爲人的“精神性存在領悟”。一旦從人的“精神性存在領悟”的視域對世界加以審視,則會發現:人的精神性存在,或者說對世界的認識的人格性,其實體現爲兩種思維方式,即“科學理性”思維與“人文理性”思維。這兩種思維方式的根本不同在於,它們分別據於不同的世界之“觀”。所謂“觀”,是對世界的一種根本觀法,它取決於人與世界共在的“關係”。這種共在關係無非是兩種:“天人二分”的關係,“天人合一”的關係。①張世英認爲:“關於哲學之爲物,或者說,哲學的最高任務,有兩種觀點:一是人與存在合一、協調,一是把存在當作人所渴望的外在之物加以追求。”〔張世英:《走向澄明之境》(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第53頁。)〕與之相應的,人類關於世界的“觀”也無非是兩種:要麽是天人“二分”的世界觀,要麽是天人“合一”的世界觀。這兩種不同的“觀”對世界總體的看法差別甚大。所謂的科學理性思維,就是從這種天人二分的“觀”來看待世界的。這種思維的特徵是重“分別”,將世界劃分爲主體與客體。其結果,人與世界共在的關係也就被理解爲以認識主體爲一方,以及要去被認識的客體爲另一方的主客觀分裂的世界。不僅如此,在二分法思維的視域中,還表現在作爲世界總體或者說宇宙全體之二分,即現象界與超驗界的二分。而讓這種二分法思維一直貫徹下去,除了主客二分、形上與形下世界二分外,物與物、人與人都被二分。假如用一個名詞概括的話,這就是一個“有觀”的世界。由於人類具有科學的理性,這個有觀的世界可以被人類認識與利用。正是因爲科學理性體現了人類特有的、地球上其他動物所不具備的先驗能力與精神,它具有了超越的精神性維度。
但是,人類作爲具有“自由意志”②康德對“自由意志”的理解過於狹隘,認爲是一種道德選擇或者說服從於“最高絕對律令”(道德律令)的自由意志。其實。人類最高義的自由意志是其選擇如何與世界“共在”。這種自由意志屬於存在論層次而非存在者層次。的“有限性的存在者”,除了從科學理性的角度認識世界外,還有另外一種與世界共在的能力,此即“天人合一”的精神力。它具體表現爲,對人與外部世界合一的認識。在“天人合一”的世界觀中,世界並無所謂主體與客體的嚴格區分。或者說,所謂主客二分僅僅在科學理性的運用上具有認識論的意義,而從存在論的角度看,世界本來就是人與世界的合一。當然,這種合一是在存在論意義上說的,而非指實體上的同一。因此,從人的精神性存在的角度看,人與世界共有同一種精神性。而且,這種精神性是從超越的維度看的普遍宇宙精神。爲了將這種據於天人合一觀的思維與科學理性思維加以分別,這裏將它稱爲人文理性思維。從這種意義上說,人文理性的思維實乃指一種不同於科學理性之二分法思維的天人合一思維模式或者說世界“觀”。
三 人文理性思維的本質規定
人文理性作爲人類所特有的,並且與科學理性思維相對立的思維方式,其基本特徵是指對世界的理解是“天人合一”而非“天人二分”的。但是,這裏除了要避免對“天人合一”作實體性理解之外,還須注意的是:天人合一雖然是精神性的,但這種精神性存在卻又不能脫離人之肉身以及自然之天的聯繫。從這種意義上說,人的精神性的天人合一其實是寄寓在天人二分的人之肉身上的。也就是說,無論是個體或者群體,人其實都是作爲現象性的存在者(主客二分的有限存在者)與超越的純粹精神性存在(天人合一的精神)的合一。就人與世界是精神性的存在而言,雖然從本性上說是純粹性的超越性精神存在,但從具體的人與世界來看,卻又是超越的精神性與作爲現象界之存在者而存在(即便世界總體作爲“自在之物”來說也是如此)的。而人文理性作爲認識論與思維方式來說,它要處理和面對的問題其實是:人在生活於“實存”的“二分法”現象界時,如何去面對存在本身以及如何去追求和實現那超越的純粹精神性存在(“天人合一”之境)。
首先,人文理性思維是一種精神,然後纔是思維方式。即人文精神作爲人文理性的本體性存在,當它開始思維活動時,就呈現爲人文性的理性思維。從這種意義上說,人文理性思維是人文精神在思維活動過程中的外化形式。因此,談人文思維,首先要理解人文思維與人文精神的關係,即作爲人文理性思維的存在論與認識論之間的關係。要言之,人文性理性思維不僅在認識方法與認識手段上與作爲科學思維的方法不同,而且在認識的目的與達成的認識效果上也與科學思維不同,即人文思維所獲得的不是如科學思維那樣的對世界與人的“客觀知識”,而是關於世界的“存在性認知”。而這種認知必然首先與人的存在問題聯繫在一起,並且由人的存在狀態所決定。因此,人文理性思維對世界是什麽的考察,其實也是關於人是什麽的認識。由此看來,人文理性與其說是關於人與世界的客觀知識,不如說是關於人能夠認識什麽、人應當做什麽、人希望什麽的對人的一種終極性理解。也就是說:人文理性思維其實是關於“人是什麽”這一問題的存在論認知與理解。
其次,人文理性思維對人與世界認識的總體性與類型性。所謂總體性,是與科學思維的分解性區別而言的。科學理性的思維對世界(包括人在內)的認識分解爲各種不同的學科,採取分析的方法加以分門別類的研究;而人文理性思維則是從總體上對人與世界作通觀的認識與研究。這種通觀的研究與其說是對研究對象不作分門別類的區分,不如說是指對研究對象該採取什麽方法加以觀察,即人文理性思維強調研究方法的“通觀”,以達到從整體與全貌上對研究對象的理解。所謂類型性,是指人文理性其實是劃分爲各種類型的。就基本類型而言,人文理性思維可以歸納爲三種,即史學的、詩學的、哲學的。這與科學理性思維可以劃分爲各種不同的學科與研究迥然不同。其實,後者雖然有不同的學科群,但其方法屬於同一種類型,都採取數理的方法對人與世界作分別與分解的研究。
再次,作爲存在論的思維方式,人文理性思維其與說是認識世界與人的“方法”,不如說是人展示其生存狀態的方式與方法。從這種意義上說,人文理性思維是即認識即存在,集認識論與存在論於一身。這種思維方式說明,人文理性思維與人的精神性存在狀態有關。作爲一種精神現象,人文理性思維其實是通過人的“精神性質料”與世界交往並且進行思維的。即言之,關於人文理性思維的研究,不僅僅是關於人類認識世界的方法論研究,而且還是對人的生存狀態以及關於人的精神性存在方式之本性的闡明。換言之,人的精神性質料的存在是通過人文性理性思維機制的揭示纔得以認識的。可以這樣說:“人的精神性存在”的奧秘與密碼,其實就蘊藏於對人文理性思維的研究之中。
最後,人文理性思維之所以稱之爲“思維”,是在與科學思維相對立的意義上使用“思維”這個術語的。但從人文理性思維的本性來說,它不僅與科學理性思維處於不同的類型,而且屬於人類認識世界的一種“精神性”的活動。因此,它的思維活動形態呈現爲“精神性”。而人類的精神性不僅表現爲超越於現象界層面,而且體現爲思維方式上超越於知性思維的方法論層面。因此,嚴格來說,它與科學理性思維在思維方法上的區別,是指它是一種建立在“天人合一”的存在論基礎之上的非主客二分的思維活動與方法,是一種“存在論”的差異而非“存在者”的差別。這種差異也即世界究竟是以“天人合一”的方式還是“主客二分”的方式存在的區別。由此,從存在論出發,這種非二分思維的思維機制是通過人的精神性去把握“天人合一”的宇宙本體存在的。這種人類特有的以精神性方式去把握與達到“天人合一”的存在論與本體論境界的思維方式,也可以稱爲“天人感應”,它與通常的科學理性思維方式是不同的。即言之,“天人感應”其實就是人以精神性存在方式去把握與達到“天人合一”那作爲宇宙之終極實在的人文理性思維方式。這種思維的內容及其過程又可以細分爲史學思維、詩學思維、哲學思維。
——史學思維。這是在人文思維的意義上加以使用的,即將史學思維視爲人文性的思維而與通常非人文性的史學研究方法區分開來。之所以將史學思維作爲人文理性思維,是因爲作爲人文學而非其他一般學科意義上的“史學”研究及其撰寫活動,它既可以很好地體現人文理性思維之特質,揭示人文理性思維之不同於科學思維的特徵,又有與作爲人文理性思維的其他思維類型的區別之所在。這種史學思維(下文不標出時,都是指作爲“人文學”的精神學意義上的“史學思維”而非其他)作爲以“精神性”的方式而非其他,追求的是對世界以及人類社會之作爲歷史的事實真相的把握與瞭解。這裏,需要區分出歷史的“事情”與“事實”。所謂事情,是指在人類以往的歷史流轉中真正出現過的事情。所謂“出現”過,是指這些事情雖然出現過並不等於它永遠存在,更不等於被人們真正理解。從這種意義上說,人文學的史學思維的目標與理想,就是如何將這些歷史上出現過的事件定格下來,並且發現其中的意義,以爲後人所理解。這種由歷史學家撰寫並且對其意義加以定格的史學文本中所記載的歷史事迹及人類活動,方纔稱得上是歷史中的“事實”。因此,任何歷史文本的撰寫,都是爲了從歷史的“材料”中整理或提煉出歷史的“事實”。然而,人文學的史學文本區別於其他非人文學的史學文本的地方,在於其在提煉歷史事實的過程中,所依照的意義參照系是作爲最高存在者的天道。這種最高天理具有絕對性與超越性。而按照“天人合一”的思維模式與要求,作爲人文學的史學文本之構成,其最基本的撰寫方法或者說思維過程,就是如何從人類之現象界活動與行爲中去發現這種超越的天理之道;或者反過來,將超越的天道原理與理想體現於人類的現象界歷史活動與行爲之中。從這點而論,史學的人文理性思維的特徵也就表現在它對歷史“事實”的構造以及如何進行歷史敍事上面。與僅僅關注世界之現象界中的人類活動與行爲,並且從現象間之經驗因果律(“規律”)尋找人類歷史活動之動機,以及解釋人類歷史活動之原因與結果的作爲人文學科的史學思維方式法不同,作爲人文理性的史學思維,是將人類的精神性存在視爲人的本質,並且強調人的精神性存在對人類與世界存在的意義。從這種意義上說,人文學的史學思維要呈現的不僅是人類歷史上作爲精神性存在的人類活動與行爲,而且要從人的精神性存在意義上對歷史上發生過的種種人類活動與行爲進行評價。也就是說,人文學的史學文本之撰寫,不僅僅是對歷史現象的描述,而且同時是評價性與詮釋性的活動。人文學的史學撰寫方法論原則在具體的史學文本中體現爲“以事見理”,具體風格可以有“事理宗”與“理事宗”。而人文理性的這兩種史學風格類型皆屬於“轉喻思維”之運用,其作爲思維方式之可行,乃是基於存在者與存在之間的“意義結構的同一性”。①胡偉希:“文體·風格·話語與‘喻’——論人文學文本的構成”,《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2019);“原史”,《南國學術》4(2019)。
——詩學思維。詩學思維典型地體現於人文學的詩學文本所採用的意象之形成過程中。人文學的詩學文本的基本單元是意象。它是以形象的東西來表達那超出形象之外的東西,這種東西就是詩學文本的“意味”。作爲史學文本的事實儘管也具有形象性,但這種形象性是對客觀真實的現象的東西的刻畫或描述,而詩學的意象則是對客觀存在的現象性之物的超越。所以,詩學的意象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現象界的真實世界的描寫之真實,或者是想象或者是虛構出來的現象界之情景;另一方面,這些無論是真實的或者虛構出來的情景,都有其超出現象性之情景或事物的象外之象、形外之旨,從而與單純立足於對於現象界經驗事物的刻畫與描寫的史學文本之事實區分開來。另外,人文學文本的意象嚴格說來屬於人文意象,即這種意象表達的象外之象、形外之旨是形而上的超越世界。一句話,通過具有形象性的事物或情景來表達或呈現那超越了現象界的世界之大全或者宇宙之終極實在,纔是作爲人文學的詩學文本之意象運用的目的。這也是它與普通的詩學文本創作中運用的詩學意象區分開來的標誌。儘管作爲人文理性思維的基本單元是意象,這種意象具有形象性,其中的形象運用是爲了傳遞出那超越了具體形象的形上之理,但是,這種形上之理的呈現又是通過意象的運用所調動或激發出來的情。所以,構成人文學的詩學文本或者說詩學思維之張力的,實乃詩學文本或者詩學思維中的“情”與“理”(“天道”之理)。如果說史學式的人文理性思維是“以事見理”的話,那麽,詩學的人文理性思維的特徵則是“以情通理”。基於作者或者讀者的個人精神氣質之不同,以詩學意象來詮釋那超越現象界的“天理”的方式的詩學人文理性思維可劃分爲“情理宗”與“理情宗”。這兩種不同風格的詩學人文理性從思維的本性來看,皆屬於“指喻思維”之運用。詩學的指喻思維方式的可行存在論依據,是基於現象界和本體界的“本質的同一性”。①胡偉希:“原詩”,《南國學術》4(2020)。
——哲學思維。人文學的哲學思維與史學的、詩學的思維的區別,在於它的抽象性。它是藉助於具有抽象性的觀念進行思維的活動。與作爲科學思維的純粹抽象性的概念思維以現象界之物作爲研究對象不同,人文學的哲學觀念思維是對世界之大全以及宇宙之終極實在的總體把握,因此,其思維之運用強調對現象界事物的超越性。因此,作爲人文理性思維的哲學思維不僅具有形而上的超越性,而且是對現象界與形上世界合一的觀念性陳述。這種既具有超越性又具有現象性的觀念及其範疇,與康德以後的德國古典哲學的代表人物如費希特、謝林、黑格爾等人追求“絕對同一”或概念辯證法的概念雖然有相似之處,但他們追求的是概念的自我辯證發展,強調的是概念的自我同一,而作爲人文學的哲學思維強調觀念的辯證運動始終是否定意義上的,是徹底的“否定辯證法”。因此,人文學的哲學思維對世界以及宇宙終極實在的理解是“即現象即本體”,並且是以悖論方式呈現的。從而,人文學之把握與理解世界及宇宙終極存在之哲學思維以及哲學語言亦是以悖論的方式展開的,悖論思維可以說是關於“天人之學”的哲學思考問題的常態。雖然西方的概念哲學思維亦可以是悖論式的,這點從康德關於“二律背反”的論述可以概見,但真正的悖論式哲學話語及其思維運用,無疑以中國哲學所使用的“本然陳述”“經驗陳述”最爲典範。對中國哲學而言,無論是表達人的精神存在還是宇宙的終極實在的感悟時,都是採取即現象即本體、非現象非本體的哲學話語方式的。這種即現象即本體、非現象非本體的悖論式哲學語言表達之根據,在於世界與宇宙終極實在既是“一即一切”的現象界存在者,亦是“一切即一”的絕對本體存在。因此,人文理性的哲學思維對人的精神性存在以及宇宙的終極實在的思考與悖論式把握,強調的是作爲現象界之物的存在者與形而上的物自體之間的“存在論的同一性”。這種哲學悖論思維方式的運用,從思維結構與思維機制看,可名之爲“諷喻”,它分別以“理道型”與“道理型”的話語風格呈現。②胡偉希:“原思”,《南國學術》4(2021)。
四 論“感應”與“精神間性”
之所以選擇作爲人文學的史學的、詩學的、哲學的思維方式加以討論,並非說人文學的理性思維就僅有這三種,而是說,這些人文學思維的方法論原則對於人文學來說具有普遍意義。這些方法論原則雖然是先驗的,但任何關於人的精神性以及宇宙之終極實在的探究又都是具體的。即作爲人類的一種精神實踐活動,它畢竟有具體的心理活動內容,並有其不同於一般的心理活動的心理機制。這就是所謂的“天人感應”。人之所以能夠以天人感應的方式把握天道,不僅在於人是具有超越的精神性的存在者,還在於人能夠將這種超越的精神性存在發展爲一種天人感應的能力。由於這種能力衹是具有精神性的人纔具有,所以,這種能力也可以稱爲“精神力”。與史學的、詩學的、哲學的人文理性思維相對應,人的天人感應的精神力有三種:感知力,感遇力,感悟力。作爲人文學的理性思維活動,必由這三種精神能力所發動。
——感知。作爲精神性存在的人對宇宙終極實在的感知,與作爲認識客體的感知不僅在認識“對象”方面不同,而且在認識的思維機制與調動人的心智能力方面也有不同。雖然它如同普通知性的感知一樣,也要藉助人的感覺器官與外部世界打交道,但這種存在性的感知要認識的是作爲“物自體”的宇宙之終極本體。這意味着,人的存在感知要有一種能夠“穿透”世界之“表象”、看到世界與事物之作爲“精神性存在”的感知能力。這種能力與通過感覺經驗知道世界是“客觀實在”的“統覺能力”不同,可以稱爲“知的直覺”的能力。知的直覺也不同於智的直覺。如果說智的直覺是對超驗的形上世界的直覺把握的能力的話,則知的直覺是對現象界之真實的直覺把握能力。從世界之觀來看,現象界之真實可以有兩種:一種是從二分法之觀出發的關於世界是客觀對象的真實,另一種是關於現象界乃理念界之“模仿”的真實。前一種真實,是康德研究過的運用人的“統覺”的能力獲得的客觀真實,後一種則類似於柏拉圖關於“理念”在現象界之“投影”的真實。而這後一種真實,衹能從超驗的角度來看待現象界之物纔有可能獲得。因此,所謂知的直覺或者人文學思維對現象界的感知,就是如何運用人的這種“知的直覺”去捕獲或把握現象界之“真知”,而不是像科學思維那樣從二分法出發去獲得關於現象界的客觀知識。爲了與作爲科學理性的感知區別開來,也可以將它稱之爲“德性之知”,而科學理性的感知所得乃“聞見之知”。對於德性之知的運用來說,它並不脫離聞見之知的經驗材料,卻又超越了聞見之知的所得。兩者的區別在於:德性之知不滿足於以先驗範疇對感覺材料的統轄,而是從價值論的立場出發,運用超驗範疇與超驗原理對普通知覺到的經驗材料加以提煉與綜合,從而形成作爲存在者的現象界之物的總體認識與評價。因此,作爲人文理性思維的對世界的感知能力,實乃運用人的精神性對世界現象界的一種改造與重新解釋的能力。從終極上看,人的精神性存在其實是一種超越了單純的感覺材料之先驗綜合的精神力,它包括着像善惡、公平、正義、自由等一系列價值論的訴求。而對於人類所能感知的世界來說,它將這些超驗的價值範疇運用於感覺經驗材料並且加以綜合,正體現了人的精神力作爲人文理性思維的本質。否則的話,它就談不上是人文性的理性,而衹能是先驗範疇之運用的單純知識理性。可以說,作爲人文學的歷史研究,或者說作爲人文學的史學文本寫作,就是這種人之具有精神性感知能力的極好範例與實證材料。
2018年5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单方面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并设置过渡期,分阶段、分批次启动对伊朗的制裁政策。虽然美国于2018年11月5日宣布给予中国180天临时豁免,但这种豁免具有局限性和不确定性。因此,了解和研究美国对伊朗能源制裁政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感遇。顧名思義,感遇有“遇”的意思,它是人的另一種與世界以及宇宙之終極存在打交道的方式。既然世界萬物都是一種“天人合一”的關係,那麽,從認識論而非存在論的角度講,所謂“認識世界”就是“天”“人”的彼此“相見”與“相遇”。這不僅是沒有作爲認識論的主體與客體的區分,還意味着彼此作爲熟悉者與依賴者而非“陌生者”的相逢與相遇。它不再唯一地依賴人的感覺器官去獲得對世界之真知的認識,而是從人的精神力的其他方面,去尋找人可以認識與把握精神性存在以及宇宙之終極實在的認識工具。這種工具,就是人的情感,就是人的一種以“感遇”方式溝通天人的反思判斷力。因此,所謂“感遇力”,其實就是人以“情”的方式與作爲“天理”之“天”相遇的一種精神能力。這裏的“情”,不是指單純作爲現象界之存在的人情,實乃包括體現宇宙之終極存在的“天情”。根據“存在通過存在者呈現,存在者呈現存在”的精神存在學原理,“天人感應”的人之情,既是“人情”也是“天情”,是天性與人情的統一。要言之,所謂感遇,就是作爲現象界中的“人情”與作爲宇宙之終極本體的天情在找到或發現“自已”之後,終於達到彼此認識,並且共爲一體。在人與世界以情相遇的過程中,除了有人的意識活動的參與之外,更多地還體現爲一種深埋於人的“潛意識”中的情感,即感遇還意味着人的潛意識中的精神力與作爲宇宙之終極實在的精神性的相遇。它突破了知性對世界的分割化的理解,展示的是一個 “無我之境”的世界。這種以情相遇的人之精神力的作用與心理機制,在作爲人文學文本的詩學創作與閱讀體驗中最爲明顯,故也可以將這種以感遇與世界打交道的思維方式稱爲“詩學思維”。
——感悟。這裏所說的感悟,是指對存在的感悟,而非某種對現象界事物之知識性的真知或者說醒悟。這種感悟,類似於康德所說的“智的直覺”。但是,何爲“智的直覺”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康德認爲:智的直覺衹有上帝纔具有,人類由於缺乏智的直覺,所以無法獲得關於宇宙之終極存在方面的知識。反過來,牟宗三則認爲,智的直覺屬於人的精神性的存在認知。這意味着,人可以把握天道之原理,獲得關於性與天道的真知。但是,人的這種智的直覺,究竟是一種人類特有的理性思維活動,還是一種人類理性無法通達的類似直覺的神秘心理現象?牟宗三始終“語焉不詳”。他衹認爲,當人類獲得關於“性與天理”的知識時,必訴諸人的這種智的直覺。從精神學意義來看,與其說將智的直覺追溯到人的神秘的或者說靈感一動的心理現象,不如說它是人類特有的一種可以感悟天道的精神力。作爲人文理性思維之一種,人還可以將這種精神力把握天道的精神過程與思維機制予以描述與闡明,此即哲學思維。可見,哲學思維不是其他,就是關於人之感悟“性與天道”的精神力如何發生作用的現象學觀察及其闡明。一旦如此來理解作爲哲學思維的感悟的話,就會發現,哲學感悟思維必須藉助於觀念而非概念的語言加以表達。雖然兩者都具有抽象性,但與概念的抽象來源於經驗現象界的所得,是以“得自於經驗而還治經驗”不同,哲學觀念並非對經驗世界的抽象所得,其觀念內容始終是從超驗的本體世界中提取的。因此,從本質上說,觀念是關於世界之大全以及宇宙之終有實在的認識。與人文學的詩學思維之“意象”始終居於形上世界不同,哲學的觀念思維始終面對的是“兩個世界”:本體界與現象界。由於本體界與現象界始終是以悖論的方式存在的,因此,人文學的哲學思維也就始終衹能是悖論式的。這種悖論式的哲學思維以觀念的否定辯證法方式加以表達。它不是通過邏輯推理或者純粹觀念思辨的概念性思維,而是立足於存在本身的人類特有的精神性思維活動。它本質上是對人的精神性存在以及宇宙之終極存在的一種“存在性感悟”,然後再根據“具體的思維”與存在的統一性原理反推於人類之精神性活動,並終於發現它乃人類特有的一種可以名之爲“哲學思維”的活動。這種精神性的思維能力,以觀念思維的方式在人文學的哲學文本中得以很好的體現。
建立於人的精神性存在與宇宙終極存在的精神性基礎之上的人文理性思維可以進行,是由於兩者的精神性之間發生了“感應”。這種精神感應現象的出現,除了因爲彼此之間皆屬於超越的精神性存在之外,還說明它們作爲“精神”發生了流動與變化,這種流動在方向上表現爲彼此在精神上的“佔有”或“交融”。這表明:兩者的精神性可以發生聯繫,並且産生共感(彼此感應),是由於它們作爲精神性的存在具有“精神間性”,因此纔能夠産生或出現“共感”或“感應”的功能效應。同樣是具有精神性的事物或存在者,如果精神性的維度不同,或者精神性的層次不同,則二者未必能産生感應。因此,無論史學的、詩學的、哲學的人文理性思維,其作爲思維機制的發生,與其說有賴於人之作爲精神性的存在方式,不如說取決於人的這種精神性存在的精神維度。也就是說,精神間性是人之作爲精神性存在的具體化,人的精神間性纔是人文學理性思維過程中人與宇宙之終極存在在精神上産生感應的前提條件。所以,當我們說史學的、詩學的、哲學的人文理性思維得以進行與發生的時候,與其說因爲它們之間具有精神性,不如說它們具有精神間性更爲恰當。精神間性是精神性之具體顯示過程,精神性則是精神間性存在之內在根據。藉助中國哲學的術語來表達,精神性是“體”,精神間性則是“用”。雖然從認識論的機制來說,精神性與精神間性有所區別,但從存在論的角度看,它們並無實質上的區分,此也即中國哲學所說的“即體即用”。而回到關於人文學的理性思維這個問題,可以看到:人的精神性存在與宇宙之終極實在可以通過人文學的理性思維加以把握,不僅是說由於人之具有精神性,而且指的是:這種關於人的精神性存與宇宙之終極存在如果是以“精神感應”方式得以呈現的話,則它們必具有“精神間性”。
五 人文學文本的閱讀與精神呈現
人的精神性存在與宇宙之終極存在之交往或産生感應,表面上看,似乎是兩者之間的直接交往,但仔細深究可以發現,人文學文本在這種精神性交往中具有先在性。這是因爲,作爲人文學的文本是人類歷史上之精神性存在的留傳物。每個人,無論世代與環境,都必須通過對人文學文本的學習或研究纔能獲得關於人的精神性存在的理解與認識。因此,作爲人的精神性存在與其說是天然生成的,不如說是由人文學文本塑造的;或者說,至少是人文學文本的內容爲人們提供了進一步去獲得人的精神性存在的認識的前提條件與支援意識。
就人與天道或宇宙終極實在的精神性交往來說,這種交往之所得也有賴於通過人文學文本的形式纔得以定格而且得以保留。也就是說,就一種精神性存在的交往的具體過程來看,假如離開了人文學文本這種形式的話,人類與天道的交往即使可以進行,但這種交往的所得卻無法保留,從而也就難以成爲一種能夠被他人所知與瞭解的人的精神性存在。因此,人雖然是具有超越的精神性動物,但這種超越的精神性存在及其意識,其實是離不開人文學文本的精神性存在的。或者說,所謂人文理性、人的精神性,其實是一種由人類歷史上留傳下來並得以保留的精神性存在的傳統;而這種精神性傳統不僅有賴於人文學文本得以保留,而且人類在與世界以及宇宙之終極實在作精神性交往的時候,也時刻脫離不了人文學文本的這種精神性。①由此可以理解蘇格拉底爲什麽會强調“德性”首先是一種“知識”,以及康德在論述道德問題時會將道德意識與自然情感加以區分。這點衹能從人文理性的角度纔得以理解,即人類之道德是通過人文學文本之教化纔得到培養與塑造的。所以,在人的精神性與宇宙終極實在打交道的過程中,人文學文本的精神性或精神間性遠不止是作爲人的精神性存在與天道的精神性之“中介”或“橋樑”在發生作用;更爲重要的是,人對人文學文本的閱讀與研習,這本身就成爲人的精神性之形成與得以挺立的前提條件。換言之,假如不經過人文學文本的閱讀與研習,作爲現象界中之存在者的人之個體,很難成爲一種具有超越的精神性人格的獨立個體,更遑論如何以人的精神性存在之方式去與作爲宇宙之終極存在的精神打交道或産生感應。這樣看來,閱讀與研習人文文本,不僅是人與宇宙之終極存在打交道的必由之路,而且人文學文本的閱讀與研習本身,實已構成人之作爲精神性存在的存在論奠基。
從人文學文本中可以學習到關於人的精神性存在以及宇宙之終極存在的知識,這種知識其實是“後驗”的。即人類是經過人文學文本的研習之後的“有所得”,纔知道這種“有所得”的知識是關於人的精神性存在和宇宙之終極存在的知識。但是,這種有所得的人文學知識對人類來說到底意味着什麽?它到底滿足了人類精神上的何種需要?較之於人文學文本研讀之所得來說,這種對人文學閱讀本性的追問纔是最爲根本的。而此種追問,也即是要回答作爲人文學文本閱讀的存在之理。其實,這個問題的解答與人作爲“有限性的理性存在者”的“希望”有關。
追求不朽與永恆的衝動,源自人是具有“精神性的自我意識”的動物。通常的物理性存在物不具有像人一樣的精神性意識,當然談不上有追求永恆的意識;而動物還沒有達到人的那種精神性存在的標準,也不會有這種意識;而一個人完全缺乏“精神性”的話,也不會有這種意識,衹會有“求生”的本能的衝動。②真正的“不朽”衹能是一個“精神學”的概念,即追求不朽就是追求精神學意義上的不朽。否則的話,它就衹能是現象界中的物體可以“不腐爛”或者生物體可以“不死”的概念。所以,追求“不朽”是人作爲精神性存在者的“天性”。當然,這裏的“不朽”不是指人在肉體上的不死,而是從精神學意義上指一個人在肉體消失之後的精神“永在”或者說“不朽”。因此,追求不朽的希望是人類精神發展的動力,也是人類宗教産生的根源。各大宗教無論其教義如何不同,但在關於“人可以希望什麽”這個問題上,不僅找到了是希望“不朽”或者“永生”的答案,而且都是從“精神不死”“靈魂不滅”的角度對“不朽”加以理解與解釋。不僅如此,它們幾乎不約而同地還會確立有一個作爲宇宙之終極存在的“最高絕對者”加以崇拜,並且將能夠實現精神永生的希望寄託在這個最高絕對者身上。從這種意義上說,宗教之所以稱之爲宗教,不僅在於它承諾給人們以“永生”的希望,還在於它要確立一位超越的作爲宇宙之終極實在者,來給人類之“永生”提供保證和使“希望”有實現之可能。
當然,人類追求“不朽”的希望也未必非得採取宗教信仰的方式或者從宗教神學上加以證明。像康德這樣重視人類“理性”的哲學家,就別出心裁地提出:從人類具有道德理性這條公理出發,可以推斷出人類何以需要上帝。但是,康德對這個問題的論證並不成功。因爲,從前提的設定開始,他就偏離了論題。本來,承認“上帝存在”是爲了解釋與論證人的“永生”何以可能這個問題,但康德不這樣認爲。他說,人的希望是獲得“德福一致”。由於這種“德福一致”的“幸福”在人類的現象性生存中無法實現,因此,就衹能寄希望於它在“天國”實現,而基督教所稱的“上帝存在”則爲人類的這種“希望”提供了可能。綜觀他的《單純理性限度內的宗教》這本書,所採取的就是這種“單純理性內的宗教”的思路。這非但沒有從理論上證明上帝存在,而且也沒有從人之“精神性存在”的角度解答人何以獲得“永生”。康德之所以從“道德理性”的角度說明道德必然會導致宗教,其思想動因除了受近代以來人文主義思潮的影響與限制,試圖從理性(道德理性)的角度對人的超越的宗教信念加以解釋外,其思想上的陷阱出在對“德福一致”中的“福”作了經驗主義的理解,這就顯得與從精神學意義上對人追求或“希望”的“德福一致”的解釋思路相差太遠。也就是說,康德承認人需要宗教是出於人是具有自由意志的動物,並試圖從道德理性的角度對人的這種宗教超越性加以論證,這顯示出他的“人是具有超驗的精神性的動物”這一卓識,但是,他在《單純理性限度內的宗教》中對“人可以希望什麽”問題的理解,與他關於“人是精神性的存在”這一大前提有了距離。
儘管如此,康德從“人可以希望什麽”出發提出的關於“上帝”爲何存在,以及人類希望追求“德福一致”的看法,對人們思考“人可以希望什麽”這個問題仍然有積極意義。衹不過,他的“上帝存在”以及基督教神學觀中“德福一致”的某些解釋與論證,衹有置於“人文學”的視野,而非道德神學的視域,其精神學的意義纔能得以彰顯。此種思路即是:通過人文學文本的研習,人可以與那作爲宇宙之終極實在的天道合一,並且收穫德福一致,即成爲“不朽”。而這也就是作爲人文學文本之研習的存在之理。
對於人文學文本包括史學的、詩學的、哲學的研讀,都涉及以語言符號形態存在的文本(簡稱“人文學文本”)、文本的精神學含義或意義(即“性與天道”),以及作爲閱讀者的文本接受者(本文中即“人”這個精神主體)。但是,作爲精神學意義上的人文學文本的閱讀或研習,其閱讀原理區別於非精神性的人文學科文本之閱讀在於:文本的符號形態、文本的意義、文本的閱讀者都是作爲“超越的精神性存在”同時出現於閱讀過程當中的。或者說,假如沒有進入閱讀狀態或閱讀過程時,它們三者雖有精神性,但無法實現與超越的宇宙之終極存在的精神交往或者說“天人感應”。從存在論的角度看,人文學文本既是人的精神性與宇宙之終極存在的精神性交往或者說“感應”的中介,同時也是精神性的獨立存在。人文學文本在人的精神性與宇宙終極實在的精神之間的中介、橋樑作用,類似於基督教“三位一體”神學觀中的“基督”的位格。但從對精神性的理解,尤其是對作爲宇宙之終極存在的“位格”理解來說,人文學的“精神三位一體”與基督教的“三位一體”又有着本質的區分。即在基督教“三位一體”思想中,無論對三位一體中的“聖子”作何種解釋,總認爲它有不同於上帝的“人神性”位格,但如果基督教神學理論要自圓其說的話,則“聖子”這種“人神性”中的“神性”對上帝而言終究是“派生”的,即它是由上帝賦予的或是作爲上帝的“替身”而“在場”的。而在人文學文本閱讀的精神結構中,同樣也有相當於基督教中的“上帝”那樣的超越的宇宙之終極存在者,但它是一種純粹的精神性存在——不僅是純粹的精神性,而且是唯一的、永恆的、絕對的精神性。這使它無法直接與普通的具有精神性的人之存在者直接感應,而需要憑藉具有“人文性位格”的人文學文本與人的精神性存在發生感應。由此,作爲宇宙之終極實在的純粹精神就通過人文學文本閱讀展示出它的位格的“時間性”。這種時間性在人的生活世界中,體現爲人的精神性存在的歷史性。故而,人文學文本的閱讀,也就成爲超越的宇宙終極存在在人的生活世界中的展示方式。
正是由於基督教的“三位一體”結構是以“上帝存在”爲中心,而人文學的精神結構是以“文本”爲中心,這導致人文學文本的閱讀與基督教的“《聖經》研修”有着很大不同。基督教很重視《聖經》的閱讀,認爲是“啓示性”的。即《聖經》宣示的是上帝發佈的真理或絕對命令,衹可以信而不能質問;即使有的宗教派別主張對《聖經》要加以理解,但這種理解也是“先信仰而後理解”。而人文學的文本閱讀模式則不然,它是建立在讀者的心理體驗基礎之上的。即閱讀者在閱讀文本的過程中,儘量把文本中的敍事、情景或思想觀念以“當事人”“見證者”的身份將其內容“心理化”,並進行“同情化的體察與體驗”,它類似於狄爾泰所謂的作爲人文學科的“精神科學”之閱讀的“移情”方法。而這種移情之所以可能,是由於人生來具有一種與人文學文本中寄寓的精神性可以發生“共感”或“共情”的精神體驗能力。因此說,雖然人文學文本的精神體驗方法也類似於通常人文學科讀物的閱讀心理體驗,但這種體驗的“心理”其實是人的精神,這與狄爾泰等人強調的普通人文學科閱讀心理體驗有着本質的區別。也就是說,作爲精神人文學的閱讀體驗雖然在表現形式上是一種心理體驗,但其所追求的目標,是對文本中人的精神性與宇宙終極實在之精神性的瞭解與把握,因此,衹能通過人的精神活動而非單純的心理活動纔能達到。
同樣是人的“精神性”,其實還可以區分出兩種不同的含義。通常,人們所說的“精神性”,限定在人的現象性層面,這包括:人受現象界生存刺激所産生的種種心理活動,如各種喜怒哀樂、悲歡離合的情感表現,以及由現象界生存所激發出來的種種慾望、意志,甚至包括道德情感等等。但是,人類所呈現的這些心理活動及精神活動還不具有超越性,因之而不屬於人的作爲超越性精神性存在所具有的精神性。而作爲人文學文本的閱讀之所以稱爲“精神體驗”,強調的是以精神性的體悟方式去領會與把握那寄寓於人文學文體中具有超越的精神性存在或“天理”。這裏的“天理”就是人文學文本的精神性。但是,這種“天理”在人文學文本閱讀過程中的展開與呈現,卻又須藉助人的現象界的精神表達方式。也就是說,人文學文本中的人之超越的精神性維度以及宇宙之終極實在的精神性存在,其實是通過現象界中的人及其各種行爲與活動,包括心理活動以及思想觀念活動纔得以呈現的。這種通過現象界之人的活動表現出來的人的超越性精神品格以及宇宙之終極存在的精神性,可稱爲“具體的精神性”。人文學研習的目的,就是通過精神閱讀的方式來獲得與把握文本中的這種“具體的精神性”。
所謂具體,首先是指文本分類的具體。它是從“精神學”意義上鑒別並分類的。史學的、詩學的、哲學的從表面上看,似乎衹是文體風格上的區別與劃分,其實,劃分根據在於人文學文本中的“具體的精神性”。以史學文本爲例,它的閱讀給人帶來的精神體驗是“追求崇高”。這是由史學這種人文學文本的內容及其敍事風格所決定的。人文學的史學文本以將歷史上真實發生過的事情從精神學的意義加以理解與認識,並以史學的“事實”或敍事的風格和方式加以呈現,這其中包括從人的精神性存在以及宇宙之“天道”的角度對歷史事實的評價。這當中,組成歷史事實與構成歷史敍事的歷史先驗邏輯一方面體現了人的超越的精神性存在以及宇宙終極存在之精神,另一方面,這種超越的精神卻又是以人類以往歷史中發生過的現象性活動加以呈現的。人之超越的精神性存在以及宇宙之終極實在的“天道”一旦落實或下降於人類活動之現象界,就不再是那絕對的或終極性的天道,而表現爲具有人間性的人類行爲之立法與倫理。這些人類歷史與社會之立法與倫理原則,體驗了史學文本展示出來的人的超越的精神性與宇宙之終極實在的“天道”,但它們同時又是“具體的”,是以現象界中的人類活動與行爲的具體形態加以呈現的。而在這些具體的歷史形態中,蘊涵着人類歷史理性的先驗原理,如公平、正義,尤其是善惡價值觀的衝突與對抗。當人們研讀這些史學文本的時候,不但會被諸多善與惡的鬥爭所激動,更會被那些爲爭取人類社會公平、正義的賢人志士的行爲所感動。從精神體驗的角度看,它使人們明白:人作爲有限性的理性存在者,其最重要的精神禀賦是“理性”。這裏的理性不限於科學理性。史學文本給人們的啓迪是:所謂人是理性的動物,本質上應當說人是具有“人文理性”的動物。而這種人文理性在人類的歷史活動中,就具體體現爲對公平、正義的追求,以及抑惡揚善等人類歷史理性的訴求。因此,史學文本的具體精神性,就是指具有人文關懷以及價值訴求的歷史理性。
同樣地,在人文學的詩學文本閱讀的精神體驗中,亦存在着這種基於不同文體風格所形成的具體精神性。作爲人文學的詩學文本,是以描寫與刻畫處於現象界的人們對那超越的宇宙之終極實在與人的超越之精神境界的追求爲依歸。從這種意義上說,儘管作爲人文學的詩學文本也可以展現人類現實生活中的種種生活內容與主題,甚至描寫的人物與場景也千恣萬態,但所有這些現象性的描寫與內容衹是作爲那超越的天道出場之鋪墊。甚至可以說,人文學的詩學文本的奧妙或最勝處,在於以現象界之在場者來表現或襯托那不在場的或者說那形而上的作爲宇宙終極實在的絕對精神或絕對理念。它的獨特表現形式就是,關於“圓善”或最高善的觀念。對於詩學思維來說,人的精神性存在與宇宙終極實在是具有道德意義的絕對存在,這就是最高善,而這種最高善在人的現象界生存活動中是以“善良”“善行”的方式呈現的。因此,作爲詩學文本呈現的“具體精神性”實乃善良意志,它是人間生活中道德行爲與倫理的依據與根源。
人文學的哲學文本以展示人類的思維現象爲內容,而人的思維現象及其思維過程也體現人類超越的精神性的“具體性”。這種具體性,體現爲哲學思維的“悖論性”。所謂悖論性,其字面意思是“似非而是”或者“似是而非”。人文學的哲學思維認爲,恰恰是這種表面上“自相矛盾”或者說“二律背反”的思維,揭示了人類生活,尤其是人的精神性存在以及宇宙終極存在的真實面目。悖論不僅是認識世界與宇宙終極實在的方式,同時也是世界與宇宙終極實在的存在方式。從存在論的角度看,宇宙本來是以“一即一切”與“一切即一”的方式呈現的,宇宙的終極存在的悖論是無法化解的。而人的精神性存在也是如此:一方面,人是具有超越的精神性存在;另一方面,人又也和地球上其他的動物那樣,是“有限的存在者”。這種集超越的精神與有限的存在者於一身的人的生存活動,其所作所爲也必會出現悖論。這種悖論既然與生俱來而無法化解,那麽,人文學的哲學思維就教人對人與宇宙的這種本根性悖論以“中觀”的法眼觀之。既承認人的超越精神的無限性,同時亦承認和肯定人的現實生存境遇的有限性。這樣,人文性的哲學思維其實是通過對人的精神活動的分析,要求人對這種悖論性存在狀況有清醒的認識。但如同史學的、詩學的人文學文本閱讀一樣,既是對人的精神性存在以及宇宙之終極存在的認識論,同時亦是作爲人的精神性存在之養成的實踐論。從這種意義上說,作爲人文學的哲學文本閱讀,其“具體的精神性”體現爲“智慧”,即認識與體認天道的原理,然後循天道而行。對於人文學的哲學文本來說,人的精神性與宇宙終極之天道是以悖論的方式出之,故人文學的哲學作爲“智慧之學”,乃是如何化解與面對人的精神性與天道的“悖論”問題。
六 人文教化與精神學的審美與宗教
在康德的“三大批判”(《純粹理性批判》與《實踐理性批判》《批判力批判》)中,《批判力批判》是爲了解決“從自然諸概念的領域達到自由概念的領域的過渡”①[德]康德:《批判力批判(上)》(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宗白華 譯,第16、32頁。,而特意提出審美判斷力這個問題並加以思考的。但他思考審美鑒賞問題時遇到了障礙。這表現在他對《批判力批判》這部書的輪廓構想中:一開始,他是想對審美鑒賞方式作專門的分析,但後來,卻又試圖從自然是具有“實在的(客觀的)合目的性”②[德]康德:《批判力批判(上)》(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宗白華 譯,第16、32頁。這個論題來展開問題,將審美問題引向自然歷史是從自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的目的論論證。其實,他本可以直接從對審美鑒賞這方面入手,對人的精神性存在方式作更深入的挖掘與探討。可惜的是,如何在兩個領域之間實行“過渡”的問題代替了他對審美鑒賞作純粹的精神學意義上的思考。對他來說,即使承認人的知性理性與道德理性具有超越的精神性向度,但審美鑒賞對人的這兩種精神性的綜合與過渡,其作用依然衹是工具性的。換言之,審美在康德關於人的精神性研究中沒有獨立的本體地位。但是,通過對人文學文本閱讀過程的思考,則發現:人的審美能力如同人的其他精神力如知性的、道德理性的一樣,是可以具有超越的精神性的。而這一審美作爲人的精神性存在,不僅對“人是什麽”,而且對“人可以希望什麽”問題的思考與最終解決,具有重要意義。
先從康德的審美觀念說起。審美判斷可以在人的感性與理性之間架起橋樑,在於它一方面是感性的,另一方面又是超出感性的。康德說道:“判斷力能夠從自己自身獲致一個原理,即自然事物和那不可認識的超感性界的關係的原理。”①[德]康德:《批判力批判(上)》“序”(第1版,1790),第6頁。本來,對審美的這種認識,假如換一個角度看,它作爲一種具有本體論或者說存在論形態的存在,從精神學意義上說,是可以解決人的有限性與無限性的衝突,也即使人的這種悖論性生存得以化解或取得“和解”的。但康德同時又認爲,作爲審美的感性經驗不能是超越的,衹能是現象界的,因此,審美作爲人的感性存在與理性存在之間的過渡,衹能從“無目的的合目的性”這個角度論證與展開。其結果就是:《批判力批判》分爲前後兩個部分,兩個部分之間並無觀念上的聯繫。由於前者討論的是審美藝術鑒賞的問題,而康德發現,這個問題無助於解釋人的感性存在向理性存在過渡的問題,於是很容易在第二部分轉入另一個課題,即對自然何以具有“客觀的合目的性”這個問題作全幅的論證。但正是在這前一部分內容中,人的審美鑒賞力不僅可以作爲人的精神力之一種,而且其重要性在於:它最終爲“人可以希望什麽”提供解決問題的新答案,從而,康德在《作爲單純理性限制中的宗教》中希望解決而未能夠解決的問題,反倒可以通過對人的審美鑒賞能力的重新認識得以解決。當然,這還得對康德美學思想中的概念運用加以澄清。
康德認爲:審美是感性的,是與感性的自然美與藝術品打交道的。但同時又認爲:審美鑒賞是對審美對象的“形式”的鑒賞。因此,他開始執著於關於審美對象的“形式”的分析,這就完全抽離了審美對象物的任何可以感覺經驗到的感性內容。這樣下去,“形式主義的審美”就成了可以脫離審美對象物的任何質性規定,而純粹關注審美對象的“形式”的審美。按這種審美觀推論下去,不僅現象界的許多本來可以作爲審美鑒賞的對象物被康德排除於純粹審美的範圍,而且這種形式主義的審美難以解釋作爲人文學文本閱讀的審美經驗。
通過對人文學文本閱讀過程的分析,可以發現:人文學文本所以可能,在於其閱讀不僅可以增進人們對人的精神性存在以及宇宙之終極存在的認識與理解,也不限於其可以提升人的精神性品格和有助於人的德性培養,還在於它作爲一種人文精神教化的實踐之道,是審美的。這種精神性審美享受在人文學文本的閱讀過程中之所以可以得到確證,是因爲任何人文學文本的閱讀審美與其說是其文體形式方面的審美,毋寧是寄寓於這些文體形式中的“精神質料”的審美。所謂精神質料,是指人文學文本通過其文體形式所表達的精神性存在內容。對於作爲精神教化之學的人文學本說,其“精神質料”是指人的超越的精神性維度以及宇宙之終極存在之質性內容。關於這種“精神質料”,舍勒曾論證過,將其稱爲“價值的實在”。對於人文學的精神教化來說,人文學的文本閱讀是這種具有形上意味的“精神質料”向閱讀者敞開的方式,它伴隨着人在閱讀過程中的審美享受。
人文學文本有多種多樣的形式,但就其審美鑒賞的“精神質料”來說,無非就是“優美”和“壯美”。與作爲人文主義者的席勒在《美育教育書簡》中純粹從經驗審美的角度分析人的審美能力與審美愉悅不同,作爲人文學的文本閱讀之審美鑒賞與審美衝動卻是宗教性的。這種審美衝動、愉悅的感受、審美衝擊,雖然其心理感受強度與純粹的感性審美相似,但其審美對象或指向卻非通常的感性存在者,而是超驗的終極實在,故這種指向超越的終極存在者的審美是一種“宗教性的審美”。它是任何通過閱讀人文文本進入人文世界的閱讀者的一種內心體驗,而這種對超驗之物的審美心理體驗是真實的存在。這種真實的審美體驗達到一定強度的時候,閱讀者往往會出現一種類似於宗教皈依者得道時的心理狀態。從人文學文本的閱讀心理看,當通過文本閱讀出現天人感應,並且到一定程度直到天人合一狀態時,閱讀者心理往往會産生一種獲得宗教皈依的強烈的高峰體驗;與之伴隨而來的,是一種極度的心理能量強度之變化。按照精神分析學家榮格的解釋,這種心理能量的改變有其精神人格心理學的基礎。①榮格在《心理人格的類型》(太原:華岳文藝出版社,1989)中,將人的精神人格區分爲若干,並對不同類型的人格的心理能量的變化流向作了分析。就人文學的文本閱讀來說,這種對超驗之物的心理體驗及其心理能量的變化有三種:(1)史學的。這種心理能量是從外到內的,是由史學閱讀對“一即一切”的宇宙終極本體的心理體驗。這種心理狀態喚起的審美衝動是“崇高”。(2)詩學的。這種心理能量的變化是從內到外的,是由詩學閱讀對“一切即一”的宇宙之終極實在的體驗而來的審美體驗。它伴隨而來的審美愉悅是優美。(3)哲學的。這種閱讀給人帶來的是兩者兼而有之的審美衝動,可以名之爲“幽默”。由於它發生了崇高心理體驗與優美心理體驗及其能量之間的碰撞與融合,因此,它的心理狀更多地表現爲心態的“平和”與“寬容”。②參見胡偉希:“原史”,《南國學術》4(2019);“原詩”,《南國學術》4(2020);“原思”,《南國學術》4(2021)。
綜上所述,在人文學的文本閱讀過程中,人的精神對超驗之物的認知與感受是以審美的方式完成的,並且這種精神審美始終與心理上情感的變化相伴隨。假如說這也是一種宗教性體驗的話,那麽,它屬於一種“情感皈依型”的宗教信念:對人的精神性存在以及宇宙終極實在的精神體驗使人相信通過人文學文本的閱讀與研習可以通達“天人”,並且最後獲得“永生”。這也就是爲什麽作爲精神人文學的中國儒家傳統文化可以沒有“宗教”,卻寧可將“三不朽”奉爲類似於宗教信念那樣的“最高真理”一樣。這其中,立德、立功都是具有人文性精神追求的人的人生目標與方向,之所以可以不朽,乃來源於它是人文學文本的內在精神訴求,也即是作爲“人爲什麽存在”“人可以希望什麽”的終極價值理想。但在現實世界生活中,無論立德或者立功,都還有具體的因緣際會的限制,唯有“立言”這一種“做人”的精神性存在方式是任何作爲“有限的理性存在者”的人都可以“希望”並且達到的。“立言”不是要求每個人都像“聖人”那樣通過著書立說而使其名聲獲得不朽,而是按照人文學文本的指引去生活與行動,即通過自己的精神行爲追隨與人文學文本的合一,將人的精神與人文學文本的精神打成一片,使個體的精神獲得不朽。此外,“立言”還意味着,將人文學的超越精神發揚光大。既要體驗與踐行人文學文本的精神,還要將人文學的知識與精神流傳和普及。也就是說,“立言”是要做一個人文精神意義上的“信仰者”去傳播人文學的教義與文本。終極地看,它不僅是中國人文學研習追求的目標,而且是“立德”與“立功”的起點。因爲,任何立德、立功之事,首先要認識到立德、立言爲何物,然後纔能身體力行,去做立德、立功的事功之事。在這一點上,“立言”即人文學文本的研習對人可以希望獲得“不朽”來說纔是最重要的。以此來看,人文學文本的閱讀與研習不僅僅是對作爲認識人的精神性存在的“知識的學問”,同時也成爲一門關於人的精神性教化的實踐之學。或者說,既傳授人的精神性存在的教化知識,同時也以研讀人文學文本的方式對人作爲精神性存在的生命加以實踐,這就是人文學作爲一門人的精神教化之學的真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