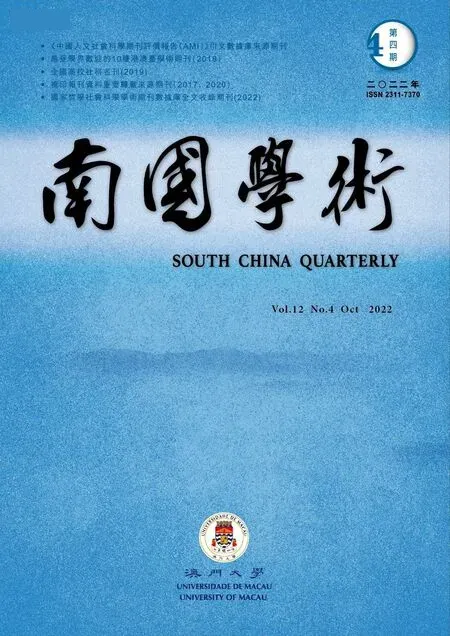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文明基礎
姜佑福
[關鍵詞]現代化 西方現代性 中國式現代化 文明基礎 儒法國家
“中國式現代化”作爲一項重要的實踐成就和一個重要的理論論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邁入新時代的突出貢獻。歷經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發展,它由一個初始方向、一個引領性概念,即“我們搞的現代化,是中國式的現代化。我們建設的社會主義,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①鄧小平:“路子走對了,政策不會變”,《鄧小平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3卷,第29頁。,到如今已成爲有着充實生動內容、有着歷史自覺的概念標識:“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②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第13~14頁。對於學術界來說,如何從學理上講清楚中國式現代化發展道路的理論內涵,講清楚它與西方現代化發展道路的異同,講清楚它與中國古代文明傳統之間的內在聯繫,就成爲各相關學科義不容辭的責任。本文試以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歷史理論爲基本視野,同時與西方現代化發展道路上的重要思想家如黑格爾、海德格爾等人對話,力圖對這一重要論題的研討有所推進。
一 哲學家對西方現代化進程的思考
自“現代”概念産生以來,關於“現代化”“現代性”等問題的討論可謂汗牛充棟。本文關心的問題是,現代化究竟意味着什麽?起源於西方甚至歐洲歷史的現代化,是否具有超越其歷史淵源的普遍性規定?如何找到一種可以普遍運用於西方和非西方國家與地區的“現代化”話語,同時又恰如其分地識別出西方現代化發展道路的特殊之處?
之所以提出上述問題,是緣於人們往往以西方現代化作爲“普遍”“標準”“尺度”去看待、衡量、評述其他地區的現代化進程,而很少去仔細辨別西方現代化發展道路自身中的“普遍”與“特殊”問題。所以,研究者應當有一個超越西方現代化歷史進程的更高、更普遍、更抽象的現代化視野。
關於這個視野,或許可以做這樣一些抽象的預想:首先,這個所謂更高、更普遍的“現代化”視野,也許衹是一種經驗性概括,甚至僅僅是一種較爲“中性化”的話語方式。其次,這個視野也可能對世界不同地區都具有真正意義上的普遍性,從而具有規範和引領的理念價值。再次,如果說這個更高、更普遍的“現代化”概念,是一種相對所有國家普遍適用的更高的“普遍性”的話,那麽,它在內容實質上究竟是更多地從屬於原發之地的西方或歐洲,還是更多地取自後發地區如中國,目前還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爲了能簡明扼要地切入問題,這裏先從黑格爾(G.W.F.Hegel,1770—1831)、海德格爾(M.Heidegger,1889—1976)、馬克思(K.H.Marx,1818—1883)對西方現代化歷史進程的思考出發。
黑格爾是第一個全面系統把握現代西方世界的哲學家,他是把現代西方世界作爲世界歷史的終點或目標來理解的。無論是現實生活的歷史,還是人類精神生活如哲學、宗教和藝術等,“現代”都意味着歷史的終結或完成。因此,在黑格爾的著作中,處處都表現出他所說的歷史與邏輯的統一。所謂“密納發的猫頭鷹要等到黃昏到來,纔會起飛”③[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第14頁。,其真實涵義也正是說,衹有當歷史進程自身真正成熟、臻於完成狀態時,纔能以概念思辨的形式進行系統的和邏輯的把握。
法哲學或國家哲學是黑格爾以“邏輯”方式對現代西方世界本質內容的把握:作爲完成形態的(西方)現代世界——之所以把“西方”放在括號內,是因爲在黑格爾看來,西方或日耳曼世界就是現代世界自身而不是現代世界之一種,就是作爲完成形態的現代國家,亦即以“家庭”“市民社會”爲自身內在環節的倫理世界或政治(公共)生活;而作爲完成形態之現代世界的概念反映,則是一部法哲學的思想體系,是法的理念亦即自由概念的邏輯展開。但無論是作爲現實倫理生活體系的國家,還是作爲思想邏輯體系的法或自由,其中的樞軸不是別的,正是作爲現代西方社會基礎和前提的獨立的個體,或者說原子式的個人,其思想上的特質是主觀性或自我意識着的自由。在黑格爾筆下,一部世界歷史的內在目標或使命就是爲了造就這種意義上的個人,使世界和社會成爲由這樣的人所組成並爲了這樣的人而存在的世界和社會。
當黑格爾以“歷史”的方式敍述(西方)現代世界的生成過程時,他給人們提供了幾個不盡相同的版本。它們的共通之處是,都以現代西方世界或日耳曼世界爲歷史歸宿。首先,在《法哲學原理》的最後部分,黑格爾列舉了四個世界歷史民族或世界歷史王國,它們在原則或理念上分別代表着從古至今承擔世界歷史任務的四種民族精神:(1)以“實體性精神的形態”爲原則的“東方王國”,“個別性”在其中還沒有得到獨立存在的權利;(2)以“實體性精神的知識”爲原則,或者說以“美的倫理性的個體性”爲原則的“希臘王國”,但這種意義上的“個體性”還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個人,因爲“意志的最後決斷並不屬於自爲地存在的那種自我意識的主觀性”,並且“對特殊需要的滿足還沒有被納入自由中,而是專屬奴隸等級”;(3)以“能認識的自爲的存在中自身的深入”或達致“抽象普遍性”的精神形態爲原則的“羅馬王國”,在其中,“倫理生活無限地分裂爲私人的自我意識和抽象的普遍性兩個極端”,“一切單個人降格爲私人,他們一律平等,並且都具有形式的權利,衹有把自己推進到驚人地步的那種抽象任性纔把他們聯繫起來”;(4)以“從無限對立那裏返回的精神”爲原則的“日耳曼王國”,在其中,精神將“回復到最初實體性”,“在自我意識和主觀性內部”實現“客觀真理與自由”的調和,“這種調和把國家展示爲理性的形象和現實”,既揚棄了塵世和彼岸的對立,也揚棄了個體與整體的對立。①[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第356~360頁。
此外,在《歷史哲學》的“緒論”中,黑格爾將世界歷史的原則進展概括爲三個階段:(1)“‘精神’汩沒於‘自然’之中”(東方世界);(2)精神“進展到它的自由意識”(西方古代世界),但仍然受制於作爲對立面的“自然”;(3)精神由“特殊的自由的形式提高到了純粹的普遍性,提高到了精神性本質的自我意識和自我感覺”(從中古到現代)。②[德]黑格爾:《歷史哲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第59頁。在《哲學史講演錄》“導言”中,黑格爾談到“自由”在東方、希臘、日耳曼世界的不同表現形態:“在東方衹是一個人自由(專制君主),在希臘衹有少數人自由,在日耳曼人的生活裏,我們可以說,所有的人皆自由,這就是人作爲人是自由的。”③[德]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第1卷,第99頁。在《精神現象學》中,黑格爾至少提供了兩個“世界歷史”原則進展的版本。其一,是第四章“自我意識”中對“主奴辯證法”的分析所蘊涵着的意志關係的三種基本類型:(1)人與人之間的生死鬥爭形成意志之間的絕對屈從關係或主奴關係(當然,鬥爭的結果也可能是不屈從,即一方消滅另一方,關係消失);(2)處於屈從地位的奴隸通過勞動(對自然的陶冶)取得相對於主人的優勢地位從而讓初始意義上的主奴關係趨於瓦解,“主人”不再是主人,“奴隸”也不再是奴隸,但相互之間仍然處於“鬥爭”狀態或“私人”狀態;(3)每一方都不再尋求對方的“屈從”,而是在完全承認對方的同時獲得自身的絕對承認,從而每一個意志都進入真正的自由狀態,或真正的“主人”狀態,或真正的“人”的狀態。其二,是第六章“精神”中所分析的“客觀精神”歷史發展的一般道路——“真實的精神”即“倫理”世界(從希臘到羅馬)、“自身異化了的精神”即“教化”世界(從基督教到啓蒙)和“對其自身具有確定性的精神”或“道德”世界(日耳曼或現代世界)。④[德]黑格爾:《精神現象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上卷,第122~132頁;下卷,第六章“精神”。
黑格爾關於西方現代世界所作出的樂觀而正面的哲學闡釋,在實踐和理論兩個方面都遭遇到了致命的挑戰。從實踐方面來說,法國大革命之後的西方世界,並沒有按照黑格爾預想的那樣建立起真正理性的現代國家,而是像施密特(C.Schmitt,1888—1985)在《憲法的守護者》中所分析的那樣,由“絕對國家”(王權專制國家),經過“中立性國家”(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分離),最後演變爲“總體性國家”(國家機器完全爲市民社會的利益集團所俘獲)。今天美國的文化相對主義和否決型政治,就是這種總體性國家的典型代表。20世紀兩次慘絕人寰的世界大戰,更是讓很多人對黑格爾的國家主義和理性主義的思想立場深惡痛絕。霍克海默(M.Horkheimer,1895—1973)、阿道爾諾(T.W.Aaorno,1903—1969)在《啓蒙辯證法》中把“啓蒙”(理性主義)之所以會走向自身反面的道理揭示爲:“主體的覺醒”是以將“權力”確認爲一切關係的原則爲代價的,“啓蒙對待萬物,就像獨裁者對待人”,“啓蒙對一切個體進行教育,從而作用於人的存在和意識”,但當人類實現了在全球範圍內“用行動來支配自然”的培根式烏托邦時,同步被加強的是人對人的“統治”本身,亦即“隨着支配自然的力量一步步地增長,制度支配人的權力也在同步增長”,而“啓蒙在爲現實社會服務的過程中,逐步轉變成爲對大衆的徹頭徹尾的欺騙”。①[德]馬克斯·霍克海默、西奧多·阿道爾諾:《啓蒙辯證法:哲學片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6~7、36、38~40頁。
從理論的方面來說,根本而尖銳的挑戰來自海德格爾。雖然他並未對黑格爾哲學展開過多直接的批評,甚至在確認其思想深度上還經常予以極高的評價,但他對整個西方形而上學傳統做了批判性的重新估價,並將西方現代性的歷史命運歸結於西方形而上學傳統的歷史性展開。
海德格爾在其成名作《存在與時間》中,通過重提柏拉圖(Πλατών,前427—前347)的“存在(是)”的意義問題,開啓了他對西方形而上學傳統的整體性批判。本體論(存在論,ontology)是西方形而上學傳統中最核心和最基礎的部分,自亞里士多德(Αριστοτέλης,前384~前322)至黑格爾都始終在回答所謂“存在問題”。但在海德格爾看來,一部西方形而上學的歷史同時是“遺忘存在”的歷史。西方形而上學傳統尤其是當代西方世界的哲學與科學,並沒有專注於“存在者”與“存在本身”之間的“存在論差異”,而僅僅專注於“存在者”。海德格爾一方面肯定,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曾經爲“存在問題”殫思竭力,並“以思的至高努力從現象那裏”爭得或贏得了某些東西;但另一方面又說,這些東西在現代社會“早已被弄得瑣屑不足道了”。其涵義不是說古典意義上的存在論本身失效了,正好相反,它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其涵義是哲學在科學中的“終結”或“完成”。
海德格爾在晚年的一篇演講《哲學的終結和思的任務》中對此有十分精彩的闡述:(1)“終結作爲完成乃是聚集到最極端的可能性中去”,“早在希臘哲學時代,哲學的一個決定性特徵就已經顯露出來了:這就是科學在由哲學開啓出來的視界內的發展。科學之發展同時即科學從哲學那裏分離出來和科學的獨立性的建立。這一進程屬於哲學之完成。這一進程的展開如今在一切存在者領域中正處於鼎盛。它看似哲學的純粹解體,其實恰恰是哲學之完成”。(2)“哲學之發展爲獨立的諸科學——而諸科學之間卻又愈來愈顯著地相互溝通起來——乃是哲學的合法的完成。哲學在現時代正在走向終結。它已經在社會地行動着的人類的科學方式中找到了它的位置。而這種科學方式的基本特徵是它的控制論的亦即技術的特性。追問現代技術的需要大概正在漸漸地熄滅,與之同步的是,技術更加明確地鑄造和操縱着世界整體的現象和人在其中的地位”。(3)“哲學在其歷史進程中的某些地方(甚至在那裏也衹是不充分地)表述出來的東西,也即關於存在者之不同區域(自然、歷史、法、藝術等)的存在論,現在被諸科學當作自己的任務接管過去了。諸科學的興趣指向關於分門別類的對象領域的必要的結構概念的理論。‘理論’在此意味着:對那些衹被允許有一種控制論功能而被剝奪了任何存在論意義的範疇的假設。表象—計算性思維的操作特性和模式特性獲得了統治地位”。(4)“哲學之終結顯示爲一個科學技術世界以及相應於這個世界的社會秩序的可控制的設置的勝利。哲學之終結就意味着植根於西方—歐洲思維的世界文明之開端。”②[德]海德格爾:《面向思的事情》(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第70~72頁。
由此可見,海德格爾對西方形而上學傳統的批判是與對現代西方文明技術性本質(表象—計算性思維的操作特性和模式特性)的批判內在關聯在一起的。他對所謂西方形而上學傳統的批判,實際上意味着對西方現代性文明弊病的根本性反思。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之際,海德格爾就寫下了著名的《關於人道主義的書信》(1946),表達了他對西方形而上學傳統以及現代西方文明所支配的世界歷史命運的憂慮,亦即由“技術文明”所造就的整個人類社會的“歐洲化”:(1)“在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中,勞動的現代形而上學的本質已經得到先行思考,被思爲無條件的製造(Herstellung)的自行設置起來的過程,這就是被經驗爲主體性的人對現實事物的對象化的過程。唯物主義的本質隱蔽於技術的本質中”,而“技術在其本質中乃是淪於被遺忘狀態的存在之真理的一種存在歷史性的天命”。(2)“迄今爲止的歐洲愈來愈清晰地被驅逼入其中的那個危險也許就在於:首先,一度標明歐洲之偉大的歐洲思想,在正在到來的世界天命之本質進程中落後了,但世界天命在其本質淵源之基本特徵上卻依然是由歐洲來規定的。任何一種形而上學,無論它是唯心主義的,還是唯物主義的,或者是基督教的,按其本質來看,而且絕非僅僅從其力圖展開自己的種種努力中來看,都不可能趕得上這個天命”。①[德]海德格爾:“關於人道主義的書信”,《路標》(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第401~402頁。
晚期海德格爾一度試圖從“無力”追趕技術文明的歷史天命的“哀嘆”中擺脫出來,更加積極地提出了在“哲學終結”時代狀況下“思的任務”:“我們所思的是這樣一種可能性:眼下剛剛發端的世界文明終有一天會克服那種作爲人類之世界栖留的唯一尺度的技術—科學—工業之特性。”②[德]海德格爾:《面向思的事情》,第74頁。
馬克思雖然在時間上是介於黑格爾與海德格爾之間的思想家,但從理論邏輯上看,他恰恰像是兩者的綜合。因爲,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不僅針對黑格爾的世界歷史哲學,而且也潜在地回應了海德格爾對現代西方文明所開啓的所謂世界歷史天命的思考。
從1843年前後接觸政治經濟學著作開始,經過多年的批判性研究,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提出了著名的三大社會形態學說:“人的依賴關係(起初完全是自然發生的),是最初的社會形式,在這種形式下,人的生産能力衹是在狹小的範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着。以物的依賴性爲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這種形式下,纔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係、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的生産能力成爲從屬於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第二個階段爲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因此,家長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狀態隨着商業、奢侈、貨幣、交換價值的發展而沒落下去,現代社會則隨着這些東西同步發展起來。”③[德]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30卷,第107~108頁。
其中,關於現代社會最概要的表達是:“以物的依賴性爲基礎的人的獨立性。”以之爲基礎,可以融貫地理解和解釋黑格爾、海德格爾對現代西方世界的哲學言說:(1)黑格爾哲學闡釋的重點是“人的獨立性”,但他忽略了這種獨立性的個人共同分享的自然基礎,自然在黑格爾哲學中實際上衹不過是科學技術化了的自然,或者說是作爲思想物和作爲知識對象的自然。(2)海德格爾闡釋的重點是“物的依賴性”,在他看來,發端於歐洲的西方現代性社會是一個“世界圖像的時代”,“科學是現代的根本現象之一”,而技術是科學的本質,技術文明所造就的人類社會在精神上的“無家可歸”狀態,可以被提綱挈領地概括爲,“人作爲animal rationle[理性的動物],現在也作爲勞動的生物,必定迷失於使大地荒漠化的荒漠中”。④[德]海德格爾:《林中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第77頁;《演講與論文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第69頁。(3)由於黑格爾眼中的自然僅僅是作爲知識對象的“思想物”,因此不可能從真正感性或有限性視角來理解人類社會的生活基礎,整個現代世界的人被他看作是自然的主宰者,是一群聯合起來“奴役”自然的自由個體,也就是海德格爾眼中的“理性的動物”和“勞動的生物”,從而遲早要遭遇人與自然之間的歷史辯證法,自然要和奴隸一樣翻身求解放(當然,這種“求解放”歸根到底還是要通過人對自然世界危機的覺察和對感性生活價值的重新領會來展開)。(4)海德格爾衹專注現代技術文明的形而上學前提,而不瞭解人對自然的控制論態度以及現代社會的技術進步強制真正的動力來自何方;在馬克思看來,由於現代社會“每個個人以物的形式佔有社會權力”①[德]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07頁。,而“每一個新的産品都是産生相互欺騙和相互掠奪的新的潜在力量”②[德]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第3卷,第339頁。,因此,現代西方技術文明進步強制的不竭動力實際上蘊藏在“以物的依賴性爲基礎的人的獨立性”的社會權力生産機制中。“以物的依賴性爲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意味着,每個人在“合理合法”的意義上應當是一個相互提供勞動産品或服務的勞動者,意味着新産品和新服務的創造是社會權力最正當的來源,從而使技術創新和産品(服務)變革成爲現代性社會的基本要求或基礎性建制。
馬克思在早期文本《論猶太人問題》中,將現代社會亦即“以物的依賴性爲基礎的人的獨立性”的第二種社會形態的誕生稱作“政治解放”。正是通過“政治解放”,實現了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分離,實現了“國家的唯心主義的完成”和“市民社會的唯物主義完成”,作爲市民社會成員的“利己的人”成爲現代“政治國家的基礎、前提”。③[德]馬克思:“論猶太人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87頁。在同一時期未曾公開發表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馬克思直接斷言,不是“國家”決定“市民社會”,而是“市民社會”決定“國家”,從而揭穿了黑格爾試圖將“市民社會”納入“理性國家”體系的“虛幻”統一。
綜上可以看到,三位哲學家對(西方)現代世界的界定,都包含一個共通的因素,即這是一個勞動者做主宰的時代,而不論他們對這種勞動者本身及其結成的社會關係做何種價值評判。至於對西方現代社會特殊性的揭示,可以說三位哲學家都有重大貢獻:在黑格爾那裏,是原子式個人、主觀性自由或西方現代社會的意見性;在海德格爾那裏,是根植於西方形而上學傳統的對待自然的控制論的或技術化的方式,其內在本質是一種表象化的世界觀和數學化或形式化的自然科學;在馬克思這裏,則是在“以物的依賴性爲基礎的人的獨立性”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起來的資本主義,也就是在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的資産者(以私人佔有爲基礎的各自孤立的勞動者)理想和初始社會秩序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勞動者之間的相互欺詐和相互掠奪。
二 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跋涉歷程
所謂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無疑指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近代以來,由於中國在生産力實際發展階段上落後於歐美國家,也由於自中國共産黨人登上歷史舞臺之後,現代化道路是在馬克思主義這一具有超越西方現代性特質的思想體系指引下展開的,因此,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具有鮮明的概念引領和戰略目標導向的特徵。由此,需要圍繞“現代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兩個核心詞匯來觀察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跋涉歷程。
(一)新中國現代化目標的探索與追求
中國共産黨人建設“現代化”國家目標的提出,尚在新中國成立之前。1949年3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届二中全會上提出:“在革命勝利以後,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生産,對付國外的帝國主義,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爲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④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4卷,第1437頁。這一工業強國的方略,可以說是中國共産黨人關於現代化的最初設想。此後,隨着實踐的發展和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認識深化,現代化建設目標經歷了一系列的調整,其中不乏曲折和教訓,直到改革開放以後纔逐步清晰、穩定和成熟起來。
新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目標的初始形式,是過渡時期的總路綫。1953年,中國共産黨根據國際形勢和國內政治、經濟條件的變化,正式提出過渡時期的總路綫:“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綫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基本上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①周恩來:“過渡時期的總路綫”,《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第4册,第349頁。簡稱爲“一化三改”“一體兩翼”,核心是國家的工業化和社會主義化。
1956年,隨着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工業建設進展順利,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在中國建立起來。擺在中國共産黨人面前的是,如何探索和開闢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國內外局勢的變化和蘇共二十大引起的對蘇聯經驗的反思等,成爲中國共産黨探索自己發展道路的一個契機。毛澤東的《論十大關係》和中共八大《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是這一探索的初步理論成果。
在這兩個綱領性文獻中,對國內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有了新的認識:國內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的實質,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與落後的社會生産力之間的矛盾。黨和人民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矛盾,把中國儘快地從落後的農業國變爲先進的工業國。②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産黨歷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第2卷,上册,第396頁。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制定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綫,仍然沿用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中國共産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的提法,正式提出了要將中國建設成爲“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改變了過去單一提倡“工業化”的表達。這個提法,後來經過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增補和修改,作爲實現國家發展的重要戰略目標,出現於1964年第三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爲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③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産黨歷史》,第2卷,下册,第673頁。這就是後來長期沿用的“四個現代化”。
“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於1978年召開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會。會議決定,把全黨工作的着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號召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同心同德,爲把中國建設成爲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而進行新的長征。④“中國共産黨第十一届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人民日報》1978-12-24。
1982年召開的中共十二大,明確提出了新的歷史時期的總任務:“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爲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未來二十年內的具體經濟建設奮鬥目標,亦即從1981年到20世紀末,在不斷提高經濟效益的前提下,力爭使全國工農業的年總産值翻兩番。而爲了實現二十年的奮鬥目標,在戰略部署上則分兩步走:“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礎,積蓄力量,創造條件,後十年要進入一個新的經濟振興時期。”⑤胡耀邦:“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第13~14、16頁。
從十一届三中全會開始,經過中共十二大,到1987年中共十三大召開,以鄧小平爲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宏觀認識又取得了新的重大突破,最重要的是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這個論斷,包括兩層含義。第一,我國社會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我們必須堅持而不能離開社會主義。第二,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還處在初級階段。我們必須從這個實際出發,而不能超越這個階段。”⑥趙紫陽:“沿着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9頁。由此成爲制定和執行正確路綫和政策的根本依據。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基礎上,中共中央對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宏觀目標做出了更爲細緻、更爲精確的表述。首先,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路綫:“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爲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爲把我國建設成爲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鬥。”其次,對十一届三中全會以後中國經濟建設的戰略部署作出“分三步走”的新概括:“第一步,實現國民生産總值比一九八〇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這個任務已經基本實現。第二步,到本世紀末,使國民生産總值再增長一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個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産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①趙紫陽:“沿着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15~16頁。
1992年召開的中共十四大,明確提出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此後,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高速增長的階段。1997年召開的中共十五大,提出了21世紀中國發展的宏觀政治目標:“第一個十年實現國民生産總值比二〇〇〇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寬裕,形成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再經過十年的努力,到建黨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②江澤民:“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 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江澤民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第2卷,第4頁。五年後召開的中共十六大,比照十五大提出的發展目標,又提出了在21世紀頭二十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任務:“使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③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江澤民文選》,第3卷,第542~543頁。
2007年,中共十七大召開,大會根據新世紀、新階段中國發展呈現出的一系列新特徵,提出了“科學發展觀”的重大戰略思想:“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爲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④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爲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努力奮鬥》(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第15、11頁。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引下,中國發展的宏觀政治目標增添了新內容,其中最爲突出的是,明確提出了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積極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建設生態文明的歷史任務。
2012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2017年召開的中共十九大,提出了“新三步走”的現代化發展戰略: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21世紀中葉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也意味着,中國式現代化發展道路逐漸進入成熟、完善、定型的階段。
2022年10月召開的中共二十大,更加鮮明地指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堅持中國共産黨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高質量發展,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實踐
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概念來說,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歷史起點應該是改革開放,但真正對這條道路産生自覺、自信則要晚得多。2007年,在中共十七大即將召開之際,國內外各種社會政治思潮風起雲涌,紛紛對中國社會現實發展道路的內涵予以解釋和評價。對此,中共十七大報告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取得一切成績和進步的根本原因,歸結起來就是:開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最根本的就是要堅持這條道路和這個理論體系。”同時還指出,“在當代中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真正堅持社會主義”,“在當代中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真正堅持馬克思主義”。⑤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爲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努力奮鬥》(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第15、11頁。可以說,這是今天高度強調的“四個自信”的最初自覺。2011年7月1日,胡錦濤《在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九十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在原來的“道路”“理論體系”的基礎上,增加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三者並列的提法寫入了2012年召開的中共十八大報告。2016年7月1日,習近平發表《在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九十五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仍然沿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和“制度”三者並列的提法,又明確提出,“堅持不忘初心、繼續前進,就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堅持黨的基本路綫不動搖,不斷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推向前進”,並且認爲,“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①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九十五週年大會上的講話”,《論中國共産黨歷史》(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第118、125、126頁。從此以後,“四個自信”成爲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鬥的重要思想基礎。從這個角度說,中國式現代化發展道路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事情的另一個方面是,中共重要文獻也一再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改革開放之前的歷史淵源和前提條件。2011年7月1日,胡錦濤《在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九十週年大會上的講話》就着重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和制度,是黨和人民“經過九十年的奮鬥、創造、積纍”的成就。②胡錦濤:“在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九十週年大會上的講話”,《胡錦濤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第3卷,第525~526頁。習近平也一再強調,要避免將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後兩個歷史階段對立起來,並且在談到“文化自信”時,多次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中華五千年歷史之間的內在聯繫。這意味着,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起點問題要採取一種真正歷史的和辯證的態度來看待,既不能違背原則,也不能割斷歷史:一方面,要肯定這條道路的現實發生或實際開闢是以改革開放爲起點;另一方面,同樣要肯定這條道路淵源有自,並非完全橫空出世或“飛來峰”。也就是說,“歷史自信”呼之欲出。
除了以“現代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兩個概念爲綫索外,實際上還可以用一種更簡明的方式概括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確立和展開的過程,這便是中共十九大報告提出的“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三個發展階段的理論。
三 文明基礎在中國式現代化道路進程中的作用
這裏所說的“文明基礎”,指的是在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發生發展過程中,實際發揮作用的社會歷史基礎和民族文化傳統。當然,困難之處在於:一方面,這個實際發揮作用的文明基礎本身是在實踐中不斷變革的,尤其是在與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作用、西方現代社會的文化壓力的碰撞中,在或促進或阻滯中國式現代化發展道路的歷史任務的具體表現中不斷調適的;另一方面,由於中國古代文化傳統自身的博大精深以及身處其間“日用常行而不知”的思想語境,使得人們有效切入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文明基礎問題存在較大的理論困難。爲了讓討論變得相對簡便易行,這裏僅以轉述和評論趙鼎新教授的新著《儒法國家:中國歷史新論》中表達的核心觀點爲綫索。
趙教授自陳,書中主要是“力圖將‘競爭/衝突’的邏輯加入邁克爾·曼(Michael Mann)版的韋伯式理論中,以發展出一套新的歷史變遷理論”,所要達到的主要目的有二:一是“解釋中國爲何且如何由秦統一並發展出官僚制帝國”;二是“探討早在西漢時期就被制度化的政治/文化結構爲何有如此強的韌性,以至於長盛不衰並綿延至19世紀”。③趙鼎新:《儒法國家:中國歷史新論》(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22),第4、6頁。
趙教授在綜合衆多哲學家、歷史學家、社會學家的論述基礎上,提出秦一統天下後,尤其是在西漢時期,中國歷史逐漸形成了六個方面的主要特徵:(1)“世界上衹有中國的帝國體系,從公元前221年秦統一中國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共延續了兩千餘載。”(2)“在世界幾大文明中,中國的國家傳統可以說發展得最爲強大。”(3)“中國早在西漢時期就實行了文官統治(civilian rule)”,雖然在魏晉南北朝和晚唐時“嚴重受挫”,但北宋時“又得以復興”;而“在前現代歐洲,軍事將領即使在和平時期也掌握着非同尋常的政治力量”,“文官統治基本上是進入現代纔發展起來的”。(4)“世界上絕大多數帝國都通過軍事征服來擴張領土,而中國在很大程度上卻是因爲被遊牧和半遊牧族群所征服而被動性地成就了領土的拓展,並且,那些馬上得天下的征服者們之後又都採納了儒法國家這一統治模式。”(5)“帝制中國算得上唯一一個超驗性宗教未能在政治領域施加重大影響的世界性文明。同時,強大的帝國政府對多種宗教信仰持以寬容甚至是鼓勵的態度(不僅對具有世界性影響的宗教如此,對民間宗教亦如是)。”(6)“與近代歐洲的城市相比,晚期中華帝國的城市,即使相當大一部分已經高度商業化,卻仍然由國家任命的官員管理。因此,商人在整個帝制中國都無法在政治領域擔當重要角色。”①趙鼎新:《儒法國家:中國歷史新論》,第8~9、11~17頁。
趙教授以邁克爾·曼社會權力的四種“理想型”爲藍本,發展出了四種權力資源的競爭性學說,對前述“中國歷史型態特徵”進行支撐性和辯護性的闡釋。主要觀點包括:(1)“雖然軍事和經濟競爭能導致纍積性發展,但軍事競爭往往會促進國家的權力的增大,導致社會權力集中在少數人手中,而經濟競爭則會促進社會權力的彌散化”,“軍事競爭和經濟競爭均會推動工具理性思維及其相應行爲在社會中的興起”;所不同的是,“軍事競爭刺激了公域導向或以公共利益爲導向的工具理性的興起”,而“經濟競爭則促進了私域導向的工具理性的興起”。(2)“在政治、軍事、經濟和意識形態四個權力面向所能組成各種兩兩組合中,政治與意識形態權力的組合最爲關鍵”,“不同的意識形態及其與國家政治的關聯方式不僅會産生各種各樣使政治統治得以合法化/制度化的價值觀,同時也爲個體的生存與社會行動者的競爭創造千差萬別的社會情境”。(3)“早期中國的迅速發展最終促進了國家權力的強化與集中,也爲秦國一統天下奠定了基礎。這樣的發展型態是由軍事競爭主導了其他形式的競爭(即發生在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諸領域的競爭)所造就的”,雖然早期中國與第二個千年期間的歐洲均深陷“列國競爭”之中,但“歐洲朝着代議制政府和工業資本主義的方向發展”,而中國則“朝着官僚制帝國的方向發展”。(4)“法家的意識形態及其政治制度與軍事動員之間的協同關係極大地增強了秦國的國家力量及其軍事優勢,這就鼓舞着秦的統治者遵行嚴苛的法家統治術,而不依靠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合作以及社會的規範性共識來進行統治。”(5)西漢初期的統治者從秦王朝不穩定的結構狀態及其導致的速朽中汲取經驗教訓,“爲中國造就了一種四種權力之間具有高度穩定關係的結晶——‘儒法國家”,即一種將政治力量和意識形態力量融爲一體、軍事力量受到嚴格控制、經濟力量被邊緣化的統治體系”。(6)“在19世紀來臨之前,‘儒法國家’的政治/意識形態架構仍像‘壓頂石’(capstone)一樣發揮着作用,並沒有受到嚴重削弱;正因爲如此,在中國迫於西方與日本的帝國主義壓力而發生改變前,工業資本主義並沒有在中國得到真正的發展與突破。”②趙鼎新:《儒法國家:中國歷史新論》,第8~9、11~17頁。
關於現代中國,趙教授着墨不多,但做了一個重要的論斷:“帝制中國與現代中國之間唯一最大的斷裂在於:中國儒家傳統在日本帝國主義和西方帝國主義衝擊下幾乎不可逆轉地衰落了。”與此同時,基於他的社會變遷理論,表達了對“更願意生活在什麽樣的社會中”的幾點意見:(1)鑒於“經濟競爭和軍事競爭會促生大量的具有方向性的正反饋機制”,而這些正反饋機制“既是人類社會的生産力、財富和所有可被稱道的成就的動力,也是人類所面臨的幾乎所有社會問題的源泉”,因此,“更願意生活在一個軍事力量被壓縮到維持治安性的警察功能,市場力量被限制在環境可持續和社會平等的框架下運行的社會中”。(2)鑒於“政治權力是人類社會獲得一些最基本的公共物的保證,它總是集中在小部分人的手中,並帶有強制性。在現代交通、通信和組織技術的支持下,作爲政治權力的集中體現,國家對社會管轄得越來越多,其主宰性地位愈發令人生畏”,因此,“更願意生活在一個彌散性的社會力量能有效平衡集約性的國家力量、國家政治受到被廣爲認可的法律和政治程序所制約的社會”。(3)鑒於“純粹的意識形態權力不具強制性,純粹的意識形態競爭也不會給社會帶來具有方向的積纍性發展”,“對意識形態的偏好和理解離不開個人的特殊體驗”,“如果沒有帶有強制性力量的社會行動者(如國家、中世紀教會)的大力推行,一個社會的意識形態應該是非常多元的”,因此,“更願意生活在一個能容忍各種思想的社會,一個在其中政治家能充分理解思想多樣性的重要意義,同時不會被任何意識形態所禁錮的社會”,“思想的多樣性是人類社會一種極其重要的公共物,但它卻需要一個帶有實用主義態度的國家來予以維持”。最後,由於趙鼎新教授認爲“人類是完全不可能改變其競爭性的本性的”,因此,他對自己上述“理想社會”的實現並不抱有很大的信心。①趙鼎新:《儒法國家:中國歷史新論》,第424、434頁。
儘管趙教授的研究極具啓發性,但如果循着他的論述思路,將“儒法國家”看作是中國式現代化最重要的文明基礎的話,卻很難認同他最後的斷言。因爲,在中國式現代化發展道路中,“儒法國家”的架構與其說不可逆轉地衰落了,不如說是無與倫比地增強了。當然,他並沒有明言現代中國的結構型態還是不是“儒法國家”,而僅僅是說“儒家”這種意識形態不可逆轉地衰落了。
之所以說“儒法國家”的架構無與倫比地增強了,主要理由有四:(1)“儒法國家”的實質是政治權力與特定意識形態的結合,對軍事權力和經濟權力的馴服,而且由於政治權力的物質支柱實際上也就是軍事權力和經濟權力,因此“儒法國家”的實質可以進一步理解爲特定意識形態對包括軍事權力、經濟權力在內的政治權力的馴服。這一點,在中國古代社會表現爲“儒法國家”;在中國式現代化發展道路中,則表現爲以馬克思主義爲指導的中國共産黨領導國家。(2)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所概括的中國共産黨人剋敵制勝的三大法寶——“黨的建設”“武裝鬥爭”“統一戰綫”表明,雖然在思想理論和鬥爭手段、團結對象等方面具有現代中國的全新內容,但在意識形態、政治、軍事、經濟四種基本社會權力的結構類型方面,中國共產黨所踐行的政治道路與傳統的“儒法國家”如出一轍,“思想建黨”原則表達的是意識形態對政治權力的馴服,“政治建軍”和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表達的是政治權力對軍事、經濟權力的馴服。(3)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雖然以儒家爲代表的中華傳統文化在話語和器物層面遭到了激烈的批評與改造,但中國共産黨人堅守自己的理想信念,牢牢掌握軍事權力和經濟權力的基本格局沒有改變,社會主義建設遭遇重大挫折的根本原因並不在於反傳統,而在於操之過急,試圖完成超越歷史發展階段的社會改造任務。(4)改革開放以來,逐漸開啓的全方位對外開放和史無前例的大規模向西方學習先進的科學文化技術和生産管理經驗,也絲毫沒有改變中國共産黨人自戰爭年代以來所奠基的意識形態、政治權力、軍事權力、經濟權力之間的關係框架;相反,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在以堅定理想信念和全面從嚴治黨爲核心的自我革命的過程中,在以加強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和黨對經濟社會生活的全面領導的過程中,隨着全面依法治國戰略的推進,隨着各方面制度建設的完善和定型,可以說,伴隨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的加快,升級版的“儒法國家”型態正在走向成熟。
當然,從狹義上看,傳統意義上的“儒家”意識形態的確是不可逆轉地衰落了,但這種衰落並不是“儒法國家”權力結構中“儒”的缺位,而衹是被新的更加強大的意識形態所取代,因此,在比擬的意義上說,中國式現代化發展道路中已經有自己的“新儒”,即以經典馬克思主義爲思想統領、兼容現代西方和中國古代優秀文化傳統的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
如果將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中的四種權力資源的結構關係比擬爲新版“儒法國家”的話,是否意味着對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偏離?還是說,這恰恰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必然結果?爲了回答這個疑問,有必要再次回到黑格爾、海德格爾、馬克思等人關於現代化和西方現代性的批判性思考上來。
現代西方國家毫無例外走的都是黑格爾所批判的“契約國家”或“外部國家”的政治發展道路,因此,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指認的“不是國家決定市民社會,而是市民社會決定國家”的道路,迄今爲止對現代西方國家的社會現實依然有效。但是,中國的社會現實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這一點上,吳曉明教授的觀點可謂振聾發聵:“不存在原子個人乃是理解中國社會的鑰匙,而中國社會轉型的可能性正在於它成爲市民社會的不可能性。”②吳曉明:“從社會現實的觀點把握中國社會的性質與變遷”,《哲學研究》10(2017):12。由於依靠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引領和背靠中國傳統文明基礎的強大支撐,新時期以來的市場化改革並沒有像許多學者所期盼或所哀嘆的那樣,使中國無批判地擁抱西方現代性;恰恰相反,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開闢倒是很有可能讓中華民族在經歷偉大復興的同時承擔起更加積極的世界歷史使命,成爲新時代的世界歷史民族。
海德格爾憑藉其對西方形而上學傳統解構以及對現代西方技術文明“虛無主義”病症的揭示,曾被譽爲“貧乏時代唯一的思想家”,但在今日的西方也應者寥寥,甚至海德格爾本人在晚年(1966年9月23日)接受德國《明鏡》雜誌記者的採訪中,一方面再次提綱挈領地談到了他關於“技術世界”降臨和“哲學終結”的基本判斷,另一方面充分表達了對人類社會未來發展前景不確定性的深度擔憂以及作爲思想家的矛盾心態,既感使命在肩同時又深感思想“無力”。在他看來:(1)“技術在本質上是人靠自身力量控制不了的一種東西”,“我們現在衹還有純粹的技術關係,這已經不再是人今天生活於其上的地球了”,“我認爲今天的一個關鍵問題是,如何能夠爲技術時代安排出一個——而且是什麽樣的一個——政治制度來。我對這個問題提不出答案,我不認爲答案就是民主制度”。(2)“按照我們人類經驗和歷史,一切本質的和偉大的東西都衹有從人有個家並且在一個傳統中生了根中産生出來”,“是不是有朝一日一種‘思想’的一些古老傳統,將在俄國和中國醒來,幫助人能夠對技術世界有一種自由的關係呢?我們之中有誰竟可對此作出斷言嗎?”(3)“思想的最大的災難是,今天,就我所能見到的而論,還沒有一個足夠‘偉大’的思想家說話,把思想直接而又以鑄成的形態帶到它的事情面前從而帶到它的道路上去。就我們今天活着的人來說,有待思想的東西的偉大處是太偉大了。也許我們能夠修修一個過程的一段段狹窄而又到不了多遠的小路也就疲憊不堪了”。①孫周興 編:《海德格爾選集(下)》(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6),第1303~1305、1312頁。按照海德格爾本人的意願,這篇談話直到1976年他去世以後纔公開發表。
海德格爾以其一生殫精竭慮的思想努力,最終不過表明自己也是現代西方技術文明“無出路”狀態的一個例證。但在馬克思的哲學中,已經包含着破解現代西方技術文明的“虛無主義”病症的思想鑰匙:現代西方技術文明的價值虛無主義和看似不可遏制的進步強制,其奧秘並不在技術自身當中,而在現代西方市民社會中“每個個人以物的形式佔有社會權力”的社會權力生産與運行機制,剋服現代西方技術文明的價值虛無主義和看似不可遏制的進步強制的本質力量,衹能來自社會權力生産與運行機制的革命性重塑。而在馬克思曾經矚望通過西方諸文明國家採取共同行動發起社會主義革命被無限延期的大背景下,來自東方大國——一個自身擁有全然不同於西方市民社會倫理基礎,同時擁有強大的意識形態號召力,能夠以有德性的政治權力統率軍事和經濟權力的全面現代化的中國,則必然成爲承擔新的世界歷史任務的新的世界歷史民族。
因此,正視自身文明基礎,尤其是切實把握馬克思主義世界歷史理論和中國古代政治文明傳統之間的暗合之處,是深入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發展道路的當務之急。這不僅可以化解近代以來中國思想領域一直糾纏不休的“古今中西之爭”問題,還可以更具開放性、創新性地面對中華民族幾千年積纍起來的優秀文明成果,並且對復興後的中華民族如何承擔更大的歷史使命,爲人類社會做出性命攸關的新的重大貢獻,形成堅定的文化自信和高度的歷史自覺。